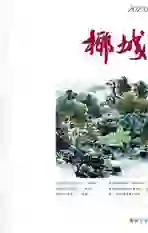白耳鹧鸪(短篇小说)
2024-06-05陈位洲
陈位洲
1
大志确信自己是被鹧鸪声吵醒的。醒来之前,鹧鸪声带着他穿越回到曾经的少年时光。那时他是一个不怎么听话的孩子,常常要母亲逼着才肯爬到床上躺下,可就是躺在床上往往也不肯睡着。屋外艳阳高照,南风吹拂,对面山坡上传来鹧鸪啼鸣,一声递一声,婉转、高亢,直冲云天。他好像还听见邻家姐姐咯咯的笑声,恍惚间又在村口一眼望见自家屋顶上升起袅袅炊烟,心里感到特别踏实,特别甜美。醒来之后,鹧鸪的啼鸣还在继续,一唱三叹,荡气回肠。他很激动,立马翻身起床,一个箭步冲到门外。
太阳已经偏西,但正是一天中阳光最炙热的时候。大志冷不丁正对着阳光,顿时两眼直冒金星,眼里有几个太阳不停地旋转,他紧闭双眼,好让自己稳下神来。可是,当他定下神来,能够辨别东西南北的时候,鹧鸪声消失了。望向村前大观岭的方向,刚才啼鸣声就是从那边传过来的,他希望过一会还会再来一波啼鸣,可左等右等,始终没等到结果。
“妈——”
他想与母亲分享一下,喊了一声,不见回应,这才想起,母亲去村里找人闲聊了。每天吃过午饭后,母亲总是喜欢去村里找人聊天,说是人老了觉少,担心睡了午觉,晚上半夜三更醒来睡不着。每次从外面闲聊回来,母亲总是笑吟吟的,心情很好,大志就猜想,她一定又是听到什么好话了。
“他们都说你孝顺呢!”这句话母亲说过好几次。
大志听了笑笑。他也是没办法。父亲走后,他就打算让母亲搬进城和自己住,一家人在一起也好有个照应,可说了几次,母亲死活不肯,他只好节假日尽量回来陪陪她。不过,这也不完全是一种负担,他发现,多回来几次之后,自己的情感好像也起了变化,年轻时觉得农村偏僻落后,总想逃离,现在反而觉得村里的一切变得可亲可近起来。其实,类似的变化早几年已经有了。小时候说的是方言,后来学说普通话,话里带地方口音,被人调侃。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克服了地方口音。可前几年,他发现自己在说话时,不经意中某个字的发音又滑回方言。春去春又来,凡事都有轮回。只是这一轮回,他就怀疑,自己真的要老了。
这两年还是不少做梦,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梦与儿时有关、与村里草木风情有关。昨晚他才梦见父亲举着一个鸟笼,送他一只鹧鸪 ,没想到今天中午就听见鹧鸪叫,简直难于置信。
他喜欢鹧鸪,特别是喜欢听鹧鸪啼鸣,那一声递一声的婉转激荡,如坐云端,如亲人自远方来,让人陶醉,安静祥和。只是村里的鹧鸪早已绝迹。他记得自从上小学之后就不怎么听到鹧鸪叫了。绝迹了几十年的鹧鸪现在又回来,难不成也是一种轮回?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一件大好事。
不行,得找个人說说,一半出于分享,一半是为了证实。
晒场那边隔巷兰嫂正在翻晒刚从地里收回来的花生。她把花生归拢在一起,然后又重新摊开,手里干着活,嘴里不停地念叨,说是一样的地亩,为什么收的花生越来越少?还说照这样下去,今后花生恐怕也要绝种了。她一干完手里的活就赶紧躲进树荫底下,用一条毛巾擦拭脸上的汗珠。大志上前跟她打了个招呼,然后说:
“兰嫂,你听见大观岭那边鹧鸪叫了吗?”
“鹧鸪叫?什么时候?”兰嫂说。
“就在刚才。”他说。
“刚才?”兰嫂有些错愕,盯着他看,片刻,又“哈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直不起腰,笑得泪眼婆娑,笑得差一点没闭过气,喘口气还继续笑,根本停不下来。大志感到莫名其妙,他不晓得兰嫂为何如此大笑不止,有些尴尬。巷口有几只大鹅在歇息,它们大概一时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如此大笑不已,伸长脖颈,昂昂向天问;还有一只老母鸡,显然是被吓着了,惊慌失措,奓开翅膀,“咯咯哒、咯咯哒……”不停地叫唤雏鸡。
安叔骑着电动单车从村那边驶来,后车垫上带着他的小孙子,背一个小书包,到跟前时将电动单车停下,单腿着地撑着。
“兰嫂,什么事那么好笑?”安叔问。
兰嫂勉强直起腰身,手指着大志说:“你问他。哎哟笑死人了!”
大志给安叔递了支烟,然后问:“安叔,您听见大观岭那边鹧鸪叫了吗?”
“鹧鸪叫?”安叔看了大志一眼,像是没听明白。这时,坐在后车垫上的小孙子嚷嚷了:“爷爷,还走不走呀?要迟到了!”安叔就说:“好好好,这就走,就走。”
安叔走后,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不知从哪冒了出来,颤颤巍巍的,大志认出那是隔几条巷子的老辉爹,他很惊讶,才几年不见老辉爹就老成了这样。“说啥呢这么热闹?”老人嘴里咕哝着。大志说:“您听见大观岭那边鹧鸪叫了吗?”老人像是没听见,两眼直直只盯着大志手里的烟盒,大志见状,忙敬上一支烟,又问:“您听见大观岭那边鹧鸪叫了吗?”。“鹧鸪吗?”老人说,“有!多得是!都藏在芒萁草丛里。”大志不敢相信,就说:“是真的吗?”老人说:“那还能假呀!”然后又说,“当年我们家永明和你是同班同学,成绩也不错,但他没有你命好。”大志一愣,这是哪跟哪呀!当年我在村里小学当民办教师,他儿子永明是我班上的学生,怎么就成同班同学了?老人家这是老糊涂了。他和老人家略寒暄几句,又递上一支烟,就借故走了。
大志顺着巷子往上走,又从另一条巷子往下走,他想找个人说一说,不再是分享喜悦,而是要证实事情的真实性。村里的青壮年人大多进城打工去了,留下来的都是老人孩子,这个时候正是上学时间,就是老人也没闲着,他们都有任务,要送孩子上学。大志连走了几条巷子,愣是没找到一个合适的人相问,只好打道回府。
一回到家,母亲也从外面回来了。大志想,母亲在村里聊天,一定能听到山坡上的鹧鸪叫,问问她看怎么说。
“妈,大观岭那边的山坡上有鹧鸪呢!”
“你怎么知道?”母亲说。
“我听见鹧鸪叫了。”他说。
“你怕是想多了。”
母亲否认。从她的表情里,大志还看出她在为他担心,要安慰他的意思。
母亲这是怎么啦?是哪个得罪她了吗?其实,刚才母亲回到家时就已经脸色不好,不像以往那样有好心情,只是他没注意到罢了。
“大志啊,”母亲又说,“鹧鸪都绝迹几十年了,不知你是哪只耳朵听见的,还到处说!你知道吗,刚才我在外面已经听到你的闲话了,他们说你怪怪的,有些不对劲呢!”
他明白了,是有人笑话她儿子,她听了不高兴呢。小时候,他会问大人,山的另一边都有些什么?蚂蚁在路上碰头是不是互相打招呼?净问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村里人认为他是个书呆子,多有取笑。现在,村里人又来笑话他了。可是,自己是真的听见鹧鸪叫了的呀,那几声啼鸣,那么清晰,那么真切,这有什么不对吗?不过,他不想让母亲担心,就说:
“妈,我知道了。”
次日一大早,他就赶回城里上班了。
人回了城,心里还是惦记老家那边的鹧鸪,一连几个夜晚,梦里总有鹧鸪相随,那一声又一声的啼鸣,叫得他心花怒放。醒来后睡不着,他就想,村里的鹧鸪是不是真的回来了?自己听见鹧鸪叫是真实的还是幻觉?这个问题时不时浮现脑海,忘不了,放不下。
2
一次偶然,他得知那是白耳鹧鸪,属于保护动物。
那天那个饭局是他朋友请客,好像是朋友有什么事要请人帮忙,要不然就是别人帮了什么忙要答谢,搞不清楚,也不必搞清楚,他只是被叫去凑热闹的。饭局上有五六个人,大志除了他朋友,跟其他的人都是第一次见面,尽管推杯换盏时皆称兄道弟,但具体一个个高姓大名、在哪高就等等,他概不知道,也没有打听。饭局散后,大路朝天各回各庙,估计今后能再见上一面都很难,更谈不上会成为熟人了。
可饭局結束时,外面偏偏下起了瓢泼大雨,还刮着大风,一时不便回去,就有人提议搓两局,于是四人成一桌,趣味相投,打起了麻将。大志不打麻将,站在一边旁观,很快就感到有些乏味。外面依然大雨如注,窗玻璃上的雨水像水帘子披挂而下。天气预报说三天后有一个强台风,想不到雨这么快就来了。他后悔来的时候没带雨具。
包厢的另一头,有一人坐在沙发上刷手机。大志迟疑了一下,也到那边的沙发上坐下。
“教授好!”他说。
“副教授。”那人说。
他叫他教授,只是因为刚才在饭局上别人都这样称呼他,他也跟着这样称呼他。这不过一句客套,没想到对方如此较真,听上去不像是谦虚,倒像是怀才不遇。
“这么年轻就当上了教授,不简单啊!”他没话找话恭维了一句
“不像吗?”那人说。
他本来没有这个意思,可那人这么一说,他倒是觉得真的有几分不像。那人皮肤黝黑,身材精干,应该经常跑野外,而且一身短打,不太注重仪表,少了教授常见的儒雅,看上去倒像是干……对了,像巡山队的护林员。这么一想,他心里乐了一下。
“袁隆平像不像教授?”那人又冒出了一句。
袁隆平当然像教授了,以他的成就和对社会的贡献,比教授还要教授,比院士还要院士。
“这么说,你是搞水稻研究的了?”他说。
“不是,”那人说,“我的专业是生物多样性研究,经常在野外搞调查。”
他伸出手和那人握了一下。那人说我姓吴。俩人算是认识了,可他一时又觉得无话可说,便掏出手机也刷起来。
窗外依然风大雨大,但屋内听不见丁点声响;那边的麻将桌上这时也显得非常安静,大概是牌局进入相持阶段了吧,不喜不怒,没有喧哗,只听见“橐橐”的落子声,很有节奏。突然传来一声悦耳悠扬的啼鸣,他一愣,望向窗外,但很快就反应过来,这声音是从吴教授的手机里传出来。
“鹧鸪。”他说。
“是鹧鸪。”吴教授说。
“这声音好熟悉。”他说。
“此鹧鸪非彼鹧鸪,你肯定张冠李戴了。”吴教授说。
“不会吧?”他凑过去,看见一只五彩斑斓的鹧鸪正在引吭高歌,耳根处有一圈白毛,“没错,就是它,我见过。”
“你看清楚了,这是白耳鹧鸪,海南特有的珍惜物种,国家保护动物。”吴教授说。
“是吗?”大志一下子兴奋起来,心中升起一股强烈的自豪感,其程度不亚于听说自己的家乡出了一位世界冠军,或者有人获得了诺贝尔奖。“我不仅见过,还养过一只呢,就是足鳞爪甲我都记得一清二楚。”他说。
他说的是真话。他是养过一只鹧鸪。那次父亲送给他一只鹧鸪,算是对他因为贪玩而受到责骂的一种补偿。那只鹧鸪浑身上下布满漂亮的小圆点,五彩斑斓,耳根处却有一圈白毛,样子十分可爱。他喜欢得不得了,又是给谷子又是喂虫子,整天围着鸟笼子转。不过,他和鹧鸪的亲密关系只持续了几天。“差不多就行了。一味纵容,心野了,开学后怎么上课读书?”他听见母亲向父亲嘀咕,担心她会行为过激,危及鹧鸪性命,当晚夜深人静时,悄悄爬下床,把那只鹧鸪放走了。
“什么时候的事?”吴教授说。
“我上小学一年级前的那个夏天。”他说。
“猴年马月的事了!现在白耳鹧鸪已经灭绝。”吴教授说。
“是这样的吗?”
他感到很失望。母亲说他想多了,兰嫂笑话他,他都可以不以为然,可人家吴教授可是这方面的专家啊,他说灭绝了,那就真的是灭绝了。恍惚中,他仿佛又听见了老家山坡上的鹧鸪声,不禁脱口而出:“可是最近我在老家还看见过它呢!”
“真的吗?”这一次换作吴教授显得格外兴奋了,他一把攥住大志的手,两眼发亮,像突然找到自家弄丢了的宝贝。大志一时被搞得莫名其妙,点点头。“哎呀,我们正到处找它呢!这下有目标了。”吴教授轻抚手掌,高兴得像个小孩子,然后又问大志老家在什么地方?大志说了老家的具体地址。“是那个地方啊……”吴教授沉吟片刻,又说,“那里属五指山余脉,平岭、尖岭、牛颁岭,几个小山头罗列,海拔300—600,山下有一条罗田溪,汇入万泉河,山坡上有许多芒萁草,正是白耳鹧鸪最喜欢的栖息地。”他像数说自家的后花园一样,对那里的山川草木很熟悉。大志不由得心生敬佩,人家毕竟是研究生物多样性的专家教授!
“什么时候我们要组织去那里实地考察一下。”吴教授说。
一听吴教授说要搞实地考察,大志就感到心里没底,有些忐忑。他只是听见而没有看见,而且是不是真的听见了,也不能确定。可话已说出,不好改口,想了想,就试探性地说:“吴教授,您说灭绝了的物种会不会再次出现?”吴教授说:“有可能。其实它不一定就真的灭绝了,只是因为生态环境恶化,它数量变得十分稀少,又远远躲开人群,人们便认为它灭绝了。比如海南长臂猿,人们一度认为它灭绝了,后来又被发现,现在它们的族群已经变得很活跃了。”大志听了,心里才变得踏实起来。
吴教授问大志有没有白耳鹧鸪的照片,大志说没有。吴教授就叮嘱,说下次再见到,最好想办法拍几张照片。大志一口应允,仿佛他所说的真有那么回事似的。
窗外的雨停了,麻将牌局也已散场,大志与吴教授还在谈论着白耳鹧鸪,俩人俨然一对道上的好朋友。
自从认识了吴教授,老家山坡上的鹧鸪声又重回到大志的梦里。他坚信,一定是由于村边的生态环境改善,白耳鹧鸪又回来了。
3
大志决定,这次回老家,要多住几天。
母亲听说他要在家里多住几天,满心欢喜,在村里逢人便讲,村里人都夸他懂事,有孝心。
其实,这次要在老家多住几天,除了可以多些陪陪母亲,他还另有打算,就是要想办法找到白耳鹧鸪。
那次在饭局上认识了吴教授后,大志和他成了好朋友。听吴教授说,如果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族群会变得活跃起来,就是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物种,也有可能重新被发现,他就很关心,村里的生态环境现在究竟怎样的一种情况。上午,他特地在村子周邊走了一圈。他记得,小时候村子周边全是耕地,就是那些不适宜耕种的荒坡野岭也都被开垦出来,美其名曰“山河一片红” ,光秃秃的一眼可望见十里开外。那时镇里有没有放电影,不用提前去镇里看海报,只需傍晚时走上村后的高坡往十里开外的电影场那里瞭望,挂不挂幕布便可一清二楚。现在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所到之处,只零零星星看到有的地块还种着一些庄稼,也不怎么打理,似可有可无。放眼望去,满山满坡几乎全都为各种林木所覆盖,郁郁葱葱,连绵起伏,和远处的大山已经连成一片。这么好的环境,白耳鹧鸪肯定是回来了,正等着人们去发现呢!他很有信心。吴教授还说过,如果重新发现白耳鹧鸪,很可能要专门成立一个保护区,帮助种群的繁衍和恢复。大志不禁回想起几十年前的情景,心里充满憧憬,若是保护区建立起来,到时候,一定又是满山满坡的鹧鸪声。他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要回村里重修老家的房子。早几年,父亲就跟他唠叨,说谁谁家又起了楼房。他明白父亲的意思,嘴上没有拒绝,却含糊其辞,说不着急,其实心里有想法,觉得农村偏僻落后,能住就将就住着,花这个钱不值得。现在,他不再犹豫了,要修家里的房子,而且打算不是搞一般的维修,而是将老屋推倒,建新式小楼。现在村里的生态环境不错,还铺上了水泥村道,空气新鲜,交通方便,要是再有一个白耳鹧鸪的保护区,那就更美了,有心情的话回来小住几天,以后退休了回来养老也很不错。一想到可以住着小洋楼,满目皆绿色,枕着满山的鹧鸪声入眠,他心里就感到美滋滋的,有些亟不可待。
中午回到家,母亲问:“干什么去了?”他说:“没事在村边随便走走看看。”母亲就说:“想看的话我带你去。我们家那些地,最大的那块早些年你父亲种了橡胶,现在没人收割没人管;有一块我自己种点地瓜、种点花生,现在也做不动了,在那里撂荒;有一块闲着也是闲着,我让兰嫂先种着;还有一块……”他觉得母亲误解他了,就说:“妈,我没有那个意思。您也老了,不要管那么多了,那些地谁想种就让谁种吧。”母亲说:“认一下也好,毕竟是我们家的地。”他不想讨论这种事,就说:“改天再说吧。”
下午,他走了一趟村委会。村委会的干部告诉他,说户口在外的人不能回村里盖房。他正要死了这份心,村里的干部又说,要回村里修房子也可以,但报建只能以他母亲的名义。他觉得这无所谓,就说等回去找到母亲的身份证,改天再来办申请手续。
之前,大志一直在等吴教授的消息。吴教授说过,他要亲自做一次野外实地考察,取得第一手材料。大志听他话里的意思,并非只是说说而已,而是十分看重的,隐约觉得这事好像与他的业绩有关,与他的职称评聘有关。可大志问过几次,吴教授总是说,再等等。还要等什么呢?吴教授没说,大志猜测,大概是要等立项等经费吧,有些事着急也没用。他就想,何不自己先做考察,如果能够有所发现,提供几张照片,说不定对吴教授他们的工作会有所帮助。
那几天,大志时常望着对面的山坡,两只耳朵抻得老长老长,盼望着突然就听见那边传来鹧鸪的叫声,可等来等去,始终没有出现想要的结果,除了偶尔有几声黄牛哞哞叫随风飘来,别的什么都听不见。到了第三天中午,他坐不住了,找了顶草帽,就往对面的山坡走去。
山坡上到处都是树,橡胶树、槟榔树、山柚树、花梨树,还有大片的人工林。树下自然也有草,有的地方的草还很茂密,植被很不错,但他总觉得好像少了什么,于是就继续往前面走去。大约又走了几百米,前面的山坡逐渐变陡起来,出现很多天然的灌木丛,还有大片的茅草和芒萁草,他心里一乐,这就是了!鹧鸪最喜欢这样的环境了。他猜测,如果山坡上有鹧鸪,大概就是藏在这一大片芒萁草丛中,于是就在一处树丛边坐下,想守株待兔。山里很热,蚊子特别多,不停地往身上扑,他候了大约一个时辰,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只好作罢。临走前,他往四处扔了几块石头,又拾起一根木棍,啊啊叫喊着打向草丛树丛,惊起一只硕大飞鸟,却是毛鸡,不是鹧鸪。
大志再次感到失望,他想,鹧鸪大概是没有的,真的是自己想多了。转而又觉得,吴教授他们不来考察也好,要是他们真的来了,找不到鹧鸪,到时问起,如何是好?
回到家时,大志满头大汗,母亲嗔怪,说大中午的不该到处跑。兰嫂也在,她们两个在拉家常。兰嫂说家里丁口多了,屋子挤了,她二儿子想另盖新房,但拿不下宅基地,上面不批。母亲就说,只要一心想盖,宅基地最后会解决的,但要是不想盖,就是有现成的宅基地也是枉然。大志听出母亲话里的埋怨,他本想说出自己的打算,让母亲放心,可话到嘴边又打住了,只是平静地告诉母亲,他打算明天就回城里。
突然,对面山坡上传来一声鹧鸪啼鸣,婉转嘹亮。大志一愣,以为自己听错了,不敢作声,凝神屏息,看能不能再次听见。只一会,又传来第二声、第三声,真真切切。他看向兰嫂,急切地问:
“兰嫂,你听见鹧鸪叫没?”
“是鹧鸪叫。”兰嫂说。
他又看向母亲,“妈,您也听见鹧鸪叫了吗?”
母亲点点头。
他不由分说,抓起那顶草帽就冲出大门。母亲在后面大声问:“你要去哪?”他头也回,只在风中甩下一句:
“去对面的山坡上看看!”
4
大志没有见到鹧鸪。还没等他靠近,鹧鸪声就静止了,而且不再叫唤,他在附近走过来绕过去,一直到傍晚,始终没能再次听到鹧鸪的叫声。
第二天中午,鹧鸪声再次传来,大志高兴得像个孩子,手舞足蹈的。现在可以断定对面山坡上有鹧鸪了,可他知道,仅有自己相信是不行的,自己说了不算,关键是要让吴教授他们也相信,他们代表权威,要搞保护区也是需要他们推动才行。要想让吴教授他们相信,得拿出点东西才行,不能仅凭一句话,吴教授不是说了吗,最好要有张照片。对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拍它几张照片。
可是,那只鹧鸪不肯配合,他只要稍微靠近一点,它就不再作声了。芒萁草高齐腰,搞不清楚它藏在什么地方,连个影子都看不见,怎么拍照?他很苦恼,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妈,小时候父亲送我一只鹧鸪,您还记得吧?他是怎么抓到那只鹧鸪的?”大志问母亲。
“我怎么知道!”母亲说,“不过,我记得那时人们捕鹧鸪,是用鹧鸪媒子。”
大志想起来了,小时候好几次见过有陌生人穿过村前的小路,手撑一块树叶扎成的遮屏,肩扛一把猎枪,枪管上挂一鸟笼,鸟笼里有一只喂养的鹧鸪媒子,晃悠悠走向对面的山坡。听说鹧鸪媒子一叫,如果山坡上有鹧鸪,就会以为领地被侵犯了,怒冲冲不顾一切地扑过来,最终中了猎人设下的圈套。他们一帮小伙伴曾向陌生人扔过小石子,因为他们认为,山坡上的鹧鸪属于村里,陌生人的行为不是偷就是抢。
用鹧鸪媒子,这倒是个好办法!
“妈,那您知道附近村里谁家有鹧鸪媒子吗?我想借来一用。”
“你想干什么呢?”母亲问。大志将自己的想法向母亲说明,母亲一听,就笑了起来。
“你这傻孩子!鹧鸪都绝种了,哪还有鹧鸪媒子?”
大志也笑了笑,有些尴尬。
大概是看出了儿子的苦恼,母亲说:“要不你去找兰嫂吧,她或许会有什么好办法。”
大志听母亲说,兰嫂的父亲当年常提着个鸟笼子四处转悠打鹧鸪,后来父业子承,传到她弟时,她弟更绝,会模仿鹧鸪媒子叫,比鹧鸪媒子更鹧鸪媒子。大志就去找兰嫂。
“兰嫂,听说你娘家的弟弟会模仿鹧鸪媒子叫?”
“是呀,”兰嫂说。“他可绝了,可以假乱真,没人能够像他这样。可现在这也算不上什么技能了。现在他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想干,还喜欢喝酒。别人喝酒高兴了去唱卡拉ok,他要是喝多了就学鹧鸪叫,你说可笑不可笑!”
大志忍不住,“噗嗤”一声就笑了出来,他说:“兰嫂,我想请你兄弟喝酒。”
“怎么,你也想看他笑话吗?”兰嫂说。
“不是的,我只是有事想请他帮个忙。”大志说。接着他又将自己的想法向兰嫂又重复了一遍。
“是这样的啊,”兰嫂说,“要我说,这事也简单,用不着去请他。你找个录音机一播不就行了!绝对逼真,我听说别人就是这么干的。”
大志一拍脑袋,明白了。他立马跑到镇上买了个音响,又从网上下载了一个音频,一播放,果真像兰嫂所说的那样。“这办法准行!”他感到十分庆幸。
相机是早已准备好的,为了便于隐蔽,他还用树枝扎了一块遮屏。做完这些,他觉得应该不差什么了,便起身往对面的山坡走去。
太阳已经西斜,不过时间尚早,不会耽误什么。一路上,大志想象着即将出现的情景,仿佛看见有只生猛的鹧鸪扑棱着翅膀,气势汹汹地扑过来……他想,到时候一定要多拍几张,不要留下什么遺憾。
穿过人工林,到达山脚下,大志找到一块大片的芒萁草,在树丛前蹲下,支起遮屏,想了想又觉得,这样似乎不妥,谁知道鹧鸪会从什么方向冲过来呢?觉得还是钻进芒萁草丛里最好,便于见机行事。
一切准备就绪,大志按下按键,山坡上响起鹧鸪的叫声,一次、两次、三次……满以为很快就会有只鹧鸪猛扑过来,可一刻钟都不止了,山坡上依然静悄悄的。他觉得有些不对劲,难道这山坡上根本就没有鹧鸪?就在他感到失望时,前面响起鹧鸪的叫声,距离有点远。他心里一阵激动,不停地播放音响,好让对面的鹧鸪冲过来。出乎意料的是,对面的鹧鸪只是一味地鸣叫,却不见要冲过来的迹象,僵持了几分钟之后,他就想,也许这里不属于那只鹧鸪的领地,据说鹧鸪只在乎它的领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他关了音响,弓腰驼背,借助草丛的掩护,悄悄往前移动,估计差不多了时才停下。音响里再次响起鹧鸪的叫声,前面的那只鹧鸪很快也叫了起来,而且就在前面不远处,大概二三十米吧。他估计在自己往前面移动时,那只鹧鸪也往这边冲过来,幸亏自己早一点停下,要不然肯定会迎面撞上,而且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鹧鸪早受惊飞走,再找那就难了。乖乖,这次要更加小心了。他一动不动地趴在草丛里,又拿过插满干草树叶的遮屏挡在前面,手拿相机,静候那只鹧鸪扑过来。说来奇怪,他一停下,前面的鹧鸪也停下,搞不明白究竟是胆怯呢还是大度。他估摸着这个距离,用长焦也能搞定,可草丛茂密,前面的鹧鸪只闻其声不见真容,无法下手,急得他不知如何是好。
又僵持了几分钟,实在没办法,大志只得再往前移动。草丛茂密,大志怕惊动前面的鹧鸪,头埋下,匍匐着身子,轻轻扒拉草丛。大概又移动了十米八米,忽然听前面的草丛里窸窣作响,一抬头,不是鹧鸪,却见一颗人头晃动,依稀可辨,似乎还有一杆枪,吓得他魂飞魄散,连忙站起身来。
“谁——”他大喊一声。
那人似乎也被吓到了,“呼”的一下子站起来,一叠声说:
“科考队的、科考队的,别误会。”
大志这下看清楚了,前面站着的,不是别人,却是吴教授,手里也拿着一部音响。
一阵风吹过,草丛偃伏。四下里静悄悄。大志望着吴教授,吴教授也看向他,俩人会心一笑,同时按响手里的音响,一时间,山坡上鹧鸪声声,响彻云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