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壮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硕果
2024-06-03覃彩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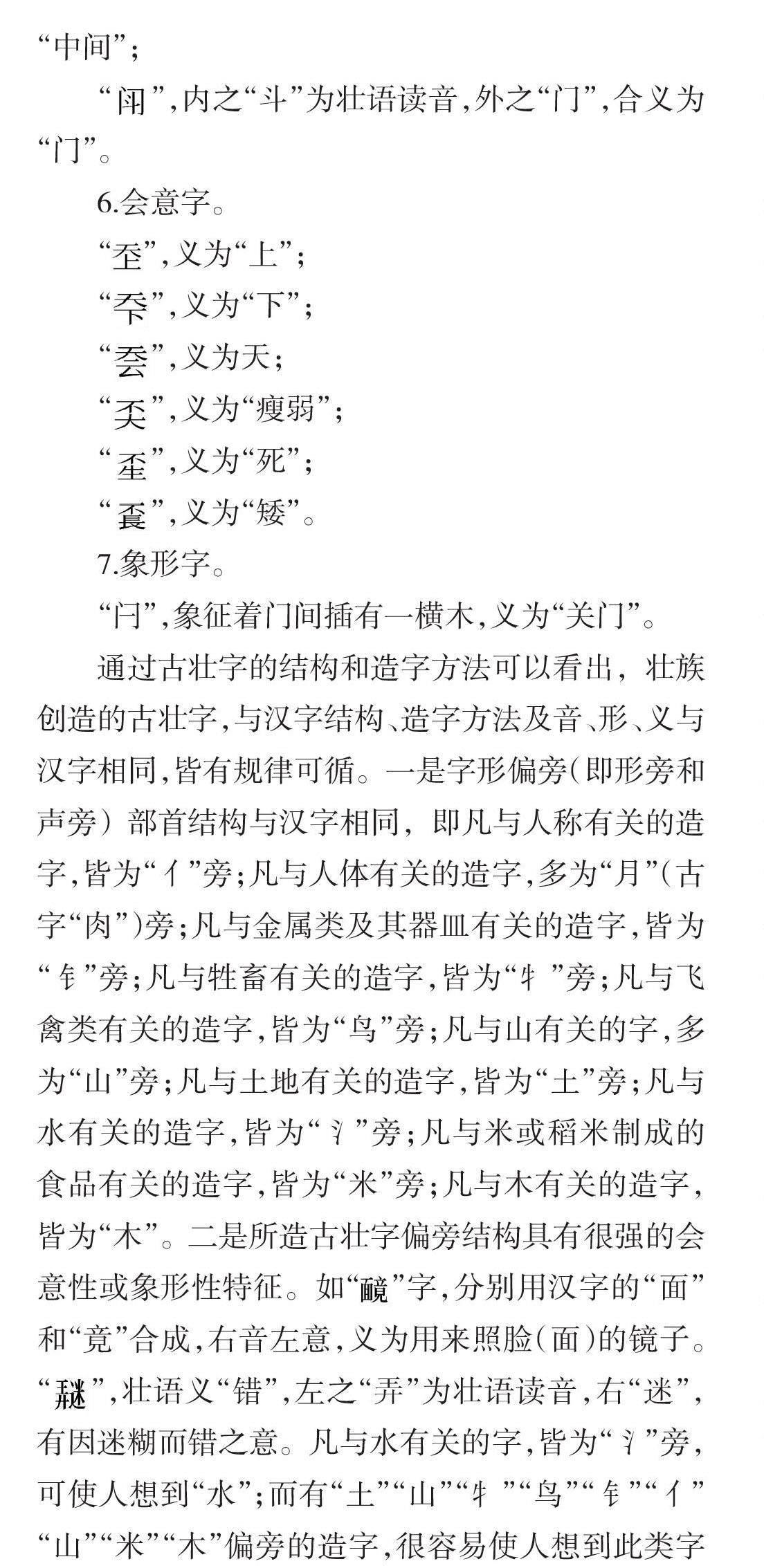
摘 要:古壮字是壮族及其先民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为便于记事和交流,以汉字为基础,仿照汉字结构和造字法创造的一种民族文字,广泛用于民间记录宗教经文、山歌唱本、长诗、神话故事等。古壮字的发展历史,萌芽于汉、成于唐、兴于宋、盛于明清,成为壮族民间的书面文学用字并传承至今,对壮族文学的发展与传承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古壮字是壮汉文化交流交融的产物和典范,是壮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精神的体现,也是壮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硕果。
关键词:古壮字;壮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4.01.011
[中图分类号]J29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24)01-0076-06
文字是人类用表义符号记录表达信息的方式,是将语言的听觉符号转化为视觉符号的工具。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中国是世界上发明和使用文字最早的国家之一,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晚期,中原华夏民族就发明了早期文字——甲骨文,开启了中国象形汉字的先河。西周时期,中原华夏民族在甲骨文的基础上开创了在青铜器上刻铸钟鼎文(也称金文),开启了早期篆体字之先,并且成为周代书体的主流。钟鼎文上承甲骨文,下启秦小篆。战国时期秦国人在钟鼎文的基础上,创制了秦小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便于交流,推行“书同文”政策,统一使用小篆为书写文字,结束了战国以来各诸侯国文字杂乱、交流不便的局面。秦末至西汉时期,隶书应势而生,成为汉代书体的主流。魏晋时期,在隶书的基础上,创制了更便于书写、字体娟秀的楷书。唐宋时期,在使用楷体字的同时,又出现了宋体字。宋体字于明代成为书写的主体,标志着汉字的完善与成熟。
随着国家的统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加深和教育的发展,作为汉文化重要载体的汉字在民族地区不断传播,学习和掌握汉字的少数民族文人不断增多,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壮族古壮字就是在壮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人文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且承載着壮族文化发展的重要使命,是壮族人民的智慧和创新精神的结晶,是壮族与汉族交往交流交融结出的硕果,更是壮汉文化交流交融的典范。
一、古壮字的创制与使用
古壮字,旧称土俗字、方块字、方块壮字,是历史上壮族及其先民中接受汉文化教育、掌握汉文的文人、民间歌师或麽公(道师、师公),在汉字的基础上,根据汉字的形、音、义的结构,仿照汉字“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创造的一种与壮族语言相一致的民族文字,广泛用于记录民间宗教经书、碑碣、讼牒、契约、族谱、信函、记事、歌谣、长诗、剧本、说唱等。2012年出版的《古壮字字典》,收录了10 700个古壮字,“其中选择使用较普遍、结构较合理的4 918个推荐为正体字,其余同音同义异形的字列为异体字”[1]。这是广西民族古籍调查整理者从明清至民国时期抄录的讼牒、券约、师公唱本、山歌本、故事传说、族谱、信件和碑文中收集、整理和遴选汇总而成的。正是由于民间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使古壮字得以保存下来,展现古壮字的历史面貌、特征以及古壮字在壮族民间流行使用的情况。
古壮字演进历程经历了萌芽、形成、发展和盛行四个阶段。汉代是古壮字的萌芽期,即南迁的汉族文人在与当地壮族先民瓯骆人接触、交往和交流过程中,用汉字作音符记录古壮语,壮族先民亦借用汉字来记录古壮语语音。如汉代杨雄《方言》中的“犟,牛也”“虢,式八切,虎也”“把,鱼也”等,应是记录古壮语使用的汉字。其中“犟”是古壮语的vaiz(水牛),“虢”是古壮语的guk(虎),“把”是古壮语的bya(鱼)。后来,“犟”“虢”都成为正式的古壮字[2]。在范晔《后汉书·南蛮传》中也有用汉字来记录古壮语,如“为仆鉴之结,著独力之衣”。其中的“仆鉴”系古壮语bouxgamj,意为居住在岩洞里的人;“独力”系古壮语dozlwg,意为孩童。整句的意思是“扎起洞人一样的发结,穿上孩子一样的衣服”[3]。这种借用汉字音符来记录古壮语的现象,应该是古壮字的雏形,标志着古壮字的萌芽,对后来古壮字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和影响。
唐代是古壮字成形的重要时期,其主要标志有四。第一,唐永淳元年(682年)澄州(今上林县)刺史韦敬瓣撰写并刻立的《澄州无虞县六合坚固大宅颂》碑文中有10余个古壮字[4]。第二,在自古流传至今的壮语布洛陀经诗、师公经书或歌本中,多用古壮字抄录。第三,古壮字所借汉字的读音,多为隋唐读音。第四,早期文字通常是在奴隶社会初期产生,也有许多古老民族文字是在奴隶社会至封建社会产生。唐代是壮族奴隶社会的发展时期。因此,古壮字成形于这个时期,符合文字产生的社会条件。
古壮字在唐代的成形,是有其社会和人文背景的。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繁荣。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唐王朝在广西因地制宜地实施羁縻政策,沿承和发展汉武帝的“以其故俗治毋赋税”政策,实行“以蛮治蛮”的羁縻州制,任用地方民族酋首为各级官吏。这一政策在政治上要求地方服从中央,地方民族事务则由其自治,保留壮族原有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不变,同时重视学校教育、兴办学校,在开启民智和传播汉文化等方面施加影响。随着中原人口不断南迁和汉文化的传播,各种官办的州学、府学或民办学校开始兴起,使当地少数民族子弟有机会入学读书,接受汉文化教育。通过学校教育,掌握文化和汉字的壮族子弟逐渐增多,壮族文人队伍日趋扩大,他们受汉文化影响也不断加深。在使用汉字的过程中,壮族文人逐步认知汉字的结构,掌握了汉字的构造方法,并借用汉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六书造字法,创造了源于汉字又有别于汉字的古壮字,用来记录本民族语言,标志着古壮字的产生。
宋代是古壮字的发展时期,创制和流行使用的古壮字日益增多,并且形成了形、声、义相统一、结构固定的文字,民间使用亦日益广泛,因而引起了地方官员和汉族文人的关注。如宋乾道七年(1171年)任静江府(今桂林)知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的著名文学家范成大,经过深入调查,于淳熙二年(1175年)写出《桂海虞衡志》。在该书《杂志》篇中,对壮族民间使用的古壮字作了翔实的记述:“边远俗陋,牒诉券约,专用土俗书,桂林诸邑皆然。今姑记临桂数字,虽甚鄙野,而偏傍亦有依附。 ,不长也。 ,坐于门中,稳也。 ,大坐,亦稳也。 ,小儿也。 ,人瘦弱也。
,人亡绝也。 ,不能举足也。 ,女大及姐也。 ,山石之岩窟也。闩,门横关也。他不能悉记。余阅颂二年,习见之。”[5]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四《风土门》中亦有类似记载:“广西俗字甚多。如 ,音矮,言矮则不长也; ,音稳,言大坐则稳也;奀,音头倦,言瘦弱也; ,音终,言死也; ,音腊,言不能举足也;仦,音嫋,言小儿也; ,徒架切,言姊也;闩,音撺,言门横关也; ,音磡,言岩崖也;氽,音泅,言人在水上也。”[6]173宋代庄禅《鸡肋篇》亦云:“广南俚俗 ,多撰字画,父子为恩,大坐为稳,不长为矮,如此甚众。”[6]173
明清时期是古壮字盛行时期,广泛应用于麽经、道公、师公经书,山歌唱本和长诗的记录,成为壮族民间书面文学用字。如产生明代、流传于右江河谷的二万多行的《布洛陀麽经》《嘹歌》,就是以古壮字抄本传世的,其中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古壮字,还保存了丰富的文化、民俗、信仰、神话故事和文学艺术成就。清初浔州(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市)推官吴淇《粤风续九》中,采录大量古壮字记录壮族的“扇歌” “担歌”“巾歌”等,即壮族男女把情歌写在扇面、刻于扁担和织(绣)在花巾上,作为信物,相赠定情,并称其“文如鼎彝,歌与花鸟相间,字亦如蝇头”。有的地方用古壮字编写的歌本数以箱计。清人屈大均《广东新语》卷8《刘三姐》条中说:“凡作歌者,毋论齐民与瑶、壮人、山子等类,歌成,必先供一本祝者藏之。求歌者就而录焉,不得携出,渐积遂至数箧。”[7]道光十一年(1831年),今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安马乡古育村廖士宽墓的诗碑,全用古壮字写成。该碑上刻有一首五言勒脚体壮歌,共120行,详尽记述了作者的身世和晚年悲凉的情景[8]。壮族民间的神话、故事、传说、歌谣、谚语、剧本、寓言、楹联、碑刻、药方、家谱、契约等,多用古壮字记录并流传。近代以来,壮族各地民间的师公、道公经书及山歌唱本,一直保持使用古壮字记录的习惯。除沿用传承的古壮字外,许多宗教经书、山歌唱本、长诗则流行用与壮语同音的汉字记录。
古壮字是壮族人民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为适应本民族文化发展、传承的需要,仿照汉字的音、形、义的特点和字形符号的造字方法,创造出的一种源于汉字、借用汉字又不同于汉字的民族文字,并在民间广泛流行,对壮族文学的创作、保存和传承民族文化、丰富壮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提高壮族的文化素质、丰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灿烂文化,有着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是壮族人民集体智慧和创新精神的体现,也是壮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硕果。
二、古壮字中的汉文化因素
公元前218年,秦始皇统一中原后,就把统一的目标指向岭南。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了岭南,并设置了桂林郡、南海郡和象郡,广西开始纳入中央政府管辖的版图,成为最早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版图的边疆地区,壮族先民瓯骆人也成为最早纳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边疆少数民族。秦王朝为了巩固对岭南的统治,采取留军戍守、移民岭南“与越杂处”等措施,开启了广西各民族与中原民族直接交往交流交融的先河。而后,经历西汉和东汉的统一和开发,迁居广西的中原汉族日益增多,特别是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不断传入,不仅促进了广西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而且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亦不断加深。由于中原民族的麦粟农业与壮族先民瓯骆、乌浒、俚、僚民族的稻作农业同属农耕文化类型,文化类型和质态相同,民间信仰亦大同小异,故具有相融性。因此,中原移民及其文化进入广西后,彼此较易产生亲近感,尤其是壮族及其先民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借鉴和吸收,将之融入本民族文化体系,为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平添了活力,实现了民族文化的创新。秦汉时期壮族先民瓯骆人创造的铜鼓文化和花山岩画文化,就借鉴和吸收了中原文化元素,是瓯骆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的成果。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和壮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不断加深,中原文化对壮族及其先民的影响亦不断加深,古壮字就是壮族人民将借鉴和吸收汉族文化推向新的深度與高度的重要体现。无论是字形结构、造字方法,还是字的音、形、义,古壮字都是以汉字为蓝本,借用汉字和仿照汉字构造创造出来的,可以说是别样风采的汉字改造或创新版。
壮族在汉字基础上创制的古壮字,可分为自造字和借用字两种类型①。
(一)自造字
自造字是利用汉字作偏旁或部首创制的古壮字,类似汉字的“六书”造字法,包括象形、会意、形声等。从《古壮字字典》及民间的壮字文献看,古壮字最多的是形声字,而且有规律可循,即借用汉字的偏旁或部首创制古壮字,用以记录壮语。其构造形式为上音下义、下音上义、左音右义、右音左义、内音外义、会意和象形等。其中以上音下义、右音左义的造字居多,下音上义、左音右义、内音外义、会意和象形造字较少。
1.上音下义。
“ ”,上之“那”为壮语“田”的读音,下之“田”,合义为“水田”;
“ ”,上之“那”为壮语“脸”的读音,下之“面”,合义为“脸”;
“ ”,上之“浦”为壮语“坡”的读音,下之“土”,合义为“土坡”;
“ ”,上之“利”为壮语“畲地”的读音,下之“土”,义为“畲地”;
“ ”,上之“台”为壮语“死”的读音,下之“死”,义为“死亡”。
2.下音上义。
“岜”,下之“巴”为壮语读音,上之“山”,合义为“山”;
“ ”,下之“九”为壮语读音,上之“口”,合义为“我”;
“ ”,下之“丁”为壮语读音,上之“山”,合义为“山顶”;
“ ”,下之“敢”为壮语“岩洞”的读音,上之“山”,合义为“山洞”;
“ ”,下之“東”为壮语读音,上之“山”,合为“山间谷地”;
“ ”,下之“良”为壮语“读音,上之“竹”,合义为“竹笋”;
“ ”,下之“礼”为壮语读音,上之“口”,合义为“得”;
“ ”,下之“非”为壮语读音,上之“木”,合义为“木、树木”。
3.右音左义。
“ ”,右之“各”为壮语读音,左之“土”,义为“路”;
“ ”,右之“南”为壮语读音,左之“土”,义为“泥土”;
“ ”,右之“大”为壮语读音,左之“氵”,合义为“河”;
“ ”,右之“寅”为壮语读音,左之“石”,合义为“石头”;
“ ”,右之“才”为壮语读音,左之“男”,合义为“青年男子”;
“ ”,右之“大”(音“达”)为壮语读音,左之“女”,合义为“姑娘”;
“ ”,右之“方”为壮语读音,左之“米”,合义为“粽子”;
“ ”,右之“后”为壮语“稻谷”的读音,左之“米”,合义为“米、谷”;
“ ”,右之“等”为壮语读音,左之“木”,合义为“凳子”;
“ ”,右之“竟”为壮语读音,左之“面”,合义为“镜子”。
4.左音右义。
“ ”,左之“介”为壮语读音,右之“鸟”,合义为“鸡”;
“ ”,左之“九”为壮语读音,右之“头”,合义为“头”;
“ ”,左之“用”(音“融”)为壮语读音,右之“吏”,合义为“用”;
“ ”,左之“弄”为壮语读音,右之“迷”,合义为“错”。
5.外音内义。
“ ”,内之“江”为壮语读音,外之“门”,合义为“中间”;
“ ”,内之“斗”为壮语读音,外之“门”,合义为“门”。
6.会意字。
“ ”,义为“上”;
“ ”,义为“下”;
“ ”,义为天;
“ ”,义为“瘦弱”;
“ ”,义为“死”;
“ ”,义为“矮”。
7.象形字。
“闩”,象征着门间插有一横木,义为“关门”。
通过古壮字的结构和造字方法可以看出,壮族创造的古壮字,与汉字结构、造字方法及音、形、义与汉字相同,皆有规律可循。一是字形偏旁(即形旁和声旁)部首结构与汉字相同,即凡与人称有关的造字,皆为“亻”旁;凡与人体有关的造字,多为“月”(古字“肉”)旁;凡与金属类及其器皿有关的造字,皆为“钅”旁;凡与牲畜有关的造字,皆为“牜”旁;凡与飞禽类有关的造字,皆为“鸟”旁;凡与山有关的字,多为“山”旁;凡与土地有关的造字,皆为“土”旁;凡与水有关的造字,皆为“氵”旁;凡与米或稻米制成的食品有关的造字,皆为“米”旁;凡与木有关的造字,皆为“木”。二是所造古壮字偏旁结构具有很强的会意性或象形性特征。如“ ”字,分别用汉字的“面”和“竟”合成,右音左意,义为用来照脸(面)的镜子。“ ”,壮语义“错”,左之“弄”为壮语读音,右“迷”,有因迷糊而错之意。凡与水有关的字,皆为“氵”旁,可使人想到“水”;而有“土”“山”“牜”“鸟”“钅”“亻”“山”“米”“木”偏旁的造字,很容易使人想到此类字的属性,这既是汉字的特点,也是古壮字的特性。三是偏旁结构灵活多变,表音手段复杂多样。无论是形声字还是会意字,偏旁部首的位置不拘一格,灵活多变,合体字有二合、三合等,形成众多异体字。無论是表音的偏旁还是表意的偏旁,大多都借用汉字的音和义。古壮字借用汉字音表壮语音的手段,超出“六书”的形声、假借,可视为对汉字的创新和发展。四是字形笔画存在随意性,缺乏一定规范,时常出现在汉字基础上的增笔、减笔、改笔、加符号等现象,同形字也较多,通常需要阅读全句,才能知晓同形字的原义。其原因主要是大部分古壮字都以汉字为偏旁或完全借用汉字,为了使古壮字与汉字有所区别,在创造古壮字时便对这些汉字有意识地加以改动。特别是近代的古壮字,直接用汉字表音(假借)增多。五是古壮字的创制方法娴熟,创制的字包含形、音、义三大要素,说明创制者对汉字偏旁结构与字义的深刻认知、造字方法的娴熟和较高的汉文化素养。
(二)假借字
假借字,就是借用汉字的形或音,表壮语的义。这种假借字,以汉字作为记音符号,据音系义,显示出与汉字的区别。这种假借字大量用于壮族道公、师公或麽公等人员记录并世代传承的经书以及民间歌师创作、记录及传承的歌本中。其字为汉字,壮语读音与汉字相同,但已非汉字之义,而是壮语之义。能够读懂此类假借的汉字,需要受过一定的汉语教育学习,掌握一定的汉字量和汉字基础,才能认识或读懂。如:汉字之“板”,壮语读音亦为“板”,其义指“村庄”;汉字“约”,壮语读音亦为“约”,义为“看”;汉字“眉”,壮语读音亦为“眉”,义为“有”;汉字“龙”,壮语读音亦为“龙”,义为“下降”;汉字“刘”,壮语读音亦为“刘”,义为“我们”;汉字“布”,壮语读音亦为“布”,义为“老人或德高望重的老人”;汉字“达”,壮语读音亦为“达”,义为“姑娘”;汉字“农”,壮语读音亦为“农”,义为“妹妹”;汉字“迷”,壮语读音亦为“迷”,义为“母亲”;汉字“博”,壮语读音亦为“博”,义为“父亲”;汉字“火”,壮语义为“穷”;汉字“斗”,壮语义为“来”;汉字“恶”,壮语义为“出”;汉字“欧”,壮语义为“要”。各地壮族借用汉字,赋予壮语含义,是一种文化创新,并且广泛应用于创作和记录民间信仰的经书和山歌唱本,极大丰富了古壮字的形式和内涵。故有学者认为,假借字虽属借字,但从使用功能来看,是用来记录壮语,以外来语理解自己的书写系统。从此意义言之,假借字也是造字[9]。
古壮字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后,随着中原文化的不断南传和学校的兴办与发展、壮族子弟入学读书、学习和认知汉字的社会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壮汉文化交流交融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壮族及其先民以汉字为基础,仿照汉字的“六书”造字法创造了古壮字,用于记录本民族的各类文献,使之成为壮族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历史上,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壮族及其先民在学习、借鉴和吸收汉文化过程中,并不是简单照搬或复制,而是根据本民族的需要,以发展创新的理念,在借鉴汉文化的同时,将之吸收和融入本民族的文化创造,实现民族文化创新与发展,凝聚着壮族人民的集体智慧,反映了壮族人独特的思维习惯、文化心理和造字特色,体现了壮族的开拓创新精神,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硕果与典范。另一方面,古壮字还对布依族、水族、京族文字的产生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许多古壮字被布依族、水族、京族直接使用,用于记录本民族语言及经书、唱本等。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上壮族人口多、分布广,方言众多,而且缺乏统一、规范的政治机制,壮族创造的古壮字遂缺乏统一性和规范性,未能发展成为壮族统一的文字。但是,古壮字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在壮族文学的创新和壮族文化的保存与传承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周作秋等在《壮族文学发展史》中指出:“一千多年来壮族及其先民创作的文学作品,就是依凭古壮字而得以注会至今。壮族的师公唱本、创世史诗、英雄史诗、叙事长诗、抒情长诗,还有不计其数的民间歌谣,无不以古壮字为书写工具。如果没有古壮字,仅仅依靠口耳相传,大量的壮族民间文学就会随风而逝,今人无法领略到《布洛陀麽经》《布伯》《莫一大王》《嘹歌》《欢乐扬》《唱英台》等文学精品的艺术魅力。”[10]这是对古壮字的作用、價值、意义的充分肯定与客观评价。
[参考文献]
[1]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古壮字字典[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12:1.
[2]覃彩銮,覃丽丹.携手谱写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篇章[J].广西民族研究,2022(5).
[3]陆发圆.方块壮字的萌芽与发展[J].广西民族研究,1999(3).
[4]黄南津,唐未平.当代壮族群体使用汉字、古壮字情况调查与分析[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5][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校补[M].齐治平,校补.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31.
[6][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M].胡起望,覃光广,校注.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
[7]壮族百科辞典编纂委员会.壮族百科辞典[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411.
[8]蔡培康,莫瑞扬.奇特的廖士宽墓方块壮字壮歌门碑[J].河池师专学报(文科版),1988(4).
[9]林亦.汉字系民族文字的研究与应用——以古壮字为例[M]//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民族语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408.
[10]周作秋,黄绍清,欧阳若修,等.壮族文学发展史:上[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27.
责任编辑:许立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