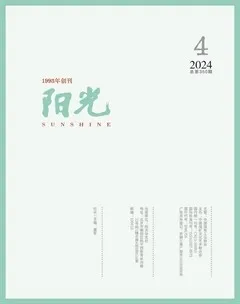乡愁三咂
2024-06-03张波
张波
泉水处处
东山魁夷说,泉水一定知道鸟儿应该飞去的方向。这是诗人的感觉。
我觉得,泉水若有知,它应该最了解山里人的心情。山里人喜爱泉水,它滋润大地万物,也滋润山里人的心田。有泉水才有溪流,才有河水;有泉水,天就不旱,庄稼人就有好年成。泉水有眼,见证着山里人面对它时脸上的喜怒哀乐。
我们村就是个多泉的村。雨季,这里处处泉涌汩汩,溪流潺潺。
村边公路旁山崖下,一道湍急的泉水,翻着雪白的水花,从山上灌木遮蔽的石缝里喷涌而下,一靠近它,浑身就被一阵清爽的凉意包围。即使在炎热的三伏天,在泉水瀑布旁待久了,你的身上也会冻得起鸡皮疙瘩。驱车经过的外地人,到这里都会被泉水吸引,停车凉快一下,或用泉水洗去脸上的汗水,或掬一捧、或接一瓶泉水解渴。我们村里人给这处泉水起了个不雅的名字:“拉泉子”,意思是泉水像是山体里排泄出来的。
有拉就有尿。在拉泉子旁边的十几米高的悬崖上,有一股细细的泉水从崖石里喷出,从高空洋洋洒洒飘落下来。我们村的人把这处泉水,叫做“尿泉子”,意思是这泉水像是一位仙人在半空里尿出来的。拉和尿,尽管这名字不是很雅,却比喻形象,反映出村民朴素的审美情趣。
这两处泉水一出,就表明雨下透地了,河水也到了丰水期。
村北三教堂(现在叫弥陀寺)下的泉水,从山脚两人多高的地方喷涌而出,哗啦啦飞溅到河滩的卵石上,从我记事起就没有干过。泉水的口感清冽甘甜,但烧水喝水锈较多,这是因为矿物质太多的缘故。村里人一般不去这里取水饮用。泉水下边长出很多“渗水石”,就是矿物质的沉结。
村南草峪嵧泉子崖,是村里的水源地。这股泉从山脚悬崖底部的石缝里流出,天再旱,也从来没有干涸过。村里多年前就引这里的泉水,通过几千米管道送到村里每家每户。这股泉水清冽甘甜,即使不烧开,喝了也决不会闹肚子。陆羽在《茶经》里论泡茶的水“其水,用山水上……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这股泉,应该很符合这要求了。外地喜欢喝茶的亲友来这里,都说用这泉水泡的茶味道确实不一样。我们家老辈人就在这泉旁住,家族里众多叔叔和姑姑是从小喝这泉水长大的,神奇的是,他们个个都有一副唱歌的好嗓子。二爷爷家二叔喜欢唱京剧,五叔喜欢唱流行歌曲。喜欢唱歌的五婶当年就是在乡“五四”青年汇演上听了五叔的歌,一见钟情毅然决然嫁给他的,这在当年是一段佳话。五婶后来唱歌,参加各种比赛,虽是草根却也登上过央视大舞台,这其中,也有这泉水滋润的功劳吧?
西石村的草峪嵧十几里长。雨季,里面的泉水多得数不清。流量较大的有凉洞、流水峪,它们是村东小河滩的源头。
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夏秋两季,人们在山上干活,累了渴了,就会到附近的泉水处找水喝。小时候,许多人家里连个水壶都没有,在山上干活时喝泉水是常事。通常是跪在地上,有时还要匍匐在地上,把嘴插到泉水里,像动物一样啜饮。泉水旁放个葫芦瓢,那就非常奢侈了。烈日当头,农活又累,当汗水湿透衣衫,喉咙里渴得冒烟时,一汪清冽的泉水,是最好不过的慰藉了。村西南的水峪岭海拔五百米,最高峰下的山凹处,有一眼泉,泉水很旺。我们常到水峪岭上割柴草,那眼泉,不知让多少人在干渴难耐的时候饱饮过。雨季,有些山岩上会有山水渗出。用泥巴在平缓的岩石坡上堵一个小坑,坑里慢慢就积满了山水,成了一汪山泉。时间一长,泥巴上长出绿色的苔藓,泉水则依旧清澈明净。
家乡人说泉水,都是叫“泉子”,仿佛它是有生命的。山上水旺的泉子,先人们通常都拿錾子在泉水渗出的地方凿一个石槽或石臼,以利存水。还有的在泉水处垒一个石龛,保持卫生。人们都爱护泉水,心怀敬畏。每处泉水,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不会有人故意弄脏或践踏。那是大地母亲赐给我们的乳汁。
消失的青石板路
此刻我行走在法国布卢瓦小城的石板巷里。这个数百年前繁华一时的古城,现在到处还保留着古老的石板路。路面上的石头,多数是琥珀色的,巴掌大见方,经过岁月的磨砺,已是晶莹圆润。市中心繁华的几条街道,不知是出于交通还是保护石板路的需要,改成了步行街。走在这样的石板路上,看着高大的古城堡和一座座建于十五、十六世纪的教堂,古城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布卢瓦现在是旅游城市,每天从欧洲或世界各地来此游览的人络绎不绝。傍晚,临街的餐馆生意火爆。在古老的石板路旁,人们坐在餐桌前边看风景,边品尝卢瓦尔河谷的葡萄酒,边享受惬意的时光。
站在这古城干净、整洁、显示着独特风情的街道上,我想起了故鄉的青石板路。
山村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村子里主要的街道,从前铺的是青石板。当然,许多路段青石板并未铺满整条街,而是只铺了中间的大部分,有些地方还露着泥土。石板就是山上开采下来的山石,大小形状不一。经过无数代人的踩踏,那些石板的表面早就磨光滑,变成了青蓝色。宽宽窄窄的青石板路,在村子里蜿蜒伸展,伴着村边河水的呢喃,仿佛它也成了流动的。石板路与两边的石头墙壁,无言地诉说着静谧和安宁。因为石头形状和纹理都不一样,村里的路面,每一寸都有着独特的印记。你站在石板路上,不用看两边,只瞅一眼脚下的石板,就知道在村子的什么位置。那有一道深车辙的地方,是桥头大槐树下的斜坡。那大石板密铺的段落,是关帝庙前,我们叫庙子台。每当大雨过后,孩子们都挽起裤腿,赤脚站在这里,街上哗哗淌的雨水冲刷着光滑的石板路面,踩上去非常舒服。每家大门口前的石块什么样,这家人肯定是熟烂于心的。
相对于小小的山村来讲,这些青石板路的修建,应该是个大工程。什么时候村里人开始修的石板路?铺完主要的街道用了多久?这是个没有记载、没有传说、无法深究的话题。它深埋在历史的褶皱里,只在你的想象中复活。
在山村漫长的岁月里,肯定有过风调雨顺的年头。那是一个邻里守望、民风淳朴的时代,人们同村而居,渴望把共同的家园建好。在那个秋后的早晨,男人们相约出动了。人们没去给自家开荒垒堰筑梯田,而是专门去采铺路石,要改善村里雨天泥泞路滑的状况。整个冬天,人们从山上开采石板,抬回村里,再铺在街上。他们知道,自己的付出不仅惠及当时的村民,也会造福后代,因此,他们对劳动有了仪式感。同样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铺路让男人心里有一种情绪在翻腾,它又热烈又温暖,充满能量。也许,一个冬天路没铺多远,下一个冬天,人们接着再铺……
石板路落成,雨后再也不用踩着泥泞在街上走了。此后悠长的岁月里,一代又一代村人,他们的麻布鞋底亲吻着脚下的石板,把它打磨平整,打磨光滑,打磨成了圆润的青蓝色。走在街上,脚印和祖先的脚印重合,大地奏出沙沙共鸣,岁月的某一个点,无数次在青石板上穿越重合。
青石板街,古朴厚重,映衬着山村的自然宁静,彰显着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勤劳淳朴。
上个世纪末的某一年,村里搞建设,把街道全铺成了水泥路。街道倒是彻底平整了,可几百年的青石板路消失了,永远封存在了我们这代人的记忆里。
直到近年村里要发展旅游、建古村落,有些人才开始反省:要是当初不把青石板起掉,要是只把青石板两边铺上水泥,也许……
布卢瓦如果没有那些琥珀色的石板路,风景将会逊色不少。二战中这个小城遭到战火重创,可现在除了教堂墙壁上的弹孔,你几乎看不出毁坏的痕迹。他们在重建中,修复了历史留下的记忆。
而许多东西,失去了,就无法再挽回了。
果园记趣
苹果园在村南的山坡上。层层叠叠的梯田里,长满了高大的苹果树。秋天,苹果盈枝的时节,果园,对我们这些饥肠辘辘的孩子们来讲,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诱惑力。
村里对公共财物是看得很严的,你若偷苹果被发现,一个苹果就罚一斤粮食。那时一个人一年也就分三百来斤口粮。村里有专门的护坡人员,在村口盘查搜寻,苹果园还有专门的看护人员,平日里巡视看护。有位村民去自留地里浇白菜,他家的白菜地上边就是苹果园,有一枝沉甸甸的苹果,从堰头上垂到了他家地里。他浇完白菜,已经天黑。瞅瞅四下无人,他就把垂到他家白菜地上空的苹果摘了。不想在村口,他的偷盗行为被护坡人员发现。他被罚了几十斤粮食。那只苹果,又小又青,人们说,他实在是运气不好。
家里人经常嘱咐,千万不能去偷苹果吃,被逮着,难看不说,还要罚粮食,那是金贵的口粮啊!
但苹果的诱惑,实在是难以抗拒。平日主粮就是煎饼窝头,难得见点荤腥。更没有糖果点心。那时候山上也没几棵果树,苹果园里的苹果,是刺激我们味蕾、让我们产生偷盗和占有念想的美丽引诱。去南边山上割柴火、打猪草,有一条小路要穿过果园。每次从果园路过,都被树上的苹果馋得直咽口水。那红得最艳的,是红玉;那又红又大的,是红香蕉;那黄橙橙香气扑鼻的,是金帅;那个头又大结得又密、压弯了树枝的是秋花皮……它们艳丽的脸庞丰美迷人,它们饱含酸甜的汁液,似琼浆,如美酒……在看护人员虎视眈眈地监视下,我们穿过果园,只能偷偷瞥上两眼,饱饱眼福,心中充满了欲望,也充满沮丧。
村民们对小孩子偷苹果的行为并没有上升到道德的高度来评判。他们对因饥饿带来的犯错,给予了极大的宽容。谁家孩子偷苹果被逮住被罚了粮食,只是经济受了损失,大家不去作过多的指责和议论。大人们有时也经不住诱惑呢。
我也有偷苹果的经历。
我带着弟弟和另外两个小伙伴,去打猪草。我们在苹果园旁边的玉米地里钻来钻去。天气闷热,我们头上满是汗水,裸露的皮肤被玉米叶子划得又疼又痒。来到靠近果园的地方,我们就看到了高处枝头上红艳艳的苹果。从玉米地出去,爬上一个小土坡,穿过一条两步宽、静悄悄的小道,再从茂密的紫穗槐丛中钻过去,就是那棵苹果树。那片地是墓地,坟头间是苹果树,周边也没篱笆,偷苹果的人常在这里下手。我们在山上割柴火、打猪草,常听到看园人在这里驱赶偷苹果者的诈唬声。此时,四周一片静谧,玉米、紫穗槐遮挡着阳光,也遮住了我们对惩罚的惧怕。
我让伙伴们拎着我的筐在地里等着。我悄悄走出玉米地,猫着腰爬上小土坡,穿过无人的小道,闪身钻进紫穗槐丛。紫穗槐一墩墩,上边枝叶密不透风,下方半人高的地方才有空隙。我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弯腰穿过紫穗槐丛,很快就来到了坟地边那棵苹果树下。被苹果压弯了的枝条,就在我眼前晃动,只要我伸手就能够到。就在此时,隔着几行被风吹得簌簌晃动的谷子,我看到了一颗人头!透过晃动的谷穗谷叶,我又看清了他上身穿的衣服。那是个看园人,他那漂亮的女儿跟我同班。他背对着我坐在谷地边,有些秃顶的头皮被太阳晒成了紫色,此时还沁着亮晶晶的细汗。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一手瞄准一个苹果,猛地揪下来,飞身钻进了紫穗槐丛。我不理会身后的吆喝声,顾不得树枝条抽打头脸,奋力冲开,扑出去跳过小路,跳下土坡,钻进了玉米地。
我们躲出老远,就在玉米地里,用镰刀将两个红了一半的大国光苹果切开,每人一块苹果,喀嚓喀嚓,嚼得满嘴流白沫。
也是这年七月十五,中元节,我提着箢篼去这片墓地给奶奶上坟。同学的父亲还在这边看果园。他肯定不知道我在他眼皮底下偷过苹果。瞅瞅无人,他顺手摘了几个大金帅苹果,塞到我箢篼的巾布下边。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打个手势让我也别说话。我回家把这事告诉母亲,她笑了笑说,咋着也是一个队的,哄小孩吧。
我们一个生產队。放秋假,我跟他女儿就一块在生产队参加劳动。现在想想他当时那表情,满是慈爱。
秋后,苹果摘完了,果园就放开几天,让大家进去找那些小的、烂的或树上漏下的果子。因为馋,也因为营养缺乏,许多人捡到烂了大半个的苹果也不舍得扔,就拿镰刀削一下,把好的部分填进肚子里。
那一次,我随着大家进果园去找苹果。树上、树下,烂的苹果也基本看不到了。大家像猎犬一样,这里瞅瞅,那里看看,生怕漏掉什么。
我走着,看着。堰根里有一棵软枣树砍掉了,发出了一蓬枝芽。这些枝芽茂密茁壮,秋天了还蓊蓊郁郁。我发现了什么不对劲的地方。那一蓬软枣丛,油绿的叶子颜色都是一样的,可在中间我发现了一个异常的浅色的斑点。那斑点的颜色,说黄不黄,说绿不绿,说白不白,像熟透的青绿颜色的苹果。它在枝头向我炫耀、对我引诱的色调,我太熟悉了。
我马上走了过去。走近了看,软枣丛里,除了油绿的叶子,什么也没有。我拨开树枝,后面堰根里有块小小的空间,我低头一看,看到了苹果!我叫了一声“苹果”,差点晕了过去。
像做梦似的,我从那里摸出了四个又大又圆、沉甸甸的、表皮上还有淡淡一层果粉的秋花皮苹果!
人们围了过来。四个水灵灵的苹果,放在地上,我蹲在人群里,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我宁愿相信苹果是上天藏在那里的,不是摘苹果的人藏的。你在远处近处,都不容易看出来,我站的那位置刚刚好。
心诚则灵,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
苹果我没舍得吃。母亲把它放进了盛衣服的柜子里。每次打开柜子,苹果的香气就弥漫开来。
它成了一个美好的念想,点缀着那段物质贫乏的日子。
张 波:先后做过矿工、新闻工作者。第六届中国煤矿作协副主席,兖矿能源集团文学创作协会主席。在《时代文学》《百花洲》《黄河文学》《阳光》《湛江文学》《辽河》已发表小说、散文,小说获过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