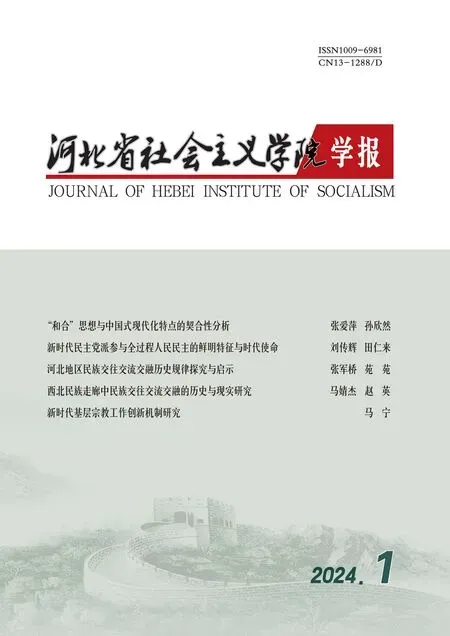西北民族走廊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与现实研究
2024-06-01马婧杰
马婧杰,赵 英
(青海省委党校,青海 西宁 8100001)
一、问题的提出
民族间的交往互依、共生交融是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古有之的客观现实。基于我国民族关系客观规律的总结,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成为当前我国民族工作中的重要内容。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方针和要求,强调“要把是否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衡量民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之一”[1]。这一科学论断深刻把握了我国民族历史发展过程的本质规律,为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和路径。此后,2010 年 6 月召开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2014 年 5月召开的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2014年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2]、党的十九大报告[3]、2019年9月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4]、2021年8月召开的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5]均提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张。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新时代十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进行了深刻总结和科学定位,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战略部署,其中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这些新思想、新论断的提出,引发学术界积极的思考和研究。学界从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等学科出发,透过马克思相关理论、民族政策理论等学理研究层面分析和讨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蕴含的民族关系结构体系和内部逻辑[6]。此外还有学者从互嵌社区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7]、民族心理与族际关系[8]等角度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行研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上述研究逐步深入,学者们开始关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间的联系,包括民族文化交流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研究[9],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基础作用[10]等。
在中国地理、生态及族际间生计互补等因素影响下,联通农、牧各廊道成为民族间交往的重要空间。费孝通先生依据中国地理、生态、经济、文化分野,提出“藏彝走廊”“西北民族走廊”“南岭走廊”等概念,并探讨了各民族走廊在民族迁徙、经济文化沟通交往、人口迁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中,西北民族走廊连接黄土高原、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11],成为民族迁徙、流动或定居,多民族格局形成与定型的重要廊道,其发展史的几个重要阶段都贯穿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容。近年来,随着学界对区域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关注,有关民族走廊中民族交往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其中石硕从民族走廊中的多民族共处过程及民族共处交往机制中,分析地域民族关系在中华民族结构和格局中的推动作用[12]。祁进玉、张瀚丹则以河西民族走廊上有史以来的人口迁徙为线索,分析讨论民族间迁徙往来的复杂社会结构和主观动因,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一内涵生成、发展过程[13]。苏文彪、杨文笔认为区域性研究个案对于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内生动力、情感认同有着重要意义[14]。张筠以藏彝民族走廊民族间的习俗互动考察为例证,讨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生成过程中民族交往过程与实践[15]。玉璐则通过南岭走廊上的通婚事实,讨论了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中深层次的逻辑与规律的事实[16]。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仅是我国历史文化、现实社会关系中的重要基础,也是党在民族理论方面作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其重要内涵,了解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与现实,对于当前所提倡的维护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促进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二、历史回顾:西北民族走廊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要历程
(一)西汉“河开西郡”与羌、汉等民族间渊源与交往
史料记载,古羌人是最早活动于西北民族走廊中河湟一带的主要民族。据史学家马长寿考证,历史中的羌、氐和戎,同为汉藏语系民族。戎主要活动于今甘肃天水以西以及青海东部地区,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氐族则活动于陇坻之南,巴蜀之北;羌族活动的地域较大,包括今青海所在的洮水以西,甘南地区、河湟一带、日月山直至青藏北部地区,以游牧为主,在河湟地区也有农牧兼营的羌族部落。羌、氐、戎文化之间既有相似的渊源,也有相互区分的方面。后与汉、鲜卑、吐蕃等民族文化碰触交流、融汇,成为华夏文化的重要源流和组成[17]。自秦建立统一的封建政权后,西北民族走廊以西的地区逐渐被纳入中原封建政权的控制范围,尤其是秦汉之际,郡县制度逐渐扩展到河湟地区,羌、汉等民族之间开始了政治、军事和经济交往。这一时期,羌、汉之间的往来主要是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例如青海西宁城市的雏形始于西汉年间的屯田设施“西平亭”,此后东汉建安年间从金城郡中折置西平郡,西平郡辖西都、临羌、安夷及破羌四县,其中西都即今西宁,为西平郡的郡治[18]55-56。西汉之前的西宁是古代羌族的活动地,自两汉设置郡县汉族人口迁入以来,西宁便经历了首次民族交往交流,这成为西宁多元民族文化格局的最初基础。两汉以后,羌族逐渐融合于汉,河湟地区逐渐融合于鲜卑、吐蕃、汉等民族中,一部分则向今陕西、四川西北岷江上游迁徙并定居。
(二)公元四世纪开始,鲜卑诸部西迁与西北民族走廊开始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公元四世纪初,辽东鲜卑人向西部和漠北等地迁徙,并逐渐定居到阴山、陇山、河西走廊、祁连山、青海湖周边地带。其中秃发、白部乙弗等部鲜卑人分别在今青海东部河湟地区、川西北至青海湖地区、青海湖北部建立政权。白部乙弗鲜卑与羌人在青海湖北联合建立了邦国。曹魏时期,辽东鲜卑的一支秃发部迁入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与汉族、羌族杂居。东晋时期,鲜卑西迁进入河湟,带入了北方鲜卑文化。南凉鲜卑人注重对汉文化的吸纳借鉴,注重儒学教育,推行联合羌部落首领制度,与羌族部落通婚[19]。鲜卑文化、汉文化、羌文化逐步融合,成为西北地区多元民族格局的第二重要历史融合期。此后,鲜卑慕容部落势力壮大,先后合并乙弗等部落,逐渐由西平郡拓展到青海湖周边。晋永嘉末年,慕容鲜卑建立了吐谷浑国,到唐高宗龙朔三年,历经350年。在其政权建立后,与十六国中的诸国产生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碰触、博弈和往来,并与隋唐时期的中原汉文化密切交流。正如史学家所言:“一部吐谷浑国历史,呈现了纷繁复杂的民族关系史。”[20]除了政治、军事方面的交往外,吐谷浑在中原与西域乃至中亚地区的经济文化往来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十六国至魏晋时期,丝绸之路南线(主要指由关中至陇西,再由枹罕西行渡黄河至官亭,经湟水流域乐都、西宁经湟源,再到吐谷浑政权所在的伏俟城并西行穿柴达木盆地进入西域)开始兴盛。在此种经济文化背景之下,佛教广泛地在西北民族走廊包括河湟地区传播,鲜卑文化成为西北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成为中华多元民族文化格局的重要组成因素。
(三)七世纪,吐蕃东渐与多民族往来涵化
唐宋时期,青海地区广受吐蕃文化浸濡和影响,实现了汉、藏、鲜卑、羌等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此时,吐蕃文化融合鲜卑、汉羌文化后成为青海地域多元文化的要件。吐蕃势力进入河湟东部地区,使得吐蕃文化与汉文化不断深入融合与发展。吐蕃与唐朝积极拓展两地交通,实行供赐往来,推进商贸发展,形成了闻名遐迩的唐蕃古道(东起长安经渭河,西行至临洮渡洮河,至河州后渡黄河到青海民和县境内,再经乐都、西宁、湟源峡、日月山、倒淌河、恰卜恰,经切吉草原到花石峡即今果洛境内,再至玛多黄河沿岸,经渡河到野牛沟,再南下渡通天河到玉树境内,最后进入西藏)[21]。这条线路经由西北民族走廊,带动了此地经济文化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中原文化与河源牧业文化乃至西域文化在内的多元文化的互补、交往与融合。此时期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广泛传播发展,与其他宗教文化尤其是汉族儒道文化互借涵化,成为河湟多元宗教文化中的重要基因。在西藏赞普朗达玛灭佛后,三位西藏僧侣辗转进入河湟地区传法,为喇嘞贡巴饶赛授戒,后贡巴饶赛在今化隆县内丹斗寺弘法,其弟子再度将藏传佛教传入西藏,河湟地区也因此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复兴中心地带。唃嘶啰政权建立后,河湟地区形成以都城青唐城为核心的藏传佛教文化中心,藏传佛教一直兴盛于西北地区,并逐渐发展诸多地方特色[18]214,250。自此,牧业生产的信仰体系与中原的佛道信仰体系并流于青海,对其间的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四)元明时期,多民族格局形成
元明时期是西北地区民族迁徙往来最为频繁的时期,也是该地区多元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蒙元政权的建立,使得蒙古族迁入河湟地区,也促使北方蒙古高原的牧业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河流并汇。随着各民族在西北地区日益频繁的交流融合,西北民族走廊中的文化逐渐具有鲜明多元文化聚合过渡特征。多元文化也映射于封建统治政治制度之中,蒙元政权为了便于对各族统治,实行土官制度即“土官治土民”。针对藏传佛教盛行,设立僧职,给上层僧人授予国师、禅师等具有行政权力的官职,开政教合一制度之始。明代政权对藏传佛教实行封赐和扶持政策,河湟地区广兴寺院建造之风,藏传佛教进入中兴时期,一些历史上有名的藏传佛教寺院大都兴建于明代,如噶举派寺院瞿坛寺、格鲁派寺院塔尔寺、民和弘化寺等,这些寺院的建筑形式、宗教艺术中融合了大量的牧业文化和中原文化内容[18]309。明代的西北地区形成了包括藏族、东乡族、保安族、土族在内的民族共同体或族群,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北民族走廊多元民族文化渐具雏形,其中土族作为新的民族共同体,其文化带型的牧业文化与农耕文化合璧的特征,其宗教信仰中兼具中原佛道文化和藏传佛教内容,也包含北方游牧的萨满信仰。土族的风俗起居、文化心理中亦兼容农业文明和牧业文化的特质。西北民族走廊间各民族文化经元明时期的发展与积淀,到清代进入繁荣期,牧业与农业文化融合其他文化元素,不断整合再衍展,蔚成西北民族走廊中地域文化的新内容,体现在各种文化之中。如著名的热贡艺术、塔尔寺艺术、富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花儿”以及藏族民歌拉伊和尕尔等。总体来看,西北地区的发展史始终伴随着民族间的互动与融合的内容,历史中的几次民族融合奠定了西北民族走廊地域文化的基调,也成为西北社会关系中的重要内容。
三、现实发展:西北民族走廊中各民族的经济、社会、文化交往交流交融
当代,随着信息、交通的迅速发展,西北民族族际间的交往和沟通更为广泛和深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人口流动、社区治理、劳务输出、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等诸多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成为团结和凝聚各民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内容。
(一)当代各民族的经济交往与互惠
西北民族走廊中的多数地区地处高原,农业生产受气候条件影响大,牧业经济时常不能自给,农牧之间的补给成为西北民族间最为基础的经济交往模式。民间的农牧生计互补,不仅是基层生活的一种方式,也是民族间社会关系的基底。族际之间通过农牧交流形成互惠关系,同时也由于农牧社会间的交流,民族间地缘社会关系得以建立,民族在经贸往来中不断重新形塑民族传统和身份认同,经济往来带来民族文化间的涵化和融合,结果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其一,农牧经济交往。西北民族走廊地区海拔由东向西和西南逐步升高,东部和南部主要出产农作物,而西部与北部、西南地区则以畜产品生产为主,地理上农业区向牧业区的过渡,体现在饮食文化中,就出现了多样杂糅的特质。西北民族走廊中的饮食取材兼备农业文化和牧业文化两种特征,主要以引种小麦、青稞、菜籽、蚕豆和畜产品(牛羊肉、乳产品)等为主。西北民族走廊中各地饮食习惯秉承了中原文化以面食为主的饮食传统,其间又融合回族、撒拉族等民族的食品加工工艺以及藏族、土族等民族的饮食文化元素,虽然食材单一,但馔制技法灵活,具有显著的西北地方特色。如河湟地区流行的一道“麦仁粥”小吃,就起源于土族古老农业生产遗俗的 “冰祭”,是土族由游牧生产转向农业生产的重要见证。农牧经济交流的模式也奠定了西北地区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基调。随着地区间人口的移动,民族杂居的社区增多。农牧经济之间的贸易成为杂居社区间的主要生计手段,手工业、民族制造业成为民族间社会交往的中介。农牧经济的交流进一步增进了民族间的互补和互依,缩小了民族间的差异(1),也成为民族间社会关系建构的重要手段。其二,现代经济环境中的民族交往交流。市场经济和人口流动,个体生计流动和公共资源调配,促使民族向城而居,互嵌式社区形成,社区治理和公共文化建设成为新经济交往模式中的重要族际交往手段和机制。相对于传统农牧互补的自然经济模式中族际间依托农牧物资交流互补的经济交往模式,在现代经济影响下,族际交往更为多元化、广泛化。尤其是随着现代商品经济带来的社会分工的细化,语言、地方知识和族际交往经验日益成为民族交往的重要策略和资本。如个人在城镇工作期间,凭借对民族语言和文化风俗知识的掌握,在族际交往中有效沟通与共处,有时还成为个人的生活资本(1)。同时,现代化、城镇化影响到农牧社区后,村民的生计模式开始多元化,“春夏务农放牧、冬季进厂做工”的生计模式在农牧地区更为普遍,农牧民人口流动以及多种生计间的身份转化、共处空间的转换,使得族际间共处的社会经验随着时势迁移而灵活变化。这些经验和观念又成为新的社会情境中的交往理念和族际相处原则,累积了当代社会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
(二)社会交往
其一,社区生活中的民族交往与互鉴。受现代化、城镇化及人口流动等因素影响,西北地区城镇社区少数民族人口中的流动人口逐年增多,社区成为容纳和管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第一扇窗口。据统计,青海省会西宁市少数民族人口为70.51万,占全市人口比例的28.57%,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占比最高的省会城市,其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20.2万,占到流动人口的一半(2)。上述情境下,城镇社区成为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社区及时为社区各族军民提供政策支持与生活帮助,并且通过搭建平台、引入社会组织,给各族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援助、养老等专业服务,为居民搭起沟通桥梁。透过人口流动的管理,社区治理正成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抓手。一些社区依托“石榴籽”家园建设,探索出一些有利于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经验。一是探索多元共治路径,形成社区党组织、党员、居民代表共商、共议的治理模式;二是打造互动平台,建立社区矛盾预防调节机制。此外,在社区党组织的带领下,借助环境卫生整治、垃圾清理等公共活动,增强了社区成员的集体认同感归属感。在此情景中,社区成为当代西北地区族际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空间和实践载体。其二,族际社会关系网络建立。西北民族走廊中民族间交错共居的现象,在廊道地理以及杂居社区中都有体现:多个民族聚居的村落或相互比邻的民族社区间,各民族往往以混合性的生计结构共居。如,在河西走廊以及河湟地区山川交错的地理空间,加之民族间生活空间的相邻与交错,各民族生计模式实际上都是相互兼容,并非泾渭分明的,如传统的农牧及手工、零售兼具。这一现象促进了民族文化间的涵化和整合,并由此建立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交往网络关系。此外,婚姻是血缘和家庭融合的重要手段,对于一个民族来讲,婚姻和家庭也是处理民族关系的一项社会策略。西北地区多民族共处中,突破族内婚的限制,族际通婚以及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金融信贷等都需要高度社会信誉和诚信关系的社会方面的互助(3)。上述,民族关系的深入和相应社会秩序的建构,逐渐成为当代族际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社会关系网络内容。
(三)文化交往
西北地区历史中的民族迁徙带来宗教传播,而民族文化间的涵化与共生也多是以信仰的形式实现的。受多文化圈交汇影响,常有道教、藏传佛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信仰设施并置在同一城镇或社区中的现象。西北民族走廊经民族迁徙、融合,逐渐成为多民族、多宗教聚集地区,代表农业文明的汉族儒释道文化与藏、蒙、土等民族的藏传佛教文化融汇并流,其中多元宗教的共存、交流、互融是西北农牧交流与共存典型构成要素。河湟地区汉族宗教场所之中存在明显的汉族儒道文化对藏传佛教的吸纳借鉴现象。如西北民族走廊中河湟地区的道观,除香烛等供奉之外,还在殿前设有煨桑炉,民众除烧香膜拜之外,还糅合煨桑、献哈达等藏文化元素。在民间文化层面,人们在多元文化与信仰习俗中表现出的尊重与认同,促生了河湟多元宗教的共生与涵化。汉之佛道文化与藏传佛教文化之间互相共存、相互融合是河湟民间信仰的典型现象,如二郎神信仰就是农牧文化共存互动的文化现象。二郎神信仰虽然来自农区,神祇却采用藏传佛教信仰的装饰,形成了土族的特殊民间信仰体系[22]。此种多元包容的文化特质也映现于西北民族走廊文化艺术之中,诸多的西北民族走廊地方文化艺术集中体现了贯通东西、通和多元的文化融合特质,尤其在西北的诸多工艺美术中,各民族以包容和共享模式进行文化再生产与创造,工艺美术也因此独树一帜。如,地处牧业和农业区交界地带的青海湟源县丹噶尔皮绣工艺品即为典型例证,皮绣取材自牧区的特产——皮革,其制作工艺深受中原地区刺绣影响。又如,湟中县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名寺塔尔寺所在地,也是历史上茶马互市的重要集散地,文化上受中原文化、藏传佛教、牧业文化以及西域文化共同影响,民间工艺品色彩和构图受草原牧业文化的影响,同时融汇农区的乡土文化,具有鲜明地域色彩。当代西北地区民间曲艺中也常有各民族文化交流、融汇的印记。如宴席曲是西北地区特有的民间艺术形式,是各民族文化交流、融汇、发展的结晶。宴席曲含有西域古歌和蒙古族古调的色彩,同时吸收了中国西部各民族民间音乐元素,其曲调风格几乎涵盖了西北民间音乐的特点,并保留着传统西北少数民族歌舞小曲的古老风貌,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典型,成为当代多民族节庆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西北民族走廊中族际文化符号交流交融的典型例证。
四、结语
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形成和凝聚的重要实践途径,同时也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关系建构过程。民族关系的形成不仅是历史的积淀,还是自然地理空间的形塑,更是政治经济制度、人口迁徙、文化交流涵化、社会交往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历史形成的族际关系内容和相关民族共处经验,并未随着时间流逝而消散,而是沉淀于当代民族关系之中,成为民族关系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国家与地方的关系结构,国家所实施的民族政策、意识形态塑造、社会关系的建构等对民族交往的形塑,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最为本质的内容。西北民族走廊中多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所呈现出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多层立体结构,充分印证和阐释了多元文化之间不断互动、交流,最终聚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实践和内在规律。
注 释:
(1)据笔者2022年6月15日对青海省贵德县中河阴镇沿街商铺的访谈整理。
(2)参见西宁市人民政府的汇报材料《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积极创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好样板》2023年4月18日(内部资料)。
(3)据笔者2022年6月15日对青海贵德县河西镇下刘屯村的访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