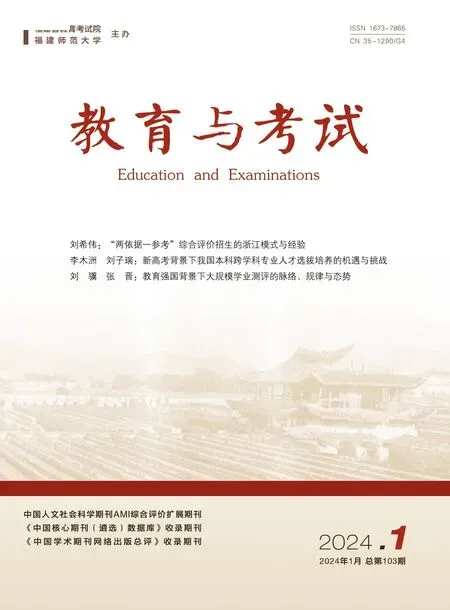机会均等与弱势补偿:普林斯顿大学选拔性入学制度探索*
2024-06-01徐传雲
胡 瑞 徐传雲
教育公平是美好教育生活的必需品。[1]选拔性入学制度(Selective Admission Policy)是高校教育公平的起点,具体指高校面临入学申请者远多于拟招生人数时,为了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采取竞争性手段,根据特定评价标准,淘汰部分申请者,筛选出最具潜力的学生。选拔性入学制度作为美国精英高校教育机会分配的基本形式之一,不仅促进了美国精英高校选择更具发展潜力的候选人,也推动了基于综合性评价的录取决策机制的发展。作为美国常春藤联盟成员之一的普林斯顿大学,成立200 多年以来,在“精英主义”与“平等主义”的博弈中,以“机会均等”和“弱势补偿”作为选拔性入学制度改革的主要理念,采取多种手段考查学生的学业素质和非学业素质,为具有特长的学生提供入学机会,注重维护少数族裔和女性的教育权益。系统分析普林斯顿大学选拔性入学制度变迁的基本理念、发展历程和实践举措,能够为我国进一步完善高校招生制度、高质量推进教育公平提供经验借鉴。
一、“机会均等”与“弱势补偿”:普林斯顿大学选拔性入学制度的理念
普林斯顿大学选拔性入学制度的变迁是一个带有“保守主义教育公平”色彩的制度不断“平等化”的过程。透视普林斯顿大学选拔性入学制度变迁的历程,“机会均等”和“弱势补偿”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两大重要理念。
(一)“机会均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博弈中的发展路向
教育机会均等一直是美国高等教育学界关心的重要问题,它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教育机会均等是指让来自不同阶层、不同族裔和不同性别的学生拥有平等的通过选拔性入学获得教育机会,同时在选拔过程中应当给予所有学生公正的评价。
普林斯顿大学在20 世纪前30 年,一直将“卓越和精英”视作办学的基本理念,秉持高等教育的首要目的就是选拔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理念。这一时期,普林斯顿大学更多表现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大学,其生源流动也局限于上流社会,在推进机会公平上并未做出有效的改变。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 S.Coleman)在《教育机会均等的观念》(The Concept of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中也指出,“在美国前工业化时期,教育领域根本没有产生教育机会公平的观念。”[2]虽然科尔曼认为20 世纪30 年代以前并未产生“教育机会均等”理念,但普林斯顿大学的前身——新泽西学院早在1774 年就招收了2 名黑人学生,[3]出现了追求“机会均等”的端倪,为扩大黑人学生入学机会拉开序幕,也奠定了选拔性入学制度公平性的基础。
与此同时,科尔曼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则认为,工业革命对社会的影响是推动教育机会均等理念产生的重要因素。伴随着工业革命在美国的快速兴起,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进入工厂从事劳动,使得教育的社会需求总量激增,普林斯顿大学也开始考虑通过扩大入学机会,招收更多优秀的高中毕业生,推动了追求“卓越和精英”的选拔性入学制度理念向“教育机会均等”理念的转变。20 世纪30 年代至40 年代,保守主义的教育公平理念在美国高等教育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该理念援引传统基督教义来阐述其观点,认为“基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所以每个人都应当具有接受教育的权利”。[4]普林斯顿大学最初由基督教长老会所创立的,利用对宗教教义的解读推动选拔性入学制度改革,使得普林斯顿大学很快接受了保守主义的“教育机会均等”理念,开始在选拔性入学中加入标准化考试,给予每位申请者“平等”的入学机会。但这种“平等”的入学机会是有限的,因为人生来具有不同的能力水平,高等教育需要照顾到才能较高的学生,因此家庭背景不突出的学生,特别是非裔和犹太裔学生,往往被普林斯顿大学认为“品性和领导力”表现不突出而拒之门外。换言之,受保守主义影响,普林斯顿大学并未将真正的“起点公平”覆盖所有的学生。另一方面,保守主义以宗教教义来阐述教育机会均等,不仅限制了教育惠及少数族裔,也限制了女性的受教育权利。普林斯顿大学在对接受女性入学上采取了消极态度,导致普林斯顿大学在招收女性学生上一直未能有实质性的举措。
20 世纪40 年代以后,“保守主义”在发展进程中逐渐难以适应高等教育质量发展的需要,也难以反映美国普通家庭的教育需求,开始逐渐被“自由主义”取代。这一时期,美国工业化进程持续加快,越来越多的普通家庭迫切需要获得优质的高等教育。保守主义教育机会均等理念过分关注学生“家庭背景”的做法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与此同时,自由主义文化(Liberalism)开始取代保守主义继续引领“教育机会均等”理念的发展。自由主义通过不断强化人们的自我意识,唤醒人们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的主体意识,强调不同个性的学生都应受到平等的对待。[5]这与普林斯顿大学后期关注学生非学业素质,鼓励学生表达个性和自我不谋而合。自由主义者主张教育应当尽可能排除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影响,以智力和能力的标准化考评结果判断学生,同时强调选拔性入学的过程公平,即无论其人种和性别都应在选拔过程中得到公正对待。[6]受到自由主义教育机会均等理念的影响,普林斯顿大学在选拔性入学制度发展进程中做出了适应性调整,一方面继续扩大来自普通公立中学的生源录取率,增加普通家庭学生就读普林斯顿大学的机会;另一方面,普林斯顿大学在60 年代末期开始招收女性学生,为女性提供平等入学的机会。“机会均等”成为普林斯顿大学选拔性入学制度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博弈中的发展路向。
(二)“弱势补偿”: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受益面
“弱势补偿”是指为来自“弱势群体”的学生提供教育上的补偿和援助,目的是让这些学生能够享受到和正常家庭学生同样公平的教育。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的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在《正义论》中将“弱势群体”定义为“最少受惠者”(Least Advantage),即指来自社会背景差、资质平庸、经济收入低、占有资源极少且生活质量较低家庭的学生。[7]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招生历程中,少数族裔、女性和贫困学生一直是“弱势群体”的主体,也是其“弱势补偿”关注的主要对象。
第一,保障少数族裔的入学权益。20 世纪20 年代美国部分大学的犹太裔学生比例持续增高,这引起了美国本土白人对自身教育权利的担忧,并很快演变为针对各少数族裔的“反移民运动”。普林斯顿大学为了限制犹太裔学生的数量,讨好其传统捐助的来源——白人精英家庭,也通过“种族配额”的方式为招生歧视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20 世纪50 年代以后,美国民众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特别是,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领导的民权运动提出“应提高黑人教育水平,增加黑人就业机会”的理念。[8]在马丁·路德·金的影响下,非裔和其他少数族裔学生成立了“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并得到了许多白人的支持,逐渐发展成为席卷全国性的民权运动,并最终迫使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民权法案》(42 U.S.C.1983 of the Civil Right Act),其中提出禁止在教育中因肤色及宗教差异而引发的歧视行为。[9]美国总统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在签署《民权法案》后,很快召集了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在内的5 所大学管理者,要求对招生制度和行为进行改革,对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申请者给予更多的关注。为了缩小少数族裔学生入学后在学业成就上的差距,普林斯顿大学在选拔性入学政策上强调不再将学生的经济背景视作入学的评价标准之一,同时对非裔和犹太裔学生予以降低学业成绩录取的优惠政策,扩大少数族裔学生在录取中的比重。
第二,强化女性的受教育权利。1870 年至1900 年间,美国女性人口数较南北战争时期增加了48.7%,[10]此后,许多州立大学都开始招收女学生,但1901 至1902年仅有21151 名女性被招收至大学学习,[11]而以普林斯顿大学为代表的私立高校仍在拒绝招收女性入学。20 世纪60 年代以后,美国妇女解放运动和妇女权利运动共同形成了“第二次女权运动”。这次运动也直接促使了长期以来被参众两院而搁置的“平等权利修正案”的通过,并得到全美绝大多数州的响应,其中就包括了普林斯顿大学所在的新泽西州。在声势浩大的女权运动的推动下,美国政府决定施行“肯定性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该计划以法规的形式要求高校在女性入学人数上必须达到一定标准,以此增强弱势群体的学习竞争力,消除教育领域长期以来的女性歧视。最终,迫使普林斯顿大学在招收女性学生和男女同校问题上做出改变,于1968 年正式开始招收女性学生,并在此后招生中将对女性的“招生配额制”视为“弱势补偿”的重要手段。
第三,消除贫困学生的入学障碍。1947 年,美国高等教育委员会发表了题为《为美国民主社会的高等教育》的报告,明确提出“使每一个公民都能得到鼓励,在他的天赋和能力范围内获得最大可能的正规或非正规的教育,消除所有影响人们教育机会的障碍”。[12]719普林斯顿大学的选拔性入学制度在发展变迁的过程中,逐步弱化对家庭背景、经济地位等因素的考量不仅是对全国性政策回应,同时为贫困学生入学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总体来看,“弱势补偿”理念推动了少数族裔、女性和贫困学生招生人数的扩大,提升了“弱势群体”的录取率,这成为普林斯顿大学选拔性入学制度持续革新的重要思想和实践基础。
二、推进“弱势补偿”:普林斯顿大学选拔性入学制度的发展历程
“平等主义”与“精英主义”的论战由最早可追溯至18 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时期,这种论战也同样存在于南北战争后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选拔性入学制度的历史发展,从精英主义时代以招收上流社会学生为主,再到尊重“平等主义”的诉求,直至20 世纪60 年代以后形成了“弱势补偿”的政策取向。
(一)精英主义的时代:选拔性入学制度的奠基时期
在美国常春藤盟校中,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被喻为美国高校的图腾,对美国文化及价值观的形成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 世纪末到20 世纪初属于美国社会发展进程中较为保守的阶段,这一阶段美国的工业化进程推动了商业巨头和垄断企业的形成,进一步加速了美国精英阶层的扩张,美国百万富翁的数量从1860 年的500 人左右急剧增长到1892 年的4000 多人。[12]720精英阶层的迅速增加,使得他们迫切需要更优质的高等教育服务,因此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美国私立高校之中。这一时期普林斯顿大学的选拔性入学制度处于奠基时期,主要以服务上流社会家庭为办学目的,呈现出较突出的精英主义和保守主义色彩。
第一,主要招收上流社会子弟,精英主义思想占据主导地位。19 世纪末,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以及普林斯顿大学都在美国商业领袖的巨额捐资下得到快速发展,其所招收的学生也大多来自商业和公民领袖等私立学校就读的精英家庭。普林斯顿大学第12 任牧师校长弗朗西斯·帕顿(Francis Landey Patten)在一次教员会议上表示“普林斯顿大学是富人的大学”。诸多具有牧师身份的校长,对于改革选拔性入学制度促进“入学公平”的意愿并不强烈。相反,牧师身份使得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更愿意招收能够为宗教扩大影响力带来效益的“富裕阶层”的子女,以寻求日渐式微的宗教文化在发展势头迅猛的工业文化中能够继续维系。当时的普林斯顿大学在很多方面像是一个排外的、自我封闭的私人俱乐部,学生主要来自美国小部分特权阶级。申请者通过普林斯顿大学自行组织的入学考试入学,入学考试难度不大,倘若一次未通过,还能反复参加考试直至合格;即使考试失利,也可通过其他“附加条件”入学。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少数族裔学生并不受欢迎,他们通常学业成绩较为突出,然而在“品性”“领导力”等非认知标准中处于劣势,故而被招生委员会拒之门外。
第二,逐步关注申请者的学业能力,选拔高质量生源。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发展历程上,宗教文化深刻影响着普林斯顿大学的选拔性入学政策的制定,忽视了大学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的提升。1902 年,伍德·威尔逊(Woodrow Wilson)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第13任校长,他是该校历史上第一位非牧师校长。威尔逊校长将严格的选拔性入学标准作为提升学术质量的前提,他执掌普林斯顿大学期间对于学业水平的重视程度大幅提升,这促使犹太裔申请者数量不断上升,犹太裔学生的学习基础普遍较好、学术发展潜力相对较高,其招收比例的增加显著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然而,犹太裔生源仅是缓慢扩增,原因是他们鲜有来自“绅士”家庭,这与普林斯顿大学招生偏向美国经济地位优势突出、社会阶层较高家庭的传统不一致。因此,普林斯顿大学并未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精英主义”选拔性入学制度仍致使广大非裔和犹太裔等处于社会底层的美国民众无法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就读,而提高学术质量则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上流社会家庭的子女。但这一时期,普林斯顿大学兼顾申请者的学业和非认知能力,选拔具有运动等特殊技能的与领导才能的学生,这在精英主义的时代无疑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也成为美国高校选拔录取制度形成的重要基础。
第三,将面试纳入选拔程序,在守护传统和提高生源质量之间寻求平衡。为了维护普林斯顿大学小规模、高质量的办学传统,1922 年学校董事会制定了限制招生规模的政策,其中对本科在校生人数设置了2000人的上限,新生入学人数控制在大约600 人左右,[13]同时给予了招生委员会“自由量度权”。时任招生委员会主任拉德克里夫·赫尔曼斯(Radcliffe Hermans)基于“自由量度权”设计了一套相对科学、全面的入学选拔程序。选拔程序不仅包括申请资料的独立审阅和委员会集体决策环节,最为重要的是创新性地将面试作为录取的过程之一,从面试中评价个人风度、行为,了解个人种族和宗教背景。1923 年1 月,耶鲁大学招生委员会的主席柯文(Kerwen)在造访普林斯顿大学后撰写了报告,描述分析了普林斯顿大学在提升质量和守护传统博弈中的科学决策,认为有效的措施就是将面试作为严格的选拔程序之一,通过对申请者进行全面了解及审核,不仅能够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充分考察,在面试交流过程中增进学生与校方的了解,也维护了高等教育选拔精英人才的传统,从而做出科学的招生选择。
(二)平等主义的诉求:选拔性入学制度的曲折发展时期
20 世纪30 年代,美国政府的收入增长了45%,人口数量也急剧增长,新出现了350 万个美国家庭,而人口增长带来的教育需求总量的增加使公立学校数量快速增长,美国中学的毛入学率也达到了66%的历史最高点。[14]在经济社会巨变以及公立学校高中毕业生持续增长的背景下,美国民众呼吁入学公平,要求平等的呼声愈发高涨,这对原先追求“精英主义”的选拔性入学制度产生了冲击。对此,普林斯顿大学选拔性入学制度在公立生源录取率、面试过程公平性以及入学标准参照等方面做出了调整,进入了曲折发展的时期。
第一,扩大公立中学招生,广泛选拔优质生源。精英主义时代下,普林斯顿大学的生源都较为单一,主要源自于美国北部的私立高中,且学生基本属于小部分特权阶层。1933 年,哈罗德·多兹(Harold W.Dodds)就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强调要加大对公立学校毕业生予以关注,以减少对私立高中生源的依赖。他创新性地提出“C 计划”以扩大学校的生源范围,增加来自公立学校的生源量,废弃了“所有申请者必须参加大学委员会考试”的要求。1952 年,普林斯顿大学招收的公立学校学生占比达到了44%,已经超过了耶鲁大学的41%,与最高的哈佛大学的48%相差4 个百分点。[15]302“C计划”的实施增强了普林斯顿大学生源的包容性,不仅吸引了来自美国西部和南部的生源,也从一些东部农村的公立中学吸引了学业基础好、发展潜力较大的学生,实现了扩大生源的目标。
第二,吸纳校友参与选拔,促进招生过程的公平性。二战结束后,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充斥着美国市场,数百万美国家庭跃入了中产阶层,越来越多的家庭能够负担起子女大学教育的费用,美国高等教育迎来了爆发式扩张的阶段。普林斯顿大学的申请者数量也随之急剧增加,如何在效率和公平之间把握平衡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1947 年普林斯顿大学决定对校友委员会进行重组,以充分发挥校友在生源选拔中的作用,提高申请选拔效率。普林斯顿大学广泛动员了50个校友联络点,邀请了400 多名校友协助招募和面试候选者。[16]时任校务委员会主席的布拉德·萨夫特(Brad Saft)提出,面试的主要目的不仅是评价学生,还可以让校友成为母校的使者,去吸引更多优秀的学生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员。[15]299这一时期公立中学毕业生人数增长较快,他们构成普林斯顿大学申请者的主体。1954 年,E·奥尔登·杜翰(E.Alden Dunham)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招生委员会主任,为应对新形势,他推动了招生制度的系列改革,提出将招生权力移交给招生委员会,且要求招生委员会必须与监视会成员、校友密切合作,同时强调教师在选拔性入学政策制定上的话语权,以确保招生过程中的民主参与,提升招生过程的公平性。
第三,参照标准化考试结果,对申请者做出客观评价。普林斯顿大学于1959 年成立了“教师专门委员会”(Faculty Subcommittee on Admission Policy and Criteria)负责制定招生政策与标准。“教师专门委员会”推行了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一是要求所有被录取学生的SAT语言成绩或数学成绩在780 分以上,且招生人员不能直接拒绝平均成绩在750 分以上的申请者;明确指出“少数学习成绩特别突出的申请者应该毫不犹豫地加以录取”。二是呼吁加强对学术标准的要求,同时要特别关照和优先录取学习潜力和能力突出的申请者。三是如果拒绝申请者,特别是成绩较好的申请者,要向“教师专门委员会”充分阐释理由并提供相应支撑材料。四是提高来自学校声誉较高的申请者的录取几率,加强校际合作。普林斯顿大学所实施的一揽子措施,既挽救了学校多年来录取率较低的境况,也从制度层面进一步规范了招生过程,有益于破除种族歧视对招生的影响。
(三)“弱势补偿”的形成:选拔性入学制度的成熟发展时期
20 世纪60 年代以后,美国总统肯尼迪(John F.Kennedy)在任期间,完善了对少数族裔权益的保障机制;同时,肯尼迪还签署了一项有关妇女权益的行政命令,并成立了妇女地位总统委员会(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旨在保障妇女权益。在此背景下,“弱势补偿”开始成为普林斯顿大学选拔性入学制度改革的重要政策取向,不仅扩大了少数族裔学生录取数量,也逐步将女性纳入招生范围,选拔性入学制度也趋于完善。
第一,提高生源的种族多样性。20 世纪60 年代中后期,普林斯顿大学招收的黑人学生十分有限,与这一时期美国社会追求种族平等的社会环境相矛盾。普林斯顿大学在新的发展愿景中提出了生源种族多样性及来源多样化的发展目标,希望在扩大黑人的招收上进行教育“补偿”,并为提高黑人的社会地位做出贡献,这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上的重要变革。1967 年,普林斯顿大学在报告中指出:“当前的局势使得提升黑人领导力的需求变得格外紧迫,招生委员会将公平地分析非传统背景学生的学业成绩报告,并考虑他们在考试成绩、学业记录和课外活动方面的特殊性;积极鼓励非传统背景学生申请就读,扩增其录取数量。”1968 年,普林斯顿大学黑人申请者达到143 名,较前一年增加了72.29%;到1970 年,以普林斯顿大学为代表的美国知名大学入学新生中,黑人数量已提高到10%,[17]黑人适龄青年的申请热情得到了极大的激发。
第二,将女性纳入招生范围。1966 年,普林斯顿大学历史性提出招收女生的议题,认为女性在选拔性入学中处于弱势地位,提出男女同校有利于扩大招生规模、丰富校园学术和文化生活,且能够塑造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极角色。为提高招收女生政策的科学性,普林斯顿大学面向在校师生及所在地区的高中生开展了关于“男女同校态度”的调查,在吸收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普林斯顿大学于1968 年9 月批准“男女同校教育”并于次年2 月正式开始接受女性申请者。到1970年,有超过2000 名女性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优秀候选人,[15]560这是普林斯顿大学在建校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突破。然而,由于招生政策在男女比率上倾向于男生,1970 年普林斯顿大学男性申请者录取率高达22%,而女性仅有14%。[15]561招生“既定比率”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的女性不论是在学业还是在社会技能上都需要比男性更加优秀。因此,女性入学政策被指“极具选择性的政策”,因为只有具备优良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女性才望达到普林斯顿大学苛刻的录取标准,但对于女性的“教育补偿”仍极大推动了选拔性入学的公平性。
三、追求“机会均等”:普林斯顿大学选拔性入学制度的实现机制
追求“机会均等”一直是普林斯顿大学选拔性入学制度关注的重点,通过构建考核机制、背景考察机制、非学业素质考评机制和多边互动机制,实现客观、全方位、多角度的评价学生,进而实现招生公平。
(一)构建完善的考核机制,确保选拔性入学的起点公平
选拔性入学的考核机制反映了招生过程的科学性和公平性,普林斯顿大学构建了由“大学入学考试——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组成的考核机制,对学生知识水平、学习基础、学习能力以及高中学业表现进行全面测评,确保对每位学生的评价是全面和公平的。普林斯顿大学的申请者通常需提交的标准化考试成绩,主要包括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merican College Test,简称ACT)和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简称SAT),两者是世界各国高中生申请美国高等院校入学资格及奖学金的学术能力参考指标,也是确保每位学生都能参与公平竞争的首要环节。
第一,依据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CT)判断申请者的学习基础、学习潜力甚至是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自律程度。ACT 考试由美国大学考试中心组实施,主要包括阅读、英语、数学、科学推理四门必考科目和一门写作选考科目。[18]普林斯顿大学借助申请者不同科目的考试情况,判断其学术能力和特长。具体来说,阅读成绩用于判断申请者的循证思维、归纳和总结能力;英语成绩用于判断申请者的英语表达能力和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等;数学成绩用于参考判断申请者的逻辑思维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其中,ACT 体系的科学推理考试综合性较强,考察内容整合了物理、化学、生物、语文和英语等具体内容,在形式上以循证和推理的形式出现,不仅测试了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更重要的是考察了学生的学习潜力、独立思考和综合运用知识等能力。
第二,依据SAT 学科测试(Subject Test)考查学生的推理能力、解决问题和逻辑思维能力。SAT 是20 世纪初在美国形成的最为重要的高校入学测试,主要通过考查学生在阅读、写作和数学三个领域的基本能力来测试学生的理解和推理能力。其中,SAT 学科测试(Subject Test)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在某科目方面特长的平台。普林斯顿大学对SAT 学科测试做出了明确要求,建议申请者至少提交2 门SAT 的学科测试成绩,且学校会依据申请者拟选择的意向专业,提出SAT 成绩参照的具体科目。例如,对于申请工程科学专业的学生,普林斯顿大学建议提交数学、物理或化学成绩,据此判断其未来专业学习的基础和潜能。
(二)创新背景考察机制,取代以家境优劣区别学生
普林斯顿大学自建校以来,对学生的背景审查一直是招生录取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在《民权法案》颁布以前,普林斯顿大学更加看中学生的家庭经济背景,倾向于从较富裕的精英家庭选拔学生。但随着“机会均等”与“弱势补偿”理念的演化,普林斯顿大学逐渐转变以往注重学生家庭背景的审查,变为主要根据申请者高中阶段GPA(Grade Point Average,简称GPA),了解学生高中学业表现;并通过申请者提供的中学报告、评分论文来综合考察学生的背景。对于学生学业胜任力的考察旨在预判学生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后胜任学业的能力,以及是否能够在学业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首先,依据申请者高中阶段平均学分绩点GPA 成绩判断其学业基础。普林斯顿大学参照高中阶段的GPA 考察申请者对高中阶段课程内容的理解和掌握程度,[19]判断其高中学习成绩的整体状况和未来学业发展趋势。如果申请者的GPA 较高,且处于稳定或持续上升的态势,招生人员会认为申请者在高中阶段的学业基础知识较扎实,其被录取的概率通常较大。此外,关注申请者是否获得促进非学术品质发展的训练。普林斯顿大学招生办公室提出,一流大学的学生不仅要学好专业知识,还必须要懂得专业以外的知识,今后要力争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仅靠智力难以预言今后人生成功与否,要给予非学术性品质足够的权重,这使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录取人员在遴选申请者时平衡各方利益,做出最公平的抉择。
其次,普林斯顿大学需要申请者提供“中学报告”,以此考察申请者的“高中教育背景”,包括高中课程体系、高中成绩单等。普林斯顿大学重视申请者高中课程设置的科学性及多样性,认为合理的课程体系是促进学生知识储备及学习能力发展的关键。为了选拔具备坚实学业知识基础的学生,以更好地应对未来学业上的挑战,普林斯顿大学重点对申请者的高中课程进行如下三方面的考察:一是看申请者是否持续学习数学和一门外语课程,且最好持续到高中的最后一年;二是认为申请者应修读多门自然科学领域的课程,且至少包括一年的物理课程,同时化学课程的修学情况也将纳入考察;三是已具备一年的微积分课程学习基础。
此外,普林斯顿大学会依据申请者高中阶段完成的“评分论文”判断其写作能力。普林斯顿大学招生主任卡伦·理查森(Karen Richardson)认为,独立研究能力、写作技能和语言技能是评判学生未来发展潜能的重要依据,普林斯顿大学至少要对申请者的写作能力有客观判断。[20]评分论文不仅可以帮助招生工作人员初步判断申请者的写作技巧,也能够预测申请者未来在学术上的书面表达能力以及可供挖掘的学业潜力。再者,语言成绩也是普林斯顿大学招生的重要标准之一。普林斯顿大学的招生面向全球学生,因此在语言技能上,要求母语非英语且高中阶段的教学语言是非英语的申请者,参加托福、雅思或皮尔逊等英语水平测试,[21]判断其英语听、说、读、写四方面的能力是否能够胜任未来的学习。以上对于申请者高中学习状况、写作和语言技能的判断,替代了原先对申请者家庭背景的审核,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在选拔过程中因家境优劣产生的不公平现象。
(三)建立非学业素质考评机制,为非学业素质突出者提供入学机会
非学业素质通常指学生在课外活动、社会活动、个人特长等方面所表现的基本素养。普林斯顿大学在招生时通过申请者提供的“艺术补充说明”(Optional Arts Supplement)和“普林斯顿补充说明”(Princeton Supplement)对其艺术才能和个人特质进行评估,给予在学业成绩上有所欠缺,但在非学业素质上较突出的学生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的机会,在公平和质量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点。
第一,根据申请者提交的“艺术补充说明”考察其艺术才能。“艺术补充说明”制度主要适用于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在艺术学习中,且能提供相关作品以支撑录取的申请者。例如,申请者在建筑、创意写作、舞蹈、音乐、戏剧或视觉艺术方面表现出色,并且希望将这些才华作为申请普林斯顿大学的重要支撑,则可以通过提交“艺术补充说明”来增加被录取的概率。选拔艺术才能突出的学生,一方面极大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另一方面也为不同特长的学生提供了平等的入学机会。
第二,通过“普林斯顿补充说明”考察申请者的个人特质及其与大学使命的匹配性。“普林斯顿补充说明”是一份申请者提交的文字陈述的材料,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申请者对拟申请专业的认知。通过差别化问题设置了解不同专业申请者对专业的兴趣及了解程度。二是申请者对参与的课外活动及已有工作经验的阐述。特别是在课外活动和工作中所产生的经验是否与普林斯顿大学所倡导的“社会服务”和“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理念相契合。三是针对未来大学生活回答开放式问题,使申请者可以在“普林斯顿补充说明”中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对未来校园生活的憧憬,从而进一步了解申请者的“生活观”和“价值观”。招收非学业素质突出的学生一直是普林斯顿大学提升校园活力和营造良好校园文化的重要手段,普林斯顿大学认为给予不同背景的学生在学校中充分表达自我会使每位成员受益,宽松良好的文化氛围也是促进学生学业成就的重要因素。
(四)强化多边互动机制,促进选拔性入学过程的公平性
招生过程的公平性是保障选拔性入学制度公平实施的重要环节和直接体现。普林斯顿大学通过建立“董事会—校友—教师”的多主体互动机制,既加强了对选拔性入学过程的有效监督,增强了过程的透明性;也加强了选拔过程中主客体的互动,主动引导校友和教师参与选拔性入学过程,打造了良性的招生互动机制以确保选拔过程公平。
第一,以董事会作为选拔性入学的最高决策和监督机构。董事会作为普林斯顿大学最高的权力机构,享有参与制定选拔性入学制度和监督选拔过程的权力。董事会首先将招生权力向校长授权,再由校长下放招生权力给分管大学行政服务和监督的副校长或是下放给普林斯顿大学共同体委员会(Council of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Community,简称CPUC),从而通过“授权式分权”的方式完成对选拔性入学的管理。[22]这种垂直分权方式使得董事会能够通过被授权人落实选拔性入学制度,充分发挥监督和调控的作用。
第二,吸纳校友参与选拔,提升选拔效率。普林斯顿大学自1947 年对校友委员会重组以来,充分给予校友组织参与大学治理的权力,鼓励校友组织成员参与招生选拔过程。普林斯顿大学在选择参与选拔招生的校友时,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标准:一是有一定的学术能力。参与入学选拔的校友需要有一定学历要求和文化水平以及较高的综合素质,以确保在面试环节能够充分展现普林斯顿大学的良好形象;二是工作领域广泛。选择来自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校友可以和怀有不同职业理想的学生进行深入交流,帮助学生了解该职业领域现状和发展前景;三是专业要求多元化。不同专业的校友形成强有力的具有专业多样性的群体,有利于满足普林斯顿大学对不同专业学生选拔的需求。此外,校友组织具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性,不依赖于学校行政管理体系,对校方的选拔过程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
第三,听取教师群体对招生政策的建议,提高选拔性入学制度的科学性。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会下设招生委员会,负责向校长或董事会就选拔性入学制度、招生程序和标准等方面提供参考意见。教授会不会直接参与选拔过程,但可以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影响普林斯顿大学的招生。教授会将教师们对专业招生的意见统一后,提交至校长办公室,校长会依据这些意见调整选拔性入学政策,从而提高选拔性入学制度的科学性。
四、公平与效率:普林斯顿大学选拔性入学制度对我国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启示
教育公平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基础。历经百年制度变迁,普林斯顿大学在选拔性入学制度中,探索了最大限度实现入学“机会均等”的路径,这对于我国从录取制度的角度推动教育公平有所启发。
第一,立足教育公平的社会历史性,构建中国特色的招生制度发展道路。教育公平从本质上看是教育追求与社会生活实际的统一,其内涵是一个历史范畴。教育公平在不同的国别和区域以及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及表现形式,这也决定了我国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具有基于自身国情的特殊性。自我国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以来,高考成绩所反映的学业成绩成为高校招生的基本依据。自此,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人才选拔制度初步确立,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 年的30%增长到了2021 年的57.8%,接受高等教育总人口已达2.4 亿人,我国也由此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23]伴随我国高等教育扩大招生,高等教育的普惠性已明显加强,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未来我国要进一步建立更加开放、多元的高等教育招生选拔体系,构建多元录取评价机制。一方面,以高考成绩作为大学招生的基本依据,确保招生标准的公平性。我国人口基数庞大,标准化考试是确保教育机会公平的首要环节,因此推进中国特色招生制度改革,首先要坚持高考制度的公平性。通过全国统一命题和统一考试的高考模式,取代现有的“统一+分省”考试模式,以优化命题资源,确保命题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减少地域差异。另一方面,继续探索基于高考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评价机制,[24]充分考查学生的学业成就、思想品德、审美能力、劳动实践等多方面素质,促进高考“选人”和“育人”等多重价值的实现。
第二,处理好“公平选才”与“科学选才”的问题,真正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已有研究表明,新高考制度改革中女性学生对新高考改革满意度低于男性学生,西部地区学生的满意度低于东部地区,乡镇城市学生的满意度也低于省会城市学生。[25]“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公平,但必须不断提高效率。如果不提高效率,所谓的公平只能是低层次的公平。”[26]因此,要处理好“公平选才”与“科学选才”的矛盾关系。一是通过“区域补偿”实现“公平选才”。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三号)》数据显示,我国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人口规模已超8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52%,[27]而中部地区与西部高校数量则占全国高校数量的53%,仅和东部地区高校数量大致持平,[28]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教育资源差异尤为严重。通过分省定额的指标配给方式,将招生计划向中西部倾斜,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以此兼顾考试公平与区域差异。同时,通过国家专项计划、学校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实行面向农村贫困地区的定向招生,增加农村学生优质高校录取比例。二是通过“差异化招生政策”实现“科学选才”。一方面,优化新高考改革,充分扩大学生的自主择业范围。当前,我国已有29 个省市施行了新高考改革,采用必选科目加选考科目的形式替代原有的文理分科。这种扩大学生专业选择的形式,体现了对学生知识和素质结构差异性的尊重,体现了因材施教理念,体现了考试内容与招生学校专业特点和考生学习性向的匹配,把全体学生在相同科目上的同质化竞争转换为特长科目的竞争,促进了实质上的教育公平。另一方面,允许有条件的高校施行“套餐式招生”[29]。“套餐式招生”是指高校依据校本特色、专业特色和学科特色,为不同专业提供不同的选考科目方案,而学生则根据自身的个性特长与优势针对性地选择考试科目,进而实现从选拔性考试转向“科学选才”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