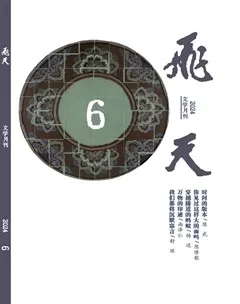万物的印迹
2024-05-31南泽仁
南泽仁
兽蹄鸟迹
侬布从小镇回来,经过磨房沟的时候,他望了一眼村口的平石板,上面坐着一位老人,孤伶的样子像另一块石头。
侬布大步朝平石板走去,裤脚掠起了一场细碎的风声,他迫切地想从那老人看他的眼光里识别出一些微妙的东西,或一眼就能识破他极有可能取代祭师的地位。快接近平石板时,侬布的脚步陡然就慢了下来,只见一只岩羊站在宽大明亮的石板上,它并不看侬布,只用一位老人平淡温和的眼神凝望着对岸的黑岩子,石坳里跳跃着几点灰白的光影。
侬布感到嗓子有些干涩,他咳嗽了一声,虚而不实地思想岩羊转过头来的时候,其实就是反穿着皮褂子的老人。岩羊在这时朝着黑岩子发出了鸟鸣般的呼唤,石坳里的灰白光影静止下来,接着,一群岩羊在回应它。岩羊开始在平石板上转着圈走动,坚硬的蹄子轻叩着石板发出了鼓点的回声,它纵身一跃消失在了平石板上。侬布随手折断路边一枝正在摆动的丑火草,拿到鼻尖嗅闻。那是一种被诅咒过的气味,他厌弃地将它丢在路边不回头地朝家走去。
两扇屋门敞开着,侬布轻轻地走进去,上了木楼梯。母亲背对着楼口在一扇窗下编织一匹氆氇,她在低声吟唱《平安歌》,一把胡桃木梭子穿过了黑白两色经线。侬布的心微微地颤了颤,他没有驚动母亲,只悄默地去歇坐在火塘边,好让她转头就看见孩子的归来本身就是一道光。母亲很快察觉到火塘边上的动静,看见儿子抱膝坐在火塘边,她惊讶地喊出了他的乳名,那也是村中一只流浪狗的名字。母亲解开盘在腰上的编织带,快速裹卷好氆氇走到侬布面前睁大眼睛确认他的归来。侬布扬起脸对母亲笑,他的笑脸很快就模糊在了母亲的眼睛里,母亲背过身去用袖口一把擦亮眼睛,然后赤着脚咚咚地踩响楼板为侬布熬茶,又在铜瓢里为他炒嫩玉米面,持续的香味使侬布感到了饥饿。这一路,侬布搭乘了吉普车、大货车,最后换乘了小四轮才辗转回到家,山路崎岖,快把他的肠肚心肺从口中颠出来了。侬布在茶汤里放入一坨酥油、一勺蜂蜜和两把炒面,开始团起一个糌粑来。母亲坐在一旁细细地端详着侬布,瘦了、黑了,眼神却更加坚定明亮了。她在等侬布详说这段日子去小镇寻马的事情。
侬布团好糌粑后,掰下一块,在手中捏出手印才送进口中慢慢地吃起来,吞咽的时候,他做出了痛苦的表情,心里却是十分香甜。母亲看见他的样子,赶忙端起茶碗递到他手中,好使他的喉咙无阻而顺畅起来。
两月前,侬布家丢失了子母骡马,找遍对河两岸三村,连个蹄印子都没有找见。有乡邻告诉侬布,在磨房沟遇见几个马贩子,赶着一群大大小小的骡马朝小镇上去了。侬布追随着线索到小镇上寻找,这一走就是数十天。此刻,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告诉母亲关于子母骡马的下落,于是他又不紧不慢地捏起一块糌粑送进口中吃起来,还没有等他做出干涩难咽的表情,母亲的拳头就已经递到了侬布的额头上,他顺势把自己当作一头好斗的牛犊,把头顶向母亲的拳头,一点点逼退她的拳头,火塘边就响起了母子俩欢快的笑声。
吃完整坨糌粑,侬布的讲述也有了头绪:“阿妈,您可知道,我找遍了小镇上的骡马交易市场、养马的人户,总之,能闻到骡马气味的地方我都到过了。”侬布说着,手指了指自己的脚,母亲就看见侬布磨破的鞋底露出了脚后跟,上面有一块结痂的伤疤同木柴上的螺纹一样结实,她的眼神立刻为此黯然了下来。侬布并不希望母亲因为心疼他而难过,他只是想表达出门找马,已尽了全部力量。
他继续往下说的时候,身体略微朝母亲倾斜了一点,语气徐缓。
“后来,我打听到距离小镇百里远的地方有个叫羊马的村庄,那里草山宽广,家家户户都养马。于是,我就找到羊马村,结交了一位养马的老汉,我利用自己的勤快帮忙他洗马、喂马,每天与他一道去放马。趁着马吃草,老汉打盹儿的时候,我朝着草原深处去寻马。就这样找了许久,我的脚步几乎踏遍了整个草原,涉过了很多条河流。不止一次地,我竟把河对岸的树木也当成了吃草的骡马,涉水过河,湿淋淋地站在树下,我就对着树大声呼唤子母骡马的名字,我是在自己的回声里逐步感到失望的。临走前的那个傍晚,我回到养马村,经过一户户人家门口,我一遍遍地向他们重复,我一直在寻找子母骡马,它们是我阿妈用七张氆氇毯子从一个赶马人那里换回来的。它们额上都有一块形似火焰的白印子,小骡马的颈脖上戴着一个氆氇项圈,上面缝缀着一朵染红的羊毛花,花心里藏着一枚小铜铃,奔跑时的声音格外响亮清脆……”
母亲听着微微蹙起眉头,母骡子坚韧,小骡子可爱,它们从不涉足泥潭,雪白的四蹄随时保持着清洁的样子在她心里越发生动明亮起来。
侬布稍微顿了顿,他平稳情绪后的讲述氛围远远超出了一位祭师所具有的智慧。
“可是,羊马村的人告诉我,羊马人的栅栏只关自己的牲畜,并且整个草原也不会留下来路不明的马蹄印。听到这些话,我的心彻底松懈了下来,并放弃了继续朝草原边缘去寻找的念头。我回到老汉家,他早知道了我寻马的事情,看到我进门时落寞的影子,他放下提起的茶壶,倒了一碗荞子酒来安慰我。我喝下一大口酒,告诉老人家,自己离开家乡已两月之久,寻不到马,明天就该返回了。当我说出‘家乡两个字的时候,不争气的眼睛就落下了大颗的热泪。老汉默默地看着我落泪,看着我端起茶碗喝茶般喝下荞子酒,我的身体渐渐轻飘起来,感觉进入了梦地。”
“老汉一声不响地起身去,抬出一张方桌摆放到灯下,我以为他这是要摆晚宴送别我。只见他捧出来一把麦面,均匀地撒在桌面上,随之拿出了一块手掌大的石盘,在轴心插入一根光滑的木杆,然后盘坐在了桌边。我有些酒醉的视线不稳定地看到老汉在朝我点头,示意我也坐到桌边去。看着他神秘的行动,我猜想这无疑是要进行一场问卜了,心中顿时升起了敬畏。我脚踩云朵般来到桌边,老汉让我捧起石盘,它其实是一个古老的纺轮,纺轮正面刻绘有古朴的鸟禽动物图案。老汉双手搓捻锤杆,我们一起放手,纺轮开始急速旋转,锤杆垂直着落在桌面上,刻绘在纺轮上的鸟禽动物全部飞腾起来,复活了一样。老汉的家人在这时关掉了我们头顶的电灯,屋子一霎陷入了黯黑里。老汉开始用方言念诵起祈请文来,那语气轻巧玲珑,像在月光下与万物轻声对话。我的手扶在桌边,感应到纺轮在微微振动,那绝不是因为我的害怕。纺轮转动得那样玄奥,似有一股细风在使它运行。纺轮逐渐缓慢下来的时候,老汉说了一声,开灯。我们头顶的灯就亮了。
“老汉移开纺锤,低头辨认锤杆留在麦面上的印迹。我看着那些凌乱的符号充满期待地望着老汉,我的心就要找到骡马了那般触动着感情。老汉看着看着,拧紧了眉头,他半晌才开口说,南方高山上的雪地里,有一群山雕重重飞落的痕迹,它们的停留和两匹骡马消失的时长来自同一件事……我听到这话,身体感到一阵寒冷,并打了一个激灵。”
母亲耐心地倾听着侬布的叙说,好奇、神秘,巴望的表情在她的脸上转变。听完侬布说出这个结果,她用宽大的袖口一把掩住了半张脸,掩住了她对这消息的惊讶和难过。侬布这颗漂泊无定的心,在这时才真正安稳了下来。窗外的天光在渐渐黯淡,火塘里的柴火在这场讲述中燃成了一堆赤红的炭火。母亲取来两只铜灯盏擦拭锃亮后,插入棉花灯芯,倒入熬化的酥油点燃,两朵小小火焰在闪烁。侬布仿佛看到远路上正有两匹子母骡马朝着微光走来,它们的蹄声从容而庄重。
这时,楼梯上响起了一阵七零八落的脚步声,那节奏打乱了侬布和阿妈静默。只见森布顶着一头蓬乱黑发的小脑袋显露在楼口,他明亮的大眼睛蓦地看到侬布,他打开手臂飞扑向侬布,把头埋在他的怀中一声声地喊阿哥。侬布用温热的大手抚摸他的脑袋,又在衣兜里摸索着,紧接着,他取出来一个绿色温热的石头作为礼物送给森布。森布接过,以为是一只圆润光滑的青蛙,吓得一把将它丢弃在楼板上。绿石头在地板上滚了几圈,发出了一块石头该有的坚硬挣扎。森布这才重新拾起它在手中把玩起来,又把它递到火塘边借着火光欣赏,它的绿是如此通透明亮,仿佛能看见它起伏的呼吸以及内里的脏腑。
火塘边煨煮的牛肉粥在扑哧扑哧地响,发着诱人的香。森布忘记了饥饿,他摆弄着绿石头,又把它放在楼板上,扶着它蹦跳,口里伴着孤单的蛙鸣。侬布沉浸在森布对这块绿石头的新鲜和好奇中,这是他在羊马村的溪流中捡拾到的,当时他以为自己踩死了一只青蛙,还尖叫着为它念出了一句真言。就在他回想这段经历时,母亲坚定有力的声音从火塘正上方传来:“你能再为两匹骡马的下落问卜一次吗?”
侬布转头去看母亲,她的样子像侬布对着老汉说出“家乡”两个字时一样失魂落魄。母亲知道侬布从小就对微妙世界充满了好奇,他只有一头牛犊那么高的时候,就背着口粮去学习用串珠占卜,后来又跟着玩伴去朵洛彝寨找毕摩学习烧羊扇骨占卜。母亲相信侬布一定也会从羊马老汉那儿学会了用纺锤占卜的本领。侬布在心里短而快地温习了一遍老汉教他的祈请文,他怕忘记,昨夜是在念诵中进入睡梦里的。
他看见自己回到了村口,离开的这些时日,平石板边长出了密集的树木,走近才看清是村庄里的人。他们一见到侬布就围拢上来喊他祭师。侬布还没有正式为谁包括自己推断过未来,他不敢轻易答应,但他还是为这个心驰的称呼整理着褴褛衣衫,他抬头就看见祭师的女儿思曼正从人众中朝他走来。思曼的眼光月亮般清冷,抑或还带着几分寒芒,侬布并不避让,是因为他的心里早为她打开了一片广阔的晴天。她走到侬布身边,自然地伸手去挽住侬布的手臂,侬布就闻到了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柏叶芳香,这加持了他内心的力量。人们更加地簇拥着他们,并不是祝福他们牵手站在一起,而是提出了占卜请求。侬布不借助任何器物,只数数自己手上的指节,就为一块土地卜算出了破土造房的吉日。他想在思曼面前显出自己的能力,便主动为新房大门卜算出了朝向,就在他要确切地指向南方的时候,他感到思曼的手像一把老鹰锁一样紧扣着他的行动。侬布试图掰开思曼的手,却不能使出一点力气,他这才发现自己在梦里一直是个旁观者。
儂布没有注重梦里的另一个自己,他沉浸在思曼留在梦里的柏叶馨香里,并不自主地扬起了嘴角,母亲就知道他是答应占卜了。
侬布从墙角抬出一张方桌,均匀地撒好麦面后,拿出母亲用来纺锤的纺轮和锤杆坐在桌边。母亲见状,握紧拳头杵在毡垫上准备起身与侬布一起运行纺锤。侬布抱歉地对母亲说,纺锤占卜的人要有文化,还是让森布来帮忙吧。母亲听到侬布的话,蹲坐回毡垫上,但知道森布要跟侬布一起占卜,她就对着森布露出了一个鼓励的笑。森布按照侬布的提示,蹲在桌边,小小的双手去捧起光滑的纺轮,他回望了母亲一眼,母亲对他点了点头后关闭了电灯,并用火钩刨起炭灰掩埋了最后一点光。他们的眼睛陷入了黑暗之中,窗外的月光散发着幽微的光照进屋子。侬布开始用羊马方言念诵祈请文,念完便观想起一子母骡马来,他的心中涌起了感动,虔诚,还有一些复杂的感情。念毕,侬布搓捻锤杆,锤杆并没有转动,直接倒在了桌上。侬布重又念了一遍,依然如此。这不符合侬布的心意,他因为局促,手感到了发麻,并把这消息传给火塘边的母亲。母亲根据自己的见识认为,在七日村庄用羊马方言说话,任谁也是听不懂的。于是母亲又从暗处传出说话声:“请用七日村的方言念诵祈请文吧。”侬布听到这声音,感觉是从另一个时空传来的,极具智慧和隐喻。他就用七日村的方言重新翻译祈请文,再次搓捻锤杆,然后和森布一起轻轻放手,纺轮带动锤杆落在桌面上快速地转动起来,他们听到锤杆在桌上沙沙地响动,窗外的风吹过杏树,也发着沙沙的动静。侬布似乎还听到,那声音是随着自己的心脉在动,过了好一阵,纺轮才慢慢减速下来。侬布请母亲开灯,并重新点燃火塘。森布因为紧张,狠劲地闭着眼,睫毛似要飞起的蛾子样抖动着。侬布对森布说:“阿弟,可以睁开眼睛了。”森布睁开眼,不看一眼麦面上的痕迹就跑进了母亲的怀抱里深藏起来。母亲见森布的额上起了一层细密的汗珠子,她就捋出袖口为他揩拭,并在额头上轻轻地印下一个亲吻来抚慰他的心灵。
侬布开始在暗淡的白炽灯下细细辨认着麦面上的印迹,那是几头野兽在雪地上对视、嘶鸣、争斗过的痕迹。侬布在一片混乱的迹象中运用起羊马老汉传授他辨别符号的口诀……他把所有印迹组织成一个词汇正要念出时,两盏酥油灯同时发出了呼哧一声响,只见两朵黑色的灯花蹿起两束幽蓝的火焰之后,就熄灭了。侬布在那刻看见了思曼的面容,就是他在村后水沿边喂马时,看到思曼采集了一大束祭祀用的新绿松柏枝叶迎面走来,朝着脸颊发红的侬布清浅一笑时的样子,侬布觉得那就是松柏枝盛开花朵的样子。母亲在熄灭的灯光中,惊讶地再次用手拍响裙袍,又用宽大的袖口捂住半张脸。她仿佛已经听到了占卜的结果,并深信不疑。侬布和森布一起看着母亲这一连贯的动作行为,他们怀疑她其实是识文断字的。
侬布收拾好桌子和纺锤,坐回火塘边,他不再说话,像倏然邃晓了占卜的本相那样沉默且庄重。
传布歌唱
天擦黑,半弯月亮就从东山顶上升起来了。
青麦从底楼抱回几捆干柴,往火塘里添进两根,就坐在火塘边捻羊绒。格荣盘坐在火塘上方的毡垫上看一本棕皮书,许久才翻过一页,那动静像一只鸟儿忽然从他手中放飞了。
阿布又一次转头去看楼口,楼板终于响起了起起落落的脚步声,伴着几声咳嗽和低语,他们一齐涌进锅庄屋在火塘边围坐起来。青麦把半瓢牛奶兑入一壶清茶里,然后提起茶壶去为劳顿了一天的牧人盛一碗热茶。格荣依旧在看书,并不听见家中有人来,又或是听见了,只是合上书前需要跟书里的人物作短暂道别。直到火塘边完全安静下来,他才抬头去打量围坐在火塘边的人们,他们笑盈盈地望着格荣。格荣的目光落在了一个年轻的牧马人脸上,他的手一把大梳子般插入了额上那片浓密的头发,他从指缝里窥探格荣的心意。格荣不说话,只上扬起嘴角对他。他才安心地将那片头发朝一边拂去,他还没有完全亮出宽阔黑亮的额头,就听见格荣开口说:“前天傍晚,我看见一只土拨鼠在对着你家院门磕头,你听到动静没有?”
牧马人的手顷刻抽离那片头发,散开在他惊愕不已的眼睛上。几个女人听到这话,呜一声抱在了一起。格荣细长的眼睛透着微妙的光,他像看着季节一样等待牧马人的回音。牧马人回过神来,他指着火塘起誓,再不去林中安置捕猎套索。格荣眼睛轻轻往下一掠,去问农场主:“听说,今年你家农场里的苹果丰收了,最大的苹果有多大?”
农场主从衣兜里取出手比画,一个红苹果就从衣兜口滚落出来,两个男孩扑上去抢那颗苹果,农场主一着急便提前说出:“这苹果是给举旗娃儿带的。”一个男孩就把那个红苹果传递到阿布的手上。阿布对着农场主答谢了一个欢喜的笑,并把那只散发着香气的苹果兜在了裙袍里。
火塘边响过一阵热闹的笑声后,人们又把眼光齐齐地投向了格荣。格荣这才郑重起身,取下一面旗子,那是一根用破开的岩斑竹棍夹起的一面发黄纸页,上面用黑墨印着一尊骑神授宝马的格萨尔王像。格荣将旗子双手递给阿布,阿布在大家恭敬的眼光中接过旗子举在手中。
格荣用方言中的连词“图裕”接住上文,开始讲述《格萨尔王之救爱妃》:
“太阳西斜的时候,格萨尔骑着神授宝马来到了斜卡乡阔吉牧场,一个少年赶着一群白云样饱满的绵羊朝河对岸的达孜村走去。格萨尔想向少年打听魔的住处,马儿通晓他的心意,一阵马蹄声惊起,他就赶上了羊群。少年看见来人佩剑持刀,威风凛凛,骑一匹枣骝马,是传说中的格萨尔王站在了眼前无疑,他停下脚步恭敬地喊道,尊敬的王。格萨尔一跃下马,双手握住一头绵羊的角夸赞少年放牧的绵羊肥美壮硕。少年的眼底露出了忧伤,好似他牧养的就是一群云朵那样。格萨尔感觉那是饥饿的神色,他让少年去生一堆火等待,少年一转身,格萨尔就宰杀了那头羊,然后与少年一同吃起烤羊肉来。少年的身体在逐渐温暖饱满,眼睛也跟着明亮快乐起来了。那只肥羊就快填满他们全部饥饿时,少年闲说起魔捉回来一个美丽女人的消息。就在这时,草原尽头一阵电闪雷鸣,一团黑云朝着草原上空飘来。少年忙起身说,王啊,一定是魔闻到烤羊肉的香气,对付我来了。你赶快走,我埋了羊的骨皮,假装哭泣,告知它丢了一只羊。”
火塘边无比安静,人们都紧着心弦,一个小男孩双手握拳,嗖一声从他母亲的裙袍里站起身来,仿佛他天生是一名将士,此刻他拥有一身的本领去守护格萨尔王一样。火塘边的人们都被他吸引过去了,并以为他一步就会跨进传唱故事里。阿布将手中的旗子抬高了一点,庄严氛围,男孩的脸一边红着一边坐回到母亲裙袍里。格荣对男孩竖起了拇指,男孩又转头去看阿布,他以为自己的勇敢来自阿布。
格荣没有中断讲述。
“格萨尔用最快的速度拼凑好他们吃剩下的羊骨头,铺盖上羊皮,他借少年的牧鞭对着羊皮轻轻一抽,那只羊一翻身复活了,咩咩地叫着跑进了羊群里。黑云就要逼近时,少年高声唱起了表达羊群如数归来的牧歌,那团黑云便消失了。
格萨尔随着羊群来到了达孜村,少年把一户高大院落指给格萨尔后,赶着羊群朝夕阳下的围栏走去。格萨尔站在院墙外,看见一个女人披散着半边头发在院中编织一匹黑白氆氇,他想向她打听爱妃的消息,刚要开口,女人唱起了一首歌……”
格荣在这时停顿下来,他轻轻地看了青麦一眼,青麦放下手中撕扯的羊绒,清了清嗓音,手掌托腮对着火塘低声唱出:
“阿拉阿拉是阿拉/塔拉乃是歌唱法/鱼儿游走河水在/河水你不用忧伤/见到冰凌融化时/鱼儿会游回你身旁/马儿走远骑士在/骑士你不用惆怅/见到春暖花开时/马儿会回到你身旁……”
唱完,青麦的脸颊被火光映得通红,她低垂眼帘,双手搓动纺锤嗖嗖地转动,一片羊绒就捻出了一根细长的白绒线。
格荣像站在城堡外的格萨尔王一样,他的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喜悦,他用轻柔的声音对着青麦唱出:
“我用阿拉来唱歌/我用塔拉来定调/雄鹰飞走岩石在/岩石你不用思念/微风吹绿草原时/雄鹰就会飞回来……”
阿布听到平常不爱言语的阿妈同阿爸用《格萨尔》说唱形式对话,她的小小内心就为他们的相爱涌动起了莫名的暖意。阿布看到火塘里的光逐渐变得迷蒙而遥远,阿妈伸出温软的手为阿布擦眼睛,火光就又重新明亮起来了。
格荣停止歌唱,他已进入讲述:
“院子里的女人听到格萨尔的声音,一把推开院门,她就看到了格萨爾仁慈的面孔和眉宇间的忧愁,她那双没有被散发遮挡的眼睛落下了一滴泪水。
“格萨尔高呼一声:江嘎佩布——
“他的枣骝马就走到了近旁,他牵住女人的手想即刻带她走,院中倏忽跑出来一个半人半魔的小孩唤她,阿妈。格萨尔听到这喊声惊得倒退了几步,女人把那小孩庇护在臂弯下,畏怯地看着格萨尔。格萨尔就知道了一切,他对魔的敌意在无限加深,只有除掉魔,他的心才能获得永久安宁。”
“女人把魔致命的弱点告诉了格萨尔,并引他藏匿在锅庄屋的房梁上。魔像一股风似的归来,他对女人说,今天心慌得很,快快把卦书拿来,我要占卜吉凶。女人知道那卦书能准确预卜,她就用半魔的那只脚踩踏卦书,使它沾染晦气消减灵力,才将书送到魔的手中。魔掐算指节,又去翻看卦书里对应的卦象,他陡然咆哮起来,一把将卦书丢进了火塘里。女人慌忙抢出没有被烧毁的部分,藏进了怀中。”
格荣停下讲述,他端起碗喝下一口奶茶,火塘边的人们也在这时轻松下来,他们互相打量着被故事贯注的神色,又不出声地笑笑。格荣压低声音对身旁的大叔说:“喇嘛们用来占卜的卦书,就是这女人从火塘里抢出,并流传下来的。”大叔像悟透了一样深深地点了点头。
格荣在这段讲述中并不对女人尊称王妃,心里也是忌讳她半魔的身体和灵魂,这也表明他对爱情持有简单洁净的愿望。青麦起身,提起茶壶去为火塘边的人们续茶,他们都在碗边捧起手,表达感谢。待青麦坐回火塘边,格荣才开始继续讲述:
“女人熬了一碗酥油酒端给魔,他大口喝下后就在火塘边呼呼大睡了。女人用很长的针脚缝缀好一件新氆氇穿在身上,魔孩见到了母亲即将离开的光景,他一把拉着母亲的衣角想要相随。魔孩对格萨尔的行动也有所察觉,他哭嚷着想要唤醒魔,然而魔从睡梦已经进入了另一个时空里。女人领着魔孩走出家门口,一边走一边反手朝楼板上撒豌豆。格萨尔看到一切妥帖,他拉弓对准魔的胸口射出一箭,魔嚎叫一声从梦里惊醒来,他的胸口突突地喷涌出猩红的热血,他站起身来想要施法,脚底却在撒满豌豆的楼板上滚来滚去无法站立,直到耗尽最后一滴血,他像一座山一样钝重垮塌在地。
格萨尔翻过房梁,吹响哨声,马儿很快迎上前来,他纵身跳上马背。格萨尔骑马到院外小路,见女人和魔孩在等他,她是想要带着魔孩一起离开。格萨尔对着女人半魔的眼睛露出厉色,就在女人有些犹豫,又想要坚持的时候,格萨尔一把拉起女人的手上马,一眨眼他们就到了达孜村对岸。格萨尔回头看见达孜村上空笼罩着瘴气,他的心感到一阵不安,他对女人说,我的箭忘记在房梁上了,你下马在此处等我。女人跳下马,跪地恳求格萨尔莫要伤害魔孩,并要他许下承诺。格萨尔急于返回,为了安住女人的心,他随口许诺不杀魔孩。我若违背,将永世不得投生。格萨尔说完便骑马朝达孜村赶去。
回到魔的院中,格萨尔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魔孩的身形忽然增长了数倍,他似算准格萨尔会返回来,正手握弓箭对准格萨尔的胸口,只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拉弓,格萨尔手中的短刀以比风还要快的速度刺中了魔孩的喉咙,他被那短刀钉在了身后最粗的那根梁柱上,口吐出半截鲜红的舌头。达孜村上空的黑云瞬间消散了,天空露出了七彩的云霞。”
格荣说着指了指压在梁柱之间的那片红布巾,说,那就是魔孩的舌头。火塘边遂响起一片唏嘘。牧人们的锅庄柱子上都压着一片红布巾,都知道是用来镇压邪气,却不知是这般来意。这时,窗口吹进来一阵细风,压在梁柱间的那片红布飘动了起来,阿布手中的旗子也窸窣地响了几声,仿佛是远古的传说对讲述者和倾听者的一次真实回应。
格荣从阿布手中收回旗子,人们知道今晚的讲述在格荣把旗子插回时就结束了。一个女人赶忙问:“阿哥格荣,女人知道格萨尔射死那魔孩了吗?”
格荣迟疑了片刻才说:“黑云散去的时候,女人身穿的氆氇随之消失,她恢复了王妃原本的模样,一切皆是心魔幻化而生。”女人听到这个回答,她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息,像是彻底放下了心中担忧的事情。
格荣说完,旗子已经插好了。农场主从火塘边起身,他一面对着格荣点头道别,一面退出围坐的人群,他要赶回农场看守几只新生的羔羊。格荣对他道了一声夜安!青麦点燃一把松光立在楼口上为他照亮,人们这才跟着陆续起身,意犹未尽地散去,楼口传回来几声高高低低的夜安!
青麦把那束松光放在火塘里的三脚架上,锅庄屋像白昼一样明亮。阿布开始吃苹果,吃出了清脆的声音。格荣继续翻看那本棕皮书,不时做着记录。阿布还不识字,只觉得它们像是一群黑蚁,正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去。格荣见阿布好奇,就让她知道了这些字是他在斜卡乡教书时搜集的《格萨尔王》传唱故事。
阿布识字后,没有翻动过这棕皮书,并不是阿布听完了里面的故事,而是每次格荣讲完一个故事,阿布都会返回故事里细细地探寻那些吸引她的光点,它们照亮了一个属于她的童话世界。
绵羊纳比被格萨尔捉去宰了,羊群陷入了混乱,纳比最好的几个伙伴吓得全身打颤,一身的绒毛像一件快要脱落的外衣。没有羊看见纳比的阿妈,它安静地退到了羊群身后,它流着泪,它嗅闻着青草,眼前浮现出纳比刚刚学会吃草时的欢喜样子,它一声声喊着阿妈,热突突的眼泪又一次打湿了它的眼睛。咩咩咩,它恍惚又听到了纳比在叫喊阿妈,它抬头看到羊群讓出了一条通道,纳比正从中奔跑而来,用冰凉的嘴唇亲吻它的脸颊,又歪着头轻轻摩挲它的身体,它感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纳比,它真的回来了,而且变得更加有情意了……
火塘里的松光在慢慢暗淡,木柴燃成了一堆雪白的灰屑。阿布把头枕在母亲的膝上,看着木窗外的月光,它在轻轻地描摹村庄、树木,还有果实的影子。
责任编辑 赵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