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金烂尾楼
2024-05-31黄奇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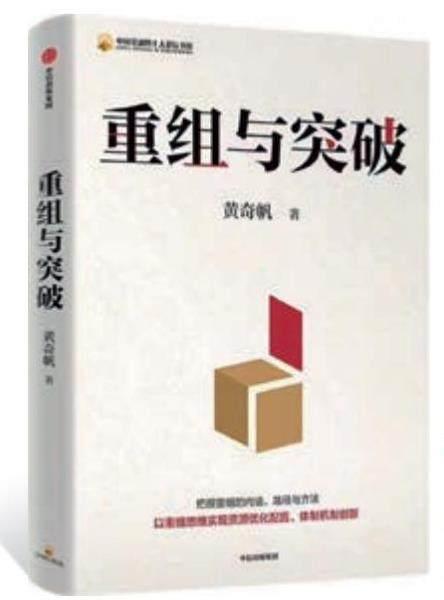
《重组与突破》
黄奇帆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4年4月
2001年10月12日,星期五,是我到任重庆市副市长的日子。当时的重庆,GDP(国内生产总值)仅1900多亿元,财政收入不到200亿元,正处在底子薄、矛盾多、任务重的发展“破冰期”。
一座烂尾楼,36次上访
重庆市委、市政府毗邻办公。报到当天,我路过市委大院,只见门口围着两三百人,黑压压一片,明显是上访的。把自己安顿好后,我顺口问了一句:“这些上访群众是从哪里来的?”马上有人回答:“是地铁中心花园的上访者。”
过了大约一个月,我正在单位办公,忽然听到市政府门口吵吵闹闹。一打听,还是地铁中心花园的上访者。事情已经过去一个月了,怎么还没解决?于是,我把当时分管稳定的办公厅副主任叫到办公室。他说:“这个地铁中心花园是1992年开建的房地产项目,包括高层住宅、写字楼和商铺。1997年,由于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成了烂尾楼,1000多户居民的钱套在里面。为了讨说法,随后四年里,他们36次到市委、市政府上访。市政府有关副市长、秘书长,大大小小的协调会开了不下20次,大家都感觉很棘手,拿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只能暂时把老百姓劝回家。可问题得不到解决,过一段时间老百姓又会来,如此反复,成了老大难。”
听了他的简要介绍,我初步判断,这是一起烂尾楼坏账造成的信访积案,就接着问:“按照你掌握的情况,这个项目是否存在严重的资金‘跑路,就是开发商有没有拿银行贷款去炒股、赌博,造成项目亏空?构不构成刑事案件?”这位同志回答:“开发投资量与实物量大体平衡,开发商的资金基本沉淀在项目上了。”
我当即决定:“你通知项目相关单位,包括银行、施工单位、房管局、重庆市建设委员会(简称市建委),还有法院、公安等方面的同志,今晚七点半开会,我先听听情况。”晚上我一进会议室,就看见房间里满满当当坐了70多个人。我之前只是说“相关单位”,怎么会有那么多相关单位?原来这件事前后协调了20多次,各方面的单位、部门都搅了进来,全成了相关单位。见状,我就让大家分别发言,报告地铁中心花园纠纷的来龙去脉。
原来,地铁中心花园的开发商是个小老板,玩的是“空手道”,其本身资本金不足,完全靠负债造楼。这个项目位于解放碑,建筑总面积近10万平方米。1992年,重庆工程造价比沿海地区低得多,每平方米仅2000多元,整个项目建完要花2亿多元。这个小老板是怎么运作的呢?
首先,征地动迁要补偿。他跟居民说:“暂时先不补偿,你们到亲戚朋友家里借住,等三年后房子造好了,我给你们分新房。三年过渡期里,我每年再给你们动迁费15%的高利息。”既然有钱拿,将来还能住新房,那么动迁居民自然乐意。而且,最初三年,大家确实拿到了高利息,所以相安无事。
其次,工程建設要花钱,他就用土地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银行答应贷给他1.64亿元,但要求利息必须是15%,而且放款之初就扣一年利息,即2400多万元,这就是俗称的“砍头债”。他饥不择食,当即答应,从银行拿到了1.4亿元。
最后,还差6000多万元,他就搞售房返租,承诺20%的回报率,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非法集资。于是,800多户购房者上了套。
等勉强凑够了2亿元,他就开工搞建设。但房子刚刚建到七八层时,建筑施工就用了1亿多元,而支付给动迁群众、售房返租户和银行的高利息,又用去几千万元,因此资金很快就见底了。1997年,银行见开发商连续两年都不能还本付息,遂起诉到法院,申请冻结资产。这样一来,开发商彻底变成了穷光蛋。老百姓的高利息没了着落,就找他算账。后来发现找他没用,就开始到政府上访。这个项目涉及1000多户老百姓,3000多人,每次只要出动10%,就是300多人,足够“包围”市政府了。因此,1998年以后,关于地铁中心花园的集访就没间断过。
其实,这件事性质很明确,就是项目业主骗了百姓、坑了银行。按照惯常思维,有两种办法。一是把开发商控制住,强制开发商还钱。但现在开发商没有钱,抓了也没用,死扣还是解不开。二是为了社会稳定,政府出钱兜底。但当年市级预算内财政收入还不到100亿元,财政本来就吃紧,没钱兜底。再说,政府有钱也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么做毫无道理。既然两条路都走不通,事情就僵住了。
打破僵局只能靠重组
我边听大家发言,边思考。地铁中心花园位于重庆最好的地段,如果10万平方米的房子能建造好,当时可以卖出4亿多元,是物有所值的。但问题是,开发商东拼西凑的2亿多元,其中一半以上付了各种高利息,现在还拖欠银行贷款本金1.64亿元、拆迁户补偿款和售房返租户购房款1.2亿元、施工单位工程款3000万元,加上1997年以后拖欠的银行利息和老百姓的利息、租金6000多万元,总共是约3.7亿元。同时,要建好房子,后续还得花6000万元。如果有人接手,总计需要投入4.3亿元,而房子卖完大体可以回收4亿多元,基本没的赚,哪有人肯干?
重组追求的是多方共赢,任何一方的利益严重受损,重组都推不动。具体到这个项目,战略重组者是“救生员”,即便不求赚大钱,起码也要有利可图。按照这样的逻辑,我提出了解决方案。
第一,银行贷款本金要收回,但高利息取消。面对空手套白狼的房地产商,银行违规放高利贷,搞的还是“砍头债”,本身运作就不规范,理应予以纠正。而且,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拍卖烂尾楼所得的款项要优先清偿老百姓和工程队的欠账。那样,银行1.64亿元贷款的本金清偿率可能低于10%。所以,我告诉银行,这个企业是个“要饭”的企业,如果重组,银行还有可能收回本金和国家法定的正常利息,就别指望收取高利息了。那天,银行接受了100%还本保息的方案。
第二,拖欠施工单位的3000万元工程款必须如数偿还,否则就会出现欠薪连环套。对此,施工单位当然满意。
第三,足额偿还老百姓的1.2元补偿款和购房款,但15%-20%的高利息不能作数。按照中央治理金融“三乱”的清偿政策,对售房返租户只能还本。拆迁户则按照补偿款加银行法定利息来清偿。因此,如果老百姓曾经有三年收到过15%-20%的利息,那么必须从补偿款里抵扣回来。总体上,归还老百姓的部分,连本带息大概是1亿元。
这三个减法算下来,项目债务就由3.7亿元“消肿”为2.1亿元。战略重组者只需支付2.1亿元就能拿到产权,之后再花6000多万元把房子建好,总成本也不过2.7亿元。而建好的房子出售时,应该可以卖到3亿-4亿元,总体上有利可图,重组者自然就有动力。
重组思路定了,下一步最重要的是找人接盘。按理说,处理烂尾楼有利可图,如果有民营企业老板愿意挑头,肯定首先让民营企业来做。但当时没人相信烂尾楼里有“黄金”,都认为这是“烫手山芋”,避之唯恐不及。
其实,这样一个矛盾多、问题复杂的烂摊子,也只有让国有企业来接盘才能“普度众生”。当时,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城投公司)的负责人就坐在我对面。我对他说:“这2.1亿元你出,明天就把楼盘接过去,春节前先还掉欠1000多户老百姓的1亿元。”这位负责人听了我的指令,看起来很惊讶,明显不愿意 这趟浑水。他说:“黄市长,你不了解情况”我打断他的话:“过去不了解,现在了解了,你按指令办就行了!”他本来还想说什么,听我这么一说,面对我这个新来的副市长,也不好再开口。短短一个多小时,我就做出这样的决定,现在回想,当时很多人肯定觉得这个决定是轻率的,甚至是荒唐的。
结局皆大欢喜
这件事是2001年11月中旬定下来的。在随后的一個多月里,欠老百姓的1亿元被陆续分发到了1000多户老百姓手中。2002年1月,我印象中正好是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闭幕的时候,地铁中心花园的拆迁户再一次来到市政府。他们送来了一块匾,感谢市政府帮他们讨回公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来访,这件事从此风平浪静。
后来的事情还有一点戏剧性。实际上,城投公司并没有真的掏出2.1亿元现金。清偿老百姓的1亿元,当然是城投公司直接掏腰包。然而,欠银行的8000多万元,由于债务主体变更了,银行对城投公司这个新业主很有信心,不急于马上收回贷款本金,甚至还愿意再借给城投公司几千万元,帮助其把楼建造好,城投公司可以等房屋销售变现以后再还钱给银行。拖欠建筑施工单位的3000万元工程款,由于施工单位不着急要钱,只要求继续承建工程,这样施工单位最后拿到的钱远不止3000万元。所以,城投公司真正需要立马掏腰包的,就是给老百姓的1亿元。城投公司通过处置这个烂尾楼项目,还赚了一笔钱。最后,这成了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
这样一个具体的重组操作,解决了一个久拖未决的信访积案,既给市委、市政府分了忧,又指挥国有投资平台救苦救难,表现出了应有的担当。其实,当时像地铁中心花园这样的烂尾楼,重庆主城就有70多座,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自此,国有企业开始介入烂尾楼处置。当看到国有企业处理了十多座烂尾楼后,民营企业也发现烂尾楼并不都是“烫手山芋”,处置过程中也有“黄金”,于是纷纷跟进,后来就连一些外资企业如摩根士丹利也介入进来。在此后的两三年里,重庆的烂尾楼通过债务重组被快速消化,最后变成了一处处亮丽的城市风景。
(本文摘自《重组与突破》;编辑:许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