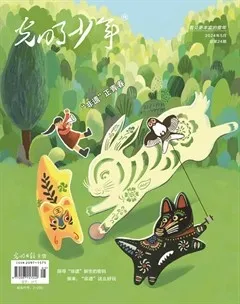从火柴的亮光中读小说
2024-05-31李浩
李浩
优秀的小说都是设计出来的,越是在外表上看起来天衣无缝、水到渠成的小说,在设计上用功尤深,只是创作者会同时致力于掩盖设计痕迹,仿若并不着力。“天然”或“浑然天成”的效果是大多数作家的追求,这需要经历不斷揣摩、掂对和精巧设计才能达到。
“深刻的思想不过是一腔废话,而风格和结构才是小说的精华”——被誉为“当代小说之王”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断语虽不乏片面,但我们或许不应因此舍弃它本有的深刻:它强调了艺术性的重要,强调了在文学中艺术的苛刻,它甚至部分地“大过了思想”。当我们在阅读中甚至是阅读之前就已大致知道了歌德、鲁迅或陀思妥耶夫的思想,为什么还会对即将展开的“这一本”兴致勃勃,甚至愿意再次阅读?吸引我们的,肯定不只是小说呈现的深刻思想,还有风格和结构这种“艺术性”的呈现。“设计”故事、会讲故事是作家的能力。优秀的作家会让它与自己的心性更匹配,更有个人面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站在瑞典学院演讲厅讲台上,发表了他的获奖演说。故事,是构成“小说”这一文本的首要要素之一,有些对故事性完全放弃的小说(或戏剧),在当时可能红极一时,但在历史中略远一点儿观看,会发现当它的开创性思想被其他新文本吸收之后,它的瞩目感便慢慢丧失,变得干瘪。
《卖火柴的小女孩》讲述的故事,吸引我们不断地替主人公操心:这个小女孩出现在冬夜,丢失了鞋子,没卖出一根火柴,家里和外面一样冷,父亲是个暴君,疼爱过自己的人早已离世;母亲消失,故事的光投在小女孩一人身上。作家为大地涂上了一层厚厚的雪,花被夺走了,塞进女孩手里的替代物是火柴,让她和她的死亡承担故事线的基本走向。
故事的高潮是女孩一无所有地死去,是她的外婆用亲情的幻影将她带走——这个情节有了,故事的基本面貌就有了。作家这样设计:一无所有的小女孩,在这个人世间的“需要”有哪些?她有多少“需要”就可以划亮多少根火柴。她需要温饱,渴望友情,有一个脆弱而可怜的“公主梦”,希望有人爱……我们想想,小女孩划亮过多少根火柴?第一次看到的是什么,第二次、第三次又看到什么?更换一下顺序是否可以?譬如,第一根火柴划亮看到的是圣诞树,第二根火柴划亮看到的是烧鹅,带给我们的感受如何?假如,我们让她第一根火柴划亮就见到外婆呢?既然她冷,为什么没有让她多划几根火柴,依次看到围巾、棉鞋、大衣,篝火、火炉……
我曾反复地、以游戏的方式掂对,发现作品中的火柴划亮是有顺序的,是不能轻易移位的:第一根火柴就得“见到”蜡烛和火炉,小女孩希望有温暖的存在;第二根火柴就得“看到”塞满水果的烧鹅,它不能和第一根火柴的“看见”互换,因为温和饱之间也有层次,而一般来说一旦解决了饱的问题,人就会对温度的感觉变得不那么敏感,尤其是寒冷;第三根,圣诞树,它出现在第一根或者第二根的前面是不合适的,因为人的需求层次问题,没有谁会在温饱得不到的时候有强烈的“别的念想”,因此它出现于第三根火柴划亮时最合适;第四根,亲情,是小女孩最强烈的情感需求,如果它出现在前面任何一处,都会造成后面一根火柴划亮后的“看见”失去效果,会把刚刚提至高点的阅读情绪拉下来,从而有种塌陷感。
假如我们用同样的拆解游戏,来拆解《老人与海》《小镇来了马戏团》《追风筝的人》乃至一些古老的神话故事《荷马史诗》等,会发现它们或多或少是“遵循”这一规律的,尽管各自做出了种种变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所谓规律性,恰恰是因为阅读者的审美期待和阅读心理的“规约”在起作用。增一寸太长,减一寸太短……小说的阅读要体味情节的巧妙。在火柴的亮光中,看见情节“设计”之美,读出故事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