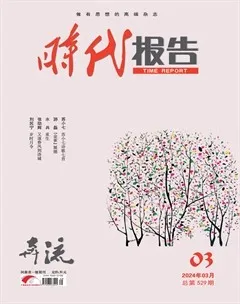冰冻记
2024-05-28季大相


一场大雪过后,接踵而至是雪后寒,气温骤降至零下八九摄氏度。人一出门,寒气迎面来袭,连打几个冷战,弓着腰,蜷缩着脖子,在结冰湿滑的路面上挪步前行,看那些小心翼翼像企鹅般笨拙的模样,我忍不住地暗自窃笑,全然忘了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分子。几乎每个人都在抱怨天太冷了,给生活和出行带来了诸多不便。偶尔在路边见到一两个不知是谁即兴堆积的雪人,虽然在鼻子、眼睛、嘴巴等造型方面富有创意,花枝招展,但与我儿时堆积的、所见的雪人相比,还是缺少了点质朴的、传神的灵气。不见了孩子们打雪仗追逐的踪影、戏嬉的喧嚣声,那厚厚的积雪也稍显落寞。儿时记忆里的冬天格外寒冷,在某个适宜的节点,似影视片中的慢镜头般回放,从中咀嚼当年辛酸与快乐交织的难忘滋味。
我对冰冻的记忆始于5岁。那年刚入冬,一阵寒风掠过,河床便已结上一层冰,冰面厚度不一,朝阳的薄一点,背阴的厚一点。我家门前的大池塘,也因此覆盖上一床冰被,上白下暗,水流静止,不见一丝微澜。人在吐纳之间,一条像流云、像袅袅炊烟的雾状抛物线,从口中缭绕发散开去。“明日最低气温,零下十摄氏度……”小广播里的播音员正在用一口纯正的普通话播报着天气预报,提醒人们气温下降,注意防寒保暖。可谁也没有在意,更不会放在心上,年复一年,低温、超低温天气已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人体产生了天然的抗寒免疫力。那天早饭后,我们几个小伙伴像往日一样,结伴到池塘的冰面上滑冰,前跑后逐,嘻笑声伴着呐喊声,似乎把冰层也吵醒了,卖力地配合。即使阳光明媚,它也没有丝毫融化的迹象。突然,阿强恶作剧地从背后搂抱住我的腰,接着又顺势用力推送出来,使我身体瞬间失去控制,像箭矢一样弹射出去。只听“咚”的一声,我只觉得眼前一黑,寒流片刻浸透全身。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已躺卧在床上。母亲告诉我,我跌落进了码头边敲碎冰层用来淘洗的冰窟窿,幸亏路过的青大伯跳入冰窟窿冒死相救,我才逃过一劫。
在冰面上敲挖出三角形对称的三个洞窝,玩小球进窝的游戏,那才叫真正的刺激。玻璃球击打玻璃球,看到对方的玻璃球飞旋着滚出去,开心地大笑,胜利的、得意的、幸灾乐祸的,童真的表情没有一丝遮掩。落下风一方狼狈地撵着球跑,没有无奈或窘态,只有乐此不疲。最开心的事,莫过于抓冻鱼。冻鱼就是河内那些被冻伤、冻死的鱼。早晨去河边转悠,经常会看到冰层下面被冻僵的鱼,拿锹锨或斧锤等工具砸开冰层,取出被冰冻住的鱼。起初以为冻鱼都是死鱼,后来发现摆放一段时间,有的被冻晕过去的鱼还会苏醒过来。不论冻死的鱼,或是因冻晕又复活的鱼,母亲都一个程序不少地刮鳞、剖腹、洗净,炊烟袅袅中,不一会儿,厨房里就飘出浓浓的鱼香味,闻一闻,就得使劲地吞咽,否则口水会抑制不住地流出嘴巴。生产队会挑个农闲的日子,组织劳力打冻鱼。打冻鱼的人携带着榔头、锤子、抄网等工具,在队长的带领下来到集体鱼塘,选个适中位置,挥起榔头或锤子砸冰,发出“啪啪”的声响,震得冰床颤抖,直至形成一个方圆一米左右的坑塘才作罢。这时,有人拿起抄网插入水中,接着一个抄捞动作将抄网平端出水,围观的人群顿时沸腾起来,网兜里掺杂着碎冰的几条鱼在无力地扭动,严寒使它们失去了往日的活力。“停!”——随着队长的口令,捞鱼结束,结果生产队里的每家每户都分到了鱼,人人脸上都挂着开心的笑容。冰层砸个洞就能捞到鱼?我充满好奇。事后,我缠着负责持抄网捞鱼的包二叔,问他为什么在冰面上砸个洞就能捞到鱼。他告诉我,榔头砸冰发出“啪啪”的震动声响传到河底,使潜伏在那里的鱼误以为春暖花开、冰冻融化的季节来临,纷纷向洞口游过来,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殊不知,这是它们的死亡陷阱。虽然包二叔的表述轻描淡写,但从神情中可以看出他对自己打冻鱼的技能很自信,面颊上透溢出满满的获得感。
腌腊味,是冬日里最诱人的风景。有人家早早的宰杀了猪、羊、鸡、鹅、鸭、鱼,加入盐及佐料腌制后,挂在绳子上晾晒,天寒地冻,一点儿也不用担心腐烂变质。腌出的腊味是过年餐桌上的大菜,平常是舍不得吃的,但孩子们经受不住诱惑,常常趁大人们不注意时偷割一片肉或猪肝,放进火盆里或去干涸的河沟里生堆火烤了吃,那香喷喷的味道,至今仍口舌生津。现在,进入冬腊月,家家户户就开始忙着腌腊味,没时间或自己不想动手的,可以去专门销售咸鱼、咸肉等腊味的门市选购,价格公道实惠。过去腊味过了春天就会变味,如今有了冰箱等冷藏条件,可以四季吃。就拿五花咸肉来说,切点肉片下锅与米、菜混煮,不用再添加其他佐料,已是诱人味蕾、久吃不腻的美食。有人专门炕菜饭锅巴卖,还是一项收入可观的行当。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谈起偷割咸肉烧烤的往事,相互揭短打趣之余,亦是感慨不已,坦言今日晾晒绳上挂满各种腊味的场景,乃是当年做梦也想不到的境况。
一场大雨来袭,在寒冷的气温肆虐下,雨水先是从屋面上汇成小溪流向下翻滚,连绵不断,滚着滚着,水滴在檐口处凝结,冒着寒气探头出门去张望,不知不觉间,屋檐下已倒悬着一溜排的冰棱,圆锥体形状,又像一根根胡萝卜,晶莹剔透,闪耀着若隐若现的光泽,无比壮观瑰丽。常常有孩子会上前掰下根冰棱,当冰棍伸入口中,牙齿咬嚼发出的“咔咔”声,听着就让人汗毛倒竖,寒气袭体。下雪天,除了打雪仗、堆雪人外,支筐捕鸟是我最爱干的一件事。漫漫雪花覆盖大地,银装素裹,地上的小动物、天上的飞鸟,都在为寻找食物发愁。我印象最深的是10岁那年,腊月里的第一场雪,鹅毛般飘洒了一天一夜,雪停了,积雪有一米多深,雪后寒的天气格外得冷,人们都围拢在火盆边烤火取暖。这时,我却逆行而出,在门前清理出一塊空地,拿出家里那只早就备好的柳筐,筐底剜了个碗口大小的洞,由一块破布大针脚线码托着,将筐体倒扣,取一根长约50cm左右、拇指粗细的竹竿支撑起筐体的前端,后端着地,呈前高后低状。往筐下的空地上撒点儿稻谷或麦子,然后拖拽着系在竹竿上的细麻绳回屋,虚掩上门,顺门缝张望筐的方向。几十只小麻雀在不远处蹦跳着、叽叽喳喳地叫唤着,似乎对筐下的食物熟视无睹。在焦急地等待中,终于有一只小麻雀钻进筐下,望了望,又跳出筐外,过了片刻,它又钻进去,开始啄食,接着二只、三只、四只……有的进去,有的又出来,总体保持在十只左右。说时迟、那时快,我手拉住绳头猛力一拽,“叭”的一声,筐沿倒扣扑下,觅食的麻雀还未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已被罩在筐体内,尚在筐体外侧的麻雀受此惊吓,一哄而散。我拉开门,抓着一只网兜走到筐前,揭开原为底、现为上的洞口上的布,伸手进去逮麻雀,一只又一只地放进网兜内,麻雀惊恐地叫着,有的拍打着翅膀试图从网兜的孔眼里钻出来。可任它如何挣扎,均徒劳无功。数一数,有八九只。接着,我又将柳筐重新支撑起来,再撒点儿粮,拖拽麻绳回屋,又将先前的程序重新操作了一番。顺着门缝向外望啊望、等啊等,那群落回地面的麻雀,不停地向柳筐这边张望,有的还沿着筐体上蹿下跳,但就是不往筐下钻,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饥肠辘辘的麻雀终是未经受住食物的诱惑,先进去二三只,啄了几粒粮又出来,反复试探了几次,叽叽喳喳的吵闹声又像是招呼声:“快来呀,这里有吃的。”就在我耐心尽失,准备放弃的时候,终于有十几只胆大的麻雀走进筐下,我喜不自禁,瞅准时机,再次拉拽麻绳,随着“叭”的声响,正在争食的麻雀被“一筐打尽”。筐体外的麻雀受此惊吓,尽皆飞去,没有一只落地。我寻思,连续涉险两次,估计今天不会再有麻雀来了。虽是这么想的,但仍心存侥幸,再次将柳筐支起,一直等到傍晚,也没见到麻雀光顾。
当年的野鸡、野兔等飞禽走兽的数量特别多,说是随处可见,绝不是夸张。早晨出门去圩堆、田野、竹园等处去拾粪,经常看到被冻死的鸟儿、小动物,包括野鸡、野兔等,可从没见到有人把这些冻死的小动物捡拾回家。一次,我在东大圩的河坡旁发现一只野兔,膘肥体壮,伸手摸摸,还有点热气,看来是刚死不久。我捡拾起这只兔子放进粪篓里,上下盖了点枯草遮挡,选择走小路匆匆回家。到家后,我拎着野兔走到母亲面前,兴奋地叫道:“妈,我捡到了一只大兔子。”母亲看了一眼说:“拿到竹园里去埋掉。”我忙解释道:“你摸摸,刚冻死的,身上还有热气呢!”母亲回了一句:“死东西不能吃,吃了会生病。”我急眼了,有点儿生气地说:“陷阱、铁夹子逮的野鸡、野兔和小鸟,早就冻得硬梆梆的,不是照样下锅吃。为什么这只刚冻死的兔子就不能吃。”结果,这只兔子还是被父亲拿到竹园里给埋掉了。明明过的是吃上顿愁下顿的困难日子,为什么放着这些冻死的小动物不吃。父亲说,捕捉的小动物都是活物,而这些冻死的小动物,是不是病死的呢,谁能保证它们身上没有病菌,如果有病菌传染给人,是不是很危险?
冬藏,我给予它一个定义,就是把自己躲起来、猫起来,也许这是片面、狭隘的认知,但日常所见、所触,恰是与躲、猫紧密关联。首要的当是贮物,在锅膛口挖一个地窖,将收获上来的萝卜、山芋、黄芽菜等掺杂些麦穰子封盖住,再借助生火做饭产生的温度,可使地窖里窖藏的萝卜、山芋、黄芽菜等免遭冻害,保持新鲜,可以吃到来年初夏。地里的庄稼避寒,则又是另一番光景。冰碴碴的日子,队里组织劳力捞河塘泥,黎明时分,队长吹响哨子,接着吆喝:“挑河泥了,带好担子和合子。”社员们闻哨而起,挑着担子、夹着合子(一种木制的,用于撂河泥的工具)前往指定地点集合,简单地分工之后,开始挑河泥下地铺盖麦苗、油菜苗。大姐12岁就参加生产队里的挑河泥劳动,穿着破棉衣、破鞋子,在寒风里冻得牙齿打战。几个来回奔波下来,又浑身冒火,脱掉棉袄和鞋子,赤脚挑河泥下地,空担子返回。几天过后,地里的麦苗、油菜苗被铺盖上了一层黑乎乎的河塘泥,好比盖上了一床棉被,它们躲藏在暖暖的被窝里养精蓄锐,静等来年春暖花开,苏醒生长。河泥还是有机肥料,给庄稼提供养分。大姐稚嫩的肩膀先是被扁担磨红、磨破、结痂,与脚底板一起,堆积厚厚的一层茧。几十年过去了,这些老茧依然清晰可见,见证着那段岁月的辛酸与艰难。
那时农村人家虽然穷,用不起厚棉被,但在床与席子之间铺垫一层厚厚的稻草,也能起到很好的保暖效果。每到入冬时节,母亲就会将事先预存的稻草拿到太阳底下晒一晒,然后铺到床上当床垫,一股稻草的清香,软绵绵的,人躺在上面既舒适又暖和。过不了多久,铺垫的稻草被身子压得板结,保暖和舒适效果大打折扣。某个晚上,我走进房间,发现床上铺垫的稻草更换了,又恢复保暖又舒适的状态。一个冬季,母亲总会给我更换三四次铺垫的稻草,母爱的暖流陪伴我度过那一个个寒冷的日子,迎接春暖花开的时光。冰冻天里,人也是需要躲藏起来的,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群体,需要睡懒觉、捂被窝。即使起床,也要穿得暖和和的,不能受凉感冒。记得庄上有位患有哮喘病的老人,因穿羊绒大衣被人奚落,索性脱甩到一边,以示身强体壮。结果受了风寒,当晚咳嗽不止,一口痰堵住嗓子眼,没有吸痰器急救,在送医途中不幸离世。晒暖,是乡村独有的风景。每家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草垛,冬闲时光,人们三五成群地躺靠在背风向阳的草垛旁,侃大山、打扑克、下象棋,吃几粒炒黄豆,磕几粒瓜子,有的人干脆傍依在干草上睡觉。
小孩子生性好动,在冰冻面前不躲不藏,不遮不掩,释放天性,哪怕是泪,依然只见坚强,没有怯懦。苦难锻炼人的意志,没有抱怨,直面相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故事,值得记录,值得铭记。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学校都是土草房,墙体裂开一道道豁口,呼号的寒风钻入室内,肆无忌惮地摄取温度,室内室外几乎没有多大的温差。人坐在教室内,彻骨地冷,通体冰凉,好似置身冰窖。一间教室里几十名学生,都清一色地穿着破旧的棉袄、棉裤。脚穿破单鞋,家庭条件好一点儿的,在鞋子里塞些棉絮保暖。那时每一个学生的手上、脚上、脸上、耳朵上都生有冻疮,先是红红的、痒痒的小疙瘩,如不及时呵护恢复,冻疮会破溃、流脓,苦不堪言。有的人脚上冻疮破溃严重,导致皮肤与鞋帮子粘连,脱鞋子会撕下一层皮来,脚后跟血淋淋的。有的人脚后跟裂口,像婴儿小嘴巴一样,走路一张一合的,看得人心惊肉跳。有一年,我手上生了冻疮,起初是又红又痒的小疙瘩,并没有在意,更没有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后来手面肿得越来越大,痒得也越来越厉害,一次实在忍不住而多挠了几下,疮面被挠破,先是流血,后来又流脓,药膏、民间偏方,尝试了多种方法,效果甚微,一直到来年开春天气转暖才痊愈,疮面却无可避免地留下一块疤痕。
冬天的课堂上,老师一般都会安排二三次跺脚搓手活动。记得老师会突然放下手中的粉笔,开口问一句“冷不冷啊?”接下来就是“大家动动。”得到老师的口令,教室里立马响起“嘭嘭”“咚咚”的双脚跺地声、双手揉搓的摩擦声和哈气声,每个人都十分卖力地运动,以此驱寒取暖。冷冻天,自然也是各种富有创意的游戏登场展示的时机。下课铃声一响,同学们一窝蜂地冲出教室,三五人聚拢在一起,踢毽子、跳绳子、弹玻璃球、斗鸡,还有多人分成两组挨着墙脚边挤扛,呐喊着口号“一二一、一二一”,这些活动既娱乐,关键还能取暖。有的游戏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比如斗鸡,某同学一使劲,将另一同学挑翻在地,落败的那一方先是尴尬地笑,转眼间又痛苦地呻吟起来,往往是胳膊或小腿骨折。胳膊骨折打个石膏,挂根吊带仍能坚持到校上课。如是腿部骨折,则要休养几个月,直接影响学业。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句诗描述得很形象、很到位,应景农村的环境。冬天,草木枯萎,树上的枯枝随风折断而落,我和小伙伴们挎着篮子去圩堆上拾柴禾,去街上的小吃部卖点零用钱。拾柴禾的间隙,最开心莫过于“烧荒”,就是在田埂上或河沟边点燃枯草败叶,很快就蔓延成一条翻腾的火龙,既借着火势取暖,又有恶作剧的快感。“烧荒”过后,枯草变成了一堆堆黑色的灰烬,接着又抓起灰来互相涂抹,一番折腾下来,个个都成了黑脸儿“包公”。原以为枯草烧了,来年就不会再生了。当来年春天小草如约而至地冒出嫩绿的芽,才知“烧荒”伤不了根,春风一吹,那草儿又是一个生命的轮回。我曾经傻傻地想过,草儿枯死了来年又发芽,人终老离世,会不会又活过来呢?也曾坚定地相信,死去的人在另一个地方又复活了。儿时的奇思妙想,真堪比科幻大片有想象力。
不知不覺,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忙碌、喧嚣的乡村也冷落下来,变得清静而落寞。当年的稚子如今已两鬃风霜,额头刻下深深地岁月印记。回想那冰冻、那人、那事,消逝的时光永不复返,唯有那淡淡的乡愁,尚有余温。
作者简介:
季大相,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协第二批“定点深入生活”签约作家,淮安市洪泽区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