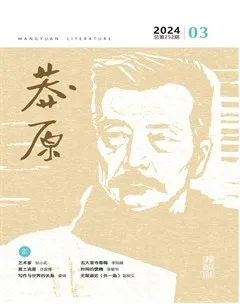秋天的蝉在叫
2024-05-19张涯舞
张涯舞
1.悬棺
一连二十多天的雨,山上的红叶便开始凋零。秋天应有的丰饶正悄然离去。
高岗似乎也走到了自己的晚秋。整个村子充斥着潮湿衰败的气息。
整个暑假,锦瑟都在四处奔波调查各类崖葬和洞葬。她的笔记本里这样写道:在贵州全境,北方的崖葬分布较多,而南方多洞葬。大体崖葬属于长江水系,而洞葬属于珠江水系。它们的起源,也是溯江而上。
高岗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发现的。
高岗是一个侗寨,方圆数十里,还有苗、水、壮、瑶等十几个村寨星罗棋布。村子里有一座鼓樓,现在空无一人,火塘里有烧过的木头,灰烬中还有一个被烧去一半的香烟壳,图案是黄果树瀑布。风雨桥上有一个闭目养神的老人。一只白色的胡子拉碴的杂种下司狗,也趴在桥板上打瞌睡。
锦瑟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回到车旁:我们直接上山吧。
不是要在这住一晚吗?
算了,还是去山上住吧。
我从后备箱拿出背包,锁好车门。
灰色的云层被风吹淡了,似乎要放晴。石板铺就的小路已经干了一半,潮湿的是被落叶覆盖的地方。淡淡的阳光似乎穿不透树荫,一只蝉叫得绝望。
看到月潭观的时候我有点震惊。
这几年陪着锦瑟穿山越岭,也看到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秘境。当它那色彩斑斓的山门突然从一片高大的阔叶林中显现,还是有惊艳之感。锦瑟扔了背包,抓起相机就冲了过去。
山门为重檐式样,以红色为主,上面两个黑色楷书大字:月潭。背阴处青苔苍翠,斑驳而古朴。此时残阳从中间拱门斜射而出,锦瑟回过头,她的脸半明半暗,侧逆光中显得蓬勃,就像多次在我相机中定格的瞬间,也许数年之后,我只能在记忆中重温。
迎接的道人四十左右的年龄,穿一身深蓝色长袍,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面容清癯。
请问是马道长吗?
两位是?
哦,您好,我是李馆长介绍来的,他说昨天给您打过电话。锦瑟递过名片。
原来是鹿女士,这位是?
哦,我是她的助手。这么多年,我的身份是助手、司机、摄影师、背篼、保镖、打手,或者研究员。我伸出右手,道长的手偏冷,干燥有力。
请进请进。
马道长陪着我们参观了一圈,道观不大,山门之后是一个青石板铺就的院子,青草从石缝中长出,两个石质水缸,漂浮着颓败的睡莲残叶,此外院子空无一物。然后上台阶,便是三清殿,供奉着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雕塑比例失调,头大身子小,配色庸俗,表情呆滞,不过也有乡野的神秘。穿过三清殿,是玉皇殿。二者之间也有一个院子,同样是长有青草的石板,左右各有三间厢房。
我对于这些道观或寺院并没多大兴趣,其实中国大多数老百姓对于这些神仙也没什么讲究,管他供的是观音姐姐还是玉帝哥哥,只要管用就行,所以也没仔细去看。
西厢的中间应该是接待室,一张原木矮桌,几个松木树桩便是凳子,灯光昏黄。
我接过茶杯,观察茶叶在热水中慢慢舒展,暮色从四面八方围拢而来。
锦瑟从腰包掏出那个小锦盒,马道长,烦扰了。
当初为了这个,还是花了些心思。李馆长听说有悬棺后,特意嘱咐了一番。所以此次有备而来,这个玉蝉是我的想法,昆仑青玉,仿汉八刀,形制古朴。
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餐风饮露,羽化而重生,的确适合修道之人。
鹿女士还这么客气,道长接过,山高路远,粗茶淡饭,两位将就一下。
道长不用客气,我们这次来……
昨天李馆长给我打电话说了,本来我也不愿去惊扰师尊他老人家,但李馆长说了这是鹿女士的重要课题,我再阻挠反而显得冥顽不化,况且这么多年风吹日晒,也该上去修整一下了。
睡前,我和锦瑟在大殿前的台阶上坐着。几颗疏星,风吹动屋檐的铁铃铛,发出空旷寂寥的声音,时不时叮咚一声,声波的涟漪荡出去,没有碰到障碍,慢慢消逝在虚空。
你说马道长一个人在这山上,不寂寞吗?
人家修道之人,岂是你这凡夫俗子所想的。
我还是觉得当个俗人挺好的。我握着锦瑟的手。不过实在混不下去的时候,或者心灰意冷,看破红尘,来这儿当个道士也好。
她靠着我的肩膀,望着夜空。
能看到仙女座大星云吗?
云太多,要大晴天才行。我的包里有个8倍的望远镜,野外的星空时不时会带来惊喜。
想一想真神奇,离银河系最近的星系,发出的光竟然是二百五十万年前的。
你想感慨什么?
锦瑟躺到我怀里。只是觉得啊,人的这一生这么短暂,欣喜也好,悲伤也罢,在宇宙的尺度上什么都不算。
所以还是当个俗人算了。我埋下头。
悬棺就在峭壁之上,我的头顶上方约百米。望远镜中暗褐色棺材只露出个头,其余的全在一个自然形成的洞中。
当初是怎么放上去的?
那时我还年轻,师傅那时也就四十来岁,身体一直很好,不知怎么突然生了一场大病,自知不治,便寻了此处洞府。
看来只能从上面下去了。
我们背上包,跟着马道长从山的另一边用柴刀开出一条小路上山。
在悬崖顶上,悬棺正上方五十米,有一棵马尾松探出。三十多厘米的胸径,树根深深地扎在泥土和石缝中,可以作为锚点。我用两根扁带加上铁锁,把静力绳固定好。只有两把自锁式下降器,锦瑟在给道长强调要点,握住用力就可以下降,但一定不能把下降器捏死。我取出一个8字环,穿过绳子固定在腰间安全带挂着的铁锁上,背靠向虚空,双腿蹬在悬崖边。
小心点。
我左手在上控制绳子方向,右手在下慢慢松绳,双脚一蹬,身体往后下方一荡,下降了一米,然后又蹬岩壁,继续向下荡去。
悬棺所在的洞口约两米高,也就四米多深,宽也不过三米。除了一口棺材,再无其他。
锦瑟下来了,我把她拉住,马道长也下来了。
他并没有用我特意留下的下降器,而是直接用绳子从左肩背后斜下,绕过右边大腿,再从胸前斜拉上去,也是左手放绳。他把绳子从身上绕下:用不惯你那高科技。
道长从随身背的小包里取出香蜡纸烛,跪在棺材前开始那一套仪式。锦瑟在旁边拍摄,我把目光转向外面,远处的青山,绿树掩映中的村庄,一条伤痕般的水泥路。
也许过了十分钟,或者更长,仪式结束。
马道长,可以了吗?锦瑟轻声问道。
我们要打开棺材,观察尸体的保存情况,或者腐烂的情况,这也是研究内容之一。
钉棺材盖的钉子并不容易取出,先用撬棍在棺盖和棺体间撬出一条缝,然后再用锤子的羊角把钉子一颗颗拔出来。每颗钉子都还很结实。
推开棺盖时锦瑟也来帮忙,我们费了很大劲把棺盖推开,再抬到一边,翘在一块石头上。
光线充足,不需要手电。
震惊,迷惑,怀疑,或许还有很多,这就是我和锦瑟萦绕许久的心情。
我们没有在月潭观停留。
马道长又是一番法事后,我们把棺盖重新钉上,然后用上升器回到山顶,这次马道长没有拒绝所谓高科技。其实我倒想看看他不用上升器怎么上来。
下山路上一直有道斜阳在眼前晃,伴随着一只或两只蝉尖厉的声音。
我不喜欢去解谜,真相也许只是我们认为的。
你是说永远没有真相?
也不是,有些我们以为的真相不过是……
是什么?
也许,是幻影。
锦瑟打开收音机,尧十三的《瞎子》,歌词源自柳永的《雨霖铃》。
秋天的蝉在叫……
汽车行驶在群山之间,窗外的风带着深秋亚热带森林潮湿冰冷的气息。
棺材里空空如也。其实应该说没有看见人。没有尸体,也没有骷髅。
只有一套灰色的道袍,陈旧破朽,却叠得整整齐齐,就在棺材正中。
我和锦瑟还来不及惊讶,只见马道长扑通跪在地上,砸起一些灰尘。
师父他老人家,竟然,飞升了。
2.变婆
县内苗、仲族谓有变婆之说。言生人死后掩埋土中,或三日或五日或七日,揭棺破土而出,形体依然,颜色不类,心尚知觉,惟哑不言,呼叫有声,腥秽之气随风飘荡,闻臭欲呕,毛骨悚然……此种离奇怪异之说,惟苗疆独有……又惟苗、仲独有之,他族
亦自古未之闻也。
——《从江县志·杂录异闻——人类变兽》
这是民国34年的记载,古籍中的仲一般是指布依族,但这里应该是侗族,因为从江没有布依族聚居。变婆的传说其实也不光在黔东南,在贵阳,小时候爸妈就经常吓唬我,晚上不要出去玩,免得被老变婆抓走。但什么是变婆,鬼知道是什么。
这几年,陪锦瑟在黔东南月亮山一带搞人类学研究,无数次听到变婆的传说,但每每问及,村民便闭口不谈,或顾左右而言他。
第一种说法,变婆就是野人。明陈继儒《虎荟》中有记录,讲一个苗族老妇,在山上迷路,只能捕捉螃蟹为食,后来“遍体生毛,变形如野人……”。这是人野化,不算真正野人。而月亮山一直有野人传说。最早是1930年,当地猎人捕获一名全身红毛的女野人。1996年还有一起耸人听闻的女野人强暴老汉致死的新闻,上了当年的《贵州商报》。那个村子叫摆拉,我还和锦瑟专门徒步去过,打听一圈,也没什么收获。还据说1984年,生态专家刘民壮教授在月亮山考察一个月,收集到野人毛发,化验下来说介于人与猿之间的未知物种。
电影《路边野餐》中有防范野人的说法,把竹筒戴在手臂上,野人抓你时,可以把手从竹筒里摆脱出来而逃走。这个说法我们在一些村里也听说过。但一说到变婆,村民马上讳莫如深。《从江县志》的记载,变婆显然不是野人,死后破棺而出,我说更像僵尸,锦瑟扬了扬手中的一本书,说人死后会僵硬,而变婆肢体柔软,这是鉴别方法之一,此外,变婆前臂只有一根骨头。说罢,就抓起我的手撸起袖子使劲捏。
我拿过书,书名《妖怪、变婆与婚姻》,作者颜芳姿,出版社是三民书局。
作者在从江边村做了一年的调查,发现变婆不仅是一种传说,还是一种身份。“一个遭遇过几十万官军镇压屠杀的族群,因为明清军事殖民和商业扩张而丧失故土,长久以来不断战争,抗争失败后逃亡山区藏匿……以恐怖的巫术谣言和传说吓阻汉人和异族,用择偶禁忌引导青年男女守住村寨内婚,对定居村内而来历不明的人保持高度警戒。……面对因战乱、逃税而依附边村的外姓与外地人,边村侗族也在社会内部抹黑邻居为变婆,好让祖先开发的土地和家产可以保留在侗族村寨内部,继续由家族传承下去,而不落入外人手中。”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锦瑟决定寒假再去高岗。
通过李馆长的关系,联系到当地的歌师吴老丢,还答应给他做一期访谈,有机会在电视播出,以便宣传旅游。黔东南以西江、肇兴为首的寨子搞起旅游,给村民带来收入,其他村子也想开发一下。
我们被安排住在原来大队部的二楼。木楼修建于人民公社时期,一楼是礼堂,上了一把铁锁,从门缝望进去,只见空旷的屋子里几十张木凳,一束光线从窗户射入,似乎有灰尘在光柱中飞舞。很多年没用了,大家有事都到鼓楼商量,歌师带着我们在寨子里转了一圈。
前几天,我们就在寨子里瞎逛,拍照。冬天难得的晴朗日子,几乎所有人都在阳光下,坐着或者靠着,看着我们,露出笑容,说:来了。然后继续聊天,用我听不懂的话。锦瑟也找个地方坐下,她会些侗话,不过需要悄悄打開录音笔,晚上回放,整理一下。我只能无聊刷手机,但阳光刺眼,最后只能打瞌睡。
然后便是斗牛。高岗有两座鼓楼,一座是吴姓家族的,一座是王姓家族的。牛就养在鼓楼下面的一间屋子里,披红挂绿打扮一番,便被一群人簇拥着往斗牛场走去。斗牛场在五公里外,其他人便各自乘坐摩托或者三轮车向那里进发。
应该来了十几个寨子,至少有二十头牛。斗牛场周围摆上许多摊子,卖各种吃食,煮米粉,油炸洋芋,水果、啤酒、方便面、饮料、瓜子、矿泉水。牛两两对战,红着眼睛用角顶,用脑袋撞,唾沫横飞,鲜血直流,直到一方转身而逃。
斗牛结束,大家散去,走路的,搭乘摩托或者三轮车,斗牛场留下满地的一次性碗筷、方便面纸碗,被风吹着飞上半空的塑料袋。
王姓的斗牛赢了,回到村子,披着红绸,被牵着,簇拥着游街,放完鞭炮才引到河边,惬意地泡进水里。吴姓的牛输了,被一个人牵回来,最后也走到河边,泡进水里。
夜里,在鼓楼,几个老汉,吴歌师也在。我们也过去,围着火塘坐下。锦瑟说他们在聊白天的斗牛。我反正听不懂,她说他们聊美国总统选举我都相信。
他们说几句,锦瑟小声给我翻译,他们说,明年要加强训练,搞几个轮胎,用绳子拖着让它拉,营养也要加强,除了草和饲料,还要掺点用酒泡过的苞谷。
突然,锦瑟插话:牛打败了怎么办?
见锦瑟会侗话,他们都很惊奇,不过这也拉近了距离,我借机散了一圈烟。我平时不抽烟,为了锦瑟事业的发展,也只能牺牲自己的身体,同时为祖国的烟草税收做出贡献。吴歌师从火塘里捡起一根木头,点燃烟,吸了两口。牛败了这一次,就没有下一次了。
啊?
你想一下,它下次再去,一看到对方,就会没有勇气,不用打都输了。
那么牛怎么办呢?
我们也舍不得,一般也就卖给屠宰场。
被选中的斗牛,平时也不用耕地,住在鼓楼里,吃好喝好,它的命运便是这每年一度的战斗。赢了,便是荣光,输了,连去耕地的机会都没有。
日子一天天,因为会侗话,锦瑟在寨子里的好感度颇高,歌师的采访也录了,但一说到变婆,村民们要么散去,要么就闭上眼睛装睡着。
又是一个晴天,我们开车去了一趟深山,在山里露营,拍山巅的落日,看冬日的星空。回到村子,不到八点。鼓楼里人影都不见,火也没生。歌塘里也没有小伙姑娘,平时这个时候,正是他们行歌坐月的好时光。家家关门闭户,街上连猫都看不到。
我去车上拿了两罐啤酒,和锦瑟坐在鼓楼的长椅上,靠着柱子看星星。参宿四的光芒似乎要比以往黯淡。它是一颗处于生命末期的红巨星,体积是太阳的七亿倍,据说一万年内,它将耗尽燃料,然后发生一次爆炸,成为一颗超新星。
那么太阳呢?也会成为一颗超新星吗?锦瑟把手放在我的手里。这个时候的气温,手放在外面,一会就凉了。
太阳也会成为一颗红巨星,体积将膨胀到现在的约250倍,扩张到地球轨道。不过太阳质量比较小,它会演化成一颗白矮星。
锦瑟喜欢和我探讨这一类的问题,甚至包括量子力学。她说,那天如果你不把照片给我看,这也是一种选择,那样我们便不会相识。那一次选择,就产生了两个结果,另一个平行世界的我们,也许也会来高岗看斗牛,但我们并不认识,也许就这样面对面走过。
那是一个春天,雀鸟,雷公山里一个遗世独立的寨子。我站在屋檐下避雨,顺便看刚拍摄的照片。雨中的雀鸟,吊脚楼层层叠叠,雾气像是在升腾,又像是降落,屋顶瓦片上飞溅着雨滴。突然响起的风铃声唤醒了我,山间一条小路,一枝下垂的树枝,苍翠的卵圆形叶子,一个穿鹅黄色上衣的女子。我举起相机,以树叶当主体拍了一张,鹅黄色的身影变得模糊,又把焦距对准女子,这样树叶就虚化了。
那天是惊蛰,一个注定会发生点什么的日子。三个小时后,在雷公山顶的浓雾中,一团鹅黄格外醒目。我对她说,刚才给你拍了张照片,我觉得拍得很好。她接过相机,嗯,不错,发给我。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那时她还在读考古系研究生,知道我在万东桥下开古玩店,假期便跑来练眼。我带着她把整个古玩城各种真假古董看了个遍。她又拉着我陪她去各种考察,照她的说法,反正你那店也是三年不开张,关上三四五六七天也没啥关系。出门顺便吃吃喝喝,聊天的内容主要是盗墓小说。我一直怀疑她的专业精神,是不是准备学了科学考古知识后再从事盗墓行业。
电筒光晃动,是吴歌师,一身酒气。
哎哟,你们今天不要在这里坐,赶紧回去,把门关好。
我递了根烟给他。见他想走,锦瑟拉住他,给我们说说嘛。
他好不容易坐下来,把一根烟抽完。两天前,就是你们开车出去的那天,寨子里的吴小花死了。
吴小花是住在寨子边上的一个老太,看不出具体的年龄,应该很老,佝偻着靠在门前,脸上沟壑纵横。她的目光像看着你,又像看着你身后的虚空。
你们不知道,她是一个变婆。
啊,变婆不是野人吗?
他瞪着我,变婆怎么是野人?锦瑟掐了我一把。
但我的无知反而激发了他诉说的愿望。你们不知道,村子里有好几户变婆。平时我们在一起下田,一起吃饭,一起喝酒,都没得事,但是变婆死了,才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你们也赶紧回家,我也要回去了。
其实我还有很多疑问,比如书里说的,变婆死后或者三天或者五天或者七天,会破棺而出,回到村子里。现在基本都火葬了,烧成灰,应该就没危险了吧。
但吴歌师已经站起来,拿起电筒。
锦瑟也站起来,似乎无意说出:你知道山上的吴道士吗?
她说的是马道长的师父,正好也姓吴。
怎么,你们还晓得他?看来我小看你们了。
三个月前,我们打开了他的棺材,你知道我们看到什么吗?
吴歌师把电筒按亮,对着锦瑟,你们看到哪样?
棺材里什么都没有。
锦瑟的脸在电筒光下一片惨白,吴歌师的脸也一片惨白。
你们赶紧回去吧,我也不知道你们说的是哪样意思。他匆匆走去,突然又回头,那个吴道士,他也是变婆。
3.道士
之后又断断续续去过几次高岗。锦瑟剪了一个短片,歌师的访谈,得胜而归的斗牛,失败的斗牛,雨中层层叠叠的木楼,暮色中的炊烟,雨后光滑石板路上的倒影,路边晒太阳的老人,风雨桥里爬上爬下的儿童,神情慵懒的猫,一副没睡醒模样的白狗,鼓楼里火塘噼啪燃烧的火苗,山里的薄雾,天籁般的大歌……那种遗世獨立的气质。在电视和新媒体播出后,又通过李馆长牵线搭桥,有人在高岗寨子旁边建了座有八间客房的高端民宿,分别命名为:捕风、捉影、抚琴、鼓瑟、批亢、捣虚、抱残、守缺。我心想怎么如此眼熟,后来想起,是《倚天屠龙记》少林龙爪手的招式。村里还开了几家农家乐,村民也摆上小摊,卖山里的土产。一拨一拨的游客,就像潮水,带来喧嚣,也把贝壳、珊瑚冲上沙滩。
锦瑟为这些事前前后后跑过几次,帮忙联系。期间,她还参加了数次家里安排的相亲。我问她如何,她叹了口气,咬着嘴唇,把脸偏向窗外。
再去高岗,锦瑟已是红人。
那是第二年初秋,歌师打来电话,说有一场玩变婆的活动,很难得,好几年没举行了。
一个男人,用棕榈树皮做的面具蒙着脸,手臂上扎着稻草,扮作变婆。大家围着他,有胆大的男孩时不时捅他一下,他回过头,张牙舞爪。小孩们四散而逃,他佯装去追逐。最后,大家都跑累了,于是炸响鞭炮,吹起芦笙,恭送变婆大人出村。
然后便摆上大鱼大肉,有人提了个大塑料桶,往碗里倒酒。前三碗是必须一口闷,我得给锦瑟挡酒。歌师一一介绍:寨老、鬼师、支书、村主任、会计等等。
一轮轮敬酒,各种说辞,屋顶的灯发出彩虹般的光芒。鬼师把锦瑟拉到旁边说话。锦瑟转述给我,说感谢我们去打开吴道士的棺材,让他们知道棺材里没人。他死后,村子里出了些怪事,现在想起来,很有可能是变婆作怪。鬼师去做了法事,以后应该不会有事了。
一桶酒下肚,寨老已经趴在桌上,被搀扶着去屋里躺下。歌师舌头打转,说去歌塘唱歌。鬼师的影子在墙上舞蹈一番,也走了。
有人又拿来一桶酒,锦瑟捂住碗不让倒,结果另一个倒满酒的碗又放到她的面前。好了好了,吃菜吃菜,大家节奏慢一点,就当中场休息。村主任用筷子指着桌子中间的猪蹄,鹿老师尝尝我们的特产。
猪蹄也就简单地剁成几大块,锦瑟举着筷子,寻找小的。
来来来,这个不晾人,来这一块。
张师也来块大的。
酒喝得慢了,话就多起来。因为月潭观申报文保的事,锦瑟便问起村主任。
这个月潭观应该也有几百年历史了。最早呢,是一个和尚庙。
哦,这么说来很有意思。
其实也没有哪样意思。据说一开始有几个和尚,香火马马虎虎,后来兵荒马乱,和尚走的走,死的死,到破四旧的时候,最后一个老和尚也死了,也就荒废了。
那怎么又成了道观?
这个说来话也不长,也就十几年的事情嘛。
怕不止哦,吴道士死了都十几年了。说话的是会计。
你这样一说还真不止十几年,我算一下,九二年还是九三年,差不多快三十年了。其实那个时候我还小,很多事情都是听老辈子说的。
吴道士,那个时候他還不是道士。他家实际上是寨子里的一个大家族,后来因为姑表通婚,家里人得了一种怪病,男人身上磕到碰到就出血,止都止球不住。
我估计是近亲结婚引起的遗传病。会计往自己嘴里丢了颗花生米。他旁边的一个胖子正拿起一块猪蹄撕扯。那个时候都说他们祖上惹到了变婆……
村支书打断了他,哪里有变婆,不要搞那些封建迷信。
反正到了吴道士他老者这一代,两个兄弟在十多岁就死了,只有他老者成年。因为有病,村里姑娘不愿意嫁给他。后来,他就和村里一户潘家的姑娘结亲。
那个潘家,村主任看了眼支书,祖上也是变婆。以前,村里的人都不和变婆通婚。后来生出吴道士。他十多岁时他老者摔了一跤,死的时候全身都是死血,乌黑乌黑的。他家妈一年后也跑了,听说跑到荡麦去了,反正他也没去找过。后来他长大了,喜欢上鼓楼旁边吴老腮家小姑娘。吴老腮家是我们这个寨子最早的几户人家,因为吴道士是变婆后代,肯定也是变婆,所以吴老腮不同意。
听到这儿,锦瑟看了看我,从桌子下拉起我的手。这么多年,我只去过她家一次。她妈从头到脚把我审视一遍。一顿饭,吃得我如坐针毡。一个住五层大别墅的千金,一个他们眼中的无业游民。他爸倒是劝我去考个公务员,说有个稳定编制也凑合。
听说吴老腮家姑娘,都怀起了,还是去找草药打的,会计说。
离这里几十公里的占里,就有用草药控制生育的说法,锦瑟曾经去那晃悠过两天,只拍了些木楼上的计划生育宣传标语。
后来有一天,吴老腮在山上被石头砸死了,会计继续说。
胖子说,肯定不是被砸死的,是自家喝酒摔到坎下死的,很可能是变婆害的。
那么高的一个坎,会摔死,会计用手比画着。
就是摔死的。有个老总,去法国玩,比这还低的一个坎,也摔死球了。
你们两个争个斑鸠,各喝一碗酒。支书抬起碗,都不要乱说话,你继续。
村主任也端起酒喝了一口。后来,吴道士伤心了,就出去打工,去的是广东还是广西。过了一年,吴老腮家姑娘也出门打工,好像也是去广东广西。
也不晓得是不是去找他。一年后就回来了,嫁到都匀那边一个寨子。没几年,吴道士也回来了。回来后也不住村里面,他家那个房子,几年没人住,早就朽了。
他就跑到山上,脑壳上扎个鬏鬏,胡子留一把,就当起了道士。外面开两块地,种点白菜苞谷,偶尔下山买点米和盐巴,打几斤菜油。几个月不下山一次,下山不是买东西就是做道场。山上有了道士,周围寨子死人,居然不请鬼师,而是请他做法事。
法事做得如何?
做得还蛮像模像样的,我记得小时候摆绞寨有个老者死了,我去看过,他戴个西游记上唐僧的那种帽子,在那里念经。
道士哪里会念经嗷?会计问道。
哎呀,叫你不要说话,反正就是那种嘛咪嘛咪吽念经样的调子。
后来一个人忙不赢,就收了个徒弟,就是现在的马道士。
后来呢,听说生病死了?
生哪样病嘛?是心病。胖子手中还抓着个猪蹄,嘴里还嚼着。听说他在广西打工时,犯了事,好像还搞死人了。
好像好像,你看到的?逼话多过文化。支书骂道。
胖子不说话,专心啃猪蹄。
不过他死之前,村里倒是来过两个外人,拿起张相片,到处打听,还问过我家老者。相片乌漆嘛黑的,鬼都看不清楚,烟也不发球一杆,我家老者没跟他们说话。
闲话少扯,喝酒,反正最后就死球。
死之后还葬到山崖上?
是嘛,当时,他的徒弟,就是现在的马道长,非要说师父的遗愿不能违背,非要把棺材放到那岩上。
一开始大家都不愿意去整,后来还是掏钱出来,一个人五十,人还是不够,后来一百才找齐人。
那个时候一百块钱还是管钱的,大家用绳子费七八力才把棺材放到那岩上的洞里。
鹿师上次你们不是上去把棺材打开了?后来那个马道士到处乱说,说他师父升仙了,又搞这些封建迷信。支书从烟盒里掏出烟,给我和村主任一人一支,自己掏出一支叼上,把烟盒扔给会计。
这样想起来还是有些蹊跷。会计给胖子一根烟,然后站起来给我们把烟点燃。
什么蹊跷?
会计自己也点上,吸了一口,从鼻子把烟雾喷出来。
那是几年前,三年还是四年,我同学家老妈死了,关系比较好的那种,在黔南那边,我们几个同学到了都匀,然后坐中巴车先到一个乡,好像叫基场。胖子你不要笑,你不要想得那么龌龊,是地基的基,不是飞机的机,也不是母鸡的鸡。然后坐摩的,最后又走了十多公里山路,才到我们同学家。上香磕头,吃饭搞酒,几桌麻将打起,和尚在旁边念经。
我其实是背对到他的,好像是对面的把火机丢给我,我没接到,火机落背后。我转身去捡火机,抬起头来,一看,哟,这和尚长得有点像吴道士。
我怕你是撞鬼了哟。
我只是说长得有点像,只是他光着脑壳,又没得胡子,只是看起来有点像。
后来我记不清是什么时候结束的。锦瑟说我一碗接一碗地喝,拦也拦不住。最后你就像头死猪,拖都拖不动。
然后呢?
锦瑟的脸就像喝了碗米酒一样红。我记得她的身体灼热,光滑,柔若无骨。
那已是第二天,车子停在山巅,太阳离西边的山脊还有三厘米。我们离开高岗,还不想回去。我们开着车在月亮山腹地,那些连村落也逐渐稀疏的砂石泥土路上,没有目标,想象浩瀚海洋中的一叶孤舟,就这样一直行驶。直到越来越浓的暮色弥漫,才把车停在山巅。我们坐在一块石头上,等待日落,等待群山把最后的光线吞没。
责任编辑 丁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