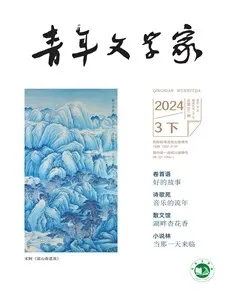于坚诗歌意境分析
2024-05-15邝启艳
邝启艳
意境是作家写作抒情性作品时充分运用各种艺术手段使作品呈现出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活跃着生命律动的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于坚诗歌的意境审美空间来自其对时代的清晰感知和个体经验的凝结,一方面基于日常化的生存体验进行场景建构,从直白的语言、直陈的叙述、“在场”的写作三点出发,呈现生活的真实性与理想的可触性;另一方面是个体精神的植入,渗透其个人生活史和精神史的集地域性、生态性、古典性于一体的精神环境。本文试通过诗人的诗歌文本创作与创作理念分析其诗歌意境空间,探讨其诗歌意境空间存在的意义与合理性。
出生于1954年的云南诗人于坚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实践日常生活诗性美学的叙事诗,其写作方向是打破之前受朦胧诗影响的隐喻和高度总结的视角,探索20世纪80年代以来诗歌语言的变迁,其中也包含着思想的转变。他的诗歌大多是基于日常生活的阐释,选取普通的、随处可见的事物,形成真实性的、可触摸性的写作。这并不意味着将事物以粗泛的方式搁置且忽视时代的变动性,其中包含着一种“祛魅”,将个人从社会主流的共鸣下剥离出来,发掘被遮蔽了的个人的真实,体现着对当代人精神本质的思考,呈现独特的时空之境。
一、日常化的场景建构
“日常”一词,一般解释为属性词,即“属于平常的”。与经过幻想加工出来不同,它一定是隶属真实本身。在于坚的诗歌中,日常被看成类似《诗经》年代关于“发生”的表达,日常视域的写作就是诗人在这种“属于平常的”前提下对诗歌场景的提取与意境的构建,回到最真实的事物与事件本身,脱离沉重烦琐的复杂语境,让诗与本真的事物在同一个平面上,从而使诗本身的发生与生活的进行保持着生动的一致性。
(一)口语化传递
诗起源于口语,这样的语言是具有活力和创造性的,有着与天地万物和人自身的紧密联系。于坚诗歌意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这种口语构建起来的审美空间而不是普通话塑造规范过的意象化、隐喻、多义的写作。口语直达思维、人与生活的本身,他的诗歌语言空间,含有非常多口语的因素,目的在于面对真实的、当下的自身,个人生活与诗的发生产生直接联系,有着现代人的自主性与自觉性。“诗人要把握的就是在每一个时代的喧嚣里面那些最基本的東西,诗人实际上不是要告诉人们这个世界又发现了什么东西,他永远只是在告诉你最基本的东西。”(于坚、谢有顺《于坚谢有顺对话录》)于坚将口语作为一种写作姿势,将对事物的思考还原到原始状态上,因此保持了一种诗性活力。例如,《芳邻》中写到樱花,“向着晴朗朗的蓝天/亮出一身活泼泼的花”,《河流》中“在我故乡的高山中有许多河流/它们在很深的峡谷中流过/它们很少看见天空”,“活泼泼的花”“很深的峡谷”等,就构成了一幅原生态的诗歌场景:真实的高原而非经过各种想象“加工”的乌托邦。与经过想象、隐喻表现出来的意境不同,这里完全就是口语化的风格,口语化的词、节奏、语气等构建了一个野性的生命空间。此外,口语化还体现在他诗歌中方言词的使用,如“补巴”等云南方言的使用,体现了云南特有的小众、质朴、特殊的社会生活场面,而这种场面无法被普遍使用普通话的社会场景替代。口语使人类社会充满流动的活性与张力,它也维系着一群人的生命状态。
(二)直陈的叙述
营造诗歌意境审美空间,离不开叙述的语言,诗歌中的叙述就是不同的语句串联形成整个诗歌。叙述的重要性可以推及《诗经》中关于“赋”的运用,“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朱熹《诗集传》),这类诗歌的叙述语言更加贴近最真实的状态且少了很多虚幻成分。于坚的诗歌就有这方面的特质。首先,他更注重事物的真实状态,所谓“直陈的叙述”,“词是自然的物,它们像树木、青草一样在大地上自然地生长”(于坚、谢有顺《于坚谢有顺对话录》)。克罗齐认为陌生的表达目的在于激发人对习以为常生活的关注,而不是进行“转述”,于坚诗歌的叙述显示了对生活的唤醒方式具有思想的自觉与身体的自觉。其次,他擅长将自己对外界事物的观察与自己的内心思考结合起来,保持自身的理性,如“有一回,我漫步在林中/阴暗的树林,空无一人/突然,从高处落下几束阳光/几片金黄的落叶,掉在林中空地”(《有一回,我漫步林中……》),摆脱了诗歌经过修饰后呈现的模糊状态,直接将自己对阳光、落叶、空地几个事物与个人的心理状态呈现出来。
这种自我与生活的同步性具有一种召唤的作用,他呼唤真实的生命感受,也是对生活本质的召唤,“唯有富于灵魂的活物才能够实现自己的本质规定性”(于坚、谢有顺《于坚谢有顺对话录》)。《我一向不知道乌鸦在天空干些什么》中“书上说它在飞翔/现在它还在飞翔吗/当天空下雨,黑夜降临/让它在云南西部的高山,引领着一群豹子走向洞穴吧”的叙述主体之间的关系包含着真实的因素,“书上”“黑夜降临”“云南西部的高山”“引领一群豹子”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可能真实的关系。
(三)“在场”的写作
“在场”是一种状态,于坚的诗歌创作非常注重诗歌中的在场性问题。
一方面,艺术灵感通常情况下是主体在创作时产生的一种激动、流畅、创造力极强的思维状态,只有真正地在场才能起到作用。中国古代感物说认为文学是创作主体对世间万物形成的一种发乎性情的感受,在个体感受下进行的创造性活动。于坚的很多诗歌就是以一个在场者的身份参与的,他很少对事件进行回忆性写作,他笔下的河流被写成一种活生生流淌的存在状态,写人能看到某种真实的生存状态、生活场景。《0档案》与“事件序列”中,他一直努力强化诗中能够引起人们感知觉的部分,具有记录性质,“档案”本身就是记录性质的、历史性质的,这种方式的写作具有一次性的特点,无法被塑造与复制,因此这是属于在场的,有效性的写作。
另外,他抛弃了“生活在别处”这样的状态与想法,更加强调存在先于本质。《避雨之树》中“寄身在一棵树下/躲避一场暴雨/……/它站在一万年以后的那个地点,稳若高山/雨停时我们离它而去,人们纷纷上路,鸟儿回到天空”,这是一个观望者,同时又是场景里的一个人,他的诗歌能与真实的经验叠合,甚至是直接体验,直接抵达诗的境界。
二、个体精神介入的意境
汉语词汇是形成句子的基础,任何句子所传达出来的意思,都是由组合分析而得。意境空间的形成也依靠词汇的使用,即作为意象的词构成,整个空间环境都是由一些典型的具有相似特征的名词串联起来形成的整体。于坚的诗歌里存在着空间整体性,这是一种真实的、当下的、身体的空间,他的一部分诗歌在写及自然的时候也呈现着这种状态。
(一)地域性的表现
口语化语言的入诗打开了不同于之前以书面语为主创作的向度,相比于普及化的语言,那种语言具有个人的记忆与信仰,塑造一个人的真实生活史。于坚的诗歌创作中时常体现着其学者的角色,对地域性的存在与演变的反思。《面具》中大量的地域性名词贯穿写作,从小的生活经验让他深刻地接触与了解他所生活的故乡,故乡的空间是他经常涉及的领域,“梦中的家宅必须拥有一切。不论它的空间有多大,它必须是一座茅屋,一只鸽子的身体,一个鸟巢,一只蛹。内心空间需要一个鸟巢的内心”(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对于坚而言,这个空间即其生长的地方,梦与现实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认识的,彼此可感的。地域性还是他建构诗歌意境空间的元素,《云南点名》中以一种游览式的笔调写云南的地名,僅仅一首诗里涉及的云南各地的地名就有二十多个,通过多个地名互相联系,互相存在构建起来的意境空间,不是一种审美化的,也不是一种至情至性化的,而是一种原本的、清晰的空间。他诗歌中涉及的地域性意象还有带有云南民族特点与历史特点的,如“高黎贡山”“下关街头”“西部高原”“双廊乡”“东川”“马龙”等诸多地名,都带有明显的“云南”色彩。他对自己生存之地的思考,同时又形成了一个故乡系列,《云南点名》的游览式抒写,打开了一个地方的生活空间,“咸要贡献盐巴/南方要贡献森林/西部要贡献高山/……/纸产于昆明/铜来自东川/……/万物呵/是否还在履职?”就是一幅云南地图,诗人以一个全知视角理解着、记叙着云南丰富的森林资源和矿产资源等。这些对地域的倾情抒写,意在让自己的心找到一个可以安住的地方,地域就是连接故乡与诗人的一个纽带,某种意义上,正是通过对地域的不断开掘、抒写,才形成了一个具有更绵长情思的意境与鲜明的个人写作特征。
(二)生态性向度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的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工业化的发展,而这对于自然生态而言,是一种大规模远离。耿占春在《失去象征的世界—诗歌、经验与修辞》中引用到托洛茨基对于工业化的描述:“艺术行为或对大自然与生活世界的创造性的转化,现在由一个伟大的社会阶级群体来集体地加以实施,对世界的创造性转化由大工业的方式在大地上、在山河之间进行。”于坚诗歌中的生态空间基于他的自然主义式的创作观,一方面,他的创作跳脱了第二代朦胧诗的向度,以一种近乎现实的城市态度面对自然,以一种既庄严又自由的态度将大量的生态事物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自然具有某些神性的启发,这种启发又被认为是自然的,《苹果的法则》中“神的第一个水果/神的最后一个水果/当它被摘下,装进箩筐/少女再次陷入怀孕的期待与绝望中”,苹果落地,本来就是自然界中最为普通的现象,这是时间形成的现象,也就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诗人将其还原为最初的状态,蕴藏着最原始的神性,生命流转的规律。在《我走这条,也抵达了落日和森林》中,诗人思考着工业和自然的关系,其结果是达成了与工业的和解,最终其实也是走向了某种神性的回归。自然意象塑造出一个和谐自然又具有强悍生命力的生态空间,“高山”“流水”“群峰”“春天”“树林”“樱花”等大量的生态系列抒写,一方面体现出于坚共生的生态伦理,另一方面又蕴藏着一种天人合一的理念。在他的这类诗歌中,生命、生长、和谐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这部分诗歌中,诗人对工业、对社会强烈的反思以及自身对于生态自然本身的亲近,构建着诗的意境系列。
(三)古典诗意的延伸
于坚在表现古典文学以及社会生活与文学的关系中,将文言表达与巫文化放入现代诗的表现中。个人经历使得他不得不与传统文学产生联系,在《于坚说》的封面上,写着“他的野心是成为古典文人”。一方面,他将古诗句与现代诗结合,表现出自身与传统文学的某些精神呼应之处,同时传统诗词与文化的联系在他的诗歌里也有着充分体现,如《苍山之光一秒钟前在群峰之上退去》中的“第九峰的积雪,第十二峰的积雪/世的界,一一亮相,复原/‘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以及“在一切之上,天空森蓝,向更深者,转过身去/‘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这样直接将现代白话文语境与诗词语境进行有机结合,就形成了极其微妙的阅读感受,使其诗歌具有了古典的气质,将古代诗词的生命力又延伸了。另一方面,他对传统诗意的理解表现在诗中,而不是将现代诗歌完全从传统中剥离出来,将自身写作看成诗歌发展的自然延续。《云南点名》里采用游览式写法,开头便引用苏轼的思想“知者创物,能者述焉”(《书吴道子画后》)来抒写云南这个神圣的地方。他非常认同诗歌自古以来的“兴观群怨”的作用,他认为“彼岸不过是一个飞机场”,从汉字的起源来谈论诗歌,将现代的诗在其古老的源头与意义里找到了皈依,新诗的“招魂”即此。这种古老的文明与观念在他的诗歌中得到最坚定的呼应,如《避雨之树》中“它站在一万年以后的那个地点,稳若高山/雨停时我们弃它而去,人们纷纷上路,鸟儿回到天空”将一棵树的母性、生命、原始之力挖掘出来,就与传统中国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契合。他的诗歌因为这种诗意的延续与重新审视而构建起来的具有个体与时代意义的境界,同时是他个体精神里的理性与感性相协调的内部空间。
总之,于坚诗歌意境空间是通过诗歌的整体性建构起来的,具有当代性的时空结合体。一方面,口语的使用使诗歌回到了日常本身上来,真实的叙述压缩了与生活的距离,去除了某些诗歌中存在的“伪”的一面;另一方面,个体精神的植入,营构了一个集地域性、生态性、古典性于一体的意境空间。他的诗歌意境建构不是靠某种简单意象建构的美学,他在诗歌里达成了个体与生存的和解,具有其自身意境审美空间存在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