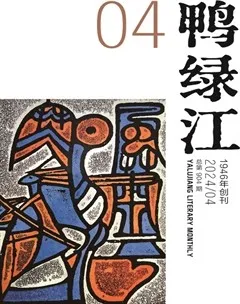南尖回响
2024-05-12佟丽霞
佟丽霞
一条坝埂,一湾稻田,一道海岸,一片大海。
姥姥家就在海边儿。
这是辽南庄河一个叫南尖的村子。为啥叫南尖?有多南,有多尖?在大孤山当过店铺伙计的姥爷说,南尖在咱辽东半岛东南边,在地图上看,比你小姨用的改锥还要尖。
改锥那么细那么尖,怎么能住人?
是像改锥,不是真改锥。
那到底是不是改锥?
姥爷边搓着手里的麻绳边说,你说啥?我听不真亮。
刚才还能听真亮,现在怎么听不真亮了?
我妈说,你姥爷有时聋,有时不聋,不聋也得让你“倒磨”聋了。
当个改锥可不错,天天只等着毛蚶、海蛎子、蛤叉从海里打上来煮熟了,一插一撬,溜鲜。
我就是出生在姥家老屋里那个叫盒子的姑娘。我出生那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两个年头,并出现了好几个派别。上级发出了新的号召,要求各派大联合。于是,我就有了一个听起来方方正正的名字——联合,但认识我的人都叫我盒子。我出生那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海里赶上了鱼群。海边的人都会拼尽全力把鱼搬回家,能搬多少是多少。我妈在家里生我,从沈阳回来探亲的我爸被派到海里搬鱼。平生第一次被鱼包围了,我爸只挑了两条又细又长绿眼睛的鱼,一手一条,甩甩搭搭回了家。
当我过了第一个本命年的时候,我作为“先遣队员”先进了城里。
我妈是在一个我假装睡不醒的早晨,把我强行拖到汽车上,再换火车,扽到沈阳的。在城里,我一下子“掉到井里”。城里的大杂院强加给我一堆眼睛滴溜溜转的小伙伴,他们嘲笑我海蛎子味的乡音,还找来一个破铁皮罐头盒子,在地上踢着,并一齐大喊:“踢破盒子,踢破盒子!”他们踢一脚铁皮盒子,看一眼我,再嘻嘻笑着,他们之间的眼神交换的内容不言自明,共同表达着对来自乡下的我的好奇和奚落。
我站在那里。渐渐地,我听不见他们发出的声音,甚至看不到他们一张一合的嘴。我只有一个人,站在收割过后,满是根茬、充满危险的田野上。
一列从深夜驶发的绿皮火车
绿皮火车,终于缓缓地启动了。哧哧的白气,从红漆曲轴连杆里钻出,在站台上弥漫开去,又被夜轻易地包裹住。浑厚的笛声,一长声连着一个短声,像一声巨大的不甘心的叹息。
这是一个挤满了人,又只有我和母亲的梦境,我的脚似乎总是踩不到地上。
两个老绿色的粗布旅行袋,被一条看不清颜色的毛巾系在一起,一前一后地搭在母亲的前胸和后背上。我的身上挂着一个小冬瓜大的荤油坛子,它装在一个草绿色旧帆布书包里,书包上面印着红色的“为人民服务”。我被母亲半拖着,走在永远走不到尽头的楼梯上。我的四周都是向前迈着的大腿,前一个人的屁股几乎顶到了我的鼻尖上。我无法停止,也无法摔倒,母亲的手紧紧地拉着我的手,我感觉我的两只脚离开了地面,前后左右的人把我拥起来,我就这样脚不沾地地被拥上了一列绿皮火车。
火车停在深夜的站台上,像一条胃口巨大的一节一节相连的绿豆虫,两排绵密的腹足在纹路清晰的叶片上一下一下地蠕动着。它好像总是要把我抛下,我因此被母亲责骂。走向这列火车的路真长啊!当母亲终于在褐色硬板座位下,挤放好她的包裹,我则像一条倒空的麻袋,一下子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装荤油坛子的绿书包挤在了一堆疲惫不堪的鞋子中间。
一车人都是模糊的,只有母亲的脸分外清晰。
母亲像是和谁商量,又像是在自言自语:“给俺孩子点儿地敞儿搭搭边儿,不耽误你们坐。”母亲重复着自己的话,眼睛一直盯着座位上两个挨着的大人之间,一块若有若无的地方。她犁杖一样的目光,不断地在两个人之间划动着。那两条挨着的腿终于略微分开了,硬板座位上露出来一个窄窄的锐角。这时,我清楚地记得母亲用食指杵了一下我的后脖梗子:“还不快谢谢姨和舅。”可我不喜欢坐在两个陌生人中间。母亲早就洞察了我的犹豫,一抓一推,我只感到衣领子一提,腋窝一紧,就像一个楔子一样,我被母亲轻巧地塞进了那个锐角。坐下来是这么踏实,是从水里踩到地上的踏实。
在夜的最深处,在类似吵架和抢夺中安顿好行李和人,无止息的骚动,随着火车缓缓地启动,终于停止了。火车上的陌生人,似乎终于接受了命运这随机的安排。
母亲和更多的人是没有座位的。母亲的一只手拉着上面的行李架,她的脸倚在拉直的胳膊上。她不动声色,眼睛的余光却从未离开座位下面那两个包裹。她的另一只手攥着一条书包带,书包里青灰色的小坛子装着醇香的猪大油,它原本是挂在我的身上的。在一个粮食和豆油都要凭票供应的时代,这里装的,就是分居两地的一家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小坛子的向往。
从沈阳到丹东,这是一列每站都要停的火车,它在深夜23:45从沈阳站始发。一车人大多有了困意,我是不困的。我在等待一个个突然的停止,和冷风吹进车门的清冷的喜悦。每停一站,都是一阵骚动。一些人上来,又一些人下去,不断地在抢抢夺夺中安顿行李和人。这像极了姥家门前的海,海潮一阵上来,又一阵退下,并不断地拍打着长长的堤坝。我分不清这是海潮的起落,还是人的来去。
绿皮火车又动了,它缓缓地动。深夜里,火车的启动是小心的,壓低着呼吸,轻轻地用力,像在看一车人的眼色,或许它也像这车里的人一样,有了强撑住的困意。呼呼的风声,车轮辗轧轨道的声响,车窗玻璃,映着车里的人和小桌板上的一堆杂物。这样的情景,和窗外无边的黑一样,一成不变。
“你往后坐一坐,靠到椅背上,帮我占着座。谁要坐都说有人。”一成不变的情景,突然被我身边的一条“锐角边”改变了。他要上厕所,临去前给我安排了一个占座的任务。而且,他是挨着车窗的,也就是说,我也可以趁机挨着车窗坐了。我早就想看看车窗外了,便往后坐,屁股下的锐角也变成了一个宽宽绰绰的正方形。我的身体被直上直下的木板靠背接住并规范着,一种陌生的坚硬和新鲜的疼,让我懂得原来人的身体和直角是如此不相容。
“锐角边”很快回来了,但他没有急于坐回来,好像是为了奖赏我替他占座的功绩,他要在过道上,靠在车座旁边“直直腿”,这让我得以有更多的时间把鼻子贴在车窗玻璃上,只有贴得越近,外面的景色才看得越清。为了表达我不想离开窗玻璃的决心,我甚至把身子侧过去,肚皮扁扁地贴在车壁上,又坐回了窄窄的“锐角”的空间。不知什么时候,我的“锐角边”坐在我腾出来的地方,好像没有察觉我偷偷换了位置。
火车又一次驶离站台。一车拥挤得变形的人和他们的影像终于隐去,一片明亮的灯海,像一大朵通了电的莲花,暖暖地浮在暗夜里,浮在天地之间。这是一场猝不及防的相遇,它不远不近地跟随着深夜里的火车,直到火车提速,那灯海才慢慢离去。等火车再次停下的时候,那片灯海又出现了,好像抄了近路,一直在火车的前面等着似的。
在一片片相似的灯海里,我记住了这条线路上所有车站的名字:本溪车站到了,本溪南车站到了,南芬车站到了,草河口车站到了,歪头山车站到了,通远堡车站到了,五龙背车站到了,凤凰城车站到了,丹东车站到了……黎明也到了。原来,火车穿过深夜,就是从一个灯海到另一个灯海,并一直把人们从深夜送往黎明。
我总是梦见坐着这列火车,从丹东到沈阳,或是从沈阳到丹东,从一个广场有毛主席塑像的地方,到另一个广场也有毛主席塑像的地方。我的脖子上,总是有一个沉重又娇贵的荤油坛子。母亲永远是健壮的,她的后背和前胸总是有两个包裹,我总是被她提着脚不沾地,她总是有办法给我找一个若有若无的位置。那些我熟悉的车站的名字,不断地被重复,它们是黑夜的刻度,标志着黑夜与黎明的距离。
这列绿皮火车,也是母亲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唯一通道。在这条路上,母亲走向父亲,后来有了我,有了妹妹。我总是在这列每站都要停下的慢车上,把鼻子贴近窗玻璃,无边无际的人间灯火从未改变,也从未离开。只是在我蓦然抬起头的时候,再也找不见我的母亲。她早已成为车窗外那温暖我一生的灯海里,一盏忽明忽暗的灯火。
哑蝉
“命——命——命——”
蝉不停地叫,像在干热的锅底下面又加了把干柴。在辽南,它还有一个象声的名字——“尖了命”。六岁的我就对小姨提了一个要求:我要一个“尖了命”。
蝉声,像一条条丝带紧紧地捆绑着夏天,密不透风。猪累了,鸡累了,鸭累了,大人累了,但我不累,我要一个“尖了命”!在没有影子的夏日的正午,两个瘦小的人,在树下,在房前,在屋后,不停地走着,脚下的地都踩热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拥有一个“尖了命”,但我要一个“尖了命”,我要一个“尖了命”!
小姨总是有办法。她用玉米秸秆缠蜘蛛网,做了一个粘“尖了命”的“神器”。选一根长而笔直的玉米秸秆,再选一根细而韧的高粱秸秆,把高粱秸秆围成三角形,接口处稳稳地插在玉米秸秆的根部。做成了这个三角形长矛只是第一步,还要举着它到房前屋后犄角旮旯儿,去粘上一层层现成的蛛网。最好是蜘蛛刚吐出的丝,刚结成的网,细而韧,白而亮,黏度最好。蛛网要缠绕上三五层,不怕多,于是这个粘“尖了命”、粘蜻蜓的“神器”差不多也就成了。
屋后,几棵簇在一起的杂树,这是初秋正午唯一有阴凉的地方。小姨突然回过头嘱咐我:“悄悄地,别放声儿。”长大了,读清代袁枚的诗,“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和小姨捕蝉的情景差不多。老榆树干上趴着一只,小姨用手指给我看。没人知道这棵榆树长了多少年,反正高得我把脖子都仰疼了,但小姨会有办法。踩着一个颤巍巍的三条腿儿板凳,她一下子就高起来了,举着缠着蜘蛛网的秸秆,扑地一下,哈哈,“尖了命”到手了!暗绿色的身子,黑棕色的条纹,翠绿色的脚,透明的翅子并在背上,大眼睛在脑袋两侧,鼓起来,亮铮铮。小姨把它放在一个箩面筛下扣着,我透过箩面筛的缝隙盯着它,只等着它叫起来。小姨有好多活儿要做,可没有那么多工夫陪我听蝉叫。后来,就是我一个人守在箩面筛旁边,我还把箩面筛欠起一条小缝儿,用一根小细篾儿一顿捅,我不信“尖了命”一下午都不叫。
这可真是奇了,它愣是一下午没叫。
小姨也用一下午的时间证明了一个事儿:这只蝉是一只不会叫的哑蝉。听到这个结论,我失望到放声大哭!小姨一边用一穗嫩苞米哄我,一边把这一切归结为她自己命不好,连累了我,可体腾孩子了。都怪小姨命不好!好不容易逮到一只“尖了命”,还是个不会叫的。
小姨确实命不好。她是我姥姥最小的女儿,前脚还有个龙凤胎的哥哥。在半饥半饱的日子里,姥姥的奶水只够给和小姨一般大的小舅舅吃,她是“理所当然”被放弃的那一个。她是我的妈妈用苞米粥上的细糊糊喂大的,这似乎注定了小姨的体质就要弱一些。哥哥姐姐上生产队挣工分,由于她是家里最小的闺女,便理所应当地承担了全家的家务。姐姐出嫁了,哥哥娶嫂子了,她又成了被嫌弃的那一个。小姨也出嫁了,一个接一个生活的难题,似乎总是让她处在困顿之中。
“尖了命”不叫,这让小姨好一阵子自责。多年之后,小姨还会抱歉地和我提起,真对不起孩子,抓了一只“尖了命”还是一个哑巴。
这种土名叫“尖了命”的蝉,它的大名叫鸣鸣蝉,又叫斑透翅蝉,是北方最能叫的蝉之一。到了50岁我才知道,不会叫的蝉太多了。有雄有雌的鸣鸣蝉,也只有雄蝉会叫,雄蝉也不是天天在叫,它只是在求偶的时候才不停地叫,雌蝉却从来都是高冷范儿地沉默。盛夏,漫不透风的蝉鸣,原來是这只成虫期只有20天的小可怜在尽自己生命的全力呼唤爱情。小姨一点都不知道这些。如果小姨还活着,我一定要和她好好说说这件事,这世界上不会叫的蝉比会叫的蝉多了去了。
对鸡鸭说话的三姑娘姨
我坐在马车的后面,别人的脸大多朝着前面。我搭着马车的边儿,两条腿向下当啷着,脸向后看着。刚下过雨,马车走得极慢,路上的泥,在车轮的碾轧下安然地向旁边翻起两道泥浪,几寸深的车辙忠实地跟在马车后面。路旁,翠蓝的马兰花自顾自地开着。它们不怕烂泥迸溅到脸上,它们啥都不怕。
我和大人们去赶席。老张家的三姑娘姨出嫁,我是娘家客。当我们坐着的马车驶出村里的时候,村西头的果园边上,一个矮壮的年轻男子的身影一闪就不见了。
我至今不知道三姑娘姨的名字,只知道她是老张家排行老三的闺女,家里人叫她三姑娘,村里的人便叫她三姑娘。我隐约记得她有一张长满雀斑的圆脸。她像我的小姨一样,因为在家里年纪最小,就理所应当地承担全家七八口人做饭的家务。因为不能分身下地劳作,没有时间到生产队里挣工分,便成了哥哥嫂子嘴里那个“吃闲饭的”,连她们自己有时也这么认为,好像欠了家里人多大的人情似的。
我之所以记住她,是因为妈妈说,老张家的三姑娘真是个怪人,还对鸡鸭说话。她家的鸡鸭都有名字。妈妈还学起她喂鸡的样子:
大芦花小芦花,快来快来吧。
大白鸭小灰鸭,你们在边上等等吧。
五花大公鸡,护好你的媳妇儿吧。
妈妈边学边笑,这是一个多么不一样的女子。我也跟着笑,虽然我并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可笑。小姨在一旁说,在家干一天活儿,实在是能把人憋坏呢!妈妈说三姑娘的脑子有时不太通,和鸡鸭能唠出个啥?
小姨有的时候也带我去三姑娘姨家玩。三姑娘姨问我叫她啥,我说“三姑娘姨”,大家都乐起来。小姨批评我不懂规矩,小姨的语气可是带着笑的,我很得意自己的机灵。三姑娘姨见到我总是很欢喜的样子。她能变出来各种好吃的给我,比如,到菜园子里去找一个被绿叶遮蔽的嫩黄瓜,摘一个藏在田垄深处的小紫茄子。实在什么都没有了,她看见我来了,就操起烧火棍,在灰烬烤人的灶坑那儿埋点什么。然后,她和小姨站著说会儿话,有香味儿飘出来了,她就从火堆里扒拉出来一个烤熟的土豆、板栗或者地瓜给我吃。
小姨便推辞,你把孩子惯成了,下回没有也指望上了。
三姑娘姨说,指望上,还能有啥?都是园子里的,长啥吃啥。
我往小姨身后稍着,抬头去看小姨的脸。小姨鼓励我,接着吧。就这个姨给的东西吃,别人给的不能要。
我便伸出手去接。我不知道三姑娘姨和别的姨有什么不同,反正我小姨就是这么嘱咐我的。三姑娘姨把好吃的递到我手里,从来不忘嘱咐我一句,大口吃,别装假。
我这边吃着,那边两个年龄相近的女子就站在院子里说着话。有一年,我记得她俩在商量一起买布做过年穿的衣裳。小姨说,她问过当裁缝的嫂子了,她俩身量差不多高,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套着裁,能省一分布。掂过来倒过去的,我听不太懂,但记得三姑娘姨说,过年家里不一定给她买新衣裳。说到这里,小姨和三姑娘姨都有了落寞的神情。说到最后,连小姨自己也不确定,过年家里能不能给她买布做新衣裳了。
三姑娘姨像突然想起来:哎!忘了喂鸡了!她便开始唤:
开饭,开饭,开饭啦!
大芦花小芦花,快来快来吧。
鸡和鸭向三姑娘姨围拢过来。四五只芦花母鸡,占据了主位,头也不抬,稳稳地霸着装满菜叶子的木头槽子。鸭子们好像晚了半步。一只顶着红冠子的大公鸡,昂着头,在母鸡四周转着,警卫着,一口食都不吃。鸭子们嘎嘎地在母鸡身边叫着、催着,一副不吃到口就不闭嘴的架势,却半步不敢上前,偶尔有母鸡吃剩下掉到槽子外面的叶子,鸭子才敢瞅空上前叼一口。不过,还没等伸脖子把这口食儿咽下去,鸭子的屁股一定会被大公鸡狠狠啄上几下。大公鸡昂着脖子,眼睛滴溜溜圆,脖子四周的黄羽毛挲着,喉咙威严地呼噜着。
大白鸭小灰鸭,边上等等吧,等等吧,
小心公鸡把你们叨成光腚鸭!
五花大公鸡,一点都不馋,
东望望,西看看,
好吃好喝都留给媳妇儿哪!
三姑娘姨继续念叨着。三姑娘姨和我妈说的不一样,她一点都不怪,她说的话真逗乐儿。她家的大公鸡也带劲儿,我立在那儿瞅,连着声地说好看、好看,却说不出这只大公鸡哪里好看。
三姑娘姨说,你也觉得好看吧?对,这只公鸡有五个颜色。我可看不出来有五个颜色,她便一个个地指给我看——红冠子、黄羽毛、绿羽毛、红羽毛、褐羽毛、黑羽毛,这样一数,六个颜色了。三姑娘姨说这是最好看的大公鸡。
长大了,看白朴的诗:“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这里写的鸡也好看,但我觉得没有三姑娘姨的大公鸡好看。唐寅在诗中这样写过公鸡:“头上红冠不用裁,满身雪白走将来。平生不敢轻言语,一叫千门万户开。”这更像是白羽鸡,不是三姑娘姨的六彩大公鸡。
过了不长时间,我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因为大舅给小姨买了两斤墨绿色的毛线,没有经过大舅母的同意,于是,愤怒的大舅母在院子当间抄起叉草用的二齿叉子,武武喧喧地扎向大舅。我正坐在灶台角吃一碗极费工夫的海钱儿。海钱儿小得像小孩儿的指甲盖那么大,我正按照小姨的叮嘱,拿一根针,用针鼻儿那头儿挑着海钱儿解馋。待我探出脑壳,姥姥家的墙头已长出全村人的脑袋。冬天的农家院里,一切都枯瘦了,人的脸显得异常大。七岁的我在最短的时间里判断了形势,并抓住了重点。我放下绿色的搪瓷小碗,紧跟在大舅母的后面,并揪住她粉底黑格的衣后襟,不断地哀求:大舅母,大舅母,别打了,看我面子,看我面子,别打了。
我之所以记住我说了啥,是这件事过后,村里人见了我,都会拉住我:来,让我看看你的面子!让我看看你的面子在哪儿呢?还看你面子别打了,你一个小破孩儿,还有面子?有人还扳过我的脸,审视着,好像在用目光丈量我的面子有多大。
小姨把大哥给的两斤毛线还了回去,事情总算平息了。但过年,小姨可以做一件新罩衣了。小姨又去找三姑娘姨,鼓励三姑娘姨也让家里给做一件新罩衣。我记得,三姑娘姨没说行,也没说不行,但那天,她没给我准备任何好吃的,这一点,我记得特别清晰。我还真是被三姑娘姨惯成了。
几天后,是三姑娘姨来找小姨。三姑娘姨长满雀斑的脸,颜色变得更深了,并不断地用系在肚子前的围裙擦她的手,说,她也可以做一件新的罩衣了。两个姨都很开心的样子。那一天,三姑娘姨还给我带了一个甜香的国光苹果。小姨被她的国光苹果晃得有点不知所措,问她哪里弄来的这么好的东西。三姑娘姨又用手搓了搓自己的围裙,说是谁谁给的。说那个名字的时候,她的声音真小啊,我费了好大的力气也没听清楚。小姨说我是狗鼻子、猫耳朵,我都没听清楚,但我清晰地闻到了苹果甜甜的味道,三姑娘姨给我的国光苹果可真香啊。
三姑娘姨还告诉小姨,有人给她的哥哥提亲,要是她哥中意,女方也看中了的话,转年春,她就能有嫂子了。有嫂子做饭,她也可以下地干活儿,不用穿件新衣裳也看家里人眼色了。
但是,后来事情的发展有点超出预料,她哥快娶亲了,三姑娘姨竟然也要出嫁了。这事儿,说起来有点麻烦。因为她家“成分高”,三姑娘姨的哥哥一直娶不上媳妇,好不容易有来提亲的,那女子有很严重的哮喘病,三姑娘姨的哥哥也认了。这个准嫂子在三姑娘姨的家里看了又看,从外屋走到里屋,从房前走到房后,看完了家,还拉起三姑娘姨的手,左看右看。回去之后,那女子又提了一个条件:要换亲。
也就是三姑娘姨要嫁给她的弟弟,她才肯嫁给三姑娘姨的哥哥。
换亲的事,就在三姑娘姨不知道的情况下定了下来。转过年开春的时候,妈妈和小姨带着我以婆家人的身份赶完了三姑娘姨哥哥的酒席,又以娘家人的身份去赶三姑娘姨的酒席。
坐在马车后面,当我把马兰花都看腻了的时候,终于到了三姑娘姨的婆家。我们这些娘家人在屋子里吃席,婆家人只能等娘家人用完了才能入席,泥泞的院子里,站着等待吃席的婆家人,他们像沉默的篱笆,把我们这些娘家人围在了中间。
成了新娘子的三姑娘姨穿着红格翻领上衣,新崭崭的,我真替三姑娘姨高兴,她终于穿上了新衣裳。只是,她的脸上木呆呆的,见了我,却没忘了像以前那样嘱咐我:大口吃,别装假。三姑娘姨的新郎,穿了一套半新的松松垮垮的藏蓝色衣服,立领,四个兜,我妈说这是干部服。我妈还低声和小姨说,这衣服像是借的。我完全没记住新郎长的样子,只记得,他家的房梁是裸露的,可以一直看到屋顶,横梁上挂着一个长长的黑铁钩,铁钩上挂着一个荆条子编的饭筐。他家的狸花猫吊在那饭筐上,不知筐里藏了什么好东西。大家都在谈论那只猫,四六不靠,它是怎么吊到饭筐上的。
来了个白胡子仙人
姥姥家前面就是海,海边有一座突兀的小山包,这个小山包上没有任何建筑。我是很少到这上去玩的,实在是没有什么好玩的,除了石头,就是沙砾,连棵树都长不正。村里人叫它龙王庙。也许是很多很多年以前,这山包上供奉过龙王吧。住在海边的人,哪里有不敬畏龙王的呢?
先前,我和小姨来这里挖过小根蒜。还是早春的时候,大地还灰淘淘的,树上的鸟窝,每根枝儿怎么搭都看得真真的,大片的绿还憋在地下面,只有小根蒜最刚烈,最着急。它细细长长的叶子早早冒出地面,在风里东倒西歪,但鲜绿绿的,耀人眼目。
我和小姨每人一把长方形刀铲、一只细荆条筐,我的小一点儿,她的大一点儿。我俩从家里一路走,一路挖,只低头,不看路,受小根蒜的指引,一路曲曲折折竟然就上到了龙王庙。或许是人来得少的缘故,这山上的小根蒜最是密集,叶子比别处的要细,一窝连着一窝,一簇挨着一簇。回到家,大人们用小根蒜蘸豆酱吃,小姨用小根蒜炒鸡蛋,翠绿金黄,只有姥爷和我吃。第二天,又来。龙王庙山上的小根蒜好像一宿之间就会长出来好多,怎么也挖不完。
过了没几天,这龙王庙上的人突然多起来,比兴隆岗大集上的人都要多。吃晚饭的时候,听妈妈说——当然妈妈也是听前阳或大邵屯或于坎屯的人说的——前几天,雷声大作那个晚上,这山上来了一个白胡子仙人,这仙人带着药来的,有求必应。没有人见过他的样子,他也不给人开方子,只赐药。求药的人要准备一杯酒,蒙上一块红布,在酒杯前跪下,把自己的病症念叨出来,求那白胡子仙人行行好,赐给一碗救苦救难的仙药。据说,所有来求的人都得了药。
一向冷清的龙王庙,上上下下、沟沟坎坎都跪满了人,每个人前面都有一杯酒或几杯酒。多出那一杯或几杯,据说是给家人代求的。
20世纪80年代,我正在乡下小学念一年级,瘦弱,多病,又细又黃的小辫子挂在苍白的脸旁,是个不让人省心的孩子。我的病有点儿多,爱感冒,肚子疼,不爱吃饭,精瘦。这让我高大健壮的妈妈着实有点烦恼。
下午放学回家,妈妈把一个酒杯递给我,说里面是龙王庙上白胡子仙人赐的药,让我一口喝下去。我闻着有酒味儿,说啥也不喝。妈妈说:“我就往里滴了几滴酒,有什么打紧!再说了,那酒也不是给你喝的,那是孝敬白胡子仙人的,你就借光闻个味儿。”
我迟疑着接过来,边闻边细细看那杯子里有啥,还别说,杯底儿那还真有几颗细小的黄粒儿,小米粒大小,清晰可辨。我嚷嚷道:“看到了,看到了,是山上的土渣渣掉进去了!”
这话受到了母亲的严厉申斥:“嘴尖舌快!不说话能把你当哑巴卖了?”母亲给了我一杵子,她接过杯子,边看边说:“这明明是仙人给的药,要是土渣儿掉进来早没魂儿了,让你一口喝下去,你就喝下去。”
说来也怪,求药的碗是盖着红布的,这几颗“小米粒儿”是咋进去的呢?我知道再多问多说一定会遭受更严厉的申斥,便学着大人的样子,念叨着“发昏挡不住死”,一仰脖便喝了下去。
龙王庙上的热闹足足持续了一个多月,不知道因为啥,山上,对着一杯蒙着红布的酒杯跪拜的人又慢慢少了,也许是农活儿越来越忙的缘故吧。但十里八村,哪些人都有些什么难以启齿的病,却不再是什么秘密。三顺子十四岁了还尿炕,二狗子的爸爸一直不能那啥,于家的三妹结婚两年总是揣不上崽儿,老王家的四儿子长了一身桃花癣……大家你挨着我,我挤着你,都跪在山上说给仙人听,仙人听没听到不知道了,紧挨着的人都听了个真真儿的,于是你传给我、我传他,最后还因此闹起了纠纷,再见面就讪讪的,连话也不爱搭了。
再说我喝了这仙药,慢慢地,身体还真是越来越好了。不再经常感冒,人好像也胖了点儿,半夜被拎起来灌药的事基本没有了。我妈总是又神秘又兴奋地对别人夸这白胡子仙人的神药,那几个小泥粒,已经被描述成仙丹的样子,连我自己都恍惚,那天喝下的是金光闪闪的神药吧?龙王庙却一直冷清下来,村里的人都在传,那白胡子仙人被别的地方请了去,人家那地方比我们这儿有钱,给盖了小庙,塑了金身,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
自从我喝了那“仙药”,我妈也加紧了对我的盯防。那时我刚刚上小学,每天中午走回家吃饭,再走回去上学,路上咋的也得几里地,但我的食量并没有变大。妈妈不知从哪里弄了一小袋白面。早上,她烫点软面,扯成小条,用油炸了给我当早饭。一起上学的孩子都馋,央求我给他们也尝一小点儿。我让他们排好队,一人一口,并大声嘱咐:“少咬点儿,少咬点儿!”
午饭,我妈采取“高压硬填法”。她给我盛好一碗菜、一碗饭,往炕上的方桌上一放,必须全吃完再上学。盛饭的时候,我眼见她用饭铲把饭盛满,压实,再盛,再压。这饭量超过我的肚量太多,我是绝对吃不完的。
我妈说:“吃不完?就别上学!”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剩下哭。这丝毫打动不了我妈,她高大的身躯堵在门口那儿,任凭喊我一起走的同学怎么催促,都打动不了她。
我在门里一边哭一边吃,一边叨咕:“晚了,晚了。”
“知道晚了就快吃。”我妈的脸拉拉着,用余光扫着我,语调平缓,一点不开晴。
“那我拿一块饼子,搁道上吃吧?”我试着和我妈商量。
“别熊我了。你以为我能信你?前天,你一到村西头就把饼子扔给老张家狗吃了。我还没倒出空儿骂你。糟蹋粮食丧天良,天打五雷轰。”我妈就会吓唬人。
“狗吃了也不叫糟蹋。”我在心里顶撞着,但一声儿都没敢言语。我一口一口往嘴里压着饭,直到全吃完了,我妈才放我出屋。
我也有不用我妈看着吃饭的时候。我妈把地瓜蒸熟,扒了皮碾成泥,加点黏米面,没有白糖,化点糖精水和进去,做成丸子在锅里用油炸。我妈做,我在边上吃。这个味道好,又香又脆;凉的时候也好吃,又香又糯。我妈还会做一种酸味的子,大铁锅白气腾腾,我妈在锅上横一个带眼儿的板子,把发酵好的细玉米面挤成子条下到锅里,再放点“海腚根”。黄子酸溜溜,“海腚根”艮啾啾,一咬一咯吱。“海腚根”,其实是海葵,在海里像朵金丝菊花,一上了岸就变得那么丑,看着硌硬人。小姨说,它在水里好看,还答应哪天带我去海里抠“海腚根”。
不过,做这样好饭的时候太少了。这些饭都好吃,但我家里有一个规矩:好饭好吃,但不让说。只要一说啥好吃,我妈一定会说一句:“啥好吃?啥不好吃?都好吃。一个姑娘家,要是嘴馋,准没有好事。”我妈说这话的时候,语速快,目光冷,剜我一下,比剜菜的小刀都快。
开始的几个月,我几乎天天中午哭着吃饭,所幸没有得胃病。我的食量却一天天大起来,不知不觉,我的身体也壮起来。现在想一想,药效最灵的那个仙人,也许是我妈吧。
再回南尖,我还会越过稻田,往远处望望那个不当不正的小山包,然后,大家又说一遍向白胡子仙人求药的热闹事。前年回去,那个小山包已被炸平了。我的心也空了一下,好像一个在路上行走的人,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路标。
老狗差点儿吃上“公粮”
姥爷养的那条老狗,一点儿不好看。我认识它的时候,它其实并不老,但就是让人觉得它老。它的皮毛以棕色为主,夹杂着黑色,暗暗的,全身都是这样,像极了一年四季只穿一套土布衣裳的老农民。它眉目低垂,看人只一眼就低下眼睑,从不敢再多看几眼。我妈却喜欢它。姥爷把它领回家半年多了,我妈才从沈阳回到庄河,但它见我妈第一面就不咬不叫,还凑上前,讨好地在我妈和我的身边转来转去。我妈就说,狗不咬嫁出门的姑娘,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姥爷出门,它要跟在身后。我出门,它也要跟着,我可不让。它实在是不好看,不威风,不神气。我转过身,冲着它喊,回家去!回家去!老狗便夹着尾巴,看我一眼,又低下头,转一个大弯儿,慢腾腾地走了。我继续走,走不多远,再回头,它还在跟着。我又转过身,冲着它喊,回家去!回家去!
反正,我不想让它跟着,它看起来属实不太体面。
我上小学的地方,要走几里地。从这个村子,越过另一个村子,再到第三个村子那儿。这一路最让人心怦怦跳的,是要经过村西头的国营农场。国营农场是国家办的农业企业,人是国家的,物是国家的,秋收打上来的粮食也是国家的。农场里的人骑自行车,穿的确良。据大人说,农场里的人每个月还拿现钱。农场里有带斗的解放牌汽车,有红色的拖拉機。农场还养了两只大狼狗,耳朵尖尖立着,狗眼上还长了两小块白毛斑,像在一双眼睛之外又增加了一双眼睛。不知道这两只狼狗每个月拿不拿现钱,我就没看见这两只狼狗睡过觉,它们像自己的耳朵那样,端端正正地立着,警惕性十足,从不萎糜。每次我路过国营农场,都提溜着小心脏,连眼皮都不敢抬。只要我敢看那狼狗一眼,它一定报我一声吠叫,好像我的目光对它都是一种冒犯。
冬天的早晨去上学,最是可怕。七点到校,最迟六点二十必须从家出发,那时还没有一点儿天光,天黑得比锅底还黑。路过农场时接近六点半,国营农场的大喇叭里播放着中央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前奏曲,在一声比一声更高的“胜利歌声多么嘹亮”的音乐里,我和同村的小同学扯着手,连大气都不敢喘。国营农场的旗杆上高挂着几盏雪亮的汽灯,帮着大狼狗把我照得无处可藏。
过了农场,上学的路重新陷入黑暗,但比起目光如炬的狼狗,黑根本不算啥。直到我们上完第一堂课,天才能真正放亮。
这样的日子不知过了多少天。一天,一个坐在教室后排的男生突然指着窗外大喊:谁家的狗?!谁家的狗?!几个同学伸出头,又缩回来,放心地坐下。我愈发地不安,往窗外一看,果然是我家的老狗。它安静地趴在教室外的墙根儿那儿,不知趴了多久。几个男孩儿跑出去,拾起地上的石头投它。老狗呜咽了几声,起身往远处走了,又趴下。它选择的距离不远不近,正好在男孩子的石块投不到的位置上。我没有办法阻止男同学的恶作剧,只能冲老狗喊,回家去,回家去!
老狗看了我一眼,站起来,低下头,弯过身,走了。我怕老狗像以前那样,假装走,再回来,便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头,冲它挥了挥。老狗没有再出现在学校的窗外。冬天真长啊,我上学路过农场的时候,慢慢已不再那么怕了,因为我时时能感到一条老狗悄无声息的陪伴。我不再撵它,我进了教室,它自己就回家了。
老狗在1975年海城地震中出了大风头,差点给家里挣来两麻袋苞米并成为吃公粮的特权狗。
国家在第一次地震工作会议上,定下了“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多路探索”的地震监测预报总方针。所谓群测群防,指的是老百姓也要参与地震监测预报。没想到的是,动物也因为对自然变化的敏锐而成为“群测群防”的一员。时至今日,各个城市的地震局仍然养着一群先知先觉的小动物。根据“预防为主”的方针,辽宁南部被作为重点监视地区,加强前兆观察。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地震,“群防群测”就展现出了“神威”。辽宁省南部有一百多万人撤离他们的住宅和工作地点——仅仅在两个半小时之后,海城被7.3级强烈地震击中。
庄河也有强烈的震感。那几天,家家户户都在院子里搭了地震棚。地震棚看起来像个粮仓,里面用半粗不细的木头起个床架子,架子上铺着稻草,四周用苞米秸子挡风,顶上是稻草搭的棚。地震那天,正是腊月二十四,立春,地震棚四面透风,冷得伸不出手。孩子们有自己穴居的快乐,妈妈和小姨再也不一声声喊我回家吃饭、睡觉了。多冷都不打紧。我们钻进麦草垛里,拱来拱去,像一头头生机勃勃的小兽。麦草有一股清冷的香味儿,一扒开草缝儿,能看见星星和细细的月牙儿。喇叭里,当时的庄河县县长张有山一直在广播:“石山发现地光,石山发现地光,石山发现地光。”石山是个村名,村里有山但不高,石头倒不少,地光,就是地面上有强烈闪光,像闪电一样。懂的人都懂,县长张有山是在提醒,这是地震前兆,可能要有地震了。会捏面活儿的邻居王姥姥耳朵不大好,一直在问她的大儿子——队长王幸福:“广播里怎么总说有地瓜,有地瓜?”
地震之后,不知从哪一级政府那儿来了几个人,到村子里打听这几天村子里哪家动物出现了异常。也许是因为与平时老成持重的做派反差太大,村里人一致举荐老狗,都说,姥爷的老狗最“格路”,和平时大不一样,它跳到柴火棚子上不停地叫。这让几个政府的人煞是兴奋,说啥要把老狗带走,并承诺拿两麻袋苞米穗子换。
姥爷说,我家狗不值钱,不值两麻袋苞米穗子。
政府的人以为姥爷嫌少。政府的人说:错了,刚才说错了,不是苞米穗子,是给两麻袋苞米粒子。
庄稼人都懂得啊,两麻袋苞米穗子也扒不出一麻袋苞米粒子。这可真没少给!怕姥爷还不舍得,政府的人又说,狗是去做地震预测,是给公家做事,吃得好,住得好,是大好事,相当于吃公粮、皇粮啊!
姥爷说,皇粮民粮,吃到狗嘴里就是一口狗粮,不换。
一旁看热闹的村民都说姥爷死心眼儿,啥狗值这么多粮。
姥爷说,不换,这是家里一口人,怎么换!
这是一辈子见人矮三分的姥爷少有的“抗上”行为。政府的人也讲道理,没有强抢民狗,没有硬来。当然,姥爷最后也答应政府的人,这条狗有了什么“格路”的事儿,赶紧报告政府。
这大半天里,老狗承受了太多的关注,这么多人目光叠加在一起的重量让老狗不安。老狗似乎也知道人们的争执都是因为它,它紧紧跟着姥爷,半步不落,偶尔看别人一眼,再赶紧低下头。
外人都走了之后,老狗对着姥爷一顿螺旋状摇尾巴,那欢喜的样子像过年得了一根大肉骨头。老狗就这么留下了。如果老狗懂得人的世界,不知道会不会埋怨姥爷让它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阶层跨越”的机会。
三年之后,從不离开家、从不离开家人的老狗不辞而别了。姥爷拎着铁锹找到它的时候,它躺在离家不远的稻田坝埂下面。那是一处又窝风又暖和的地方。它已经死了。姥爷在它自己选定的地方挖了一个深坑,把它埋了。
在那个小小的土堆前,姥爷站了好久。
“好狗不死在家里”,这话还真是不虚,但到底是为啥,没人讲得清楚。
点“序儿”
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人在年里长胖了,月亮在天上也变圆了。正月十五的晚上,是农历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天上,是明晃晃的月亮和清冷的星子;地上,一向节俭的农家大院灯火簇簇。有的灯火,在屋檐下安静地跳跃着;有的灯火,在乡村的土路上疾走。在这万千灯火里,有一盏是属于我和我的“序儿”的。
正月十五的晚上,水缸里要放鱼灯,用豆面捏的卧鲤鱼,背上驮着蜡烛,安放在葫芦瓢底,漂在水缸里,祈祷年年有鱼;灶台上要放一只头颈高昂的豆面大公鸡,等着吃锅里剩下的米粒,象征勤俭持家;粮囤里也要有灯,而且要十二盏,代表一年四季丰衣足食。大人们还神秘兮兮地说,能从灯盏里剩下的油占卜出新的一年是旱是涝。这看起来一模一样的灯,怎么能代表十二个月呢?大人们聪明,在豆面上捏出褶,褶的数量代表月份,捏一个褶代表一月,两个褶代表二月……十二个褶就代表十二月。面盏里放油,等到灯火熄灭了,盏内剩下多少油,就能知道哪个月旱、哪个月涝了。其实大人们并不会因为这简单的占卜结果而较真儿、纠结,这算是个占卜游戏吧。
小孩子们也拥有自己的灯——属相灯,你属什么就用豆面捏个什么动物。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属相,它会跟随一个人一辈子。在庄河,属相也叫作“序儿”。至于为什么叫“序儿”,大概是方言的原因吧。在庄河,读书,叫读须,又加上庄河话多读去声,听起来狠丢丢的,加上喜欢儿化,属相就成了“序儿”。“序儿”听起来也理直气壮,属相不就是代表着一种年龄的秩序吗?
现在庄河过年,集市上披红挂绿的属相玩偶应有尽有,很多款式美得不要不要的,小孩子们挤在属相摊前,想要啥买啥。我小时候在老家,传统的属相灯就是用豆面捏成的。最好是上一年打的新黄豆磨成的豆粉,用清水和成面团,小姨也会往豆面里偷偷给我加几滴豆油,再在粗陶盆里揉来揉去,豆面团便会表面光光,不沾手,还筋道。豆面就是黄豆的颜色,没有别的啥颜色。豆面团捏好了,小姨就会把豆面团把往我手里一放:“拿好了。去!找王姥姥吧!”
会捏面活儿的王姥姥,在正月十四、十五这两天白天,便成了村里娃们最敬畏的老人。十几个孩子,一人手里拿着一块和好的豆面,像一群小黑佛围坐在她的周围,目不错珠儿地看着王姥姥。王姥姥坐在炕上,豆面团在她手里,一手托着,一手转着,她像在回忆什么事情。不知道啥时候,也没看到哪根指头用的力,再左一捏,右一挤,用红色的火柴头或者黑色的小豆粒当眼睛或当鼻孔,便有一只只小动物神气活现地立在那一双粗糙的手上了。马站着,猪卧着,蛇盘着,狗叫着……孩子们惊讶着,翻看王姥姥的手,怕那里藏了什么魔法。王姥姥抽出压在炕席底下的长烟袋,叼上,点着,缓缓地吐出一口青烟后,才用手一指胸口:“都在这儿呢!”
我扶着王姥姥的烟笸箩,殷切切地对王姥姥说:“讲讲,讲讲。”王姥姥有时候不讲,有时候讲。一个属兔的男孩儿又把一块豆面交到王姥姥手里。王姥姥歇够了,话好像也多了,手里团着面,嘴上说着故事:“这兔啊,三瓣嘴。十二个属相就没有一个全全活活的,牛没上牙,虎没脖子,蛇没脚,马蹄不分瓣,猴没有腮……”
“那我呢?”一个大小子把脸顶到王姥姥面前,“我属龙。”
“我还不知道你属龙?”王姥姥边捏着兔子的短尾巴边说,“最有神通的就是龙,蛇身、鹿角、驼头,驴嘴,偏偏忘了给自己安个耳朵。没耳朵就听不见,要不怎么管耳背的人叫聋子。”
娃子们似懂非懂地点着头,捧着自己的“序儿”回到家,等待着晚上点灯时刻的到来。也有的孩子跑得急,绊到门槛上摔坏了手中刚捏好的属相,哭着回来,求王姥姥再重新捏一遍。
我是属猴的,自然要点猴灯。我的猴灯是个胖胖的坐猴,头戴一顶瓜皮帽,手里捧着一只硕大的桃子,不可爱,也不调皮,倒是老气横秋,温良敦厚。邻家姐姐是属马的,王姥姥的马捏得最是招人稀罕,双眼皮,毛发打着卷,黑贝壳一样的小蹄子好像在刨地。那个姐姐比我大两岁,我暗暗想,两年以后,我就和姐姐一样大,我也能属马了,也可以让王姥姥给我捏一个这样好看的马了。两年之后,我还是属猴,好像一辈子都属不上马了。家里人给我讲十二属相,讲天干地支,讲什么也没有用,我就得属一辈子猴了,这让我沮丧了好一阵子。
正月里,天仍黑得早。平时贪玩的孩子们最不喜欢天黑,但正月十五这天不同,孩子们盼着天早早黑下来,好各回各家,等着大人们点灯,再点亮自己的“序儿”。多少年后,看印度电影《大篷车》,听到那热情奔放的吉卜赛女郎高唱一声:“要过节了,户户点灯!”那时,我便会想起童年这一幕。
家里点亮的第一盏灯,要送给灶王爷的,民以食为天,绝对马虎不得,再把灯送入粮囤,送入水缸。妈妈端着灯,照照屋里屋外,照照我也照照她自己,口里念念有词:
正月里,正月正,
正月十五闹花灯。
花灯好,花灯妙,
我拿花灯照一照。
照照头,能长寿,
照照眼,看得远,
照照牙,能发家,
照照背,不受累,
照照肚,一生富,
照照手,一生有,
照照腚,不得病,
照照脚,不吃药,
照照家里亮堂堂,
各路神仙来帮忙。
我就在炕沿儿那儿,点亮我的“序儿”。有的孩子在“序儿”的旁边点亮一根细蜡烛,有的在“序儿”的背上点一盏小灯。小灯,就是在“序儿”的背上捏一个小窝窝,再用火柴棒缠上棉花做灯芯,插在灯碗的中央,倒入豆油,就可以点灯了。到晚上七时左右,小孩子将蜡烛或小碗窝窝里的灯芯点起来,静默地守在旁边,不多言也不多语,仿佛被烛光散发出的神秘力量慑住了一般。
隔壁老曹家的三小子比谁都急。天一擦黑,他就赶紧点亮他的“序儿”。当蜡烛灭了的时候,他就从锅底坑里扒出点火,放上一片碎瓦,把“序儿”切成片儿,放在瓦片上面烤一烤,满足地吃下去。他一口口吃掉自己的属性,一点儿都不可惜。第二天,他看到别的小孩儿手里拿着豆面属相出来玩,就会很有经验地说:“这要是烤着吃才香呢。”另一男孩子接着说,用油煎着吃才香。妈妈说,半大小子就是饿,肚子就是一个无底洞。
在这一天晚上,大人们最重要的事,是去给故去的先人送灯。每个大人都很勇敢。他们拎着点亮的灯,在暗夜的乡路上疾走,直到把灯送到埋葬先人的地方。灯,是生命不息的象征。据说,这也代表家族兴旺,后继有人。小孩子是不必去的,我们只需在家陪着自己的“序儿”。
我在山东泰安大汶口镇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看到过叫陶鬶的小陶猪、小陶狗。据说,这是远古时期人们用来烧水或温酒的容器。小陶猪、小陶狗的背上,有一个浅口小碗,小陶猪卧着——憨厚,小陶狗立着——機警,它们像极了王姥姥捏的豆面“序儿”,只不过脊背上多了一个半圆的提梁。隔着六千多年的时光,我任性地看到,在如豆的灯光下,几个父系氏族社会的小孩子,和我小时候一样,在每一年的正月十五,听长辈给予的穿越千年、从未老去的祝福:
正月里,正月正,
正月十五闹花灯。
花灯好,花灯妙,
我拿花灯照一照。
照照头,能长寿,
照照眼,看得远。
……
直到我离开庄河姥姥家,我共攒了十二只“序儿”。临去沈阳前,我把这些豆面猴安置在姥姥家东房门框上方的横木板上,它们终于整齐地蹲坐一排,仪态严整。多年之后,时光抽干了这些豆面猴身上的水分和油性,它们尘灰遮面,开裂破碎,就像我的长辈亲人一样,在时光中老去,最终归于尘土。但我一直毫不怀疑,它们也和我的亲人一样,一直在尽心尽意地守护着一个孩子遗落在田园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