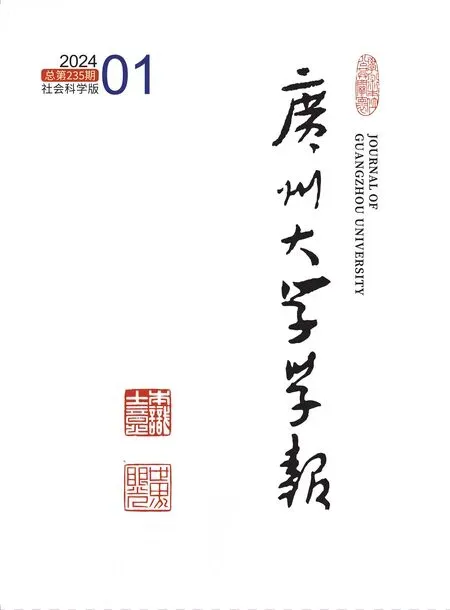“河朔唐诗之路”研究
——兼论文学景观与文学地理意象
2024-05-10马吉照
马吉照
(河北大学文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
一、引 言
“唐诗之路”被用来描述和指称唐代诗人行迹和诗歌相对集中因而具有诗路性质的交通行旅线路,对“唐诗之路”的揭示和研究,通常以特定线性空间中的诗人行迹、创作,以及沿途的文学景观为中心,考察地理环境、交通路线等同唐诗创作之间的影响与互动,可以视作文学地理学研究中打破行政区域局限的一类个案研究。
从竺岳兵先生首揭的“浙东唐诗之路”到后继研究者论列的陇右、两京、商於、大庾岭等处“唐诗之路”,皆各有其丰富而独特的内涵。就研究的侧重点而言,或重在文学景观的揭示和研究,或重在交通与唐诗之关系、诗路创作与沿途区域文化之关系;就不同“唐诗之路”上的景观风貌而言,浙东、浙西的奇山秀水,与西北的粗犷宏阔、唐代岭南的荒蛮偏远等,又各自呈现迥乎不同的风格面向。不同的“唐诗之路”,其空间距离和时间绵延的长短各不相同,涉及地域空间的广狭不同,诗人经行与创作的密集度、作为诗歌之路的典型性亦有所差别,诗人在诗路的活动、创作与文学史、与唐代历史文化的关联度和价值意义也存在差异。丰富而多元,既有相似相关的共性又各具特色与价值,无法彼此代替。因此,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和更多研究者的加入,必然有更多“唐诗之路”被发现和描述出来,与“浙东唐诗之路”等诗歌线路共同构成璀璨唐诗版图上纵横交错、熠熠生辉的经纬线。
从根本上说,全国各地必定存在不同风貌、不同价值的“唐诗之路”,这是由中国文化丰富的区域性、地方性所决定的。放眼世界,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既有辽阔的国土、复杂多样的区域格局,每个区域又各自积累了源远流长、丰富海量的地方文献和文学叙说。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如齐鲁、燕赵,如江南、岭南,其文化的丰富性比之一般中小国家不遑多让;体量相当的大国,就悠久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地域文化的多样性而言,较中国似有不及。因此,笔者对刘成纪关于“地理的区域性、地方性就是文化的中国性”①这一论断深表赞同,应当说,地域空间之多元,不同地域空间文化风貌之丰富,与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罕有其匹的历史连续性一样,都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属性和重要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区域性、地方性有着深切关注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就是关于“文化的中国性”的研究,关注不同地域空间的唐诗风貌及其独特价值的“唐诗之路”研究,自然也不例外。
二、“河朔唐诗之路”的路线、诗人行迹与诗歌创作
在洒满星辉的唐诗地理版图上,太行山东麓连接中原与北方巨镇幽州(今北京)的南北交通大道和燕山南麓自幽州通往碣石、榆关等东北边塞之地的东西交通线路,如同一撇一捺画出一个巨大的“人”字,同两京之间、浙东、陇右等处具有诗路性质的文化线路一样,是一条地位举足轻重、具有突出自身优势和鲜明地域文化特质的“唐诗之路”。因唐人常以“河朔”代称河北,本文遂将这条地处唐时河北道的诗歌线路称为“河朔唐诗之路”。
“河朔唐诗之路”起自今豫北冀南地区,以幽州为中点,终点在今河北秦皇岛的碣石、榆关一带,是一条早在商周时期业已形成的古老道路。诗路南段,连接燕赵与中原的太行东麓南北大道,唐人常称为“邯郸道”,如储光羲《效古二首》“晨登凉风台,暮走邯郸道”[1]1380,李德裕《秋日登郡楼望赞皇山感而成咏》“北指邯郸道,应无归去期”[1]5429。唐时“邯郸道”沿线由南至北分布着殷商旧都所在的相州(今河南安阳),历史底蕴深厚的赵都邯郸(今河北邯郸),以邢窑白瓷闻名天下的邢州(今河北邢台),成德藩镇驻地、太行东麓大道与五台山进香道十字交汇点的名城镇州(今河北正定),全国重要的丝织业中心定州(今河北定州)②,易定节度使驻地易州(今河北易县)等重要城邑。这段诗路比自幽州折向东北后的东西路线更为繁荣、喧嚣。而诗路北段所处之燕山一线,地处历史上农耕与游牧两大文明的交汇线,也是唐朝与契丹、奚族“两蕃”展开东北边塞战争之最前沿,陈子昂、高适、张籍、李益等著名诗人都在这一线写下了他们诗歌生命中的重要篇章,可以说,自幽州至碣石、榆关的燕山南麓一线与西北的陇右诗路共同孕育造就了古代诗史上灿烂夺目的唐代边塞诗。
特定交通行旅线路中拥有数量众多、分布密集的诗人行迹与创作,以及作为歌咏对象的文学景观与文学地理意象,这是决定一条“诗歌之路”所以能够成立的基本条件。
唐代前期诗人在“河朔唐诗之路”的活动与创作,撮其要者,最早是唐太宗及其群臣东征高丽途中的君臣唱和。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唐太宗率大军发自洛阳,途经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为文祭魏武帝曹操,经定州,为文祭北岳,并诏皇太子留定州监国,作《违恋》诗,薛元超、李元嘉等有和作。四月誓师于幽州城南,行至平州(今河北卢龙)有《春日望海》(许敬宗、杨师道等有多首和作)、《于北平作》等诗。九月班师,十月入临渝关,归至定州时有《宴中山》,许敬宗等有和作。此行完整经行“河朔唐诗之路”全程,回师时诗路南段没有走完,沿太行东麓南下至定州后取山中陉道西上晋阳(今山西太原)。初唐时期,多位著名诗人曾经从军河朔,留下诗篇。调露元年(679),骆宾王从军北方边塞,在河朔作有《于易水送人》《边夜有怀》等名篇,易水送别处的燕下都在今河北易县,为太行东麓大道沿线的重要历史文化遗址和文学景观。万岁通天元年(696)七月,唐朝以梁王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防御契丹,著名诗人崔融随军东征,杜审言、陈子昂皆有诗赠别,崔融此行至今河北东北部、辽宁南部一带,作《塞垣行》《塞垣寄内》等篇。九月,建安王武攸宜为右武威卫大将军讨契丹,陈子昂随军为参谋,“负剑登蓟门,孤游入燕市”(卢藏用《宋主簿鸣皋梦赵六予未及报而陈子云亡今追为此诗答宋兼贻平昔游旧》)[1]998,写出千古绝唱《登幽州台歌》及《蓟丘览古赠卢藏用七首》《登蓟城西北楼送崔著作融入都》诸篇。
盛唐时期,张说先后两次任职河北,玄宗先天二年(713),张说出为相州刺史,充河北道按察使,开元六年(718),又由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迁幽州都督、河北节度使,张说先驻节于诗路南段的相州,后驻节于诗路的中点幽州,在河朔留下名作《邺都引》及《幽州送尹懋成妇》《幽州元日》等篇。开元十九年(731)至开元二十一年(733)间,高适北游河朔,经魏州(今河北大名)、巨鹿(今属河北)至真定(今河北正定)、蓟门(今北京南),全程经行“河朔唐诗之路”,迎来其诗歌生命中一次重要的创作高潮,数年后,又结合此行见闻,写出一生最负盛名的代表作《燕歌行》。其时,王之涣亦流落蓟门,高适访之不遇,有《蓟门不遇王之涣郭密之因以留赠》。开元二十四年(736),杜甫“放荡齐赵间”,“春歌丛台上”(杜甫《壮游》)[1]2363。开元二十九年(741),岑参游河朔,经行河朔诗路南段的邯郸、井陉、定州等地并留有诗作。天宝九载(750)冬,高适在封丘尉任上送兵至清夷军(今河北怀来),有《送兵到蓟北》《使青夷军入居庸关三首》等篇。天宝十一载(752),李白游燕赵,沿太行东麓大道经邯郸、临洺(今河北永年)等地北上幽州,有诗《登邯郸洪波台置酒观发兵》《赠临洺县令皓弟》等多首,并在《北风行》中留下“燕山雪花大如席”这样带有鲜明北方地域色彩的千古名句。储光羲约于天宝十三载(754)取河朔诗路南段的太行东麓大道,奉使北上至幽州,有《效古二首》《观范阳递俘》等作。
中晚唐时期,太行东麓大道沿线的本土诗人如李嘉祐、崔峒、司空曙、于鹄、刘言史、贾岛、无可、公乘亿等都有在家乡生活、创作的经历。大历时期多位避地南方的著名诗人来自河朔诗路南段,除赵郡(今河北赵县、赞皇一带)人李端未见与故土相关作品,赵郡李嘉祐、土门(今河北鹿泉)崔峒、广平(今河北永年)司空曙、中山(今河北定州)郎士元等,均有怀念家乡的作品,如李嘉祐《送从弟归河朔》、司空曙《贼平后送人北归》、崔峒《送王侍御佐婺州》(一署郎士元作)诸篇。范阳(今河北涿州)人贾岛于元和五年(810)离乡南下之前曾长期生活创作于河朔,后来在《明月山怀独孤崇鱼琢》《怀博陵古人》等多篇诗歌中表露乡关之思。
中晚唐时期在“河朔唐诗之路”留有诗篇的著名客籍诗人还有白居易、韩愈、张籍、王建、杨巨源、李益、窦常、窦牟、张继、姚合、许浑、雍陶、刘叉、张蠙、贯休、刘邺、聂夷中、罗隐、温庭筠、杜荀鹤等。其尤可值得注意者有:贞元二十年(804)岁暮白居易河北之行有名篇《邯郸冬至夜思家》及《冬至夜怀湘灵》《除夜宿洺州》等诗;长庆二年(822)韩愈宣谕镇州(今河北正定),途中及归后写有《镇州路上谨酬裴司空相公重见寄》《镇州初归》等多篇诗作;建中、贞元间,张籍、王建曾在诗路南段的今邯郸、邢台一带,“十年为道侣,几处共柴扉”(张籍《登城寄王秘书建》)[1]4325,留下不少作于“鹊山漳水”之间以及后来追忆此段经历的诗篇;张籍、王建、杨巨源、李益、姚合等人有入职河朔藩镇幕府的经历,李益且曾因在幽州作有“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献刘济》)[1]3212之句而遭降职;分别驻锡真定、赵州的两位佛教史上的著名禅师临济义玄、赵州从谂皆有诗偈存世,赵州从谂留诗17首,其圆寂后成德节度使王镕为作《哭赵州和尚》二首。
三、“河朔唐诗之路”的文学景观和文学地理意象
当自然、人文景观或者某些地名、地域、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名物反复进入文学家的吟咏和书写,并且有的还被赋予了某种特殊的人文意蕴,那么,这些景观、地名、地域、名物所涵容的人文意蕴、审美特征,它们与文学之间富有意味的互动关系,就会成为文学地理学研究重点关注的话题。而历史地理学者也常常从他们的学科角度利用文学材料对以上对象展开研究。于是出现了许多近似的概括和命名——曾大兴以岭南为重点,侧重研究“文学景观”[2],胡阿祥将刘禹锡诗中的“乌衣巷”等金陵意象称为“地名意境”[3],张伟然称“地理意象”[4],胡晓明称“‘地方’意象”[5],由于研究对象情况复杂多元,研究者各自命名,但求自洽,其所指和侧重点既多有交叉,亦各有差异,并未形成一致通用的概念和明确清楚的区分。杜华平近年对此做了专门关注和深刻探讨,他从意象与现实地理客体的对应关系出发,将地理意象分为写实性地理意象、符号性地理意象、虚拟性或象征性地理意象三种类型。在这一分类中,现实中真实可见的文学景观如泰山、岳阳楼,或齐鲁、燕赵,皆属写实性地理意象,而包含历史典故、与作家本人所在地点无关的地名(如本文要论及的“漳滨”等)则被归为符号性地理意象。如此说来,现实可见的文学景观就被包含在地理意象的大概念之内,是地理意象的一种类型。不过,杜先生又说:“文学景观写入作品的时候,它是地理意象;地理意象写在大地的时候,它是文学景观。”[6]如此,文学景观又与地理意象不做区分,将两者视为呈现于文本内外的同一回事。以上可见,反复进入文学家吟咏和书写的地名、景观、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名物等,虽已成为广受文学地理学乃至历史地理学研究者关注的热点话题,但应如何为其定义,应赋予其怎样的理论术语,仍有待于学界同人在更多的研究、交流,以及更多个案研究的实际运用中逐渐形成共识。而澄清概念,恰恰是今后提升相关研究的可操作性和深度、广度的必然前提。有鉴于此,本文以“河朔唐诗之路”的情况为例,对前述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古代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视阈中,一切自然、人文景观,经文学家反复吟咏和书写,即可谓之文学景观。文学景观通常是现实可见的,文学作品中虚构的地理空间可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景观。
文学景观或特定的地名、地域,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名物,反复进入文学家的吟咏和书写,并因此具有了某种特殊的人文意蕴乃至特别的文化标志意义,则可谓之文学地理意象。文学地理意象的根本特质是其意象性,即必须相对稳定地承载某种特定的意蕴和情调。
同一个与地理空间有关的名词、名物,在不同的作品中,可能作为文学地理意象使用,也可能仅具有文学景观的意义。文学景观作为具体、实在的“地方”(place),往往是文学地理意象在地理空间中的现实载体,但文学景观并不因此即等同于文学地理意象。虽然文学家在作品中写到文学景观和文学地理意象,都并不一定要亲临其境,但相比之下,文学地理意象更加不受时空限制,它更接近于人文地理学者所说的那种“空间”(space)。作者会说,总之我知道大地上有这样一个地理空间存在(或曾经存在),我写它,既不意味着我看见,也不意味着我要送别、赠答的对象会看见,我只是确信它可以寄托我要表达的意思,而作者和读者之间对此种寄托必然拥有共同的认知和足够的默契。
和其他“唐诗之路”一样,沿途分布着密集的文学景观与文学地理意象,是“河朔唐诗之路”之所以成立的重要依据。在指认和描述文学景观与文学地理意象时,李仲凡着眼于空间范围提出的点、线、面的三分法,极为简明、方便,对实际操作富于启示意义。李仲凡指出,在目前的文学景观研究中,主要研究的是“点”,借鉴地理学中的尺度概念,文学景观中的“线”和“面”涵容更为巨大的文学空间,我们应该关注到那些大尺度的文学景观。[7]我们将以“河朔唐诗之路”为个案样本,试析文学景观和文学地理意象的“点”“线”“面”。
先谈河朔诗路上的“点”。
曹魏邺城在今河北临漳西南,于杨坚灭北齐时被焚毁,至今犹有遗址可寻,唐时更应是可供现场凭吊的文学景观。由于建安文学诸子的文章功业和邺下之游对后世的巨大影响,曹魏所筑铜雀、冰井、金虎三台,建安文学家游宴赋诗的西园,邺城以西的曹操西陵等皆经常成为诗人吟咏的对象,其中尤以铜雀台诗数量最多。铜雀台母题诗歌或为乐府旧题,或为现场怀古,大量作品不只是对文学景观的描写。从南朝到中晚唐,不同时代诗人借助曹操遗令铜雀分香、歌伎望陵作歌的故事,寄托了不同的思想主题和时代心曲,铜雀台遂成一意蕴丰富且随时代变迁屡有变奏的文学地理意象。[8]邯郸丛台,是战国赵武灵王遗迹,杜甫、岑参、王建、李益等20余位唐代诗人写到过,且大部分都是亲自登临之作。但这些诗歌基本上属于杜华平所说的“对现实地理客体作出较写实的描述,或者说地理客体经文本化之后,面貌没有发生什么变化”[6]。因此,我们把邯郸丛台看作河朔诗路南段最为举足轻重的文学景观之一,但不认为它是文学地理意象。易水北岸战国燕下都遗址附近的河北定兴有黄金台,蓟丘(蓟门)、幽州台在今北京境内,几处遗址在唐诗中唤起的都是诗人对燕昭王千金买马骨、建黄金台招贤纳士、礼遇人才的历史追忆,因而相关诗歌总是与怀才不遇、渴望伯乐的情绪相联系,所以黄金台等既是文学景观,也是文学地理意象。
作为河朔诗路北段的著名文学景观,碣石(今河北昌黎北)在唐诗中同时寓有两层特殊的文化标志意义。它首先是征人远戍的边塞之地的代名词,如著名边塞诗人高适“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燕歌行》)[1]2217、“碣石辽西地,渔阳蓟北天”(《别冯判官》)[1]2228,其中碣石及榆关、渔阳、蓟北等地名皆可视为唐代东北边塞的代表性地标,诗人只需集中列举一下这些地名,字里行间便自然弥漫一股烟尘之气;然而,碣石有时又与战争烟尘并不相干,而是同南方的潇湘、衡阳等地理意象对举,作为北方极其僻远、苦寒之地的象征,如张若虚名篇《春江花月夜》中名句“碣石潇湘无限路”[1]1185,卢照邻“荆南兮赵北,碣石兮潇湘。澄清规于万里,照离思于千行”(《明月引》)[1]523,都只是借助碣石、潇湘两个北方、南方的地名,写月光之普照,状距离之遥远,诗中的离人,可能是边关征戍之人,但也完全可能是商人或宦游者,碣石意象此时所蕴涵的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共同认知和默契,不过是标记了地理方位上的极北之地,主要强调的是空间距离之远。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碣石附近的卢龙塞(在今河北迁安境内)虽然同样兼有文学景观和文学地理意象的双重性质,但它在唐诗中就只是与边塞之地这一层象征含义紧密联系,如“声声捣秋月,肠断卢龙戍”(刘长卿《月下听砧》)[1]1522、“自有卢龙塞,烟尘飞至今”(戎昱《塞下曲》)[1]2998等,而并不像碣石那样被当作北方极远之地的地理标志来使用。
再谈河朔诗路上的“线”性文学景观和文学地理意象。
“唐诗之路”本身就是一条条“线”状的文学景观,它们既各自包容了许多作为文学景观的“点”,又与其他的“线”纵横交错。所谓“线”性的文学景观,主要指山脉、江河、道路。就河朔诗路而言,沿途最主要的“线”性文学景观,其纵向者,是被唐人视作“天下之脊”的太行山③。河朔诗路南段大致沿太行山前海拔50米以上一线延伸(易县以北位置稍偏东),诗人走在路上大部分时间向西可以远望见黑魆魆连绵起伏的太行山脉。唐诗中直接写到太行山者有数十首,其中不乏李白“将登太行雪满山”、韩愈“谁把长剑倚太行”等奇绝佳句,但实际上太行这条景观线路又同时容纳了若干次一级的“线”和许多“点”状的文学景观。所谓次一级的“线”,如滏口陉、井陉、飞狐陉等沟通东西的山中诸陉道;有通道即有关隘,太行山中的轵关、天井关、土门关、居庸关等“点”,在唐诗中亦有广泛反映。再如古北岳恒山(今名大茂山,在今河北保定西)也是太行山中的一个重要的“点”,河朔诗路途经的恒州、镇州、常山、真定、定州等历史地名之由来,皆与古北岳恒山有关,贾岛、姚合、马戴等著名诗人皆有诗咏及北岳,特别是贾岛,早年即生长、活动于北岳一带山中,故相关诗作甚多。
太行山之外,河朔唐诗之路途经的“线”性文学地理景观以东西向为多。诗路南段主要是自太行山中流出的三条大河:漳水、滹沱和易水。
漳河今天是河北、河南两省的界河,为唐诗中“出镜”最多的河北大河之一。盛唐之李杜高岑,除了杜甫虽曾“放荡齐赵间”,但在河朔游踪较少,李白、高适、岑参都确定到过并写过漳河,前文已经提及中唐著名诗人张籍、王建,曾在河北南部同窗十载,“鹊山漳水总追随”(张籍《逢王建有赠》)[1]4346,邺城、漳水一带是两人早年经常来往流连之地。此外,由于建安文学家刘桢卧病漳水之滨的典故广为人知,漳河也经常被用作一种文学地理意象,诸如“闻说漳滨卧,题诗怨岁华”(李端《酬秘书元丞卧疾见寄》)[1]3253、“如何此幽胜,淹卧剧清漳”(李商隐《崇让宅东亭醉后沔然有作》)[1]6241等句,在这些例子中,漳滨、清漳成了卧病、退隐的代名词,而与诗人的真实行迹全然无关。
滹沱河横穿河北平原中部,平原中部的区域中心城市镇州、赵州,以及中古望族赵郡李氏、土门崔氏(博陵崔的分支)、博陵安平崔氏皆受其灌溉滋养,也是频频出现于唐诗的重要文学景观。滹沱河在亲到河朔的唐代诗人或河朔本土诗人笔下往往是实写,如赵郡李颀《欲之新乡答崔颢綦毋潜》“寒风卷叶度滹沱,飞雪布地悲峨峨”[1]1350,李嘉祐《少年行》“身居骠骑幕,家住滹沱河”[1]2170;出现在其他唐诗中,常具有指代整个河朔地区或燕、赵故地的标志性意义,如杜甫《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其九:“东逾辽水北滹沱,星象风云喜共和。”[1]2519
燕太子丹送别荆轲的潇潇易水,显然兼有文学景观与文学地理意象的双重性质。唐诗中写到易水,以骆宾王《于易水送人》为典型代表,其独特的人文内涵和审美特点有二:首先是必然与慷慨壮烈的燕赵地域文化气质相联系,诗人身临其境会陡增一份雄豪侠义之气;其次,反抗暴秦的悲壮气氛与北方苦寒印象叠加在一起,使寒冽成为人们对易水的突出印象④,易水因此得与更北的桑干河一起成为北方之河的象征。
河朔诗路北段的文学景观主要有桑干河、燕山及绵延于燕山之中的古长城。桑干河唐时由并州流入幽州,今天从山西流到河北,在唐诗中出现20余次。其中有些是亲临其境的歌咏,如晚唐诗人雍陶《渡桑干河》:“今朝忽渡桑干水,不似身来似梦来”[1]5968;在另一些送人游边的诗作中,则以桑干河指代幽蓟一带,如刘长卿《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逢君穆陵路,匹马向桑干”[1]1493;更多情况下则基本脱离了指示地理方位的意义,纯是作为边塞之地的代名词,如皇甫冉《奉和对雪》“连营鼓角动,忽似战桑干”[1]2818,贯休《战城南》“万里桑干傍,茫茫古蕃壤”[1]9389等。
燕山山脉,自古是农、牧两种文明的重要分界线,也是唐人眼中东北边塞的天然屏障。骆宾王《边夜有怀》“汉地行逾远,燕山去不穷”[1]857,诗人沿绵延不绝的燕山走向边塞,离汉地越来越远,应是其北游边塞时期的写实之作;李白《奔亡道中五首》其四“洛阳为易水,嵩岳是燕山”[1]1848写奔亡途中所见,则是对文学地理意象的巧妙运用——作为自然地理标志的易水、燕山,在文化心理上具有分隔夷夏的意义,安史之乱爆发后,诗人写洛水、嵩山成了易水、燕山,形象蕴藉地说出大片国土失陷,中原沦为边疆的沉痛现实,平添了打动人心的力量。
唐诗中屡次出现的“塞垣”,泛指北方边塞的长城及各类城池关塞。战国燕长城及秦汉长城均远在燕山一线以北,但唐时之燕山上并非没有长城景观,北朝诸政权曾多次在这一线修筑长城,特别是北齐天统元年(565)斛律羡主持修建的从古北口沿燕山南缘到大海的长城,与后来的明长城线路大致重合。[9]这一段长城,有时唐人也一概泛称为卢龙塞,由此可知,当亲临东北塞垣的高适写下“东出卢龙塞,浩然客思孤”(《塞上》)[1]2190时,卢龙塞理应是平时供行人出入、战时由重兵扼守的具体门户,是一个“点”,但在更普遍的从文学地理意象的意义上咏及卢龙塞的诗歌中,卢龙塞也可以是一条线,指的是从“幽州以东迄于海滨之长城塞”[10]。
最后谈一谈“河朔唐诗之路”所依托的“面”。
李仲凡在论及“文学景观的‘线’和‘面’的尺度”时举例说,黄河、三峡、长城这些是“线”,地中海、黄土高原、蒙古大草原和撒哈拉沙漠等就是“面”。从这样的宏观视野看“河朔唐诗之路”,诸如河朔、燕赵、幽燕、幽并、幽蓟、蓟北、辽西这些,可以视为“面”状的文学景观,并且,它们在唐诗中大多同时具有文学地理意象的性质。
燕赵自古多感慨悲歌之士。从隋末窦建德、刘黑闼与李氏争雄,到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自幽州起兵,发动造成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叛乱,以及此后形成的“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11]的强藩割据,使得唐人对河朔地域的雄豪尚武、桀骜不驯气质印象尤深。所以,当唐诗中写到河朔、燕赵,常常包含着对这一地区慷慨豪侠的地域风格的体认和强调,如张说《奉和圣制行次成皋应制》“夏氏阶隋乱,自言河朔雄”[1]921,韦应物《送崔押衙相州》“礼乐儒家子,英豪燕赵风”[1]1933。
相比之下,从地理方位上更靠北的幽燕、幽并、幽蓟等地名则一方面仍有豪雄、苍凉之意,一方面成了北方边地的代称。蓟北、辽西,所指地点就更加模糊。唐时已无辽西郡,秦汉至北朝辽西郡治屡次迁徙,管辖范围大致在今冀东的唐山、秦皇岛及辽宁西南,于北齐时并入了北平郡(治今河北卢龙北)。蓟北更非具体地点,基本上可以肯定是因为作诗对仗方便才盛行起来的一个词,在唐诗中与其他地名配合方位词对举的例子比比皆是,如上官昭容《彩书怨》“欲奏江南曲,贪封蓟北书”[1]62,卢照邻《送幽州陈参军赴任寄呈乡曲父老》“蓟北三千里,关西二十年”[1]532等。辽西一词也有类似用法,如沈佺期《杂诗三首》其二“妾家临渭北,春梦著辽西”[1]1030,王勃《八仙径》“代北鸾骖至,辽西鹤骑旋”[1]679。总之,辽西、蓟北,几乎总是和征人、思妇、鸿雁等意象一起出现,不仅在唐诗中,在中古以后历代的中国古典诗歌里都是典型、常用的文学地理意象。
上述点、线、面的文学景观之外,文学作品中还经常出现一些带有明确地理标记和地域文化特征的其他名词、名物,可以看做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地理意象。河朔诗路最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唐诗中频频提到的赵女、燕姬、邯郸倡、邯郸女儿、燕赵佳人和邯郸儿、邯郸少年、幽燕客、幽并侠少等。据笔者粗略统计,咏及上述各类燕赵佳人意象的唐诗总计起来不下50首,堪称现象级的存在,学界也已有一些关于“邯郸倡”“赵女”等意象的探讨文章。咏邯郸儿、邯郸少年诗有6首,咏幽并游侠类诗有近20首,这两类豪侠性格的人物之间的个性和文化意蕴在近似中又存在差别,此处限于篇幅,留待以后做专题讨论。总之,诸如此类本身虽不是地理景观或地名,但也打着鲜明的地方烙印、有着特定人文内涵的人物或名物意象,也理应纳入文学地理学和诗路研究的关注视野之内。
四、“河朔唐诗之路”的特点及诗史意义
“河朔唐诗之路”南北两段一在太行东麓,一在燕山南麓,所经地貌,主要为山前台地和平原阶地,与其他各处具有诗路性质的文化线路相比,山水不及浙东,亦缺少西北边塞的奇崛色彩,其突出的自身优势和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河朔唐诗之路”不仅与其他唐诗之路一样串联起众多诗人的行迹和诗篇,并且串联起诸多中古时期顶级的文化士族,是为唐代诗坛输送诗人最多的诗路之一。曾大兴对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所收文学家的籍贯分布统计显示,隋唐五代燕赵籍文学家共107人(河北103人,北京4人),为全国最多。[12]景遐东以陈尚君《唐代诗人占籍考》为基础编制的《唐代各地区诗人数量统计表》中,唐河北道诗人数量则仅次于江南东道之后列全国第二。[13]星光璀璨的唐代河北道诗人,半数以上占籍在“河朔唐诗之路”南段的太行东麓南北大道沿线及附近地区,最主要的原因是唐代最为显赫的“五姓七家”中的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的聚居地均分布于这一线。其中博陵崔氏贡献了初唐崔湜、崔液、崔涤三兄弟,“大历十才子”中的崔峒⑤以及中晚唐诗人崔立之、崔护、崔涯等;范阳卢氏则有“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大诗人陈子昂的好友兼诗集整理者卢藏用、中唐“韩孟诗派”重要成员卢仝等;赵郡李氏涌现诗人最多,如名列初唐“文章四友”的李峤,盛唐名家李颀和李白遗集的编辑整理者李阳冰,中唐名家李端、李嘉祐、李绛、李纾、李华,晚唐名相李德裕等。以上几大望族之外,河朔诗路的著名诗人还有魏徵、郭震、苏味道、阎朝隐、郎士元、司空曙、刘言史、于鹄、刘叉、贾岛、无可等。
其次,“河朔唐诗”与“陇西唐诗”分别承载着唐代边塞诗的东西两极,不断演绎着战争行役、征人思妇等主题的古典诗歌传统,都涌现出许多名篇,特别是共同成就了以高、岑为代表的盛唐边塞诗这座诗史上的高峰。唐代边塞战争,西北和东北是两大主要方向,东北方的主要对手是契丹和库莫奚。岑参曾北游河朔,但其雄奇瑰丽的边塞诗作于西北;高适曾入河西哥舒翰幕府,但他首先是在“河朔唐诗之路”写出《蓟门五首》《塞上》等大量风格苍凉、思想深刻的边塞诗,代表作《燕歌行》也是基于东北边塞经历见闻创作而成。高、岑之外,崔颢早年北游边塞,是沿河朔诗路北上幽蓟,其《古游侠呈军中诸将》《赠轻车》《赠王威古》《辽西作》诸诗背景皆为东北边塞;王之涣《凉州词》作于西北,但是早年流落蓟门的经历为他提供了最初的边塞经验和豪情。盛唐之外,初唐之崔融、陈子昂,中唐以后的张籍、李益等名家也都写出了反映东北边塞的优秀诗作。另外,正如前文论述文学景观和文学地理意象时指出的,“河朔唐诗之路”北段的燕山南麓一线不仅留下了众多诗人的咏歌,且因唐诗的书写,为中国文学贡献了诸多具有文化符号和象征意味的文学地理意象,蓟北、渔阳、卢龙、榆关、碣石、辽西等地名在古典诗词中已经紧紧与征人思妇和边地征战之苦联系在一起,成为边关、边地的代名词。
再次,流淌在“河朔唐诗之路”的慷慨悲歌的燕赵文化传统,作为一种“边缘的动力”[14],为唐诗注入了贞刚之气和独立不屈的人格精神,促进了南北文风的交融和唐诗高潮的到来。文学地理学研究认为,文学家写作风格的养成、思想内容的广度和厚度,乃至其创作最终抵达的高度,当与文学家一生的地理根系有重要关系。[15]“河朔唐诗之路”所给予唐代诗人的地理经验是宝贵而独特的。在浙东诗路,唐诗中丰富密集的自然山水意象,实际是继谢灵运等南朝诗人之后对江南风景的再发现;在陇右,以岑参为代表的西北边塞诗是古代诗人对西北瑰奇壮阔风光的初次发现和尽情描摹;相比之下,临近华夏文明核心区、早早参与进逐鹿中原的历史大戏的河朔诗路,在唐人眼中缺少由“发现”带来的陌生感和新鲜感,而更多与得自书本的“燕赵自古多感慨悲歌之士”印象相互参证的熟悉感和亲切感。此间的自然风光,与青山秀水、云蒸霞蔚的南方诗路迥乎不同,与陇右诗路的雄浑硬朗接近,但却不及西北之瑰奇壮阔,而带有更多质朴、家常的人间烟火气。但是,如果就人文景观的密集、厚重而言,无论西北还是南方,在唐人眼中,与河朔相比恐怕都要更荒蛮一些。在河朔诗路,战国时期燕赵人物留下的桀骜不驯、自由不屈的历史遗事,边塞驻防之地的鼓角峥嵘和刀剑之气,诗路沿途所见河北“绵衍庞魄”之山⑥,北方大河寒冽的河水和草原上呼啸吹来的朔风,以及一路结交的邯郸少年、幽并侠客的豪放爽朗,经过一番的感觉、知觉、理解、记忆等过程之后,都必然与诗人的精神生命发生深刻联系,并内化成诗人的人生资源和精神力量。河朔诗路的本土诗人魏徵、卢照邻、郭震、高适、李颀等人的创作中不乏悲壮豪侠的河朔贞刚之气;客籍诗人行走于河朔诗路留下的作品中,诸如骆宾王的“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于易水送人》)[1]861,李白的“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北风行》)[1]1690等感人至深的典型诗句说明,当诗人的满腹经纶、绮丽文采与“河朔唐诗之路”慷慨悲壮的文化传统相遇合,确乎曾迸发出壮烈贞刚的火花,从而开阔了诗人的胸襟,丰富了唐诗的风貌,使诗国的星空与河朔的土地一并因之踵事而增华。
五、结 语
“河朔唐诗之路”在唐诗版图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众多唐诗之路中地位举足轻重、具有突出自身优势和鲜明地域文化特质的一条。本文在全面考察河朔诗路沿线的本土诗人分布、客籍诗人的行迹与歌咏、不同类型的文学景观和文学地理意象的基础上,总结提出河朔唐诗之路具有贡献本土诗人最多、与陇西诗路分别代表唐代边塞诗的东西两极、为唐诗注入河朔贞刚之气等区别于其他唐诗之路的三方面特点和诗史意义。这一方面是对纵横交错、丰富多彩的唐诗之路图景的进一步开拓和完善;另一方面是以河朔诗路为样本,对唐诗之路个案研究的合理范式所进行的探索和推进。此外,本文还对文学景观和文学地理意象的概念、内涵及研究方法作出探讨,认为在古代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视阈中,一切自然、人文景观,经文学家反复吟咏和书写,即可谓之文学景观;文学景观或特定的地名、地域,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名物,反复进入文学家的吟咏和书写,并因此具有了某种特殊的人文意蕴乃至特别的文化标志意义,则可谓之文学地理意象;以点、线、面的三分法对唐诗之路沿线文学景观、文学地理意象进行分类考察,极为简明、方便,对实际操作富于启示意义。
整体来看,唐诗之路的研究,既是“唐诗研究的一个部门、一个方向”[16],同时也归属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其在近年骎骎日盛,俨然成为新兴学术热点。在“中国知网”检索“唐诗之路”关键词可知,自2019年11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唐诗之路研究会成立以来,有关学术论文每年以数十篇的数量涌现,社会媒体的宣传报道更不可胜计,关注对象也从“浙东唐诗之路”扩展至京洛、陇右、岭南、齐鲁等多条诗路。正如本文引言中指出的,地域空间之多元,不同地域空间文化风貌之丰富,与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罕有其匹的历史连续性一样,都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属性和重要特质,关注不同地域空间的唐诗风貌及其独特价值的唐诗之路研究,在本质上是关于“文化的中国性”的研究。揭橥并呈现中国文学的这种基于辽阔国土和复杂区域格局的丰富性,既是唐诗之路乃至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责任所在,也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时代需要。此外,从学界到民间,之所以对唐诗之路研究迅速贯注了极大热情,根本原因还在于,基于地域空间的文学研究体贴和回应了人对脚下土地的眷念和好奇、对地方文脉的尊重和自豪。人对脚下土地和地方文脉的情感,当属文学研究最真实、最根本的学术动力,而唐诗之路研究在近年的蔚兴,充分说明了这种天然、朴素的情感,值得研究者的体贴和回应,包涵唐诗之路研究在内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正是近年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开辟出的“接地气”的、与当代人的思想情感保持联系的、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可以发挥作用的新视野和新方法。
关于唐诗之路的未来研究空间和谱系建构,卢盛江、胡可先等先生均曾有过高屋建瓴的论述,梅新林、曾大兴等先生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构和理论探索对唐诗之路研究同样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不过,就如同创业者注册公司、制定规章不是目的,生产和贸易才是创业的目的一样,理论突破和概念体系的建构固然必不可少,但理论和概念并非目的,呈现诗人在东西南北、大大小小的诗路上的行走和栖居才是唐诗之路研究的目的所在。从横向的空间角度看,除了多条基于交通线路的唐诗之路外,诸如黄河、长江、大运河等大河,太行、燕山、秦岭等山脉,本身也容纳或连缀着丰富的诗人行迹和诗意空间;从纵向的时间角度看,大部分唐诗之路在唐代之后继续有众多诗人走过,不断塑造和丰富着沿途的文学景观和文学地理意象。遗憾的是,基于交通线路、山脉、大河所包蕴的如此深厚、富饶的文学矿藏,我们至今还未能拿出一部如“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系列中的《莱茵河》那样既“以追求客观知识为唯一关注”[17],又是“个人的情感与文采交融的产品”[18],成功抉发人与大地山河的深刻、复杂关系的典范著作。因此,依笔者愚见,拿出更多有深度、有温度的个案成果,仍然是唐诗之路乃至文学地理研究的当务之急和核心使命。以“河朔唐诗之路”为例,应追溯诗路的自然与人文地理背景,讲清楚诗路的渊源;全面观照沿途本土诗人群体与客籍诗人在诗路的行迹与创作,讲清楚“人”“路”“诗”三者的面貌和关系;重点关注文学景观和文学地理意象,以唐人的吟咏为基点,延及唐前及唐以后文人的相关贡献,全面揭示和呈现道路和山河串联起的诗意空间。总之,放眼未来,只有越来越多的诗路和地方文学空间得以具体、深刻地呈现出来,我们才能像过去从时间维度讲述唐诗史和中国文学史一样,从地域空间的维度描绘出更完整、清晰、生动的唐诗版图和中国文学地理。
【注释】
①刘成纪《中国美学与传统国家地理》一文认为:“当代中国学者对地理问题的关注,并不仅仅是考虑人文精神落地的一般问题,而是包含着以此为视点重建中国文化和美学研究范式的企图。也就是说,地理的区域性、地方性就是文化的中国性。”其文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1期。
②天宝元年(742),河北道18郡常贡丝织品占全国常贡总数的50%,其中定州博陵郡独占41.8%,为天下第一。(杜荣泉:《河北通史(隋唐五代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第102页)
③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引唐人《括地志》:“太行连亘河北诸州,凡数千里。始于怀而终于幽,为天下之脊。”(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六,中华书局,1955,第1921页)
④直至当代作家张承志散文《悼易水》仍以“寒冽”为易水最突出的特性,该文开头即云:“我也曾在易水,掬着销肠伤骨的冰冷河水一口口喝下。已经时隔二十年了,忆起来仍然禁不住打一个寒噤:好凉啊……”(张承志:《风土与山河》,作家出版社,2005,第21页)易水在该文中与“北方那种解释不清的悲壮气氛”紧紧相连,作者借悼易水之干枯,追悼“汉文明之中的烈士传统”。张承志的易水书写,是易水这一在唐诗中常见之文学地理意象在当代文学中的确认和回响。
⑤中唐诗人崔峒、崔季卿系出自博陵崔氏迁至今石家庄鹿泉一带的望族“土门崔”,亦在太行山东麓。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七“获鹿县”条:“鹿泉,出井陉口南山下。皇唐贵族有土门崔家,为天下甲族,今土门诸崔是也,源出博陵安平。”(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第481页)
⑥明人焦竑引《玄中记》评价各地山地特征云:“桂林之山,玲珑剔透;巴蜀之山,巉差窳窆;河北之山,绵衍庞魄;江南之山,俊峭巧丽。”(焦竑:《焦氏类林》卷七,明万历十五年王元贞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