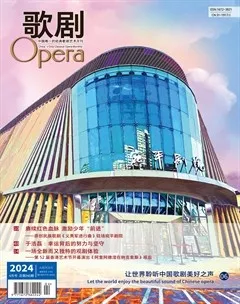室内歌剧《庄周起死》:将观众带入理性音乐空间
2024-05-08单金龙
2023年12月20日,由温德青作曲、编剧,易立明导演的室内歌剧《庄周起死》,在北京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世界首演。
室内歌剧《庄周起死》的创作始于2022年。当时,北京大华城市艺术表演中心艺术总监、导演易立明委约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温德青教授,从鲁迅《故事新编》中挑出一个故事并将其改编为室内歌剧。鲁迅《故事新编》是一本向人生求索的读物,包含众多探讨人生境遇的题材,涉及女娲、后羿、禹、老子、墨子、庄子等人物,最令作曲家更感兴趣的是其中《起死》这篇改编自庄子《至乐》中髑髅杨大的故事。
温德青这个名字,在我印象中代表着“听觉至上,向作品开放自我”。他的音乐,会在自己的意识与对象辩证统一后,为观众制造出一种可贵的认同感,因此他的作品能突破音响的局限,在广泛的意义上获得丰富的解读。他以往的室内歌剧,无论是《赌命》(根据高晓声的同名小说改编)(2003)、《布莱梅的音乐家》(2011),还是超现实主义歌剧《隧道》(2022),以及微型歌剧《杨宗保与穆桂英新传》(2023)等,都带有人文精神的隐喻——将音乐融入当代文化生活,是他作品中不可或缺的话语。

此前,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曾于2022年与温德青合作超现实主义室内歌剧《隧道》,本次是他们再度联手。室内歌剧《庄周起死》的剧本保持了鲁迅原作的荒诞性,但又不同于原作。《庄周起死》有着全新的人物造型和开放时空的设计,通过对原文本的浓缩、转喻、移置的表述,将庄子笔下髑髅拘累劳苦与自由之精神,转变为当下信息时代中人与人之间相处冷漠(精神失联)的新表达。这场极富寓言精神的先锋音乐“造型”,显示出了温德青不同以往且独具现代艺术表征的歌剧特点。
对于观众而言,这或许更是一种挑战——在这样一部较先锋的室内歌剧面前,是否能够完全把握人物与剧情?又是否能够接收到作者隐含的人文思考?而对于作者而言,问题则在于这部室内歌剧所具有的音响特质,是否会因过多的现代性技法甚至全新的音响观念,给观众制造诸多的不友好?
髑髅杨大的历史文本
庄子《至乐》的思想,距今已2300多年。《至乐》文中叙述了这样一则故事:庄子到楚国去,途中见到一个髑髅,便想请司命大神将其复活。髑髅却回答:“我怎么能抛弃南面称王的快乐而再次经历人世的劳苦呢?”庄子借髑髅的口吻,表达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拘累劳苦的人生。这个原初的故事,通过对自由精神的追求与人性解放的疾呼,展示了庄子自我意识的觉醒,表达了他以无为换取自由,以自由为人生至乐的超脱生死之乐的思想。汉代以来,对髑髅的故事从未停下诠释与改编,从张衡、曹植、李康、吕安、李寿卿①到鲁迅,这则故事在多次创造性的变异后,如今已成为关于自我意识觉醒的文化母体存在。

1930年代,鲁迅耗时13年集腋成裘写出的《故事新编》,其中便改编了庄子的这则髑髅的故事,名为《起死》。改编后的故事描述了庄子请司命用神力复活了髑髅,但好心却没有得到好报,髑髅醒来后发现自己财物不见了,又赤身裸体,以为是庄子抢了他的东西,要求庄子归还。在鲁迅的笔下,故事荒诞离奇,他以髑髅的复活去批判庄子的虚无主义和1930年代知识分子的虚无主义情绪与民族失败情绪的联系,讽刺了当年生存的荒诞感和知识分子的无力感。
约一个世纪后,这则故事被温德青拿起,他打破了鲁迅《起死》中“救人—骗人—压人”带有象征意味的叙事结构,不仅让髑髅从鲁迅复活的手里死去,还进行了全新的人文反思。在剧本中,温德青写道:“汉子发现,他已经身处家人早已死去的700年之后,他顿时感到存在的无望。”一种精神失联的绝望,让髑髅选择从复生中死去,因为它厌烦了信息时代下人与人之间关系,以一种存在主义视角探讨了在这关系之下生存的荒诞。歌剧剧本的诙谐、荒诞的语言,让包裹在嬉笑之下的这份思考,可批判可娱乐,可走耳可走心。

开放时空的馈赠
鲁迅笔下的《起死》,展示着一种荒诞的时空错乱之感。温德青并没有回避这样的时空问题,且给予了剧本更开放的时空特质。除了东周战国、商纣王的“商朝鹿台”,以及民国时代“巡警”的设定外,一系列如“研究经费”“手机”“微信公众号”“健身房”“躺平”“佛系”等符号,延续与强化着当代审美意象。同时,该剧的舞美设计(包括服装设计)也更为符号化,平行时间的蒙太奇手法及国际象棋的人物服装造型,充满隐晦多义的反思性,皆显示了“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智慧。
作品采用了开放时空的模式,但与其说是关注了时空,不如说消解了时空——将歌剧的主题放在一个超越时空的设定中进行精神的对照与反思,以便直观地展示主题的核心思想。开放时空的设定,也强化了语言的符号功能,独特的语言和多面的指涉,激发了观众对于时代瞬间的体验感,从而实现多维时空(时代)精神对话的目的。譬如,在汉子身上,至少可以读出三个时代的影子:生活在商纣王时代,复活在东周战国,却拿着现代人的手机;庄子虽在东周战国,却手提文件包、身着道袍或西装,参加楚国论坛、喝着农夫山泉等等混搭的表现;还有巡視所在的民国时期,却知道“微信公众号”和“健身房”这样的当下社会生活化词语。
温德青正是通过开放的时空,展现了人与人、人与不同时代之间关系的思考,在共时的时空中制造多重的反思与比照。这显示出温德青一开始就将人与人的精神失联主题放在宏阔时空视野中,也展现了作品的存在主义视角。他将不同的时间,聚集在一个非封闭的时空中,以此作为道德情感反思的手段,这对于当今开放时空理想的读者,是一种特别的馈赠。

除了语言,视觉符号也具有时空性。第二幕第一场结束后的《间奏曲》中,舞台也可以看见时空符号的建构,“众警察押送着用树枝挡身的汉子,在台上来回穿梭,犹如英雄凯旋。背景电子屏幕闪现巴黎、伦敦、纽约的大街小巷景象,台上的演员似乎身在其中”。这种失联的人文反思,持续地被压缩在宏阔的视野和跨时空的场景下,使得观众不得不去思考。正如温德青所说:“我们在一晚上横跨了几千年,对人生的哲理会领悟得更透彻一些。”
音乐隐喻人与人的精神失联
在虚无主义思想的今天,被现代性裹挟的人们,正被迫投入越来越快节奏的日常生活当中;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似乎都在追求快速、高效;网络世界的时空,则被压缩成无数个简省的片段,限制着人们的耐心……信息技术时代,引发了一种病态社会现象,这种现象的典型特征就是人的自主行为与不自主行为的并存。想想我们对手机的依赖,信息时代或信息技术时代,很多人在这样的空间中呈现出自主权的任意扩张状态,却又是一种缺乏理性层面的自我主宰的表现。人们变得不再愿意反思,或者说很难反思,失去了深度思考后,人与人变得精神失联。歌剧《庄周起死》通过使自我主宰能力缺失或者主体性消失,来寓意彼此的精神失联。正如该剧服装设计曾韵竹谈人物设计时说:“巡视、局长、司命大神和小鬼,以国际象棋的形象呈现。因为将髑髅设计为人偶形象,我希望以一种棋子的视角来展示个体的精神境遇。”

在开放性时空背景下,这种人与人精神失联的展示及其寓意,通过音乐得到了强化,尤其体现在歌剧的结尾(第二幕最后一场)。作曲家在这里指示声乐演员捏着鼻子抬高调门,以戏谑性音调建构与亲人失联的话语:“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是空号……”“空号”的背后,仿佛存在着一个令人发笑的灵魂,使汉子更加迷惘,甚至產生了一种与生命对决的状态,死亡成了他最后的归宿。《庄周起死》通过手机这个符号隐喻,以手机失联寓意亲人的失联,而捏着鼻子的音响效果则制造了一次心灵阵痛,以达到阵痛之思。
阵痛之思,可以思考的是当代人的生存状态——人与人的失联。倒回歌剧《庄周起死》的开头与发展过程,“失联”的隐喻无处不在,如生与死终极性质的失联、司命做法的生死续连、误解争吵的无奈断联、巡视欺下的拒联,以及局长虚荣的选联等等,展示了众多人物之间无法与汉子关联,与种种隔绝的话语及其深层的心理状态,由此揭示出存在的荒诞感与无力感。
在“巡视”这个角色的音乐刻画上,他对庄子一开始是咄咄逼人的,当他得知对方是庄子这样的“大人物”后,他的音乐语言立刻转变为一副卑躬屈膝、结结巴巴、谄媚权贵的嘴脸——他以同音反复的音型,喊出庄子的名字,整个弦乐组同时配合庄子的语音音调,来展现一个弱小圆润、妙趣横生的反转关系,直观呈现了“巡视”这个角色的虚假。

歌剧也通过庄子温和而有力的声音去联动“汉子”这个角色。不同于其他角色,作曲家对庄子的角色塑造,始终给观众以一种语言温和的感觉,并通过语言的音乐化,强化庄子的温和语音音调。譬如庄子发现髑髅后,对“请司命大神复他原形”的口语化的音调设计,语调的重音被落在“原形”二字上,这二字被处理得十分温和;再比如当复活的汉子污蔑庄子时,庄子依然以平和的语调,平静地说出原本会激发矛盾情绪的“你这人真是不讲道理”。在“你这个人真不讲道理”一句的设计中,句首的四个字“你这个人”,用较为极速的语调发出;而“真是不讲”四字时,又突然以文质彬彬的口吻一字一音地表达出来;特别是最后的“道理”二字,通过拖腔完成。这样快—慢—再慢的句式,刻画出庄子在受气的状态下,努力平复身心、保持温和状态的人物形象,制造出一种亲近感。
这部歌剧对每个角色的“旋律”设计,都统一以语言表情音调为基础,通过表情音调去直观地展示角色的心理活动。这种让音乐贴近日常语言的设计并不新颖,语言音调在歌唱中的设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作曲家刻画人物所使用的典型手法。如金湘的《原野》(1987)、郭文景的《狂人日记》(1994)和《骆驼祥子》(2015)、温德青的《赌命》(1999)、谭盾的《秦始皇》(2006)、周湘林的《康定情歌》(2022)、郝维亚的《画皮》(2018)和《七日》(2022),都是以语言的夸张化来进行人物歌唱的设计,以音调揭示人物心理与动作,从而推动事件的发展。观众也大可以把当代歌剧的表情音调写作,当作音乐化心理剧来体验。

音调器乐化对戏剧的建构
在人与人关系的表达上,汉子的生死、局长的“中心”和巡视的“边缘”,通过时空错乱的语境,不断强化着汉子、庄周、巡警、局长荒诞性的对话,音乐则以统一的设计,推动他们之间的戏剧化动作进行。
除了表情性音调在人物唱段中的应用,作曲家又进一步将语言音调在器乐的表情性中进行了表达。他通过歌剧人声语调的触发,将编制不大的乐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音调器乐化熔炉”,这语言音调同时在人声与器乐两个维度上进行音乐化设计。这样做,既能帮助角色与戏剧动作的展开,又制造了戏剧所需的氛围感。同时,器乐自身的丰富语言,又显示出作曲家对于歌剧背景及环境的音响设计理念。如此,这部歌剧的音乐就仿佛两个引擎,一个驱动戏剧情节、营造意境,一个不断将音乐最大限度地转化为隐喻。

第一幕第一场,合唱队被分解为小鬼们的不同声音,交叉铺垫在司命做法时的整体音响化建构中。作曲家将打击乐声部作为新音响单元,直接简单地铺垫在其他器乐音响下,制造出情绪发生需要的基本氛围。弦乐声部则作为夸张化的叙述外衣,兼具趣味音调和情感表达作用。合唱与打击乐,显示出与弦乐声部共用的设计。这个设计让这部分的戏剧内容既分立又互为嵌套,既交替复合又显示出多面情绪。作曲家以音乐形式的建构,让这部歌剧变得更深刻与更具哲理,甚至传达出文学、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所不能达到的深刻性。
再如,第一幕第三场围捕汉子的场面,音乐使用长笛、圆号与打击乐,以较大幅度的波动音响,制造不断升级的紧张趋势,为抓捕营造气氛。缉拿汉子后,紧张的音响依然在巡警与庄子的对话中持续,直到两人更进一步的对唱,两人相应的器乐化语言音调才开始跟进。叙事性内容与相应音调,总是以预示或滞后人物心理的方式,先于或迟于人物的唱段出现。这种前后关系错位的处理,作曲家意在将其设为一种始终流动的状态,整个戏剧动作和人物心理被音乐辩证地统一在一起,制造出一种关联性的象征性表达。

此处,双簧管以极为幽暗的波动音调展示庄子的处境,而庄子动机音型则在钢琴更低的音区中发展且走样,形象地传达了庄子的荒诞性境遇。配器中,除了钢琴和双簧管外,还有单簧管用倒影的方式同双簧管声部进行搭配,制造出多声部的重叠与阴影,继续推动庄子痉挛挛缩的状态。最后,在以长笛为主导的发展中,将庄子的处境变得更加戏剧化,刻画了庄子被污蔑后的心理状态。尽管几件乐器所建构的器乐化表达,与交响乐相较仍显简单,但极简的乐器使用,彰显了作曲家的功力。
温德青的音乐设计,在服务于人物和戏剧动作的同时,还制造了一个无始无终的流动音响,将音乐形式的戏剧化功能消化于音乐形式自身的意味里,从而让音响内容更加丰富,一面铺垫和预示人物角色与戏剧动作,一面又由音乐的象征性制造人与人联动的思考。

面对愈演愈烈的多元文化生活,作曲家以包容的态度,释放音响内在的可能,包括对完全不协和音响的接纳,音乐也就具有了可思性。作曲家放弃了可听的音响,将目光投向不同的艺术媒介,以一切可能联合的艺术手段进行创作尝试。因此,今天的音乐艺术也比以往的内涵更丰富、更复杂且特点鲜明。音乐艺术正在挣脱传统体裁的基础,带给人出人意料的结果。
温德青拒绝简单地拉拢观众的主观情感,这让他的音乐总贴有“反音乐”的标签。但他的音乐恰恰是从生活中而来,他关注的是生活里的一切現象,无论是人物类型、面目、声音、身体姿态甚至复杂的精神活动,还是社会和心理冲突的尖锐性,都可以通过声音予以表现。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考验着当代公众的理解力与想象力。室内歌剧《庄周起死》,某种意义上给人的体验是抽象的。歌剧对语言的音调化和进一步音响化的表达,将观众带入思考性与理性的音乐空间。而对于《起死》这个故事,以歌剧体裁制造可思的直观形式,比以往任何时代的改编或许更能引人深思。
(单金龙,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美学在读博士研究生,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讲师)
① 历史上对庄子髑髅之死的故事曾出现不同改编版本:汉代的张衡《骷髅赋》、曹植《骷髅说》元代的李寿卿《鼓盆歌庄子叹骷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