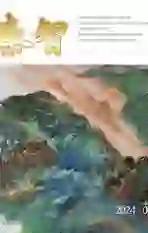网络暴力刑法规制实践、困境及完善建议
2024-05-07龚一帆刘珊郑杰中宋潇王静怡
龚一帆 刘珊 郑杰中 宋潇 王静怡
[摘要]网络暴力犯罪近年来一直被大家所关注,2023年10月“两高一部”更是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笔者通过对网络暴力犯罪的裁判案例分析来反映其现状,同时就刑法规制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说明并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
[关键词]网络暴力犯罪;刑法规制;治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TN915.08 [文献标识码]A
[DOI]:10.20122/j.cnki.2097-0536.2024.04.013
一、网络暴力犯罪现状及犯罪人特征
(一)网络暴力犯罪现状
1.网络暴力犯罪刑法规制路径
对于涉及网络暴力犯罪的罪名较为广泛,在刑法实践中常用的罪名有侮辱罪、诽谤罪、寻衅滋事罪,同时根据最新的“两高一部”联合印发的《指导意见》中还涉及到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在上述6种罪名中,笔者检索案例统计到了4种,分别是侮辱罪、诽谤罪、寻衅滋事罪以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其中犯罪类型主要集中在侮辱罪、诽谤罪和寻性滋事罪上,案件量分别占比43%、31%和18%。
2.犯罪数量
笔者通过裁判文书网以及北大法宝对2016-2022年涉及网络暴力的案件进行了统计,一共检索到747件案例,2016年62例,2017年82例,2018年80例,2019年103例,2020年137例,2021年132例,2022年151例;2020至2022年是犯罪的高发期,每年的数量均在130例以上;在变化趋势上,2016至2022年案件数量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
3.网络暴力犯罪人年龄
在犯罪人年龄分布上,集中在20至40周岁的青年群体,占比达到61%。在2021年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发布的《网络科技犯罪白皮书》中,也指出涉网络犯罪犯罪人年龄总体呈现青壮年化。
二、网络暴力刑法规制的困境
(一)以侮辱罪、诽谤罪规制网络暴力的困境
1.情节严重认定的唯数据论
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行为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依法才构成诽谤罪。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二条是关于侮辱、诽谤“情节严重”的认定情况,其中关键就在于浏览量和转发量是否达到相应标准;然而不同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同,看待事物的态度也不同,因此相同内容的诽谤信息的浏览量和转发量对于公民个人的伤害程度也是不同的。在最高检发布的指导案例——检例第138号岳某侮辱案中,诽谤信息的浏览量仅为600余次,远远达不到《诽谤问题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浏览次数5000次,但是却造成了受害人死亡的严重结果;试想如果仅仅因为浏览量达不到相应标准导致被害人无法得到救济,只能眼睁睁看着相关不实消息传播更广从而寻求司法救济或者像本案导致被害人死亡后司法机关介入,都是有违公民基本的法律观念的。
2.第三款的规定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缺位
《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三款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被害人向人民法院告诉,但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在司法实践中,“可以”的规定给了法院自由裁量的空间,但也会导致认定的随意和缺位,例如自诉人谭某收集了其被网暴的部分证据,请求法院立案并要求公安机关进行协助,但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谭某的起诉,后谭某上诉,二审法院受理后认为一审法院应当立案并要求公安机关协助,因此裁定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该案。[1]
(二)以寻衅滋事罪规制网络暴力的困境
1.寻性滋事罪中规定的公共空间无法涵射网络空间
在学理上,曲新久教授认为:“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信息社会,网络空间也具有公共场所的属性,由此认为在信息网络上编造和传播虚假信息,符合‘起哄闹事的特征,造成社会公共秩序混乱的,完全符合《刑法》第293条规定的‘破坏社会秩序的要求。”[2]但仝宗锦教授则认为:“将公共场所解释为包括信息网络,这个解释过程意味着有关罪行和法益發生了实质性变化。”[3]
在司法实践中,例如赵某某寻衅滋事案[4],司法机关是肯定了网络中的起哄闹事;但也有部分案例,司法机关认为没有现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是无法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即无法构成寻衅滋事罪,例如“王某军寻衅滋事案”[5],法官认为构成该罪需要发生在公共场所,进而扰乱公共秩序[6]。
笔者认为随着网络的普及与发展,将网络空间认为是一种社会空间无可厚非,但就《刑法》中规定的起哄闹事中的公共空间不论从文义解释还是目的解释来看都应当是严格限制在现实的空间之中。就如陈兴良教授所说:“司法解释实际上是将网络传谣这种刑法没有规定的行为,利用起哄闹事这一中介加以转换,由此实现了司法解释的造法功能。”[7]虽然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现行法律的漏洞,但其不能以解释之名行立法之实。
2.寻性滋事罪适用泛滥
《刑法》条文对寻性滋事罪的规定本身就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容易造成司法实践中对此罪解释的随意性和司法实践中的选择性执法。对于同样是在网络上侮辱、造谣,针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司法机关往往都会积极主动追究当事人责任;但针对普通公民在适用寻衅滋事罪上就会显得犹豫不决,这种司法随意性只会导致司法公信力下降。
(三)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规制网络暴力的困境
1.人肉搜索网络暴力行为的入刑主体存在争议
有关人肉搜索的网络暴力事件中参与主体往往涉及多人,包括组织者、参与者、传播者等。在这些人当中,不同人对个人信息的侵害程度存在不同,因此如何认定应承担人肉搜索刑事责任的主体,目前仍是一个难题。对于该问题,《指导意见》做出了部分回应,其中第四条将实施人肉搜索而应受到刑法规制的主体进行了限制,规定“组织人肉搜索,并非法收集和发布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指导意见》将应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限制在实施人肉搜索的“组织者”这一条件,重点追究恶意发起人肉搜索、并以非法目的获取或向网络群体发布个人信息的发起者、组织者的刑事责任,这一规定为解决人肉搜索入刑的主体提供了一定的解决思路,但如何在实践中界定网络暴力的“发起者、组织者”也是要面临的难题。
2.人肉搜索网络暴力行为的入刑标准存在争议
有关人肉搜索的网络暴力行为在入罪的标准也存在分歧,如侮辱、诽谤罪一样死板地以数量作为判定此类规范构成要件要素的依据,难免会使条文失去其应有价值;而“情节严重”本属于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中的一种量的评价要素,法官仅仅根据法律法规的记述仍不能确定该类要素的内涵,需要进一步就具体的事实关系进行判断与评价才能确定[8]。因此,对于所产生的危害后果可能波及现实生活的网络暴力,如仅仅根据数量标准来认定犯罪情节是否达到严重的地步,则可能忽略网络暴力才是引起被害人实质危害的内在原因[9],从而导致现行刑法规定过于追求数量标准,而难以在其中规制网络暴力下的非法人肉搜索行为。
三、完善网络暴力刑法规制的对策
(一)以侮辱、诽谤罪规制网络暴力的完善
1.以名誉的实际影响程度为判断标准
笔者认为,之所以《诽谤问题解释》中相关诽谤信息传播的数量标准难以适应现实情况,是因为对于“情节严重”的判断过于武断。对于传播量和浏览量,我们要精确化判断,不能单一看某一种的数量,更多的需要结合现实情况对个人社会评价造成的影响进行实质判断。对此,有学者认为,《诽谤问题解释》还应当对名誉权的外部损害结果予以规定,将第2条第1项规定的数量标准修改为“导致被害人的社会评价严重降低或者名誉贬损严重的”。[10]
2.增加司法解释,维护自诉人合法权益
考虑到自诉人维权困难、收集证据难等问题,笔者建议针对《刑法》第246条第3款规定增加司法解释来加强适用,将相关举证的标准进行完善,强调当事人的初步舉证即可;同时对于当事人达到初步举证证明时人民法院原则上应当要求公安机关提供相应协助。
(二)以寻衅滋事罪规制网络暴力的完善
对于网络暴力犯罪用寻衅滋事罪来规制是不妥当的,应当排除这一选择。网络暴力型寻衅滋事,本身司法解释“立法”的合法性问题就令人质疑,加上司法机关适用该罪的标准具有太大的主观色彩,造成司法随意性很大。从这一罪名本身出发其模糊性导致被大众批评为“口袋罪”,再把网络暴力犯罪纳入寻衅滋事罪之中只会加剧这种矛盾。
(三)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规制网络暴力的完善
1.对相关罪名的构成要件要素进行适当地扩大解释
笔者认为,其中可以着重对非法收集和公布他人个人信息的组织者的主体认定标准进行明确;同时有必要以在网络中流转个人信息时,以当事人的基本权利是否受到侵犯为主,对侵犯个人信息的非法手段做出合理的扩大解释,以应对网络中不断变化的犯罪形式。鉴于《指导意见》对于非法人肉搜索入刑的规定,可以通过网络信息溯源、违法信息的传播范围和社会影响力,以及人肉搜索者的主观过错等要件进行综合判断,从而追究其刑事责任。
2.新增刑法条文
有学者认为,出于《刑法》对公民隐私权进行特殊保护的现实需要,应当增设有关网络人肉搜索的罪名,原因是众多网民在“人肉搜索”过程中非法出售、提供、传播公民个人信息,侵犯公民隐私权的行为无法进行刑法规制,而后者的社会危害性显然更为严重[11]。另外,《刑法》对保护公民的隐私权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也是有暗含的,如第245、252条等,因此也不会造成体系上的矛盾。
参考文献:
[1]参见裁判文书网:(2020)辽09刑终125号.
[2]曲新久.一个较为科学合理的刑法解释[N].法制日报,2013-9-12(7).
[3]仝宗锦.对曲新久教授《一个较为科学合理的刑法解释》一文的评论[EB/OL].http://tongzongjin.blog.21ccom.net/?p=21.
[4]参见裁判文书网:(2020)豫0482刑初475号.
[5]王某军寻衅滋事案:浙江省龙游县人民法院(2020)浙0825刑初31号刑事判决书.
[6]王广利.寻衅滋事罪的性质及其构造[J].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3(5):113-129.
[7]陈兴良.寻衅滋事罪的法教义学形象:以起哄闹事为中心展开[J].中国法学,2015(3):265-283..
[8]张明楷.刑法学(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121.
[9]刘晓航.网络暴力的刑法规制困境及应对[J].北京社会科学,2023(5):106-117.
[10]刘湘廉.师晓东.网络诽谤“情节严重”标准之探讨[J].海峡法学,2015,17(1):68-75.
[11]马松建.论恶意“人肉搜索”的刑法规制[J].中州学刊,2015(7):53-58.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名称:网络暴力刑法规制的实践、困境及路径研究——以近年来典型网络暴力案例为例(项目编号:S202310656088)
作者简介:
龚一帆(2003.8-),男,土家族,湖南常德人,本科,研究方向:法学;
刘珊(2003.10-),女,汉族,湖北宜昌人,本科,研究方向:法学;
郑杰中(2002.11-),男,汉族,福建福州人,本科,研究方向:法学;
宋潇(2004.2-),男,苗族,贵州铜仁人,本科,研究方向:法学;
王静怡(2003.6-),女,汉族,河南洛阳人,本科,研究方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