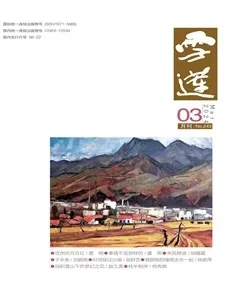纸片人
2024-05-04戚佳佳
【作者简介】戚佳佳,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中短篇小说见于《清明》《山东文学》 《当代人》《阳光》《四川文学》《延河》等刊。
1
在回老家之前,她还不知道脖子上鼓出了一个包。
接近清明,按老家的风俗要提前给故人上坟,她和家人相约了个周末,一同去给双亲上坟。天气热燥燥的,她穿了件开领的蓝碎花连衣裙,里面配了件白衬衫,大翻领,有意露出细白的脖子,整个人显得饱满昂扬,有精气神。
这身行头是她专门要穿了给地下的母亲看的,母亲在世时说过,她这几年穿得越来越等样了,不像以前,没有等样的衣服。以前是什么样?她已没有机会再问母亲了,每當想起这些,她心里就不是滋味。
她跪在双亲坟前,风呼呼的,随着火炮咚咚响起,点燃的冥币成了青灰,打着卷向下风处的草丛里飞。那里站着一棵树,嫂子说是豆树,那年,母亲还在,嫂子随手在树旁插了根树苗,不曾过问的树苗越长越大,枝叶蓬松,繁茂的像在双亲坟上支起的华盖,遮在坟上。
她跪在燃烧的冥币前,心里默念着,妈,我来看你们了,以后我会记得保持让自己穿得等样的。话没念完,眼泪涌出来,迷瞪瞪中,她听见有炮声从空中散落下来,在不远处的田野上“咚咚”炸响。她扭脸朝响声处望去,嫂子说,那是高家儿女来上坟了。
果然,上过坟,人群从不同方向朝马路上停放的车子走去,他们遇见了高家人,互相打招呼,一个中年模样的妇人问她,你是小四子?她说是。她也问,你,是小桃子?中年妇人点头。她张大了嘴巴看眼前的人,想从这完全陌生的样子里找出曾经熟悉的影子。她说,我一点都不认识你了!
三十多年,真是“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
没上学之前,她们是多么好的玩伴,只要睁眼,她们就喊对方的名字,跑到对方的家中,玩在一起,吃饭时,碗挨碗,头对头。
可是,一切的变化,都是来自于她的变化。她是庄里第一个上学的女娃,也是第一个硬是要往外面考的女娃。那时候关于她的消息很分散,她爸说她考了怎样高的分,还带了奖状回来,引得一个庄子的人都投过来羡慕的眼光,可就是不见有录取的信息来。
她不下地,不放鹅鸭,也不去菜地,天天待家里,一有时间,她就抠腿,一抠一个血印,一抠一个脓疮,脓疮愈合后,留一处伤疤,大腿小腿上布满了紫黑色的疤。她不敢看那些疤,像一个句号。开始,逢到假期,小桃子还偶尔来她家喊她,让她不要再抠腿,说留下疤,丑死了。她听了气得要死,对小桃子怒目而视,以后,小桃子再来,她要么嘟着脸不说一句话,要么转身进房。渐渐的她跟小桃子撞见,即使撞破了头,也不说话。
新学期开始,她照样得去上学,她都不记得自己到底念了几个初三,她父亲早就不让她上,但谁说了都是放屁。最后,是在县城工作的哥哥帮忙,把她转到了县城的补习班,她才如愿考上了中专。
庄里人说她心高,心里拧着一根绳子,是跟二子较劲。她不解释,也不争辩。她喜欢二子,在庄里已不是秘密,好多次她主动去找二子,见了二子脸又红,话也说不齐整。她真的喜欢二子啊,可是她知道自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她有心,二子没意。二子不喜欢她,也不说,他躲,躲到镇上的二叔家,不给她面见,也算是断了她的念想。那时候,她才明白,想要爱一个人,原来是那么难,那么累。有时,她觉得,心都碎了。却什么也不能说。
上中专后的第二年,她带回来一个戴眼镜的男朋友,夏天晚上乘凉,她和男朋友坐在河岸的凉床上,聊天说笑唱歌,她有意让声音长出翅膀,在夜空里飘,庄里人听了,就说,这回她如愿了。
但下一年,跟她回来的男朋友换了,是一个皮肤黝黑,精瘦,个头跟她差不多,猴子一样,庄里人不明白,也不过问。她毕了业,很少再见她回来。她结婚之后,庄里又传,说她被灌醉了酒,遭那个瘦猴强奸,被迫嫁的。她哥哥不喜欢瘦猴,说她不听话。
她什么也不说,也不争辩。
她再次看看这个叫小桃子的中年妇人,小桃子也看着她说,你要不说,我也不认识你了,你也长变了。那时候,你系着两个短短的羊角辫,红绸布系的,翘翘的,我每次看着,嫉妒的眼睛要滴血。
几个人唏嘘着,都笑,站一会,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似乎有千言万语,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小桃子拉开车门,说,我们先走了。她点头说好,车门砰地关上,小桃子把车窗摇下,冲她摆摆手,她弯腰,把耳朵伸向小桃子。她的脸听得变了色,她极力不让自己抖。
2
脖子上的包是在嫂子家转身倒茶时,被嫂子看到,问她,你脖子上怎么鼓起一个包?她用手摸了摸,没感觉,又站在镜子前,让镜子对着脖子,随着嫂子的往下往下,她终于看见了它。像平原上突出的一小块高地,小的却因为盘踞在细脖子上就显得大的软软的包。她看了又看,看了又看,摸了又摸,摸了又摸。
她咔咔地有意清清嗓子,想试试嗓子,却带出了一口痰,阻塞了咽部,咔咔声戛然停止,痰像胶一般黏住了嗓子。
回来后的次日早晨,她去了医院。偌大的医院,纷乱的人群把她裹挟其中,随着滑动的电梯,她茫然四顾,竟不知路在何方。她想起在这家医院里上班的邻居,虽不联系,也无交集,应该可以咨询一下。她翻到微信通讯录,发觉自己已记不清对方的网名。她的思维在越来越密集,在不知谁是谁的网名间穿梭,跳跃,迷失。这才发觉,不知不觉间,她居然有这么多好友?不知名的好友占了大半,多数已对不上到底谁是谁。她点开其中的一个,头像是风景画,朋友圈里设置了三天可见,网名是“人体与心灵”,对话框里空空如也,再无其他信息,她略一思忖,翻到删除页面,把这个人删了。她还想点开下一个,如法炮制,滑行的电梯把她推带到了二楼,她没注意,鞋尖磕在梯棱上,身体不自主地踉跄了一下,后面的人潮试图绕过她,也有人撞到她的后背,她的上身不由得朝前倾,身体便再次矮下去。她陡然清醒,赶紧抽直了身体,跨出电梯,站在二楼梯口,她看了看朝各个方向蜂拥而去的人群,莫名的忧伤,像无数碎裂的花瓣在心底泛开。
那张没有签男人名字的纸还躺在床头柜的抽屉里,她不知道自己还留恋什么。每天,他们像一棵树根上的两个树杈,同住一个屋檐下,却又隔了十万八千里。他们的房子是他们有了女儿之后买的,八十多平,两个房间都朝南。二十多年,她一直待在这个房间,没挪过窝。女儿飞走之后,男人去了另一个房间。偶尔女儿回来,就挤沙发上,像一个只是来留宿的旅人。女儿在外面的工作并不顺,饭也饥一顿,饱一顿的,比在家时还要骨骼分明。她有时想让女儿回来,参加统招考试,几率大些,不必再这么左冲右突的。可女儿却说这个家太阴沉,没有活气,不想回来。她听得心里涩涩的。
有时,她想问女儿,这个家是不是应该散了?可是她到底也问不出来。那句话像刺,每次就要到达嘴边时,都扎得她生疼。
男人不常在家,不在家时他的房门总是关着,她看着占了客厅小半面墙的紧闭的门,感觉凉丝丝的,风经过门时又被弹出去,旋在她的身上,透过衣饰上针尖般纤细的布孔钻进她的身体。她早就知道,男人的心不在这个家了。一个人一旦心不在了,九头牛也拉不回来。这些她都明白,一个到了知天命年龄的人,还有什么不了然。可她又不想什么都明白,两年前,她没有接男人递过来的纸,男人也没有拿回去,把纸放在了茶几上,继续喝自己的茶。她问:“你心里有人了?”男人说:“你从未正眼看过我,我知道,一开始我就错了,一切都是我的错,我累了,不想再这么耗。”男人的声音还是那么粗糙而沉闷,像从腌菜坛子里发出的。有时,她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么单薄而矮小的一个人,怎么会有那样的一副嗓子。她说:“我们有资格离婚吗?”男人端起的杯子停在了嘴边,抖了下,水从男人的嘴角溢出来。她又说:“穷人是没有资格离婚的,也离不起婚。”男人喝下一口茶,把茶杯放在茶几上,操着腌菜坛子里发出的声音说:“房子一人一半。”她说:“那女儿呢?”男人没接话,拿着茶杯进了自己的房间,门发出“砰”的声响。她怔怔地站了一会,有点难过,她不明白男人怎么会连女儿都不提,女儿刚出世时,他天天都说,女儿是他前世的情人,今生来找他了。可现在?难道女儿不属于这个家的一员?几个切断的房间横截面的平面图像冰面般在她的脑海里浮现、翻腾,她恍惚地看了看躺在茶几上的纸,弯腰拿起,看也没看,进了自己的房间。
男人在家时他们也不一起吃饭,她不问他,她吃她自己的饭。退了休之后她常偎在家里,看看闲书和手机,在自己房间的小阳台上侍弄一些袖珍花草。她想忘记那张纸,事实上,两年来,她真的没有拿出来看过,她以为自己忘了。
从嫂子家回来,她躺在床上,手摸着脖子上的包,感觉心里有股冷飕飕的风在吹。她想,倘若这个包不是好包,倘若这个包赖着不走,要在她的脖子上攻城略地,无限扩张,她该怎么办?想着那些五彩缤纷的美味,可能无法进入她脖子的通道,她感到后怕。若真是那样,恐怕也不会有多少能容她选择的空间。人生大多数时候,能真正供自己选择的事物并不多。
就像她的父亲和母亲。
父亲走前,念叨过他自己的父亲,说他只想活到六十,活过他父亲,就知足了。那年父亲只有五十五岁,父亲话说没多久,就走了。后来,她以为母亲能活到一百岁,她天天跟母亲说,您身体这么好,肯定能。母亲听得脸上乐开了花,直说,不要活那么大,活到你外婆那么大,就够了。结果母亲在七十六岁时突然离去,而外婆被连续摔了两跤,还捱到了九十五岁。她有时想起母亲,会觉得自己是给母亲打了剂麻醉针的人,意同一个杀人犯。
3
她对着镜子试了又试,喝水的时候,包鼓得更高,比男人的喉结都高,都大,像是被塞进了小石子。她张张口,想嚎几句歌,嗓子里却出不来音。她颓丧到极点,仰脸盯着吸顶灯,灯光软软地伏在她脸上。
她想着在自己的肉身里,潜伏着的一个异物,心里就哆嗦。她忽然很想很想找一个人说说,能跟女儿说吗?她望着渐渐黑沉下去的夜,感觉到从未有过的慌乱。在没确定之前,她不想让女儿跟着瞎操心。她又看了看男人房间关着的门,她想如果男人现在在家,她会敲男人的门,告诉男人她脖子上长了一个包,她不管男人愿不愿意听,或者听过之后会怎么看,她都要说。可惜房里没人,她六点半到家后,就没有看见男人,她没有告诉他,她今天回家,她把客厅,房间,连卫生间的窗帘都放了下来,打开灯,晚饭也不想吃,更懒得做,整个身体陷进了沙发里。身体是歇下了,脑海里却翻江倒海,怎么也闲不下来。
她又开始想母亲了,越是这样的时候,越是想母亲。如果母亲知道她脖子上长了个包,不晓得要怎样!母亲在世时,哪怕只是在电话里听到她声音柔软了些,都要追问是不是生病,受委屈了?
母亲走后,她的世界塌陷出一個坑。一个她终其下半生都无法填平的坑。
她在沙发上坐了很久,她闻着女儿的味道,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等她醒来,没见男人回来,她看看男人的门,又抬头看了眼墙上的钟,十点半,客厅里所有的摆设还是她睡前的样子,男人放在门前垫子上趿拉的拖鞋还在。她挣扎着从沙发里站起来,换洗衣服都没拿,直接进了卫生间,粗略地冲了一把澡,在灯光的逼视下,赤裸着身穿过客厅,走进自己的房间,倒在床上,盖上被子。躺了一会,又想起了什么,爬起来,歪着身拽开床头柜的抽屉。纸还在,曾经鲜亮的纸暗淡了,像沁过一层薄水,未干透,微光小心翼翼地打在纸上,她看见男人那像飞龙上天一样签下的名字,她的心猛然一揪,鼻尖前的空气变得稀薄,手不停地抖着,眼泪不争气地流出来。
泪眼婆娑里,她看见系着红绸布,扎着羊角辫的女孩,默默地看着她,看着她。
4
电梯前,她稍一停滞,身体像一根无根的棍子,被人群抵向了楼梯旁靠玻璃墙的地方。她索性站住,这里总算有了些空隙,眼睛也空了出来,不至于被人群填满。向外的一面全是玻璃墙,透过玻璃,能看到楼下园子里靠墙的一溜发出了新鲜绿叶的竹子和冒着白色水汽的扭动的喷泉。人们在氤氲的水汽里穿行。喷泉池子的不远处,有几株盛开的樱花树,一朵一朵,一串一串的粉红的樱花像一张张张开的伞,布满了树的枝头。只有为数不多的叶子有序地穿插在花间。叶不是全绿,微微泛紫红。
今天风很冷,她在路过那个喷泉旁时,风紧了些,夹带了冰凉的水丝拂到她的脸上,把那些附着在她脸上和耳垂边际的头发一股脑地掀起,又继续朝她的脖子里钻。她略略颤动了一下,禁不住缩了缩脖子,那个鼓起的地方也跟着缩了缩。她有种想保护它的冲动,抽出插在大衣口袋里的右手,捂住了那个地方。它一直是不疼的,一直是沉默的,沉默的让她忽略了它的存在。可是,这两天它似乎有被唤醒的意思。她不断地摸它,手掌在它的身体上来回摩挲,像抚摸自己待出世的孩子。她已经能感觉到它了,它的悸动,它的颤抖,甚至还有它不安分的跳跃。有时,她觉得它在她的脖子上踢了一下,翻转了个身,又牢牢地贴合着占据着她脖子上的那块地,一块肥沃、白皙、柔嫩,从没让她为它操过心的,接近脖根的地方。
每次,她往脸上涂了一层又一层时,从未涂过脖子,脖子有衣领遮,或者系一条丝巾,丝巾有多漂亮,脖子就有多漂亮。她有很多条丝巾,纱的、线的、羊毛的、真丝的,颜色、花样各异,如果摆齐,就是一长溜,能摆摊了。她总说不买了不买了,可要是再遇见中意的丝巾,她还是会买,忍不住买。
那次,她站在省城的街头,等女儿的间隙,进了一个卖服饰的店面,像是中魔了,在那么多漂亮的衣服里,只放了一条点缀店面的丝巾,被她一眼相中,浅绿上绣了一朵朵紫色的小碎花。老板开价三百,一分钱都不让,她踌躇了一会,在女儿来找她之前买下它。丝巾到手,她出了店门,丝巾在光里现出了陈旧的气息,一丝悔意掠过。但她固执地没有停下,迎着和女儿说好的方向疾步走去。见了女儿,女儿并没有注意她手中捏着的丝巾,她却忍不住地说:“可好看,新买的。”女儿看看说:“像旧的。”她说:“猜多少钱。”女儿说:“二十。”她一听,像做贼的,赶忙把话题转移开。
她又抬手摸了摸它,这个动作怎么会在倏忽间成了她的一个习惯性动作,在这习惯性动作的背后,是让她莫可言状的心悸。是那种不在乎,又不得不在乎的压迫感。她觉得憋屈,一个连自己的皮囊都不能压制住的自己,她还能坚守和维系得住什么?
风抽打着玻璃,把她游离的思维拖回到眼前。她觉得脖子的某个地方有疼的感觉。哪里疼了呢?她手摸的那个地方还老老实实地待在她的掌心下,没感觉,到底是哪里疼?
她去挂号的时候,才想起来,她连这个包属哪个科都不知道,她焦躁地看着墙上分布的各科室的小字。
5
早晨,绿碎花窗帘布透出微弱的光,她从混沌的梦中醒来,做了一夜的梦,在梦里,她赤着脚,总在被人追赶的仓皇奔逃的路上。地上黑漆漆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她像悬浮物一般,路不在脚下,脚下没有路,她却在跑。脚明明是向前跨的,身体却还在原地。她好急,叫起来,手脚并用地挣扎中,她被自己抓醒了。
她看了看天花板,感觉有人在看她,她猛地看向房门,门前什么也没有,门是洞开的,客厅的灯还亮着,桃色的门像一个人,她看它时,它也在看她。
门怎么是开着的?
她已经保持了二十多年的习惯,即使女儿在家,她也不能容忍门是开着的。门开着,她会睡不着觉,总觉得门那里站着人,那时候,她和男人还居一室,男人出去应酬,回来得晚,后上床,忘了关门,她在梦里都要喊关门。
她的手触到了自己的身体,光溜溜的,她居然没有穿衣,连内裤都没有穿。她不禁有些后怕,又有点脸红,要是被男人看到了,会怎么想自己?
男人呢?
朦胧中,她终于想起来,睡觉前她拿着那张纸哭得颤巍巍的,想着一个没有父母的人,将要失去另一半,她的眼泪就止不住。以前她没好好想过这些事情,她想男人只要回来,就还属于这个家,他们就还是一家人,她就不是别人眼里嘴里的那个离婚的女人。她心里的那个位置就还是满的。可是现在她感觉那个位置有了印痕,像是坑沿,坑已见雏形。所有人都要知道,她要变成一个孤独的女人。
她从床上一跃而起,拽过睡袍套在自己白花花的身体上,带子没系,只用手抓着中线,她要看看男人到底有没有回来。夜里她没有听到一点响声,男人如果回来,就算动作再轻,锁芯摇动的声音也不会逃过她的耳朵,她对自己的耳朵深信不疑。在静寂的夜里,她感觉即便是一根针掉落的声音也难逃过她的耳朵,她的耳朵经常能捕捉到夜深时,来自于天花板上窸窣的脚步声,这让她会无由地想起那些在春雨绵延的深夜,无数棵春芽破土而出的样子。
往常即使她的门关着,不管有多晚,也能听到男人回来的声音。开门,锁芯转动,咔哒声,门开,摁亮灯,放包,换鞋,进厨房倒水喝水刷牙,拿换洗衣服,进卫生间洗浴,关卫生间和客厅的灯,进他自己的房间,门合上,锁咔哒一声。
她就那么一直听着,眼睛闭得久了,睁开,黑便像一团麻缠绕在她的眼眸上。男人终于忙完,房间里安静下来,世界安静下来,她的耳朵重新回到了放空的状态,也安静下来。人间是如此安静,尘世连一丝风也吹不进来,她喜欢这种极致的静,心满意足地倒在黑夜里,昏昏欲睡。
她扑向男人的门,却又在门前戛然停住。左手依然抓着两边的衣襟线,右手搁在门上,要叩门时,手背又停住了,男人的门在这一刻变得坚硬无比,寒气逼人……
她竟不知道是进是退,她犹豫着,想抽身回屋,身体却像一块面板贴着另一块面板,一动不动,她指挥不了自己的身体。许久,她感觉自己的身体都僵硬了,才终于举起手。先是轻叩,再叩,攥起的指背用了点力,叩门声重了些,发出“嘟嘟”的音,门没有反应。她再叩,空气里凝结的固体气息扑面而来。她攥紧了的拳头又张开,她的手在拍,打,捶之間交替,门却依然纹丝不动。她的身体由冷变热,由热变冷,凉丝丝的感觉再次冒出来,她的身体僵硬地颤抖着。晨光已穿过窗帘探了进来,她的心悬起又落下,她感觉好累,歪头把脑门顶在门上,搁了一会,她的脑门突然离开门,身体向后退了半步,眼睛盯着门,冷不丁抬脚恨恨地往门上踹。门开了,她却收不住脚,身体趔趄着向前,脚跨进了房里。
门向后退去的一瞬,她的心也跟着咕咚一下。
她不记得自己有多久没进过这个房间,房间里黑洞洞的,原来粉色的窗帘换成了墨绿色,盖住了一面墙。床上只有床板床垫,房间里除了木质的家具,她什么都没看到,连一张纸片也没有。男人没有别的嗜好,搁家拉杠铃,看新闻,翻手机,只要电视开着,饭都可以不吃。男人待的房间的桌子上竟然没有杠铃?她看得心惊肉跳,心提了上来,不好的预感压得她透不过气。
她已顾不得没有系带子的睡袍和她赤裸的身体了,敞胸奔向柜子,抽屉,并把它们拉开,什么都没有,连纸屑线头,废弃的衣服和破袜子都没有,真干净!
男人到底是走了。
她原想只要男人打开门,不管以什么样的眼神看她,哪怕是不屑的,恶狠狠地恨不能要吃了她,她都会不管不顾。
她要当一个瞎子聋子,不等男人说话,毫不犹豫地扑进他的怀里,向男人哀嚎、哭诉,任凭男人发落。她全不在乎,只会迎合男人,她已经很久没有被谁拥入怀中,连那是什么滋味都忘了。她想现在自己的脖子上都长包了,还有什么可顾及的?所有包藏的爱意恨意,以及残存的矜持怯懦,都让它们随风去。
她想起了男人以前的样子。那时,他很爱说话,整天像个蚊子般绕着她,一有时间就要拉着她看这看那,一脸喜气一副讨好她的样子。她却面若冰霜,男人说什么她都不爱听,男人说什么她都不爱看。她听男人嘟嘟的,会忍不住,扭脸,撮眉,翻眼,冷若冰霜。她不喜欢一个人,即使他口吐莲花,她也懒得搭理。有了女儿后,她对男人的冷淡成了她的习惯,男人也习惯了她的冷淡。她不理会男人,男人就逗女儿。只有女儿的笑,才能引起她的笑,他见她笑,他便也笑。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女儿的笑越来越少,越来越珍贵,他们的笑也跟着越来越少,越来越珍贵。
可是,现在她才知道,她习惯了的生活,随着男人的离去,将轰然坍塌。
在一片废墟中,她似乎看见一个系着红绸布,扎着羊角辫,花一样的女娃,向她笑,又向她哭。
6
她在二楼大厅转了个来回,又勾头进了大厅旁的几排屋子看了看,每一队人群都从门里排到了门外,队伍外也站满了人,不知道医院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在普内科,她看见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被几个人推出屋的女人,手里拿着化验单,上蹿下跳,往外退时,嘴里泛出了白沫,带着哭腔地叫骂着,奶奶的,都是什么人?让帮忙看一下化验报告比吃屎还难。她凑上前问:“不给看?”女人像遇见了知音,停下来,义愤地说:“钱没出到位。”女人哼哼着抖手中的单子,报告单被抖得哗哗啦啦响,女人情绪激动,扯着身体,对着那间办公室,像是要伺机回去。几个已经松开的手,垂在自己身体的两侧,没有动,眼睛怔怔地地看着女人,也或许什么也没看。女人在原地窜了窜,身体像赘了冰渣,没动,女人再次翻动着细薄的嘴唇嚎道:“我来医院验血体检,我怎么知道看检验报告还要另外挂号?”几个人捂嘴似笑非笑,女人冲他们看看说:“别以为他只对我这样,下一个就是你们。”几个人甩开手,脸绷着进了办公室。女人叫嚷时的声音越来越低,已陷入人群裹挟中的她,看见女人满是委屈的眼神,像是要哭了。
她不忍心再看女人,脚步往后缩,身体也往后缩。女人却停不住地说:“我家在河北(河的北边),昨天有事,没等到单子出来,今天特意赶了个大早来,就是想听听医生怎么说。”女人的眼睛朝普内科办公室的门死死地盯了一会,像是要记住什么,可是她能记住什么,记住什么,又能怎样?女人收回目光,无奈地看着手里的单子,又看看门,无助的样子像一个找不到回家的路的孩子,她不忍心再看女人,想把脸扭向一边,却又想知道女人到底会怎么办?有一阵,她恨不能接过女人手里的单子,跟她说个所以然来,也让她不白跑这一趟。可是,她能道出个什么道道来?女人要走时,嘟囔着:“现在哪都讲钱,没钱,寸步难行。”女人说时,已夹在人群中,朝电梯口走去。她不知道说什么好,也没法接话,只大张嘴,人们很快就把女人忘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都忙。她愣愣地目送女人的背影融进人流中,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
她的眼睛在大厅的人群间穿梭,偶尔有白色的身影夹杂其间,她终于想起那个邻居的网名了,单字“白”,她记得她们互加好友的时候,她还有意开过玩笑,说:“白?”邻居说;“好记啊!你只要看到了白,就会想起我这个白。”邻居的话没错,她果然在一片白中想起了白,找到了白,她拨通了白的语音,心里咚咚地激动起来,没等白说话,她赶紧说,她赶紧说时,又发觉自己不记得白的真名姓,该怎么称呼?稍一犹豫,她嘴里已经模糊过去,说我是某某,脖子上长了个包,该挂哪个科?她正等着白的客套话,哪怕是一句安慰话也好,或者酝酿一会,她没想到白会回答得那么快,言简意赅,只有四个字:“肿瘤外科”。她一听到“肿瘤”两个字,心一紧,眼泪出来了。她想她怎么能挂肿瘤外科?她在心里说,白,你要是没时间,或者懒得搭理我,也不要敷衍我,诅咒我啊!
她的心怦怦跳起来,头迷迷瞪瞪的。眼前晃动的黑漆漆的人影突然间变成了红色,一张张行走的红色的纸,布满了大厅的各个角落。一阵风从玻璃墙上穿进来,风到之处,纸被吹得东倒西歪,乍开的四个边抖动着,发出噗噜噜的响声。她真怕他们会飞起来,因为不顺着风向,会被扯碎,扯得四分五裂。
她的身体紧贴着墙面,有一阵,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进入了墙里。瓷砖冰凉地划过她的脖子,那个微微鼓起的包穿过瓷砖锋利的牙槽,没有疼,一点感觉也没有,身体像海绵,瓷砖的牙槽也像海绵。风这时发现了她,向她吹来,她也变成了红色的纸片,她不敢看自己纸片的身体,她看向大厅,惊异地发现有几张纸片上出现了图案,随着风势,图案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几张出现了图案的纸片上刚现身,众多的纸片像听到了指挥,被施了魔法,纷纷朝一旁闪去,给出现了图案的纸片让道。
她的纸片身體从瓷砖的牙槽里滑出,脖子上的包不见了,出现了一个深红的小圆圈,她想用手摸摸,却发现手没有了,手和身体成为一体。
7
她正不知所措,突然一阵怪叫声由她的身体里传出,她感觉身体在颤抖,她猛地抽出右手,风戛然而止,大厅里那些行走的红色纸片没有了,穿着颜色各异的人群,在大厅和电梯之间的科室,机子间忙碌着,脸上写满了焦虑、烦躁、痛苦、迷惘,仿佛人间所有的苦难都在这里汇聚。
所有的人都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她抓出挎包里的怪叫物,随着她双手乍开,她感觉有东西从她的双臂间洒落。电话是女儿打来的,她的心抖了抖,又赶忙镇定住自己,才接通了电话,女儿粗喉咙音响一般闷炮蹦了进来,她一直不喜欢女儿的声音,她觉得女儿什么都遗传了自己,五官清秀,体形细瘦,不高不矮,唯独嗓音遗传的男人。而她偏偏喜欢有一副好嗓门的人。女儿小时候因为这嗓门,没少挨她的吵。她说女儿,女孩子家,说话时也不知道捏一下音,别像你老子,他是没救了。女儿听了似懂非懂地点头,可转脸说出来的话,还是粗喉咙。她再说女儿,女儿的话便越来越少,她不问,女儿就闭嘴。到后来,不管她问不问,女儿都不用嘴答,只用眼神和动作作答。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女儿上大学,才有所改善,女儿总算能和她说两句话了。她看见女儿的电话,心扑扑的,女儿不轻易给她打电话,女儿说“妈,在哪,这么吵?”她想说,她在医院。可她没说,她回:“干嘛?”女儿说:“妈,你怎么把我微信删了?害得我都不好给你留语音。”她懵了,说:“删了?”她迅速在大脑里过了一遍,说:“你,你换名了?”她没想到女儿是为了男人的事打电话的,女儿说:“我爸让我跟你说,他出去住了。”她不假思索地张开嘴:“出去,让他出去,死在外面才好。”女儿突然安静下来,她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粗糙的男人的声音,像是从腌菜坛子里发出的,她的话音没落,身边的人都看向她。她慌忙垂下头,有雨从脸上滑出,她感觉脖子那里像是有什么东西赘着,用手去摸,在原来小包的地方鼓出了大包,快要填滿她的掌心。她用手盖住大包,她感觉有人看她,她抬起头,目光顿然消失。几个人头顶头,窃窃私语。
她木然地站着,天地旋转,她想跟女儿说什么又不想说,她感觉有股凉风从心底吹过,她怕一张口,声音会颤,会控制不住泪腺。她不等女儿再说什么,切断了通话键。她上了下行电梯,下行电梯上的背影,和一旁上行电梯上的人群,是那么陌生,前后都是人,她被固定在她脚下的那一格里。下行电梯越来越慢,像被施了魔法。
她感觉身体的某个部位在变化,她下意识地抬手抚在大包上,包似乎更大了,超出了巴掌的范围。她惊恐地发觉自己的上身变得越来越重,迷迷糊糊中,她看见一张中年妇人的脸,她伸手去抓自己的腿,她要让她看看,她的腿是多么干净,白皙。可是,她的腿却怎么也抬不起来,她的腿几乎要撑不住身体,额头沁出了汗珠。
她双膝一软,身体向空,眼前出现了一片鲜艳的红,两个翘翘的羊角辫,系着耀眼的红绸布,像系着一束花。她伸手去抓那束花,却什么也没抓到。她想叫却叫不出来,也不敢叫,她害怕他那像腌菜坛子里发出的声音,再次响起,又再次把自己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