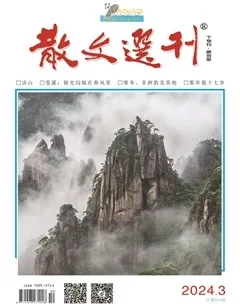吾乡俚语
2024-05-01杨文隽
杨文隽

世界本是一个方言场,方言本无所谓好坏,但在吾乡人,只觉得吾乡话好听,正宗。
吾乡本地,则又极复杂,东边人笑西边人,南边人笑北边人。一家之中,所操又不同,比如我爹说西边话,我妈说东边话,西边人说“泥土”为“拿泥”,我妈常说“真难听”,比不得东边人说“奶泥”好听,在我看来,“亮月就是月亮”,其实大抵还是类似的。有一种人,读书或当兵到外头去了,见识了所谓世面,回来就再也没有一个“乡音无改鬓毛衰”的贺知章了。大家听着他们的普通话,很别扭,称为“洋泾浜”。有时候大家把他们说的词汇当作笑料,讥讽为:“天不怕,地不怕,只怕本地人说官话。”
吾乡话土得掉渣。金黄的银杏叫“白眼果”。青鱼的尾巴叫“划水”。打雷叫“阵头响”,闪电叫“忽现”,也有人叫“过海面”,可远方的亲戚为了“过海面”寻瞎眼睛。有的词,翻遍《辞海》也找不到发音,找不到对应的字。东的“ ”在《新华字典》中就没有gang 这个发音,以前的电脑里也打不出这个字。回家,吾乡的话是“转气”,土!还有更土的,膝蓋叫“青馒头”,有本地的厨师一说青馒头,外地人以为要端馒头上桌了,而且是青颜色的,闹出不少的笑话。
吾乡人很排斥外来语,要想融入这片土地就要入乡随“话”。遇到外地人在这儿生活的,就直接以他们的语种称呼,什么“江北佬”“湖北佬”“东北佬”等等,多少有些无伤大雅的地域歧视的意思了。
我们村上有七个兄弟,他们的爷爷辈是从苏北淮安迁来的。从我记事起一直以为他们是本地人,因为到他们这一辈已经能够讲一口地道的本村话,丝毫感觉不出他们曾是外乡人。记得大哥家的一个孙子跟我同桌,有天村上摇来一只苏北船,摇船人大概认识我同桌的爷爷,在我同桌爷爷家歇脚吃饭,其中有一个刚高中毕业的小青年,对我们的方言极感兴趣,用普通话问我同桌:“你们这里螃蟹怎么说?”他答:“哈。”小青年重复:“你们螃蟹怎么说?”他答:“哈。”小青年很无奈地问:“那鱼怎么说?”他回:“嗯。”他奇怪地问:“那虾怎么说呢?”他说:“呼。”小青年又问:“那鸭怎么说呢?”他说:“啊!”他又重复:“鸭怎么说?”他说:“啊!”小青年很同情地看着我同桌:“多好的一个孩子,可惜是个哑巴。”
过去,一条村巷上几十户人家,沾亲又带故,知根亦知底,房屋显高低,生活有穷富。好人占绝大多数,但总有个别“坏人”,譬如“折脚”“瞎子”“戆头”,这是指身体有缺陷的人,是让人怜惜同情的,不是真正的坏人。真正的坏人,譬如“贼骨头”“姘头”,前者偷东西,后者偷人,是让人咬牙切齿痛恨的。
吾乡人重伦理,崇礼仪,忠孝传统、耕读传家的理念根深蒂固。批评人的语言特有嚼头,拥有质朴、率真、风趣、智慧之美。
常用一个“ 贼”字,如“ 贼腔”“ 贼坯”“ 贼魂”。贼头狗脑、不光明正大的叫“贼腔”。
但是不同的对象表述的内涵是要你用心体会的,对陌生人骂“贼腔”,带着轻蔑和看不起,不入流之辈,绝对不在我们的眼里。对熟悉人骂“贼腔”,有时是指对方搭足架子、不理不睬的“死腔”,有时指对方没有正形、挤眉弄眼的“怪腔”,骂中有责备的意思,但没有仇视。对小孩骂“贼腔”,大多指行事不合常理、夸张滑稽的“疯腔”,也有指蒙头转向、一百样侪弗晓得的“戆腔”,基本等同于“古灵精怪”。尤其要求小孩做个“贼腔”,那就是满腔的爱了。“贼特兮兮只面孔”,就好像本地言话里的“小鬾头”一样,绝对是“我的甜心”之同义词,粗则粗矣,心里还是疼煞俚爱煞俚的。
做坏事情、像贼一样的家伙叫“ 贼坯”。其词汇色彩多带贬义,贬义的程度有轻重之别。用第二人称骂“恁只贼坯”,是直面斥责,虽贬,却含些许友善、爱怜;用第三人称骂“俚只贼坯”,是深度嫌弃,有种娘肚皮里就生成的“血统论”之嫌,这种人是要与之断交的。
过去社会不开放,一对男女哪怕是合法夫妻,要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搭搭摸摸、搂搂抱抱、啃啃咬咬,看上去就有点“贼腔”、像个“贼坯”了,恐怕要被轻贱称呼的。
“贼魂”其词汇意义为语气助词,通常语气加重变“娘个贼魂”,所以“贼魂”和“娘个贼魂”是两句吾乡田头巷间的粗口,正因为它们是粗口中口味较淡的那种,因此流传得更广。男的可以讲,女的也可以讲。小户人家可以讲,读书人难般讲讲,好像也不怎么有伤大雅。于是,就这样稀里糊涂讲了许多年。真要认真问起来,这两句话啥意思,恐怕没多少人可以讲得清爽,就好比宁波人的口头禅“娘希匹”,并不只是蒋介石一个人这样讲。然后,有一个人写了一套四本《金陵春梦》,书里的蒋介石一口一个“娘希匹”,弄得大江南北人人皆知。到底啥意思?从字面上详,是无论如何也详不出来的。
需要说明的是,这三种最常用的“贼”既是骂人,也可能是亲人密友间的昵称。
大热天,老底子没空调也没电风扇,大家都坐在弄堂口晒谷场上乘风凉。突然之间,木格楞窗户里一个刚刚结婚的新娘子的声音飘出来:“恁只贼坯,碰着人家难过煞落了。”其实并没啥,就是翻只身不当心碰着了,汗嗤嗤哩嗰。“娘个贼魂”,本来大家就热得心烦气躁,你让单身男女如何入睡!
不过近年来风气大变,吴方言区的人也开始流行起普通话来了,而且大有看不起自己方言之势,我见小孩子中,能说正宗吴方言的几乎已经寻不着一个了,倘若今后祭祖,祖宗在天之灵,恐怕也不晓得子孙在说什么了!我记得自己读书时候,即使读英语单词,也是带着吾乡口音的,比如“Window”就读成“馄饨”,“English”读成“阴沟里去”,甚至还模仿着英语的腔调,把黄鳝、泥鳅叫成“捏不牢滑脱”。
总有那么一天,吾乡的后人也能听懂柴可夫斯基、莫扎特,也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德语,却终究听不懂这里不同鸟的叫声,辨别不出这里每一棵草的名字,忘记了那一口“醉里吴音相媚好”的语言。
终究会这样的。
那么,留住乡音,不忘乡言,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我们可以做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