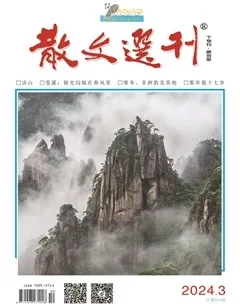抽屉
2024-05-01何宗焕
何宗焕

我家有一张抽屉桌,是那种旧式的书案式长桌,看不出它的年代和年纪,桌面厚实,四条腿上方下圆,通体是陈旧的暗红色,却并无斑驳和脱落。和它相配的还有一箱一笼一柜,图案式样都显示出一种华贵气象,不像普通人家的东西。母亲说,这是她嫁到我们老何家的嫁妆。
这张抽屉桌靠窗,窗子朝北,不大,光线并不好。桌上是一面镜子,一盏煤油灯,一个像镇纸样的方木条,一支毛笔,一块墨条。有三个抽屉,左边抽屉里是各种碎布条,还有鞋样、鞋垫、针线之类,是母亲的百宝箱;右边抽屉是各种碎纸边儿,也有我们弟兄的陀螺、弹弓等玩具。中间抽屉不如左右两边深,但宽大多了,里面有不知年头的通书,两本没有书皮的《幼学琼林》,还有一本《医方便览真本》,再就是父亲的烟叶卷。这张抽屉桌既像母亲的梳妆台,又像父亲的书案,但我从没见过母亲在镜子前梳头,家里人多,洗衣做饭已够她忙的了,有空闲时她就用那些碎布条给我们兄弟纳鞋底。倒是父亲,我时常见他在桌前流连,但也不是读书写字。
父亲在抽屉桌上切烟丝。父亲切烟丝非常仔细,那些烟叶挂在墙上晾得差不多了,父亲就会一张张抻平叠好卷紧,用线细心扎起来,然后切成烟丝,细细的烟丝可以拉得好长好长,父亲一次不会切太多,父亲吸水烟,他的水烟筒有一个烟斗,装满烟斗的烟丝够他抽上三四天,所以他隔几天就会切一次烟丝。他的烟叶卷就扔在抽屉里,像在地窖里放久了的一截老蔸番薯,那烟叶的颜色也跟屋檐下晾干了的番薯叶一样,晦暗枯黄。我闻过那烟卷,淡淡的,没什么烟味。
父亲其实是一个读书人,抽屉里的两本《幼学琼林》,他时时会念上一两句:“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患难相顾,似鹡鸰之在原;手足分离,如雁行之折翼。”他念得摇头晃脑。还有那本《医方便览真本》,毛笔手书,蝇头小楷,清秀可爱,他说那个人不仅医术了得,字也是真功夫——可惜书上没有著者名姓,父亲也不知道是谁写的。多年来,这个抽屉,以及抽屉里的这几本书,我一直以为就是我们家“书香门第”的资本,也是父亲“家学渊源”的见证。父亲读的书肯定不只这些,但在那个年月,他从不跟我们讲这个话题。后来听人说,大队上民兵营长家里,有好几套我们家的线装书,都是从这个抽屉里抄走的。
父亲写得一手好柳楷,大字遒劲,小字端严,一寸左右的中楷尤其风华雄健。他常用的也就是寻常的毛笔,但握在我手里就是写不好。我最喜欢看他写字,那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让我肃然起敬。他的字写得好,却没有用武之地,几乎没人请他写字,他只好在箩筐扁担上显示自己的笔下功夫了。有一回他在新打的谷筛上沿端端正正写了一行老长的文字,“公元一九七四年农历甲寅四月上澣榖旦立”。我不知道“上澣榖旦”是什么意思,便问他,他把谷筛举起来,仔细端详那一行字,说:“以前人都这么写,讲了你也不懂。”我时常疑心,父亲把他对旧日时光的怀念,留在了那支自在的得心应手的笔下。父亲始终不肯教他的几个儿子写字,大概觉得一辈子都是被这些东西耽误了,没有必要再害下一代了。可是下一代也看不出出路在哪里呀。
那个抽屉是没有任何秘密可言的,但我觉得父亲一定有一些秘密。不然,为什么大队上的民兵经常来抄家呢?
那时,谁家里也藏不住什么秘密,我们去小伙伴们家里都可以穿堂入室,翻箱倒柜,有一次躲猫猫,有个小伙伴就钻进了人家大柜。我的好朋友也经常从自家抽屉里分享他们的宝贝,弹子啦、电池啦、纸牌啦、滚珠啦。有个时期,孩子们忽然流行养蚕,有同学甚至把蚕宝宝带到了学校,藏在了课桌里。我也跟上了这股时髦之风,我的蚕就养在了家里那个大抽屉里,蚕盒、桑叶、白花花的蚕宝宝、黑点一般的蚕屎,整个抽屉成了蚕的世界,父亲的烟叶卷也被我清了出来。父亲也不恼,蚕子儿出蚕前,他还问我:“放在抽屜里不好吧,要不要放进被窝里?”
我一直认为父亲的秘密都在那口皮箱里,不说别的,光外面的铜扣和皮褡襻就有七八个,还有那个把手,昂然突出,盈盈一握,手感柔软温暖,箱子里面的衬里都是质地滑溜细腻的绸缎。这口皮箱出身高贵,身世不凡——父亲不说我也知道。我疑惑的是,家里那么多宝贝都抄走了,为什么这口高档皮箱没有被抄走。父亲是当过伪保长的人,村上民兵老是怀疑他藏有手枪、子弹,或是敌特联络簿、“变天账”之类,不过,这些东西从来没有抄出来过。
在我读初中时,父亲的秘密藏不住了。那一年开学,我没有交学费的钱,父亲给了我两个银圆,说到镇上的银行可以兑换几块钱。我大惑不解,家里明明被多次抄到了底朝天,父亲怎么还藏了这样的东西?抽屉显然藏不住这样的秘密,皮箱也藏不了。我不敢多问。镇上的银行门脸不大,柜台很高,我非常紧张甚至有些惶恐地把银圆交到了柜上,我担心柜台里的那个人要问我什么,比如银圆是哪里来的?什么人给你的?那我怎么回答呢?我紧张得头上冒汗,好在他什么也没问,给了我六元钱,正好是交学费的数目,我如释重负。
父亲显然还有一些秘密没有跟我们说,比如他当“保长”的事,他怎么就当上了呢?干过什么“坏事”吗?
上世纪80 年代,父亲中风后偏瘫,整日坐在这张抽屉桌前写家谱,我小心翼翼地说,何不写写自己的身世?他没作声。他把家谱整理得细致清晰,自己的事终究一个字也不写。
让我想不到的是,好几年过去了,父亲还在给我们制造惊奇:我的两个哥哥结婚,父亲竟然还给了他们每人一块银圆。父亲怎么留了那么多呢?我好想打开那个秘密之门,可是一直不得其门而入。
直到父亲去世,他也没给我们讲过有关他过去的任何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