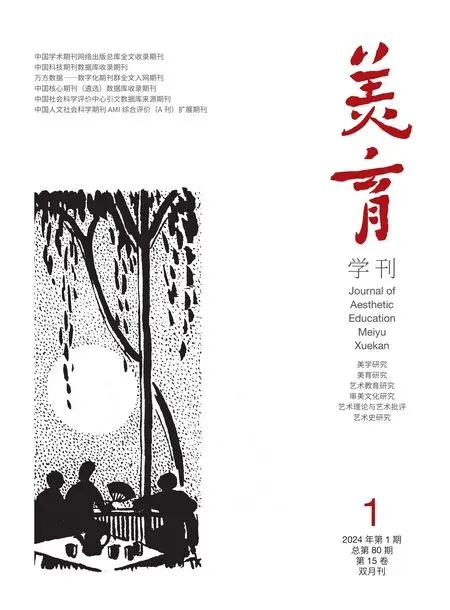艺术史的人文性质及其在艺术教育中的价值与定位
2024-04-30刘强强
刘强强
(杭州师范大学 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12)
作为一门学科的艺术史诞生于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其正式的创立者被认为是以研究古代艺术而著称的温克尔曼。特定的研究对象和历史语境,使艺术史有着与生俱来的人文性质,此种人文性质亦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反复论及。在《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史》一文中,潘诺夫斯基首先对“人文”(humanitas)的概念予以阐释,认为其分别指向了人与低于人者及高于人者的差异,前者意味着对原始生命状态的脱离,后者则显现出对在中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意识形态的反叛。与之相应,在潘氏看来,关于人性价值的坚守和对于人类有限性的承认构成了“人文主义”(humanism)的核心内涵。传统记录且表达着人类的伟大与渺小、自由与限度,所以对于传统的尊重构成了人文主义者的基本特征。艺术史以独特的方式承载着传统的信息,并由此展现出鲜明的人文性质。且传统的信息在此又并非以知性的方式传达,而是通过感性的经验获致。此种对于个性、体验的强调,亦是潘诺夫斯基所理解的艺术史人文性质的重要方面。[1]3-4、11。
本文的探讨首先从艺术史与历史的关系入手,其次将艺术史的习得视为学习者个体经验与艺术作品所传达经验的交织,并由此寻绎艺术史在艺术教育中的价值与定位。
一、艺术史与历史
在西方语境中,艺术史有着两种不同的表达,一种是“history of art”,另一种是“art history”。这两种表达虽然可以互换,但又有着微妙的差异。根据雅希·埃尔斯纳的观点,后一种表达相比前者而言更为宽泛,它不仅指向了通过历史来阐明的艺术,同时亦可说明通过艺术来阐明的历史。[2]5而无论就何种表达来说,艺术与历史均有着不可分割的因缘。艺术史从其诞生之日起,便是一种关乎历史的事业。作为艺术史学科的开创者,温克尔曼首先为艺术注入了历史意识。他通过经验主义的观察总结出艺术作品的风格差异,并以此建构出艺术发展的序列。在《古代艺术史》的开端,温克尔曼如此说道:“艺术史的目的在于叙述艺术的起源、发展、变化和衰颓,以及各民族各时代和各艺术家的不同风格,并且尽可能地根据流传下来的古代作品来作说明。”(1)转引自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17页。但与此同时,温克尔曼又是在“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的视野中思考艺术的,也即将艺术置入具有总体性与普遍性的社会文化与时代氛围之中,并将其视为民族精神的集中显现。这也就意味着,艺术史不仅是关乎艺术自身的历史,同时也与总体的历史进程紧密相关。更进一步言之,艺术的秩序化推动着历史被纳入一种理性化的结构之中,进而促进了人们对于历史的理解,正如有关论者所说的那样:“(温克尔曼)从古代艺术作品中归纳出来的一个能让各种经验事实变得有意义的理论模型、一个赋予经验材料以更宏大秩序的理性结构。”[3]
温克尔曼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如同埃尔斯纳所论,自此以后,“研究对象和艺术作品的意义不再能够与其诞生的语境分离”(2)参见雅希·埃尔斯纳:《全球转向下的艺术史——从欧洲中心主义到比较主义》,胡默然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4页。。这首先意味着,对于艺术史的研究必然要诉诸更为广阔的历史情境。唯有置于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语境当中,艺术史才能获得更为合理的叙事。另一方面,艺术进入了历史,艺术史不仅成为后人理解历史的重要途径,亦是历史研究者不可忽视的关键对象。之所以如此,正因为艺术作品不同于文字记录的特点。艺术不仅是民族文化与时代精神的感性凝结,亦是人类情感世界的集中表达,从而使艺术史对于历史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为例,作为文化史研究的奠基之作,该书虽然没有探讨任何具体的艺术作品,却常常被列为艺术史学科的必读书目。其原因在于,布克哈特正是通过对特定时期艺术作品的感受与认知,形成了对于该时期社会心理与文化氛围的理解。也正是因此,曹意强称之为一部“省略了艺术的艺术史”[4]。作为布克哈特的学生,沃尔夫林并未亦步亦趋跟随乃师的脚步,而是致力于建立一种消解了艺术家的艺术史,也即将艺术史描述为形式自身的变革与演进。但与此同时,沃尔夫林又不能忽略流派、民族等因素在形式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时代风格”这一超越了具体作品风格的观念。而同样被视为形式主义者的李格尔,亦认为每一种时代与民族都有其独特的“艺术意志”。“每个时期都拥有它自己独立的、植根于同时代一切文化之中的艺术意志。”[5]一反在当时艺术史学界流行的物质主义观念,李格尔认为艺术家自身的审美趣味和创作冲动构成了艺术形式变迁的主导因素。而比艺术家个体意志更为本源的,是由时代精神所构成的集体意志。也正是因此,贡布里希标注出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于李格尔的重要影响。[6]无论是沃尔夫林的“时代风格”还是李格尔的“艺术意志”,均显现出历史对于艺术史的强烈渗透。艺术史所承载的不仅是具体的历史信息,同时也表现了幽微而难言的时代精神,不仅是形而上理念的具象化,同时也以感性的方式储存并表达着特定社会环境中人们的内心情愫。因此,不存在一种脱离了历史的艺术史,亦不存在一种缺少了艺术史的历史。脱离了历史的艺术史将沦为一盘散沙,缺少了艺术史的历史则会为不断加高的故纸堆所深埋。
二、艺术史与经验
对于历史的理解需要理性、知识与逻辑,但由于艺术史的直接对象是艺术作品,所以审美体验构成了艺术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本维度。潘诺夫斯基曾将艺术作品定义为“要求人们对之作审美体验的人工产品”,并随之阐释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史的特殊性。他说道:“人文学家虽处理人类行动和作品,但他必须从事带有综合性和主观性的心理活动:他必须在内心重新体验人类的行动,重新创造人类的作品。实际上,正是通过这个过程,人文科学所研究的真正对象才得以形成。”[1]11艺术作品是人类经验的物质化呈现,对于艺术作品的感知必然要诉诸欣赏者的个体经验,如此也就形成了欣赏者自身经验与艺术作品所携带经验之间的往复流动。可以说,每一次对于具体艺术作品的亲临,都是一次经验的激发与重构。而这必然形成个人的、主观的审美体验与普遍的、客观的历史研究之间的矛盾,此种矛盾在艺术史学科甫一诞生的时刻即已存在。埃尔斯纳曾对温克尔曼充满抒情性的文字予以分析,并认为此种在绝望与希望之间转折激荡的强烈情感,正是艺术史写作事业所必需的冲动。换言之,正是对于具体艺术作品的审美感知和情感体验,构成了艺术史写作的根基。如果丧失了对于具体艺术作品的感性经验,那么艺术史的大厦也就会轰然倒塌。埃尔斯纳说道:“尽管西方传统总是希望通过历史来驯服和限制艺术本身,但它总会发现历史那被拉开了距离且具有支配性的叙述被绊倒在当下,绊倒在艺术作品引发的存在(bing)自身的存在主义欲望与绝望脚下。”[2]40对于具体艺术作品的经验永远不会为客观的、理性的历史意识所湮没,这正是艺术之本质对于艺术史所提出的必然要求。
对艺术作品的欣赏主要诉诸人的感性能力,这里所谓的感性并非仅指感官与身体,亦非对于理性能力的拒斥。依据鲍姆嘉通的观点,感性的范围不仅仅包括视、听、味、触、嗅等外在感性机能,同时也包括情感、想象、记忆、趣味、预见、直觉、表现力等多种内在感性要素。感性并非达至理性认识的前提与准备阶段,而是自身的方式容纳着理性,即鲍姆嘉通所说的“近似理性”。在对艺术作品进行欣赏的过程中,个体的外在感官以及情感、想象、记忆等内在感性能力均得到充分的激发与调动,这些感性能力均是个别的、独特的,它们与个体的先天禀赋与成长经历密切相关,这也就决定着对于艺术作品的欣赏有着其他活动不可比拟的个体性。与此同时,在不同的情景氛围与身心状态之下,个体对于艺术品的感受亦是有所差异的。因此,我们以赫尔曼·施密茨所说的“原初当下”的五个方面来概括艺术作品欣赏活动的特征,即此地、此时、此在、这个、我。[7]对于艺术作品的经验虽然具有鲜明的个体性与情境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种经验是漫无边际、捉摸不定的。正如上文所论,对于艺术作品的感知是观赏者个体经验与作品所负载经验的相互激荡,在此过程中,欣赏者的身心活动必然会为艺术作品所传达的种种信息所指引,从而呈现出较为一致的倾向性。因此,欣赏者对于艺术作品的感知既是独特的,又是可传达的,从而有利于共通感的形成与主体间性的建构。个体的生命经验总是有限的,而艺术史作为艺术作品的序列化,可谓人类经验有规律、有秩序的集聚。以艺术史为线索所进行的艺术经验活动,形成了个体经验与集体经验之间的持久张力,从而可实现个体经验的扩展与升华。
三、艺术史在艺术教育中的价值与定位
根据杜卫的观点,艺术教育可区分为专业艺术教育和通识艺术教育两种类型。前者以培养专门的艺术人才为目标,主要存在于专业艺术院校与院系;后者则以培养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为目的,遍布于广泛的教育活动之中,是面向全体学生的通识教育。[8]而无论是在专业艺术教育还是普通艺术教育领域,艺术史教学均是不可或缺的关键维度。首先就专业艺术教育而言,艺术技能的习得虽然在该领域占据重要位置,但学生审美素养和人文素养的提升却需要借助艺术史的学习来实现。上文已经提到,艺术史并非纯粹知性的知识习得,而是建立在对于具体艺术作品的欣赏的基础上。在一般的艺术欣赏活动中,学生所获得的审美经验多是个别的、零碎的,难以形成体系与系统,而以艺术史为线索所进行的欣赏活动则不然。如同上文所论,艺术史赋予艺术以历史叙事,既可谓艺术作品的序列化,亦可谓艺术经验的系统化。正是因此,学生通过艺术史的学习,可以系统化的方式对历史上的艺术作品进行欣赏,进而实现审美经验的体系性建构,有效促进审美素养的提升。不仅如此,由于艺术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即风格史,所以经由艺术史的学习,学生可获得对艺术形式语言的全面感知与系统把握,这不仅可以使学生的艺术素养得到提高,亦可使其创作活动更具自觉性,将自身的创作纳入艺术史的谱系中去,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自身独特艺术风格的探索。与此同时,在学习艺术史的过程中,学生可实现对经典艺术作品的理解与持续性共鸣,从经典艺术作品中汲取充足的养分,并通过与历史上伟大艺术家的对话来追随大师的脚步。这些要素对于艺术创作能力的提升无疑均是有利的。
此外亦如上文所论,人文主义与传统具有密切的关系。传统之中保存着文化的记忆,记录着人类的伟大与渺小、自由与限度,因此,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必然要诉诸传统,而艺术史正是一种面向传统的学科。由于艺术史的学习伴随着对艺术作品背景知识的了解,故而可让学生对历史语境有充分的认知。而更为关键的是,艺术史以感性的方式凝结了历史,表现并传达了难以言传的个体心理与集体精神。在以艺术史为序列对具体艺术作品进行感知时,学生触碰到了历史中鲜活的生命跃动,体会到了特定时代的心理活动与情感氛围。知性的理解与感性的感知相结合,可以使学生置身于历史的现场,获得丰富的、立体的有关传统的讯息,切身地感受历史的行进脉络,对人类文化与民族精神进行个性的、属己的体会,从而在整体上实现人文素养的提升。正如杜卫所论:“从人文学科的角度看艺术,艺术绝不仅仅是技艺以及关于技艺的知识,而是富含人文内涵的文化活动,而经典艺术就是民族文化、人类文化沉淀积累的优秀成果。学习艺术不仅要学习艺术知识和技能,更要深入体认民族文化、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从中汲取人文精神。”[9]
其次就通识艺术教育而言,技能的训练虽然是不可或缺的环节,但通识艺术教育不像专业艺术教育那般强调艺术技能的学习,但其目的并不在于技能自身的提升,而是为美育的总体目标而服务,即培养学生的审美素养和人文素养。艺术史正因其与历史的密切关联和体验性而承担了这一任务。卡尔·雅斯贝尔斯曾论及艺术史的人文性与教育性:“人文学科是有其价值的,因为它允诺了一种对人类历史实质的领悟,一种对传统的参与,一种对人类潜能之广阔性的认识。……从黄金时代的神话、雕像与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本身自有其教育意义。”[10]艺术史不仅使学生了解传统,同时也使之走出自身、参与传统。对于传统的参与主要是通过体验活动而获致的,如同上文所论,在此过程中,学生个体经验和艺术史所承载的经验相互交织,此种交织不仅扩展、丰富了学生的经验世界,同时也促进了共情能力的培养,而后者正是努斯鲍姆所理解的人文教育的重心。在《告别功利:人文教育忧思录》一书中,努斯鲍姆认为当今的教育普遍陷入了功利主义的泥潭,仅仅注重知识的传授与技能的训练,忽视了人文素养的培育。努斯鲍姆将想象力和同情心视为人文素养的核心要素,并将对于他者的共情性想象称为“叙述性的想象力”,她说道:“这种能力是指想象穿上不属于自己的鞋子时的感受的能力,是有智慧的读者阅读别人的故事的能力,是想象别人在其处境中可能产生的情感、希望和欲望的能力。”[11]106“叙述性的想象力”意味着情节、语境、情感等要素,相当于对于他者境遇与心境的具身化重现。在努斯鲍姆看来,这种“叙述性的想象力”虽然潜藏于人性之中,但唯有经过后天的专门培养才能发展壮大。“我们不会自动地认为他人具有广阔的内心、各种思想、各种心灵渴望和各种情感。将他人视为一个肉体——由此想到我们可以用它来为我们的目的服务(无论是善良目的还是邪恶目的),就再容易不过了。在肉体中看到灵魂,就是后天培养的成就,而支持这个成就的,是诗歌和艺术。”[11]114艺术之所以对于“叙述性的想象力”的培养不可或缺,关键即在于其提供了丰富的“情感资源和想象资源”。如上文所提到的,对于艺术作品的经验使个体走出自我生存的狭窄界域,不仅锻炼了自身的想象力,同时也体验了多种多样的情感世界与人生历程,从而为以情感和想象力为主要心理资源的共情活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持。也正如上文所论的那样,艺术史源于历史意识对艺术的注入,是艺术作品的历史化与序列化。与单个的、具体的艺术作品相比,艺术史所提供的经验更为系统,其对于经典艺术作品的广泛吸纳,不仅可以使欣赏者实现与伟大心灵的持续共鸣,亦可对心灵世界的深度与广度进行开拓,这无疑使“情感资源和想象资源”获得了更为充分的滋养,有效地促进了努斯鲍姆所理解的以共情能力为核心的人文素养的提高。
由以上论述可知,无论就何种类型的艺术教育而言,艺术史的教学都尤为重要,是培养学生审美素养和人文素养的核心环节。在专业艺术教育课程体系中,艺术史类课程与艺术理论类、艺术技能类课程相并列,是支撑专业艺术教育的主干课程,缺失了艺术史的专业艺术教育将会变得盲目。在通识艺术教育课程体系中,艺术史类课程与艺术实践、艺术欣赏类课程相融合,共同为新时代美育目标而服务。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中提出:“逐步完善‘艺术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艺术审美体验+艺术专项特长’的教学模式。在学生掌握必要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着力提升文化理解、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等核心素养,帮助学生形成艺术专项特长。”[12]2023年12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其中指出:“以美育浸润学生,全面提升学生文化理解、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等核心素养,丰富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学生身心更加愉悦,活力更加彰显,人格更加健全。”[13]在以上两个文件中,文化理解、审美感知均是学校美育工作的重点,而艺术史正是建构、提升文化理解和审美感知的关键途径。艺术史以其独特的人文性质发挥着重要的育人功能,缺失了艺术史的艺术教育是不完整的,亦不可能达成培根铸魂、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