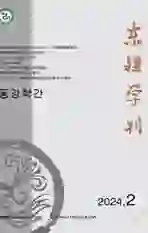朝鲜日据时期的“阿Q”
2024-04-20徐玉兰金春姬
徐玉兰 金春姬
[关键词]鲁迅;金史良;阿Q;《Q伯爵》;朝鲜
[中图分类号]I315.5.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24)02-094-07
[作者简介]1.徐玉兰,女,朝鲜族,延边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朝鲜韩国学、国际传播;2.金春姬,女,朝鲜族,延边大学亚非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朝鲜文学。(延吉 133002)
金史良(1914—1950)作为朝鲜日据时期拥有中国和日本双重文化背景的作家,他的文学作品虽用朝鲜语和日语创作而成,但内容却与中国密不可分。
1939年,金史良在日本大学毕业后,曾到北京游学,并与众多中国、朝鲜的有识之士相互交流。待返回日本后,金史良便正式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1940年,其创作的隐含着浓厚民族意识的《走向光明》获得了日本最高新人奖“芥川奖”的提名。自此,金史良开始活跃于日本文坛,并备受关注。
在日据时期的朝鲜知识分子中,有不少作家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鲁迅的文学影响。他们学习鲁迅的文学思想与创作精髓,并以此为标准,将鲁迅作品的题材、人物形象、创作技巧等运用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韩国学者朴宰雨曾指出,金史良的短篇小说《天马》和《Q伯爵》,便是受到了鲁迅的正面影响。[1](381)此后,有关金史良与鲁迅相关性的研究在韩国引起了关注。
目前,有关金史良和鲁迅文学相关性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国外代表性研究者主要有:金允植(2003)、任明信(2004)、郭铉庭(2005)、郑百秀(2007)、黄镐德(2008)、周若山(2014)、金在湧(2016)、高桥梓(2019)等。其中,任明信在《韩国近代精神史》中首次指出《Q伯爵》是日据时期知识分子版的《阿Q正傳》[2],但并未具体分析两部作品之间的关系。在国内,对金史良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成果有《简论金史良和〈驽马万里〉》(2010)、《金史良的抵抗文学研究》(2021)等,但均未对《Q伯爵》和《阿Q正传》之间的传播、接受关系进行考察。是以,本文拟将《阿Q正传》和《Q伯爵》中的“Q”作为重点,一方面,通过比较“阿Q”和“Q伯爵”两个人物形象的异同,分析金史良具体在哪些方面受到了鲁迅的影响,以及金史良通过《Q伯爵》想要表达何种思想;另一方面,通过考察金史良对《阿Q正传》的理解与接受,重塑近代中韩两国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共同抵抗,探究民族独立过程中启蒙思想和批判精神的构筑,继而挖掘两国抵抗文人思想交流的深层意义。
一、“Q伯爵”的诞生
随着中国沦为半殖民地,鲁迅选择弃医从文,试图以锋利的笔尖唤醒中国民众。他的作品在广泛流传的过程中,也引起了日本文人的关注。《改造》杂志社的创办者山本实彦与鲁迅交往颇深,曾多次向其约稿。自1920年开始,朝鲜和日本陆续出现了鲁迅作品。1930年1月4日到2月16日,《朝鲜日报》连载了梁白华翻译的《阿Q正传》。1932年,早在中国出版鲁迅全集之前,日本就已经出版了井上红梅翻译的《鲁迅全集(改造社)》[3]。鲁迅病逝后,山本实彦又出版了《大鲁迅全集》,发行量达十万册。在出版社的大力推广下,这部全集在日本盛行一时。
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现状,鲁迅通过其文学作品对此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批判,同时也正是其中所呈现的社会问题和文学思维,引起了朝鲜民众和知识分子的共鸣。
朝鲜知识分子金史良在观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朝鲜时,意识到了民族性的重要性,开始追求和表现殖民地民众的反帝精神。这种反帝国主义以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化为契机,是一种全球性的视野。同时,这种反帝国主义意识,又是其以中国为媒介培养、建立起来的。其中,鲁迅的思想对他的影响最大,他一直想成为“朝鲜的鲁迅”。台湾作家龙瑛宗在1937年杂志《文艺首都》8月号发表《东京乌鸦》后,曾与之后同在《文艺首都》开展文学活动的金史良进行私下交流。在二人相互交换的书信中,金史良曾提及鲁迅,其写道:
鲁迅是我喜欢的人。他很伟大。请贵兄作为台湾的鲁迅把自己积累起来。不,这样说也许是失礼了。只是希望贵兄像鲁迅一样做泛文学工作的意思。我也尽量写出好的作品。不急不躁,打算稳扎稳打下去。[4](210)
从与龙瑛宗交流的信中可以看出,金史良十分尊崇鲁迅,努力向鲁迅学习,并致力于成为像鲁迅一样的人。在朝鲜,包括金史良在内的众多作家早已接触到鲁迅文学,并效仿其作品。韩国的文学批评家金允植曾指出:“如果不是有着‘朝鲜鲁迅的自豪感,金史良就无法写出《草深》这部作品。”[5](150)可见,这种影响源自于鲁迅作品在韩国、日本文坛的盛行。
1936年鲁迅逝世,此时,金史良也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1940年以后,金史良的作品主要以日本读者为对象,旨在如实反映日据时期朝鲜的现实、朝鲜民众的生活,以及朝鲜知识分子的苦闷与彷徨,表现出民族的抵抗态度。金史良曾委婉地批评了“内鲜一体”政策,讽刺了当时朝鲜作家的行为,并通过细腻、多面的描写,呈现出日据时期朝鲜的现实面貌。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朝鲜,金史良的文学作品随着“延安派”的被肃清而消失,直到1987年才得以恢复。在朝鲜,他被评价为活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良心的民族主义者。而在韩国,他却一度被划定为亲日作家。
日据时期,日本提出并积极实施的“内鲜一体”的同化政策,使朝鲜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在极端压抑的环境中艰难求生。金史良坚持用朝鲜语、日语开展文学创作的行为犹如在刀刃上行走,也曾因此被逮捕。他用朝鲜语发表的《在拘留所见到的小伙子》(《1941年文章》)讲述的便是自己被逮捕的真实经历。后来,金史良又把《在拘留所见到的小伙子》翻译成日文,题目改为《Q伯爵》,并发表于作品集《故乡》(1942年《甲鸟书林》)中。《Q伯爵》是一部以伪满洲移民为背景,以两人见面的空间、拘留所和火车为舞台,表现时代痛苦的小说。在翻译过程中,金史良强烈希望可以更加真实地反映出被殖民时期朝鲜民众的生活状况和知识分子的苦恼与仿徨,因此,他借用了鲁迅《阿Q正传》中的“Q”代码,把原本作品中的主人公“王伯爵”改为了“Q伯爵”。两部作品最大的差别便在于标题的视角从第三人称变为第一人称。对此,韩国学者郑百秀认为,拘留所制度是国家权力对社会成员进行控制和监督的典型象征,是以对社会现有秩序的叛逆为前提成立的空间,被殖民者体验拘留所的动机,与对统治者压迫的抵抗或对统治者价值体系的破坏等存在有形或无形的关联,因此,把说话者“我”在拘留所中所看到的拘留所体验者作为作品的题目,其本身就是作者对当下意识形态的反映。[6](351)此外,两部作品的内在精神基本一致。
《Q伯爵》中的“Q伯爵”代表了生活在殖民地的朝鲜民众和知识分子,带来的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说服力和真实感。在日本战后最早开展现代中国研究的学者竹内实,曾就《Q伯爵》表示:“读过鲁迅作品的人,再读这部佳作,必然会联想到《阿Q正传》,并不禁会将两者进行比较。”[7](4)
金史良的文学关心的是朝鲜民众贫瘠的生活,以及面对这些现实却无能为力的朝鲜知识分子的苦恼。金史良通过被当作“虫子”而茫然死亡的阿Q的人生,想到了像虫子一样受到歧视和压迫的朝鲜民众,并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从写给龙瑛宗的书信来看,金史良的“Q伯爵”便是这种“阿Q”的典型。
二、朝鲜“阿Q”的悲哀
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期间,鲁迅的《阿Q正传》连载于《晨报副刊》。在这部作品中,鲁迅生动地再现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希望可以以此刻画并改变国民性,通过精神胜利法,阿Q脱离了社会现实,成为了漂泊在外的存在。他无力改变现实,最终无奈地沦为了时代的牺牲品。被视为“虫子”的阿Q,遭到了人们无情的嘲弄。鲁迅将底层人物“阿Q”的存在描绘成一种匿名的文化符号。他自己也曾表示,创作《阿Q正传》的意图是为了展现中国人寂寞的灵魂。也就是说,这种符号可以代表每一个中国人,因而具有一种集体的象征意义。鲁迅文学的真实性便在于,没有挂出任何虚伪的招牌,而是与构成现实的“死亡壁垒”实现碰撞。
“Q伯爵”是身处殖民地的高等浪子,并在脱离社会现实后漂泊在外。日据时期的朝鲜人“Q伯爵”,因为父亲是朝鲜亲日派特权阶层,可以随心所欲地频繁出入拘留所。再加上没有确切的证据,所以对于日本警察而言,“Q伯爵”可谓令人头疼的人物。颇具戏剧性的是主人公“Q伯爵”既滑稽又充满悲壮感。由于对殖民地现实充满绝望,这个折射了金史良自画像的人物“Q伯爵”,在作品的后半部分,同20世纪30年代以后剧增的经济难民在火车上一同自虐、彷徨。换言之,金史良在描写移居伪满洲的悲惨移民中,同时安插了“Q伯爵”这个人物。
匿名的“Q伯爵”只能悲伤和哀叹,并没有任何改变世界的力量。正如“阿Q”虫子般的存在受到人们的无视一样,“Q伯爵”也不会成为人们关心的焦点,因为群众眼中的“Q伯爵”已然是狂人的模样。两部作品的意图略有不同,金史良认为,这部作品与在帝国文坛一起活动的龙瑛宗有连带感。因而,他创造了匿名的“Q伯爵”,使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知识分子的认同感可以通过这部作品得到抒发与交流。
“Q伯爵”自称是“思想家”“无政府主义者”。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指的是拒绝日本国帝主义的天皇体制中心,反对殖民地体制的人。他说:
“无政府主义者是什么?”
“要說起无政府主义者的话……”
“所以说我是无政府主义者。一有案子就会被抓走。但是你知道什么是无政府主义者吗?应该不知道对吧。”[8](58)
身为记者的“我”第一次见到“Q伯爵”是在东京的某个拘留所。在拘留所内,“Q伯爵”虽为知事的儿子,但却表现出败坏贵公子身份的性格,无知、狂妄且爱吹牛。虽然是贵族,但“Q伯爵”却与《阿Q正传》中愚昧无知的“阿Q”别无两样。
韩国学者任明信指出,说话者遇见“Q伯爵”的场所是“东京某拘留所”,拘留所作为守护所谓“大日本帝国”安宁和秩序的场所,是一个重要的机构,被关在拘留所里的朝鲜知识分子的情况设定本身就具有挑衅性,而如果他是正常人,这本身就是对殖民地当局的直接挑战。出身朝鲜上流阶层却处于日本殖民统治的知识分子“Q伯爵”,不可能被刻画为普通人的理由就在于此。
韩国学者黄镐德表示:“金史良在翻译自己小说的过程中,能想到将‘王伯爵变为‘Q伯爵,很可能是认识到了‘王伯爵与《阿Q正传》中‘阿Q的相似性。”[9](399)
“Q伯爵”像孩子一样,“无知、狂热、爱吹牛”,但又表明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从监狱中获释后,他仍想尽一切办法重入监狱。他是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知识分子,但却不想在帝国的阴影下生活,“Q伯爵”的苦恼袒露无遗。但是,自称“无政府主义者”,并想尽办法入狱的“Q伯爵”的烦恼实则只是被表面化了而已。
我看到一位中年绅士披着黑色外套、白色的绸缎围巾,摇摇晃晃地走进列车。他呆呆地站在车门周围,环顾着火车里。眉头一皱,厚厚的嘴唇一耸一耸。脸红了。额头上横着三四道折皱,似乎很轻松。我想“原来我喝醉了”。a[8](61)
“Q伯爵”停留的空间是监狱和火车。“Q伯爵”是亲日派知事儿子的这一事实,对“Q伯爵”来说更是一个苦恼的因素,所以他能够安心停留的空间只有拘留所。也正因如此,这部作品的朝鲜语题目是《在拘留所遇到的小伙子》。目睹被统治在帝国意识形态下朝鲜民众的悲哀,他为同胞流泪哭喊。
“Q伯爵”的哭声越来越高,我不知所措。他好像再次发作一样抬起头,这次开始用朝鲜语叫喊。我认为这个疯狂的男人使我们偶尔也会陷入绝望的孤独之中。“我现在被自己报复了。脖子被勒住了。没有想要的东西,没有喜悦,没有期待。希望也是,啊!我只有坐上这趟移民列车时才能得到救赎。我也能和他们一起去。可以哭喊。”b[8](62—63)
Q伯爵身穿“黑色外套”“系着白色华丽的丝绸围巾”,一副华丽的上流阶级形象,与寒酸的移民者相去甚远。最终,他既无法融入移民,也无法完全回归自己,只能处于边缘,样子近乎狂人。记者听到“Q伯爵”的呐喊,合理化地认为,“我们也偶尔陷入绝望的孤独感中”,但“脖子紧缩”“没有喜悦和希望”的狂人Q伯爵其实是“因为有意识反而更痛苦的奴隶”。
韩国学者金哲指出:“奴隶的觉醒,是把奴隶带到‘无路可走人生最痛苦的恐惧,如果不能忍受这种恐惧,从梦中醒来的瞬间,他的道路就会消失,有的只是绝望。”[10](42)“Q伯爵”的悲哀正是奴隶觉醒的痛苦,他的疯狂行为可以看作是他为了逃避而找到的一个突破口。在《阿Q正传》中,就像被无数孤立的“阿Q”们的集体一样,中国没有真正的“个人主义”,也没有真正的“集体主义”。“Q伯爵”就是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在自身无能和羞愧感、罪恶意识中挣扎的朝鲜知识分子形象,是无论身处何处都被孤立的存在。
记者曾在火车上见到过几次“Q伯爵”。
我去年夏天曾进过江原道的山中。暴风雨持续了十天,有一天那条河边传来求助的声音……我感觉那不就是Q伯爵吗……今年春天,一个中等个子的男人对站成一列横队的团员进行了某种训示。我只见过那个男人的背影。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那是伯爵。a[8](65)
火车中记者看到的“Q伯爵”正是日据时期朝鲜的知识分子形象。金史良以匿名的存在者刻画了如果不是狂人就无法忍受的“Q伯爵”等朝鲜知识分子到处求助或向人们呼喊的样子。“Q伯爵”无法逃跑、无法离开,醉酒痛哭,在移民者中像幽灵一样彷徨,他的悲哀是被殖民的朝鲜知识分子生活的一部分。但是“Q伯爵”的悲哀在封闭的空间里,会因与同胞在一起的喜悦而得到治愈。就像在拘留所时心情舒畅一样,在移民火车上“Q伯爵”反而感到幸福。“Q伯爵”虽然是知事的儿子,但比起华丽却痛苦的贵族生活,他在监狱或火车上流下的则是喜悦的眼泪。与那样的“Q伯爵”相比, 记者已经走上了“更生”之路。
三、本同末异的“Q”
由上可见,“Q伯爵”的形象受到了鲁迅《阿Q正传》中阿Q的正面影响。拥有亲日派父亲的、身穿华丽衣服痛哭的知识分子——多余人“Q伯爵”的呐喊贯穿了整个作品。另外,观察“Q伯爵”和记者的重生,也是日据末期压迫文学家重生意识形态的呈现。
在《阿Q正传》中,阿Q在封建统治的压迫下,过着无家可归的贫穷生活。但阿Q不仅没有意识到封建意识形态的弊端,反而使用精神胜利法,意图将现实中经历的失败全部转化为胜利,即使经历艰难的现实,也不会因此感到痛苦。通过精神胜利法,每天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阿Q”的形象,是充满讽刺性的。《阿Q正传》表达的主题严肃而沉重,而阿Q这个人物却自始至终充满戏剧性。讽刺,在作品中不仅起到了凸显阿Q典型性的作用,同时还衬托了作品的艺术性。因为他的行动所体现的封建意识是被肯定的,而近代思想却是被否定的。作品通过讽刺阿Q这个滑稽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一种滑稽美。反观《Q伯爵》,初期的“Q伯爵”将自己歪曲成无政府主义者,其在日本看守者面前卑躬屈膝的行为,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一样,给人以一种讽刺感。然而,随着故事的进一步发展,“Q伯爵”的讽刺性逐步转向了悲剧性。“Q伯爵”因患脚气而忍不住呻吟的模样令人同情,而为了分担同胞的痛苦,乘坐满员列车时痛哭的样子,又令人无比悲伤。他在开往伪满洲的列车上表露出疯狂,大喊“这家伙别动”,让被殖民者对帝国主义的压抑愤怒不已。
“Q伯爵”这个悲剧人物,在沦为殖民地的朝鲜现实中,在对“内鲜一体”意识形态的抵抗和屈从中,无从选择,只能痛苦地生活。即作者通过描写“Q伯爵”这一无穷悲伤和愤怒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一种悲壮美。如果说“阿Q”是流露出滑稽美的讽刺性人物,那么“Q伯爵”则是流露出悲壮美的悲劇性人物。究其根本,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第一,中国半殖民地与朝鲜殖民地的差异。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后,朝鲜人民因被殖民权力强加于“内鲜一体”意识形态而几乎丧失自由,民族性遭到完全压制。由此,朝鲜半岛的主要矛盾集中体现于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民族内部矛盾相对弱化,是否接受“内鲜一体”的意识形态几乎变得毫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讽刺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讽刺很有可能导致再次遭受殖民者的侮辱。因此,金史良以朝鲜知识分子的存在状态为依据刻画了“Q伯爵”这个典型形象。
第二,读者的差异。作者希望通过《Q伯爵》揭露朝鲜民众的弱点,首先需要以朝鲜人为对象。但是在使用日语的生活现实中,这种揭露是面向日本人的,因此,作品在感情上会有自我羞辱的取向。与此同时,金史良用日语写成的另一个“阿Q”,与《阿Q正传》的功能也大不相同,因为这给帝国殖民者展现的是殖民者的野蛮形象。因此,金史良无法自由讽刺“Q伯爵”,最终“Q伯爵”只能成为悲剧性形象。
第三,作家与人物关系的差异。对于鲁迅来说,“阿Q”更接近于启蒙的对象,而对于金史良来说,“Q伯爵”则类似于“关注”和同情的“朋友”。
对于自己写小说的目的,鲁迅曾这样写道: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1]
如此看来,鲁迅小说中的人物“阿Q”是在病态社会中得病的“患者”,是鲁迅想要改造的对象。尖锐地批评和讽刺才能引起注意,所以当时《阿Q正传》的很多读者,都产生了一种此文像是在骂自己的错觉。而对于金史良来说,“Q伯爵”不像“阿Q”那样是作家需要改造的对象,反而更接近于他患难与共的同伴,因而,呈现人物以及人物所代表的民族群体的悲哀才是其最终落脚点。
总之,“阿Q”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众的普遍自画像,是依靠精神胜利法回避现实的讽刺性人物。相反,“Q伯爵”是生活在日据末期闭塞现实中的朝鲜知识分子的自画像,是只能继续在卑微无力的自愧感和罪恶意识中挣扎的悲剧性人物。但无论是讽刺性人物,还是悲剧式人物,“阿Q”和“Q伯爵”都是在时代造就的病态社会下,痛苦祈祷自我救赎的同类人。因此,鲁迅塑造的“阿Q”和金史良刻画的“Q伯爵”,皆成为了超越历史、呈现出人类在矛盾中痛苦挣扎的一面镜子。金史良想用“Q伯爵”塑造出像鲁迅的“阿Q”一样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但又不能完全塑造成朝鲜知识分子的缩影,这也是金史良《Q伯爵》的局限性。
四、结 语
鲁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背景下,希望用革命改造国人愚昧无知的精神和理念,对日据时期朝鲜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出身来历不明的下层雇佣农“阿Q”是一个文化代码,映射了跨越空间却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朝鲜日据时期知识分子的处境。而也正是困境中文人的惺惺相惜,造就了朝鲜本土的“阿Q”——“Q伯爵”。
本文分析了鲁迅和金史良作品的相关性。其中,可以看出《在拘留所见到的小伙子》翻译成《Q伯爵》,其主人公成为了朝鲜的“阿Q”。父亲是亲日派贵族的“Q伯爵”与身份不明的底层人“阿Q”具有同格性,都是苦闷不堪的多余人。另外,在日本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经历“更生”过程的记者“我”和狂人“Q伯爵”在本质上都展现了知识分子在矛盾中痛苦挣扎的形象,可谓殊途同归。可见,在《阿Q正传》的影响下,金史良设定的人物“Q伯爵”,由个体及群体,最终构建了朝鲜被日本殖民的末期无数个“Q”群像。
[责任编辑 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