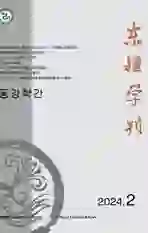20世纪80年代朝鲜族小说的爱情叙事研究
2024-04-20李光一林圆
李光一 林圆
[关键词]朝鲜族小说;爱情叙事;治愈;觉醒;虚假;精神分析
[中图分类号]I20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24)02-081-07
[作者简介]1.李光一,朝鲜族,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韩国现代文学、中国朝鲜族文学;2.林圆,女,朝鲜族,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韩国现代文学、中国朝鲜族文学。(延吉 133002)
爱情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展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文学作品作为人类意识形态的表达媒介,其爱情叙事也在不断地发展和推进。与时俱进的爱情叙事更容易引起文学界的争鸣,并在观点分歧与激烈探讨中持续激起读者的共鸣。一些超前的爱情观会引发争论,而合乎大众期盼的爱情也会引发不同的解读。所以,爱情主题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更是文学作品中永恒的题材。
“爱情”亦是20世纪80年代朝鲜族文学史的关键词之一,是人性与情感的真实流露,是挖掘民族文化与道德风貌的文学表象。在“文革”时期,爱情题材在文学中是不可触及的禁忌,时代的特殊性使文学处于无情无爱的状态。在这种爱情空白时期,人性、人情都被视作是资产階级的产物,只能避而不谈,但爱情是人性的本能,不断地压抑、回避会导致青年男女的婚恋观畸形和扭曲,长此以往会酿成悲剧。
20世纪80年代是个大变革的年代,社会经济与文化思潮的巨变,使文学突破禁区,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新局面。首先有一批思想先锋如贾平凹、张抗抗、刘心武、陆文夫等作家,重新打开了爱情叙事的大门,爱情叙事得以重生,压抑的情感得以抒发。爱情叙事的回归也意味着婚恋观的重新构建,在构建过程中又不断地受到社会、文化、经济、时代的影响,呈现出多样的婚恋观。更重要的是,爱情叙事的回归引发了人们对压抑已久的情感欲望的凝视,对自我的发现和回归,进而为作家提供了书写的窗口。受主流文学的影响,朝鲜族作家开始尝试爱情叙事,朝鲜族作家的文学作品中爱情叙事也逐步增加,代表作家有金学铁、郑世峰、李元吉、朴善锡、林元春、崔红一、高信一、李惠善等。20世纪80年代朝鲜族的爱情叙事随着文化环境的变迁可分为批判与治愈、世俗与觉醒、放纵与找寻三个阶段。本文以精神分析理论为视角并从每个阶段爱情叙事的差异性入手,分析其差异性的原因,进而探索20世纪80年代朝鲜族文学中爱情叙事变化的构建意义及对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作用。
一、批判与治愈:历史创伤的情感转写
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的解放和文学的恢复,社会上迅速涌起对爱情文学的呼吁。在这种环境下,朝鲜族小说开始直接或间接地涉及爱情叙事,迎来创作热潮。借助主题的多样性以及艺术性的不断提高,人们试图找回在动乱时期丢失的正常的爱情和婚恋观。80年代前期对爱情问题的强烈关注,使爱情叙事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文学思潮的出现,通常将爱情叙事作为批判社会问题的出口,作家们想要表达的并非爱情本身,而是造成爱情苦难的社会问题以及历史原因,并通过自我感情的抒发从而得到内心的治愈。荣格的治疗思想将心理分析划分为四个阶段——倾诉、阐释、辅导、转化,虽然患者的症状在倾诉阶段有所缓解,但关键的问题是要帮助患者发现潜意识的意义,而治愈的首要任务是要将伤痕症状暴露出来。
美国精神创伤治疗专家朱迪斯 · 赫尔曼在《创伤与复原》一书中直面伤痕症状,将创伤经历视为创伤复原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又可分为“回顾与哀悼”两个层面。第一层面为回顾,就是直面痛苦记忆,释放出内心的恐惧,从而缓解精神伤害。第二个层面为哀悼,赫尔曼形容,“陷入哀悼的感觉好像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泪水的投降。”[1](253)哀悼必然充斥着悲伤,但哀悼的意义在于完全揭露伤痕,只有彻底直面悲痛体验,受创者才会真正从这段创伤中解脱出来。
然而,20世纪80年代朝鲜族小说中的爱情叙事,有一部分并不是纯粹的想要描写爱情,而是将爱情作为一种宣泄工具。这些作品想要传递的不是正确的婚恋观与浪漫的爱情故事,而是承载着一代人的伤痕与创伤。这种爱情叙事肩负着使命感,勇敢批判着社会现实,控诉着时代造成的苦难。虽然相关作品没有正面积极地去探索爱情本来的意义,但是通过症状的暴露从而得到心灵的治愈,这亦是接受正确婚恋观的前奏。
首先,通过个人形象去批判因冤假错案而造成的爱情悲剧。郑世峰的《压在心底的话》(《延边文艺》,1980年第4期)以李锦姬给自己前夫写的一封信的形式,讲述了其因社会问题不得不被丈夫抛弃的故事。尹林浩的《斗士的悲痛》(《延边文艺》,1980年第6期)不仅描写了“文革”时期的惨淡命运,而且挖掘人性,探索纯粹的爱情。男主人公昌勒曾经为了心爱的英玉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日联军传递消息,但却在“文革”时期含冤而死。柳元武的《妻子》(《道拉吉》,1984年第10期)中张仁燮是一个前途光明的大学生,在特殊年代因为无意中一句抱怨的话而入狱。妻子玉兰为了撇清关系急忙递来了离婚协议书。好在一直暗恋着张仁燮的金善不离不弃等着他出狱,几经波折后走到一起。金阳今的《坡道》(《阿里郎》,1986年第25期)中男女主人公因特殊年代社会成分问题没能结成连理,从而在心中留下了永远无法磨灭的伤痕。这些作品揭露了因社会历史原因而饱受摧残的爱情和婚姻生活,以个人心灵创伤的暴露批判了社会的极端和人性的脆弱。
其次,集体创伤的情感转写。在社会成分决定社会身份的年代,人们随时都会面临社会身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社会都直接或间接地经历着极端亢奋和莫名其妙的身份变动。这不仅给社会造成伤害,还在人们的心理上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如李元吉的《百姓的心声》(《延边文艺》,1981年第10期)讲述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因“左”倾错误引发粮食匮乏,导致整个村庄陷入饥荒状态的故事。在这种情况下,妻子的盗窃行为才使丈夫幡然悔悟自己的盲信与盲从造成的严重后果。南株吉的《万里的梦》(《阿里郎》,1986年第24期)和李元吉的《皮毛癞的士兵们》(《阿里郎》,1987年第30期)等作品讲述了特殊年代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大学生下乡开垦北大荒的故事,在此期间所有的个人感情都没有革命目标重要,家庭成分决定了个人地位。爱情是为革命而存在的,是可以牺牲的。青年人的私人情感是不被认同的,所有青年男女只能谈革命工作和阶级情谊,萌生的男女之情只能化作遗憾,永远地埋藏于心中。在这种集体身份归属迷失的情况下,社会前景一片光明的大学生来到偏远山村历尽磨难,怀才不遇。在这种集体自我意识迷失的状态下,人们对巨大的身份变动也变得麻木不仁。甚至一些人随时会被扣上“反革命”的罪名,不仅会被剥夺爱的资格,就连拥有配偶的资格都没有,埋藏心底的爱情都会是一种卑微的奢望。
20世纪80年代前期朝鲜族小说受到主流文学的影响,其中心任务正是暴露“文革”灾难,批判反动分子的罪恶,恢复人民正常生活。作为表现个体生命形态和精神追求的工具,这一时期的文学运用曾被视为禁忌的爱情叙事去揭露特殊时期的创伤,从而达到治愈心灵的目的。文学治疗其实是把意识衔接到文学作品中,又通过文学叙事激活潜意识的过程,人的高级需求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明确感受到的,思想敏锐的作家以小说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使自己或者他人的需求在叙事中得以释放,从而实现疗愈。文学对人具有疗愈功能,是因其可以满足人的高级需要。
叶舒宪认为“精神分析将古巫医、后代哲学家和文学家所承担的‘语言治疗任务接管下来,并且使之发展成为专业化极强的精神医学系统,让克尔凯戈尔、尼采等人面对的文化病理问题还原为诊所中的个体无意识诊疗病例,从患者的梦境、幻觉、呓语中去捕捉富有意蕴的象征,籍此发掘个人童年的心理挫折,找出治病根源,再用催眠、暗示、疏导、宣泄诸方法加以治疗”。[2](4)然而,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朝鲜族小说家不仅通过爱情叙事进行自我疗愈,还对有着共同创伤的整个民族进行疗愈。
在精神分析疗法中有疏導法与宣泻法,这两种方法是通过诉说的方式将心里的苦闷痛快淋漓地倾诉出来,从而防止产生心理疾病。作家们充当着叙述者的角色,将自己发现的问题外化,通过小说表达出来,运用叙事进行自我疗愈,同时也是与自我的一种对话。然而,阅读也是文学治疗的手段之一,读者通过小说作品去倾听作者的叙事,再找到心灵相通之处进行再叙事,从而呈现出自己内心的故事,得到间接性的治愈。这是“被治疗者主动参与文学创作或文学欣赏等审美实践活动,缓解或消除自身心理压力或偏差,解除心理困扰,从而有效地恢复内在自身生态系统平衡,促进身心健康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3](79)读者通过小说欣赏,接受作品中的人物,在该人物的基础上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也是换个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释放内心苦闷,达到治疗效果。在压抑的情感创伤得到治疗后,作家们开始找寻埋藏已久的本能天性,从更广、更深的层面去探究爱情叙事的多样性。
二、世俗与觉醒:道德与欲望的边界试探
瓦西列夫在《情爱论》里说:“爱情是一种复杂的、多方面的、内容丰富的现象。爱情的根源在本能,在性欲,这种本能的欲望不仅把男女的肉体,而且把男女的心理推向一种特殊的、亲昵的、深刻的相互结合。但是爱情又不仅仅是一种本能,不仅仅是柏拉图式的神奇剧、淫欲、直观和精神的涅磐。爱情把人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联结在一起,它是生物关系和社会关系、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的综合体,是物质和意识多面的、深刻的、有生命力的辩证体。”[4](42)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前期朝鲜族小说专注于创伤的暴露与疗愈的话,那么80年代中期,朝鲜族小说的爱情叙事重点则转移到了爱情本身,即从伦理道德的矛盾冲突中阐释爱情与婚姻。随着主体意识的觉醒,长期受到社会指责与道德压迫的个人欲望开始苏醒,传统伦理思想浸染下的爱情缺失的家庭得以直面矛盾,结束相互折磨的婚姻关系。但随之而来的是有部分人会利用这份自由去挑战原有的家庭结构和伦理道德。针对这一矛盾,朝鲜族作家针对道德与欲望的矛盾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金学铁的《被践踏的贞操》(《天池》,1985年第9期)中身为大学生的赵凤顺被流氓玷污以后,昔日的恋人李仁植无法接受周边同学的嘲笑,更不能接受将与自己结婚的人是一个失去贞洁的女人,所以逐渐与赵凤顺渐行渐远。但是,同为大学生的文大成则更注重两人之间的感情,并堂堂正正地与凤顺在一起。崔红一的《她和他,B县所在地》(《天池》,1987年第2期)中的春玉是一个大胆追寻爱情的女人,但这条路比较坎坷,在经历3次失败的感情后春玉与正植结婚,却因曾经做过第三者而被抛弃。春玉从不畏惧他人的指责与唾弃,还以书信的方式去控诉男性社会对贞洁的执念。尹林浩的《山村的枫叶》(《道拉吉》,1986年第3期)讲述的是英松与妻子已经没有了爱情羁绊,并开始了婚外恋。这篇小说反问了在婚姻关系中无限的争吵与折磨是不是还需要维系这段关系,探索了什么是灵魂自由等问题。金京莲的《心中的波浪》(《天池》,1986年第3期)描写英爱为了报恩,以身相许嫁给了南秀,但婚后婆家只是将她视作传宗接代的工具,这让英爱尝尽了婚姻带来的苦楚,内心渐渐倾向于与自己灵魂契合的第三者。尹哲柱《啊,路,她的路在哪里》(《松花江》,1985年第4~5期)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勇敢找寻爱情的新时代女性,即使离婚让自己丢了工作,常常被人指指点点,她也不想因为外在条件而委屈自己,离婚后的她大胆追寻着自己的爱情。
上述小说抨击了朝鲜族根深蒂固的封建伦理思想,并对社会政策与传统思想给朝鲜族带来的巨大影响进行了剖析与研究。作家们大胆涉及了“离婚”“出轨”“第三者”等主题,对于无条件反对结束婚姻关系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并指出了强行维系没有爱的婚姻和家庭才是不道德的行为,与其互相折磨不如各自安好。离婚后的单身男女不必再看人眼色、如过街老鼠般人人喊打,出轨也不再是男人的专属权利,第三者也未必就是品行不端之人,人们的思维方式从刻板、固化转向开放、包容。在人们的生活观念还停留在怕被周边评头论足的保守年代,习惯于随波逐流的盲从年代,这些小说的横空出世给朝鲜族文坛乃至朝鲜族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给处在思想沉滞期的人们带来了自由的可能性,使沉睡的自我意识开始苏醒。
朝鲜族传统的家庭观、爱情观、伦理道德观随着社会的变化开始转化。这时期的朝鲜族作家开始充当批判、倡导、探索的先驱者角色。但人性贪婪,人类在尝到自由的快感后开始逐渐迷失自我。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结构是由“本我”“自我”“超我”构成的。“本我”是无意识(潜意识),也是“里比多”的本能冲动。“自我”是意识或自我意识,它是一切感觉、直觉和理性思维的机构或主体,是自觉活动的激发者。自我与外界直接联系,它对处于本我的欲望冲动与超我的压制欲望冲动这两种矛盾力量起到调节作用。“超我”指的是后天的道德、宗教等社会意识所构成的一种是非或就是“道德化了的自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良心”之类的东西。它处于本我与自我之间,对本我的欲望冲动起到抵制和压抑作用,它阻挠本我的欲望冲动任意闯入自我的领域。[5](90)如果说尘封已久的爱情话语重见天日,以多种形式充分地激起自我意识的找寻,那么当压抑太久的内心突然得到自由时,那个本能“里比多”将这种压抑的欲望以小说的方式释放出来呈现在大众面前时,爱情叙事就会无节制地泛爱化。
许莲顺的《很多男人的她》(《长白山》,1989年第3期)中的玉莲不断与多个男子有着亲密关系,自己却美其名曰找寻真爱,其实却过着荒淫无度的放荡生活。黄衡久的《爱情条件》(《天池》,1986年第2期)叙写了丈夫家暴导致妻子不孕,后利用妻子的贤良涉足婚外恋,还丢弃糟糠之妻与其离婚,想找已经怀孕的婚外恋对象结婚时,反遭背叛。方龙珠《酒家老板娘》(《阿里郎》第29期,1987年)里的崔锡弼利用自己的干部职权威逼芬女与自己发生关系,兽性未能得逞后反诬陷芬女诱惑自己。韩正花的《回旋的裙摆》(《道拉吉》,1986年第3期)中的景熙与美善是要好的朋友,景熙的丈夫事业心很重,难免会对家庭和妻子疏忽一些,而美善的老公温柔体贴,夫妻关系如胶似漆。与朋友相比,景熙总觉得自己生活不够美满,所以开始通过婚外恋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李惠善的《下雨天》(《天池》,1984年第5期)讲述的则是妻子景顺发现丈夫钟哲与景顺的弟子淑姬的恋情。令她震惊又失望的是,丈夫居然会跟自己的学生有染。以上小说叙述了“好丈夫”“好妻子”未能得到满足的本我转而通过第三者去寻求。
在20世纪80年代,自我意识的不断扩展,势必会与社会道德观念产生矛盾。弗洛伊德认为,爱情文学可以给人们的压抑欲望带来一种替代性满足,“人们可能做得更多,可能试图再创造现实世界,建立起一个世界来取代原来的世界。在那里,现实世界中最不堪忍受的东西消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人们所希望的东西。”[6](21)回观80年代中期的社会背景,人们的自我意识确实在不断觉醒,但社会道德观念还是会很大程度地束缚“自我”。在压抑的欲望没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人们通过虚拟的小说世界刻画出了想做又不可为之的爱情叙事,不断地试探着道德的底线,这样肆意的刻画与虚构将爱情叙事推向了对“性”的探索。
20世纪80年代中期朝鲜族作家多从政治、历史、伦理、道德、文明的角度来思考和叙写爱情问题;以诗意的语句和委婉的方式去表达爱情的美与丑;以文化批判的态度给予自我意识以肯定;以伦理道德的视角去否定传统婚恋关系。然而到了80年代后期,作家们笔下的爱情叙事从婉约之美、人性之美、生命之美转向目的性、丑恶性、非人性。那种无处不在的性也是对爱情本身的一种变向否定,表现出了现代人的性观念,性成为了一种生存方式和交易筹码,这也间接地反映了现代人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社会经济文化变化时产生的爱情观和价值观的困惑。由此可以看出80年代后期的爱情叙事更加接近精神分析学的病理学特征。
三、放纵与找寻:虚假与交易中的爱情话语危机
20世纪80年代后期伴随着现代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的转型与思想上的解放推动了文学的发展空间。深受市场经济和商业化影响的朝鲜族作家的价值观和情爱观再一次受到了挑战。一方面文学永恒的爱情话题重获自由,并且开始以新的观念与方式进行阐释和探讨。另一方面在“个性化”的时代,文学不仅探讨情爱与道德之间的矛盾关系,还试图挖掘新时期人们更为复杂的深层欲望。在逐渐商业化的社会,爱情叙事呈现多样化趋势,不仅兼容着80年代前期控诉创伤的爱情叙事,还有80年代中期探讨欲望与道德之间矛盾关系的爱情叙事。具有80年代后期特点的爱情叙事类型则是虚假型和交易型的爱情叙事。
首先,在虚假型爱情叙事方面,如姜孝根《诱惑的界限》(《阿里郎》,1989年第35期)中孝植为了从农村进入城市宁愿丢弃女友,也要为了金钱与社会地位选择跟毫无感情的局长千金结婚,扮演一个“好丈夫”的角色。高信一《人间百态》(《长白山》,1985年第6期)中的德希的悲惨人生也是从一场没有爱的虚假婚姻开始的。为了能够拿到城市户口德希不惜与不喜欢的男人结婚,此后便是无尽蹂躏的开始。方龙珠《白发幽灵》(《天池》,1987年第5期)中宥敬因男方税务局长的身份与权力,嫁给了比自己大12岁的50岁中年男人,后发现丈夫另寻新欢,于是决心收集证据进行报复。韩正花《被窝里的眼泪》(《道拉吉》,1986年第2期)中的恩香为了脱离贫困,不顾父母的反对嫁给了瘸腿的善哲,在见识到繁华的都市以后觉得善哲配不上自己,所以开始出轨。这一时期崇尚金钱万能主义的消费性社会思潮开始蔓延,所引发的快乐原则与追逐欲望的本能开始膨胀,再加上经济社会环境带来的宽松的、多向度的思想环境,使人们的生存方式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在这种生存环境下对情感的反映也是多样的,因此进一步激活了小说的爱情叙事,多元化的爱情叙事集中体现在人性认知和人性行为的揭示上。在80年代后期的朝鲜族小说作品中,这类小说开始崭露头角,虽然作品量不是很多,探索人性深度方面也有些许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在人的欲望探究方面,以独特的角度与深度为90年代的爱情叙事指明了方向。
其次,在交易型爱情叙事方面,如李如天《被挡住的墙》(《阿里郎》第30期,1987年)中的妻子为了救丈夫,不惜用自己的身体做交易,与隔壁家境优渥的邻居昌秀发生关系,最终得到了丈夫的谅解。在姜孝根的《蠹物,浮萍草,三棋枰》(《阿里郎》第32期,1988年)中,玉蘭游走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职场中,为前程不惜与他人进行不正当交易。80年代后期的爱情叙事已经跳出了单一的道德训诫,也不再是就事论事的单一呈现,它表现出了作家对人性的理解与探索。作家们通过爱情叙事把人性的复杂展现出来,直面人类被物质异化后的情感之痛,叩问经济时代中肉体与灵魂该如何安放的问题。爱与欲望之间的博弈离不开消费文化,对经济利益的过分执着,最终导致道德与伦理观念不断被削弱。弗洛伊德说过,“在一般情况下,凡健康正常的爱情,需依靠两种感情的结合,一是温柔而执着的情,另一种是肉感的欲”。[7](217)然而在80年代后期的小说中,性与爱常常是分离的。在现代价值体系尚未健全的时期,原有的价值观遭到破坏,对欲望的追逐有压倒道德情感的趋势,这使部分作家开始警觉,反思爱情的缺失与变异。道德与人性的冲突、情爱与利益的纠缠直至现在也使人困惑不已。爱情与性不应该脱离自然人性,但又无法完全无视社会性而存在。所以爱情叙事呈现了现代人的隐痛,揭示了现代人的伦理困惑与精神缺失。
然而令人欣喜的是朝鲜族作家们没有丢弃对爱情的找寻,在这些逐渐泛爱化的爱情叙事中,仍然对纯粹的爱情抱有期盼。如车镇灿的《生活的变奏曲》(《长白山》,1987年第2期)中的七星是个身体残缺的残疾人,而英姬心地善良处处帮扶着七星,两人之间的感情也迅速升温,但是在一起没多久英姬却因病去世。该小说不乏一些对两性关系的性描写,但作家将七星与英姬的爱情故事以纯洁凄美的方式呈现出来,他们的爱无关世俗身份与金钱利益,始终遵循着生命的自由意志,因爱而爱,始终纯粹。在消费文化影响下爱与欲望激烈博弈的场景中,这类作品展现的是对美好爱情的期待,让人们看到了爱情与人性最美好的样子。
毋庸置疑,这一时期的爱情叙事混乱的作品数量很多,一些作家放逐欲望,贬低爱情,两性关系充满着猜忌和背叛,夫妻之间同床异梦。这是小说中的爱情叙事的“感情危机”,也是整体作家创作倾向的“感情危机”。文学不仅要以艺术的方式将人民大众的命运遭际与读者产生共鸣,还要提供善和情。爱情叙事“真实细腻地呈现了人类可能具有的性与爱以及与之相关的诸多心理、社会元素纠葛冲突的状态,进而思考人类自然层面和精神层面可能具有的关联方式和跃迁潜能,因此爱情叙事在塑造人性、创造人们对可能生活的想象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8](27)爱情叙事的生命力不在于把故事情节写得吸引眼球,更不在于赋予主人公动人的外貌和殷实的家境等外在价值,而在于写出人最真切的感情和人的精神。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界掀起了第二次“弗洛伊德热”,精神分析学理论中的泛性观对80年代后期的文学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精神分析理论的病理学特征与朝鲜族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80年代后期小说中,即使书写错综复杂放纵情欲的爱情叙事,也多以揭示人物的沦丧感和罪恶感为主,一直遵循着善恶到头终有报的主题思想。这一时期一些作家的小说充斥着对本能欲望病态化的追求与对性的罪恶和肮脏的描述。文本中失去了很多对性与爱、灵与肉的痛苦纠缠,更多的是已经失去自身价值的、被沦为生理需求乃至交易方式的性书写。但也有一些作家与描写忽略情感、放纵情欲的作家產生鲜明对比,他们高举情感的旗帜,在欲望与情欲的废墟中重新呼唤纯粹、清澈的爱情,以恢复爱情本来神圣、崇高的面貌。
四、结语
弗洛伊德说:“造成‘恋爱的条件是什么? 或者说,男人和女人根据什么选择自己的爱恋对象? 当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合乎自己理想的对象时,他们又是如何来满足自己的要求的,这一向是一个由诗人和想象力丰富的作家们描述和回答的问题。”[7](203)朝鲜族作家就这一爱情难题给出了深度的解答。综上所述,对于朝鲜族小说作家们对爱情叙事的阐释,笔者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首先,朝鲜族小说在进入新时期以来,关于爱情的叙事大多是在控诉因历史原因带来的创伤,从而释放压抑在内心对爱情的渴望。其次,20世纪80年代中期小说中的爱情叙事折射出作家们为人们找寻自我而感到庆幸,同时又对过分的放大自我而感到担忧。最后,从80年代后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在金钱、利益、欲望的驱使下,爱情和身体都是可以用来交易的商品,作家们对已经无情化的爱情叙事感到悲哀,深入探究人性,并对美好的情感与健康的婚恋观构建抱有些许期许。
社会的发展、时代的更替、文化的进步都会影响爱情观念。精神分析学对20世纪80年代朝鲜族小说的爱情叙事有着特殊的意义。第一,它使爱情叙事实现了社会向自我、向内心世界的转化,由一种群体“超我”的表达进入到个体“自我”的宣泄。第二,使80年代小说正视人的本能欲望,将属于人的东西还给了人,深化了人本主义,扬弃了僵硬化的创作束缚,打破了以理性化、单一化的传统观念解释人的自我意识。第三,泛性观则是拓宽了爱情叙事的表现形式,更深度地解释了人性心理领域,使朝鲜族小说中爱情叙事的深度不断加深。
最后,文学中的爱情叙事包含着文学立足与人本身的平民性,和注重人内心深处自身的文学性的特点,是探究文学现象过程中的主要切入口。但在朝鲜族小说研究中,特别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爱情叙事研究往往处于文学史的边缘,也常被质疑爱情叙事是非主流的,是对文学道德理想的消减。但纵观朝鲜族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不乏对爱情进行描写的名著。文学本是对人生人性的表达,本质是为了推进人类精神文明,然而爱情叙事不仅是一种题材的选择,也是反映历史和人性的一面镜子,需要更多的作家进行更深更广的探究,也需要更多的学者就这一文学现象进行不断的研究与更新。
[责任编辑 朴莲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