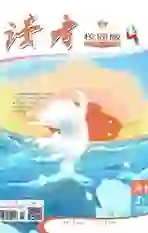旋转木马和宝玉挨打
2024-04-12岑嵘

假如你站在一架旋转木马前,看着上面游戏的孩子,你能发现些什么?你或许会说,这些孩子玩得很愉快,他们都很喜欢这个游戏。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喜欢观察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即便是观察一群旋转木马上的孩子,他也能够看到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戈夫曼说,儿童对自己的年龄非常敏感,他们会骄傲地告诉别人自己的年龄。儿童了解什么样的规范适用于多大的年龄,他们也清楚地知道大龄儿童的行为应当有别于低龄儿童。
因此,在乘坐旋转木马时,不同年龄的儿童,反应是不一样的。四岁以下的儿童享受着在父母的陪伴下骑乘,四五岁大的儿童则可以独自骑乘——他们对自己的成就深感自豪,不断地向等候在一旁的父母挥手示意。更大一点的儿童骑旋转木马时,他们的内心很兴奋,但极力表现得若无其事。
戈夫曼曾经观察了一个13岁的男孩,他先是不安分地骑在一匹马上,随后换到了一头鸵鸟的背上,接着又开始变换坐骑,在游戏音乐停止之前,他就下来了。为什么大龄儿童会有上述行为呢?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旋转木马。大龄儿童和低龄儿童同样着迷于这种旋转的游戏和音乐,但其内心充满矛盾。他们既喜欢这项活动,又认为这只是给小朋友玩耍的,而自己已经长大了。
好的作家一定和戈夫曼一样观察细致。同一件事情因为身份的差别,其表现也会千差万别。
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例子。《红楼梦》第三十三回中,贾政因为宝玉“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淫辱母婢”,所以结结实实打了他一顿。这时每个人的反应差别是很大的。
宝玉的母亲作为贾政的夫人,她只能抱住板子,肯定丈夫的做法,并委婉地求情:“宝玉虽然该打,老爷也要自重。况且炎天暑日的,老太太身上也不大好,打死宝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时不自在了,岂不事大!”
贾母作为贾府最高地位的人,只有她可以教训贾政。贾母厉声道:“你原来是和我说话!我倒有话吩咐,只是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却叫我和谁说去……你说教训儿子是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怎么教训你来……你的儿子,我也不该管你打不打。我猜着你也厌烦我们娘儿们。不如我们赶早儿离了你,大家干净!”
袭人的身份是丫鬟,哭也轮不到她,她只有等贾母、王夫人等主子离开后,这才走到宝玉身边坐下,含泪问他:“怎么就打到这步田地?”宝钗为人理性,采取实用的做法。她送了丸药来,“晚上把这药用酒研开,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热毒散开,可以就好了”。黛玉是真情流露,“两个眼睛肿的桃儿一般,满面泪光……虽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这等无声之泣,气噎喉堵,更觉得利害”。王熙凤是贾府的管家人,她问宝玉:“可好些了?想什么吃,叫人往我那里取去。”但用黛玉的话说,“必定也是要来打个花胡哨,讨老太太和太太的好儿才是”。周瑞媳妇等人身份低微,但一定也要过来问安的,这几个媳妇都悄悄地坐了一会儿,向袭人说:“等二爷醒了,你替我们说罢。”
这一段情节中,每个人都在做符合自己身份的事情,说着符合规范的话,其中的差别表现得一清二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在《身份经济学》一书中说:“人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社会类型,身份影响着人们的决策,因为不同的行为规范与不同的社会类型紧密相连。”什么身份的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规范,是真实存在的。即便是旋转木马上的孩子,因为年龄不同,也存在不同的规范。这种规范才让大龄儿童对旋转木马产生了矛盾的心理。
在宝玉被打接下来的故事中,有了一个有趣的发展。袭人对王夫人说了一番既符合自己身份,也超越自己身份的话:“我今儿在太太跟前大胆说句不知好歹的话……太太别生气,我才敢说……论理,我二爷也须得老爷教训两顿。若老爷再不管,将来不知做出什么事来呢。”因为这些大胆的话,从此王夫人对袭人另眼相看。
(画中花·未来香摘自《今晚报》2023年12月5日,老老老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