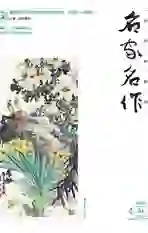戏曲从舞台到银幕的跨媒介视角研究
2024-04-12张文钰
[摘要] 戏曲和电影作为不同的艺术形式,具有各自独特的表现方式和艺术语言。粤剧电影《白蛇传·情》成功地将传统戏曲元素与电影技术手段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呈现方式。影片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利用蒙太奇手法打破传统戏曲的线性叙事结构机制,删改情节突出主线,通过多线叙事在人物形象特征上进行创新性转换,画面巧妙处理“虚与实”的关系,实现从舞台到银幕的叙事、人物形象及虚实的转换。从戏曲到电影的转换过程中,两种媒介形式不可避免地出现冲突与融合,电影《白蛇传·情》为戏曲从舞台到银幕的跨媒介转化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对于进一步推动传统戏曲艺术的发展和传承、探索戏曲与电影相互影响的艺术创新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 键 词] 戏曲;跨媒介;电影;粤剧;《白蛇传·情》
粤剧电影《白蛇传·情》运用电影特效、4K全景声等视听技术,以中国写意美学统摄全篇,突破了戏曲电影的传统表现手法,实现了戏曲从舞台到银幕的跨媒介转换。这种跨媒介的实践既延续了戏曲的传统魅力,又注入了现代电影的视听冲击力。
一、从舞台到银幕:传播媒介的差异性
媒介是信息、知识的载体。当下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趋势日益明显,艺术也呈现出明显的跨媒介趋势,中国许多传统艺术经典在不断通过跨媒介实践来求得新的发展。戏曲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它们在传播媒介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
戏曲作为一种传统的艺术形式,通常在舞台上进行,注重舞台表演、唱腔、音乐伴奏等元素,通过演员的表演来传达情感和故事,每一场演出都是独特的、一次性的,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技巧性。演员在舞台上实时呈现故事,利用特定的动作、手势和面部表情来表达情感和表现角色特征,与观众产生即时的互动,观众的反馈也会影响演员的表演。而电影是一种录制媒体,通过影像、音效、剪辑等技术手段来呈现故事,通过镜头语言和剪辑手法创造出视觉冲击力和情感共鸣,注重画面、音效的表现和影片的叙事结构。电影可以利用特效、CGI(计算机生成图像)和后期制作等技术来呈现各种想象力丰富的场景和特殊效果,利用剪辑技术来切换不同的场景和时间段,通过摄影技术创造逼真的视觉效果,使观众更直观地理解故事的发展和场景的变化以及所展现出的不同时间和空间。
二、从舞台到银幕:叙事、角色与虚实的转换
《白蛇传·情》是中国第一部4K全景声粤剧电影,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巧妙地将现代观念融入其中,以“情”为主线,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以更贴近当代观众的方式传达出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
(一)叙事的转换
从舞台到银幕的叙事转换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是涉及角色类型、环境呈现和情节安排等固定模式基础上的故事改写;另一种是对故事进行艺术性表达所采用的叙事形式与技巧,包括叙述视角的变异、叙述时间的扭曲、公开或隐蔽的非叙事性评论等。
从叙事结构上看,十六场京剧《白蛇传》采用的是线性叙事结构,而粤剧电影《白蛇传·情》除了序言和尾声,主线拆分为游湖、端阳、盗草、水斗、断桥。《白蛇传·情》前置结局并设下悬念,在影片开头白素贞被困于塔内表达对许仙的思念:“圆我的愿,心事千里,只等你遇见……为了他,我愿塔里,再困千年,情已深,思忆点点甜。”打破传统戏曲的线性叙事结构机制,使叙事更为紧凑。影片首尾呼应表现同一个情节,即“守塔”,序言以白素贞的视角展开,结尾以许仙的视角展开,两人在一起的镜头是他们想象与思念的外化。同时,电影采用蒙太奇手法来制造一些多线叙事,在讲述许仙和白素贞故事的同时叙述法海的故事。电影运用镜头和剪辑手段控制节奏, 有效地对原戏曲文本中的时间进行了叙事性处理, 并打破了舞台文本的固定形态, 突破舞台限制, 侧重电影艺术的表现力, 成为一种新的文本的叙事表意特点。
从内容上看,在戏曲电影创作的过程中,对于戏曲的删减集中在情节叙事方面,影片通过精简情节,加强细节呈现,利于电影叙事连接。为了适应电影的表现形式,电影《白蛇传·情》对故事内容进行了调整,删减了舞台剧中的多个情节唱段,删除了观众熟悉的艄公、南极仙翁等角色。如第一折的游湖中,影片删去借伞还伞的情节,白素贞当天主动请许仙到家里小坐;在昆仑,白素贞在打斗过程中,伸出袖子救了差点坠落悬崖的鹿仙童,没有靠南极仙翁这一人物直接感动了两位仙童;在金山寺,由传统程式化的踢枪改成水袖舞与十八罗汉战斗,极具情感张力。在戏曲表演中,“合钵镇塔”这一折戏重点表达母子分离的情感,影片《白蛇传·情》的“情”以“爱情”为重点,为突出重点、明晰主线,確保情节流畅,精简了“合钵镇塔”这折戏。影片只保留了关键的情节与人物,按照戏曲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的规律来组织情节,这样的调整使得故事更符合电影的叙事要求,观众更容易理解和欣赏。同时,影片也在顺序上对戏曲内容进行了调整。电影里法海第一次出场,是白素贞与许仙相识,小青飞在空中赶路,法海与弟子行舟湖上,徒弟惊呼:“那个人会飞的。”法海漠然开口:“她非人类,自有去处。”这句台词出现在粤剧《第四折·伤情》中,许仙在被救活后心中充满疑云,决定去烧香拜佛。在道路旁,他遇到了等候的法海。法海向他透露白素贞是一位千年蛇妖,并建议他皈依佛门、忘情渡劫。法海回答他的疑问:“世间万物皆有其归宿,她并非人类,自有她应去的地方。”导演移花接木,把原本在第四折的台词,放在了第一折,将法海的提前出场合理化。戏曲中,法海在第二折才会出场,且以负面形象出场——警告白素贞并告知许仙真相,这一情节改动也是人物形象从舞台到银幕的一大转换。
(二)人物形象的转换
戏曲从舞台到银幕的跨媒介转换中,创作者会在人物形象特征上进行创新性转换。电影独特的表现形式,可以突破舞台的限制,不局限于从白素贞的视角走剧情流程,还可以从其他人物视角走剧情。
《白蛇传·情》在不改变剧情单元且不乱加戏的情况下,为“法海”这一人物形象重新定位,由负面特质走向正面。法海不再是戏曲中的“大反派”,回归了形象立体的正义高僧形象。早期的《白蛇传》中,法海铁面无私,白蛇妖性十足。但在流变中白蛇的形象被塑造为典型的传统贤妻惠母,与之相对立的法海被塑造成“大反派”。在田汉版的《白蛇传》中,法海成为“封建势力”的代表,他挑唆许仙在端午节下雄黄,许仙在被白素贞舍命相救后却被他强掳上金山,最后镇压白素贞……在电影版中,改动了部分细节,法海形象更为饱满、立体,更易于体会,回归最初的形象。
第一折末尾,白素贞与许仙离开后落下了小青,小青回过神来飞起来追他们的背影被法海师徒看到,法海说了第一句台词:“她非人类,自有去处”。这句台词展现了法海坚守的理念,即秩序中人与妖不应同处。同时,这句话也反映了法海的慈悲心,在妖未侵扰人间之前,他并不急着收妖,避免赶尽杀绝。端阳一折,影片中的法海没有在背后挑唆许仙,而是直面白素贞,警告她之后让她自行离开,法海从白府出来遇上许仙却但并未点破,只念一声“许施主保重”。由于戏曲舞台的限制,法海与白素贞的对戏上演后,没间隙来演法海如何与许仙相遇的细节,只能让许仙再上场时发了一句牢骚:“哪来的和尚,胡说八道。”这就显得法海挑唆许仙。而电影媒介的特征使得画面不受场地限制,可以将法海与许仙相遇这一情节表现出来,这一改动将法海的形象由“小人”变得光明磊落。除此之外,影片给了法海许多细节特写来表现法海的内心世界。如在击退白蛇青蛇后,天空飘下一朵雪花,法海接在手心上,慢慢融化;许仙被小和尚放走,小和尚跪在殿中领罚,法海叹道“仁者有心,也难怪于你”等。
同时,影片在塑造“许仙”这一人物形象时,弱化了人“自私懦弱”的一面,强调了许仙“重情”的一面。与戏曲舞台中的人物形象不同,影片中的许仙买雄黄酒并非怀疑妻子白素贞,只是因为端午时恰巧遇到商铺卖酒,而端午这天家家户户都备着雄黄酒。许仙买酒一是因为习俗,二是为了庆祝。他回家后的三次劝酒是在进行情感诉说——第一次劝酒是敬“一盏柔情觞”;第二次劝酒是许仙得知白素贞怀孕后“为我们孩儿祝祷,愿他喜乐平安”;第三次劝酒许仙感谢白素贞不嫌弃他的身世并下跪立誓“一心一意一世人,不离不弃终百年”,愿夫妻终老百年。三杯酒,杯杯情真意切,让观众摈弃对许仙“渣男”的刻板印象,欣赏许仙的“真情实意”。
可以说,《白蛇传》从舞台到银幕的转换,重新塑造了“法海”正直正义的僧人形象,表现出他内心的善良与慈悲,转变了“许仙”自私懦弱的形象,突出许仙对白素贞情感的真挚,使故事情节更加合理和切题。影片深度挖掘角色特征,人物特质更富层次性,带给读者新的阅读体验。
(三)虚与实的转换
戏曲写意,电影写实。《白蛇传·情》继承戏曲美学的写意风格,影片力求保持戏曲的“写意性”风格,巧妙处理“虚与实”的关系,将极具中国特色的水墨画融入其中,在保留戏曲本质的基础上弥补传统戏曲在演员表演、时空关系等方面的不足。
在“水漫金山”这折戏中,传统的戏曲舞台上借助众多位演员甩水袖来制造大浪滔天之效果,凸显戏曲的写意特征。影片中,水袖的挥舞与电影特效结合,白素贞立于江心礁石上之中挥舞长袖,卷起滔天巨浪,那水袖恰似漩涡中心,真正做到人与水浑然一体。导演张险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电影的水浪里糅合着很多水墨写意的东西……它其实是削弱的,是偏平面化、形式感的,浪与浪之间或者浪与环境之间,有很多水汽和雾气,会有中国写意画‘留白的那种气韵在里面。”可见,《白蛇传·情》这部影片借助先进的4K技术和视觉特效,通过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成功跨越了戏曲写意与电影写实之间的鸿沟。
三、从舞台到银幕:跨媒介的冲突与融合
时至今日,如何借用电影的表现手法展现戏曲,仍然是戏曲与电影融合的一个难题,因此也便有了“以影就戏”和“以戏就影”的说法。如何平衡戏曲的舞台表演与电影的场景切换、演员形象远观与近看等问题亟待解决。
(一)舞台与实景
如何表达舞台空间的是戏曲电影的一大困境。郑君里认为:“戏曲的舞台空间是虚拟的程式,一出戏曲的地点和空间往往通过唱词和动作暗示出来。”舞台布景和背景是表演的一部分,舞台上使用具象或象征性的道具、布景和背景来营造不同的场景和环境,表示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很多观众心中舞台技巧就是无实物表演。如果将戏曲舞台直接记录在电影中,会削弱舞台和演员的空间感以及观众与演员之间的距离感,丧失舞台的独特特点。因此,大多数戏曲电影倾向于写实的布景,甚至在实景环境中进行拍摄。然而在实景拍摄中,演员的表演风格及妆容与实景之间存在冲突。演员的写意表演与实景的现实主义风格不协调,电影观众会认为人物表演和妆容过于夸张,而戏曲观众则会感觉人物不在戏中。
《白蛇传·情》为戏曲电影舞台布景提供了典范,保留传统粤剧的念白方式,参考粤语的声韵与语序语法,经过艺术化的处理区别于日常语言,改变戏曲妆,虚实结合,在画面处理上体现“人在画中游”的美感,通过具象的视觉画面呈现出朦胧的幻境,让写实与写意有机融合,把握好虚与实在影片中的比例,既有现实中的真,也有意象中的美。
(二)演员形象
演员的表演魅力是戏曲的一大特色。戏曲角色从舞台到银幕的转换中存在一些难以化解的矛盾。在舞台环境中,观众只能“远观”戏曲演员,通过想象主动地为人物角色补充面部表情及容貌细节,戏曲演员更重视气场、声音及肢体语言,面部表情比较程式化、妆容夸张。而电影中的近景特写将演员的细节放大在画面之中,五官和肌膚的缺点暴露于观众面前,戏曲妆显得有些夸张僵硬,破坏了观众的想象力和演员的美感。若在戏曲电影中去掉近景特写,不仅无法充分展现角色的形象,还会导致影片的视听结构变得单调乏味,几乎变成纯粹的记录性影像。
在粤剧电影《白蛇传·情》中,导演通过增加特写画面中的动感和缥缈感赋予演员美感,在拍摄演员近景时,增加流动的光线,减少画面的僵硬感,增加眼神光和色彩对比的协调程度,用最佳角度拍摄,通过各种手段提升演员的美感,从而解决了戏曲电影特写带来的演员美感问题。
四、总结
粤剧电影《白蛇传·情》在保持传统戏曲艺术特色的基础上,巧妙地融入了电影的叙事手法和视觉元素,为观众呈现了一部视听盛宴。这一跨媒介的尝试,不仅丰富了戏曲的艺术表现形式,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深层次地诠释了中国美学精神,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陈力丹,闰伊默.传播学纲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8.
[2]唐留文.现代白蛇传改写的叙事研究[D].延边:延边大学,2022.
[3]宁辰,李勇强.传统戏曲的跨媒介改编及其结构艺术:以《白蛇传》为焦点[J].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19,17(4):20-26.
[4]乔慧婷.戏曲从舞台到银幕跨媒介转换的美学思考:以蒲剧电影《山村母亲》为例[J].西部广播电视,2018(2):107-108.
[5]李钢.戏曲电影对传统戏曲的影响:以粤剧电影《白蛇传·情》为例[J].大舞台,2023(2):40-45.
[6]李镇.郑君里全集:第7卷[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6:292.
作者简介:
张文钰(2002—),女,汉族,山西晋城人,本科,研究方向:艺术理论与美学。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