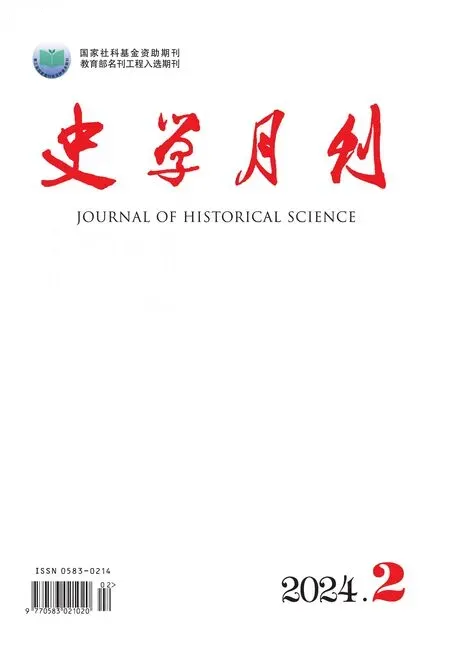唐代武职事官阶官化论析*
2024-04-06张明
张 明
《旧唐书·职官三》详细罗列了唐代武职事官的名号,分布于南衙十六卫,地方都督府、都护府、折冲府、镇戍的大将军、将军、中郎将及折冲都尉、果毅都尉等,品级森严、职事明确,都是名实一致的实职武官(1)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四《职官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98~1906页。按,需要注意的是,南北衙诸武职事官在唐后期已经基本没有职事,部分武官有职事时需加“知军事”衔。。而到了《宋史·职官六》的记载中,所有带“将军”号的武官都是无职责的虚衔,“诸卫上将军、大将军、将军,并为环卫官,无定员,皆命宗室为之,亦为武臣之赠典;大将军以下,又为武官责降散官”(2)脱脱等:《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32页。。北宋真正的武官则主要由环卫官、正任官、遥郡官、武阶官及其所任差遣钤辖、都监等组成。可以说,除环卫武官名号与唐代有明显的继承性之外,其他都不相同。唐宋武官制度的截然不同,从根本上讲,是由军事制度和职官制度的剧烈变革导致的,而直接原因则是“武职事官阶官化”。所谓“职事官阶官化”,是指职事官变为空名虚衔,用于表示官员的身份、品阶,却没有了实际职任,其根本特征是官、职分离。武职事官阶官化则是唐宋时期职事官阶官化进程的一部分。
阎步克指出,唐代散阶与职事官结合的职官制度,是汉代以来官制演变的成果总结。在“品位分类”的原则下,散阶的本品地位动摇后,必然会产生新的品阶序列,唐代的职事官阶官化即属此类(3)阎步克:《“品位-职位”视角中的传统官阶制五期演化》,《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3~14页。。一般认为,职事官阶官化主要有两种途径(4)“某些职事官因位高职重,不轻易授人,不掌管实务而阶官化……某些职官闲简无事,或为外官所领而阶官化。”(张国刚:《唐代阶官与职事官的阶官化》,《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2期,第79页)。然而较为特殊的是,唐宋时期职事官长期从事使职差遣而造成阶官化,成为另外的新途径。张国刚曾指出,“差遣期间本官是不管本司事的,原来的职事官只是表示该官受差遣时的身份地位而已,这样一来,就埋下了职事官阶官化的种子”(5)张国刚:《唐代官制》,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9页。。这一论断指明了唐宋时期职事官阶官化的时代特征。此外还有学者从散官、勋官、员外官和试官等视角,多方面论述了唐代官制的变化及职事官阶官化的产生(6)相关成果,参见马小红:《试论唐代散官制度》,《晋阳学刊》1985年第4期,第52~56页;黄正建:《唐代散官初论》,《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2期,第91~102页;陈苏镇:《北周隋唐的散官与勋官》,《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第29~36页;杜文玉:《论唐代员外官与试官》,《陕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3期,第90~97页;吴宗国:《三省的发展和三省制确立》,《唐研究》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5~165页;卢向前、熊伟:《本阶官位形成与演化——北周隋唐官制研究》,《浙江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第92~100页。。
作为唐代职官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武职事官,同样发生了阶官化并由此影响了唐宋之际武官制度的变革。不过,唐代武职事官阶官化问题的研究较为薄弱,或在唐代军制问题的研究中被归结为因丧失职事而成为虚职,或在部分职事官阶官化研究中有所提及,尚无专文探讨(7)在唐代职事官阶官化的研究中,有学者关注了唐代武职事官的阶官化问题,但仅有总体性的概括,并无详细研究。阎步克说:“随着‘使职差遣’的发展,三省六部官、御史台官、卿监长官、诸卫大将军等等官位,借助‘检校’、‘试官’、‘加宪衔’一类形式而开始阶官化了,开始变成为‘使职’之‘阶’。”(阎步克:《“品位-职位”视角中的传统官阶制五期演化》,第9页)张国刚提及“诸卫大将军特别是金吾大将军”完全阶官化了(张国刚:《唐代阶官与职事官的阶官化》,第81页),进而认为:“南衙诸卫成为闲职后,将军、大将军便成了武臣以至宦官表示资望的迁转之阶。”(张国刚:《唐代官制》,第117页)在唐代南衙诸卫演变及府兵制崩溃的研究中,对诸卫及军府武职官丧失职能多有论及,但也缺少对其阶官化问题的深入探究。如谷霁光说,“十二卫除左右金吾卫、左右千牛卫,尚有实职外,其他都是保留官职、机构,很少兵员……仍保存其名号以养勋阶”(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16~217页)。在宋代武官制度研究中,对唐代以来武官制度的发展多有回顾,但同样缺乏对唐代武职事官阶官化过程的考察。相关成果,参见束保成:《论宋代环卫官》,《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第77~81页;林煌达:《南宋环卫官的演变与发展》,《中山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第88~100页;束保成:《南宋环卫官再探——与林煌达先生〈南宋环卫官的演变与发展〉商榷》,《中山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第27~37页。。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受到唐代军事制度和职官制度变革的根本性影响,在武职事官长期从事使职、武官使职化、军赏形式转变等因素的直接冲击下,武职事官在唐代已经率先完成了阶官化。
一 武职事官兼领使职与阶官化的条件
唐前期武职事官都有明确的职掌,是名实相符的职官。如南衙诸卫武职事官的本职,包括掌领宫廷禁卫、管理本卫事务等;地方折冲府武官负责本府事务,即所谓的“掌领五校之属,以备宿卫,以从师役,总其戎具、资粮、差点、教习之法令”(8)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二五《诸卫府》,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44页。。不过在循名责实的纸面规定之外,唐前期的武职事官也会广泛出任各种使职差遣,包括管理厩马、参与礼仪等非军事性使命与担任押当官、检校北衙、充任行军等军事性使命。
唐代马政系统较早地推行了使职差遣制,“马政系统的使职差遣制开始于马匹生产部门,是由当时严重缺马的现实决定的,并终于以彻底取代原有职官系统而告结束”(9)马俊民、王世平:《唐代马政》,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3页。。很多武职事官都曾充任马政使职人员,比如以检校右领军卫将军知六闲马事的乙速孤神庆(10)参见《乙速孤神庆碑》,王昶:《金石萃编》卷六一,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1037页。、长期检校祥凤苑厩的索礼(11)参见《索礼墓志》,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8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8页。以及唐玄宗时期任“检校内外闲厩兼知监牧使”的左武卫大将军王毛仲(12)刘昫等:《旧唐书》卷一〇六《王毛仲传》,第3253页。等。唐代武职事官参与礼仪活动虽然在其职责之内,但是在相关活动中会派生出一些另外的临时差遣。贞元二年(786年)制定百官朝谒时的武班仪仗:“武班供奉宣政殿前立位:从北,千牛连行立,次千牛中郎将,次千牛将军一人,次过状中郎将一人,次接状中郎将一人,次押柱中郎将一人,次又押柱中郎将一人,次排阶中郎将一人,次又押散手仗中郎将一人……”(13)王溥:《唐会要》卷二五《文武百官朝谒班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61页。以上仪仗武官中,“过状”“接状”“押柱”“排阶”“押散手仗”等诸号中郎将,都是根据武职事官在仪仗中的站位和职责临时赋予的使命。
除马政和礼仪外,武职事官也广泛接受其他使职差遣。如《茹守福墓志》记载其任陇州大候府果毅时,“特进王毛仲闻而重之,召为监牧都使判官”,后又充当“京苑总监,杂掌农衡”,也曾“奉使陇右道巡盐牧”(14)《茹守福墓志》,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5页。。不过,唐前期武职事官最广泛兼领的还是军事使职,包括担任事务性押当官,检校、押领北衙禁军及充任行军军职等。
所谓事务性押当官,是指临时担任某项任务的主管。《唐六典》中有一条记载为“诸应外职掌押当及分司者”(15)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第154页。,“分司”为外任东都分司,“押当”即为此。从史料上看,武职事官执行的事务性押当主要包括以下数种:一是宫门守卫。《裴昭墓志》载其“迁绛州长平府果毅,仍留长上,押东宫问安门”(16)《裴昭墓志》,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128~1129页。。二是皇陵守护。元和十一年(816年),宗正寺上奏建陵门戟被毁,诏“所由阙于周防,敢尔侵犯,各据事状,宜有科惩。知山门押官决六十,削一任官;骑三卫,并决四十”(17)王溥:《唐会要》卷一七《庙灾变》,第411~412页。。三是扈从行幸。“神龙三年十月十七日敕:行幸每顿入宿兵及三卫,并令伍伍相保,其押官责名品,明作文簿,别送与金吾”(18)王溥:《唐会要》卷二七《行幸》,第604页。。四是其他看守性任务。如看守谏匦,“伏以旧例,诣光顺门进状,即有金吾押官责定住处,匦院投状”(19)王溥:《唐会要》卷五五《匦》,第1125页。。又如开元年间的“展仗押官”,“开元初,卫士为武士,诸卫折冲、果毅、别将,择有行者为展仗押官。右羽林军十五人,左羽林军二十五人,衣服同色”(20)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九上《百官四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89页。。其他类似使命亦如是。
武职事官检校、押领北衙禁军和充当行军军职这两种情况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此处以阿史那忠为例,略做阐述。
(永徽中)为左武卫大将军,寻迁右骁卫大将军。属兴师辽碣,以公为使持节长岑道行军大总管……(契丹)近侵卉服,外结鸟夷。公回师诛翦,应机殄灭,虏获万计,三军无私,蒙赏缣帛,仍于羽林军检校……总章元年,吐蕃入寇,拜使持节青海道行军大总管……西海诸蕃,经途万里。而有弓月扇[煽]动,吐蕃侵逼。延寿莫制,会宗告窘。以公为西域道安抚大使、兼行军大总管(21)《阿史那忠墓志》,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1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第50~51页。。
阿史那忠的本职为南衙左武卫大将军和右骁卫大将军。本职之外,他还充任过两种使职差遣:其一,检校羽林军。唐初北衙禁军尚未设立完善的职官体系,大多选择南衙亲信将领分别检校、押领,也就是以南衙武官兼领北衙职事。诸如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等人,都曾以此名号统领北衙禁军(22)唐前期以南衙将领统领北衙禁军是通例,史书上对此有明确记载。如“(贞观)十二年,始置左右屯营于玄武门,领以诸卫将军,号‘飞骑’”(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〇《兵志》,第1331页)。。检校和押领是武职事官领北军采用的不同称呼,一般以检校羽林、检校屯营、押飞骑、押千骑、押万骑等固定组合出现。其二,担任行军职务。行军出征期间,行军的军职名号由大总管、总管、子将、都虞候、虞候等构成,人事上主要抽调武职事官充任(23)参见孙继民:《唐代行军制度研究(增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6~76、100~143页。。阿史那忠历任“使持节长岑道行军大总管”“使持节青海道行军大总管”“西域道安抚大使、兼行军大总管”,就是在不同行军中担任军职。
以上使职大多数是针对临时任务的专门派出,性质上属于军事制度直接衍生的附属使命,是对职官制度运行的补充。因而这一时期武职事官出任使职既没有“侵夺”职事官的本职,也不会对官职体系造成不良冲击,反而弥补了职官制度的缺陷,维系了唐代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例如在唐初行军体制下,尽管武官充任行军军职较为频繁,但是并不影响其履行本职。行军只有在大规模战争时才会择机组建,事平则罢。而唐初行军多是短暂的对外征伐,战争也多以唐军胜利告终,出征时间不长。因此,南衙将军基本都能很快回归本职。又如南衙将军检校、押领北衙禁军,虽然一般是较为固定的长期差遣,但唐前期北衙禁军规模较小,需要的武官数量也较少(24)唐长孺认为,“北门军的数量在玄宗以前不会超过万人”(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9页)。。所以,南衙将领充任北军通常被看作是皇帝信任的恩宠。抽调南衙武官统领北军,既可以拉拢有军功的将领,又可以简便地解决北军管理问题,还不影响南衙职事的正常运作。
不过,此时确实存在部分武职事官长期固定充任使职的情况,实质上造成了职与官的分离。如前引茹守福被王毛仲简拔为监牧使判官后,“判官如故,前后十余岁焉”(25)《茹守福墓志》,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275页。,已经是长期脱离本职了。更为典型的是索礼,从其墓志来看,他一直是挂武职事官衔,实际从事的是马政。
索礼祖父为“敦煌郡王”,其以门荫授武散官游击将军而获得武官身份。在未授职事官的情况下,他实际出任的是“检校祥凤苑厩”这一使职。随后,索礼实授武职事官“左豹韬卫洛汭府左果毅都尉”,成为有正式职事的武官。但从志文来看,索礼并没有真的参与该军府的职事,而是“仍令长上,兼检校祥凤苑厩如故”,也就是带武职事官的职衔,实际充任的是马政使职。武周换代之际,索礼的武散官再次获得提升,而兵府职如故,仍然实任马政使职。
从表面上看,索礼是先以武官身份领使职差遣,积累劳考(27)“劳考”即“年劳”。相关研究,参见胡宝华:《试论唐代循资制度》,《唐史论丛》第4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0~199页;《唐代循资制度补证》,《河北学刊》1990年第6期,第88~90页。刘琴丽:《唐代武官选任制度初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6~41页。后再授武职事官。但实际上管理厩马的使职是索礼获得资历的依靠,连续获得晋升的是其武散官本品,而授予的实职武职事官更像是用以标明身份等级的额外酬赏。显然,这种情况已经非常接近武职事官虚衔化的意味。而且索礼的情况绝非个例,部分南衙武职事官在兼领北衙禁军期间已经不理本司公事,反而主要在北衙任职。田归道即为一典型事例:
累迁左金吾将军、司膳卿,兼押千骑。未几,除尚方监,加银青光禄大夫。转殿中监,仍令依旧押千骑,宿卫于玄武门。敬晖等讨张易之、昌宗也,遣使就索千骑,归道既先不预谋,拒而不与(28)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八五上《田归道传》,第4795页。。
田归道始以左金吾将军、司膳卿押千骑,后除尚方监,再转殿中监,依旧以左金吾将军押千骑(29)“田归道为右金吾将军、殿下监,押千骑宿卫于玄武门。敬晖等将讨张易之、昌宗也,遣使就索千骑,归道既先不预谋,拒而不与”(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六二七《环卫部·忠节》,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530页)。文中“殿下监”当为“殿中监”之误。。可见不论田归道如何迁转,一直是以左金吾将军的身份押千骑。也就是说,金吾将军的作用是表明其武官身份,押千骑才是其主要职责。从神龙政变时敬晖等遣使索要军队的举动来看,也可以确认田归道掌握着北军千骑的实权。
总的来说,唐代武职事官兼任使职的情况非常普遍,所担任的使职范围广、类型多。在长期与使职结合的过程中,武职事官开始出现比较固定的官、职分离现象。也就是说,长期从事使职差遣成为唐代武职事官阶官化的先声,这显然符合唐宋时期职事官阶官化的时代特征,也是唐代职官制度和军事制度发展的必然。
二 武职事官阶官化现象的发展
随着战争形势和军事制度的变化,不但边军中出现了将武职事官当作阶官使用的现象,中央禁军中的一种特殊情况也显示了同样的趋势,共同昭示着武职事官阶官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先看边军中的情况。自高宗以后,唐在西域、吐蕃和辽东的战事久拖不决,北面突厥的复兴也带来了较大的压力。与此相适应,行军变得长期化、固定化,充任军职的武职事官也被迫长期脱离本职公事,造成了普遍的官、职分离情况。《阳玄基墓志》就很好地反映了由行军向镇军转变时期武职事官的任职情况。
唐显庆三年,从薛仁贵平契丹。龙朔元年,随契苾何力破鸭渌[绿],授游击将军、左骁卫善信府果毅。总章元年,授鹿陵府长上折冲,仍检校东栅州都督府长史……俄授左卫翊府右郎将,于鄯城镇守,频破吐蕃贼。永隆二年,加授左金吾中郎。永淳元年,加壮武将军、太子左清道率,奉敕于岚州总材山守捉……弘道元年,制加三品,授左骁卫将军……降三阶,授大中大夫、行戎州都督都府长史……以功授庄州都督,寻改授忠武将军、行左卫勋一府中郎,仍借紫兼充清边军总管……圣历元年,授三品左鹰扬卫将军……遂以君检校左羽林军(30)《阳玄基墓志》,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8辑,第330页。。
阳玄基从军的时候,正处在唐代行军制度变化的过渡时期。他跟随薛仁贵、契苾何力的两次出征仍然是行军,其后就是长期带武职事官在外镇守,已经转变为镇军。授鹿陵府长上折冲时,阳玄基实任检校东栅州都督府长史;晋升左卫翊府右郎将、左金吾中郎、太子左清道率时,他实际上又分别担任了鄯城镇守、岚州总材山守捉。可见,阳玄基一直在行军或镇军中任职。其历次迁改的南衙诸卫(左卫翊府右郎将、左金吾中郎、左骁卫将军等)、率府(太子左清道率)和折冲府武官(善信府果毅、鹿陵府长上折冲)都不真领职事,实际上已经可以视为比较典型的阶官现象。再看崔思忠的情况:
咸亨元年,以左卫翊卫擢入羽林军……文明元年,奉敕简充引驾,仍每番明堂检校。载初元年,授左卫开方府左果毅都尉。其年九月,制加游击将军。如意元年,奉敕于玉门镇,经二周讨贼,再立功……圣历元年,除斜谷府折冲,奉敕于白草军防御。至军,又为左军总管……圣历二年,奉敕镇安西。至镇,又于拨换城守捉……神龙元年,制除廓州刺史,兼知积石军事……景龙二年九月七日,薨于积石军之公馆(31)《崔思忠墓志》,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8辑,第366页。。
崔思忠由羽林军授开方府左果毅,如意元年(692年)带此职出镇玉门。圣历元年(698年)升为斜谷府折冲,转到白草军镇守;其后再镇守安西、守捉拨换城。从其所任职官来看,崔思忠虽然长期在河西和西域等地镇守,但在任廓州刺史前,其正式职官一直是内地军府的果毅、折冲。
唐玄宗时期行军完成了向镇军的转变,最终确立了节度使体制(32)本文所谓节度使体制的确立,是指开元、天宝年间设立边疆八节度时期。此间节度使辖区较为稳定,兵役、作战、僚佐、武将节级等各项制度已比较成熟。相关研究,参见严耕望:《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年版,第177~236页;张国刚:《唐代藩镇军将职级考》,《学术月刊》1989年第9期,第71~76页;荣新江:《唐五代归义军武职军将考》,《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76~87页。。在这个长期变化的过程中,边军使职体系也高度发展了。节度使体制下,主帅以“节度使”衔为核心,兼领经略、支度、采访(观察)、营田、水陆运等使,全面掌握边军、边地的军政财权;围绕主帅,形成了以节度副使、行军司马为核心的文职僚佐和以(都)押衙、(都知)兵马使、都虞候为核心的武职僚佐体系;军、城镇、栅堡、烽燧等军事组织,也分别由军使、镇使等使职统率(33)以上名目各异的军事使职,都是在长期的军事体制变化中逐渐出现并最终在节度使体制确立后才形成了以上结构和层次。。
需注意的是,节度使体制下的军事使职与行军体制下的军职,本质上虽然都是使职,但对唐代职官制度的影响却不可同日而语。行军军职是抽调武职事官充任,来源单一,行军停罢即回归本职,对武官制度基本没有影响。节度使体制下的军事使职则不同,人员构成复杂,既有武职事官外出边军充任使职,也有自行伍中简拔的白身。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长期在边军中任职,外出边军的武职事官不能在本司履职,行伍出身的武将甚至只在军内升迁,由此形成了边军武将身在边地、职在军中、官在朝廷的普遍性官、职分离的局面。从职事官阶官化发展的视角观察,应当认为边军中确实已经出现了武职事官充当阶官的情况。授予边军武将以武职事官的性质,已由国家任命武官的一般程序蜕变为容纳边军使职进入国家官僚体系进行管理的手段。
边军中首先普遍出现武职事官阶官化现象,是由于边将与朝廷官职之间出现了不可克服的时空分离。就此而言,中央禁军中武职事官阶官化现象的发展似乎应该比较缓慢,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唐中央禁军中出现了另一种以武职事官为阶官的隐蔽现象,主要表现为武将的官职在果毅、折冲及中郎将、太子卫率等中级武职事官层级内反复迁转,长时间不升进。这种现象既不符合常理,也违反了唐代武官晋升的正常秩序。
据日本学者爱宕元(愛宕元)考证,唐前期武官的一般性晋升序列为“果毅都尉→折冲都尉(或郎将)→中郎将→将军”(34)爱宕元:“唐代府兵制的一点考察——通过对折冲府武官官职的分析”(愛宕元,“唐代府兵制の一考察—折衝府の武官職の分析を通して—”),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编:《中国中世史研究续编》,京都:京都大学出版会1995年版,第173~215页。。开元、天宝时期不乏径直走完这一序列的实例。如《董公墓志》记:
公解褐授游击将军、左卫龙交府右果毅,转洛安府折冲,寻除右威卫翊府中郎将,迁右威卫将军,又加宣威将军。扈从东封,加云麾将军。昊穹不吊,享年五十,开元十四年九月五日薨于位(35)《董公墓志》,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319页。。
再如《高钦德墓志》记:
伊先君身死王事,鸿泽酬汲,赠一子官,解褐拜陶城府果毅。职自先君遗效也,每夕惕乎位,乾乾在躬,贺承天休,匪懈惟恪。自束发从仕,总八任焉。首自果毅,毅可济时;再授折冲,艺能保塞;三授郎将,翼侍于天人;四调中郎,武匡于帝里;五登二率,捧佐乎储尊;六事将军,乃分忧于阃外。凡此六者,若非雅政特达,焉能致于此乎……以开元廿一年九月十有九日,终于柳城郡公舍(36)《高钦德墓志》,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416页。。
从墓志看,董府君的任职经历可谓顺畅,首任为果毅都尉,又升折冲都尉,然后就由地方军府转入中央三卫,为右威卫翊府中郎将,再迁本卫将军。高钦德的仕宦生涯同样顺利。其由先祖功勋荫庇,解褐陶城府果毅都尉,再升折冲,第三任为郎将时已经升入中央十二卫,第四任为中郎将,第五任官时转入太子率府,第六任为右武卫将军。总体来看,以上两人虽没有成为唐代大将,但一路升迁顺畅,仕途堪称平坦。与他们相比,另外一些人的仕宦经历看起来颇为积滞,如《单重忻墓志》所示:
弱冠应平射举高第,解褐京兆□谷府左别将,仍左羽林军长上、平射内供奉,寻迁同州安远府左果毅都尉,赐绯鱼袋,从班例也。累迁京兆沣浩府左(果)毅、蒲州兴乐府折冲、潞州黎城府折冲都尉。无何,拜蒲州石门府折冲,仍右金吾卫都知队仗长上、内供奉,悉如故。开元廿六年改同州南乡府折冲都尉、威远营副使、上柱国。出身历职凡经七任……开元廿七年秋七月遘疾于威远营官舍,谢病还家(37)《单重忻墓志》,齐运通主编:《洛阳新获七朝墓志》,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27页。。
单重忻解褐为军府左别将,然后升任同州安远府左果毅,又调为京兆沣浩府左果毅。其后更是四次转任折冲都尉,逡巡于蒲州兴乐府、潞州黎城府、蒲州石门府、同州南乡府之间。从左别将至折冲都尉,七次迁转仍不出兵府武官,乃至终其一生都没有升至中央十二卫武官。唐代折冲府只有上、中、下府三等,折冲都尉的品级分别为正四品上、从四品下和正五品下,因而其四任折冲的经历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是正常的迁转。虽然府兵制崩溃的原因之一,是兵府武官常年不得迁转,但单重忻的情况显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府兵制崩溃的前兆。问题的关键在于单重忻的身份,他虽名义上历七任地方折冲府武官,但一直是在京城禁军之内任职,并不曾实任外府。
以单重忻实任的宿卫职务来看,其起家左别将之时,所任实际职事为“左羽林军长上、平射内供奉”;任蒲州石门府折冲都尉时,职事为“金吾卫都知队仗长上、内供奉”,都是中下层禁卫任务。单重忻最后兼任的“威远营副使”职事需要特别说明。威远营虽然是唐后期南衙主要禁军之一,但在开元年间还只是鸿胪寺下辖的警卫部队,兵力不多,地位也不高(38)关于威远营的研究,参见齐勇锋:《唐后期的北衙六军、飞龙、金吾、威远和皇城将士》,《河北学刊》1989年第2期,第80~81页;张国刚:《唐代禁卫军考略》,《南开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第155页;杜文玉:《关于内诸司使与威远军使研究的几个问题》,《河北学刊》2011年第3期,第47~48页;刘琴丽:《再论唐代的威远营》,《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28~138页。。可以说单重忻实任职事级别都比较低,以折冲都尉的品级作为阶衔,完全可以与其职事匹配,甚至可以称作高配。因此可以认为,兵府武官只是赏赐其勋劳的阶衔,在各府之间空转并不会影响其实际意义。另有《高德墓志》可做参照:
(唐元有功)圣恩念劳,授平州白杨镇将,转鄜州之龙交、岐州之杜阳两府果毅,俄迁陕州之万岁,降[绛]州之长平、正平,怀州之怀仁,同州之洪泉等五府折冲。擢授右武卫翊府郎将,超授定远将军、右龙武军翊府中郎,赐紫金鱼袋、长上、上柱国、内带弓箭。府君虽官授外府,而身奉禁营……以天宝元年二月(薨)(39)《高德墓志》,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2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528页。。
墓主高德的仕宦经历看起来和单重忻一样艰难,尽管最终超擢龙武军翊府中郎将,但也经历了两任果毅、五转折冲的曲折过程。而造成其迁转如此艰难的主要原因,同样是“虽官授外府,而身奉禁营”。开元、天宝时期还有很多类似的实例,禁军普通将领反复在果毅、折冲等地方武官或郎将、中郎将等中级武官内迁转,却迟迟不能升迁。从实际需要上看,这是由于唐玄宗时期充任中央宿卫的武官经常三四十年不外出,他们没有战功,却有赏“劳”的需要(40)在玄宗时期,北衙禁军将领长期稳定,基本就是由参与“唐隆政变”“先天政变”等重大事件的龙武军将领统辖,诸如王毛仲、陈玄礼等人。不仅高级将领如此,在墓志中也可以见到中低级武官长时间稳定的实例,如《冯思顺墓志》记,“以开元二载补右羽林军平射飞骑……至天宝三载又转授上郡万吉府果毅,又转授咸宁郡宜城府果毅。至天宝十载十二月卅日,恩制赐绯鱼袋。至天(宝)十二载又转授五原郡盐川府折冲。自微至著卌余年,不离羽林”(《冯思顺墓志》,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5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7页)。。因而在禁军中产生的这种特殊现象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积滞,而是将武职事官用作阶官,使武将在已经空名化的兵府武官位阶中反复空转,用以赏赐。
尽管边军和禁军中都普遍出现了阶官现象,但如何界定唐代武职事官阶官化发展的程度却成为难题。幸而随着职事官阶官化程度的加深,唐代官员的结衔结构也出现了变化,这成了一个明显的、可供观察的标志。
经过汉末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官制发展,在唐初形成了“品、阶、勋、爵与职事官相互为用的复合等级体系”,其核心是以“职官”为实际任职,以“散官”为阶,以“散官”为“职官”本品的制度(41)入仕者的出身(做官资格)、品级以及俸禄、服色等诸多权益都依靠散阶来区分等第。唐代散阶又以是否取得职事官为区分,任职事者所带称“本品”,无职事者称“散品”(参见阎步克:《“品位-职位”视角中的传统官阶制五期演化》,第8~9页;张国刚:《唐代官制》,第164页;马小红:《试论唐代散官制度》,第55页)。。但自武周以来频繁使用“泛阶”的做法,使得散官愈发猥滥。散官制度的不合理和烦琐,使得它在中唐以后基本失去了作用(42)黄正建:《唐代散官初论》,第99~101页。。尽管如此,唐代品阶与职事并立的职官制度却并未改变。因此,在散官的本品地位动摇及使职广泛发展之后,又形成了新的组合方式,“以‘职’为实,以‘散’为阶的制度低落之后,以‘使’为实、以‘职’为阶的新制一波再起”(43)阎步克:《“品位-职位”视角中的传统官阶制五期演化》,第9页。。由此可以发现,唐代职事官阶官化会有明确的表面特征,即官员的结衔结构会发生变化。
在唐初官制设计中,“散官+职事官”是职事官官衔中最为核心的部分,散官表示官员在官僚体系中的等级和特权,职事官表明其实际担任的事务。在职事官阶官化后,变成了以“职事官+使职”作为核心要素,职事官作为阶官,表示品阶,使职表明实际从事的事务。由此,唐代武职事官的阶官化过程可以从使职是否入衔这一标志性变化中得到较为清晰的呈现。
以前引《阿史那忠墓志》为例,其墓志题名为“唐故右骁卫大将军兼检校羽林军赠镇军大将军荆州大都督上柱国薛国公阿史那贞公墓志铭”(44)现今能见到的唐代官员完整的官职结衔,一般出现在授官诏书、官员上表以及墓志中,尤其是官员墓志题名,依据墓主生前的官职构成,可以视作其官职结衔的一般样式。。可见,阿史那忠武散官的最高品阶为死后所赠镇军大将军(从二品),武职事官的最高品阶为右骁卫大将军(正三品),故其官职结衔中最核心的部分是镇军大将军、右骁卫大将军。超出唐前期一般官职结衔的,是阿史那忠题名中还包含了“检校羽林军”的使职差遣。但阿史那忠经常担任的另一种使职差遣——行军军职,却没有包含在结衔中。同样是使职,一个入衔,另一个不入衔,这其中隐含了唐前期官制演变的逻辑。
使职是否入衔并无明文规定,但从史料上看,唐前期的使职在设立初期都不入衔。如礼仪使,“高祖禅代之际,温大雅与窦威、陈叔达参定礼仪。自后至开元初,参定礼仪者并不入衔”(45)王溥:《唐会要》卷三七《礼仪使》,第784页。;甚至宰相的“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二年八月)己巳,侍中、燕国公于志宁为尚书左仆射,侍中兼刑部尚书、北平县公张行成为尚书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三品,犹不入衔”(46)刘昫等:《旧唐书》卷四《高宗纪上》,第69页。。显然,临时性使职不入衔是唐初的通行做法,既表明使职设置的短暂性,也体现了使职对职官制度影响的有限性。直到这些使职在发挥了重要作用并长期固定设置之后才会入衔,如“群牧使”从不入衔到入衔的转变过程就在史料中有明确记载:
贞观十五年,尚乘奉御张万岁除太仆少卿、勾当群牧,不入官衔。至麟德元年十二月,免官。三年正月,太仆少卿鲜于正俗检校陇右群牧监,虽入衔,未置使。上元五年四月,右卫中郎将邱义除检校陇右群牧监。仪凤三年十月,太仆少卿李思文检校陇右诸牧监使,自兹始有使号(47)王溥:《唐会要》卷六六《群牧使》,第1353~1354页。。
群牧使设置之初,与其他使职一样,并不入衔。麟德三年(666年)鲜于正俗检校陇右群牧监时,使职已经入衔,但并未使用“群牧使”一名。至仪凤三年(678年)李思文检校陇右诸牧监使时才成为置使并入衔的固定使职。由此,阿史那忠的两个使职入衔与不入衔之间的原因就较为清楚了。阿史那忠长期兼领“检校羽林军”的使职,而且此使命具有一定的荣誉性,所以墓志撰写者将之加入了结衔中。而唐初行军时间短暂,临时的行军军职就不再入衔,符合唐初的惯例。
在行军向镇军转化并最终形成节度使体制的过程中,边军使职成为武官长期固定的实际职事,由此也开始在武官的结衔中被体现出来。开元十五年(727年)去世的窦九皋,其墓志题名为“唐故游击将军守右金吾卫河南府承云府折冲都尉上柱国前摄左威卫郎将墨离军副使借鱼袋窦公墓志铭”(48)《窦九皋墓志》,毛阳光主编:《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版,第211页。。从题名来看,其临终所居官为承云府折冲都尉,曾摄本卫郎将、充墨离军使。窦九皋墓志题名中将“墨离军使”这一边军使职列入,可能是因为墨离军(49)《唐会要》河西节度使下记载,“墨离军,本是月支旧国,武德初置军焉”(王溥:《唐会要》卷七八《节度使·每使管内军附》,第1690页)。据相关考证,这一条可能是误记,墨离军应当是在高宗末至武后初期设立的(参见钱伯泉:《墨离军及其相关问题》,《敦煌研究》2003年第1期,第61~68页)。为长期设置的军镇,不再是事后旋罢的行军。
担任军事使职的边军武将并非都是国家正式武官,必须要有朝廷授予的武职事官。但由于边军武将长期固定在外地担任军事使职,朝廷所加武职事官实质上就蜕化成表示身份、品阶的虚衔。武职事官与军事使职在名实之间的联系,反映了唐代官制的根本特征,又在结衔方式上明显地体现出来。由此可见,武职事官阶官化现象在边军中已经普遍发生,其明显标志就是边军武官结衔的核心变成了“职事阶官+使职差遣”。
值得注意的是,开元、天宝时期使职差遣是否出现在武职事官结衔之内仍没有规律可言,也有很多武职事官兼领此类使职却不写入阶衔之中。安史之乱后,自节度使、防御使、经略使等高级使职乃至镇将、十将、副将等基层使职才稳定地成为官衔中的固定部分。本文认为,这反映了安史之乱前武职事官阶官化现象对唐代职官制度的影响仍然有限,安史之乱后节度使体制在内地普遍推行起来,军事使职数量急剧增长。军事使职发展推动的武职事官阶官化与文职事官阶官化共同造成了唐代职事官阶官化在中晚唐时期全面发展起来。相应的,使职入衔也就成为普遍且通行的做法。
三 军赏形式转变与武职事官阶官化的完成
安史之乱前,在边军和禁军中普遍产生阶官化现象的主要是中下级武职事官,而诸卫将军等高级武职事官多为员外将军、将军同正员等,正员官比较少见。表明此时武职事官尚未完全阶官化。安史之乱期间,朝廷开始滥用大将军、将军正员官赏赐军功,唐代武职事官阶官化才最终进入完成阶段。可见,唐代武职事官阶官化除了要从使职发展的角度阐释外,还必须结合军赏形式的转变再做申述。
一般认为,滥用职官赏赐军功是造成唐代职事官阶官化的重要原因。但在本文看来,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长期存在着制度上的互动影响。唐前期(除开国时期外)赏赐军功,总体上是以政治激励为主、物质赏赐为辅,金帛财货是作为政治赏赐的附属利益出现。唐后期转为以财帛赏赐为主、政治激励为辅,而且两者之间相互割裂,不同于以往研究所认为的滥用职官赏军造成了阶官化的情况,反而可能是武职事官的阶官化发展趋势使其赏军的激励效果减弱。这一方面迫使朝廷大规模地用高级武职事官赏军,最终完成了武职事官阶官化;另一方面也不断促使赏军的手段偏重财帛,军赏形式也发生了逆转。
唐初军赏以勋官为主,散官、爵位为辅,职官最为难得。得勋可以享受政治、土地、赋税和劳役等方面的优待,也可以积勋授散官,获出身后再经过番上、简选得职事官。勋官的附加利益,尤其是政治利益较大,与唐初的政治、军事、经济制度都有紧密的联系(50)参见张国刚:《唐代兵制的演变与中古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182~184页。。白身士卒一般只授勋转,能破例获得职事官者较少;有官职者多累加勋官、晋本品、赐爵位,仍不足者再升职官。用金银、钱帛、庄宅等赏赐武将的情况虽然也普遍存在,但这些显然无法与政治奖励的收益相比。
太宗时期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多是对外进攻性作战,持续时间短,间歇期比较长,因而将士积累勋劳的速度并不快。而且朝廷尚注重维护国家名器,对于职事官的赏赐尤为慎重,赏军的政治和经济优待皆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但高宗朝以后边疆形势骤变,军事行动频繁且经久不罢,严重冲击了以勋赏为主的赏军机制。比如刘仁轨给朝廷的奏疏里就显示了勋赏在长期的辽东之役过程中是如何失效的:
往前渡辽海者,即得一转勋官;从显庆五年以后,频经渡海,不被记录……显庆五年,破百济勋,及向平壤苦战勋,当时军将号令,并言与高官重赏,百方购募,无种不道。洎到西岸,唯闻枷锁推禁,夺赐破勋,州县追呼,求住不得,公私困弊,不可言尽。发海西之日,已有自害逃走,非独海外始逃。又为征役,蒙授勋级,将为荣宠,频年征役,唯取勋官,牵挽辛苦,与白丁无别。百姓不愿征行,特由于此(51)刘昫等:《旧唐书》卷八四《刘仁轨传》,第2793页。。
征行者的功勋不被记录、得勋者的特权不被承认,甚至朝廷以勋爵引诱民众而又施之以枷锁。这些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反映了勋赏机制已经无法维持的实质。唐廷不仅无法兑现勋官附加的政治、经济利益,选官途径也因求仕者众多而堵塞,勋赏基本成为一纸空文。在政治激励为主、物质赏赐为辅原则不变的情况下,用服色特权(紫绯服色、鱼袋),员外官、试官,甚至大量使用中低级武职事正员官等赏军就成为朝廷的主要手段和必须的选择。只有如此,才能使将士通过官职俸禄的形式获得物质赏赐,而不是直接发放金帛财货。而且政治特权也能抵消一部分数量的物质付出,减少财政压力。
“镇军-节度使”体制时期,唐代军事重心进一步外倾,呈现积极防御、伺机开拓的战略态势。频繁的边疆战事使得军赏需求急剧增加,军中借紫衣绯者比比皆是,得到中低级武职事官和员外官、试官的将士人数愈发众多。结合前文,可见边军中广泛形成的武职事官阶官化现象并非仅出于使职发展的正向需要,也应当归结为军赏制度惯性发展的叠加效果。若仔细分析赏军所用职官的性质,则可以更具体地发现武职事官阶官化与军赏制度转变之间的互动。
赏军所用的中低级武职事官基本都是已经阶官化的虚衔,而这并非完全是由赏功所造成的结果。开元、天宝以前用以奖赏军功的武职事官,主要是折冲府别将、果毅、折冲,太子卫率、副率和南衙郎将、中郎将等,其中又以折冲府武官最为常见。《通典》描述“哥舒翰统西方二师,安禄山统东北三师,践更之卒,俱授官名;郡县之积,罄为禄秩”,小注中说明了士卒所授的职官为折冲府武官:
按《兵部格》,破敌战功各有差等,其授官千才一二。天宝以后,边帅怙宠,便请署官,易州遂城府、坊州安台府别将、果毅之类,每一制则同授千余人,其余可知。虽在行间,仅无白身者。关辅及朔方、河、陇四十余郡,河北三十余郡,每郡官仓粟多者百万石,少不减五十万石,给充行官禄。暨天宝末,无不罄矣。麋耗天下,若斯之甚(52)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四八《兵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780页。。
唐代每个折冲府只有1名折冲、2名果毅,一次性同时颁授易州遂城和坊州安台两个折冲府别将、果毅千余人,显然只能用阶官化解释。一般认为,天宝八载(749年)停折冲府上下鱼符标志着府兵制的正式崩溃,“李林甫奏停折冲府上下鱼书;是后府兵徒有官吏而已”(5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玄宗天宝八载五月,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014页。。唐长孺则认为开元十三年(725年)征募骑之后,府兵制实际上已经不发挥作用(54)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409页。。因此可以认为,在府兵制衰落的长期过程中,折冲府武官早已阶官化;府兵制从制度上崩溃后,仍保留了折冲府武官,以继续发挥其阶官作用。至于太子卫率、副率和南衙郎将、中郎将等武官名衔,在边军中的拥有者也极为庞大,同样远远超出典制规定的员额,也应当视为阶官用法。
员外官、试官与军赏之间的关系密切,甚至其主要用途之一就是用于军功授官(55)参见杜文玉:《论唐代员外官与试官》,第94页。。开元二年(714年)五月诏:“员外等官,人数倍广,禄俸之辈,何以克周。诸色员外、试、简较[检校]官,除皇亲诸亲及五品以上,并战阵要籍、内侍省以外,一切总停……自今以后,除战功以外,非别敕不得辄注拟员外等官。”(56)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六三〇《铨选部·条制二》,第7550页。唐廷停罢了大部分员外官注拟,唯独豁免了战功一途,表明了员外官、试官与军赏的紧密联系。
员外官、试官既包括武职事官,也包括文职事官,这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高级武官以员外官、员外置同正员的形式大量授人,推动武职事官阶官化进一步发展。天宝十三载(754年)二月,安禄山曾向朝廷大量奏请赏官。“安禄山奏:‘臣所部将士讨奚、契丹、九姓、同罗等,勋效甚多。乞不拘常格,超资加赏,仍好写告身付臣军授之。’于是除将军者五百余人,中郎将者二千余人。”(57)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玄宗天宝十三载二月,第7043页。显然这些将军大多数都是员外官。与之类似,次月哥舒翰也同样邀赏,“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破吐蕃洪济、大莫门等城,井牧九曲,其将咸来策勋,翰采摭具奏”(58)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一二八《帝王部·明赏二》,第1534~1535页。另可参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玄宗天宝十三载三月,第7045页。。此次赏功涉及的陇右13名高级武将,均授予中央诸卫员外大将军衔。另一方面,文武职事官的阶官化进程互相联通。唐后期的武将普遍加领文职事官衔,大历元年(766年)所立《李宝臣碑》的碑阴即详细记录了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以下使府文武僚佐的职衔(59)参见《大唐清河郡王纪功载政之颂碑》,沈涛:《常山贞石志》卷一〇,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3324~13329页。按,此碑简称《李宝臣碑》。。其中记录了大约50组较为完整的武职僚佐职衔,武将几乎都加有试卿监衔。但作为文职事官阶官化的主要形式,员外官、试官、检校官、兼宪官等在开元、天宝年间已经少量用于赏赐军将。如天宝八载哥舒翰以战功“拜特进、鸿胪员外卿,与一子五品官,赐物千匹、庄宅各一所,加摄御史大夫”(60)刘昫等:《旧唐书》卷一〇四《哥舒翰传》,第3213页。。
在战争形势和军事制度都发生了变化的情况下,唐廷仍维持以政治赏赐为主的军赏机制,就不得不面对持续性的品位泛滥,散官、勋官、服色特权、员外官、试官、检校官、宪官无不如此,即所谓的“传统政治中名号位阶往往趋于猥滥”(61)阎步克:《“品位-职位”视角中的传统官阶制五期演化》,第9页。。职事官一旦作为品阶,也不可避免地加速其自身的阶官化进程。由此而来的沉重俸禄负担,更使得以政治赏赐为主的军赏机制不可持续。这一切都预示着重大变革即将到来。
安史之乱猝发,肃宗朝廷偏居西北,与主要贡赋地域隔绝,转运路线短时间内也无法畅通。唐廷能借以收拾人心的只剩下官爵名位,甚至附带的政治地位和俸禄收益也一概无法兑现。由此,唐廷最终毫无顾忌地将高级武职事的正员官用以赏功,文职事官的检校官、员外官、试官也同样大规模用于军赏。
是时府库无蓄积,朝廷专以官爵赏功,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自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下至中郎、郎将,听临事注名。其后又听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异姓王者。诸军但以职任相统摄,不复计官爵高下。及清渠之败,复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轻而货重,大将军告身一通,才易一醉。凡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仆衣金紫,称大官而执贱役者(6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唐肃宗至德二载四月,第7141~7142页。。
在失去俸禄等附加收益后,中低级武职事官及其他惯用的政治赏赐已经失去吸引力,唐廷只能拿出更高级的官爵名位。即便如此,失去了经济收益的空名化官位也泛滥得一文不值,所以才出现了“大将军告身一通,才易一醉”的极端景象。安史之乱后,朝廷官爵名位的价值虽然有所恢复,但武职事官阶官化确乎已经在极端环境的推进下不可逆转了。
四 余 论
职事官阶官化是唐宋时期官制发展的主要趋势,但并非所有职事官都是在唐代已经演变为丧失职事的寄禄阶官。唐后期的部分南衙政事机构及其职官仍然在发挥本职作用,职事官基本全部阶官化要持续到五代、北宋时期。但是,武职事官是在唐代就已经较为彻底阶官化的部分。
在以府兵制为基础的兵役制度长期衰落的过程中,因兵源问题导致禁军和边防军备体系的正常运转都逐渐困难,募兵制成为主力。随着战争形势的转变和军事制度的改革,军事使职在唐代军队中日渐繁盛,而从中央禁军到地方的武职事官都基本丧失了职事。尽管唐德宗时期一度试图在北衙禁军中恢复武职事官的职权,但自柏良器被排斥后这一努力也最终失败(63)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第449页。。不过武职事官阶官化并非唐代独有的问题,从长时段观察可以发现,中古武官制度就是在不断阶官化的推动下持续发展。唐代武官制度继承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阶官化发展的成果,又通过两次阶官化进程开启了唐宋武官制度的变革。
秦汉时代的武官名号,乃至西魏新创的府兵军号,魏晋南北朝以来已经完成了一次阶官化,成为唐代散官和勋官序列的历史渊源(64)有关唐代散官、勋官研究,参见本文开始部分的整理。有关府兵军号的阶官化,参见熊伟:《北周府兵军号阶官化的政治过程与意义》,《山西师大学报》2015年第6期,第84~88页。。阎步克认为,北周、北齐克服了自汉末魏晋以来名号、散官委积泛滥的“弊端”,发展出了职位、品级及文武阶官相辅相成的新体系,至唐代而成为一个总结。“唐代文武散阶的产生及其与职事官品的配合,标志着一个重大演进的完成:汉代‘禄秩’那种以‘职位分类’为主的单一等级,已经演变成为以‘品位分类’为主的复合体系了。”(65)阎步克:《周齐军阶散官制度异同论》,《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28页。在散官与职事官配合的体制下,唐初武官形成了以“武散官+武职事官”为核心职衔。
为补充职官制度运行的需要,唐初武职事官广泛担任各类使职。在唐代使职发展和战争形式转变的背景下,武职官出任的部分使职都有了长期化、固定化的趋势。由此造成的官、职分离促使武职事官阶官化较早地发展起来,唐代武官职衔的核心组合转为“职事阶官+军事使职”。赏军形式变化的影响叠加后,又使得武职事官与文职事阶官化联系起来,程度加深,影响扩大。安史之乱期间,唐廷因物质赏赐匮乏而滥授高级武职事正员官,武职事官至此彻底阶官化。正如张国刚所说,“职事官的阶官化与使职差遣的普遍化、固定化是相为表里的”(66)张国刚:《唐代阶官与职事官的阶官化论述》,第87页。。
邓小南指出了唐代职事官与使职差遣并立的制度根源,“隋唐以来,职事官系统与散官系统的并行,从制度上明确了治事系统与品阶系统的分立。而在此基础之上,职事官体系内部,又发生着进一步的复杂变化,并从而产生了以‘职事官’与‘差遣’相分离为特征的设官分职方式”(67)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4页。。因此,可以认为武职事官兼领使职差遣导致职、官分离,进而发展为阶官化,本是唐代职官制度设计所致。
安史之乱后,藩镇的节度使府僚佐体系成为地方最普遍的统兵体制。藩镇的武职僚佐体系为了满足赏功和叙阶的需要,又出现新的阶官化趋势,也就是军事使职的阶官化。武职事官阶官化与军事使职阶官化构成了唐代武官阶官化的两个周期。它们的叠加发展一直持续到五代十国,使得武官内部发生了群体分化,最终形成了宋初复杂的武官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