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将如何演变
2024-03-28郭晔旻
郭晔旻
《演变:西方政治的新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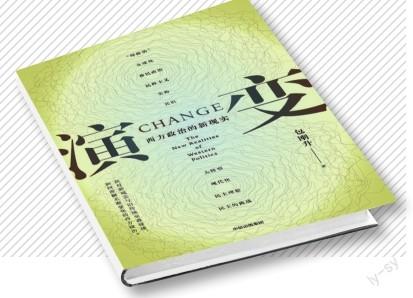
如果要评选近年来的西方政治“明星”人物,唐纳德·特朗普一定是个知名候选人。2016年时,这位纽约富商以政治素人的身份击败老派政客希拉里·克林顿而入主白宫。尽管在2020年连任美国总统失败,特朗普依旧不甘寂寞,时不时冒出惊人之语。到了2024年,这位前总统更是俨然有卷土重来之势。
特朗普何以成为美国乃至西方政治舞台上的焦点人物?这正是包刚升在其著作《演变》中所企图回答的问题之一。正如作者在书中后记所言,《演变》是“我过去几年所写的12篇学术论文、学术演讲稿与书评文字的合集”,“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从政治理论与比较政治学的视角来理解现代民主的运作及其面临的挑战”。
实际上,特朗普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与之相类的还有法国国民阵线的领导人玛丽娜·勒庞,以及德国的选择党(AfD)。这些政治人物或党派有其共同点,即坚持本国优先、部分地反全球化、严格限制外国移民以及警惕本国人口的伊斯兰化。
在大众的普遍认知里,这类政治人物的崛起,意味着欧美民粹主义的兴起。但《演变》一书却指出,“大家认为的民粹主义很多时候只是伪装了的现实主义。在民粹主义的表象之下,其实是政治现实主义与大众政治的联姻”。在作者看来,“希望新当选的政府首脑或议会不断提供廉价食品、廉价汽油、免费住房以及各种高福利,甚至最好政府能够免费提供一切所需”是典型的民粹主义现象。如果按照这一定义看美国政坛,主张全民医保计划、大学教育免费的民主党的左翼政治家伯尼·桑德斯,似乎要比给富人减税的特朗普更符合“民粹主义”政治家的定义。
因此,《演变》一书提出了“政治理想主义(自由道德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的概念。在作者看来,“从康德到美国《宪法》,从《世界人权宣言》这样的文本到如今我们习惯于把西方民主视为多头政体,都可以被视为政治理想主义传统的一部分”,“这一原则主张人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一员应该平等相处,而不应该以种族、族群、宗教、财富等身份差异而彼此有别,更不应该因此而互相冲突”。与之相对的则是“政治现实主义”,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里。在他看来,政治与道德是互相剥离的,政治就是政治,政治不是道德,不是伦理。
而在二战结束以后的70年间,即1945—2015年,“西方世界的主流政治家和思想家更多地被政治理想主义传统支配”。“对秩序、保护、安全、信任和合作条件的保证”曾被政治思想家威廉斯视为基本的政治问题,但对二战后的欧美主要国家来说,这一基本的政治问题已经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战和二战记忆的新一代欧洲人和美国人”的关注度,逐渐从物质文化转向“环保议题或绿色政治议题、性别政治议题或女性权利问题、同性恋议题、堕胎问题等”。
如果欧美一直是个长期和平、安全无虞的“政治温室”,这样的情况继续持续下去自然。但“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政治后果”,极大冲击了欧美的政治平衡。在作者看来,全球化带来的穆斯林移民浪潮,使得欧洲的人口与宗教格局发生了引人注目而不利于本土人口及宗教(基督教)的多样化:“在高度移民条件下,2050年欧洲穆斯林将占欧洲总人口的14.0%。”“随着这部分新的‘主权者的到来,他们完全有可能成为重塑民主政体下政治规则、政治观念与公共政策的新力量。”“这就导致了一個悖论:一种政治文明因为高度文明化,反而在文明程度较低的‘硬政治面前失去了保卫自身的能力。”
另一方面,“全球化过程中欧美国家制造业部门就业机会的缩减,给特定的社会阶层(工薪阶层与中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自由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主导的全球化使西方世界产生了一系列利益受损的要素、部门乃至国家”。这容易理解,资本可以进行“逐底”而远去他乡,但劳动力要素却不能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而且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即便能够流动到资本前去的发展中国家,也不见得能够接受当地的工作与生活条件。
因此,作者提出,“当一个人没有工作机会,要求国家采取某种政策保护自己的工作机会的时候,不能说这样的诉求就是民粹主义;当一个普通公民感知到周围异族移民大量增加、处在恐怖主义袭击新闻报道的恐惧情绪之中,要求限制外来移民的时候,不能说这样的诉求是民粹主义”。这些诉求不过是向政治现实主义的回归。而特朗普(们)的成功,正是在于“率先发现了这一尚未被传统主流政党满足的选民‘蓝海市场”— 2016年特朗普之所以能够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关键原因正是在于赢得了五大湖区域“铁锈州”的选举人票。
那么,为什么特朗普能够一度赢得总统宝座,而德国的选择党在议会中始终处于孤立而无缘执政呢?作者认为这与各国不同的选举制度有关。在政府首脑选举制度上,总统制或半总统制下的直接选举更容易导致新政治家的崛起。因为在总统直接选举制度下,总统候选人只需要在一场简单多数制或两轮选举中获胜即可。
而在议会选举中,“多党制的国家,其主流政党越容易受到原先选民阵营和政治立场的束缚。因此,新的右翼或极右翼政党更容易在这样的国家崛起”。因为“当实行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时,一个富有魅力的政治家外加一个富有号召力的政治纲领,往往很容易帮助一个新兴政党的快速崛起”。这也就是为什么特朗普能够“横空出世”却仍然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当选总统,而德国的两大主流政党(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议席却在被选择党蚕食的原因所在。
无论作为政客还是政党,这样的新兴或曰另类政治势力在欧美政坛的崛起,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民选领导人会否威胁民主”。其实从历史上看。阿道夫·希特勒就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担任德国总理,进而毁灭了魏玛共和国而成为独揽大权的第三帝国“元首”的。实际上,“早在2000多年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民主政体的重要威胁来自德谟咯葛(demagogue)”。“德谟咯葛往往是极富煽动力的政治人物,他们善于许下许多动听的诺言,取得一大批轻信群众的追随”,这一点倒是很容易让人想起特朗普及其“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
德谟咯葛一般被译成“民粹领袖”,但如同作者之前在书中提到的,“民粹”一词并不太适用于特朗普。但今天人们可以看到,身为一介平民的特朗普竟可以遥控美国共和党在国会中的决策。在他身上,倒是的确印证了《演变》中对“德谟咯葛”之所以能够崛起的解释:“本来,如果所有主要建制派都选择排斥德谟咯葛和极端派,后者就无法获得在权力中心崛起的政治机会”,但“正是主流建制派的背书,使德谟咯葛得以获得从权力边缘切入权力中心的政治机会”,而“德谟咯葛的特质决定了他们一旦获得机会,就会反过来胁迫或控制建制派,甚至干脆消灭建制派”。
不过,按照《演变》里的描述,“德谟咯葛想要取代民主政体,需要跨越两个关键障碍:第一,德谟咯葛要通过选举完成从一般的民粹活动家到实际的掌权者的转变;第二,已然实际掌权的德谟咯葛还要采取一系列手段来削弱民主政体下各种支持民主的力量、机构与制度,最终完成完全的去民主化”。以此看来,现在就预言某个当代“德谟咯葛”将会颠覆欧美国家的代议制民主制度似乎言之过早。更值得注意的倒是作者在《演变》一书中对欧美政治前景的判断:“如果沿袭20世纪60年代以来流行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西方自由民主政体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只会继续恶化”,“西方国家在移民、边境、族群、宗教的内外政策上很可能会转向更加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立场”。
2024年是个“超级选举年”,全球6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多亿人口(超过全球人口的一半)将投票选出新的立法机构或行政首长。其中对世界影响最大的美国大选将于2024年11月5日举行。人们可以拭目以待,西方国家的政治格局,是否会发生趋向政治现实主义的“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