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是一个清晨
2024-03-22沈念
沈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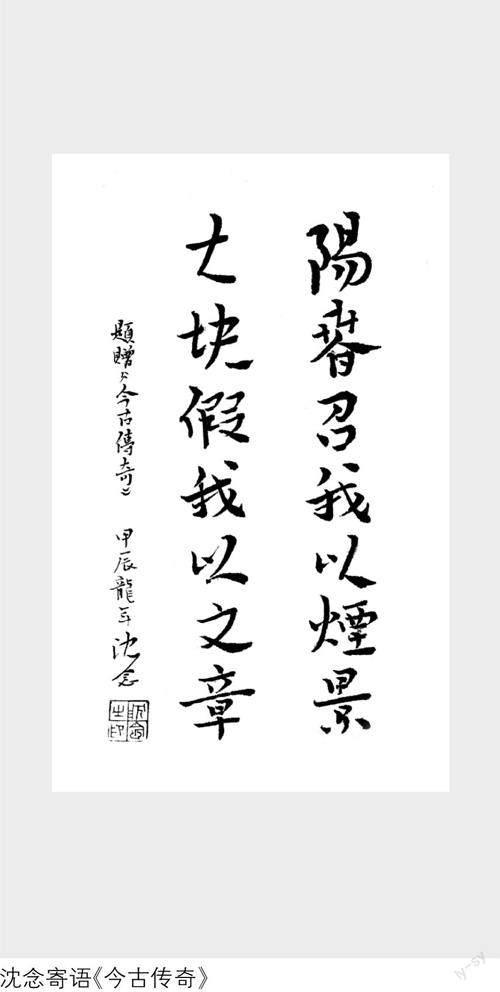
真正意义上对生态文学的关注,是在我写作并出版《大湖消息》之后。我在有的评论和采访,都会谈到这个话题。但是在我写作之初,我的意识深处,并没有想到我是在写生态文学。
那我写的是什么呢?我写的是洞庭湖这片土地上的人和动物、植物,是人的命运,也是动物植物的命運;是人的精神,也是物的精神。那我可以说,生态文学在我的写作理念里,就是生命文学。要表现的是人和万事万物在自然天地间的命运,思考的是环境危机、生态危机下的社会根源和人的缺陷,表达的是人与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期待和基于生命本质平等之上的文学审美。
多年前看过法国导演雅克·贝汉执导的一部自然纪录片《迁徙的鸟》,以及美国导演大卫·弗兰科尔执导的《观鸟大年》,倒是给过我震撼和灵感。前者拍的是各种候鸟为了生存而南迁北移的艰难旅程,从寒冷的北极到炎热的沙漠,从深邃的低谷到万米高空,不同鸟的境遇和生命危机。该片于2001年12月12日在法国上映,影片的解说只有不到五百字。后者是改编自1998年马克·欧布马克西的同名小说,讲述三个男人竞争观看一种稀有鸟类的故事,是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出品的喜剧片。这两部影片有两个关键词:生命和情感。
但有什么写作不是在写生命写情感呢?就创作而言,语言、结构、叙事等等技巧都是可以学的,唯有情感体验、生命遭遇、欢乐与悲伤是学不来的,因为情感属于独立的生命个体,是无法替代的。我所写的《大湖消息》之所以有真切动人的基础,那都是来源于生命的经历和情感的积淀。从生命和情感来谈我为什么写这部作品,具体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说一说。
首先,我从小在洞庭湖、长江边长大,处理江湖关系成了一种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我出生在一个小镇,傍着一条叫藕池河的河流,属于围湖造田地区。整个县城,或者说湖区的人们有他们的生活方式,不会考虑盖多好的房子添置多好的物件,吃穿用度大手大脚;人们喝早酒,吃夜酒,无辣不欢,以此驱逐体内的湿气;人们习惯了洪水肆虐,习惯了你抢我夺,习惯了一无所有又从头再来……人与湖的关系就是人与水的关系,人与湖的矛盾,也是人与水的矛盾。20世纪的洞庭湖围垦史,就造成了今天的湖区面貌,也是洞庭湖区历史的一个缩影。这片土地上的变迁,人的生活变迁,都深深地影响了我并成了我的一种生命经验保存下来了。当我写作之后,发现我其实是在处理这片河汊众多、江湖川流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地方性格、地方经验和地方故事。从自己生命的根据地长出来的文字,本身是有情感浸染的,能迅速激活读者心中沉潜多年的故土记忆。一个人的根长在这里,他的写作也就必然带着这里的气息和味道。所以说,一切的写作,每个人背后却有着自己的精神谱系。这个精神谱系,就是不断地重申那些从故乡而来的古老信念。
其次,我做记者的经历,让我从经济社会民生的层面了解了洞庭湖。我做了八年记者,多次深入洞庭湖。当你进入到湖区更多次,与湖上的人交流更深,情感就会越深,你又会对他们产生一种新的观点,他们有和我所理解不同的喜怒哀乐,他们是经历过风浪的人,是在水流之中获得生命的力量。比如那些多少年在湖上的渔民都是“天吊户”,他们没有户籍,也不是农耕文明的农民,而是沿着水流四处飘零的人,他们所赖以生存的是真正的江湖世界,他们是本源上的江湖儿女,他们的流动性所孕育出来的地方性格,走到哪里,就传宗接代在哪里。有一部分湖区文化,是依靠渔民在随波逐流,愈行愈远的。他们相信神意、邂逅、善良、浪漫,有把自己交付给陌生人的勇气。他们的命运,经常会让我心中流淌感伤、悲情,也流淌感动、豪迈。
我对洞庭湖和湖区人的认知也是在这种返回的过程中变得深刻的,你对它越熟悉,越了解它的过去、现在,你就会越关注它的未来。这从另一个层面说明,去过一个地方,对这个地方有深入的了解,积淀了一定的经验和情感,就有了现场感,你去谈论它,感受它,回忆它,写作它,就会不一样。现场有神明,其实也是谈经验和情感的形成。所以尼采说,一个好作家的身上,不仅有他的精神,还有他朋友的精神。我想说,一种好的写作,不仅有人的精神,还有物的精神。要写出这种精神,情感是重要的因素。
再次,每年的冬季水鸟调查,保护区工作者和志愿者的艰辛、湖区生态变化引发了我的思考。我在古罗马奥维德的长诗《变形记》读到一则王子厄律西克的神话。厄律西克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掘地者”。他拼命地不停歇地砍伐森林,盖成片的房屋,扩大自己的耕地。神对这位掘地者自有惩罚,就是让他永远有一种吃不饱的感觉,让他有着无穷无尽的欲望。他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满足吃的欲望。当他找不到任何可吃之物时,让他用锋利的牙齿咬啮自己,用自己的身体来喂养自己。
我在冬天洞庭湖空旷寂冷的湖洲上,就在想,这个时代里的“人们”是不是现实版的“厄律西克”?只要当你置身那片被“占有”和“掠夺”过的土地,听知情者讲述被破坏的事实和影响,你一定会这样去想。这些年过去,我还有一个认知上的改变,原来以为岸是水的疆界,但在行走中我懂得了水又是没有边界的,飞鸟、游鱼、麋鹿、茂盛的植物、穿越湖区的人,都会把水带走,带到一个我们未曾想到达的地方。
最后,我想强调写作中的人。人是生态文学书写的主体,也是对象。人作为大自然的主宰者,并不代表人可以肆无忌惮、肆意妄为,人的命运其实是与自然万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万物是一体的,天地本是一个有机整体,写下生态文学经典之作《沙乡年鉴》的利奥波德说:“我们蹂躏土地,是因为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属于我们的物品。当我们把土地看成是一个我们隶属于它的共同体时,我们可能就会带着热爱与尊敬来使用它。”
山可平心,水可涤妄。山水自然教诲我们做简单的人。简单的关系,才是和谐关系。我觉得,好的生态文学写作一定是建立在真切的情感和真实的生命体验之上的。面对自然万物,看到什么,想到什么,你的思考广度有多广,深度有多深,通过倾注情感的语言浸润在作品中,情感有多重,就会有多重的生命的重量,也才会有千姿百态的文学呈现。
生命只有一次,未来也许只是一个具体的清晨。生命是有时间长度的,真正的生态文学是扎根,是在这个长度里,完成生命和情感的转化和创造。
(责任编辑 丁怡1596371626@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