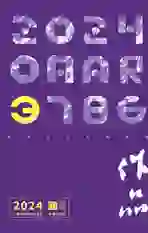现实与幻境之间(印象记)
2024-03-19水笑莹
水笑莹
《收获》杂志六十五周年庆典后,我在回去的途中碰到了幸逸,恰好是晚饭时间,我们便在小巷子中寻找饭馆。虽然同是创意写作专业的学生,但因为差了一级,算起来那还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当时他的脑袋后面扎了一根细细的小辫儿,头发未到及肩的长度,不能算留长发,但因为有了这根小辫儿,也确实不属短发的范畴,现在想来,这大概就是幸逸的个人特色吧,总是在规则之外有一两处不甚明显的“旁逸斜出”。
那时候是五月末,上海的热天还没有正式到来,但春天已经结束得很彻底了,路边不少饭馆挂上了售卖“麻辣小龙虾”的招牌,庆典上演奏的交响音乐我早已忘记,麻辣小龙虾的气味却记得很真实,当时同行的还有我的两个学妹,原本以为同三个女生一起吃饭,作为唯一的男生的幸逸会感到不自在。但事实证明是我多虑了,他跟我们聊天的时候没有任何隔阂,关于毛豆和红烧肉的做法他似乎颇有心得,感叹这边吃毛豆只知道炒或者煮,如果加上虾子和豆干做成酱,冬天也能食用。红烧肉嘛,大可不必加那么多南乳汁和糖,肉本身的味道最重要。在他的描述中我才发现,关于吃食,我们有着很接近的个人记忆,这种记忆来自于我们家乡地理位置上的接近。
我与幸逸算是同乡,虽然来自不同的县,但都属芜湖市管辖。因此,幸逸在小说中使用的方言,对我来说异常亲切,例如《登仙》中出现的“家奶奶”“清清丝丝”等词语。但幸逸关注的焦点似乎不在某一地、某一城或者某一时代,历史事件、地域色彩仿佛只是为他的表达所服务,他有着更高的视野和追求,不会让已经被定形定性的文学类型所框定。读他的小说,我总能在文本中找到熟悉的身影,《异闻》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罗马玫瑰》则能看见伤痕文学的印记,然而他自有一套自己的处理方式,将新的因素加在文本之中,于是我们能看到他的语言和叙事与既有的文学类型呈现出某种“斜出”的倾向,这是属于他的浪漫化的表达方式,正如他脑袋后的那根小辫儿。
也正是那次在饭桌上的闲聊,我知道了他在本科期间就有写作的经历,读研后,他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学术研究上,这或许也解释了他在写作中总是有意识地将现存的叙事方式进行扩展,赋予新的内容。他写的人物几乎总是处于一种“中立”的“思考者”状态,因而其行动总是表现出延宕和踟蹰,这或许也与他平素的思考习惯有关,是一种文人学者式的写作方式。我总是期待能够在他的小说中看到形而上之外的更为鲜活的生活,例如初看《登仙》,我期待能够看到一段家族史,但转念一想,单纯的家族叙事或许从来不是他的追求所在,但无论如何,《登仙》中涉及了大量他熟悉的生活情节,他从中展现出了很好的对现实细节的把握能力,我相信如果他志在处理现实议题,也能够写得很好。
后来有一次与幸逸再碰头,巧的是依旧是晚饭时间,他依旧点了红烧肉,这次的红烧肉在我看来,比上一次的更甜,他也似乎习惯了上海红烧肉的口味,又或者是因为当时他有着更加紧迫的任务——撰写毕业论文和申博,所以无暇评价食物的口感。他跟我讲了他想要研究的方向和志趣所在,在他看來,小说大可不必只展现现实,又或者说,在一个写作者的写作初期,可以尽情去尝试一些新的写作方式。他坦言自己对“江湖世界”本能地有一种抗拒,因此读博是他最理想的选择,正如《登仙》中的孩童,期待一面镜子中的幻境,却迟迟不愿进入现实的成年人的世界,学院生活某种意义上来说,又何尝不是一个“幻境”呢?但与我不同,幸逸是一个甘愿活在文艺花园的“幻境”之中的人。
如果再年轻几岁,我可能会在饭桌上和他争论,告诉他世界的底色还是他口中的“江湖世界”,我的文艺梦早早地结束于一段段工作经历,但转念一想,在毕业那么多年后重新回来读书,我真的是像自己想的那样,那么适应外面的世界吗?不过他或许已经说出了自己的顾虑,在谈到三岛由纪夫时,他说:“三岛认为太宰懦弱,或许正是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懦弱的人,因此害怕面对另一个懦弱的人,强烈的爱和恨原本就是很接近的情感。”——他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只不过经过对自我的剖析,他认为自己还是适合待在学院,这并不意味着“懦弱”,至多是有一丝丝的“胆怯”,像Sekai No Owari乐队在Starlight Parade这首歌的MV中所表现的那样,一个男孩半夜醒来,骑车来到户外,旁观外面的一场狂欢,但最后还是回到了安稳的睡床上,第二天继续过自己的生活。“胆怯”是一只想伸出去却又收回的手,是每个人对自己人生轨迹之外的世界的一种复杂情感,这种“胆怯”,在他的小说中延伸出了一种对现实情节的刻意规避取向。
在我看来,幸逸在小说中编织材料的方式大多基于现实状况,但总是会不自觉地滑向浪漫的语境中去。通常意义上来说,现实的引力越强,浪漫能施展的空间也越小,因为浪漫关乎对现实的逃逸和超脱,在写作中,幸逸几乎总是将天平上的砝码更多的加在浪漫的一端,现实素材也基于这一需要被作出了取舍,呈现出碎片化的倾向,即使在现实感最强的《登仙》一文中,他所塑造的坚实的家族叙事,在最后也被红楼式的幻境所消解了。在他的小说中,现实问题被解决与否或许不重要,其关注的重点仿佛永远在于,现实在主人公心灵中投下的阴影,以及由此展开的哲学思索。
他认为《忽闻歌古调》是他最“现实”的小说,同他一样,小说的女主人公出身于小城的背景,在大城市过着一种彷徨的生活,她对一切现实而坚固的东西本能地持怀疑态度,除了从异性身上偶得的慰藉,她几乎总是会耽于孤独的幻梦之中。
但在我看来,与《忽闻歌古调》相呼应的另一篇,却是最不“现实”的一篇——《罗马玫瑰》,虽然两者故事发生的年代背景不同,但主人公所呈现出的精神面貌却惊人的一致。《罗马玫瑰》用一系列的隐喻(如人物的名字)告诉读者“我”所处的时代背景,彼时“我”和千千万万个体一样,处在时代的十字路口,“站在红绿灯前”等待的工夫,“我”已经对未来进行了一番思索,是像老右一样南下闯荡,还是对得起自己“赵红卫”的名字去当人民教师,这一短暂的对现实的考量、纠结,实际上并没有被赋予意义。与“伤痕文学”作品中对惨痛历史经验的回顾不同,幸逸将小说的重点放在“我”对“维纳斯”的追求上,在追求爱的同时,“我”于是也体会到了宏大主题下个体的失落、伤感、迷惘等诸多情绪,直到最后,在老右的点拨下,“我”才知一切皆是幻梦,连那枚曾让“我”无比坚信“维纳斯”是真实存在的人的戒指,也一同消失了。主人公几乎总是处于一种“仰望”的姿态,仰望罗马,仰望维纳斯,仰望一些可能并不存在的幻梦,于是便成了一个“走不好路的人”,成了一个“摇来晃去的人”。
这种失落的感觉,在《忽闻歌古调》中得到了延续。与《罗马玫瑰》中被高度抽象化的北京城不同,《忽闻歌古调》中的上海要具体得多。或许是因为幸逸目前正生活在上海的缘故,他捕捉到了这座城市对浪漫的碾压,“她”总是耽于形而上的东西,“他”虽然也有浪漫的一面,但在现实中,想的也只能是成家立业之类的事,彼此唯一的连接在于对性的需求。故事的最后,他们同时听出来《忽闻歌古调》,“难道我们正爱着彼此吗?”是故事的结尾,它既是对爱情的质疑,又是对“爱的瞬间”的肯定,它是在上海这座超级城市以及人生现实问题的重压下,逃逸出的一丝爱情的气味。它若有似无,也可能很快会消散,故事在这里结束,琥珀一般保存了这个瞬间。幸逸擅长制造这样的“琥珀”,事实上,假如他能继续写下去,我毫不怀疑有一天能在他的小说集中发现一座琥珀花园。
在现实与浪漫的“拉锯”之中,幸逸几乎总是耽溺于孤独的思索和浪漫的想象之中,正是这种特质,让他的小说超越了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抵达一种他渴望的境地。目前看来,对这境地的营造,正是他所努力的方向。作为读者,我天然能够更好地接受与现实相关的部分,而那幽深的幻境,则是不可名状而难以捉摸,如雾的形状、闪电的轨迹,然而作家真正要做的努力,可能正是在于捕捉那猫舌一般舔舐窗棂的雾的瞬间意向、闪电划过天空的瞬时蓝光,正是这些短暂的瞬间化无形为有形,文学文本亦具有相似功能。期待未来在幸逸的小说中,能够看到一座属于他的幻境花园,那里陈列着他精心挑选的一枚枚琥珀。
责编:郑小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