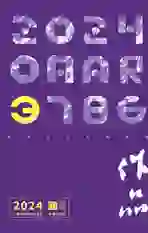仰面看羽痕:古典兴味与现代小说(访谈)
2024-03-19奚榜王幸逸
奚榜 王幸逸
奚榜:王幸逸你好,作为被读者关注的正在冉冉上升的青年作家,你可以向读者用王幸逸特有的方式,详细介绍下自己的文学之路,以及各方面的近况吗?
王幸逸:老师您太抬举了!“被读者关注”“正在冉冉上升”“青年作家”,这三个词好像都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只是偶尔学着写几篇小说的普通人。文学是从小就热爱的,但是县城图书市场很小,除了语文老师推荐的经典,也不太知道哪些是好书。高中时写过几篇小说,但很不成熟。系统阅读当代文学作品,是刚读大学时候的事。那段时间真是各种文学狂轰滥炸,非常快乐,从汉魏六朝诗到莫言余华苏童,从雨果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到马尔克斯波拉尼奥科塔萨尔,看得特别杂。有两个月我集中读日本文学,从《平家物语》《源氏物语》到夏目漱石和谷崎润一郎,读进那种氛围里去了。自然而然,就在那样的氛围里作出一篇小说来。记得那是2019年夏天,一万字出头的篇幅,我花了三四天写出,之后投给中山大学中文系举办的广东省大学生原创文学大赛,就是现在“逸仙文学奖”的前身。后来,这篇小说很幸运地拿到了小說戏剧组的一等奖,并且承蒙《作品》杂志的赏识,发在次年《作品》的“网生代”栏目上。这也是我第一次在文学期刊发表作品,给了我很大信心。可以说在那之后,我才产生了“我可以写小说”的认知。《作品》杂志近几年一直在不断帮助文学新人,十分感谢。小说发表后的一年多时间,我的精力转移到学术方面,开始阅读文学理论和研究著作,小说创作方面就基本暂停了,直到2021年我到华东师范大学的创意写作专业,得到老师们的帮助和同学的鼓励,又开始了小说写作。我目前研三,未来计划在本校读博,在学术研究之余,继续我的小说写作。
奚榜:看了你五篇小说《胧月夜》《罗马玫瑰》《异闻》《忽闻歌古调》《登仙》,发现不仅题材从古代到抗战到“文革”到现在都有,其语言以及处理方式都不一样。我还注意到你还会写科幻、评论、诗歌等,你这样全面开花,风格各异,是一种顺其自然,还是某种刻意的探索呢?能具体说说你写上述作品的缘起、困厄,以及回头再看的感受吗?
王幸逸:顺其自然,许多事感兴趣就去做了,个中联系我没想过,想得太清楚反而无趣。关于各部作品,让我按时间顺序先后说明一下吧。最早的是《罗马玫瑰》,初稿2017年就写出来了。当时正好放假,宿舍只剩我一个人,第二天一早我要赶高铁,从广州南站回安徽。越急着睡偏偏越睡不着,脑子里开始出现故事情景。那时候读多了王小波和王朔,连我脑子里的描述语言都是京腔,于是一个句子,又一个句子,怎么也停不下来。我就打开手机,躺在床上一口气写了下去。这么写着写着,就写出了小说开头的两千多字。这时候天也亮了,我就起床收拾。我后来很快就写完整篇小说,发给几个朋友看过之后,就放在电脑里摆了好久。以后我加入话剧社,忙着排练和读书,几乎不怎么写小说,直到2021年才把这篇稿子重新拿出来看,觉得简直不是自己如今的语言和思维能写出来的。不足之处也有很多,比如对当时的北京不了解,历史背景其实算很虚浮,但回头看,我作为自己多年后的读者,会感动于结尾那声“无所谓啦”。读到这里,我想起了很久没有读过的王小波,想起他的作品给我带来的感动和震荡。对这篇早年的作品,我只做了很少的修改。我认为,它是曾经的我献给王小波先生的花环,今天的我应该没有权利去大改。《异闻》的创作契机,其实是来自对三岛由纪夫的阅读。2022年,我集中读了《潮骚》与《金阁寺》两部长篇小说,觉得前者沉静而后者动荡。过分沉静未免纤弱,过分动荡又至于癫狂,以至于《金阁寺》的故事本身几近崩毁。整体来看,我还是更喜欢《金阁寺》,但我尝试将静美的因素引入其中,中和那股过分邪躁的美学气息。在静美和癫狂这方面,我也吸收了沈从文先生从《边城》到《七色魇》若干作品的有益营养。尤其是《边城》,静美而富有生命力,比《潮骚》好太多。写这篇小说时,我在确立语言方面花了不少功夫,呈现效果还算是有特点,但故事讲得太简单,情节改编上也没什么出彩的地方,可能练笔的意义要多一点。写完《异闻》,我又对一个或许并不为大众熟知的人物——尾崎秀实,感兴趣起来。《胧月夜》设计一个美国记者的叙事视角,一方面以叙事人物的犹疑,配合小说整体的朦胧感,另一方面还可以造成一点隔膜感,为我本人于历史知识方面的欠缺提供点合理性。必须坦白的是,小说写到后面几乎变成对白体,这是我把自己驱进绝境,只好将错就错写下去了。当时结构故事的本领,还是太拙劣。我对历史和政治方面所知有限,更感兴趣的是,怎样用审美的眼光探寻尾崎这个献身于国际解放事业的人物,就像小说主人公所思的那般:“如果说过去在上海结交的尾崎,是我于野林漫步时偶然发现的新苗,那么事件中的尾崎,则已臻花满叶涨之盛。即使其后受狂风摧残,飘零四落,依旧具有夺魂摄魄、不可思议的美丽。”对美国记者与日本军国政府来说,这种“不可思议的美丽”当然带有强烈的异质性,因为那是属于革命者的美丽。或许与尾崎同代的中国革命者,更能够领会这一点吧。《登仙》和《忽闻歌古调》都是2023年夏天写的。《登仙》最初是受《宇宙探索编辑部》这部电影的启发,想写个外星人绑架的伪登仙故事。小孩子眼里的大车其实是宇宙飞船,昆仑山则是外星球。后来推敲大纲的时候,反而把这个最初想法删掉了。我想,干脆别去谈“登仙”的真相是什么,我们就当它是一场梦吧。为了写好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细节,我还找我父母询问了不少信息,他们过去就是氮肥厂的职工。当然,我的父亲并没有像故事里那样消失(笑)。《忽闻歌古调》尝试写当代的鸳鸯蝴蝶派故事,只是呈现出来的,或许是秃头鸳鸯和僵翅蝴蝶……尽管为了写好女性叙事者,我特意集中读了很久张爱玲、朱天文和当代韩国女作家金爱烂的小说,但可能我还是不太会写爱情。这两篇小说完成时间离现在最近,所以我目前还没有形成比较客观的认知距离,但我觉得还是《登仙》有趣一点。
奚榜:看《胧月夜》,想起在十几或几十年前,中国文坛的权威都曾特别谈到过生僻知识能让小说厚重的问题。如今信息爆炸,读者也可以轻易获得生僻知识,那么,对于小说来说,生僻知识与语言、人物形象等之间的比重,你认为应该有变化吗?
王幸逸:信息爆炸带来的另一后果,是信息的碎片化,读者大众对生僻知识的接受是相当散漫的,往往注重趣味性的一面。写作者对生僻知识的摘引、构造和加工,才是生僻知识“小说化”和“当代化”的关键所在。信息碎片化造成的影响,还往往以一种效仿先锋文学和魔幻现实主义的形式,体现在当代青年写作中。如果说老一辈先锋作家用拆解宏大叙事、反抗“合理性”的路径抵达了先锋,那么在如今这个碎片化的时代,我们还能够沿用这种拆解的方式组织信息吗?或者说,在碎片化的时代使用碎片化的方式,我们还能称之为“先锋”吗?在这个意义上,怎么运用生僻知识是值得思索的。是用一种“去历史”的、高度私人化的方式,还是用一种“再历史化”的、有一定结构设计和现实对接的方式?我倾向于后一种方式,也就是说,生僻知识应该降落,应该服务于语言风格、人物形象和情节构造的因素,而不是突兀地插入和悬浮在小说里,甚至将小说写成生僻知识的胪列和“信息爆炸”。我也是在写作过程中逐渐反思到这些的,如今正对此加以注意。
奚榜:《异闻》是你改写的《聊斋志异·长清僧》,我感觉语言非常古雅,外紧内松,韵律与节奏感均在。我想起我写作之前,有一大批七〇后作家靠改写古典小说而成名,他们那时依赖的是戏仿,抵达的是解构,是對东方文化的一次集体的质疑。而你的改写又是想为我们带来什么呢?当然,我这样问,没有任何倾向。我并不主张文以载道,小说仅仅谈审美就很好了。
王幸逸:或许我和前辈们一样,也是想用旧石激出新火。本科时写过关于《聊斋志异》僧人形象的课程论文,借此机会了解许多篇僧人故事,尤其对《长清僧》感到兴味。当时我觉得,故事里的高僧要是更纠结一点,更为世俗所困,那就有意思了。在改编《长清僧》的时候,我把原文的确定性的基调改为不确定,比如少爷介于生死间的不定态,宅内的少妇很可能是狐妖,二僧间的机辩。我并不想彻底质疑和解构佛家文化,不如说,我对“东方文化”本身的复杂性和自我悖反感兴趣。老爷太太的求佛问道,仆众谈狐说鬼的世俗传奇,还有对狐妖、离魂的想象,都是东方文化的一部分。它相当驳杂,异彩纷呈,我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往里面添加这些异质性的元素,或许更能体现东方美学整体的多面性。
奚榜:《登仙》也许是五篇中我个人最喜欢的,因为它塑造的不靠谱的父母都特别形象又有新意。在处理父亲离去后的情形时,我觉得你用了特别成熟的一种方式来处理,用传说或者想象。这是非常高明的。我感受到了你在写作上的日渐成熟、松弛,塑造出很好的人物形象,并用技巧让它飞起来,走向多维指向。你能比较具体谈谈写这篇小说的过程与想法吗?
王幸逸:这篇写起来非常顺利,从脑海里有第一个画面到列完大纲,一共才花了半个多小时。从落笔到写完全篇,一共花了十天,因为设计了许多有趣的情节,写作的状态也很快乐。小标题是写到一半的时候拟的。张怡微老师的小说集《四合如意》里的篇名,都是好听的曲牌名,这启发我在小标题上做文章。我最初也考虑过选曲牌,最后还是觉得合适的太少,于是决定自己想。第一幕“云隐苍梧”,基本是“我”正式出场前的背景交代,父亲形象是怎样的,他的失踪如何带有神秘色彩,母亲的等待、失望和寂寞,等等。第二幕“青蚨目连”,“青蚨”出自志怪传说:“青蚨似蝉而稍大,母子不离,生于草间,如蚕,取其子,母即飞来。”(《搜神记》)“目连”既是指目连救母故事,又是指我家乡的南陵目连戏。这个标题已经在暗示说,家奶奶利用和鼓动“我”“拯救”母亲的一系列行动,本就是一出家庭戏。所以主要对家奶奶、母亲和“我”进行塑造。第三幕“琅嬛逢椿”,是写“我”九岁生日夜遇到登仙成道的父亲,也暗示母亲已远徙都市。这一幕已经见出家庭的分崩离析,和“我”的懵懂不知所措。第四幕“叱石谘镜”是我一早定好的结尾。我特别喜欢叱石故事的点在于,推演牧童登仙离去的数年,那些被遗落的羊群怎样将自己等候成一丛丛白石。这也是“石”与等待父亲的王磊之间的寓意关联。读者朋友或许要问:第三幕并没有写镜,下文这宝鉴仙镜是从何处来?为防此问,我提前准备了参考答案:王磊把智能手机臆想成保存万物至理的仙镜,仅此而已。但这个答案非常无趣,仅供求真务实的读者们参考。
奚榜:在你的小说中,大量用到古典的词句,与现代的气息龛合在一起,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王幸逸:这首先出于对古典美学的热爱。当然,无论多热爱古典美学,我们都是在现代中国生活着的,哪怕使用的词语和句法再怎么古奥,我们写作出来的也一定是现代小说,必须用现代的气质去引渡古典,“泥古”的态度断然不可取。这不但是一种文学观,也是作为现代中国青年必须有的时代责任心和在场感。尼采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里说过,民族历史就像大树看不见的根系,它服务于新的民族精神与现时生活。如果把根系的维持看得比枝叶的繁茂更重要,就会守固所谓本根,将新的东西当作枝节末梢抛弃掉。然而尼采说,更深刻、更崇高的正是这些枝叶开散的现时之物,“如果历史感不再是保存生活,而是将它变为木乃伊,那么大树就会从上至下不正常地枯死,最后树根自身也会枯萎。从不再给予现在的新鲜生活以灵魂和灵感的那一刻开始,怀古式历史就退化了。”怀古之人就在疯狂收集旧尘土的过程中,将古人真正宝贵的精神创造力,降格为对古旧事物的好奇与占有欲,他贪于保存过往的生活,却再也无力创造新的生活。在中国不泥古的作家中,最得尼采三昧的是鲁迅。随手从书架里拆出一册鲁迅的杂文集,你就可以见到,他不止一次嘲讽从《庄子》《文选》和《晚明小品》当中撷取辞藻的文人习气。抄撮古雅、寻章摘句,在鲁迅看来正是怀古病灶的体现。他因此主张,要创造明白如话的新语言,尽力祛除老庄韩非的毒,把那些佶屈聱牙的古奥语言逐出现代中国。他的批判或许有些过分严厉,但意思是很鲜明、很有益的。鲁迅所主张和努力建设的“杂文时代”,是基于经典与时代必须有共鸣这一观点的,即所谓“伟大也要有人懂”。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杂文时代”对经典文苑的侵入,仿佛可以彻底将古文从中国文学的数据库当中删除。然而,文体意义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再没有比互联网语言更鲜活、更新颖,然而也更虚缈的“白话文”。当新媒介的时代本身变得虚缈,难道文学还要亦步亦趋、羽化成仙吗?我以为,现在是到了重温古典的时候了。其实,鲁迅杂文本身就浸着古文的味道。试看《“题未定”草(三)》的这一段,全然是文言的结构章法:然而现在又到了“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的危机,弱国文人,将闻名于中国,英美法德的文风,竟还不能和他们的财力武力,深入现在的文林,“狗逐尾巴”者既没有恒心,志在高山的又不屑动手,但见山林映以电灯,语录夹些洋话,“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真不知要待何人,至何时,这才来“求一究竟”。那些文人的作品,当然也是好极了的,然甲则曰不佞望洋而兴叹,乙则曰汝辈何不潜心而探求。旧笑话云:昔有孝子,遇其父病,闻股肉可疗,而自怕痛,执刀出门,执途人臂,悍然割之,途人惊拒,孝子谓曰,割股疗父,乃是大孝,汝竟惊拒,岂是人哉!是好比方;林先生云:“说法虽乖,功效实同”,是好辩解。尤其“‘狗逐尾巴者既没有恒心,志在高山的又不屑动手,但见山林映以电灯,语录夹些洋话”一句,白话杂以文言,根本上却是骈四俪六的气味。对古文彻底隔膜的人,反而难以读懂鲁迅的文学底色。
奚榜:我看了五篇小说下来,你的语言一直在变。如果小说要有属于小说的语言,你这个阶段认为的好的小说语言是什么?
王幸逸:一要有味。这“味”是随着作者个人才情和所讲述的故事而定的,因此很难给出一个客观的标准说明,怎么才算“有味”。我很喜欢激烈浓郁的味道,但囿于性情与才力,或许只能写那些从平淡当中洇出来的悲喜而已。好在这方面的佳作也非常多,值得我们用心学习。比如张爱玲《桂花蒸·阿小悲秋》里写市井,疾风骤雨般掠过的喧哗,以及沉郁苍凉的吆喝:雨仿佛已经停了好一会。街下有人慢悠悠叫卖食物,四个字一句,不知道卖点什么,只听得出极长极长的忧伤。一群酒醉的男女唱着外国歌,一路滑跌,嘻嘻哈哈走过去了;沉沉的夜的重压下,他们的歌是一种顶撞,轻薄,薄弱的,一下子就没有了。小贩的歌,却唱彻了一条街,一世界的烦忧都挑在他担子上。又比如,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李健吾译)写包法利和艾玛最初相识时候的情状:她送他永远送到第一层台阶。马要是还没有牵来,她就待在这里。再会已经说过,他们也就不再言语;风兜住她,吹乱后颈新生的短发,或者吹起臀上围裙的带子,仿佛小旗,卷来卷去。有一次,时逢化冻,院里树木的皮在渗水,房顶的雪在融解。她站在门槛,找来她的阳伞,撑开了。阳伞是缎子做的,鸽子咽喉颜色,阳光穿过,闪闪烁烁,照亮脸上的白净皮肤。天气不冷不热,她在伞底下微笑;他们听见水点,一滴又一滴,打着紧绷绷的闪缎。所谓“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真是极平淡而值得咂摸的语言。二要好读。我写完一段话,自己多读几遍以后,总能找到语句顺序不对、语义重复或者句子相同结构重复出现的情况。这时候我就会进行修改。我有时候帮朋友看小说稿子,也会忍不住建议她们,哪个句子读得不顺,哪个地方最好加个逗号。最后是我个人一点审美倾向,我觉得小说语言还可以尽量“好看”一点。古典的用字,不但在义,也在字声字形处费考量,比如同义同音的,何处用“词”,何处又用“辞”,在视觉上都有不同。这方面值得我们推敲学习。主张汉字拉丁化的鲁迅,在《人生识字糊涂始》里反对使用“崚嶒”“巉岩”“玲珑”“幽婉”“蹒跚”“嗫嚅”之类的字句,因为这些形容词只是“从旧书上钞来的”,意义太含糊,作者和读者都说不清楚所以然。他是为了主张“先把似识非识的字放弃,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搬到纸上来”,也就是像孩子那样平白地说话。古旧遍纸、雕缋满眼,在当下确实显得过分做作,但我觉得,在自然写来之余,适当保留一些“巉岩”之类的词,不也很美吗?像“巉”的字形,本就有审美性。我很喜欢萧红那部孩童般的《呼兰河传》,特别“天然去雕饰”,但究竟少了方块字本身的况味。当然,我说的“好看”只是锦上添花,对小说语言来说,更重要的还是有味、好读。
奚榜:我想到我们70后是反着来的,先从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小说看起,后来才看十九世纪现实主义高峰,理性写作后才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尤其关注白描、意境、中国文字的形象化,甚至中国小说讲故事的能力,等等。你能谈谈自己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和开掘吗?
王幸逸:我对古典文学并没有系统的研究,倒可以谈一些古典文学对我文学创作的滋养,以供参考。比起白描的技法,我更喜欢在小处、在语言上袭化古意,把语言和意境连通起来。我读唐人传奇集,觉得《柳毅传》一篇文辞精彩,豪壮昂扬,在唐传奇当中至少能排到前三的位置。《登仙》里出现过的黑羊,其实化用了《柳毅传》开篇龙女所牧的乌云雨工,“矫顾怒步,饮龁甚异”。不过,我把它们写成跟在雨师傅身后的小工,这就添加了一些工厂单位的人际特色。《登仙》里出现的签文,来自曹唐的游仙诗:“洞里有天春寂寂,人间无路月茫茫。”相比而言,《忽闻歌古调》的古意要更浓。这是受朱天文影响,她的小说集《世纪末的华丽》,很有晚唐秾艳的味道。《忽闻歌古调》里关于“红紫事退”“未到晓钟犹是春”之类的表述,直接用的唐宋诗句,而小说结尾,也建立在对杜审言诗句的共鸣上,虽然这里的“古调”既是似有似无的曲调,也是指现代都市几近消亡的爱情。我以前写过一首有关现代爱情的诗《古意》,举第一节为例:
回波池畔我们打過赌:万一离人泪
滴成两处池水,我能分辨此间的区别。
忠贞总是咸苦,而背叛盛大如芙蓉——
蜜意暗滋,与明月调情或纠葛江风。
这里直接化用自孟郊《古怨》:“试妾与君泪,两处滴池水。看取芙蓉花,今年为谁死!”只是我削减了怨怒,把结尾宣誓般的气势,改成“气婉而多讽”的表述,我觉得,这样更适合现代爱情游戏那种玩世不恭的腔调。或许这节诗也算是《忽闻歌古调》的一个前史和注脚吧。现代小说的结构与意趣,也可以从古典美学所谓“兴”的范畴获得启发。按郑樵《六经奥论》里的定义:“凡兴者,所见在此,所得在彼;不可以事类推,不可以义理求也。”小说家张大春据此说,兴这种手法“有如另一种形式的韵脚,以极少限制的意义规范,使看来不必相侔相从、不可互诠互解的符号与文本彼此有了意义联系”(《小说稗类》)。这不正是一种小说的“飞行”技巧吗?在“兴”的起落之间,各种关乎现代生活的情感和寓言碎片,蒙太奇般排列在一处。我们阅读小说,就像仰望羽毛从大地升上高天时那不可见的轨迹。
奚榜:在你的文学阅读方面,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可以提供给广大写作者参考的吗?
王幸逸:我其实在文学阅读方面不算很独特,虽然偏好古诗,也爱读旧小说,附庸风雅地看一点六朝文赋,但整体而言阅读得非常随性,也没什么值得参考的地方。在阅读文学作品之余,我比较爱读一些文史研究的论著,可能这算是有些特别?比如尾崎秀实其人,我最早是从赵京华老师的论文里知道。《登仙》从当代文学批评界关于“新东北文学”和“新南方文学”的相关讨论当中汲取了灵感。《忽闻歌古调》两个人物的塑造,和我从笛安老师的小说中勾画的“幸存者”形象有关。对于当代学术和文学批评现场的阅读和关注,在很大程度影响了我的写作思维。
奚榜:最近几年对小说改革提得比较多,你认为符合未来的小说应该是怎样的?
王幸逸:我不相信有“符合未来的小说”,不相信我们可以讨论出一个客观单一的标准,然后我们好像就可以据此来衡量、检验和判断——哦,这些小说“符合未来”!哦,那批小说“不符合未来”!我觉得,与其谈论什么是“符合未来的小说”,不如关注不同小说指向的未来。小说的未来,恰恰是在当下各种写作实践当中生成的,因此是复数性的。小说的未来,是在小说或小说写作者的历史实践当中形成的,简单来说,如果没有了面目不一、观念各异的写作小说的人,小说就根本没有未来可言。并且,在“小说指向的未来”变成真正的现实之前,每一篇小说都符合不同作者所向往的、彼此不同的未来境况。萨特说得好:“我们每个人通过呼吸、吃喝、睡觉或者用随便什么方式行动,都在创造绝对。在自由存在——作为自我承担责任,作为存在选择其本质——与绝对存在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因此,我只能谈我心目中的“小说的未来”。我希望小说被用来捕捉现代社会当中的古意,这古意不是安置和沉睡在博物馆、纪念堂、浩繁卷帙和宣传长栏里,它不是符号化、概念化的东西,而是寄身在我们平凡生活当中的一缕游魂。这古意,还不在课堂上一遍遍诵读古文的懵懂少年那里,而要等到若干年后,少年已经长成惘然无措的“青年漂泊者”,一位多年不曾温读文章的都市异乡客。在迷蒙氤氲的华灯下,他的心也随潮汐般起落的人群而腾起了辞句: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奚榜:文学在你的人生中具有怎样的意义?
王幸逸:想象不到没有文学的日子该怎么过下去,文学是我重要的灵魂器官。
责编:郑小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