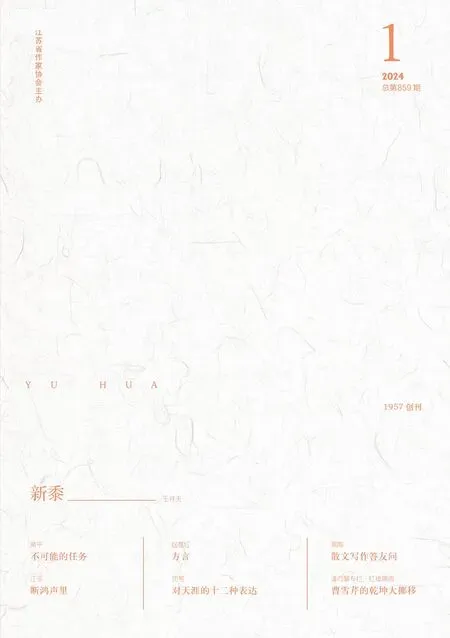父亲的失语症
2024-03-18邓跃东
邓跃东
闲下来了,我想跟父亲说说话的,准备张口时,他却低下头去了。父亲常常认真地看着我儿子小清做作业,目光跟着小清的摇晃而移动,好像在辅导,其实他不懂。我不好打搅他们爷孙俩。长久以来,我跟父亲之间的对话,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错过。
我和父亲习惯了沉默,有时几天都不说一句话,父亲没什么异样。要说他还有点动静,就是吃饭时咀嚼声响亮,“吧嗒、吧嗒”,显示出他对这顿饭的满足。我提醒父亲嚼动轻一点,他不吭声,移动一下身子,声音渐渐低下去,但过一会儿又恢复原样。父亲的话太少,这点难得的声响就不剥夺了吧。
我非常矛盾,父亲没来城里时总盼着他来,来了却没话说。小清有时拿着童话书,说要爷爷讲故事,可父亲不会讲。他觉得不能让孙子扫兴,就让小清讲,他听。小清伴着动作,学着我们给他讲故事的腔调,讲述各种故事。一直没听到父亲讲什么故事,可他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人。
一
父亲是个泥瓦匠,雨天闲下时,他不跟人闲聊,一个人坐到屋檐下抽烟,烟团腾起,飘到檐口。屋檐上的瓦,是他盖上去的,遮挡着风和雨。他的故事,正是从一片瓦开端的……
弟弟有次说笑要父亲和母亲交代,当初是谁看上了谁。母亲生气地指着父亲说,是这个背时鬼打的主意。这些年,母亲一次又一次地复述着这场婚姻的起始,她老了,这流露出她对这个世界不多的留恋!
许多年前的一天,父亲在屋上捡漏,待字闺中的母亲寻猪草从屋檐下经过,突然“啪”的一声掉下一块瓦,母亲吓了一跳。父亲下来招呼,招呼她进屋喝杯茶。奶奶看到了,明白父亲对母亲有意,便托了人到外公家提亲。母亲不愿意,外公觉得爷爷家知书明理,是可以托付的,便一人做主,把母亲嫁了过来。后来有了我们三兄妹。孩子可不是一片瓦,是璞玉,而玉要琢,离不开瓦——仔细去看屋檐上的两溜瓦,像极了一本打开的书。父亲想要把这本书打开。
父亲及时准备学费,管吃饱饭,但从不过问我们的成绩,更谈不上辅导。他不跟家里其他人多说话,母亲跟他说话,他一般只有两个字,第一声的“嗯”和第三声的“嗯”。对我们兄妹三个,常常是第四声的“嗯”,表示反对、不允许,同时还有严厉的目光逼视而来。
第四声的“嗯”用在我身上较多。十一二岁时,我十分顽劣,惹是生非,常有人找上门来。父亲动不动就暴打我一顿。他往往是关起门来打,别人不能拉,直到把棍子打断,把皮抽烂。我不喊痛,也不认错,他打得更狠了。有时挨了打,我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夜里躲到树上不回家,爷爷奶奶提着马灯到处寻找。为了躲避父亲,有一次我甚至流浪到外乡好几天,因为肚子饿得慌,最终又灰溜溜地回来了。但我不再怕他。我对抗他的方式就是保持沉默,不再喊他。时间一长,我竟叫不出口了。十五岁后,他不再打我,但直至如今,我再没恭敬地喊过他一声“爹爹”。
我长期不叫父亲,他是不满的。我问母亲要钱,她故意叫我问父亲要,我就硬邦邦地跟他说给我几块钱。父亲说你问谁要钱,我有名有姓。他要是不给,我转身就去问奶奶要,爷爷有退休工资。奶奶给了后,又不无乖态地说给母亲听,父亲知道了更生气,骂奶奶多事。
我曾读过一篇分析人为什么会失语的文章,研究者说,长期的少言,可能是心里紧张导致的。父亲紧张什么呢?因为我吗?
我向奶奶推卸责任说,你怎么养了这样一个儿子,是不是小时候你不准他说话,管得太严了,别的父亲好亲昵的。而奶奶把父亲沉默寡言的原因归咎于时代。父亲出生不久,社会环境愈加复杂了,当教师的爷爷被下放到了农村。在一次集体劳动中,爷爷被从屋顶落下的一根大梁砸中,一条腿残废了,虽然多年后复职,但一瘸一拐没干几年就提前退了休。父亲刚满十七岁,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我问过父亲家里当时的境况,他冷静地说,还好,没有人过分地为难咱们,不要打听,去读你的书。我觉得父亲那时被吓怕了,心里紧张。多年来,父亲把一切吞在肚子里,村里分粮、分树时老是吃亏。母亲埋怨他,父亲横竖不作声,母亲更气了,干脆自己出面。母亲初中毕业,能讲道理,让人家没法反驳。母亲维护了这个家庭的体面,纵观几十年的光景,父亲是配不上母亲的。
但从后来的情况看,父亲又是很有个性的。前些年,有伙人在村里开砂石加工厂,未经同意,在我家菜地里栽下一根水泥电线杆,迅速通电经营。父亲知道后,一人跑去跟对方十来个人争了起来,要求他们移走。他们不肯移,父亲便用锄头将电线杆根挖出,要将电线杆推倒。对方担心出大事,只得道歉。父亲骨子里不是胆小的。这个事,就是我回来处理,也没他这样有力度。
二
如果与父亲发生了言语冲突,他总要说到我不好好读书这件事。而我一直在读书进取,活学活用。每次跟他发生争执,他不好再打我,便气冲冲地跑去瓦厂,甚至不回家吃饭。他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我的不满。母亲要我给他送饭,我老远就把饭篮放下,也不告诉他,转身走开。晚上他将饭篮提回来,饭没动。
父亲每天回家,早早就上床了,说站了一天,腰痛,扯着五脏六腑。第二天清早又匆匆出工,我们跟他几乎说不上话。做瓦比外出务工效益要好些,但是很苦,多数人不愿干。我后来有过切身体验:一是累,要踩泥垒墙,颇耗力气;二是机械,站在太阳下,抹瓦皮、蜕瓦衣,一整天重复着同一个动作;还有寂寞,瓦匠之间的晒场隔得远,几乎没法说话,大家都要抢天气、多出活,也没时间说话。
父亲做瓦,不啻于一种赌博。一年一窑,要是烧得不到位,火候太过或太嫩,一片都卖不出去,一年的力气就打了水漂。我记得,因自己家的瓦没烧好,一些妇人在窑门口呼天抢地哭喊,咒骂老天爷。父亲就这样一年年地赌着,有年赌输了,他一整天站在窑前不说话,母亲不敢哭,怕把父亲压垮了。他们还要冒着奇热,将烧坏的瓦搬出来,给别人腾窑。我们兄妹也去帮忙,大家沉重得说不出一句话,本想卖了瓦添衣割肉的。母亲安慰大家,明年再来,有劲就会烧好!
爷爷退休时,父亲符合接班条件,可以借此改变瓦匠身份,但爷爷把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给了叔叔。有次我对父亲说,要是你去了,我们成了公家人的子弟,条件会好很多。父亲不吭声,就跟爷爷和他谈这件事时一样。这件关乎一生命运的事情,三两句话就决定了,可见父亲心里并没有太多的纠结。
瓦,如此幸运地成为了我们家烟火岁月中怎么都绕不过去的器物。我们兄妹也如此幸运地成为父亲手里的一片瓦——得烧好,不能掉落于地。他捧在手里,小心得不敢说一句话。
可是,我想离开父亲,我受不了这种沉闷!村里其他的瓦匠也养家糊口,一样的劳累,他们却互相取乐,享受着苦难中不多的快乐。父亲为什么不一样呢?
初二时,我常去瓦厂浪荡,有时装模作样做上几瓦桶。父亲不准我触摸瓦桶,我偏要玩。有天他大发脾气,把做好的一坪瓦坯用脚踢倒,嘴上说着“我让你玩,我让你玩”。他的举动把我惊住了,没想到他竟如此愤怒,我很久不敢再到瓦厂去。
我明白,他是想让我好好在学校读书,不要成为一个瓦匠。可是,我的心事在另外的地方。
我喜欢看小说,还模仿着写了几篇往外投稿。父亲却反对,说我不务正业。有次我正在读一本叫《黑三角》的侦探小说集,他抢过去把书撕成两半。我把破书合拢订好,偷偷拿出来看,结果又被发现。这次,他不但彻底撕毁了这本书,还把我收藏在箱子里的其他小说全部撕烂。我气得要跟他打架,可是打不赢他,就瞪着眼睛对他高喊:“你不读书,还不准我读!”父亲扬着棍子,没有打下来。
父亲这个举动,深深留在我的脑海里,比跟他打架产生的影响还要大。我很久没跟父亲说话,准确说,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不再喊他“爹爹”的,我恨他。挨打只是皮肉之痛,过两天就消失了;撕书却给我留下另外的痛,无法愈合。
此后,我更不想读课堂上的书了,决心远走,要写一部书出来,让他怎么都撕不烂……
三
乡下的檐口,瓦片一溜溜叠放上去,两溜瓦像两只欲飞的翅膀。每个瓦匠都有飞天梦呢!当然,父亲对我并没有过高的期望,只希望我多读两年书,不要早早成为一个农民。但是,高一暑假我就告诉他不想读书了,因为我对理科一窍不通。我自愿成为一个农民!
父亲默默地坐在屋檐下抽了一宿烟。虽然那时村里去广东打工的年轻人已不少了,但是得知长子读书读出这样一个结果,他还是不舒服。我去意已决,父亲只得卖了一头肥猪,给我凑了一笔路费。我转道衡阳,坐火车到了广州,后来又辗转惠州、惠阳、新圩等地。
儿子小清今年十七,上高三,懒散,爱玩游戏,对家庭、社会事务不太关心。我几次用父亲十七岁便成为整个家庭顶梁柱的经历来引导他,可他并没有什么反应。我又说起自己十七岁时开始与在广东务工的亲戚通信联系,十八岁毅然南下。他说,你去打工是你的事,难道也要我去?我气得捏了拳头要揍他。他不高兴,关门不出。他们这一代人的人生跟电脑编程一样,早已设计好,平淡无奇。
我担心小清学了我的脾性不理我,得及时开导。那晚跟他交流后,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喝着早已凉去的茶水。这跟父亲坐在屋檐下抽烟一样,我们想着同样的事情,心里是同样的滋味。
第二天早上,小清对我说,要是明年高考没考好、学校也不让复读的话,就去广东打工,不再用你的钱。我并没有感到惊讶。我知道,他说的只是气话。但是一连几天,我仍止不住地想,要是明年小清真的去打工,我会内疚一辈子的。
我终于理解了,当年我去打工时,父亲心里是十分失落的。他不是舍不得我离开,而是被我撞伤了“腰”,把话语权撞没了——儿女的成长、求学、就业等,父母是要发表意见的,那是他们应尽的责任。继我之后,弟妹们很快都有了自己的选择。被剥夺了话语权的父亲,每天是怎样度过的?
我以为逃离了父亲就无拘无束了,可事情并非想象的那样简单。我在广东并不顺利,很久没有找到称心的工作,后来进了一家石膏玩具厂,干了不久又毅然辞去,开始漂泊。父母曾叮嘱我多写信给他们,因为工作不顺,我没有及时给他们报讯,父亲很着急,每天到村部去等候邮递员,一坐就是半天。弟弟放弃读高中,去了岳阳的石油学校;妹妹执意到广东韶关复读高三,后来考到广州一司法学校。这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从哪里来?不久,我入伍去了大西北,入伍第四年,我参加成人高教培训,需要四千块钱,父亲跑了三天,给我凑齐寄来,这笔钱差不多是他一年的收入了。两年后我成为军官,却高兴不起来……
母亲来信说,你在信上总是称双亲大人,不能像弟妹那样喊爸爸妈妈吗?我盯着信看了许久,动了动喉咙,可怎么也喊不出来。但我注意到信纸上布满洇团,字迹也不一样。原来,父亲向不少亲戚借过钱,有的怕我们一时还不起,催得急切。父亲难以接受,想告诉我,写着写着眼泪就落下来了,母亲便接过父亲手中的笔写上一阵。父亲没有好点的办法,只能靠沉默来应对一场毫无蓝本、紧张惊险、起落悬殊又无法缺席的人生大戏。这些年,别人都到广东打工去了,父亲能去的地方只有瓦厂,陪伴他的是水、泥巴和空气,一个人不用说话了。
外面的世界,父亲一点都不了解,只要是儿女有需要,他都无条件答应。我们利用了父亲的沉默和顺从,一有想法就对他发号施令,要是有什么做得不合我们意的,我们就对他使性子。面对这些,他往往是一言不发,好像做错了事。父亲的粗暴脾气被磨掉了,他不再骂人,也没人可骂了,变得胆怯了,和善了。
我曾向在省城当医生的表哥咨询,父亲的失语是不是大脑有问题。表哥告诉我,失语症里有一种表现并非神经受损。如果一个人长期不说话或不曾展露笑颜而造成面部肌肉紧张、组织板结、神经传递失灵,是会导致失语或伴有轻度失语现象的。父亲会不会是这样?
我曾想,要是让我走一遍父亲的路、负荷同样的家庭重担,我会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我肯定会患上失语症。我还想,父亲要是个话多些的人,会这么憋屈吗?我成年后遇上事,不管悲喜,喜欢第一时间与人倾诉,倾诉之后,心里会畅快很多。
四
这些年,我常常回到村里去,很多老房子坍塌消失了,瓦厂已被平整成稻田,唯有父亲工作过的那座瓦窑还在。远远望去黑墩墩的,很像父亲站在那里,说着什么。父亲辛劳了一辈子,是否获得过幸福感,或者说在日子宽松一点的时候,是否有过享受一下生活的想法?我反复观察,他是有的,只不过方式比较特别。我是在他病倒时发现的。
家中生活状况渐渐好转,弟弟妹妹在广东成家,母亲去给他们带孩子,我从部队转业到老家邵阳。我希望父亲早点来城里生活,多拉拉家常,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但有好些年,父亲陪着奶奶在村里生活。父亲从不玩牌,不喜欢出去旅游,也不大串门跟人聊天,我也很少主动跟父亲谈个什么话题。
奶奶在九十一岁时去世,我想,父亲可以过来了。可是父亲突然病倒了,六十三岁,肝硬化,腹部积水,过去一直没有发现。我将父亲接到市医院检查,发现胆红素持续偏高,有天突然昏迷了,我急得直喊“爹爹、爹爹”。这是三十多年来我唯一一次喊他。经过一番紧张抢救,父亲醒了过来。我舒了一口气,提出转往长沙的省医院。父亲说,还是算了,省医院也是这样治疗。我知道,他是担心治不好,还要花更多的钱!看着父亲蜷缩在病床一角的孤单模样,我难受不已,连夜找了车,疾奔长沙。这样做了,我心里要轻松一些。
父亲的肝脏因长期得不到治疗和养护,不能正常发挥作用了。省医院努力月余,检测指标仍是居高不下,医生建议使用抗病毒的西药,帮助肝脏解毒,但要终身服用,一天一颗。要救命,只能这样选择了。住院三个月,快要过年了,父亲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他坚持要出院。
父亲在乡下休养,有天母亲对我说,他在医院昏迷时,你呼唤他,他是听到了的,说想不到还会有这一天。此后,我还是没有喊过他“爹爹”,也不打算改变。这个称呼在我看来过于灼热,我怕被烫伤。我在外人面前,可以口若悬河、眉飞色舞,可跟自己的亲人在一起,包括和母亲、弟妹,都没几句话。他们多次给我提过意见。我深知这是一种心理障碍,但太难为情,改不掉了。
父亲习惯了我不喊他,他并不为此感到虚空,相反对我是满意的。他在我这里看到了他最初愿望的实现。我曾干过线务员、记者、指导员、参谋干事,转业后任过文秘、负责过工程项目,还成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听村里人说,这么多身份里,父亲最满意的是作家。他常拿着我发表的作品给他们看。现在条件好了,村里人还是推崇读书,挣了钱的老板多,大家却不怎么在意。
父亲为我重新成为读书人而倍感高兴,但是又伴随着一种疼痛。母亲曾说父亲对她讲,过去撕书伤了我,他一直想给我买本书,就是他撕毁的《黑三角》,但走了很多书店都没买到。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一本小说,他以为在书店还会买到。我非常惊讶,他居然还记得书名!
有一次,我在客厅偶然看到父亲站在我的书房里,望着满墙的书籍,抽出一本,抚摸着封面,跟抚摸一个孩子一样。我想,父亲的心里是复杂的。我的事业、我的幸福,包括我带给他的声誉等,都是从一书本开始的。父亲想不到我会成为一个作家、一个写书的人,而当初写作的目的竟是为了报复他、打倒他。
五
父亲坚持吃药和复查,大病后七八年了,各项指标都较为稳定。他觉得什么都好吃,见到谁都开心,但不能跟伙计们去砌墙了。父亲时而在中山,时而在邵阳,但他还是喜欢乡下,每年都要回去居住一段时间。他不是寻找归宿感,而是觉得在乡下与邻里谈得来、被人在乎着,有存在感。他觉得有位置的地方才是好地方……后来他希望把老屋翻修成亮丽一点的楼房,我们也照办了。
在我们的要求下,他已戒烟多年。现在,他又时不时地点上一支。想抽就抽吧,不管他了。他不喝酒,有回我烧了姜汁可乐,开玩笑说是茅台,可贵了,他说没什么味道,还没可乐好喝。于是,我买了整箱的大瓶可乐放在家里,他喝得津津有味。我会陪他体检、买药、选衣服,给他做饭。弟弟不会做饭,弟媳做,要么去餐厅吃,点很贵的菜,他觉得浪费,吃得不安。父亲愿意跟我在一起,我们不需多说话,连称呼都不要,彼此默契,包容和放任着对方的缺点。
这就是日子吧,日子的滋润,是靠心安去感受的,而非话语。
可我常为一件事情的不顺而喋喋不休,我做不到跟父亲一样,遇事保持着沉默。在这个躁动的时代,我多想感染上父亲的失语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