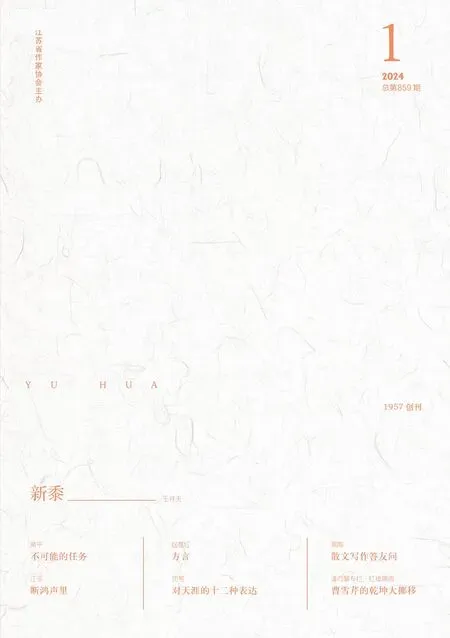送别柳河君
2024-03-18周加军
周加军
一大早,群里跳出一条信息:
定于本月初七日,在布心山布心寓所举行本人的葬礼,鉴于人手所限,恕不一一奉告,望各位好友周知。
柳河君叩请
微信群里炸开了锅。我们这个群埋伏着三十八位诗人,平时深藏不露,关键时刻都冒出来,证明自己还在呼吸。可问题是柳河君也在这个群里,自己造自己的谣言,开这种玩笑,头脑有毛病了?难道他真不想活了?
三年前我们在草泥诗会见面。草泥诗会每年举行一次,由当地诗群部落发起,邀请全球汉语诗人参加。今年已经是第五届了,主题是“山、诗人与远方”。开幕式过后,主持人点了几个人上去朗诵诗作,需要朗诵的诗人太多了,主持人就不再点名字,柳河君自告奋勇上台朗诵。草泥诗会结束,柳河君提议建一个群,以便大家继续讨论诗歌。不久,我们每人收到一盒薰衣草,柳河君在里面夹了一张邀请函,让我们去布心山做客。
柳河君占据一个山头,号称布心山诗者,在那里写诗、种薰衣草。最令我们不解的是,上周他还在群里发布诗集即将出版的消息,我们大家都送上了祝福。两天后,我收到一个蓝色封面类似于招商广告的小册子,打开扉页是他狂草式的签名。这是他的第三本诗集——《跌跌撞撞》。我刚读,他的电话就刺过来,很是兴奋,问诗集收到没有。我老实说收到,夸赞他的诗越发有禅意。他说这是出版社的样本,大批量的一个月后出来。我明白他的意思,他不是一个小气的人,我向他保证不会把诗集发到群里。他恳请我认真看一遍,写一个评论,作前言。我突然想起他送过我一本诗集,有一天他突然问起,我才把它从书橱里翻出来,走马观花地浏览一下,我在电话里端出评论家的腔调说他的诗很独特。他羞羞答答地说,他的诗来自泥土,就是土坷垃,不值得一提。没想到两年后,他的看法就变了。
我们几个跟他走得近的人迅速建立一个小群,在里面继续讨论,柳河君怎么会突然想死,还定下了葬礼的具体日期。
木子说,柳河君就在群里,你们真是诗人啊!何必舍近求远,问问他本人不就行了?
“对呀!”我们被点醒了。
但是柳河君退群了,而且电话也打不通,难道他要从这个世界上不辞而别?
这下我们还真慌了。以前也没听说他生病,因此除非是暴病,或者是意外事故,比如车祸,但是他住在深山里,怎么可能撞上车子?我们猜测他坠崖了,因为他经常到悬崖边上寻找灵感,石头下面是空的,空的好填满想法,他整理好诗人的歌喉,向天发问,在生命的至暗处探求诗的矿脉。他朗诵他的得意之作:石头看见的,它在远方;诗人看见的,它在脚下……风摆起来,山鹰的翅膀一只在岩石上,另一只抵达我的诗行;风问住了吗?我说住了。方言朗诵,但节奏明朗。朗诵完毕,他扬眉吐气,问我们怎么样。我们第一次全体沉默,担心不是他的偶得,而是山风什么时候停止。现在果不其然。
他是山的行者,没有十足把握怎么可能登临绝顶。他坠崖了?我们亲眼所见,还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我们在群里肆无忌惮地讨论,不能贸然,大家一致推举我去探路,因为我是他最好的朋友。
虽然理由不充分,但我还得去。柳河君以前曾力邀我去做客。每次他邀请,我都爽快地答应,但真实施起来,才发现身不由己。这一次,我无论如何也要去,否则真没机会了。
坐了七个半小时的绿皮火车,再坐出租车。司机在打盹,我敲了一下车窗,他摇下玻璃,懒洋洋地问去哪里。我说去布心山,他嘟囔道,为什么去那里?
“我的朋友住在那里,他是一位诗人。”
“住在那个鬼地方,都是脑子不正常的人。”司机拍打方向盘,发动车子。
车子一开,我就靠在后座上,闭上眼睛想柳河君不是一个凡人。他醉酒了还假装清醒,拉着我在走廊里转圈。我清晰地记得那宾馆的布局,不见阳光的角落里摆放着盆栽冬青,凸出的阳台严阵以待地拉满钢丝网,长长的走廊里响彻着风的歌声,两只布沙发并列在一起,适合两个人彻夜长谈。他从农民身份谈到了走上写诗的道路,由写诗的道路谈到了眼下。眼下他已经钻进了牛角尖。一颗流星划过天幕,什么东西都不是永恒的,就像他柳河君从来没想过参加这样一个诗歌盛会。然后他说起他的家史,三百多年里的先人识的字加起来填不满一张A4 纸的空间。他父亲在世时说,他写诗算是祖坟上冒青烟了。他自己也很怀疑,有一天带着疑问去祖坟祭奠,他想给爷爷烧纸,但是打火机总是不肯冒火,他很纳闷,准备再尝试一下,就听“噗”的一声,坟草里窜出一个黑色的物体。“看样子,爷爷显灵了。”他笑着说,“我接棒了那个黑色物体的衣钵。”
出租车到不了的地方只能用脚步代替。走到山脚下天已经黑透。山口悬着一盏马灯,山风穿过,发出“呼哧”的响声。
“是欧阳先生吗?”黑地里声音也是黑的,“我在这里等一个小时了。”
“我是欧阳春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我是木子,等不到先生我不会回去的。”一个温柔的声音传来。
“木子!”我心里一惊。
木子不是草泥诗友,柳河君中途把她拉进群里,她的头像是一个舞着的侍女。她在群里推崇柳河君的诗歌,我们猜测她跟柳河君的关系。后来知道她是柳河君的徒弟。柳河君一共收了三个徒弟,她是其中一个。柳河君出了一本诗集,让三个徒弟分担出版费,另外两个当场跑路。木子自告奋勇,承担了全部出版费,柳河君十分感动。就凭这一点,他们的关系不止师徒这么简单。
柳河君坐在围椅子里,一动不动,像是圆寂了。我拉一下他的脸,柔软如面团,黄眼珠子转动了一圈。
“你是人,还是鬼?”我往后跳了一大步,“你捣什么鬼!一大早在群里发讣告,然后无影无踪。”
“你说是人就是人,你说鬼就是鬼,但你不来,我怎么敢死?”柳河君发出的笑声,在我看来像是一个鬼在猖狂地笑。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鬼,柳河君拄着双拐站起来,舞了一圈,然后吩咐木子沏茶做饭。
木子走后,柳河君冲着她的背影说:“小丫头。”我问他什么时候用上了拐杖。柳河君用它捣了捣脚下的泥土,责问我:“是不是我不发那样的消息,你就不来看我?欣慰的是,那么多人就你一个来看我,看得出你我关系非同一般。我以一个将死之人的身份打搅你,博得你的同情,这很羞耻,但我不得不那样做,所以你不是主动来的,是被我诓来了,这让我更加羞耻。”
“我没有那样感觉,反而很荣幸。”我说。我跟他一起回忆起草泥诗会。七天时间,我们住在同一个房间,形影不离,像度蜜月。白天讨论诗歌,晚上喝了酒去湖边散步,一直走到湖心小洲。柳河君捡到一枚鹅卵石,说是鸡血石。就着通亮的月光,我瞧了一眼说,不是鸡血石,但是一块好石头。他立即严肃起来,这不是石头,这是诗,是流质的,像湖水一样柔软,遗留在湖水里,虽凝固成石头,但仍保留着流动的姿态和感觉。我奇怪地看着他,觉得他在说鬼话。他跟我赌气,一晚上不跟我说话,一个人趴在宾馆的阳台上,看看夜色,看看楼下的灯火。柳河君突然自言自语起来,说着谁也不懂的话。
“你那时简直着魔了。”
“一个农民受邀参加那样盛大的诗会,你体会不了那种感觉,就像刘姥姥第一次进大观园,手足无措。”
我们还约定下届草泥诗会再见,但被疫情阻止了。
柳河君总自诩自己是农民,然而在我看来,他除了具有农民的外貌,举止和谈吐根本不是一个农民。我们的一个诗友说:“天啦,那是诗心掩盖了某种本质。”柳河君是个拖拉机手,早年在农场里,他开着东方红,拖着巨大的犁,尘土飞扬,一年到头都在耙地,每天到家两眼一抹黑。有一天他在犁地,听到鸟的叫声,一抬头是一队雁阵,他感慨“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决定走出农场。
“一个农民变成一个专门写诗的人,够传奇的。”
“没那么传神,但我在犁地的时候,听到泥土在呐喊,心就跑路了,耳边另有一个声音:‘写诗啊,写诗啊。’”
木子沏的是工夫茶。她沏茶的时候,我盯着她的手看,她的手指纤巧,像没骨头的银鱼。涮杯、洗茶、斟茶,一气呵成,轻盈得像首诗。
我呷了一口茶,说木子沏茶的功夫是大师级别的。
“她本来就深谙茶道。”柳河君很自豪,“茶是她种植的,也是她采的,清明前三天采摘,上等的好茶。”
我又呷了一口,赞不绝口。
木子做饭也很神速。柳河君高兴,吃了两大块红烧肉、一整只鸽子,各种蔬菜都尝个遍,又喝了些白酒。我说:“你胃口不错,不像病人。”他笑了一下,拿起一支筷子敲碗,唱:“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悲悲切切,吓跑屋檐上一只蹲着的乌鸦。
乘着酒兴,柳河君硬要拉我到山上走走。我看了看天,犹豫不决。柳河君竭力说,这里一年四季都这样,像下雨又不下雨,但夜景保证不会让你失望。我这才下定决心。
木子手里的马灯照出一个圆圈。柳河君开始东倒西歪,我不得不拽着他的一条胳膊,走得很艰难,两只脚要分家,一只完全撂出去,另一只才拔起来。柳河君熟悉这里的山,对它们的脾性了如指掌。我就想他每次去悬崖上寻找偶得是不是走这样的山路。柳河君说,你不懂,住在山里的人必须学会谦卑。
柳河君停下来,手撑着腰,问我看到了什么。我看了看,到处都是山的影子,黑森森,旋转的气流呼呼响,好像无数个大风车。柳河君正颜说,那不是风车,那是山的胳膊,左边的胳膊,右边的胳膊,合起来是身子,中央拽出来的是头颅。我承认自己想象力不够。柳河君说爷爷就站在里面,每次见到爷爷都是同一个样子,穿着玄色、装饰仙鹤的寿衣,很喜庆。但爷爷每次都拄着拐棍,风尘仆仆的,山里的石头太多,他是怕被绊倒,用拐棍探一下,才敢把脚送出去。他胆子越来越小了。
木子插话:“这就是通灵。”
我承认自己没有通灵的本领,无法确定他说的就是他的爷爷。
“错不了,我经常在白天看到死人,当然也包括我爷爷。那些人走过他的身边一言不发,爷爷说他们都是高傲的祖先。我想跟他们说话,但是他们的脚步太忙了,好像急着去做一件更重要的事。他们不会停下来跟我说一句话,只有爷爷会停下来,摸着我的头说又长高了。爷爷睡在停尸床上的时候,我被人拉着去跟他告别,我以为他睡着了,喊他起来,给我扎风筝。
“我那时真幼稚,以为死了的人还会醒来。”柳河君补充说。
柳河君在前面带路,精神抖擞,好像他不是癌症患者。我和木子怕出意外,伸手够他,被他的胳膊躲开;劝他在石头上歇脚,他倔强地跑起来,于是我和木子就假装他是一个身体好的人。又走了一段路,他突然停下来,用两只手拢住耳朵,“嘘”了一声,说:“你听到了什么声音?”我学他的样子听着,但什么都听不见。“这是脚步的声音,这是叹息的声音,这是打鼾的声音。各种声音混合音响,山越高,声音越亮。”柳河君说,附带比画,好像有个人在跟他演对手戏。
终于爬到山顶,柳河君要带我实地考察。岩石后面路更难走,并不是陡峭,而是各种林立的岩石在黑暗中笼罩我们,根本没有路,又杂树丛生。起了夜雾,石头被打湿,很滑。柳河君攀着树枝,又滑下来,重复好几次,他嘟囔起来,以前的路并不这样。木子赶到了前面,我以为她要把柳河君拉上去,但她用身体挡住了岩石缝,爱怜地说,不要上去了吧。我也劝说,已经感受到那种偶得的氛围了。“不到长城非好汉。”柳河君振作精神,但终因体力不支,跌坐在一块石头上,嘴里只倒气,很遗憾地说:“那就带你去更好玩的地方吧。”
下山比上山难,柳河君闷着头,不敢说话,好像一张嘴就松气。我和木子有一搭没一搭地大声说话,想把他的话钓出来,但柳河君不会上当。走到一棵山竹桃树下面,他突然立住,东瞅瞅西瞅瞅,神叨叨地说他看到了自己的来世。木子问那是什么,柳河君说,一只玄色的大鸟,他用手在空气里比画,眼睛是这样,翅膀是这样,尾巴像爷爷扎的蜈蚣风筝,一扫就上了天空。落下的一块石头惊起另一块石头下的山雀,它飞上树梢,丧心病狂地叫唤。柳河君说他就是那只山雀。
我表示怀疑,人怎么会通灵,能知道自己的来世。
“我的来世是什么?是一只鸟,还是一条鱼?我怀疑过,但我想做一只蚂蚁,与世无争,在野外自由觅食,背负比身体重几十倍的食物回到自己的洞穴,累并快乐,幸福不过如此。”
“这很简单,”柳河君说,“只要在绝对安静的地方,闭上眼睛什么都不想,你就会获得这种力量。”
木子是一个善良的人,她在柳河君的指导下,在密室里静坐了一个下午。柳河君问看到了什么,她说看到一只画眉,在树林里叽叽喳喳。柳河君说,恭喜你有了通灵的本领。但木子跟我说,哪有什么通灵的本领,她只不过在安慰他,让他镇定,不要担心。
所谓更好玩的地方,就是他的薰衣草基地,石屋前面的一块地一直铺到山坳里,他尝试对外卖票,但失败了。柳河君发现自己成不了真正的农民,就来这里建石屋,种植薰衣草。柳河君夸大薰衣草的药物功能,枕着薰衣草,盖着薰衣草,穿着薰衣草,保证百病不染。柳河君还获得了一种启发,背着一口袋薰衣草去找酿酒师。他找到的酿酒师一个比一个不靠谱,告诉他这种酒酿得出来,但销路难找。柳河君不得不承认种植薰衣草是为了实验,写诗也是为了实验,但都不是他的得意之作。他去伊犁采风,大巴在沙漠里跳了十几个小时,把他扔在那拉提。风吹皱了草原,显出点缀着的薰衣草,十几个大妈围着柳河君转,搔首弄姿,手捧薰衣草,采摘薰衣草,头戴薰衣草,大呼小叫,一群薰衣草仙子。柳河君讶异的不是她们的疯狂,而是从来没有见过那种颜色,回来就在屋前空地上实验种植。
柳河君除了写诗,还跟一群白鹅较劲。鹅又高又大,是非洲品种,根本不像鹅类,平时规规矩矩的,一到薰衣草地里就撒野。鹅不吃薰衣草,但它们在薰衣草地里横冲直撞,把薰衣草撞得东倒西歪。柳河君本想让它们引导自己的灵感,但是它们总是走动,让他不能安静思考。因此更多的时候,因为鹅们的捣蛋,即使他一天到晚都想着写诗,让自己的思维劳累,也写不出好东西。
柳河君说他心里住着一个魔鬼,怂恿他去死,导致他经常梦见被一群人拖着走,或者赤身裸体,头发掉光。他写不出诗,就半夜爬山,坐在崖边的大石头上直至日出,很是奇怪那些灵感躲得无影无踪,脑子里只剩下生与死的概念,灵感也不知道哪里去了,越写不出越着急。有一天他发现肚子里长了一个瘤,就去看医生。病人的称呼、挂号、CT、剧痛和病友的安慰让他厌烦。扩散、化疗、Ca 报告,自第一天起,他便为这些词语而恐慌。总之,医生说是不好的东西,建议立即割去。身上每样东西都是上天赐给的,柳河君不愿意跟它们分离,请求医生保留。医生表示惋惜。但他还是吃了药,西药和中药。化疗带走了他诗人的头发。他查阅医学论文而不是梦境解析来搜寻线索,计算自己还能活多久。读得越多,就越害怕死于残酷又昂贵的治疗过程。接下来的几个月,不甘心的他在眼前的数据和假发店的买家评价中交替往复。他想象自己身上戴着一百件假物,体内含着另一百件假物——一百件假物即将出现,一百件假物正汇聚成形,而另有一百件假物逐步退却。
木子叫我们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茄子。”闪光灯一闪。我的眼睛不适应那种光,眯了一下。木子说重来。闪光灯又一闪,柳河君的眼睛也眯了一下。木子喊停,再重来。木子认真的样子太可爱了。柳河君摆着腿说,瞎了一只眼就瞎了一只眼吧,人看不到自己的身后事总是太遗憾。柳河君的态度坚决,木子只好作罢。
柳河君谈起了木子,说她的经历可以写成一本大书,主题是一个女人不屈的奋斗史。木子二十八岁结婚,三十二岁最后一次离婚,结了三次,离了三次,没有儿女羁绊。她打过工,开过店,成为漆器店老板时,手下有三百个讨饭吃的人。柳河君走进医院那天,木子决定关门歇业。我问柳河君他们为何不走到一起,并表示我多么希望他们能尽快停止目前状态,正式对外宣布他们的新关系。但柳河君认为那样谁都不快乐。柳河君说,他们向来没办法做到共处一室而不睡到一起,但睡到一起后他们又总是不快乐,就这样他们不断回归到这样的处境。
在布心山我没写下只言片语的感受,因为我于心不忍,还有我的脑袋里空空的什么都装不下,想要跟柳河君讨论的几个问题,也羞耻地躲了起来。
更加遗憾的是,儿女成群的场面并没有出现。来的是一群当地的山民,他们都是木子张罗来的帮工,供吃供喝供抽,每人每天一百元。柳河君生前清静,“死后”却如此热闹。我问他的感受。他感慨,这一生算白活了。
柳河君想要的场面,木子必须撑起来。我想这就是迁就,或者是一种变异的爱。
哀乐环绕、薰衣草盛开的灵堂,柳河君端坐在山竹、藤条、鹅身上最细的毛组成的担架上。网状的藤条凹成坑把柳河君下半身填满。八个人抬起担架,鸣锣开道,吹吹打打,把柳河君送到了指定的位置。柳河君微闭双目,手捧三本诗集,身面竖着一人多高的捧腹大笑的照片。一切看上去都是真的,唯他的头发是假的。木子小声嘱咐我不要哭,因为柳河君不喜欢哭声,因此我在灵堂里是笑着的,那些来的帮工也是笑着的,人人开怀大笑,像中了五百万大奖。木子没工夫笑,忙好里面忙外面,巨细靡遗。吃饭的时候她伏在案板上,我把她喊起来,前一秒她微笑着,后一秒钟,她哭倒在我的怀里。
我问柳河君,难道真的没有遗憾?他说除了诗。我让他再想想,他说还是诗。真够残忍的!他关心那些专业哭丧的人的哭词。那些人都是小人。他们骗他说那是诗。柳河君就让他们以他的诗为哭词。
其实柳河君不应该过早离开。刚开始,他对癌症知之甚少,让他恐惧的也并非癌症本身。他的恐惧来自搜索引擎,他害怕流传在博客和论坛间的疾病文化,害怕被动变为病人的过程——胖子经受的化疗使他难以行走;瘦子在第一次化疗输液后摔坏了腿,导致两处骨折;单眼皮因为化疗几乎掉光了牙齿,并且不受控制像麻风病人一样抽搐。他不想听这些故事,把头埋在被子里,伤心地想不是他的身体病了,而是他的诗生病了,他们的干扰,让他无法进行诗的思维。
柳河君说他不怕死。沉默了一下,他发现那天与众不同,突然来了一个灵感,他找不到笔,就用吊水的针头,把它刻在香烟壳上,确信它不会跑。他幻想自己很快出院,在电脑上打印好,寄给一位熟悉的编辑,但他最终没有如愿,癌症进入了他的大脑,他一出院,就把那首雕刻在香烟壳上的诗忘了。
帮工的人走后,柳河君从担架上走下来,虽然痛苦不堪,仍旧大呼要酒喝。木子舍不得,偷偷在酒里掺水,他发现了非常生气,说他从来不作假。柳河君喝着酒,跟我回忆草泥诗会的那个晚上。那个晚上让我对酒鬼重新定义。我们已经停止喝酒了,他仍在自斟自饮,喝得烂醉如泥,我和老邵一个抬腿一个抱头,好不容易把他弄到床上,害怕他冻死,压了五床被子,半夜我扒开被子,他瞪着圆溜溜的眼睛,问我为什么不睡觉。我问他当时为什么要喝那么多酒,他反问,你以为喝酒能减轻痛苦?
我说,好吧。
什么好吧?他说,我喝了酒,而且吐露了心事,应该没事了吧,我们睡觉。
我们两人很快在那些死去的薰衣草上各自丢下身子。因为酒后,柳河君的鼾声特别大,我睡不着,把他推醒。他说,你不要推,我现在就死。等我喊来木子,柳河君已经闭上了眼睛。木子摇着他的尸身,哼唱那首诗:
石头看见的/它在远方//诗人看见的/它在脚下……风摆起来/山鹰的翅膀一只在岩石上/另一只抵达我的诗行//风问住了吗?/我说住了。
我在微信群里发布最新消息:柳河君真死了,走时安详、平静,没有痛苦。
我们安葬了柳河君,让他和他的诗一起重归泥土。
临别,木子送我到路口,从地上捡起一支香烟壳,惊悚地问,你看到一只黑鸟了吗?
我也是一惊,视线越过木子戴着白花的披肩,扫向四周,再折回来,发现她迷迷瞪瞪地站着,好像着魔了,又好像大白天碰见鬼了。
“什么黑鸟?”我说,“我什么都没看见!”
木子不依不饶:“我亲眼看见,烟壳就是那只黑鸟叼来的。他临死还惦记着它,他在上面写了一首诗。”
没等木子答应,我抢过烟壳,迫切想知道烟壳上写的是什么诗。但上面什么都没有,一片空白。
“上面没有诗。”我说。
木子说你再仔细看看。他是用注射器的针头写的。
我又辨认一会儿,终于发现一些类似于史前遗迹的划痕,但我确定那不是文字,而是好多个不规则的圆圈,大圆套小圆。我把烟壳归还木子,抱怨说,你自己看看,他死了还要再跟我们开一个玩笑。
木子接过烟壳,只瞄了一眼,脸色瞬间变得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