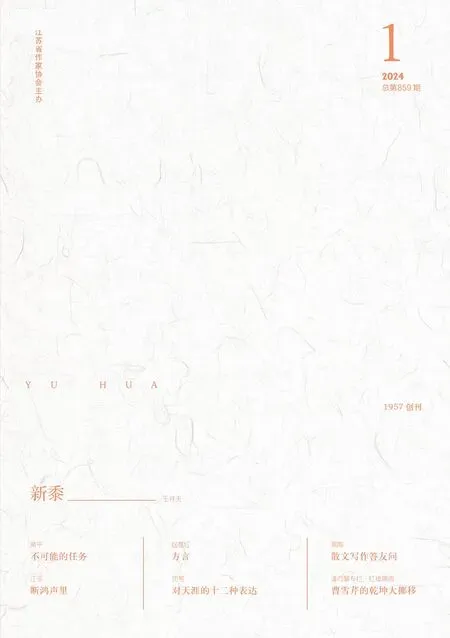冤家
2024-03-18鬼金
鬼 金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喜欢医院旁边的那条无名的巷子。狭长,被两侧的建筑物遮挡,有些阴暗。晴天的时候,也会有阳光在雨搭和雨搭之间的缝隙落下来,落在地面上,形成一条狭长的光线地带。它是这座医院的附属物,正是有了这家医院,才有了这条巷子。其实巷子的左面就是医院出租的门面房,右面是一片低矮的棚户区。看样子棚户区是先于医院存在。那些看上去破败的棚户,因为医院出租的门市,也变成了门市,连成一条巷子。从医院后门出来朝着巷子里走,小饭馆居多,飘出葱花爆锅的香味。有时候,在医院的楼上开窗户都能闻到。再就是扎花店,有两家。门前挂着被雨水淋湿褪色的花圈,作为招牌。一家修鞋店,主人是个瘸子,看上去像是从大腿根截肢了。我看见过他是爬着走路的,像一只动物。五金店、旧家具店、中介公司、蔬菜水果超市、日用品超市……顺着右侧走,快到巷子尽头,右拐五米左右的棚户区内,有一家按摩店。看上去隐秘,透着暧昧,像是棚户区的心脏。零星的电线杆上可以看到治疗性病的广告。灰色的墙上被喷上了办文凭的电话号码。巷子的街道还算干净,但还是能看到小饭馆泼出来的脏水和一些菜叶什么的。
从医院病房的楼上可以看到下面的棚户区是三角形的,像一块巨大的肩胛骨。在肩胛骨的顶部有一户的屋顶上竖着个木头十字架,令我好奇。我正是那天从病房里看到,才第一次去了那巷子里,走了一圈,给朱明浩买了一斤橘子和两斤苹果回来。医生说,可以吃一点儿水果。朱明浩是我丈夫,四十七岁,肝癌晚期。这宣判死刑的疾病对于他和我,还有他的家人都是致命打击,像晴天落下来的一个炸雷,炸得全家的生活秩序都乱了。但朱明浩却是乐观的,仿佛他已经参透了生死,已经是局外人,而我们还在为生而困惑和迷惘着。他的乐观并没有让我们高兴起来。我们表面上跟他一起乐观,但心里已提前弥漫着他即将离开的悲伤。几次,朱明浩想出院,但都被我们阻止了。用他母亲的话说,公费医疗为什么不住院?出去干什么?等死吗?母亲的呵斥让他无语。朱明浩甚至在父母和弟弟不在身边的时候和我说过,他不想死在医院里。我说,那你想怎么办?朱明浩说,我想离开医院,去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等待死神来临,而不是在这医院里。我说,虽然你是我丈夫,我也不能做这个主,毕竟,你还有父母,如果我答应了你,他们会找我算账的。我不能背负这个,而且,我也背负不起。朱明浩躺在病床上,叹着气说,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你也不能帮我?我说,你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这就是答案。如果你只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我会帮你。朱明浩说,你们这样,只会更早地招来死神……也许,这是你希望的吧?我生气地说,你什么意思?朱明浩说,没什么意思。我说,你还在记恨我。朱明浩说,我都要告别这个世界了,记恨对于我早就不存在了。那时候,我原谅了你,就原谅了你。你说,从那次之后,我提过那件事吗?我心里当然知道朱明浩说的那件事指的是什么。他嘴上说原谅了我,但他还记得,还耿耿于怀。也许是我敏感,我想。无论朱明浩怎么伤害我,在这个时候,我都不会答应他的请求,放他从医院里逃走。我说,如果你非想那样的话,我们可以开个家庭会议,把你家的人都叫来,他们同意,我就同意。朱明浩说,我知道他们不会同意,所以才求你的。我说,你也要想想我的处境,我怎么去面对你的家人,我会被唾沫星子淹死。尤其是你母亲,她会和我拼命的,会让我还她儿子。这些都是可以预料到的。你想过吗?朱明浩说,我累了,要休息一会儿。我说,好。我坐在旁边刷了会儿手机,站到窗边,朝下望着巷子,遮挡的雨搭下面仍可看到走动的人影。其中一个男人进了扎花店。这个男人我在医院走廊里见过,总是坐在走廊的椅子上抽烟,一根接一根地。他进了扎花店,我大概猜到了什么。
其实,在病房里,我何尝又不是窒息的呢?但作为他的妻子,我能逃离吗?我应该尽做妻子的本分,守护照顾他,直到他离开。这最后的陪护,我必须完成。婚姻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像一根绳子,会生出各种东西捆绑着你。尽管我和朱明浩的婚姻名存实亡,但还是在捆绑着我……捆绑着我。此刻,我多么希望他的弟弟快点儿来接我的班,那样,我就能从这间病房逃出去,透透气,放松一下,明早再来,也算是满血复活。他在苦熬,我们这些亲属也跟着苦熬。这么说不是抱怨,而是我真实的心境。也许有人会谴责我,那么就谴责我好了。
我坐在床边望着他,消瘦得脱了人形,像一具骨骼。我心疼他,只是心疼而已,我什么都帮不上。他这样的状况,是人看了都会心疼,何况我是他妻子。朱明浩原来一米七八的个头、一百八十斤的人,现在看上去顶多八十斤左右,人也缩小了,像个孩子。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他还会缩小,缩小……这么想,我的眼泪禁不住流出来。我拽了张纸巾把眼泪一一按灭在脸上。我不想让他看到我哭。我曾经是一个脆弱的女人,但随着日常生活的磨砺,我变得坚强起来,甚至有了反抗他的意识,直到有一天,我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朱明浩是望城某机关的科长,这些年他一直考虑着升迁的问题,本来已经准备十万块钱给一个朋友,让那朋友帮忙给上头的大领导,没想到那大领导被双规了。他升迁的希望破灭。从那之后,他仿佛变得病恹恹的,干什么都没了劲头。直到上个月,他查出肝癌……
我妈和他妈是一个厂的同事,因为这层关系,我和朱明浩认识。那时候,我大学毕业,刚分配到轧钢厂机关人事科。朱明浩大我五岁,上班四年,已经爬到副科。我妈非常看好朱明浩,说这个人还有前途,而且他家境也不错。我不同意。我不想处对象。因为在大学里,我有一个男朋友,但在毕业分配时,他去了另一个城市。我们还保持着关系,在节假日的时候,我会坐火车去他的城市……这些,我没告诉我妈。突然有一天,我没告诉男友,去了他工作的城市,去了他的宿舍。我站在宿舍门外,听到他和另一个女孩……当时,天下着雨,我怔怔地站在门外,像丢了魂儿似的。我跑开了。雨越下越大,要淹没整个世界似的。我在雨中,站在过街天桥上,望着下面拥堵的车流。我哭得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因为男友的背叛,整个世界对于我都是陌生的。我想起在大三的时候,曾为他做过一次人流……在那些冰冷的器械中,在血流中,我躺在床上,仿佛死过一次。那一刻,我感觉到一缕光从手术室的窗帘照射进来,落在我赤裸的下身,仿佛把那被器械戕害的未成人型的婴儿接走,让它成为光的一部分,精灵般在屋子里飘浮着,跟随那缕光飞走。
雨还在下,稠密的雨丝是坚硬的,从天上垂挂下来。过街天桥下拥堵的车辆,四个轮子都淹没在水里。雨水好像要浮起世间的万物。我还站在天桥上,那种悬空感令我想跳下去。我仿佛看见一张张丑陋的面孔在天空中望着我。尤其男友的脸孔,极其丑恶,都变形了,在张着大嘴喊叫着:跳啊,跳啊!雨骤然停了,坚硬的雨丝橡皮筋般被收回去了。一道光穿透云层落下来,裹挟着我。我仰望着,那光像一个隧道。一个手捧着鱼缸的男孩从我身边走过,他停下来。我看到鱼缸里游动着两条金鱼。男孩说,你不会是……我没吭声。男孩说,这两条金鱼送给你。我说,不要。男孩还是把鱼缸放到地上,说,我放这儿了,我走了。男孩走下过街天桥。我看着他消失在人群中,不见了。我盯着地上鱼缸里的那两条金鱼,红色的,像两团凝聚的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在我对一个世界绝望的时候,却有人送我两条金鱼。难道这是老天的安排吗?我弯腰把鱼缸捧起来,小心谨慎地走下天桥。路上集聚的雨水朝着下水道流淌着,发出哗哗的声音。那水流的去处是否是另一个世界?我不知道。我站在路边,被雨水淋湿的衣服往下滴着水滴。阳光出来了,我能感觉到衣服上的那些雨水在蒸发。白色的帆布鞋都变成黑色的了。鞋窠里都是水,被脚踩着,发出那种近乎交媾的声音。我脱了鞋,把里面的水倒出来,甩了甩,又穿上了。我终于拦到一辆出租车,去了这座城市的火车站。往常我都是要在男友的宿舍住一宿,第二天早上才回到我的城市。这个时间,已经没有直达车。只有一趟到沈阳,再转车。我夜里九点多钟才坐上车。那趟车人很少,车厢几乎是空的。我一个人坐在窗边,把鱼缸放到茶几上,开始注意观看那两条金鱼。虽然都是红色的,但看上去还是有区别的。其中一条的尾鳍少了一小块。也许是近距离观看和鱼缸玻璃折射的原因,它们的眼睛格外大,都令人恐惧了。它们注视着我,仿佛在问,你是谁?是啊,我是谁?我是谁?我看累了。怕火车在停车的震动中,鱼缸掉在地上,我只好两臂抱着鱼缸,头贴在茶几上,想睡一会儿。被雨淋湿的身体有些不舒服,加上淤积在心里的愤怒和伤心,我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好。男友曾经的海誓山盟都是一堆屁话。火车开了一段时间,我饿了。正好,有卖东西的。我买了桶方便面,抱着鱼缸和那桶方便面,去车厢连接处的接水处打了开水,泡上面。鱼缸变成了累赘,我一手抓着鱼缸的边缘,一手擎着泡面,回到座位。吃泡面的时候我哭了,想起在宿舍里,我和男友做爱后,他说饿了,我给他冲泡面,我们一起吃着,他还会喂我,说爱我。想到这些,眼泪止不住流下来,都落到泡面里了,吃起来能感觉到眼泪的咸。黑夜中的车厢禁锢着我。吃完泡面,我又捧着鱼缸,去把泡面桶扔到垃圾箱里,回到座位上。我望着窗外,不知道外面是什么地方。大片的黑是夜的一部分,车厢像是黑夜的隧道。又行驶了一段时间,我适应了黑暗的眼睛突然被远处升到半空的烟花刺到。有人在放烟花。烟花飞升到天空上,又落下来,像一个个星星的碎片。火车飞速前进,那烟花也一闪而过。我的心情好了很多。火车再次进入到黑暗中,我还沉浸在刚刚看到的绚烂的烟花影像中。火车到达沈阳北站,我从车站出来,坐了拼车回到我的城市。车内的乘客一直盯着我抱着的鱼缸,问,很珍贵的品种吗?我说,不知道。那乘客说,哦。
我带着那两条金鱼回到我的城市。这两条金鱼陪我度过一段艰难的岁月。我心里感谢那个陌生的男孩。有一天,我忘了关窗户,下班回家发现两条金鱼不见了,只剩下一个盛着水的空鱼缸。我在窗台上看到猫的爪痕。是邻居的猫……
那个空鱼缸在窗台上放了很久,里面的水都变绿了。我才把水倒了,刷了鱼缸,把鱼缸扔到储物间。鱼缸放在窗台上留下的灰尘痕迹,我擦了很长时间,连钢丝球都用上了才擦干净。那段时间,我偶尔会目光扫过窗台,空空的,心也是空的。男友几次给我打电话,都被我按了,直到最后把他拉进黑名单。他还通过同学给我传信,但都被我拒绝了。我的世界并没有因为他而坍塌,我变得坚强起来,我就是我的世界。
我妈那段时间已经看出我的状态不对,问了几次我也没说。她还在不停地跟我提朱明浩,我刺了她几次,但她好像没感觉到似的,仍旧没有死心,还在给我传递着朱明浩的各种信息。朱明浩也来过家里几次,但我除了礼貌上的搭讪,并没有深入的交谈。我能感觉到他目光中的火,但这火并没有点燃我。
和朱明浩能在一起,是源于我的一次独自去卡尔里海旅游。夜晚,我独自在海边的沙滩上行走,尽力避开那些亲热的情侣。他们在我眼里是我嘲笑的对象,那种亲热我也有过,后来咋样?我开始远离人群,走累了,坐在沙滩上,望着被黑夜涂成黑色的海水。偶尔有溅起来的白色浪花,但也是一闪即逝。我承认夜色笼罩的海令我产生一种渺小感。对于眼前的大海,我又是什么?对于浩瀚的宇宙,我又是什么?那种渺小感延伸出一种厌世感。那涌动的海水在吸引着我,那黑色中一定藏着一个现实世界之外的世界。
初冬了,海风瑟瑟。海边的人渐渐稀少,可我还坐在海滩上,仿佛在等着海水中走出来的什么东西把我带走。海水撞击岩石的声音,也波及我的身体……莫名搅动起我肉身的欲望。我狠狠地掐了下自己,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恶毒的脏话。我甚至手捂着耳朵,拒绝听见海水撞击礁石的声音。如果那一刻有一把刀子可以杀死大海的话,我一定会把它扔到海水之中。即使杀不死大海,也可以让大海的局部受伤。我在海滩上跑起来,只见海边聚集了一群人,我停下脚步。有几个人手机开了手电,几束光照射着什么,看不真切。人群的喧嚣缓解了我身体的那种欲望。我挤进人群,想看个究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一刻,我突然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我想看看大海会把什么送到岸上来。我撞到前面的一个男人,他回头望着我。是朱明浩。他说,怎么是你?我说,是我,周末到这里来玩玩。你呢?朱明浩说,单位里有个会,在这里的宾馆开。开完会,吃过晚饭后,我就出来走走。我说,哦。朱明浩问,你一个人吗?我说,嗯。也是巧了,竟然在这里遇到了你。那些人看什么呢?海水里飘上来什么了?朱明浩说,看上去像个美人鱼。我说,拉倒吧,你骗小孩吗?那都是童话故事,哪来的美人鱼啊!朱明浩拉了我一把,说,不信你看。我站到朱明浩前面,看着躺在岸边的美人鱼,还真的是啊!我惊呆了。我甚至怀疑自己的眼睛,这怎么可能?但那确实是一条美人鱼。朱明浩说,我没骗你吧?我说,我还是不能相信,一定是什么人搞事情,想做网红什么的。朱明浩说,即使是那样,也不能说那不是一条美人鱼,即使那是人装扮的。我心想,朱明浩说得也对。已经有人拿出手机开始录像。果然被我猜中了,是有人策划的。那个女人慢慢从海水中爬起来,和一个男人走了。围观的人都觉得上当了,被欺骗了。还有人骂骂咧咧的,作鸟兽散。朱明浩夸我说,还是你清醒,我们刚开始都信了。我笑了笑。
我们在海边走了走,又在海滩上坐了一阵,望着海水。海已经变成了涌动的夜。朱明浩抱住了我,我没有拒绝。
我们交往半年时间,结婚了。婚后,我几次怀孕都没成功,还做了三次试管婴儿,还是失败了。我已经筋疲力尽,心力交瘁,身体也变得虚弱。我仿佛成了朱明浩他家的生育实验机器。我也开始感到他家人和他对我冷漠起来,有一种冷冰冰的东西阻隔在我们之间。那种冷漠犹如身边堆起来的一座冰山。我妈看我那个样子,心疼我,让我回家住一段时间,调理调理身体。我甚至和朱明浩提出离婚,但他没有答应。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就是他不和我离婚,我也不想回那个家了。我也在思考,我为什么会走到今天?但,没有答案。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就我一个女人这样,还是有一部分我这样的人。那年,我已经四十岁。我开始喜欢旅行,只要到了假期,我就会全国各地去旅游,不是参加旅游团,而是一个人走。我更喜欢那些自然景观,我觉得人更是自然里的动物,回到大自然中,我才是愉悦的,获得了新生似的。我还学了车,买了辆二手车。我在郊区香蜜湖旁边的村子里买了一个单室楼房,没有产权,但有使用权。坐在阳台上,可以看到整个香蜜湖。虽然香蜜湖是人工湖,但看上去已经开始有了野性。那种野性是周围的植被赋予的。周末的时候,我更多是躲在那里。朱明浩在我离家后找过我几次,我都没回去,他也再没找我。他还是不答应离婚。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还握着婚姻这根绳子……但这对于我已经无所谓了,我是自由的。我那时候的生活就是上班,下班开车回香蜜湖的房子,做一口吃的,之后冲一杯咖啡,坐在阳台上,看香蜜湖的四季轮回。季节和时间是神奇的,仿佛真的有一双大手在改变着周围的一切,包括我。
在这期间,我遇到了金钺,但他就像幽灵似的,出现又消失了。我本以为可以和这个男人度过余生,没想到他是一个桀骜不驯的男人,不喜欢那种被羁绊的生活。这件事不知道为什么被朱明浩知道了,他在电话里旁敲侧击,让我有所收敛,毕竟我们的婚姻关系还是存在的。我几乎发疯地冲他喊着,你为什么不和我离婚?他撂了电话。那一刻,我心里对他滋生了恨意。我哭了,我想,这难道就是命吗?偶尔回我妈家,从她嘴里会知道一些朱明浩的事情,说朱明浩还在等我回去。她的唠叨让我厌烦,在我心里朱明浩已经与我无关。我妈愧疚地说,都是我害了你,当初要不是我坚持的话,你也不会这样。我说,和你没关系。
那天,我正在香蜜湖的房间里,躺在床上看一本玛丽·奥利弗的诗集《去爱那可爱的事物》。我想学习写诗。突然手机响了,是朱明浩的母亲,她说,朱明浩住院了。我说,哦。她说,你不过来吗?我僵持了一会儿,说,严重吗?她说,还没出结果,作为他的妻子,你应该……我厌恶她用这样的口吻和我说话。我说,我知道了。我又给朱明浩打电话,他没接。他妈说的医院,是这座城市的肿瘤医院。我想,朱明浩不会是……我去了阳台,坐在椅子上抽了支烟。近年,我学会了抽烟。边抽烟,边望着不远处的香蜜湖。秋天的香蜜湖周围层林尽染,仙境般包裹着香蜜湖,让香蜜湖看上去像一个金色巢穴。朱明浩他妈又打来一个电话,被我按掉了。我回到房间冲了个澡,傍晚赶到肿瘤医院。朱明浩的弟弟和弟媳妇,他妈他爸都围在病床边。朱明浩躺在床上,处于昏迷状态。他们看到我出现,睁大眼睛看着我,仿佛要审判我似的。他们脸上的惶恐表情,让我感觉到朱明浩病得不轻。我说,既然这样了,我们就安排轮流看护朱明浩吧。我和弟弟白天和晚上轮着,爸妈在我们有事的时候来打个替班。如果都同意的话,就这么办。他妈点着头说,同意。我说,那好,今天我在这儿,你们都回去吧。他妈说,晚上我给你们送饭。我说,我们可以叫外卖的。他妈说,外卖不干净,还是我做好送过来吧。我说,也好。他们走后,我坐在病床边,望着朱明浩,刚开始看个轮廓,他瘦了很多,脱相了都。再细看,目光一寸一寸地,他对于我已成了陌生人。我确定那种陌生是来自心理和生理上的。晚上六点多钟,他妈送饭过来,朱明浩还没醒。我简单吃了一口,剩下的在保温盒里,等他醒来再给他吃。他妈和我说了朱明浩的病情。尽管在我预料之中,但我还是感到惊讶。他妈说,之前那么对你是我的不对,现在明浩这样了,你还能来,我谢谢你。我说,我毕竟还是他妻子。她说,是,是。我看到她用手抹了一下眼角的泪珠。她说,有你在,我就放心了。她说完,又看了一会儿躺在病床上的朱明浩,叹了口气,才离开病房。我望着她苍老的背影,像一团浮云。我在心里原谅了她对我的过往。
那天,朱明浩是晚上八点多钟醒过来的。他是虚弱的,看到我,轻声说,你来啦?谢谢。我说,说这些干什么?你妈打电话了,我不能不来。毕竟也在一起一场……朱明浩怔怔地盯着我看,我低下头。我问,吃饭吗?你妈送来的,还在保温盒里。他说,不饿。我问,咋之前没发现呢?他说,人啊,就是这样,总是不在乎,等在乎了,晚了。我仿佛听出他话里有话,但我没有深究。他说,对不起,其实我应该放手,但我……如果我说我爱你,你一定不会相信。我说,不说这些好吗?你会好的。他说,我知道我的状况。我劝说他,吃点饭吧?他点了点头,目光还在盯着我看,仿佛不认识了。我给他下巴下面围上毛巾,一口口给他喂饭。他慢慢咀嚼着,眼泪竟然落下来。我问,咋啦?哭什么?我给他擦去眼泪,继续喂他吃饭。吃过饭后,他看上去有些累了,躺在那里闭着眼睛,嘴里说,你即将自由了。我问,什么意思?他没吭声。我明白他说的意思了,心情黯然。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在这个时候。也许说什么都是徒劳的。
半夜的时候,他突然疼醒了。我喊来护士。护士给他注射了止痛药,他才慢慢睡去。夜晚的病房是安静的,我突然有一种恐惧。我轻轻来到窗边,望着星空。那星空令人看不到尽头。我在窗边待了很久,才回到他临床,躺在上面,久久不能入睡。我是不敢睡,我怕在我睡着的时候,他突然停止呼吸。
虽然和他弟弟朱明翰轮班,我还是感觉很累。我跟单位请了假。在他弟弟来的时候,我会开车回香蜜湖的房子,坐在阳台上,望着下面的香蜜湖,树叶已经开始落了。秋天即将结束它的色彩斑斓,进入萧瑟和荒凉。我抽烟抽得很凶。我是矛盾的。我希望这样的日子早点结束,又希望它无限延伸下去。延伸下去,他就还是活着的。必须承认,这些天,我也想了很多,最明澈的一点是,我越加孤独。有一天,我回来的时候,天还没黑,我跑到香蜜湖的草地上,躺在上面,直到黑夜来临,我感受着那些野草带给我的慰藉,耳畔响起那些在风中飘落的树叶发出的沙沙声。夜空中的飞机,尾灯闪烁。直到夜凉了,我才回家。冲个热水澡,我才上床。莫名的,我竟然感觉到肉身里的欲望复活了。我轻轻地抚摸着自己,想象着和朱明浩在一起的那些日子。还记得第一次怀孕失败的时候,他抚摸着我。我说,再不能怀孕的话,我就生下你。这些天,我知道他尽管是乐观的,但也是渴望生的。在我给他擦拭身体的时候,他抓住我的手,放到他的器官上。那器官已先于他而死去了。
我折磨着自己,直到筋疲力尽才昏昏睡去。
自从喜欢上那个巷子,有一天朱明翰来接我的班,已经晚上七点多钟。我从医院出来,没有回香蜜湖,而是走进那条巷子。小饭馆还都开着,巷子里灯火通明的。我慢慢地走着,有站在门口的服务员问我,吃饭吗?我摇了摇头。我继续走着,看见一家小饭馆门口的玻璃鱼缸内有一条鱼,好像是鲤鱼,在浑浊的水中游来游去。我盯着它看了好久才离开,没走出几步远,就听到有人喊,把那条鲤鱼给我捞出来,做个红烧鲤鱼。另一个声音回答,好嘞。我心里一颤,继续向前走,站在那个灯光粉红的按摩店门前,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进去。里面的几个女人看着我,问我,要做什么?从她们的眼中我能看出来,这个店很少接待女人。我说,按按头。其中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接待了我,把我领进一个包间,让我躺在按摩床上,开始给我按头。她的手法很好,我很享受,都要睡着了。一个多月来,陪在朱明浩身边,看着他被痛苦折磨着,我整个人也要坚持不下去了。隔壁房间有男女的声音,我还是睡着了。朱明浩说,我看见有人在病房外面,你就成全我,让我和他们走吧。我犹豫着,还是拿起临床的枕头,蒙在他脸上,狠狠地按着,直到他不再挣扎,一动不动。
我的手机响了,是朱明翰,他带着哭腔说,嫂子,哥走了。他临走的时候,还在喊你的名字。我听完,一动没动,但眼泪控制不住流了出来。我想,我们可能都是凶手,如果我们让他出院的话,也许他不会这么快就……但这个世界没有如果。女人问,还按吗?我说,按。隔壁男女的声音还在持续,动静越来越大。女人喊了一声,那边才消停下来。
从按摩店出来,下雪了。我穿过那条巷子,头上的雨搭在风雪中发出呼叫声,像是要把整个巷子都刮到天上去似的。我艰难地走着,回到医院,进了病房。病房空了。朱明翰打电话说,嫂子,你不要着急,下雪了,你从香蜜湖过来,直接去殡仪馆吧!518 房间。我“嗯”了一声。在病房里转了一圈,我站在窗前,望着下面,看到那屋顶上的十字架亮了,尽管光线不那么强烈,但还是照亮了屋顶,可以看到灯光中簌簌落下的雪花。
我来到朱明浩睡过的病床前,爬上去,躺在那里,眼泪从眼角滑落到面颊上。我没有管它,任它们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