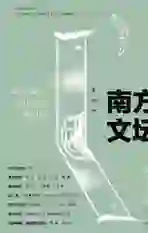在转变、构拟与连缀中拥抱大的世界
2024-03-12丁茜菡
引言
弋舟著作丰富,只从小说创作数量上来看,短篇、中篇和长篇均已可观,但如有读者产生了基于作品的进一步了解的兴趣,就会发现作者已有的人生经历、部分小说的写作时间和背景等还较不清楚;此外,如果读者要想简述其一篇小说的内容以飨友人,恐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对作品方方面面的精心打磨往往难以在简述中呈现,一次仓促的概述反倒会让光怪陆离的故事平淡无味,甚至一不小心沦为俗套,远失了本身的精彩。作家自述、他人访谈的补充能很大程度上改变前一种情形;后一种困难,或许可用弋舟本人在阐释他人作品时提及的阅读感受来解释——它符合“‘好小说拒绝转述的定律”:“一定是拒绝简述与归纳的”,“如果你想了解它,对不起,你必须、只能、唯有去逐字逐句地读它”①。
弋舟的小说写作实践着“文学对于‘复杂性的永恒的要求”②,作品内部的复杂多样容易在概述的输出中急剧损耗,作品与外界相通的整体意识的难于呈现,也加剧了概述无效的体验。例如,其最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辛丑故事集》和同属其“人间纪年”系列的其他短篇小说集(《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庚子故事集》)都选择了在集名中使用干支纪年,在秩序感之外,还明显地体现了作者已赋予小说在单组故事之中和单个年份之外对于更大的整体的呼应。这种呼应不易厘清,但干支纪年法中蕴含着的与公元纪年法不同的循环时间意识,提示了弋舟小说中和小说间结构的尽心考量。
提到结构,阅读弋舟的多篇小说便很难不注意到重复的现象。当作者决定在某处使用重复,他便已作出了某些结构上的考虑。很多时候,重复会被等同于放弃成长,会被视作完全退败,但事实上,有可能是在方向上坚守,也有可能是在制约中创造。本文以弋舟小说的重复为切入点,理解弋舟为何未因小说的重复而被拘住,相反,发现他拥抱了一个大的世界。首先对《辛丑故事集》的开篇故事《敲开千禧年的最后一声钟声》进行版本变化和标题渊源的分析,从中管窥在对之前作品版本的继承之外,弋舟写作上开阔敞亮的转变;其次,从此篇延伸到对弋舟这些年来多部小说作品中不同类型重复现象的讨论,认识其中除个人烙印以外构拟巨型故事世界与同源异流的意图;最后,指出反复开掘固定主题时的写作方法背后密不可分的整体思维,并以《辛丑故事集》中的另外篇目理解弋舟写作中对截面与整体关系的把握及效果。转变、构拟与连缀,弋舟小说的重复现象生动起来。
一、使一二十年前的“钟声”转变得开阔敞亮
《敲开千禧年的最后一声钟声》③是《辛丑故事集》主体收录的六个故事中的第一个。据落款标注,该作品完成日期在2021年,实际可以进行更早的溯源——此篇是由弋舟长篇小说《跛足之年》第一章《抽屉》第五节和第六节合并修改而成。《跛足之年》面世与最初动笔的时间存在着较长间隔,动笔在2000年以前,初版于2009年。与初版时这部分内容④比对,2015年再版时这部分⑤仅有极少量文字标点的变化,但到了2022年《辛丑故事集》中的《敲开千禧年的最后一声钟声》,尽管基本的故事没有变,修改却遍布整篇,字句锻造上精益求精之外,有许多不应忽视的地方。
首先是故事中人名、地名中的现实气息的刻意去除。原本在“抽屉”第五、六节出现五十次以上的人名“马领”在《敲开千禧年的最后一声钟声》中消失殆尽,而以“他”替代。原本向读者透露了人物来处的“兰城话”⑥,在《敲开千禧年的最后一声钟声》中被改为了“家乡话”⑦,使得“他”在读者眼中进一步成为一个不知源头的人。在人物关系上,《敲开千禧年的最后一声钟声》更为强调人物的萍水相逢,用“小旅馆房间里邂逅的两个男人”⑧取代了原本的“他们”⑨,由此弱化人物之间的关联度。
并且,在《敲开千禧年的最后一声钟声》中,有意淡化故事中现实的具体困境,而引向相对抽象的整体思考,表现为:删除原本通过父亲讲述的现实当中马领遇到的麻烦;对倒转时光后果的猜测时,从“重新坐在那张令人费解的办公桌前,年复一年地进行着上拉下托的动作了”⑩的具体情境变为“重新坐在既往那貌似可被理解的生活里了”11的抽象概括;还在个人自身价值思考时拓广了人物的视野,将原本父亲说自己“快六十岁”12,变为父亲意识到“过了今晚”父子二人“都是活过两个一千年的人了”13。
修改还包括更清晰塑造人物内心的趋势。《抽屉》第五、六节中多处人物说话的内容专门单独成行地呈现,《敲开千禧年的最后一声钟声》中则不同,原本醒目地单独成行着的说话内容都被挪移到紧跟说话人的位置,客观上降低了人物说话内容在整篇故事中的重要程度。这一点上不能完全排除文字规范编辑的原因,但与此同时,《敲开千禧年的最后一声钟声》中对难用言语表达的人物情感反映更加直接,证实了这种趋势的存在。一个直接的例子是在“闭着眼睛摇摇头”的动作后面,以新增的一句——“感觉眼皮已经快要关不住泪水了”——加强对为人子与父亲隔阂下情绪的直白反映,向内深入14。
不仅如此,《敲开千禧年的最后一声钟声》还以极少的文字改变调整了故事中的一些氛围。当提到作为对外沟通工具存在的外形笨重的手机时,量词使用上发生了变化——统一从《抽屉》第五、六节中到《敲开千禧年的最后一声钟声》中,统一从“部”变成了“只”,这将沉重中带着的冰冷化为沉重中夹杂着某种轻飘。原本作品中刻意拎出来聚焦的一个“现在”15,在这版作品中改为“后来”16,轻而易举地将之变为时间序列中的平淡一环,是有意的淡化。但作品中,又有有意的加强——《敲开千禧年的最后一声钟声》里把这段故事发生的时间提前了一天,是新千年既未降临又即将到来的那个晚上。调整方式上仍然显出作者的游刃有余,原本,《抽屉》第六节中以老王的话向读者指出故事的发生时间是在“今天”“新千年的头一天”17,《敲开千禧年的最后一声钟声》直接把“今天”改为“明天”18。
尽管《敲开千禧年的最后一声钟声》是曾经的故事的再次出场,但从对之前作品内容的修改中读到当下的弋舟与二十年前写作的不同,作品在修改中变得开阔敞亮——关注人的普遍境遇多于状写特殊个体;抽离具体现实而思考人类普遍命题;向人物内心深入而减少外在事物的醒目程度;用词更加精準并注重作品氛围的打磨。
变化也直白地显现在小说标题中。《敲开千禧年的最后一声钟声》的标题取自此篇结尾最后一句“不,这是敲开千禧年的最后一声钟声”19,也即《跛足之年》第一章《抽屉》第六节的最后一句。在故事的最后,“一声巨大的轰鸣从天而降”20扎扎实实地完成了千禧之年的到来在人物内心分量的外化,也即这“敲开千禧年的最后一声钟声”。这一标题出处中的尘埃落定和豁达敞快,与《抽屉》第五、六节中原本紧扣故事内容发展的标题“睡哪张都无所谓的”和“得救”带来的氛围差异感极大,似乎在远离青年马领的现实生活和即时反应,而更注重精神层面的梳理。
将视线从篇章移到整本,单从《跛足之年》和《辛丑故事集》的名字,也会发现写作改变的蛛丝马迹。前面已经提到,《抽屉》第五、六节来自《跛足之年》;《敲开千禧年的最后一声钟声》是《辛丑故事集》的开篇第一个故事。《跛足之年》的“跛足”,对于个体而言是肢体在外在形态上出现的缺憾,具有特殊的寓意;而《辛丑故事集》的“辛丑”,是真实的纪年,真实而具有森严感,并非以个体人物具体事件为转移。比较“辛丑故事集”和“跛足之年”这样的标题,由“跛足”之年到“辛丑”之年,似乎走向了某种境遇上的开阔。
虽然《敲开千禧年的最后一声钟声》是弋舟新小说集《辛丑故事集》中所列的第一个故事,此篇的修改选择却在今昔对比中客观地呈现出弋舟写作的变化,和集名一起,反映出弋舟的写作在某阶段过后开阔敞亮的转变。
二、个人烙印之外,构拟巨型世界与同源异流
以上看到的是弋舟小说写作基于原有版本的转变,但弋舟小说写作上有着不同类型的重复。不单如《敲开千禧年的最后一声钟声》这般更新版本,弋舟在一些不同的小说中重复呈现着部分情节和主题。与许多作家唯恐避之不及不同,他似乎享受以此在小说作品中留下某种个人的印记或者是建立起不同作品之中及超过作品群的联系。
首先是在不同作品中打上了很深的个人烙印。“‘很难看吧?他解释道,‘嗯,它受过伤,被砸扁过,刚刚恢复不久,还不太像只脚……”21——这是《辛丑故事集》中《敲开千禧年的最后一声钟声》里独立的一段,原本《抽屉》第六节中,这句话便单独成段吸引视线。《敲开千禧年的最后一声钟声》此处的差别,不过是将人物说话内容后的标点从“。”改为了更为醒目一些的“……”,这一处细微改动,未经求证不能肯定出自作者本人之手,却提示了此句中原本就有的强调意思,那便是,这“被砸扁”的“左脚”背后是有故事存在的。
这个背后的故事出现在弋舟定位为自己写作的“母体与元文本”22的《跛足之年》中。但即使未读过《跛足之年》,比较熟悉弋舟的多数小说便应当不再陌生于这个故事,因为即便不把故事讲全,他也时常在其他小说中提及它一下。脚部受伤变形的情节屡次出现,并且常常带有一套固定的程序——在刨冰摊上发生的争执导致“我”的脚受伤,“我”被送往医院治疗,但脚的形状未能恢复如初。这情节时常出现又有些许区别,例如,中篇小说《雪人为什么融化》中有一段情节:李二水等人一边挟持着“我”一边在刨冰摊向摊主挑事,“那块城墙砖一样巨大的冰块掉了下去,就在它落地的一瞬间,我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左脚迎了上去”,随即“我”成了他们口中被摊主的冰砸伤脚的“兄弟”,被欺侮的摊主成了“我”因脚伤住院医药费的负担者23。弋舟曾解释:“我要不断地回溯它,……,有时候,我都不禁要以譬如‘左脚之类的重复来向它24致敬,或者是跟它打一声‘嗨的招呼。”25“左脚”的故事及许多小说作品中与其有关的暗号一般的只言片语,赋予作品以作者本人的深刻烙印,执着一如“丙申”“丁酉”“庚子”“辛丑”故事集的命名。
但弋舟对作品的“招呼”不止于对《跛足之年》等作品时不时说上“一声‘嗨”,同一情节于不同小说中的大小复现,又宣告了其在创作上构拟着读者未能把握的巨型故事世界。——他乐于重复,继而在重复中形成一种氛围,似乎作者本人在讲一个大得始终看不到头尾的故事,而读者在其反复诉说中只是“撞到”一个故事整体中的某一部分。如,《金枝夫人》与《所有的故事》中的女孩有着相似的与初恋男友的认识过程与相处模式;再如,《所有的故事》与《时代医生》中的医生夫妇有着相似的共同职业经历;又如,《赖印》中的男人是《空调上的婴儿》中女人的丈夫,而《赖印》中的男人、《空调上的婴儿》中的女人又分别是《谁是拉飞驰》中少年的父亲、母亲,虽然三篇小说分别以丈夫、妻子、儿子的故事为主,但是各篇或多或少涉及对主角之外的其他二人的描述或暗示。
即使是“撞到”了某一部分,对于身临的这一境地,读者也未必看得真切,在一个故事读完后,经常还是不能确信是否真正解锁了弋舟构拟的那个世界中某一块区域的地图。如,《所有的故事》与《金枝夫人》在相似的初恋之上生长出的关于女孩的故事情节并不相同,再看两个作品主体的内容,更是千差万别;再如,看似漫不经心,《时代医生》三言两语补充出一个比《所有的故事》中隐瞒着的医疗事故更大的秘密——其实,男医生在很久以前便单方面发现那场医疗事故并不成立,却秘而不宣,任由女医生心惊胆战下去,让她以为是冥冥中化险为夷,共同保守着这个秘密并结为夫妇;又如,虽然《赖印》《空调上的婴儿》《谁是拉飞驰》每篇印证着主角之外的其余二人的故事碎片,但每篇小说都做到了为主角经历或经历中所思所感提供出重要的新信息点,只不过有着量上的差别,由弋舟本人有意识地决定内容的重复一样,这也是作者决定好的。
除了不避免情节的重复,弋舟还重视一些固定主题的反复开掘阐释。《辛丑故事集》中,个人烙印以外,更常呈现出的是人生命题的反复开掘。还是以《敲开千禧年的最后一声钟声》为例,部分情节中以截面展现了父子的关系:正给儿子写信的父亲接到儿子打来的电话,在千禧年前夜这样一个背景下,他带着哭腔说出了希望儿子“正常”的心愿;儿子先是试图向父亲列举自己“‘正常的依据”,后又小心翼翼用别人的手机拨打了第二个电话,谦卑地小声请教为什么父亲会觉得自己“不正常”26。父子双方都處于爱与痛苦之中。
亲子关系的隔阂的呈现,在弋舟的小说中并不陌生,除了短篇小说,在中篇小说《等深》、长篇小说《蝌蚪》等体量更大的作品之中,或多或少都有相关的反映,读者在弋舟的众多小说作品中对于这些主题体验颇深。例如,《等深》中,虽未主要表现父子关系,却有着让人印象颇深的两对父子的关系——通过“我”追踪到男孩与其父亲的关系,也让读者看到“我”与父亲的关系。男孩失踪,是因三年前见到了母亲的一段婚外情,现在他已等待自己长到了能担负法律责任的岁数,要去报复母亲的出轨对象。相比较男孩的报仇雪耻,男孩父亲主动失踪并杳无音信,显得怯弱得多。尽管男孩给予自己的父亲三年前的出走行为以很高的评价——“这样的行动,才是和生活等深的”27,但当同样怯弱的“我”,在故事最后想冒充男孩的父亲给男孩母亲的情人以道德的谴责时,却发现男孩的父亲已在几次报仇不成功之后为其收服。而“我”也有一个父亲,虽然他已经衰老,但因此次寻找男孩,“我”使用起由他教会“我”的在纷扰环境中的“吐纳”,之后在“我”面对恶意时一些“狠”的“手段”又来源自他28。这指向了“我”与父亲的联系。
弋舟的小说中,反复描绘亲子隔阂,但与“被砸扁”的“左脚”等相关意象及故事情节的反复出现不同,虽主题一致,读者很难在其中有重复之感,而体验到同源异流。由此,读者习惯在弋舟阅读涉及同一主题的不同小说作品时,仍然有获得丰富体验层次的信心。隔阂当然不只限于父子间,在弋舟长篇小说《战事》等作品中,母女关系中彼此的生疏与伤害也被细致充盈地刻画出来,例如,《战事》中有这样的场景,寄居男友家的少女丛好俨然成了一个小主妇,有一天在菜场见到了抛弃自己的母亲——“丛好的心最初是没有丝毫波澜的,……,她已经完成了对于母亲的埋葬和祭奠,……可这个不复存在的人,现在,红彤彤地站在她的面前,却又存在了。……当母亲的眼泪从眼眶中滑出来的瞬间,丛好的心也跟着猛烈地痛起来。”母亲“嘴唇一直在抖”,“说一句‘好好怎么会这样……就再也说不出什么了。”在菜场这个拥挤的场合相顾无言,母亲塞了钱又许诺下次带她离开,便“像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离开了丛好的视线29。
弋舟以不同作品中同一情节的大小复现强化了作品中的个人烙印,此外,他还在一些情节的参差中徐徐展现一个读者未能把握的巨型故事世界,又通過反复开掘阐释着一些固定主题而给予读者同源异流的丰富体验层次。
三、以一截截的“海浪”
连缀出整体之“海”
固定主题的反复开掘阐释是以截面的方式来完成的,截面的累积,是形式意义上的重复。弋舟反复开掘阐释亲子关系的隔阂,短篇小说《敲开千禧年的最后一声钟声》、中篇小说《等深》中以截面呈现了父子关系的状态,长篇小说《战事》中的母子隔阂又是以一个个截面构成。与整个情节相比,这些都是琐碎的截面,但这些截面使作品丰盈起来,也和其他作品区别开来。弋舟清楚自己的这种写作能力,不仅在同一主题的演绎中带给读者惊喜,在不得不平衡着外部旨义与个人意识的“任务”《春秋误》中,他便有意识通过“琐碎”完成了让“两个千年的英雄”“有了人的气味”的构造30。在承受了选择尊重他人意愿而非更多彰显个人观察的“断臂之痛”的《空巢:我在这世上太孤独》的写作中,仍然有意识地直呈“每一个具体而微的个人”而非“泛指”的“空泛的‘整体”31。
“截面”呈现得丰富,是依托于对“整体”的理解。“很多时候,我都会忘记了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空巢老人。面对老人,我只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竭尽全力去深入具体地理解对方是个怎样的老人,并力图以其本来面目记录下来。”32——这段虽然是对自己非虚构写作过程的自述,却让人联想到,在描述一个人时,他也会去“尽可能竭尽全力去深入具体地理解”,他的思考也不会局限于人和事的表面,而是如此进入并不“空泛”的包罗万千的“整体”。
弋舟故事中许多构造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顺理成章地形成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整体”思考,弋舟的小说中,亲子关系的隔阂不止步于亲子间,他跟踪了其连锁反应。还是在《战事》中,从母亲离去开始,被弃的不安感便持续地影响着丛好,在她从少女到中年的几段恋情中都留下了痕迹。初恋之时,男友张树犯罪服刑,丛好的感觉是张树突然抛下了她一人;婚后,丛好又从与丈夫的互动中得到许多不安之感;到与张树死灰复燃,却被张树用来与丈夫做了交易,意味着她人生中的又一次被弃。《战事》以丈夫的眼睛看到,丛好在阅读沈从文小说《边城》时用铅笔勾出描写老船夫去世后少女翠翠的无依无助的语句,这个细节将中年时期她内心深处仍然孤弱的状态暴露无遗。
也因“整体”,《战事》中对茕茕孤立的丛好起到安慰作用的,竟是遥远的伊拉克战事。伊拉克战事的新闻,陪伴着在具体日常间挣扎着的丛好,以地理上的距离,冲淡了她的悲伤,“因为实在是与己无关,所以就不是令人难以承受的”,“把她从现实中带离,成为了一个不知愁苦的旁观者”33。这一“妙想”,不免让人想起张爱玲《倾城之恋》,《倾城之恋》中战争“成全”了渺小个体的亲密关系。也是“整体”思维的体现,《战事》中还以时间层次减轻了青春少女故事中的悲伤之感,中年作家身份下丛好对少女时期生活的回忆,与少女时期经历的即刻描述间隔着出现,叙述的语调仿佛杜拉斯《情人》中那般从容,多了岁月的沧桑。
此外,弋舟长篇小说《蝌蚪》和《战事》同样从青春时候开始写人物的成长史,同样是与上一代有着很多情感和经验上的隔阂并曾身处暴力的边缘的人物,《蝌蚪》中少年“我”的成长感受与《战事》中的少女丛好却大不相同。《蝌蚪》中,因为父亲,年少的“我”过早地对世间的暴力感到“苍老和厌倦”34,但在观察到父亲的初恋对牢狱之灾中的父亲的不离不弃后,为女人对父亲的极度付出以及父亲后来的恩将仇报感到疑惑。这使得读者意识到自己踏足了弋舟构拟的巨型世界中的不同区域。
回到最新短篇集《辛丑故事集》中的篇目,短篇小说《拿一截海浪》标题中,便有从整体中“截取”一部分的意识。《拿一截海浪》中,男人正自驾回乡参加女儿的婚礼,并斥巨资准备了砗磲雕刻成的“一截海浪”作为新婚礼物,不料途中撞死了一条黑狗,因为内心难以跨过撞死一个生命的坎以及遭遇了另一条狗对他的声讨,他感到寸步难行。小说借丘吉尔名言“心中的抑郁就像只黑狗,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35来暗示本来他的心中便有如同黑狗啃咬的抑郁情绪。女儿、交通事故报警接线员和曾经爱过而后因家庭负罪感而放弃的女人都未能理解他在撞死一条黑狗后的情绪。
这几次求助的失败,正是男人与他人及社会长期隔阂的一个反映。自我放逐到缺乏家庭和社会关系的海南岛,是因背叛了家庭和所爱之人而选择自我惩戒;“拿一截海浪”,潜意识里是以能够代表自己的部分来取得与他人的联系,因为“那个岛上,除了海浪,什么都跟我没关系”36;不顺利的男人发现,自己“不过是从一片海去了另一片海”,“不过是从一片海回到了这一片海”,他“拿着一截海浪,又好像双手空空的人”37。在小说的末尾,男人的认识似乎颇为无奈,但又未尝不是解脱,因为这样的认识实际会使得他获得消极的联系感——在心中对于联系、对于故土的执着消失后,便生活在整个同一片海中,无所失去而既空虚又强大起来。而这篇小说反映出的又不止他一个人而已,有足够的素材供给读者以对故事中的他者的想象空间。
《拿一截海浪》的标题中有“海”字,《辛丑故事集》六篇故事中有一篇故事标题中也有个“海”字,是《德雷克海峡的800艘沉船》。“德雷克海峡”是轮船到达南极的必经之路,穿越德雷克海峡的行为意味着在大自然中冒险的精神和勇氣。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这篇故事中几个相似又不同的小人物分别沉浸在他们各自不幸而又特别平凡的生活中,他们自发能做到的极限只是若有似无的反抗。例如段欣慧。亡夫的财产使得中年的段欣慧衣食无忧,她的生活似乎不会出意外,但又过于平顺。她在飞机上看到一则称得上稍稍能打破平静的海难报道——“目前已有800艘船只沉入德雷克海峡”,身临其境地想到了“寒冷的海峡,疾风骤雨,怒浪惊涛”38。又如吴尤莉。同为中年丧夫,吴尤莉从婚姻中继承下来的是累累债务,父亲从中学退休后帮其开网约车,在此过程中父女关心爱护着彼此。儿时没有幸福的家庭,长大后又为亡夫所累,后在爱情中不能跨越年龄的差距,并眼看对方可能由于自己而发生了严重车祸,吴尤莉“成了一艘正奋力穿越着凄苦海峡的、破浪的巨轮”39。这只是《德雷克海峡的800艘沉船》中人物和故事的一部分。这些小人物,像800艘沉船中的一艘、一艘、另一艘,非常独立。在海面航行时,一艘艘轮船与整个德雷克海峡相比,便像一片片飘零的树叶,到它们不幸沉入海底后更是如弃草芥。但它们同处在德雷克海峡的地理位置,以数量的叠加构成了整体,就像显现了那没有在生活整体中浮起的一部分,自有一份属于人的壮阔。
在《德雷克海峡的800艘沉船》中,不仅故事的本身是发生在生活整体中的一部分,故事间一些人物的关联在俯视的角度才能发现。虽说在《辛丑故事集》的另一篇小说《化学》里,化学家感受到“大家同在一个环形的跑道上,在一个开放却又互相关联的世界里”40,但一些人物关系是身处故事中的人物不会清楚的,要以作者、读者所处的上帝视角或者说是模拟“整体”的视角才能看到,例如《德雷克海峡的800艘沉船》中段欣慧和吴尤莉的关联。段欣慧和吴尤莉在故事中会有着什么关系呢?这在故事的最后才可厘清——段欣慧下飞机后乘坐了夜间吴尤莉父亲帮女儿开的网约车,这位网约车司机一反常态地表现出了“古怪而热情”41,给段欣慧留下深刻印象;而他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段欣慧的“武汉口音”42勾起了他对自己在武汉大学历史系生活的回忆。这些弱联系,也显现在2020年《庚子故事集》中的《人类的算法》、2018年《丁酉故事集》中的《缓刑》和在2017年《丙申故事集》中的《但求杯水》。
弋舟多写、擅写个体,是以截面的形式完成对个体敏锐刻画的“心灵捕手”。这些捕获得益于对整体的观照。他笔下多有具体姓名、职业的个体,同时服务于整体,如同一截截“海浪”,悄然无声连缀起整个的“海”。
结语
没有停下来,弋舟小说的重复在转变、构拟与连缀中彰显出生机。《敲开千禧年的最后一声钟声》已变得开阔敞亮;多部作品中情节和主题的大小复现,除个人烙印外,也有巨型故事世界和同源异流的构拟;在对整体的观照之下描摹的一截截“海浪”,使整体呼之欲出。
从重复中理解这些已成为他写作过去的作品,似乎便能够立体地认识这位作家的写作空间了。在这个有序又恣肆的空间中,他的创作还在新增。将会有承载着新变的小说沿着某一轨道径自飞来,又拓宽弋舟的写作空间。
【注释】
①②弋舟:《犹在缸中》,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第13-14、6页。
③⑦⑧1113141618192021263536373839404142弋舟:《辛丑故事集》,中信出版社,2022,第11-21、20、21、16、17、18、19、18、21、21、19、19-20、109、110、112、119、140、39、143、132页。
④⑤⑥⑨⑩121517弋舟:《跛足之年》,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第11-15、16-24、15、15、12、13、14、14页。
2225弋舟、程立源、陈舒遥:《小说与人间消息》,《绿洲》2022年第5期。
23弋舟:《雪人为什么融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第38、39页。
24这里的“它”指弋舟作品《跛足之年》。
2728弋舟:《刘晓东》,作家出版社,2014,第38、50、62页。
2933弋舟:《战事》,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6,第45、46、53页。
30弋舟:《春秋误》,作家出版社,2018,第294页。
3132弋舟:《空巢:我在这世上太孤独》,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第15-16、16页。
34弋舟:《蝌蚪》,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0,第46页。
(丁茜菡,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