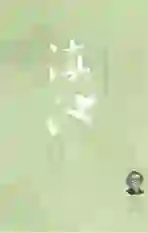雕刻者
2024-03-08黄建林
黄建林
点睛前:
午后的阳光像一把刀
把锋芒藏在温暖里
在老人的背和大地上雕刻
老人俯下身子
与倾斜的大理石平行
娴熟的用铁锤敲打刻刀
一个个名字就整齐而飘逸的
刻进石碑
石头是加厚的,仿佛这样
才能记得更深更久
老人说:灵应寺重修大殿
勒石铭记捐了功德者
每敲下一锤
就有木鱼和钟磬之声
刻了那么多的墓碑都是记录生死
这次,锤和刻刀
和菩萨走得最近
点睛后:
老人把一个个名字
刻进墓碑。刻刀尖利
石头厚重,一笔一划都是
一个人留在世间的足迹
也是刻碑人,磨损殆尽的
砂石飞溅的一生
唯一的一次,老人给灵应寺
刻功德碑,锤子、刻刀和
石头的撞击声,像一道道
激越的瀑布,汇入
木鱼和钟磬的河流
那一刻,老人肃穆的脸上
泪水滂沱,他觉得自己
在为菩萨抄写经文
那一刻,阳光辽阔
大地舒展,如一本打开的经书
点睛师评论:
这首诗的叙述支点是“雕刻”——老人在碑上刻字,温暖而暗藏锋芒的阳光雕刻大地上的万事万物,包括刻字者。相较于老人刻碑,后者显然更庞大、深刻,也更具备叙述的张力和延展性,有深厚的阐述和想象空间。
我猜测作者也是这么理解的,所以一开头就先写了阳光,以为后续的叙述營造一种具体的语境或者场景。这样写本身无可厚非,但缺乏铺垫,稍显头重脚轻,后文对前文缺乏必要的回顾和回应,导致情感密度、语言力度明显弱了下去。我的建议是,调整前后文的位置,以此调整叙述的重心,并对“雕刻”进行大刀阔斧的升华,既然诗歌中提及寺庙、木鱼和钟磬,何不把“雕刻”,延伸为“抄经”?
这首诗的另一个叙述核心是雕刻者在墓碑上刻字时和在功德碑上刻字时的不同心境,以及其间微妙的感受和情绪——作者是旁观者,但经由对叙述对象(雕刻者)动作、言行、神态的细致观察,以及身临其境的想象,作者进入了雕刻者的内心,在写作这首诗时,作者与叙述对象是合二为一的,他们互为彼此的肉身和投影。
可惜的是,作者的叙述流于表象,未持续深入,稍显浅薄。如果沿着这条脉络持续拓展,诗歌可能呈现出另一种更加动人的样式。
另,标题“雕刻者”是实指,语意稍显狭窄,建议改为“雕刻”,其内涵和延展性会强一些,也更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