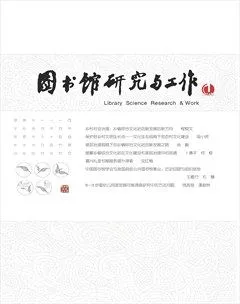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康熙《御制文第四集》稿本考述
2024-02-09杨国彭
本文系202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故宫博物院藏康雍时期内府稿抄本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2CTQ004)的阶段性成果。
摘 要: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康熙《御制文第四集》稿本一部三十册,是雍正年间内府编订《御制文第四集》时形成的一部修改稿本。其内容有可能是在康熙间王掞编录本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书通过夹条和浮签等形式呈现了修订的过程,并在收录篇章、文辞表述、人物评价、诗文字句、人名地名译法和涉及康熙诸皇子记述等方面不同于刊本。该稿本是对康熙朝史料的还原和补充,诗文部分则保留了康熙帝诗稿原文。同时,该稿本也展现了雍正帝修改康熙稿本的意图,并呈现了雍正朝内府稿本的修订方式,因此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关键词:康熙帝;《御制文第四集》;稿本;雍正帝
中图分类号:G256.2文献标识码:A
An Examination of the Manuscript Version of Kangxi's Collected Imperial Writings Volume Four from the Library of the Palace Museum
Abstract The Palace Museum Library houses a thirty-volume manuscript version of Kangxi's Collected Imperial Writings Volume Four, which represents a revised edition created during the Yongzheng period when the imperial court edited Collected Imperial Writings Volume Four. It is possible that this manuscript was based on Wang Yan's compilation during Kangxi period, and the revision process is evident through the use of interlinear notes and marginal comments. In terms of the included content, literary expressions, character evaluations, poetic passages, transliterations of personal and place names, and descriptions of Kangxi's sons, this manuscript differs from the printed versions. This manuscript serves as a restoration and supplement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the Kangxi period, preserving the original text of Kangxi's poems. Furthermore, it sheds light on Yongzheng's intent in modifying Kangxi's manuscript and provides insights into the editorial practices of the imperial court during the Yongzhengperiod, making it of significant academic value.
Key words Emperor Kangxi;Collected Imperial Writings Volume Four; manuscript version;Emperor Yongzheng
康熙帝玄烨一生诗文作品蔚为可观。除《御制避暑山庄诗》《御制千叟宴诗》等单行本诗集外,有诗三集、文四集刊行于世,其中,三部御制诗集刊行稍早,其内容为后辑之四部御制文集所囊括①。康熙四部御制文集共一百七十六卷,录有康熙帝的敕谕、碑、论、说、解、序、记、碑、颂、赞、箴、铭、赋、诗等大量作品。除《御制文第四集》(以下简称《第四集》)外,其他各集均于康熙帝生前所刊,惟“五十一年以后御制未及辑录,雍正十年,世宗宪皇帝命编录校刊。凡三十六卷,内勅谕二十卷,论、序二卷,记、碑记、碑文一卷,铭题、跋文、颂一卷,杂著七卷,诗五卷,是为《四集》”[1]。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有康熙《第四集》稿本一部三十册,各册内页中所夹签条琳琅满目,文字上所贴浮签连连,初步判断,此书是内府编订《第四集》时形成的底稿本。那么,该稿本是何时形成的?内容来源何处?与刊行本《御制文第四集》有哪些不同?其史料价值如何?这些问题,值得探究。
1 稿本《第四集》的编录及写成年代
1.1 《第四集》的编录
前引史料称康熙“五十一年以后御制未及辑录”,然考诸档案,《第四集》之辑,非自雍正间始。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六月二十四日,大学士王掞奏称“臣蒙恩命编录《御制诗文第四集》,谨照前缮写进呈,仰乞皇上睿览”[2],显示王掞早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已受命编录《第四集》,揆其语意,是書当时已有成稿,并进呈给康熙帝御览。然而直至康熙帝去世,此集仍未见付梓。
雍正十年(1732年)所刊《第四集》已将王掞除名。据卷末所载编校诸臣名衔,编录官为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果亲王允礼、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蒋廷锡,校对官为翰林院侍讲学士方苞,另有校刊翰林十四人、监造官六人。
1.2 稿本《第四集》写成年代
既然《第四集》在康熙和雍正间分别有稿本问世,那么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稿本《第四集》是何时写就的呢?首先,从篇目次序上看,稿本与雍正十年(1732年)刊本《第四集》相差无几,说明其内容与雍正年编录本有直接关系;其次,稿本《第四集》有康熙“遗诏”一篇,其内容与刊本亦近乎相同。学界已经明确,康熙“遗诏”是雍正帝根据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的“上谕”改写而成的[3],证明稿本的书写时间是在康熙朝之后;第三,稿本全书避玄不避弘,可知写成年代是在乾隆朝以前。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判断此稿本写成年代是在雍正朝,进一步来说,该书是雍正帝命人编录康熙《第四集》时形成的底稿本。
2 稿本《第四集》的校改形式及流程
全书存二十九卷三十册,与刊本相比,该稿本无卷二十五至三十一“杂著”部分。各册用纸捻毛订,半页八行十八字,无栏框。末一册系五篇时文之誊清稿本,有版框,无界栏。全书除最末一册外,内容皆非直接写于书页之上,而是裁剪各篇字纸,分别粘贴排列。从其笔迹上看,全书由多人合力写就。其相邻各纸色偶有深浅不一者,字迹也多有不同者,说明中间必有内容被裁去。据此推知,编录官先成一稿,遇有不宜入集之篇,即行剪除,仅留合适之篇分粘于各页,另成一稿。由此避免在字面上留下删削痕迹,又省去誊录之繁。此种形制之内府稿本,为目前仅见。书内带有大量夹条、浮签,并偶有朱笔批改之处。兹将三种形式的改动介绍如下:
2.1 夹条拟定修改意见
夹条为尺寸一致的细窄长纸条,夹置于各页之间,上写改动意见,语意敬谨谨慎,有以下5种改动形式:
(1)拟改
拟定更换的字句。如卷一“谕大学士九卿”一则,记述了两江总督噶礼和江苏巡抚张伯行相互攻讦之事,负责审讯的张鹏翮等人并未审出何等明确结果,康熙帝认为这是他们“似为两边抵饰合解,瞻徇定议。事至此极,岂可不徹底审明,乃两面调停……率大张其事,以极利害之辞参奏……这案发回,著大学士九卿等详看”。夹条四则,分别对这段文字提出了拟改意见,其中,“抵饰”拟改“掩饰”,“事至此极”拟改“大臣互相参劾”,“极利害之辞”中的“利害”二字拟改“重”字,“这案”拟改“此案”。
(2)应改
提出修改字词中有讹误者。如卷二十“遗诏”中的“非朕凉德之所至也”一句,夹条指出“至”应改“致”。“随文帝亦开创之主”,夹条指出“随”应改“隋”。
(3)似不可用
拟定删削字句意见。如卷一“谕大学士九卿”,“共享安乐,各安生理,优游闲居而已”。夹条提出“‘各安生理四字似可不用”。卷三“谕礼部”,“乃推诿僧官不能奉行,奏称可恶,拿送刑部,深为溺职”,夹条提出“‘奏称可恶,拿送刑部八字似不可用”。
(4)请旨
校审官对难以决断之处,呈请雍正帝裁定。如卷十“谕大学士马齐理藩院尚书赫寿等”一则,是康熙帝对鄂罗斯国强买强卖之事作出的谕示,与前后两则讨论米仓之旨并不相干,夹条提出该则谕旨“似无关系,应否入集请旨”。卷十一“谕诺尔布色楞布达礼等”一则,夹条提出此内容是“边外军机”,“臣未能深知,字句不敢轻动,伏候圣裁”,可知此则谕旨之相关改动,系雍正帝所亲断。又如卷十“谕各路将军”一则,“杭霭地方兵主之祁里德并巴尔库尔之将军雅木布等”,夹条提出“‘兵主二字可疑,谨请旨”。
(5)奉旨
此种改动用词直接,与其他敬谨语气明显不同,当系校审官奉雍正帝之旨而进行的校改。如卷六“谕大学士等”一则,是康熙帝对汉大臣于科场及保举荐官之事极力营私提出的批评,夹条提出此道谕旨“不必入集”。又如卷十九“谕吏部”一则,指出捐纳官员升任太速,夹条提出“谕吏部一篇与次页谕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一篇文义相同,此篇不必入集”。此两篇谕旨均未收进刊本中。
2.2 浮签修改文字内容
浮签内容多数是遵照夹条拟定意见修改的,但是亦有其他情况。
(1)无夹条之修改。此类情况颇多,如卷二“谕王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一则,在无夹条的情况下,多处文字直接粘贴浮签进行修改,“朕昨进京,见各处为朕六十寿庆贺”改为“朕昨回宫,见京城内外为朕六十寿庆贺”,“今已成矣,难毁众志”改为“今已成矣,难违众志”,“朕已老矣,有若无,实若虚,夙夜匪懈,履薄临深之念与日俱增,岂敢自有满假乎?”改为“朕已老矣,夙夜匪懈,履薄临深之念与日俱增,岂敢稍自满假乎?”此外,除前二十卷之敕谕、诏以及二十一卷之论外,其余各卷之记、文、诗等均无夹条,是直接粘贴浮签修改的。
(2)未据夹条而另改。如卷三“谕礼部”,“各处游僧尝致僧官等置身无地”,夹条提出“尝致僧官等置身无地”拟改“岂肯受其约束”,但实际浮签并未按此修改,而是改为“各处游僧尝胁制僧官至无容身之地”。
2.3 朱笔批改
书中另有多处改动,是用朱笔直接涂写于字面之上,字迹皆较随意。在康熙帝稿本上如此批改,只能是出自雍正帝御笔。其中,卷五“谕议政大臣等”一则,改动最多,如“济卜宗丹巴胡土克图”朱笔点“济”改为“泽”;“被我二百汉兵几个子杀得不堪”朱笔修改为“被我二百汉兵几个子击败,令不堪”;“将噶尔旦之尸首,伊女准齐海解送前来”,朱笔改“尸首”为“骸骨”,“伊女”前添一“并”字。“尔汗可放心安居矣”,朱笔在“尔汗”后添一“等”字,又涂去。卷六“谕议政大臣”一则,“将现在所议之事,发于博贝,或派勤劳章京或笔帖式作速飞驰”,夹条提出改“勤劳”为“勤力”,朱笔改为“勤慎”。卷七“谕议政大臣”,“况今天暖草发之夏季”一句,“天暖”二字以墨笔圈出。卷二十一“朱子全书序”,“读书五十载,只认得朱子一生所作何事”,朱笔点出后,浮签改为“只认得朱子一生居心行事”。同卷“历代年表序”,最末句“翰林检讨马豫锓板告竣为序,其大指如此”以朱筆勾出,并粘覆空白浮签。
综合以上分析,推断该稿本改动流程如右:编录官编选内容,形成一稿,校对官提出修改意见,书于夹条上,呈请雍正帝御览审阅。获允则粘贴浮签改动,不允则将夹条折起不作修改,或另作它改,雍正帝亦会亲自参与批改;夹条有两次以上修改者,说明雍正帝与臣工之间曾往来反复商酌多次;诗文部分仅覆浮签而无夹条,似说明校对官对此项内容的改动具有一定决定权,而雍正帝亦未提出深入意见。
3 稿本《第四集》的版本性质及内容来源
在归纳出稿本《第四集》的校改形式和流程后,有两个基本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一是稿本《第四集》虽然有大量修改痕迹,但是这些呈现在夹条、浮签上的改动,是否是《第四集》成书的最终依据?换言之,该稿本是一部初稿本,修改稿本还是定稿本?二是该稿本的内容是如何形成的?
3.1 稿本《第四集》的版本性质
首先,稿本全书的结构框架及整体次序与刊本《第四集》并无区别,可知该稿本在內容上已基本成型,由此可知该书并非是一部初稿本。
其次,经与刊本进行对比,发现夹条、浮签上提出的改动意见,并未被刊本所完全采纳,例如卷四“谕大学士松柱左都御史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揆叙”一则,稿本中并无改动意见,但刊本增入了“再科道官员职任甚重,亦有任意告假回籍者”一句;卷十“谕学士星俄特常鼐郎中三宝吴硕色鄂启卿齐布员外郎吴黑达赖”中的“第如此查验,商船或致稀少,然船少于贸易,亦更有利也”一句,夹条提出“此数句似可不用”,而浮签却将“更有利也”改为“更有益也”,实际上刊本均未予采纳,该段文字未作任何改动;卷三十四“汤泉道上遇雪口占”一诗,稿本末句为“即使天公难不平”,浮签改为“须识天公有不平”,但刊本最终作“莫道天公有不平”。另外,稿本内所有“泽妄阿喇布坦”“贼旺喇布坦”“?妄阿喇布坦”等称呼,夹条、浮签均提出改为“贼妄阿喇布坦”,但刊本最终统一刊作“?妄阿喇布坦”。这些情况显示夹条和浮签并非改动的最终依据,该稿本仍处于尚待进一步修改的阶段。由此可以推知在此稿之后,当还有一次或多次改动。
综合上述判断,可知该稿本是介于初稿本和定稿本之间的一个修改稿本。只有最末册《时文》四篇,书页上未有任何改动痕迹,其内容也与最终刊本完全一致,应即付梓前的定稿。
3.2 稿本《第四集》的内容来源
上文虽然已经明确该稿本的性质,但是仍需要通过与其他史料的对比,分析其内容是如何形成的。
(1)关于谕旨部分的对比
《第四集》所收部分谕旨,在《康熙起居注》中亦有记载,如稿本《第四集》卷二《谕各直省老人》载:
《书》称文王善养老者,孟子云七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帝王之治天下,发政施仁,未尝不以养老尊贤为首务,近来士大夫只论做官之贤否,移风易俗之效验,所以不暇讲究孝弟之本心。朕因今日之会,特宣此意,若孝弟之念,少轻而求移风易俗,其所厚者薄而其薄者厚矣。尔等皆是老者,比回乡井之间,各晓谕邻里,须先孝弟,倘天下皆知孝弟为重。此诚移风易俗之本,礼乐辞让之根,非浅鲜也。昨日甘霖大沛四野沾足,朕心大悦。尔等毋误农时,速回本地,特谕。康熙五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此谕在《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三月二十五日,记曰:
《书》称文王善养老者,孟子云七十非帛不暖非肉不饱。帝王之治天下,发政施仁,未尝不以养老尊贤为首务,近来士大夫只论做官之贤否,移风易俗之效验,所以不讲孝弟之本心。今日之会,特出此意,若孝弟之念,少轻而求移风易俗,是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矣。尔等老者,比回乡井之间,各晓谕邻里,须先孝弟,倘天下皆知孝弟为重。此诚移风易俗之本,礼乐辞让之原,非浅鲜矣。昨日甘霖大沛田野沾足,朕心大悦。尔等无误农时,速回本地,特谕。
《康熙起居注》基本上是当时人记当时事,所载内容距离事件发生时间很近。兼之《康熙起居注》的“所以不讲孝弟之本心”等句,不及稿本的“所以不暇讲究孝弟之本心”等句合理妥当,可知《康熙起居注》记录此谕在前,稿本《第四集》修改在后。成书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的《万寿盛典初集》亦收录了此谕,其文字与稿本《第四集》完全一致[4],证明该谕是在康熙朝修改完成的。此类情况,在稿本所录敕谕中颇为常见,以此可以推知,稿本《第四集》收录的大部分谕旨文本,在康熙朝即已润饰过。但亦有例外,卷十六有“谕大学士马齐等”一道,内容是康熙六十年(1721年)康熙帝痛斥王掞立储事。稿本《第四集》所录该谕旨有大量内容不同于刊本,节录此谕如下,其中括号内为刊本文字:
六十年大庆,大学士王掞等不悦,以朕将终(衰迈),建储为要,欲放出二阿哥。伊等借此邀荣,万一有事,清朝之亡与不亡(安危休戚),意谓与我汉人何涉。至于国中似畜类愚昧(凶顽愚昧)之徒,一无所知。不顾身命及发掘祖父坟墓、绝灭宗族行者亦不少(不顾身命宗族,干犯叛逆之罪,而行者亦不少)。朕不得不以厉语还答,故不计是非(年老将衰,难以隐忍),随手书此发出。王掞以伊祖王锡爵在神宗时力奏建储之事为荣,常夸耀于人,不知羞耻。王锡爵尽力(极力奏请)建立泰昌,不久而神宗即崩,崩时亦不甚明……至愍帝不能保守,为陕西马牌子李自成所偪,自尽尸暴于东华门桥上,官员无一(无)寻收者……王锡爵行事,汉人(同时之人)亦甚恶之,故作牡丹亭歌曲(词曲)极肆诋詈……
二阿哥两次册立为皇太子,教训十年,不能成就。朕知迟久必为所害(朕为宗社及朕身计),故严行禁锢……凡此皆为父之私情小惠,不能自已,所谓姑息之爱也,人何得因此生疑?尔等若不心服,可将大阿哥、二阿哥并朕举国评断,孰为非孰有实据,即正其是非,以解祖宗、皇太后之郁忿。朕预知必有此事,前旨微寓其意,今既显露,故降明旨……今朕衰老,中心愤懑,众人虚诳,请行庆典,朕岂屑此乎?康熙六十年三月十五日。
此谕亦载于《圣祖仁皇帝实录》,文字与刊本《第四集》相同[5]。据《圣祖仁皇帝实录》载,此文是康熙帝手书,传谕给诸王大臣的。该谕存于《第四集》中,十分突兀,明显针对的是王掞。由于雍正帝对王掞上奏立储事十分反感②,而王掞又曾在康熙朝奉命编录《第四集》,因此,将这道谕旨编进《第四集》,显然是出自雍正帝打击王掞的诛心之举。稿本收录的此道谕旨,文字语气之激愤、措辞之露骨,颇为少见,当是未经润饰的康熙帝上谕原文。
此外,稿本《第四集》所收“遗诏”与刊本相比,仅有两处讹字改动,即“非朕凉德之所至也”一句中的“至”改“致”,“随文帝亦开创之主”中的“随”改“隋”。康熙“遗诏”是雍正帝根据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的“上谕”改写而成的,严格来说,不能视作康熙帝的作品,把它收录进《第四集》,显然出自雍正帝的旨意。
(2)关于御制诗文部分的对比
稿本《第四集》中的部分文章,散见于其他史料,如卷二十一至二十二收录书序9篇,包括《朱子全书序》《御选唐诗序》《康熙字典序》《周易折中序》等,俱已刊入各书中流行于世,文字与稿本《第四集》并无差异。稿本《第四集》中的部分诗篇在其他书中亦偶有记载,如卷三十五《赐老大臣》:
旧日讲筵剩几人,徒伤老朽并君臣。
平生壮志衰如许,诸事灰心懒逼真。
求简逡巡多恍惚,遇煩留滞累精神。
年来词赋荒疎久,持笔无文每自嚬。
据王鸿绪《横云山人集》载,此诗是康熙帝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六月十一日御书于金扇上赐给王鸿绪的,稿本句首的“旧日讲筵剩几人”在《横云山人集》中被记为“旧日讲筵有几人”[6]。又如卷三十六《挽总督赵弘爕》:
四十余年辅近京,旗民称善政和平。
保全终始君恩重,奄逝彷徨众涕盈。
不畏刁顽事反覆,久司锁钥务精明。
官方无愧怆新别,节钺空悬揽辔情。
该诗亦记录在康熙《顺义县志》中,诗名为《御制挽北直总督赵公诗》[7]。稿本《第四集》中的“久司锁钥务精明”一句,《顺义县志》记为“欲图锁钥务精明”;“官方无愧怆新别”记为“官方无愧怆情切”。这两首诗均是康熙帝赐给臣下的,所依据的当是康熙赐诗的原文。稿本《第四集》比其他两书所录诗句更为妥适,当视作后来修改的。需指出的是,康熙帝生前刊行的三部御制诗集中诗句的矛盾、错误、遣词不佳等低级问题十分普遍,而四部御制文集重新予以收入后则大有改观。说明康熙帝生前即已对其诗作不满,并进行了大量修改[8]。可知稿本《第四集》收录御制诗在康熙朝亦经过了修饰。
从以上对比来看,稿本《第四集》的内容来源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采录康熙朝已经润饰过的谕旨、诗文。如前文所言,康熙时王掞曾奉旨编录《第四集》,并且已有成稿,因此,不排除这部稿本《第四集》是在王掞编录本的基础上编选而成的。二是直接采录康熙上谕原文,如康熙帝怒斥王掞谕旨一道。三是编入雍正帝即位后组织人员撰写的“遗诏”。通过这三方面的糅合,由此形成了这部稿本。
4 稿本与刊本《第四集》的内容差异
(1)收录篇章不同
稿本中有三篇谕旨及一篇序文,为刊本所无。如卷六“谕大学士”一篇,内容是康熙帝对汉臣在科场及荐官之事中极力营谋的批评,该篇谕旨是在雍正帝的指示下予以删除的,为何要删掉此篇,原因尚不明确;卷十“谕大学士马齐理藩院尚书赫寿等”是康熙帝对鄂罗斯强卖中国商人皮抄现象所作谕旨,删除的理由是“似无关系”,即该篇谕旨与前后内容不相干;卷十九“谕吏部”,是康熙帝对捐纳官员升迁太速的谕示,“与次页谕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一篇文义相同”,因此予以删除;卷二十九“温泉试士序”是一篇骈文,辞藻华丽,内容空洞,刊本未予收录。
(2)文辞表述不同
稿本与刊本之间的大部分不同,主要体现在文辞表述上。如稿本卷十一“谕大学士马齐松柱李光地王掞等”中有“历观自古以来建立起居注或数月而废,或一二年而废,未有似朕设立如此之久者也”一句,此语未免有失严谨,刊本改为“历观古来帝王建立起居注亦间有废置者,朕在位日久,设立多年”则妥贴许多。又如稿本该谕中有“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身亲理,无可旁贷,若一事而两人分理,则断断不可”一句,刊本改为“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断不可”,更符合康熙帝的意思表达;卷十七“谕大学士”一则,稿本文为“以今观之,若受庆典,则朕之非不可枚举矣”,康熙帝仁圣如斯,焉可自论其非不可枚举?此句遂被刊本改为“则私议朕之过者不可枚举矣”。对比来看,刊本的字句表述更加合理。
(3)人物评价不同
稿本与刊本《第四集》对官员的评价用词不尽相同。对比来看,稿本《第四集》中的用词颇为通俗,例如稿本卷一“谕九卿”中的“朕以张伯行为天下第一清官”,刊本作“朕以张伯行操守为天下第一”;卷三“谕吏部”,稿本文为“鄂海屡任陕西,熟谙地方,兵民情性俱所深悉,且人品端方,居官甚优”,刊本作“才具颇优”;稿本卷三十三诗“浙闽总督范时崇陛见来京,朕每念祖为开创宰辅,父乃忠义名臣”,刊本作“父乃尽节忠义”。稿本中的“天下第一清官”“忠义名臣”等词,口语化明显,经刊本润色后,则雅驯了许多。此外,稿本对一些官员的评价也并不十分严谨,如卷十二“谕大学士马齐等”,稿本为“陈瑸居官甚优,操守极清,如伊者朕实未见,即从古清官亦未有如之者”,此语未免失实,刊本改为“陈瑸居官甚优,操守廉洁,清官如伊者朕实未见,恐古人中亦不多得也”,则合理了许多。
(4)涉及皇子的记述不同
《第四集》中涉及皇子的记载屈指可数,但是稿本与刊本皆有不同,说明《第四集》对此十分敏感。如稿本卷二“谕礼部”中的“朕惟愿臣清子孝兄友弟爱”一句,刊本改为“兄友弟恭”。自康熙帝两废太子后,皇太子位置悬空,三皇子胤祉和四皇子胤禛俨然处于长兄的位置,雍正帝将“兄友弟爱”改为“兄友弟恭”,有借先帝之口对其他皇子进行训诫的意味;卷十七“谕宗人府”一则,为康熙六十年(1721年)六月初六日康熙帝嘉奖平逆将军颜信之谕,其中提到颜信“此番一遵大将军王指授,统领满洲蒙古绿旗兵丁,过自古未到之烟瘴恶水无人居处之绝域”,“大将军王”即皇十四子允禵。允禵在康熙末年储位之争中是胤禛的强力竞争者,对雍正帝来说,此段文字显然没有必要出现,“一遵大将军王指授”八字在刊本中遂予以删除。上述改动显示,雍正帝一方面通过“兄友弟恭”这种字词来训示诸弟;另一方面通过删除“大将军王”的记载,来抹去政敌的功绩。可见雍正帝在处理康熙诸皇子的相关记载时,手法是十分微妙的。
(5)人名地名译法不同
稿本对人名、地名的译法较为混乱,刊本进行了统一。除上文提到的对“?妄阿喇布坦”译名的修改外,稿本中的“济卜宗丹巴胡土克图”“哲布尊旦八库兔克图”等一律被刊本改为“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虎枯诺尔地方”改为“青海地方”;“章京”改为“司官”;“哈尔哈”改为“喀尔喀”等。
(6)诗文字句不同
《第四集》卷二十一至二十四收录康熙帝《论》《序》《记》《碑文》《铭》《题跋》《文》共30篇,其中刊本与稿本完全相同的仅有8篇。少则一二字词略有不同,多则大段文字被改写。卷三十二至卷三十六共收录康熙各种御制诗184首,其中未予改动的仅有16首。如稿本卷三十五“病中忽尔问及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徐元梦,乃同学旧翰林,康熙十六年以前进士再无一人矣,率赋一律以遣消闷”一首“七旬彼此对堪怜,病里还思一慨然。少小精神皆散尽,老年英气薄言旋。常怀旧学穷经史,妄想无能力简编。诗兴不知何处至,茫茫手摄韵难全。”其中的“忽尔”,刊本作“偶尔”;“以遣消闷”,刊本为“以遣闷怀”。“病里还思一慨然”,刊本为“病里回思一慨然”;“老年英气薄言旋”,刊本为“老年岁月任推迁”;“妄想无能力简编”,刊本为“更想余闲力简编”;“茫茫手摄韵难全”,刊本为“拈毫又觉韵难全”。
上述对比显示稿本有大量内容不同于刊本。其中,大部分区别是字句润色,无涉文章大旨,但是仍有部分内容,刊本与稿本原意产生了一定偏离。尤其是诗文部分,刊本的很多诗句改变了稿本原意。例如上文所举诗句,稿本“妄想无能力简编”一句表达的是晚年康熙帝对编书力不从心的消极心态,刊本改为“更想余闲力简编”,则变成了他晚年仍不辍笔的积极态度;此外,稿本的少数篇章及字句未经删减,其内容较刊本更为丰富,例如上文所举卷六“谕大学士”一篇,通过康熙帝之口,描述了科场中的种种弊端,其内容为《康熙起居注》《圣祖仁皇帝实录》等史料所阙载。兹录全文如右:“朕观汉大臣等于科场及荐官之事,不惜身命,极力营谋,每每因此名声大坏,抡才钜典讵可存私?即中式亦必迟至数年后始以中书知县等官补用,奚能骤跻显职?何至于奔竞如此?总之,科场弊端百出,防闲甚难,必诸臣不存私干预始佳。如大臣中有作诗文与士子诵读,士子读其文即仿其文,闱中阅卷便知是何人之派。甚至有觅卷而中者,往往未届试期安排早定,即预知中式之人。故每科进呈试卷,朕不甚观览。设若朕选文一部,士子有用朕选文中词句者,试官见其语必迎合朕意而中之矣,朕不为此也。前考试翰林时,有一人字甚佳,朕一见即知学朕书法,问之诚然,盖是人因在武英殿行走,日临朕所书《千字文》故耳。可见文字各有家派,此等事断不能欺朕也,惟在平日不存私心乃善耳。近贿赂虽不敢公行,而弊亦巧密。总之大臣切不可干预,可传谕九卿至保举官员,至公无私,岂可朋比?公私二字,所关甚重,公则百事理,私则众务隳。每见汉大臣于保举官员殊多滥荐,无所顾忌,更有自不署名,令他人保举,而己从旁相助者,其弊尤巧。此事亦传谕九卿,特谕。五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5 稿本《第四集》的价值
首先,稿本《第四集》是对康熙朝史料的还原和补充。稿本保留了康熙朝文本的内容,尤其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起居注馆被裁撤,稿本《第四集》所载谕旨原文,尤显珍贵。例如前文所列康熙帝斥责王掞谕旨一道,稿本中有颇多关键记载。原文中的“不得不以厉语还答,故不计是非”一语,道出了康熙帝明知自己枉顾事实,仍不惜对王掞及其祖王锡爵肆加污蔑,展示出他极其强烈的泄愤情绪;他甚至要将自己与大阿哥、二阿哥“举国评断”,展示出康熙帝在太子被黜一事中,极力辩称自己并无任何责任,且已仁至义尽。然从“祖宗、皇太后之郁忿”一句来看,其内心并不自信,所以才用“举国评断”这种不切实际的做法来进行辩解。康熙帝将太子被废之事,完全归咎于太子胤礽狂虐,而对自己纵容溺爱、教育失职之过完全不提,正如姚念慈先生所指出的,这“其实仍属于一种心理解脱”③。稿本《第四集》中这些未被删改的内容,对于分析康熙帝晚年在废太子一事中的心理状态颇为重要。又如卷十六《谕满汉文武大臣》一则,是康熙帝对诸臣奏请庆贺其在位六十年的谕示,稿本展示了诸多不同于刊本的字句,节录此文如下,其中括号内为刊本文字:
本朝受命以来,惟知万民(惟以爱养万民)为务,如庆云景星、凤凰麒麟、灵芝甘露、天书月宫诸事,从不以为祥瑞,而行庆典;亦无封泰山、禅梁父,改元贻诮之举。为臣下者劝请举行,以贻事后讥议,奸诈以极(有损无益)。此事朕不准行,自无可谈论,若或准行,必有非之者。朕既明知,可不择其宜而行乎?前朕六旬举行庆典,书生辈议论,朕已备悉,修书等事,朕亦深悔。(前朕六旬举行庆典,无知之妄议,朕已备悉,亦深悔之。)
康熙帝严斥劝行庆典之人为“奸诈以极”,用词十分严厉,这与后文中“微贱无耻之徒谓举行庆典必有殊恩”等语前后呼应。刊本改为“有损无益”后,与康熙帝本意相差甚远。康熙末年,内外困顿,此时若再行庆典,已然不合时宜,是以康熙帝说:“朕既明知,可不择其宜而行乎?”稿本被删去的“书生辈”,是指朝野中的汉官文人;修书之事,當指玄烨六旬大庆时修成的《万寿盛典初集》,该书描绘了遐迩臣庶迎銮呼祝的盛大场面。稿本这段文字,实际上是康熙帝对朝野议论六旬庆典靡费太过,颇有顾忌,并后悔编修《万寿盛典初集》,为汉人讥议留下把柄,这与后文中“幸灾乐祸者借此为言,煽惑人心,恣行讥议,诸如此类,私相纪载”亦相呼应,这段文字折射出晚年康熙帝对内外交困局面极为焦虑的心态。稿本中此类未经删改的内容,不仅可以补充康熙朝相关史实,还能还原出康熙帝晚年文字的本来面貌,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其次,稿本《第四集》中的诗文是康熙帝本人的情感表达。稿本所载诗文形成于康熙朝,有康熙帝本人的审定,而刊本所录诗文,经过了雍正朝的修改,其文意与稿本产生了不同。例如卷二十三《赋得时人不识予心乐》,稿本颈联是“白发筋骨犹能强,半世悠忧足是非”,是康熙帝感叹其一生充满是非之事,刊本改为“暮年筋骨犹能强,半世忧劳幸免非”后,却成了感叹自己一生幸无过错;卷三十三《上元前三日立春》,稿本颈联“难堪慵懒惭词赋,勉强雕虫愧未能”,原是晚年康熙帝年迈心懒的写照,刊本将“难堪慵懒惭词赋”改为“殷勤祈谷宁辞瘁”后,转而突出了康熙帝勤政形象。又如稿本卷三十六《恶繁华》:“村野无知太古风,心依先进是吾衷。傍人问到繁华乐,久历多年烟雾中。”该诗表现了康熙帝对村野淳朴之风的向往之情,对世间的繁华之乐则充满了迷惑、厌倦。刊本改为“不须问到繁华乐,愿与生民遡受中”后,变成了与民同乐的帝王情怀。上述修改,显示刊本《第四集》所录康熙帝诗句与稿本原意产生了偏差,这提示研究者在利用刊本《第四集》诗文分析康熙朝的相关问题时,需十分谨慎。而稿本《第四集》中康熙帝诗文原稿,对于分析他晚年的思想活动及心理状态极具价值,因此可以视为第一手资料。
第三,稿本《第四集》展现了雍正帝修改康熙稿本的意图。需指出的是,由于涉及继位争议,过于敏感的材料并不会被雍正帝编录进《第四集》,因此,该稿本并不能完整呈现雍正帝修订的全部内容。尽管如此,我们仍能从中一窥雍正帝的修改动机。其中,书中的大部分的改动,使字句更加雅驯、合理、积极,可视为维护康熙帝的圣主形象;此外,雍正帝通过改“兄友弟爱”为“兄友弟恭”,以及删掉“大将军王”等记载,来训示诸皇子,抹去政敌功绩,其目的无非是为了维护其自身权威。这为我们审视雍正帝如何处理康熙朝史料,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第四,稿本《第四集》是雍正朝内府稿本书籍的典型代表。雍正朝内府稿本存世稀少,此稿本《第四集》作为雍正帝亲自参与修改的乃父遗作,缮写、改动规格当是很高的,也颇能代表雍正朝内府稿本的修订方式。其裁剪字句粘贴成书的方式,颇为独特;夹条、浮签改动形制严格,虽布满全书,但是皆有章可循;雍正帝在稿本上的偶尔涂写,又展示出他并不十分拘泥于形式;部分字词,往来校改多次,显示慎重之至;书内奉旨改动之处,皆以白纸条书写,与乾隆以后动辄以明黄纸签的形制有一定区别。这些特征反映了雍正朝内府稿本修订的独特之处。
综上,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康熙稿本《第四集》是一部修改稿本,其有可能是在康熙间王掞编录本的基础上,糅合康熙朝“上谕”稿及雍正帝改定的“遺诏”等内容修改而成的。稿本《第四集》大量展示了不同于刊本的内容,并呈现了稿本校改的过程及细节。因此,无论是探究康熙朝的相关史实,还是研究雍正朝内府书籍的修订,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注释:
① 据《四库全书总目》载“(圣祖)《御制诗集》二十八卷,乃高士奇等所校刊,恭检篇目,皆己编入《文集》,次第亦无所更易。”见《四库全书总目》卷173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一百七十六卷》条,清武英殿刊本。
② 关于王掞奏请建储始末及雍正帝对王掞的态度,参见梁绍杰:《清康熙朝大学士王掞奏请建储始末》,《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1期,第120-143页。
③ 关于康熙帝在废太子一事中的心理状态,详见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11-127页。
参考文献:
[1] 鄂尔泰,张廷玉.国朝宫史:卷24[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521.
[2] 王掞.奏为恭请圣安蒙恩照缮御制诗文进呈事:04-01-38-0001-015[A].1717.第一历史档案馆.
[3] 王钟翰.清圣祖遗诏考辨[M]//王钟翰.王钟翰清史论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1169-1193.
[4] 王掞.万寿盛典初集:卷8[M]//纪昀,等.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
[5] 马齐.张廷玉.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9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实录:第6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834-835.
[6] 王鸿绪.飏言集[M]//王鸿绪.横云山人集:卷5.刻本.1721(清康熙六十年):16.
[7] 黄成章.康熙顺义县志:卷4[M].北京:财政局印刷局,1916:47.
[8] 王志敏.谈康熙对诗词的修改——兼谈康熙诗词各种版本[J].语文学刊,1993(2):19-22.
作者简介:杨国彭,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清代内府典籍研究。
收稿日期:2023-08-10本文责编: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