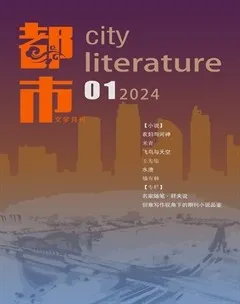故乡的黄荆条
2024-01-31王丕立
故乡土路两旁的田塍地坎上,总会长出一蓬蓬散发着馥郁药味的黄荆条。黄荆条茎干上长有四条棱,五片菱形的叶片从同一叶腋处生发,沿圆弧向四周散开,仿佛指向天穹的绿色鹅掌。
冬天的黄荆条,树叶陨落成怎样的秃枝,我没有一丝半点的印象,只是每到五黄六月,蓬勃惹眼的黄荆条才一下子涌入我的视野。我走在家乡任一条土路上,都能闻见浓烈得让人头晕的黄荆条味道,它紫色长束的花序从来不见有毛毛虫、蚜虫之类的侵扰,只有蜜蜂、樵叶蜂将头钻进花心,露出笨拙的尾部,在里面采集花蜜。我很纳闷,这些让人头晕的花朵,蜂儿采去后会酿出什么蜜来呢?这无害虫问津的灌木引我动念,何必去大山里砍烧柴,砍上几蓬路边的黄荆条岂不更省力?可姐姐告诉我,黄荆条不扯火,一烧全是烟尘。我不相信,偷偷砍过一回,不仅砍的时候茎干绵韧难断,砍回家后,曝晒好多天仍旧无法引火,只在炉膛里腾起呛人的浓浓黄烟。此后砍烧柴时,黄荆条再未入我青眼。
但夏天的许多时日,我仍旧与黄荆条交缠在一起,它的气味便重重地落入我的嗅觉储藏库,成为我记忆的秘藏。
如今,天气炎热的时候,我时不时就会闻到飘上鼻尖的涩涩药味,我知道黄荆条的气味应季而出了,许多儿时与黄荆条打成一片的情景,像江面上的浮标一尾尾从记忆中冒出头来。
记得那时夏天的早上,母亲总会给我布置任务,要我砍几捆黄荆条,然后一束束铺在辣椒、茄子、豆角垄上,盖住它们的根部,一来减少水分蒸发,二来避免滚烫的土壤灼伤植株。剩下的黄荆条,母亲会将它晒得半干,然后晚上煴烟,驱赶稠密得撞脸的长腿蚊。
掺杂着黄荆条浓烈味道的烟尘滚滚而过,蚊子被席卷而去,净场之后的晒场只有月光清洒,如今想来,那真是一幕令人留恋的场景。如今,当我一个人走在异乡纵横交错的街道上,心中不时有怦然心动的暖流淌过,这温暖中竟裹挟着一丝丝黄荆条的味道。
虽然黄荆条不能做烧柴,但那时我们上山砍柴的时候,常常砍两根黄荆条对搭成捆条,用它将零散的一铺柴火束成柴个子,扎在冲担的两头挑回家去。黄荆条特别有韧劲,仿佛茎干中注入了一个顽强的灵魂。一根拇指粗的黄荆棍,若长在不缺水的地方,茎干上的四棱便会被日月抚平,它的顽劲更足,舞动起来更能“呼呼”生风,弹射出去的力度足可打跑一只扑上来咬人的恶狗。因了这,在港台武侠片风靡乡村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和许多小伙伴们手中都握有一根很漂亮的黄荆棍作为打狗棍,拿在手中不时乱舞一阵,享受它 “呼呼”作响带来的惬意。
我二姐最会琢磨着制作玩具,她觉得玩打狗棍太过单调,在她的策划下,我们玩上了打陀螺。任何一个中心对称的实物都可做陀螺,只是抽陀螺的鞭子二姐有所创新。她将打狗棍的末端凿了一个小孔,然后系上长长的枸皮,为了防止枸皮晃动,二姐还发明了一种新颖的编织式打结法,枸皮系在打狗棍末梢,简直与它浑然一体。缠着陀螺朝地上一放,“啪”一声抽动,然后一下一下,打在陀螺上,仿佛一种柔劲包裹着陀螺,又有一种刚强注入陀螺,陀螺旋转出“呜呜”的风声。在“呜呜”风声中,我们所有的疲劳、对食物求而不得的失落,一下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打陀螺累了的时候,我们便一溜儿坐在晒场的凉床上,我的父亲,一个乡村教师,便开始他每天一个故事的讲述。讲故事前父亲往往会提出一个问题,这是他一贯的程序。他问:“你们知道黄荆条为什么总也长不高、长不大吗?”
坐在凉床边,年龄小的孩子直摇头,年龄大的孩子便会说,它是灌木,当然长不高大,长高大了不就成乔木了吗?
父亲会说:“那它为什么只能成为灌木呢?这里有一个传说,我说给大家听听。”于是,父亲便开始了故事讲述。
相传在三国时期,刘备的儿子刘禅年幼时不爱读书,常常惹得他的老师生气。有一天,刘禅又没在学堂读书,而是去了山里掏鸟窝。
他的老师秦宓十分生气,直接追到山上,恨铁不成钢的秦宓顺手折下一根黄荆条抽打刘禅。
但是刘禅不但不害怕,反而因为被打痛了,对这种植物生了怨恨,他颁下一道敕令:“我与丹景傳敕令,黄荆从此永不生。黄荆黄荆,千年不许长,万年不许生。”从此以后,黄荆条就一直长不高了。
父亲讲的故事拉近了我和黄荆条之间的距离,我那时个子出奇的矮小,村里甚至有人开玩笑说我吃了石头,从而长不高。我想我和黄荆条属于同款,它因冒犯权贵受到责罚,那我呢?二姐说我太淘气,所以长不高。我不相信她的说辞,露天电影中出现的主角都是淘的,可他们长得不仅高大,还俊俏呢。我私下里认为,我还淘得不够,既然淘就得淘出水平来。从哪儿学来这水平呢?我犯难了。身边没有榜样,他们都是循规蹈矩的乖孩子,这让我苦闷不堪。稍后没多久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找到了解决的希望。
山旮旯的村民生活过得特别艰苦,家里劳动力强壮的,到年终时才有进项,能得到一点儿生产队的分红。可许多家庭一年到头出队工,到头来还是只能“吃周转”,所谓“吃周转”就是另外拿钱再买一些供全家人吃的口粮。所以除了几粒饭,村里哪一家都极少能吃得上有口味的食品。让人诧异的是,端午节吃粽子本就奢侈,我的母亲还能包出别有香味的碱水粽子。因此,村里条件好一点的人家都请我母亲去包粽子,完工时,他们还会给母亲几个粽子作为酬谢。那时不像现在,商场售卖的东西极其有限,我母亲用的碱竟然是她自己生产出来的。
我见过母亲生产那种碱水。她将晒干的黄荆条烧成灰,将灰倒入适量水中制成草木灰水,用纱布滤出渣滓,黄色透亮的碱水便出来了。她用碱水把糯米泡上一个晚上,第二天,将米沥干后便开始包粽子。
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粽子颜色微黄,看起来就很有食欲,而且它独特的香味和粽叶、糯米混合在一起,吃起来更是香味四溢,再加上口感非常的软糯,因此会让人胃口大开。
我悄悄问母亲她是怎么知道这个包粽子的秘方的,母亲说书上都有记载,包粽子的方法来自一本杂书,书名是什么她忘了,但黄荆条的药用价值她很清楚,并且记得是从一本叫《本草纲目》的书上看到的,书上说黄荆条主要有“祛风涤痰镇咳”的作用。
听了母亲的话,我对书籍产生了无限的渴望。只要看到地上有一片类似于书页的纸张,我都会拾起来看看,要是上面还有铅印的文字,我便如获至宝,仿照它写无数遍,直到对字里的每个笔画了如指掌,我才稍稍停歇。然后,我用树枝写在泥地上,让高年级的大孩子辨认,有些字他们也不认识,我就去问父母和老师。这让我特别受益,在生产队的学校学习仅两年,老师便让我去了大队学校读四年级。我对老师说,我还没读三年级哩。老师说,你认的那些字比三年级课本上还要多。
大队学校的厕所旁是供销社和五七工厂的畜栏,养着好几匹驴子,看护驴子的老头还兼拾荒,拾来的破铜烂铁他就放在驴棚的上面。一次上完厕所,我走在驴棚边,看到上面拾来的荒货袋口骤然滑出一本书来,我情不自禁伸手拿来翻看。没有封面,没有封底,全部是一些代数公式和算法,我对这本书充满了好奇,我决定偷偷带回教室,一个人研读。
每天我都看上面一个例题,然后思考每一个数学符号蕴含的逻辑性,像一个益智游戏,我深陷其中,解着一个又一个扣。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县一中停办一段时间的初中又开始招生了,学校让我前去一试。我还记得语文是看图说话,一个老汉,一手捏一只蚌壳,另一只手提一只鸟儿,满脸得意的神情,我没动笔,读课外书太少的我看不懂这张图画的含义。但那一年数学题很难,我却得到了唯一的满分,后来,我在总分不足的情况下被破格录取到了县一中。
十一岁的我进入县一中就读后,身高不足一米二,到食堂去打饭的时候,打菜的师傅总会把头从窗口探出来寻找我,看到我个子这么小,往往会额外加一块肉给我,并大声对我说:“多吃点,长高些。”
在教室上课时,我的咳嗽声常常打破教室的宁静,年幼的同学往往露出烦躁和厌恶的表情。父亲来学校看我,得知我的近况,他将我带去医院。医生扫一眼我身上的黄色裸棉衣,那是村上一位退伍军人捐给我的,没有罩衣,又扫一眼我父亲蓝色中山装手肘上的那块颜色黑蓝的补丁,这才如释重负地对我们说,肺部没毛病,主要是阴虚,需要静养。在得知我在县一中读初中时,医生对父亲说,孩子学业这么繁重,又没钱补充营养,连吃有营养的菜都没条件,还是别在县城读了,毕竟活下去才有一切。
我和父亲从医院前那条窄窄的巷子出来,惧怕中,我紧紧抓住黄荆条留存在我心中的影子,我想,它可以忍受任何恶劣的条件生存,我也能。
父亲的脸愁苦得快淌下水来,我不以为然地对父亲说,我就在这儿读,像黄荆条一样,栽到哪儿都能长成一蓬。父亲听了我的话,眉头因焦虑而拧成的疙瘩才稍稍散开,他也开始说起黄荆条来。说黄荆树生命力很强,基本不挑生长的环境,而且它花开得茂盛,花期也很长。突然他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般叫出了声:“回去我养一桶蜜蜂,黄荆蜜是蜂蜜中的佳品,又有营养,一定可把你的身体调理过来!”
父亲后来在来信中不断告诉我他养蜂的进展。暑假的时候,偏屋里已聚拢一大桶蜜蜂了,父亲戴着母亲制作的防护帽,把一波波的蜜蜂转场到一个又一个堤坝沟渠上,蜜蜂“嗡嗡”的喧闹声响彻在一蓬蓬盛开着淡紫色黃荆花的树丛中,父亲瘦削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我吃着父亲从蜂巢上割下来的奶黄色蜂蜜,咳嗽声渐渐稀落,个子也噌噌上蹿。
初三那年暑假,我挑一肩公粮随父亲送往离家三里地的葛家垭粮库,我头戴一个自制的黄荆条圈,走起路来飒爽英姿,当村里人问我中考的情况时,我骄傲地对他们说,我被录取到县一中了。至此,父亲彻底放下了对我身体的担忧,他期待着我在求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今年七月,当我坐在鲁迅文学院宽敞明亮的教室,向老师和同学们介绍我自己的时候,家乡黄荆条的影子一下浮现在我眼前,我突然意识到,我就是家乡那株长不高长不大的黄荆条,是母亲给我的精神引领,是父亲给我的强身之功,将我灌溉成一个稍有点儿正型的模样。是我适逢的风调雨顺,以及太多有人文情怀的领导和老师给予我的关怀和帮助,让我一个一直奋战在高中物理教学一线的老师,在即将退休之际能重拾儿时的文学梦。每当夜阑人静的时候,我坐在书房兴味盎然地读着一篇可心的文字,一抬头,窗外清朗的月光下,黄荆棍舞动的“呼呼”声似乎从岁月深处呼啸而来。
责任编辑 高 璟
作者简介:
王丕立,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毛泽东文学院21期作家班学员,鲁迅文学院第二期湖南作家班学员。作品散见于《延河》《都市》《当代小说》《短篇小说》《雪莲》《青春》等杂志。荣获第六届“读友杯”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2023年“小百花儿童文学奖”提名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