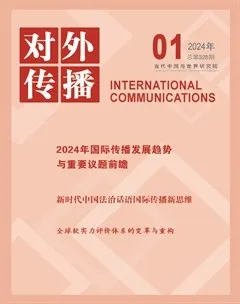提升重大国际新闻首发率的探索与思考
2024-01-31任晓东王刚禹雪
任晓东 王刚 禹雪
【内容提要】重大国际新闻首发率的提高,是我国国际传播效能全面提升的关键环节,对于打造具有强大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具有重要意义。鉴于首发新闻的首因效应增强引领力、技术加持的新闻首发赋能传播力、新闻首发的生产机制塑造影响力,本文结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大国际新闻首发的媒体实践探索,从首发范围和首发内容两个视角出发,建构了以重大国际新闻首发率为切入点的国际传播效能评价指标体系,以精准度量我国媒体在重大国际新闻首发率上的成长趋势,为找准提高重大国际新闻首发率的突破口提供了评估依据。在这一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本文围绕信源、技术、制度、管理等四个影响首发率的重要因素,进一步探讨了有效提高我国媒体重大国际新闻首发率的实践策略。
【关键词】重大国际新闻 首发率 即时性 国际传播效能
国际舆论场中,媒体抢占首发是抢夺国际话语权和重大新闻事件第一定义权的关键。实现首发,能够做到权威发声、及时回应、澄清谬误,牢牢掌握国际舆论的主导权;失去首发,则可能导致权威失语、众声喧哗、谣言四起,话语主动权也将大大削弱。以提高重大国际新闻首发率为切入点,增强我国媒体的国际舆论引领力、传播力和影响力,对于推进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我国国际传播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际传播实践中重大国际新闻首发率的重要意义
(一)首发新闻的首因效应增强引领力
首发新闻的重要作用与传播心理学中的首因效应有关。首因效应表明,信息接收者更容易接受最先传达到的信息,用其进行自我建构,并在潜意识中用其对后续信息进行解释与加工。其结果是首发信息比后续信息对受众认同产生的作用更强、持续时间更长。当首因效应作用于议程设置,其效果将最大化。研究发现,媒体议题与公众议题显著相关,媒体可以影响受众关注哪些议题以及谈论议题的先后顺序。①因此,国际传播中的率先发声者往往更容易抢占国际舆论制高点,吸引受众关注并创设第一印象,迅速形成集群效应。受沉默的螺旋机制影响,首发新闻及其潜在观念将形成强有力的扩散,使得后续报道的媒体处于被动地位,受到首发新闻观点的牵制和引导。这也意味着提高重大国际新闻首发率有利于增强我国媒体的国际舆论引领力。
(二)技术加持的新闻首发赋能传播力
李普曼认为,由于实际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人们无法对与之有关的整体外部环境保持经验性接触,所以对其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他们大多在新闻媒体建构的拟态环境中了解认知,并将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来看待和作出反应。在被建构的拟态环境中,媒体带有特定价值导向的新闻报道就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对于现实生活中某一国家或某一事件的印象与态度。②当前,随着新型融媒技术的迭代升级,媒体平台跨国、跨区域、跨语种的全球落地已经逐渐成为现实。在这种技术条件下提高重大国际新闻首发率,有助于在国际舆论场中率先构建起符合我国主流价值观的拟态环境,从而广泛影响全球受众的认知、观念和行为。
(三)新闻首发的生产机制塑造影响力
长期以来,欧美媒体通过掌握意识形态的文化领导权、媒介资源的集中垄断权和传播网络的纵向控制权,主导着国际传播的霸权秩序,③新闻首发所代表的即时性(immediacy)正是其构建记者专业身份、建立与受众信任关系、将自身权威角色合法化的重要因素。④然而,其充满偏见的媒体框架严重影响甚至误导了国际受众对于诸多新闻事件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需要我国媒体在国际传播实践中高度重视新闻首发,逐步建立起提升重大国际新闻首发率的生产机制。这不仅有益于在激烈博弈的国际媒体竞争中塑造我国媒体的专业性和影响力,也是在碎片化、流量化和算法化的信息社会趋势下重构世界主流话语体系的必要举措。

二、以重大国际新闻首发助力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的指标体系建构
为了精准度量我国媒体在重大国际新闻首发率上的成长趋势,找准提高重大国际新闻首发率的突破口,本文结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大国际新闻首发的媒体实践探索,建构了以重大国际新闻首发率为切入点的国际传播效能指标评价体系。这一评价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从首发范围和首发内容两个具体视角出发,综合国际舆论引领力、传播力和影响力在国际传播效能评估中的映射维度,进行了各项指标的权重赋值。
着眼于首发范围和首发内容,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重大国际新闻首发实践中提炼出的宝贵经验。具体来看,首发范围包括全球首发和国内首发:全球首发指重大国际新闻在全球范围内的首次发布,考验媒体是否具有对全球新闻事件的敏锐嗅觉和高效优质的采集处理能力;国内首发指重大国际新闻在国内范围内的首次发布,与全球首发相比,其更加关注国际新闻的本土化解读。首发内容包括消息首发和观点首发:消息首发指媒体首次发布一个重大国际新事件的消息,对于引起其他媒体的跟进报道和公众舆论的反应发酵具有促进作用;观点首发指媒体对重大国际新闻事件首次公开表达特定态度或观点,侧重以站位的高度和解读的深度来影响国际社会的舆论风向。
具体而言,首发范围视角下的原创首发引领力由全球/国内首发率来评估,首发内容视角下的原创首发引领力由消息首发率/观点首发率来评估;覆盖、技术传播力由跨国覆盖率、跨区域覆盖率、跨语种覆盖率、传媒技术迭代升级来评估;用户反馈影响力由用户互动总量、用户好感评价来评估。评价体系中的各个权重代表了不同指標对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贡献程度。例如,原创首发引领力、覆盖与技术传播力、用户反馈影响力的贡献程度依次递减;原创首发引领力中,全球首发率、消息首发率、观点首发率、国内首发率的贡献程度依次递减;覆盖、技术传播力中,跨国覆盖率和跨区域覆盖率、跨语种覆盖率和传媒技术迭代升级的贡献程度依次递减;用户反馈影响力中,用户互动总量、用户好感评价的贡献程度依次递减。
三、提升重大国际新闻首发率的有效途径
在上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本文围绕信源、技术、制度、管理等四个影响首发率的重要因素,进一步探讨有效提高我国媒体重大国际新闻首发率的途径。
(一)扩充信源渠道
霍夫兰等提出,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信源的可信度会成为影响个人态度转变的重要诱因。信源的可信性和专业性越高,接受者的态度越有可能转变。⑤广泛的信源依赖于遍布全球的立体化全方位傳播网络,包括四通八达的新闻信息采集和销售网络、形式多样的媒体终端和业务产品、数量众多的受众群体等。我国媒体平台需继续努力扩大全球采集网络的覆盖面,主要包括增加新闻站点、促进与当地新闻媒体的合作、扩大国际新闻人才储备和外派力量、强化新闻节目落地等,推动新闻信源的逐步扩大。在具体业务层面,媒体平台工作者应加强并拓展新闻信源采集的渠道,包括新闻采访、专家采访、新闻发布会、政府官方公告通知、政府会议、领导人行程计划安排等。记者应勤于到采访对象处采集观点,在会场、政府机构、企业团体和社会组织采集新闻,在突发事件现场或热点地区现场目击记录、亲身体验,在事件发生一线调查研究,提高新闻采集的专业能力和原创能力。
(二)注重技术赋能
国际新闻的首发报道获得传播效果的手段不仅在于及时生产和采集全球新闻信息,还在于媒体的信息聚合、加工和分发能力。通过算法提升精准推送能力以及平台渠道占有能力与拓展能力,有助于媒体提升舆论引领力。因此,提高重大国际新闻首发率的技术手段,应重视强化应用新型融媒体的传播技术,加快运用信息科技革命成果,如5G、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和增强现实技术等,破除传统体制,实现媒体深度融合,促使新闻首发报道快速获得传播效果,推动对外传播事业高质量发展。媒体平台可以利用新兴技术实现智能推荐,满足用户个性化、多样化和沉浸化需求。同时,媒体平台可以利用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掌握用户个性特征和心理期望,了解受众需求,不断改进和完善用户体验,进而运用大数据和智能推荐技术,深化对不同产品的专业化和垂直化推荐路径。
(三)深化融合发展
我国媒体在提高重大国际新闻首发率的同时,还应当在首发新闻中进一步提高新闻原创率,即在国际新闻生产中有机融入独家报道的特质,注重以带有中国视角和中国价值的原创内容触达国际受众,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工作实践中取得先发优势。影响原创率提升的因素不仅在于采编人员业务素质的不断提高,还在于科学合理国际新闻融合生产与分发机制的构建完善。具体而言,我国媒体需要建立一体协同联动的国际新闻融合生产机制,再造新闻采编流程,推动跨媒介、跨语种、跨类别的“三跨”资源整合、信息聚合和媒体融合,达到重大国际新闻首发的效率化、覆盖化、精准化、原创化。同时,构建“新闻+政务+服务”的内容与产品服务体系,以便捷、友好、交互、智能的移动媒体终端吸引更多国际受众成为我国媒体的订阅用户,使得我国媒体的重大国际新闻首发能够得到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接受和高度认可。
(四)创新运营方式
媒体组织要提高重大国际新闻首发率,还需建立创新的运营管理体系。媒体平台要加强对国际新闻报道的规划、统筹和监控,建立高效的国际新闻采编、制作、推广、营销等工作流程,以提高工作效率和报道质量,进一步提高国际新闻首发率。此外,媒体平台还应充分发挥媒体联合的优势,加强与相关机构和企业合作,充分利用合作伙伴的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提高国际新闻采集、加工、分发的整体效率和水平,从而为新闻首发提供更多有力的保障和支持。
综上,鉴于国际传播实践中重大国际新闻首发率的重要意义,依托以重大国际新闻首发率为切入点的国际传播效能评价指标体系,我国媒体需要从信源、技术、制度、管理等四个方面展开国际传播效能的提升工作:第一,积极拓展信源网络,加强国际新闻采集的能力和水平;第二,创新应用新型融媒体技术,提升新闻传播的效率和质量;第三,优化制度环境,建立有利于国际新闻首发的机制;第四,创新构建运营管理体系,提高工作效率和报道质量。这将提高重大国际新闻首发率,将有助于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切实提升我国媒体的国际舆论引领力、传播力和影响力。
任晓东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编室评估考核部副主任;王刚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禹雪系中视前卫媒体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释」
①郭镇之:《关于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3期,第19-20页。
②[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23-24页。
③虞鑫、王刚:《多种声音,共同世界:“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传播秩序重构》,《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第71-78页。
④Usher, Nikki. Breaking news production processes in US metropolitan newspapers: Immediacy and journalistic authority. Journalism, vol. 19, no.1, 2018, pp. 21-36.
⑤[美]霍夫兰、贾尼斯、凯利:《传播与劝服:关于态度转变的心理学研究》(张建中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2页。
责编:霍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