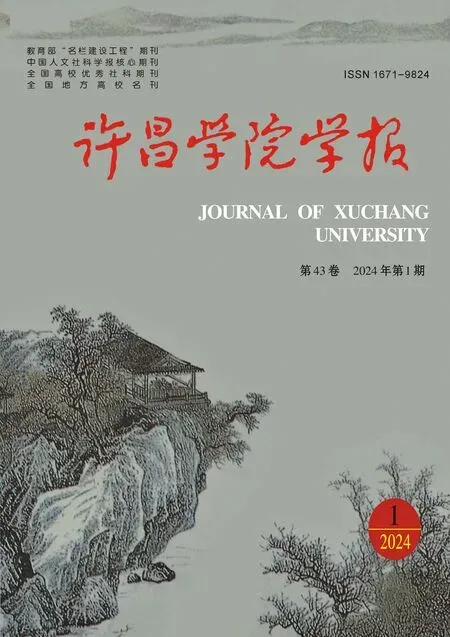秦汉初“县内尉”考述
2024-01-29姚立伟
姚 立 伟
(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秦代是否设有县尉,因文献缺乏而存在争议。安作璋、熊铁基依据传世文献没有县设置尉的明确记载,认为“秦本无县尉,只有郡尉”[1]655-656。睡虎地秦简、秦代玺印封泥等出土资料,似乎也不支持秦代县内设有县尉的观点(64)邹水杰指出,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很多处提到长吏对县中事务负责时,都提令、丞,而不及尉。特别是《语书》这样重要的文书,其中都没有言及尉之事,所以甚至有人怀疑秦不设县尉。只有在与军队、屯戍有关的情况下,才是尉与县令负责”。王伟指出,“秦玺印封泥中未见县‘尉府’类资料”。分别见邹水杰:《两汉县行政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0页;王伟:《秦玺印封泥职官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0页。。里耶秦简刊布后,根据其中“尉”的记录,多数学者认为秦代存在县尉(65)杨振红:《秦汉时期的“尉”、“尉律”与“置吏”、“除吏”——兼论“吏”的属性》,《简帛》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33-342页;吴方基:《简牍所见秦代县尉及与令、丞关系新探》,《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2期。。此类研究多认为里耶简8-157和丞某敢告尉类文书中的尉为县尉。实际上,里耶简8-157和丞某敢告尉类文书中的尉可能皆非县尉。里耶简8-157中的尉是指县内诸官的尉官,丞某敢告尉类文书中尉可能是洞庭郡尉派驻迁陵县中的尉,主要负责戍卒管理。我们将这一时期郡派驻县的尉称为县内尉,以与汉代县尉相区别。县内尉地位较高,与县令同为县内长官。秦洞庭郡迁陵县内尉有一套相对独立的属吏系统,直属吏员有尉官、发弩、尉史、士吏等。迁陵县内尉带有从军事系统向行政系统过渡的色彩,职责上开始涉及群盗的追捕。张家山汉简显示,汉初县尉已为县令长佐官,并担负起逐捕盗贼的职责。汉初县尉可能由尉官转化而来,拥有与之联系紧密的尉史。西汉中后期,尉史进一步属县化为县廷吏员。根据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等相关记录,我们大体可以梳理出汉代县尉典型形象形成的历史过程。
一、文书用语差异所见秦县内尉、汉县尉地位变迁
在里耶秦简与西北汉简的县级政务文书中,县丞对县内尉、县尉文书用语存在差异,即在里耶秦简中为丞某敢告尉,在西北汉简中为丞某告尉。对此,苏卫国已有注意,他指出秦代县丞对尉用“敢告”,与汉代用“告”不同[2]232,但对差异背后原因未予深究。
里耶简中丞(守丞)某敢告尉类文书有数件[3],仅举一例如下:
(廿七年)(前220)三月庚戌,迁陵守丞敦狐敢告尉、告乡、司空、仓主听书从事。尉别书都乡、司空,司空传仓;都乡别启陵、贰春,皆勿留脱,它如律令。扣手。庚戌水下六刻,走袑行尉。
三月戊午,迁陵丞欧敢言之:写上。敢言之。扣手。己未旦,令史犯行。
【三】月戊申夕,士五(伍)巫下里闻令以来。庆半。如手。(16-6)[4]208
从中可见,此类文书的行文格式为迁陵丞(守丞)某敢告尉、告某官。
西北汉简中类似文书则呈现出另外一种格式,为县令(守长)某、丞(守丞)某告尉、谓乡,如悬泉汉简中有:
(永光五年)(前39)七月庚申,敦煌大守弘、长史章、守部候修仁行丞事,敢告部都尉卒人,谓县官,官写移书到,如律令。掾登、属建、佐政、光。
七月辛酉,效谷守长合宗、守丞敦煌左尉忠,告尉谓乡置,写移书到,如律令。掾禹、佐尊。(Ⅱ90DXT0216②:869-870)[5]78
居延新简中有:
建武五年(29)八月甲辰朔丙午居延 令 丞审告尉谓乡移甲渠候官听书从事如律令(EPF22:56A)[6]443
从中可见,在西汉元帝、东汉初年的西北边县行政文书中为丞(守丞)某告尉、谓乡的行文格式。
在里耶秦简文书中也有告的用法,但丞某告的对象往往为县内诸官。吴方基认为县丞(守丞)在文书中用“敢告”和“告”来区分其行文对象,“县丞行书县尉是平行,行书尉官是下行,行书用语不同,为‘敢告’者是行书县尉,是‘告’者为行书尉官”[3]。邹水杰也将“丞告(谓)某”形式作为判断县内诸官的重要依据[7]。因此,我们认为里耶秦简中丞(守丞)敢告尉类文书的对象为县内尉,而告尉类文书的对象为县尉官。
在汉代并未弃用敢告类行文格式。前举悬泉汉简中有“敦煌大守弘、长史章、守部候修仁行丞事”给部都尉的文书仍然用“敢告”部都尉卒人(66)对于汉简中的卒人,多代指其前的郡太守或部都尉等官。王充在《论衡·谢短》中已指出:“两郡移书,曰‘敢告卒人’,两县不言,何解?”陈直认为:“卒人指府门卒而言,内官公卿、外官太守及都尉府皆有之。县令长无府门卒之制度,故王充设作疑问,称为两县不言何解也。但卒人虽系指府门卒,实指太守或都尉而言,等于后代人之称阁下也。”汪桂海指出汉代“敢告卒人”一语主要出现在三类文书:一为甲郡太守移乙郡太守的文书;二为郡太守移本郡诸都尉、校尉的文书;三为郡级官府移所属县级官府的文书。秦代官府文书中也有卒人称谓,如下文所引里耶秦简8-61+8-293+8-2012,陈伟通过对比《秦律十八种·传食律》简179-180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传食律》的内容,认为“秦简的‘卒人’相当于汉简的‘诸二千石官’。睡虎地秦律大致抄写于秦统一之前。‘卒人’或许是秦郡长官在称‘守’‘泰(太)守’之前的称述。在‘守’‘泰(太)守’流行之后,‘卒人’作为文书用语保留下来,继续指称郡级长官,并流传到汉代”。分别见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72页;陈直:《居延汉简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36页;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102页;陈伟:《秦简牍校读及所见制度考察》,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5页。格式。在居延汉简中,不仅有丞某敢告部都尉的情况,还有丞某敢告农都尉、护田校尉等的情况,如下:
得仓丞吉兼行丞事敢告部都尉卒人诏书清塞下谨候望督蓬火虏即入料度可备中毋远追为虏所诈书已前下檄到卒人遣尉丞司马数循行严兵(12.1A)[8]42
二月戊寅张掖大守福库丞承熹兼行丞事敢告张掖农都尉护田校尉府卒人谓县律曰臧它物非钱者以十月平贾计案戍田卒受官袍衣物贪利贵贾贳予贫困民吏不禁止浸益多又不以时验问(4.1)[8]8
丞、长史、部都尉、农都尉等地位大致相当[9]343。汉简中郡太守、丞对部都尉、农都尉用敢告,县令、丞对县尉则用告。平级的逻辑,显然较难解释这一行文格式差异。那么,不妨从统辖系统的角度考虑,在边境地区,部都尉、农都尉等具有独立治所并配有相应管理机构,他们的权力更大、独立性更强。因此,“敢告”类文书应该多适用于独立性相对较强的机构之间,例如里耶秦简中的两郡之间、两县之间。邹水杰在《里耶秦简“敢告某主”文书格式再考》[10]中对此已有详尽考察,仅列两例以作说明。两郡之间往来文书:
□/未朔己未,巴叚(假)守丞敢告洞庭守主:卒人可令县论
□/
卒人,卒人已论,它如令。敢告主。不疑手。·以江州印行事。(8-61+8-293+8-2012)[11]46
两县之间往来文书:
八月乙巳朔己未,门浅□丞敢告临沅丞主:腾真书,当腾腾,敢告主。定手。(8-66+8-208)[11]52
我们推测,秦县内尉、汉县尉与丞的关系有两种变化:所属系统方面,从两分到合一,秦县内尉与县丞分属军事、民政不同系统,汉县尉与县丞同属民政系统;地位差异方面,秦县内尉地位高于县丞,汉县尉地位与县丞相当。从属系统有别和地位不同,是县丞对秦县内尉、汉县尉文书用语差异的原因。
二、秦迁陵县内尉及其职能系统
秦县内尉主要管理军务及发动和安排徭戍、屯戍、屯卒和追捕盗贼等事务,与此相关的人事任免、户籍管理、上计等亦有涉及[12]78、81。秦迁陵县内尉可能是迁陵三主官之一,军事色彩浓厚。在迁陵置县前,县内尉身份可能为属邦候。县内尉由洞庭郡尉派出,为大啬夫。迁陵县内尉所辖属吏有尉官、尉史、士吏、发弩以及与其事务往来较多的司空、髳长、校长等。
(一)由属邦候转化而来的迁陵县内尉
秦洞庭郡迁陵县中存在高于尉官的尉,如简8-67+8-652载:
廿六年(前221)十二月癸丑朔辛巳,尉守蜀敢告之,大(太)守令曰:秦人□□□
侯中秦吏自捕取,岁上物数会九月朢(望)大(太)守府,毋有亦言。问之尉,毋当令者。敢告之。(8-67+8-652)[11]52
文书中既有尉守,又有“问之尉”,校释者认为尉守是尉的属吏[11]52。尉守当为尉官守,是迁陵县内尉的属官。与上一文书可作对比的是简8-62载:
丗二年(前215)三月丁丑朔朔日,迁陵丞昌敢言之:令曰上葆缮牛车薄(簿),恒会四月朔日泰(太)守府。·问之迁陵毋当令者,敢言之。(8-62)[11]47-48
同为答复太守令的两件文书,展现了尉—尉守与迁陵—迁陵丞两套机构的并存。李斯在考察里耶简中县主官称谓时已尝试提出,秦边县中存在分管军事与治民的“守”和县令长[13]。秦边县中军、民分治的观点可从,但我们认为迁陵县内主管军事的长官为县内尉。
迁陵县中的尉可能由属邦候转化而来。秦国在灭亡楚国后,为了稳定新征服地区的统治,实行军事统治向行政统治过渡的模式。孙闻博认为,秦通过兼并战争扩张领土的过程中,在关中内史区域之外逐步设郡,郡与封国相当,因而早期的郡也称为邦[14]60(67)杨振红则认为,秦代邦指王畿,“邦尉军是秦王畿(京师)的军队”。杨振红:《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续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页。。里耶简8-649载:“邦尉、都官军在县界中者各□/ 皆以门亭行,新武陵言书到署□/。”整理者注曰:“邦尉,似即郡尉。8-461有云:‘郡邦尉为郡尉。’”[11]190在简8-657中也有与内史、郡守地位相当的属邦的记载[11]193。简9-2287中文书记录显示迁陵县界内有“属邦候”[15]453。因避讳,汉代改“属邦候”为“属国候”。在汉代边防系统中,属国候归属国都尉管辖,属国候与县令相当,属国都尉与郡守相当[16]。在秦统一前,里耶秦简中的洞庭邦—属邦候系统,与汉代边防系统的属国都尉—属国候系统类似。随着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迁陵置县[11]217和改“郡邦尉为郡尉”法令[11]157的颁布,洞庭邦—属邦候军事体制转化为郡县管理体制。迁陵置县后,应另设有一套由朝廷派出的县令、丞系统负责日常政务文书事务的管理。简8-67+8-652显示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十二月迁陵县内尉管理涉及“侯中秦吏”[11]52。那么,迁陵县内尉可能即由迁陵属邦候转化而来,依然负责军事管理。联系8-657简文中之“军吏在县界中者”[11]193,表明郡尉在县域内设有派驻机构和军队,主要管理者即丞某“敢告”之尉。
《迁陵吏志》中记载有“长吏三人,其二人缺,今见一人”[15]168,水间大辅用汉制倒推,认为长吏三人为县令、丞、尉[17]183。迁陵三长吏中无疑包含县令,但另外两人可能分别为郡太守、郡尉所派出吏员。睡虎地秦简律文中显示有县令、县啬夫、大啬夫共存的情况,早期研究一般将三者等同看待[18]。苏卫国根据里耶简16-5中“洞庭守礼谓县啬夫卒史嘉叚(假)卒史谷属尉”的记录,并与秦律中相关记载对照考察,认为县啬夫是“郡长官为办理军政要务而派遣至所属县的吏员”[18]。李斯在汉制县令与佐官县尉的框架下推测秦律中的大啬夫为主官的助手,行使的是县尉的职权[13]。我们认为大啬夫可能即秦县内尉,但其地位非县令佐官而为主官、长吏。秦代洞庭郡中有郡守、郡尉、郡监三长官,分别主行政、军事、监察,郡守所辖丞、卒史等,属文吏系统,负责文书签转与政务运作,郡尉所辖的司马、发弩、司空、候、武库、卒长、轻车等属军事系统[19]76-102。迁陵县中三长官、行政与军事系统并立的格局与洞庭郡有相似之处。
(二)过往研究中误尉官为县尉情况的厘清
学界先行研究中长期存在误认尉官为县尉的情况。这涉及确认尉与县丞地位高下和迁陵县内尉的属吏系统,因此,对此需予以详细考辨。
里耶秦简8-157载:
丗二年(前215)正月戊寅朔甲午,启陵乡夫敢言之:成里典、启陵邮人缺。除士五(伍)成里匄、成,成为典,匄为邮人,谒令尉以从事。敢言之。
正月戊寅朔丁酉,迁陵丞昌却之启陵:廿七户已有一典,今有(又)除成为典,何律令(应)?尉已除成、匄为启陵邮人,其以律令。气手。正月戊戌日中,守府快行。正月丁酉旦食时,隶妾冉以来。欣发。(8-157)[11]94
该文书内容较为完整,字迹清晰易辨,已经胡平生、邢义田、杨振红等多位学者解读。胡平生认为其中的尉为迁陵县尉,在基层官吏任免中,县尉的权力大于丞[20]123。邢义田[21]325-326、杨振红[22]335也认为简文中的尉为县尉。上述三位学者对该文书的解读,均认为其中的“尉”是县尉。问题的关键是对“谒令尉以从事”一句的句读与理解。张春龙、龙京沙初次披露简文时将此句句读为“谒令、尉以从事”[23]。胡平生[20]122、邢义田[21]325的研究中均作此句读。该句读容易给研究者造成令指县令、尉指县尉的错觉与误读,其中“令”非县令,已为日本里耶秦简读书会所纠正,认为令指命令(68)陈剑指出:“‘谒令尉以从事’句现所见论著多于‘令尉’两字间加顿号,解释为县令与县尉两人,说为‘向迁陵令、尉请示’、‘报请县令和县尉批准’之类,甚至进而被作为秦制称县主官为‘令’的确证,一些讨论秦代官制的论著又有进一步的发挥引申,这是完全错误的。日本学者早已对此有正确解释,见里耶秦简讲读会所撰《里耶秦简译注》(《中国出土资料研究》第8号,2004年)。”陈剑:《读秦汉简札记三篇》,《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73页。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5页)中采信了《里耶秦简译注》的说法。,在杨振红的解读中,已将该句解释为“请求让尉批准”。但简文中的“尉”是否为县尉,尤可考辨。简文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诸官向县廷的上书,其格式为年月日,某官负责人敢言之:具体事项,谒令某官做某事。敢言之。第二部分为县丞的批复,其格式为月日,迁陵丞某却之/告某官:批复内容,其以律令/以律令从事。残缺不全但与8-157类似者有简8-69:
□/【里】士五(伍)辟缮治,谒令尉定□/
□/□丞绎告尉主,听书从事,它
□/□日入,隶妾规行。(8-69)[11]53
简文中残存“谒令尉”部分和丞某告尉主部分,按吴方基、邹水杰的判断,丞某所告之尉为尉官。此类行文格式的文书在里耶秦简中并非个例,还有另外四份文书,分列如下:

三月辛亥,迁陵守丞敦狐告司空主,以律令从事……昭行(8-1510)[11]341
廿八年(前219)七月戊戌朔癸卯,尉守窃敢之:洞庭尉遣巫居贷公卒安成徐署迁陵。今徐以壬寅事,谒令仓貣食,移尉以展约日。敢言之。
七月癸卯,迁陵守丞膻之告仓主,以律令从事。逐手。即徐□入□。
癸卯,朐忍宜利锜以来。敞半。 齮手。(8-1563)[11]361
城旦琐以三月乙酉有遝。今隶妾益行书守府,因之令益治邸[代]处。谒令仓司空薄(簿)琐以三月乙酉不治邸。敢言之。(卅二年)(69)简文载“五月丙子朔”,据李忠林《秦至汉初历法研究》(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08页)可知该年为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五月丙子朔甲午,迁陵守丞色告仓司空主,以律令从事,传书。圂手。(8-904+8-1343)[11]246
丗四年(前213)七月甲子朔癸酉,启陵乡守意敢言之:廷下仓守庆书言令佐赣载粟启陵乡。今已载粟六十二石,为付券一上。谒令仓守。敢言之。·七月甲子朔乙亥,迁陵守丞巸告仓主:下券,以律令从事。壬手。七月乙亥旦,守府卬行。(8-1525)[11]349
四份文书中,“谒令”后所加为司空、仓等县内诸官(70)邹水杰指出,“迁陵县设官啬夫的十官为:司空、少内、仓、田、尉、畜官、船官、都乡、启陵乡和贰春乡。”邹水杰:《秦简“有秩”新证》,《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3期。,上书者也为启陵乡、库、尉等诸官。那么,简8-157中“谒令尉”中的尉是指县内诸官中的尉官而非所谓“县尉”。
在先行研究中,误认尉官为县尉的情况并非仅有上例。在岳麓书院藏秦简中《尉卒律》《戍律》等律文涉及违令的处罚标准时,尉、尉史、士吏与丞、令、令史相对出现,相关简文如下:
为它里典、老,毋以公士及毋敢以丁者,丁者为典、老,赀尉、尉史、士吏主者各一甲,丞、令、令史各一盾。(1291正+1293正)[24]115-116
尉令不谨,黔首失令,尉、尉史、士吏主者赀各一甲,丞、令、令史各一盾。(1292正)[24]112
尉、尉史、士吏、丞、令、令史见及或告而弗劾,与同辠。弗见莫告,赀各一甲。(1257正)[24]117
疾病有瘳、已葬、劾已而敢弗遣拾日,赀尉、尉史、士吏主者各二甲,丞、令、令史各一甲。(J46正)[24]130
岁上舂城旦、居赀续〈赎〉、隶臣妾缮治城塞数、用徒数与黔首所缮用徒数于属所尉,与计偕,其力足以为而弗为及力不足而弗言者,赀县丞、令、令史、尉、尉史、士吏各二甲。(1248正+1249正)[24]131
朱红林[25]、沈刚[26]均注意到简文中尉、尉史、士吏和丞、令、令史的组合,且认为其中的尉当为县尉。岳麓简中有其他吏员和丞、令、令史同时受罚的处罚标准,如下:
●田律曰:毋令租者自收入租,入租貣者不给,令它官吏助之。不如令,官啬夫、吏赀各二甲,丞、令、令史弗得及入租貣不给,不令它官吏助之,赀各一甲。(1224正+J45正)[24]125
为(?)取传书及致以归及(?)免(?),弗为书,官啬夫吏主者,赀各二甲,丞、令、令史弗得,赀各一甲。(1428正)[24]134
从中不难看出,其中是将官啬夫、吏与丞、令、令史并举。因此,我们认为《尉卒律》《戍律》等律文中的尉当为尉官。另外,在岳麓书院藏秦简《尉卒律》中有“县尉治事,毋敢令史独治,必尉及士吏与,身临之,不从令者,赀一甲”[24]114,其中的尉也应是尉官。在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中有县尉及县司空的记载,如下:
戍者城及补城,令姑(嫴)堵一岁,所城有坏者,县司空署君子将者,赀各一甲;县司空佐主将者,赀一盾。令戍者勉补缮城,署勿令为它事;已补,乃令增塞埤塞。县尉时循视其攻(功)及所为,敢令为它事,使者赀二甲。(40-42)[27]177
睡虎地秦简还有县少内的记载,《法律答问》云:“‘府中公金钱私貣用之,与盗同灋(法)。’·可(何)谓‘府中’?·唯县少内为‘府中’,其它不为。”[27]195由上可知,秦代县内诸官如司空、少内之前也可冠以县字,简文中的尉当为尉官。岳麓书院藏秦简《尉卒律》《戍律》等相关简文中呈现出尉与县各自具有相对独立的属吏系统。从尉官与丞并举来看,其时尉官较之其他县内诸官可能地位更高(71)孙闻博认为尉官属于秦县内诸官。邹水杰所列迁陵县中设官啬夫的十官也包含有尉官。郭洪伯认为《洪范五行传》中的尉官为县尉,不属诸官,并认为尉官为统称,早期包含校长、髳长、发弩,后来为游徼和亭长。其西汉时县尉官为县尉的观点可从。在尉官即县尉的基本判断前提下,沈刚指出里耶简中县尉地位比较特殊,与诸官类似但稍高,介于令、丞与诸官之间。分别见孙闻博:《秦县的列曹与诸官——从〈洪范五行传〉一则佚文说起》,《简帛》第1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82页;邹水杰:《秦简“有秩”新证》,《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3期;郭洪伯:《稗官与诸曹——秦汉基层机构的部门设置》,《简帛研究》二〇一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116页;沈刚:《秦代县级行政组织中的武职系统——以秦简为中心的考察》,《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秦时县内存在两套相对独立的职能系统,即尉—尉官—尉史—士吏与县长官—丞—令—令史系统。于中可见,尉与县长官地位相当而高于县丞。
(三)迁陵县内尉的职能系统
县内尉的职能系统范围较广,既包括属吏尉官、尉史、士吏、发弩,也包括司空啬夫、髳长等。换言之,秦代县内尉职能系统包括诸官中的尉官、发弩、司空等,佐吏有尉史、士吏等。

综上,迁陵县内存在与迁陵县令地位相当的尉。在迁陵设县前,可能由军事色彩浓厚的邦尉派出的属邦候负责迁陵县内事务管理。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迁陵置县后,由朝廷派出的县令、丞为首的政务管理系统随之设立,属邦候转化为尉,专司军事。由此,迁陵县内存在军事与行政职能相对独立的两套系统。洞庭郡派出郡卒史为县啬夫,负责对相关事务予以指导与监察。迁陵县内的主官应有三位:一为县令;一为郡府派出卒史,称县啬夫;一为郡尉府派出尉,称大啬夫。县丞负责文书签转,应与三位长官均有业务联系,而与县令的关系更为紧密。秦及汉初县诸官啬夫负责具体部门、有印、拥有较大独立性[29]34-35,诸官因政务关系与县内主官产生业务往来。秦代迁陵县诸官中的尉官、司空可归入县内尉的职能系统。尉官与县内尉关系更为紧密。
游逸飞指出,秦代至汉初郡制的发展大体经历了秦代郡守、郡尉、郡监三府分立至汉初守、尉并行的阶段,郡尉之权较大,具体到里耶秦简所反映的秦代洞庭郡尉,其所处理之事务以军事为主兼及财政、司法、人事、监察等,戍卒事务在郡尉的管辖之下[19]94、299-305。秦代洞庭郡尉的权力之大、地位之高若此,那么,由其派驻迁陵的县内尉之权力、地位也不会很低,应与县令守平起平坐,可能具有独立治所。里耶秦简中迁陵县丞对尉用“敢告”之原由也可明了,尉为长官、丞为佐官之地位使然。县内尉与县丞分属于军事、民政系统,也为迁陵丞对县内尉用“敢告”的原因之一。从秦代的县丞对县内尉用敢告到汉代的县丞对尉用告的文书用语差异,显示的是县内尉到县尉的地位变化,即独立性逐渐丧失。
三、秦迁陵县的边防地位与县内尉的主要权责
秦代迁陵县地处帝国边防线,县界中有来自内地的戍卒。宋艳萍、邢学敏和王焕林均注意到《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中披露出的J1(9)1-J1(9)12等12枚[30]有关秦内史或颍川郡管辖下阳陵县(72)后晓荣、王伟等认为阳陵县属内史管辖;晏昌贵、钟炜认为里耶秦简中的阳陵前身为包山楚简中的阳陵,在今河南许昌西北;游逸飞进一步认为阳陵县属于秦颍川郡。分别见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页;王伟:《秦玺印封泥职官地理研究》,第361页;晏昌贵、钟炜:《里耶秦简所见的阳陵与迁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4期;游逸飞:《战国至汉初的郡制变革》,台湾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44页。戍卒的简牍。宋艳萍、邢学敏认为,“迁陵是秦朝中西部一军事重镇,与越人居住区杂处或临近,承担着防范越人反抗及向周边各郡输送甲兵的军事任务,阳陵卒可能是政府出于军事目的而被遣戍到迁陵的”[31]121。王焕林认为,“晚至西汉,濒临酉水的里耶古城,才彻底完成了其边防重镇的历史使命而成为内郡县邑”[32]75。公宅潔亦指出:“秦的迁陵县是边境之县,甚至是进军路上之县,为一军事据点。”[33]37
高恒根据睡虎地秦简相关律文指出,“秦县尉的职责,远非‘主盗贼’一事,而是掌管一县军务”,具体表现为对“征发戍卒、培训军官和地方防务”负责[34]15-16。秦县内尉主管军事的特点,在迁陵县中有较为充分的展现,其职责除涉及地方防务外,还对县内戍卒进行管理。
秦代迁陵县中有来自帝国各地的、数目可观的戍卒,其主要管理者为县内尉及其属吏尉官、尉史等。池田雄一认为秦朝迁陵县中的居民有六成为戍卒[35]52,可见迁陵县中的戍卒数量较大。里耶秦简8-132+8-334载:
□/冗募群戍卒百卌三人。
□/廿六人。·死一人。
□/六百廿六人而死者一人。
尉守狐课。
十一月己酉视事,尽十二月辛未。(8-132+8-334)[11]70
该文书为尉守狐任尉官守时的“冗募群戍卒”的登记情况,从中可看出尉所掌握的戍卒数量至少有626人之多。据游逸飞统计,迁陵县中戍卒的来源地除颍川郡阳陵县外,还有内史坏(褱)德县、临淄郡益县、颍川郡襄城县、汉中郡长利县、济北郡高成县、衡山郡襄县、淮阳郡城父县、上郡宜都县和南郡之醴阳、孱陵、巫、夷陵、竟陵五县以及巴郡之涪陵、朐忍、资中三县等[19]144-147。尚可补充者,有临沮、阆中二县。里耶简8-140载有“屯戍士五(伍)桑唐赵归”,校释认为桑唐为里名,可能属于临沮县,临沮县属南郡(73)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66页;陈伟:《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0页。。简9-552载有“屯戍阆中下里孔”[15]154,阆中县属巴郡[36]1603。另外,还有来自琅邪郡的戍卒,见简8-657[11]193。那么,迁陵县中的戍卒来源地区辐射帝国的西北、东南、西南等地,戍卒从全国各地汇聚到迁陵县进行更戍与屯戍。迁陵县内尉为戍卒事务的主要管理者,如简9-757载:
更戍卒士五(伍)城父成里产,长七尺四寸,黑色,年卅一岁,族□/
卅四年(前213)六月甲午朔甲辰,尉探迁陵守丞衔前,令□/(9-757)[15]199
文书中尉的排位在迁陵守丞之前,这给我们提供了三方面的信息:其一,尉对戍卒管理负有总责;其二,尉的地位要高于迁陵守丞;其三,在守丞前特意嵌入“迁陵”二字以与尉相区分。简9-1861载:
【廿】六年(前221)二月癸丑朔庚申,洞庭叚(假)守高谓县丞:干雚及菅茅善用殹(也)。且烧草矣,以书到时,令乘城卒及徒隶、居赀赎责(债)勉多取、积之,必各足给县用复到干草。唯毋乏。它如律令。新武陵布四道,以次传,别书。书到相报,不报者追之。新武陵□书到,署厩曹。以洞庭发弩印行事。(正)
五月乙酉,迁陵守丞敦狐敢告尉、告乡官主:以律令从事。以次传书,勿留。夫手。即走辰行……(反)(9-1861)[15]374
简文内容为洞庭郡代理郡守高要求各县丞注意收集雚、菅、茅等干草以“足给县用”,收集工作的主要实施者是乘城卒、徒隶、居赀、赎责,其中涉及尉所管辖的乘城卒,于是迁陵守丞敦狐在继续传达这项命令时,会分别“敢告尉”“告乡宫(官)主”。
迁陵县内尉的职责还涉及求盗的管理,如简8-1552载:“敢告尉:以书到时,尽将求盗、戍卒喿(操)衣、器诣廷,唯毋遗。”在该文书中除用“敢告”外,另有“唯”字,《里耶秦简牍校释》中释为“祈请”,并引“《韩非子·初见秦》:‘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虽然,臣愿悉言所闻,唯大王裁其罪。’《史记·乐毅列传》:‘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不察疏远之行,故敢献书以闻,唯君王之留意焉。’”[11]356该两处“唯”字,皆为下对上。因该文书发出者身份不明,我们推测该文书当为县廷的上行或平行文书,显示出县内尉的地位较高。该文书还表明迁陵县廷不握有对求盗、戍卒的实际管辖权。对于30人的大群盗贼的警戒乃至逐捕,需由尉处理,如简9-1112载:

二月辛巳,不更舆里戌以来。丞半。壮手。(9-1112)[28]198
由文书中的“尉下亭鄣”,也可看出迁陵县的边防性(74)《史记·张仪列传》载张仪说魏王言语为:“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地四平,诸侯四通辐凑,无名山大川之限。从郑至梁二百余里,车驰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万。”《史记·黥布列传》中《索隐》注“分卒守徼乘塞”曰:“徼谓边境亭鄣。以徼绕边陲,常守之也。乘者,登也,登塞垣而守之。”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778、3155-3156页。。

秦代县内尉还拥有人事任命权,即负责除吏[40]78-79。《秦律十八种·置吏律》载:
除吏,尉已除之,乃令视事,及遣之;所不当除而敢先见事,及相听以遗之,以律论之。啬夫之送见它官者,不得除其故官佐、吏以之新官。 置吏律(159-160)[27]126
尉的除吏权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其属吏士吏、发弩啬夫拥有任命权,《秦律杂抄·除吏律》载:“除士吏、发弩啬夫不如律,及发弩射不中,尉赀二甲。”[27]155二是尉的属官尉官还对乡里之邮人、里典具有任命权,里耶秦简8-157所载迁陵县启陵乡成里典、乡邮人出缺,要通过尉官予以任命[11]94。秦国向东方扩张的过程中,对内史区域外的新占领地区采用设置郡的方式以稳定统治,孙闻博认为郡是“以内史为中心横向派生的军事管理区”[14]151。在内史—郡体制下,内史区的朝官中尉与郡尉握有除吏权,在汉初亦然,如《二年律令·置吏律》载:“受(授)爵及除人关于尉。”[38]37对于其中的尉,有不同说法。整理小组认为尉可能是廷尉[38]37。李均明认为尉是县尉[41]。杨振红认为尉应指郡尉、县尉[22]337。游逸飞认为尉当指郡尉、中尉,并指出“汉初郡尉的人事权当承秦制,渊源于早期郡的军事功能”[19]185。我们认为游说可从,秦县内尉除吏权可能来源于中尉或郡尉。
四、秦县内尉属吏在西汉的属县化历程
西汉统治稳定后,国家管理模式从重军事到重行政。弱化军事而强化行政的举措率先在县中展开,由此,秦时相对独立的县内尉属吏开启了属县化历程,主要表现为尉官转化为县尉、尉史转化为县廷吏员。
(一)尉官属县化为县尉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捕律》中载:“盗贼发,士吏、求盗部者,及令、丞、尉弗觉智(知),士吏、求盗皆以卒戍边二岁,令、丞、尉罚金各四两。令、丞、尉能先觉智(知),求捕其盗贼,及自劾,论吏部主者,除令、丞、尉罚。一岁中盗贼发而令、丞、尉所(?)不觉智(知)三发以上,皆为不胜任,免之。”[38]28该律文显示,西汉初年,县内三长吏为令、丞、尉,士吏、求盗已地方化并对县廷负责。
张家山汉简《秩律》显示秩八百石的县,其丞、尉秩四百石,秩六百石的县,其丞、尉秩三百石[38]71-74。秦代县内尉的职能系统中的司空亦并入县行政系统,在八百石的县,司空秩二百石,在六百石的县,司空秩一百六十石[38]72、74。可见,汉初县中之尉的地位已然下降为县令长之佐官,秩石为县长官一半。
《二年律令·捕律》中载:“群盗杀伤人、贼杀伤人、强盗,即发县道,县道亟为发吏徒足以追捕之,尉分将,令兼将,亟诣盗贼发及之所,以穷追捕之。”[38]27可见汉初捕盗之事已由县尉负主要责任。《续汉书·百官志》载,汉代县尉的职责为“主盗贼。凡有贼发,主名不立,则推索行寻,案察奸宄,以起端绪”[42]3623。两相对照,可发现汉初县尉的职责已与汉代一般制度规定相近,即其职能较为单一,以逐捕盗贼为主。《洪范五行传》中载:“午为尉官,驰逐追捕。”[43]134这表明在西汉人的认识中,追捕为尉官的职责所在。在秦县内尉属吏系统,尉官可能与县丞地位相当,汉初之县尉可能即秦县内尉之下属尉官转化而来。因此,汉初县内不复存在郡尉派出之尉,使得县内长官一元化,权力更为集中。
张家山汉简《秩律》中还显示“县有塞、城尉”,其秩级为“各减其郡尉百石”[38]80。廖伯源认为简文中的“‘郡尉’,非谓郡都尉,应指属郡之塞尉、城尉”[44]。游逸飞进一步推测郡之塞尉、城尉秩石有六百、五百、四百、三百四等,县之塞尉、城尉秩石有五百、四百、三百、二百四等[45]267。那么,县内城、塞尉的秩级较之县尉的秩级略高或相当。
汉初边防任务较重的县中应并存县尉和城、塞尉两套系统。县尉,由秦时县内尉所管尉官转化而来,专司追捕盗贼、维持地方治安。城、塞尉,专司军事防卫,其地位与县尉相当,在秦时可能也处于县内尉的管辖之下。里耶简9-1861中有乘城卒的记录,也似可佐证迁陵县中有城尉,当在县内尉的管辖之下。
综上,秦时县内尉的属吏系统在汉初开始了属县化进程。郡尉派出县内尉不再设置,其部分职能可能归入县令,实现了县内长官的一元化。秦时县内尉所直属的尉官彻底属县化为县尉,尉史继续与县尉保持紧密的关系。士吏、求盗虽然可能与县尉、尉史存在业务关系,但已直属于县廷。
(二)尉史的属县化
张家山汉简相关律文显示汉初尉史依然为县尉直辖属吏,在职责上与县尉保持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二年律令·捕律》载:“□□□□发及斗杀人而不得,官啬夫、士吏、吏部主者,罚金各二两,尉、尉史各一两。”[38]29《钱律》载:“盗铸钱及佐者,弃市……尉、尉史、乡部、官啬夫、士吏、部主者弗得,罚金四两。”[38]35这两条律文显示出在捕盗、盗铸钱等事处理不当时,尉史与县尉一同接受处罚。李迎春认为其时尉史为县尉直辖属吏[46]474。
尉史与县尉的职责一致性在西汉中期的相关史实中亦有展现。在追捕盗贼方面,《汉书·酷吏·田广明传》载公孙勇谋反,其“衣绣衣,乘驷马车”到陈留圉县,为圉县“守尉魏不害与厩啬夫江德、尉史苏昌共收捕之”[36]3664。严耕望认为汉代县尉还主更卒番上[47]220,《史记·游侠列传》载汉武帝时河内郡轵县尉史可免人践更[48]3871,亦显示出尉史与县尉职责的一致性。
西汉中期之后,尉史与县尉的特殊联系逐渐消失,尉史成为县级机构中的一般吏员。西北汉简和尹湾汉简均可见到直属于候官与县廷的尉史存在。边地中的候官和塞尉的关系与县令长和县尉的关系类似,尉史为候官的属吏,秩佐史,较令史地位略低,但行政职能与工作场所和令史差别不大,“都负责收发粮奉、签署、封发文书,直符,诣府等事务”。尹湾汉简《东海郡吏员簿》中存在有尉史而无县尉(75)李解民指出,西汉后期东海郡“不设尉的县有合乡、承2个,不设尉的侯国有新阳、东安、建陵、山乡、武阳、都平、郚乡、建乡、干乡、建阳、都阳11个”,在20个县邑中,未设尉的有10%,18个侯国中,不设尉的占61%。李解民:《〈东海郡吏员簿〉所反映的汉代官制》,《简帛研究》二〇〇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0页。亦可参看纸屋正和《汉代郡县制的展开》第九章“西汉末地方官府的构成——从吏员设置状况考察”中“不置县尉的县、列侯国”部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32-339页。的现象,显示出西汉后期尉史不再直属于县尉,县尉是否存在对尉史影响很小。西汉中期之后,内地县与边地候官中的尉史均逐渐从尉的直属吏转变为县廷或候官的属吏[46]479。
五、余论
在传世文献中,尚有疑似秦代县尉者,如邹水杰引《汉书·樊哙传》“后攻圉都尉、东郡守尉于成武”及颜师古注“圉即陈留圉县”[36]2067-2068,认为“秦县似有都尉之设”,“县尉在秦可称都尉”[40]72。秦及汉初县内诸官,前多有加都字者,如睡虎地秦简《效律》中所载:“都仓、库、田、亭啬夫。”[27]152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还提到“都市亭厨有秩者”[38]80,都尉未尝不可指尉官。秦代玺印封泥中有尉的玺印,如“秦县尉玺印有:杜阳左尉、灋(法)丘左尉、高陵右尉、乐阴右尉、利阳右尉、曲阳左尉、邑尉印、原都左尉、邳鄣尉印等。秦县尉封泥有:高陵□尉、高陵左尉、高陵右尉、平舆□尉、下邽右尉”[49]278-279。上述材料似乎又表明秦代县内有县尉之设,但玺印封泥资料,一方面其年代较难确定,另一方面所含信息具有较大的解释空间,如其中的邳鄣尉印,赵平安认为是设置于下邳的鄣尉所用的官印[50]51-53。县中之尉亦可认为是县尉官或军事系统中的尉。
随着秦国国力上升并不断向东方用兵,秦代县内职官的设置渐次增加并日趋复杂。在秦孝公十二年(前350)的商鞅变法中仅设置有县令、丞,史载商鞅“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48]2712。次年在县内设置有秩史即诸官啬夫(76)孙闻博认为“‘有秩’在类别上主要对应县所辖诸官啬夫”,“初为县有秩史”的记载反映出“商鞅在设置县长吏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县属吏设置,初步建立起县行政组织的基本架构。而架构重要构成的属吏系统,主要是以设置诸官有秩啬夫为标志的。”孙闻博:《商鞅县制的推行与秦县、乡关系的确立——以称谓、禄秩与吏员规模为中心》,《简帛》第1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21页。。但史书中并无设置尉的记载。守屋美都雄认为,秦孝公十二、十三年设立的县令、丞、有秩史为治民官吏,没有武官县尉表示其先已存在[51]72。孙闻博则认为,“《商君列传》还言及‘置’‘丞’,而不及县尉……此或显示商鞅推行县制,秦县最初确立的是令、丞(及史)的系统”[52]119。经过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县内行政系统中并未置尉,但可能存在由朝官中尉派出的尉官,即《商君书·境内》中所载“爵吏而为县尉”[53]116。通过秦简律令和政务文书的记载,我们可以拼凑出秦代地方管理模式。在县内,由朝廷派出令、丞,县中设置诸官与朝官进行业务对接[54]。在新占领地区,出于稳定统治与继续用兵的需要,由郡守、郡尉分别派出卒史、尉成为县内的县啬夫、大啬夫,对县内事务进行管理与监督。郡尉与中尉平级,在非内史区,尉官与郡尉进行事务联系,成为郡尉所派出县内尉的属吏,佐助县内尉管理县内军事尤其是戍卒事务。尉与县令同为长官,地位相差无几,其既有直辖属吏尉官、尉史、士吏、发弩等,还因业务关系将司空、髳长、校长等纳入其职能系统。至西汉初年,县内尉撤出县内事务管理,其属吏尉官转化为以捕盗为主要职责的佐官县尉,县内长官实现了一元化。尉史在西汉时期也逐渐从尉之直辖吏转化为县廷吏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