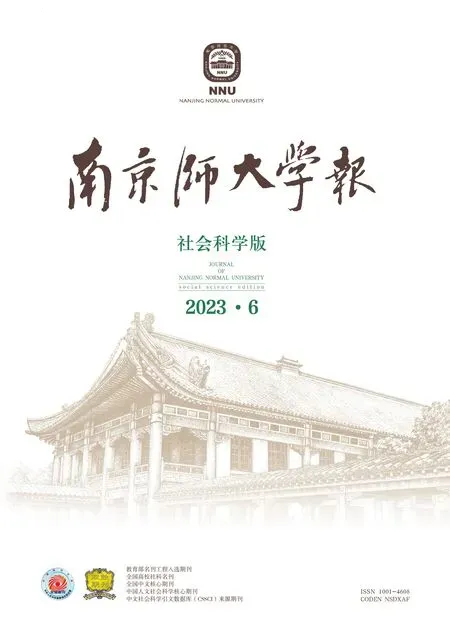寻绎教育概念的逻辑与表达方式
2024-01-26曹永国
曹永国
长久以来,教育是一个充满歧义和纷争的概念。人人皆可对之品头论足,却似乎难以登其堂奥。即使对于那些专业的教育研究者而言,教育的概念也是众说纷纭,难以准确界定。教育哲学家布列钦卡说:“说起来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在‘教育’一词背后居然隐藏着如此不同的概念”“不仅在日常或口头语言中,而且在教育学的文本中,‘教育’一词都具有非常不同的含义、含糊性。”(1)[德]布列钦卡:《教育科学的基本概念:分析、批判和建议》,胡劲松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24页。教育哲学家索尔蒂斯也认为,教育概念如同希腊神话中的怪物——半人马(centaur)一样是虚幻缥缈之物,“假如有人要我们简单说出一般教育之概念,恐怕我们将无辞以对”。(2)[美]索尔蒂斯:《教育概念分析导论》,简成熙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第3页。
事实上,对教育认识之混乱状态似乎有增无减。(3)曹永国、吴丽红:《教育概念的演进、纷争及其逻辑辩证》,《高等教育研究》2021年第7期。一是,大量的教育认识并未得到澄明,反而遮蔽了认真探索。这种情形如同柏拉图《美诺》篇中的场景,给出了一大堆美德的概念,却对美德是什么依然无知。二是,在纷杂的教育概念中,除了熟知的套语、陈词外,我们常常竟不知以何种方式去严肃地谈论教育概念。教育理论与知识的贫乏、杂乱是不争的事实。现实中,为了避免这种理论的杂乱和纷扰,便出现了两种现象:教育实践上大谈方法,将教育降格为教学与实务管理;教育理论上则保持沉默,认同“多样化现象”,所谓既然说不清楚,干脆不再纠结。于是,实践上以现实需要和实时要求为主;理论上则为这种实践做好诠释、支持和优化。然而,这不仅导致了理论和实践的更大混乱,而且使得理论与实践更加趋于功利化、工具化与迎合现实化。各种碎片化的认识、标签式的口号、短命性的实践及随意、浅尝辄止式的规划与“创新”层出不穷;教育边界泛化、模糊,教育新闻化,(4)教育新闻化,主要形容今天的教育日益成为新闻的附庸,即使最严肃的教育思考也需要委身于“媒介文化机器”,追求“新闻轰动效应”。如此,新闻、媒介指导甚至支配了教育及教化,人们的教育知识与观念日益受控于记者、报纸和媒体,与此同时,教育知识与观念不断向新闻看齐,追求教育和教化的新闻化。甚至教育庸俗化、教育消亡论等问题亦日益尖锐。特别是,面对当下教育及其研究愈加技术化、数字化、智能化、时令化的趋向,如何使教育归正返本而又呈现出理论特有的声音与力量,产生一种理性抵制与纠偏作用,这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 问题提出及历史概览
教育概念混乱的一大根源在于,不同人站在不同的角度、立场和利益取向谈论之。不同的学科、理论中的教育,亦大相径庭。如同《会饮》中对“爱”的谈论一样,众人分别从利益、科学、诗歌和故事出发,每个人都振振有词、似有道理,但是忽略了谈论方式的适当性。在一干人发表宏论后,苏格拉底提出了爱的本质和普遍性问题,提出了入思爱的恰当方式的问题。在他看来,对爱的论述应该超越片面的立场和狭隘的管见,不为各种绚丽的言辞所惑,采取一种完整的方式去探寻普遍性的爱。苏格拉底的发言像美妙的音乐一样,沁人心脾而久久不能忘怀,其他言辞与之相比则黯然失色。这里的启示在于:重要的是用一种恰当的方式去探究普遍的教育概念。明晓了普遍的教育概念,知悉恰当的探究方式,如此才能清楚不同的教育概念。
何谓恰当的谈论方式?何种意义上的普遍性?这是必须面对的前提性问题。恰当的方式首先意味着要跳出狭隘的自我窠臼,走出自我观念或偏见的洞穴。其次,恰当的方式不是碎片化的观点杂糅,不是从一种观念走向另一种观念,即由一个偏见转移到另一个偏见,恰当的方式意味着更完整的思维和整体性审视。最后,恰当的方式意味着与普遍性寻求的适切性,即这种方式是寻求普遍性的适切方式。所谓普遍性,是相对于特殊性而言的,意指一种共同的认同,即当我们在谈论教育时,最不能丢弃或遗忘的那些东西是什么,否则,教育也将不是教育。显然,这些东西并非某一时空性的。它们不仅存在于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而且符合人们对于教育的永恒期待和理性审思。
何以为之?我们首先需要回溯那些谈论教育的经典方式,从中汲取思想智慧。在教育历史的演进中,我们才能弄清来龙去脉。亚里士多德曾说:“我们如果对任何事物,追溯其原始而明白其发生的端绪,我们就可获得最明朗的认识。”(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页。
诗,显然是人类最早谈论教育的方式。在中国上古时期,教育往往表现为“诗教”“乐教”,以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在一种“诗乐”形式的教化中,民众获得了对教育的理解与领悟。“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兴于诗、成于乐”。诗之于教育教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古希腊时代,诗人们是最早的老师,通过戏剧、史诗,人们敬畏神明、净化心灵和情感。采用诗歌、戏剧等艺术化的表达是教育教化最主要的方式,人们往往也是通过这些艺术作品谈论、探究和理解教育。这一点,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可见一斑。(6)尽管《理想国》引发了哲人与诗人的冲突,但是柏拉图的对话常常被誉为最好的诗作。在柏拉图的诸多批判诗人的对话如《伊翁》《会饮》《斐多诺》中,柏拉图都塑造了一个更好诗人的形象。后来,哲学逐渐取代了诗歌,成为表达和探究教育最主要的方式。在柏拉图的哲学体系中,《理想国》一直被视为探究教育的伟大经典,《理想国》中的“洞穴隐喻”是谈论教育的经典方式。“洞穴隐喻”生动描绘了一个完整的教育过程,并为人们提供了对于教育的丰富想象。洞穴表达了人类生活的真实情境,教育被描绘成个体摆脱束缚走出洞穴又重返洞穴的完整而复杂的过程。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几点认识:第一,谈论教育需要以理想观审现实,追求现实的超越;第二,使用对话的方式探究教育,重现教育的生活关怀;第三,谈论教育关涉对人类美好心灵的探究与想象。亚里士多德赓续了这种探究教育的方式,从人的幸福和完整德性出发,将教育、幸福和德性统一起来,使得教育理想的寻求与现实关怀结合起来。在他看来,教育在于促使人完整德性的完整发展,因此,谈论教育就离不开对人的实践德性和理智德性的探索。与苏格拉底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更加关注教育实践智慧,即崇高目的在现实中运用。随后的希腊化时期的诸多思想流派,如斯多葛主义、伊壁鸠鲁主义、怀疑主义与犬儒学派等,它们均基于美好生活和完整人性的思考,对教育教化展开了多种丰富的探索与理性实践。当时盛行的各种“学园”实践,其实质为人性与精神的操练。这些哲学流派对教育的思考是本体论的、终极性的,体现出了一种教育追求美好生活和崇高精神的“生活美学”。(7)[法]福柯:《说真话的勇气》,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89—292页。
思想家阿多说,古典哲学的智慧是生活的智慧,是如何更好生活的实践智慧。(8)阿多在《古代哲学的智慧》《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别忘记生活》等著作中均表达了这一观点。在阿多看来,哲学教学就是哲学生活,这里没有学科和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知识,不是知识体系的建构,而是走向美好生活的实践,是作为生活智慧探寻的哲学。在这里,教育关注德性、真知、永恒,将教育放置人的理性成长和美好生活的理想之下去考量。这是一种强大的博雅教育传统,知识、德性、美好心灵和美好生活是统一的,(9)P.H.Hirst,“Liberal education and the nature of knowledge”,in R.F.Dearden,P.H.Hirst &R.S.Peters(eds.),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ason,London:Routledge &Kegan Paul,1972,pp.292-293.这便是对教育的普遍性认同。教育成就个体生活的能力和智慧,对教育的谈论必须基于人及其生活的思考。这种对教育的定义和理由是基于知识本身的性质、德性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而不是基于学生的偏好、某种社会的需求或政治家的突发奇想。这是非常强大的教育传统,后经中世纪教育理想和人文主义思想的冲刷与洗礼而得到巩固与赓续。事实上,每当教育出现迷惘、偏离时,这种传统就会被不断提及、加强,促使人们进一步全面地反思教育。即使在当代,它依然熠熠生辉,得到了诸多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强烈捍卫。阿诺德、马里坦、赫钦斯、白璧德等著名教育家便是其中的代表。
与这种以艺术、哲学的方式探寻教育的普遍性不同,夸美纽斯开创了以经验科学探究教育的先河。这是另一种教育普遍性的寻求,其出发点、呈现方式和志趣与古典时期皆有所不同。它是以科学志趣和实用目的为基础的普遍性寻求,亦是教育不断寻求科学化认同的过程,并且伴随着自然科学兴起、兴盛与支配。这一过程体现为:从教学方法体系化到教学方法理论化,从教学方法理论化到教育理论普遍化,从教育理论普遍化到教育科学化与多元化发展。就教育概念而言,其亦经历了从实用性、功利化目的转型到普遍性、理论化改造再到人文性的抗争与复归。
夸美纽斯并未立足于人文教化理想(Paideia)的教育传统去思考教育,而是从教育服务于工业社会的实用性出发。在这里,实用性、操作性、便捷性成为谈论教育的首要考虑。在《大教学论》中,夸美纽斯认为,从学校里出来的人都应该成为一个积极的行动者,教育必须为经济而考虑。(10)[捷]夸美纽斯:《大教学论》,傅任敢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55页。这里的逻辑是,教育教学存在着普遍的规律,就像自然界中事物一样,可以被总结、被揭示;同时,唯有用这种普遍规律改造教学和学校,才能提高教学效率。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教育者,夸氏对教育教学的思考不仅仅是方法,而是一种“大教学论”,体现出了对“方法论”“理论化”的思想追求。然而尽管如此,教育史学家博伊德和金仍然认为:17世纪绝大部分改革家……一般说来,他们不接触教育和人生的根本问题,仅把自己局限在教育方法的较肤浅的细节上。(11)[英]威廉·博伊德、埃德蒙·金:《西方教育史》,任宝祥、吴元训主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39页。为克服这种并不“普遍”的教学理论,赫尔巴特用“普通教育学”表明自己的理论取向:寻求普遍性的客观的教育知识,超越单纯的方法论探究。为了建立普遍的教育学,赫尔巴特借助了当时最为普遍的科学——伦理学和心理学来论证,从目的与方法两者的统一性上致力于教育知识的构建。这的确是一种更为高明的教育论证:一是教育知识必须科学、普遍;二是对教育的探究必须“合目的性”与“合兴趣性”或“合认知规律”。然而,随着自然科学和实验心理学的兴盛,赫尔巴特的后继者则似乎偏离这种统合考虑的思路,沿着技术化、实验科学路线越走越远,对教育的谈论也大都立足于如何快速掌握知识,坚持日益分化的技术理性操作和实用功能。(12)曹永国:《近代教育学思维的三次浪潮及其检视》,《高等教育研究》2016年第1期。这似乎又回到了“方法论”的老路,但是以“自然科学的范式”去规范。如此,对教育的思考和探究也就越来越趋于普遍性的通用的技术开发上,那些难以用自然科学范式探究的东西便被无情地忽略了。雅斯贝尔斯说:“教育一再出现的特有现象:放弃本质的教育,却去从事没完没了的教学试验”(13)[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邹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46页。。
在这种以功利化、自然科学范式入思教育的浪潮中,卢梭是一个反例。他试图恢复对古典教育思考中的人文、人性因素,以抵制和制衡这种自然科学化、方法化的教育取向。卢梭的独特性在于:一是以小说故事表达教育;二是以人的生活和理想来谈论教育。卢梭对教育的谈论并未局限于儿童教学方法,而是如同柏拉图洞穴隐喻那样,努力书写教育的完整过程。卢梭认为教育必须基于个人自由、美好的生活以及未来美好社会来筹划。在爱弥儿的教育中,精神教化、德性能力和生存技能三者统一,既不能偏废,也不能僭越。在卢梭看来,以小说的方式谈论教育,可以避免简化、片面化的危险,能够促生更多关于教育的想象。以美好生活和理想社会安排教育,既可以避免仅就现实来谈教育,将教育仅仅视为现实与当下的工具;又可以指向教育的普遍性寻求——美好生活和美好教育。卢梭认为,教育必须追寻自然、以自然为师,而自然一词意味着超越、本质、本性,因此追寻自然就表明自己是在寻求一种最普遍的本真性教育。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作为近代科学和理性启蒙的重要旗手,卢梭并不反对教育科学和普遍性方法,(14)事实上,卢梭在《爱弥儿》中提出了诸多养育儿童的实用方法,但是《爱弥儿》却非“育儿大全”。而是主张思考人的教育需要,从人性和美好生活出发,以生活和人性的普遍性、本真性作为基点。
这里我们可以得到几点认识:首先,对教育的思考呈现出“目的论”与“方法论”两种不同的普遍性追求;其次,思考教育概念就是探寻教育之本质,而非某种偶然性或经验,这种思考绝非局限于当下需要,甚至不是出于当下考虑;再次,对教育概念的思考需要捍卫人类教育的伟大理想和美好想象;最后,博雅教育传统仍是思考教育概念的重要理论。
质言之,古典教育传统探寻永恒和普遍性,以德性卓越和崇高信仰建构教育理想,它对教育的思考是超功利性的、本体论的。近现代教育思考转向了方法论和认识论,对教育的探究旨在寻求普遍规律,关于教育的定义往往基于自然科学范式、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定义,尽管其中有科学与人文之争,但都表现出对普遍性、本质性的坚持。
然而,这种渴望超越、寻求普遍、探究本质的取向与范式在现当代遭到质疑与否弃。首先,人们认为,谈论教育应致力于解决当下问题,而非对普遍规律和本质东西的寻求。再次,人们认为,教育离不开教育所处的具体环境,离不开人们具体的历史文化,对教育的谈论就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状况。这两点的影响巨大:一是关于教育的独立性自由探索丧失,教育的当下性、工具性绝对凸显;二是教育本质性探寻的消亡,以及历史主义、相对主义教育取向的合法化、垄断化。尽管我们并不否认这种取向所产生的教育理论贡献,但祛除了普遍性的教育探寻,教育理论与实践则容易陷入一种“诸神纷争”的境况。事实上,表面的繁荣景象也流露出一种“混乱”“无序”及“怎么都行”的隐忧。碎片化、功利化、主观主义、时髦化等教育谈论在今天惊异地纷呈出现,同台唱戏。这种现象不仅不令人欣慰,而且令人担忧。如同麦金太尔所言,我们如此多地用来表述分歧,而表达分歧的争论的最显著特征是其无终止性。这些争论不仅没完没了,而且显然无法找到终点。(15)[美]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戴扬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5页。事实上,如何谈论教育正滑向种种相对主义、支离破碎、主观武断和相互不宽容的泥沼。与之相随,一些对教育的谈论则被“分散到心理技术的诀窍上去,发散到大量的功利主义活动中”。(16)[法]马里坦:《教育在十字路口》,高旭平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页。
二、 “清思行动”及辩解
解构了教育“宏大叙事”,越来越走向相对化、个人化、多样化和当下性的教育概念论述反而使“教育的困惑与隐忧”越发加重。“教育的迷惘”与“教育学的迷惘”都不仅是感受,更是事实。人们有时戏谑:“一百本教育学教科书,不仅有一百个不同教育概念,而且有一百二十个不同教育概念。”面对如此现状,如何思之、为之?
应对同样现象,分析教育哲学家们试图进行“清思行动”,寻找对教育概念的正确表达,并在教育学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主张明晰的概念分析和清晰的逻辑论证,要像建立科学概念那样探寻教育概念,至少应该有对不同教育话语背后所隐藏的观念和标准的认识,即使人有“清醒认识”“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最初,这些哲学家们致力于最基本教育命题的逻辑分析,立足于提供符合逻辑的教育概念、命题;随后,他们转向了对教育价值的分析,纠正了前期单纯的逻辑分析的偏狭。
作为最初的代表人物,谢富勒系统地进行了教育的语言分析,祈求在理性的基础上探究通观知识。他详细分析教育的三种语言:定义、口号和隐喻叙述,检视这些语句在使用中的情境、力量与效度。为此,谢富勒批评教育概念的随意、含混、空泛与词义不明,廓清教育基本概念和论证模式,“希望能通观事物……力求视野至广,迷思至少”,(17)[美]谢富勒:《教育的语言》,林逢祺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第3页。达成“逻辑性目标”。作为伦敦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彼得斯深感教育概念的混乱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教育实践的混乱。他提出了“教育规准”概念,用它来标识教育和其他人类活动或社会化进程,譬如学习、训练、疗愈、社会化等之不同。尽管彼得斯的论述相当复杂,但我们还是可以指出几个特点。在他看来,教育活动必须满足:(1)教育涉及知识、技能的获取,它们包含一般公认的价值和意义,即不能使个人变得更糟;(2)教育必须符合人类公认的美好价值,并服务于这些价值;(3)教育涉及一种宽广的文化或宽厚的知识,而不是单一类型的知识,即教育是关于完整性发展的活动,这种兼具深广的知识能够理解事情的“所以然”;(4)教育应该是符合自愿性的,是个体自愿的投入,至少不能破坏学习者的自由反省能力,质言之,教育应避免对学习者进行灌输、规训和心智操控。后来,彼得斯在《教育的逻辑》等著作中又重新论及了这一主张。彼得斯对教育的定义影响巨大,既产生了大批拥趸,也产生了诸多批评者。赫斯特、蒂尔登、威尔逊等人支持对教育概念进行严格的逻辑分析论证,卡尔、斯坦迪许等人则支持对教育的历史文化主义探寻。其中赫斯特和卡尔之间的论争持续了十数年,极大地丰富了对教育概念的认识。(18)曹永国:《教育哲学之学科认同危机及自我启蒙》,《高等教育研究》2018年第5期。
赫斯特等人认为,教育应具统一的、普遍的、明确的定义,这是谈论教育的前提,也是治理教育概念混乱的前提。在这里,谈论教育必须建立在科学的逻辑和规范的论证之上,唯有建立在规范的科学的逻辑分析之上的、经过澄清的教育理论才是可靠的。对教育的谈论就在于寻求教育的普遍性、明确性,逻辑不明、论证不清就无法确保真确性。卡尔等人则认为,教育的概念不同于科学事实,也不是像猫、狗这样的具体物,而是涉及一种人类构建的具体的教育实践,谈论教育不能忽视教育所处的具体社会文化环境。在卡尔看来,教育是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根本不会有什么客观中立的教育规准,也无可避免地要与社会文化传统和现实现状联系起来,企图提供一次性的标准注定没有用处。(19)W.Carr,“Professing education in a post-modern age”,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Vol.31,No.2,1997,pp.309-327.这种社会建构论观点获得了很多的认同,并流行于当代教育学的研究之中。人们认为,双方的争论本身就说明教育并不具有一种清晰的认识和明确的定义,逻辑分析和清思行动于教育本身无益。事实上,这种认识经过后现代思潮的推波助澜,竟形成了一种垄断性的偏见。然而,这种主张却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困境:(1)失去判断和批判任何教育观点的立足点;(2)教育概念日趋松散,或失去严肃性,例如我们会将一次难忘的经历或惨痛的教训或看一场电影视为教育;(3)各执一端、各自为政,难以产生开放和真诚的对话。
事实上,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传统、政治制度会产生不同的教育观念和实践。然而,如果仅局限于此,则容易导致思想的保守,陷于自我偏见、陈规、习俗之窠臼,容易产生相互对立、彼此排斥的混乱状态,并且难以产生开放的心灵。阿兰·布鲁姆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中批评这种看似自由而多样化现象,视其为一种走向自我封闭的心灵。因为失去了对永恒、普遍的寻求,个人就会自觉自己观点和行为正确,从而无法在心灵深处认真对待他者观点。在布鲁姆看来,唯有对普遍的、永恒的、不变的理念的探求,才能促使心灵的真正开放。如果说探寻知识、真理是表达个别化、主观性和短暂性观点的话,那么这在逻辑上是难以理解的,甚至是荒诞的。为了克服这种虚无主义的错误,对真理抱以真诚的探索实为关键。探寻教育概念的逻辑就要超越各种具体观念和具体处境的限制,寻求普遍性认知。分析教育哲学正是立足于普遍性的考虑对教育概念进行逻辑分析。唯有一个科学的清晰的教育概念,我们才能知晓我们的行为是否合乎教育,在何种程度上合乎教育。彼得斯说:“要定夺这些相互冲突的信念和标准,唯有在可兹评估的参照标准规准之后,方为可能。”(20)[英]皮德思:《伦理学与教育》,简成熙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68页。
尽管分析教育哲学家们与他们的反对者一直争论不休,但他们对自己的辩护却并非出于战胜的目的。面对诸多批评之声,分析教育哲学家们进行了自我完善和更新,彼得斯、赫斯特等人都吸收有益的见解,亦逐渐转入对现实教育和教育价值的关注。彼得斯曾提出,当代教育哲学最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应对时代的挑战,因而,要与时俱进、关注现实。但是,严肃和规范的论证,清晰的逻辑以及对教育概念的普遍性、客观性寻求之传统被保留下来。他们对于教育概念的逻辑分析,严谨的治学态度,系统性、批判性的审思等都极大地影响了学术界。并且,这种影响不仅局限于教育学界,而且扩展到哲学界、政治学界等领域。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如欧克肖特、赖尔等也被吸引进来,美国哲学会还专门设立教育哲学的专属学术机构。它改变了当时乃至后来谈论教育的方式,使得分析的方法、规范性的论证和严谨的科学性成为谈论教育必须坚持的基本要求。后来,彼得斯重提了这一点:“学科概念的严肃界定、知识理由的耐心说明以及不同论述形式的预设探究等……分析哲学家们新颖之处在于对本质觉察得更为透彻”,(21)[英]皮德思:《伦理学与教育》,第67页。对教育的谈论必须避免失之偏颇与肤浅,要在坚持规范性论证和普遍性追求下不断自我更新,既不成为随风转舵的“变色龙”,又不被僵死的教条束缚。
三、 教育何以谈之
梳理教育概念发展的逻辑以及分析教育哲学的遗产:尽管人们在寻求教育及言说方式的真确性与普遍性上会不断地触礁,但多元主义的极端化、主观观念的随意建构、狭隘立场的强力捍卫等对于教育都具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探寻教育需采取客观公正和负责任的态度。如今,谈论教育面临两大变化:一是,技术化、实证化的单一性话语体系越来越垄断了对教育的谈论,入思教育也愈加工具化、功利主义化;二是,本质性、普遍性的教育内涵及话语探究不断遭到解构,从而忽视了对教育本质或本真性探寻。重提如何谈论教育概念,对于理论和实践仍然具有重要价值。正如当代教育家卡尔所言“这项任务需要更进一步的关注,因为毫无疑问的是,此一基本概念的问题,将持续地成为当代教育理论建构及政策决策中最深刻、也最持久困惑的来源。”(22)D.Carr,“Liberal education and its rival”, From Liberal Education to General Education:A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Taipei:University of Taipei,2015,p.10.
1. 谈论教育概念须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
以往我们批评分析教育哲学只重视逻辑分析,忽视了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因素,忽视了教育是关注价值的行为。但是,这或许是一个偏见。分析教育哲学家们重视博雅教育的传统,认为教育是关乎全人的行为。这一点从他们的专著可见一斑,如《伦理学与教育》《教育与美好生活》《教育的目的》《知识与博雅教育》等。但是,他们又的确“忽视”了具体的历史文化对教育价值的规范,至少他们不认为谈论教育首先应该考虑这些。
与之相反,我们在谈论教育概念时,往往将其视为一种社会活动,一种受制于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制约的活动。于是,我们就首先从社会现实出发,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谈论教育。这固然很合理,但更多的时候是指向了一种外在化要求对教育的规范。基于各种功利主义的考虑,我们将教育视为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这常常使得我们根据一个人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职位来谈论教育,在种种务实的技能中定位孩子,让系统的教育、学习事业为现代工业、商业和其他外在事业所绑架。(23)刘济良、马苗苗:《教育场域中个体生命自由性的隐退表征与复归路径》,《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年第4期。这种要求和计划将个体发展不断撕裂成特定的碎片化技能,使其不断地适应“此时此地的主宰”。彼得斯在《教育与教育人》一文中提出了“教育人”的概念,认为教育关乎人的完整发展。在彼得斯看来,对教育的理解必须基于何为一个受教育人的考虑,需要问询一个受教育人具有何种素质。后来,哲学家欧克肖特发表了《教育事业及其挫折》,认为教育是人类的事业,必须从人的生活来谈论教育,从个体作为一个新来者融入人类生活角度去理解教育。在我们都热衷于教育如何服务于各种社会角色时,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谈论教育无疑有正本清源之功效。从人的全面发展来谈论教育,这不仅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更是对教育的本体性的捍卫。
如果没有立足于人的发展,没有对人的全面理解,我们就不能很好地谈论教育。我们说教育使人成为人,对人的认识、理解是我们谈论教育的前提,也是我们筹划教育的前提。人的发展是教育最根本的要求。偏离或不考虑这一点,教育对于人而言似乎将成为多余的事业。教育是完整的人的教育,博雅教育传统的伟大生命力正蕴于此。也正是基于这点,我们才能更加清楚为何要把人培养成各种所谓的“经济人”“政治人”“技术人”“学术人”等,知晓这些各种人在教育中的限度。习惯于将教育工具化,不但容易产生本末倒置,而且容易造成人发展中的碎片化、功利化、任务化。因此,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谈论教育,就必须尽力避免从单一一点谈论人的发展,避免过度放大某个特定方面的能力。保护人发展的完整性和全面性,一直是教育和个人发展的目标与理想追求。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发展造成人的异化时,就特别强调要避免人的能力的片面化、单一化、畸形,必须推进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今天,教育要解决“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的根本性问题,就是要重新理解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重新树立人的全面发展的时代使命。“新时代教育方针的制定必须坚持立德树人、德育为先,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把教育的重点转向人本身,在教育过程中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中心地位。”(24)翟博:《新时代教育工作的根本方针》,《中国教育报》2019年9月16日,第1版。
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这意味着谈论教育概念始终要将人自身的价值和独特意义放在首位,尊重人的内在价值和独立性,正确维护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各种价值秩序,真正回归到教育对人的价值和目的的重视上来。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谈论教育概念就需要推动对人的发展的多方面、全方位、高质量理解及其实现。
2. 谈论教育概念须是“普遍性的”“本质性的”寻求
尽管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对教育指点江山,但是谈论教育概念却应是“本质性的”“普遍性的”。对教育概念的谈论在于更好地理解教育的本质,更好地揭示教育的本质性,而非只是呈示个人的感想、观点和建议。尽管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教育有不同的要求和诉求,教育也不是存在于虚空之中,但是教育概念首先探寻的是教育之本真、教育的本质,即何种教育才可谓真正的教育。“本质性”首先意味着超越性,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悬置个人的立场、偏好、观点和不同社会的要求。哲学家欧克肖特写道:“教育事业既是一项纪律,又是一种摆脱;它们相互依存……这是艰难的事业,它呼唤谦卑、耐心和勇气。它的奖励是从仅有的‘谋生的事业’,从出生地点和时间的即时的偶然性、从瞬间的主宰、从当下环境的奴役中解放出来。”(25)[英]欧克肖特:《人文学习之声》,孙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107页。
本质性要求我们,教育谈论要从人及其生活的本质去考虑。这意味在谈论概念教育时,需要认真思考人的世界是一种什么样的世界,它是由什么构成的,新来者如何才能成为这个世界的合格成员,他们又是如何表现得像一个人,等等。这些思考并不是对人的事实性、生物性的客观描述,也不是政治家们的具体规定。这些思考关乎人的命运和本质、意义和价值、人性与使命,对于人及其生活而言是根本性的、本质性的,而教育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使得新来者获得这种理解和认识,能够参与且正确地参与这个世界。这种对人自身的本质性理解高于我们对教育的功能性理解或者对教育的社会本位主义的定位,“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去指导人成为人的那种活生生的动力”。(26)[法]马里坦:《教育在十字路口》,扉页。在教育中出现的人首先应是“本质性的”,而非“具体的”“特定的”“历史的”。卢梭在《爱弥儿》中写道:“从我的门下出去,我承认,他既不是文官,也不是武人,也不是僧侣,他首先是人:一个人应该怎样做人,他就知道怎样做人,他在紧急关头,而且不论对谁,都能尽到做人的本分;命运无法使他改变地位,他始终将处在他的地位上。”(27)[法]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页。这种对人及其生活的本质性关注能够把具体的现实和对人的终极性关怀联系起来,能够有效克服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现实主义方式思考教育的局限,使教育概念具有更大的视野和宏伟的抱负。
今天,谈论教育更多的是历史性的、时代性的,更多地谈论教育的特殊性,却忘记了教育的普遍性、共同性、永恒性,遗忘了教育对人的普遍性的关切。这往往使得我们无法清楚地知晓现实教育的优劣,或者只能从其他非教育领域评判教育的好坏。事实上,当我们过于关注于教育的个别性、特殊性、历史性时,我们就容易破坏人们共同生活、团结和相互理解的纽带。
3. 谈论教育概念须坚守认知与价值的统一
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人,这是教育的内在规定性。在彼得斯看来,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需要从认知和价值两个方面规范,不可偏废。在认知方面,我们对教育的谈论需要围绕推进人的理智发展,促进个体理性精神的成长;在价值方面,对教育的谈论需要关涉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体现出对人类共同价值的捍卫。教育是人类崇高的事业,它通过真善美关怀个人心灵、生活和美好社会。教育如果没有对真理和对绝对价值的虔敬,那么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或者至多只是一种劝学的态度。(28)[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第44页。第斯多惠曾说,如果离开了对真善美的关注,教育如同一个叮叮当当的小铃铛。(29)[德]第斯多惠:《德国教师培养指南》,袁一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页。柏拉图坚守教育是一种灵魂对良善和美好的向往,对教育的谈论必须为青年人提供一种对理性和好人的希望、热情和信心。(30)[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3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89—407页。
认知与价值的统一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蕴:一是认知与价值的规范性,二是认知与价值的统一性。前者是说谈论教育离不开对认知因素和价值因素的考量,要有理性的真诚和价值的追求;后者是说谈论教育不能是认知和价值的分裂,认知与价值要相互融合,即认知中体现价值取向,价值中有理性判断或认知合理性。在这里,认知因素不同于我们平时所讲的智育,而是对事物的一种完整而独立的判断与理解能力,它来源于博雅教育的理性传统或知识传统。理性和知识让我们知道何为真实的、正确的,何为虚假的,这种知识指向人心灵中的“神圣领域”而非致力于功利化意图,使我们知道何为心灵中最可靠、最有益的营养。质言之,它们和我们的幸福、心灵、精神相通。价值因素意指实践方面,指向教育对个人德性的关注。“教育,其一贯的原则乃在发展优良的品德。因此,教育理由与优良品德的发展必然有关。”(31)[英]赫斯特、彼得斯:《教育的逻辑》,刘贵杰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4年,第27页。教育所要求我们的是一种人格和道德的成就,“道德考虑进入教育成就方面的方式比进入其他任务方面的方式更清晰”。(32)R.S.Peters,“What is an educational process?” in R.S.Peters(ed.),The Concept of Education,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1967,pp.1-23.显然,这里知识和美德是统一的,知识体现了德性的价值并能够判断何种德性是心灵最好的营养,而德性则表达着我们的理性和实践智慧。
谈论教育需要关涉认知和价值两个方面,并应指向知识与德性的内在性和完整性。以往我们在谈论教育时,尽管都会谈及知识与美德两个方面,但是存在着两种普遍的现象:一是容易出现知识与美德的割裂;二是容易立足于知识与美德的外在功用谈论教育。如今,重提认知与价值的统一,就是要求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知识和价值关怀影响到我们的教育观。因此,在谈论教育概念时,需要认真审视自己的知识观、价值观的合理性与完整性。审视和完善我们的知识观和价值观,关注知识与价值的内在性,这是我们更好地谈论教育的前提。
4. 谈论教育概念应规范性多元
分析教育哲学家们所带来的最大启示是一种规范性的探寻与严肃性的论证。由于谈论教育概念并非一种口舌争锋,而是如何看待教育和如何实践的重要之事,因此,规范性的论证、严谨客观的态度就十分重要。这种规范性既包含了论证的规范性、逻辑的合理性,又包含了价值的合理性以及理性的判断。今天,教育所面临的环境较以前更加复杂,人们对教育重视的程度也更加空前,所以这一点尤为必要。
规范性多元指规范性和多元化的统一,即对多元的规范与对规范的多元。规范性拒绝以多元之名而滑向相对和虚无,多元则限制以规范之名迈入教条主义和原教旨主义。首先,规范性要求必须避免谈论的随意性,避免哗众取宠、肆意创新。对教育观念的谈论在逻辑上要值得推敲,经得起推敲,体现一种理性和求真的真诚,而不是一种浪漫化、个人化的描绘。尽管今天难有一种统一的教育学说,但是规范性论证却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原则。其次,规范性要求我们在谈论教育时秉持一种价值理想,要使这种谈论体现出我们对美好教育和美好生活的向往。由于教育是一种规范性实践,谈论教育概念应是对好的教育的追求。这就意味着,规范性要求我们自觉抵制那些有损于教育,或者将人完全工具化、降格化的偏见性言论。第三,规范性侧重于形式和论证上的要求远远大于对具体内容的实质性规定。规范性不是对教育的具体的、详细的规定,而是对我们谈论教育的合理限制,限制那些所谓的轻率之举。因为离开了这些形式上的规范,我们几乎无法进行有益的对话。
规范性多元要求谈论教育概念须表现出一种谦卑、开放和理性宽容的品德,不能唯我独尊。在这里,首要的任务不是确定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性地谈论教育的问题,致力于获得一种合理的、中肯的、深思熟虑的认识。这一点要求我们的谈论更具启发性,以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探问教育之本真,而非“自说自话”式的封闭。概观教育概念演进历史,教育概念及其探问方式是有争议的,但是解决争议的方式却绝非加大偏见、固守成规、寻求一尊、制造鸿沟,滞留于各自的不可通约性和特殊性之中。不同的理论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恰恰证明我们应该放弃那种自以为是的单一化尝试,避免非此即彼的思维。由于教育问题所面临的复杂性、偶然性,明智之举就是坚持思考的完整性、严肃性和审慎性,保持开放性的态度。规范性多元的意义也许正如索尔蒂斯这段话所言:“关于‘教育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并不能直接回答,而是藉着询问一些原初性问题,更能澄清这个问题的预设;再者,第二个目标是介绍一些哲学思考的方式,以探讨教育与教育概念。我们希望在承诺教育行动前,能先作思想的澄清。”(33)[美]索尔蒂斯:《教育概念分析导论》,简成熙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