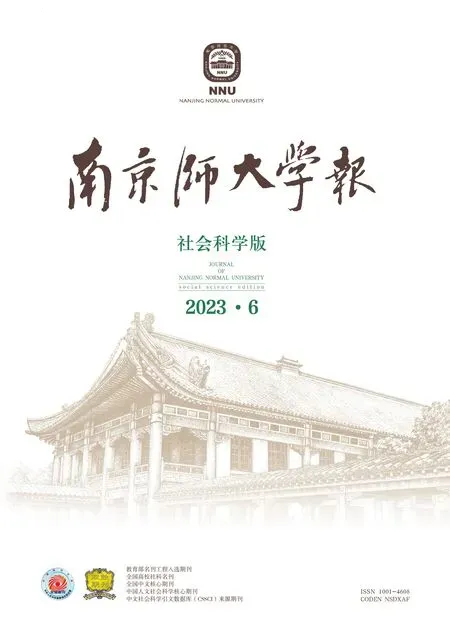奈保尔笔下身份困境中失语他者的主动言说
2024-01-26张弛
张 弛
受西方教育影响,奈保尔描绘的后殖民社会向来被霸权语境笼罩。欧洲人借助殖民暴行和文化霸权,否定被殖民者的能动性,剥夺他们的独立身份;在作家的推波助澜下,被殖民者沦为殖民者膝下的沉默“他者”,其微弱的反抗也被视为对西方的模仿,“这种自欺欺人获得尊严的方式从本质上反映了他们自信的缺失”(1)D.S.Traber,Whiteness,Otherness,and the Individualism Paradox from Huck to Punk,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p.11.。同时,被殖民者往往表现得虚弱且无能:他们无法打赢任何一场反殖民战斗,甚至无法对殖民活动心生半点抵抗之念,丧失了其“原本拥有的能动性和创造价值的能力”,因此,殖民者们得以堂而皇之地“将自己的价值观、能动性和人生意义强加在被殖民者身上,迫使他们变为为自己效忠的仆人”(2)赵飒飒:《旅行写作“讲述”与“展示”的“真实”——以V.S.奈保尔“印度三部曲”为例》,《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17年第2期。。在奈保尔作品中,无论是旅居群岛的印度后裔,还是受困身份危机的混血儿,抑或身处多重压迫之下的女性角色,都是缺乏能动性的他者。特拉博(Daniel S.Traber)认为,在主体制定的霸权中心话语体系中,他者是与“合法性、理性和文明截然相悖”的存在,甚至被打上“不在场”的标签(3)V.Plumwood,Environmental Culture:The Ecological Crisis of Reason,p.106.。因此,重新发现、阐释、肯定他者群体的能动性是消解他者身份、挑战霸权话语的先决条件。奈保尔通过塑造包括华司沃斯、吉米、图尔西夫人和海瑞拉夫人等勇于挑战种族、阶级和性别桎梏的社会底层人物,对殖民主义霸权话语提出了质疑和挑战,间接实现了对主体、他者二元对立关系的解构。
一、 文化飞地的权力对抗
出版于1961年的《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AHouseforMr.Biswas)是奈保尔耗时三年完成的长篇巨著,评论家们纷纷称赞其独特的叙事视角和戏剧化的情节设置,认为这部反映“特立尼达和印度社会真实物质场景”的幽默作品堪称“作家早期创作生涯中的巅峰之作”(4)J.Levy,V.S.Naipaul:Displacement and Autobiography,New York:Routledge,2015,p.1.。就连那些对奈保尔的写作风格和创作立场颇有微词的学者们也不吝溢美之词。维斯(Timothy Weiss)指出,奈保尔的人物刻画从早年的“粗浅勾勒”进阶至“细腻的笔触”(5)T.Weiss,On the Margins:The Art of Exile in V.S.Naipaul,Amherst,MA: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2,p.47.。尼克森(Rob Nixon)曾批评奈保尔的前殖民地描写充斥着“非理性、历史缺失、没有希望、庸俗、寄生和模仿”等诸多负面标签,却称赞这部小说是“最与众不同的作品,蕴含无与伦比的独创性”(6)R.Nixon,London Calling:V.S.Naipaul,Postcolonial Mandari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3-6.。奈保尔本人则将该书视为“能与自己产生情感共鸣的作品”,尽管在创作中历经前所未有的“精神和肉体的疲乏”,付出了“任何嘉奖都难以弥补的代价”,但撰稿过程依然是“生命中最充实、最快乐的时光,是人生中的伊甸园”(7)V.S.Naipaul,“Foreword to A House for Mr.Biswas”,in P.Mishra(ed.), Literary Occasions:Essays,New York:Alfred A.Knopf,2003,pp.128-135.。
小说主人公毕司沃斯先生在其短暂的46年人生中经历了“精神和肉体的疲乏”,饱受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迫。作为婆罗门,种姓荣耀随着其祖父以契约劳工身份离开印度、定居特立尼达而消失。在与图尔西家族的婚姻中,尽管种姓充当了门当户对的符号,但他并未因此获得主动权,反而因为来自“一点儿钱都没有的阿约德哈家族”(8)V.S.Naipaul,A House for Mr.Biswas,New York:Penguin Books,1977,p.91.本文对《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的研究,皆基于此版本展开。而遭到鄙视。在特立尼达的后殖民社会中,毕司沃斯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就连图尔西家族也在流散中历经了阶级落差和文化疏离。家族创始人梵文学者图尔西在殖民地印度人中颇有声望,但是其家族成员仍被视为外来者,“他们远离印度的房屋和土地,也不再与那些追忆梵文学者的劳工、租客和朋友们联系,他们的印度地位变得毫无价值”。这些印度移民以宗族聚集,“形成一个独立于主流社会中心的边缘地带”,以此避免“被主流社会同化或排斥,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移入的社会中艰难地生活”(9)张德明:《流散族群的身份建构: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2页。。家庭的疏离和拒斥也是导致毕司沃斯先生身份困境的重要因素。他在最不吉利的半夜出生,胎位不正,长着六根手指,被视为厄运的象征。父亲始终对他心怀恐惧和戒备,认为这个邪恶的孩子“总有一天会把家族变得一贫如洗”。入赘图尔西家族后,这种偏见依然存在。他是整个哈努曼大宅中地位最低的人,无论他如何示好,大宅里都无人关注他,甚至当他独自离开大宅前去西班牙港工作数月后返家时,亲戚们觉得他“仿佛从未离开过”。
毫无疑问,自幼断裂的亲情纽带和入赘后的冷落境遇使毕司沃斯先生在特立尼达的印度文化飞地中陷入身份困境,成为游离在家庭核心和殖民地主流群体之外的局外人。但是,他既不屈服于命运安排的颠沛流离,也不甘心寄人篱下,更不愿一辈子在大宅的权力空间内受到规训和监视。房屋,不仅是其“遮风避雨之所”,更是“安身立命之地,是他的身份、地位、尊严和人格独立的物质象征”(10)张德明:《悬置于“林勃”中的幽灵——解读〈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他一生居住过不少房屋,但大多数时间只是寄居其中,未曾真正摆脱无家可归的状态。奈保尔多次运用黑暗意象衬托他在寄居空间中的不安和惶恐。幼时弄丢邻居的小牛犊后,他躲在家里的大床下,“整个房间一片黑暗……他一个人待着,心中异常恐惧”;住在梵语学者家里时,他患上胃病,被迫只能在夜间如厕,偏僻阴森的厕所让他倍感害怕;哈努曼大宅的厨房也没有一丝光线,“黑暗仿佛坚实的固体一样充斥整个空间”;在狩猎村独自经营店铺时,“封闭、闷热的房间里一片死寂”,他孤独地站在店里,“不敢打破这种沉默,也害怕打开店铺的门,走进阳光下的世界里”。可以说,奈保尔借助这些黑暗场景在“腐朽、沮丧、慌乱或迟滞”的后殖民世界中塑造了一个“外表平庸、内心却充满人性和尊严的英雄人物”,体现了毕司沃斯先生对人生困境的“清醒认知和理解”(11)P.G.Rohlehr,“Predestination,frustration and symbolic darkness in Naipaul’s A House for Mr.Biswas”,Caribbean Quarterly,Vol.48,No.2,2002,pp.87-94.。
黑暗空间加剧了毕司沃斯先生在社会权力空间内所受的疏离和压迫,催生了一种强烈的独立意识,迫使其努力工作,不断寻求建房或购房的机会,以此重现被禁锢的个体价值。他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待每一份工作。当广告牌画工时,为了迎合“店主们浮夸奢华的品位,他在外国杂志上找寻合适的字体和故事”,反复练习绘画技巧;当汽车售票员时,他忍受竞争压力,屡屡冒险把身子探出车外招揽生意;成为扶贫基金调查员后,他每日在粪水四溢的贫民窟奔波,在泥泞和黏液中艰难穿行,尽管时常受到粗暴对待,但他依然恪尽职守,严格筛选出真正需要救济的名单。始终如一的工作态度给毕司沃斯先生带来稳定的收入,这既是他改善家庭关系的契机,也是他实现房屋理想的保障。毕司沃斯先生每次建房或购房都倾其所有,锡金街危房的巨额债务虽然让其健康每况愈下,但他依然乐此不疲。因为房子既是他孤独舔舐伤口的庇护所,又是他反抗压迫、并最终建构自我身份的主阵地。同时,他对房屋的不懈追求和努力奋斗也丰富了死亡的意义,使之不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家族延续的希望,更是其个体独立价值的圆满体现。作为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他不顾健康风险努力工作,将四个孩子抚养成人,并先后将其中两人送至英国留学。正如他苦费心思种植的蝴蝶兰再度盛开一样,他的努力和舐犊之情也带来了回报。小说结尾,女儿留学归来,变得成熟且善解人意,很快找到了薪水丰厚的工作,并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
在健康部门将其遗体火化后,图尔西家族的姐妹们“回到各自家里”,莎玛和孩子们“开着汽车回到空荡荡的房子里”。这里,“房子”和“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凸显了毕司沃斯先生的家庭地位。他不再是家里可有可无的局外人,正是他的存在让房子从物理空间升华为充盈人性的情感空间,而他的消失剥夺了空间的情感价值,使其重新变回毫无意义的、空荡荡的房子。可以说,毕司沃斯先生充满波折的人生是后殖民社会中底层居民的真实写照。在恶劣的社会环境、复杂的家庭矛盾和冷漠的人际关系中,他虽有屈服、不甘、逃避,但始终硬着头皮坚持,并以一种不完美的方式实现筑居欲望并确定文化身份。他以生命为沃土滋润了疏离冷漠的家庭关系,赢回妻子和孩子们的信任与陪伴,房子、家和再度盛开的蝴蝶兰构成了一幅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妙图景,不仅意味着他未竟的事业和人生价值将在女儿身上得以延续,也体现了奈保尔对乱象丛生、饱受殖民摧残的特立尼达社会的同情和信任。尽管作家并未直接以文字谴责“西方殖民强权对殖民地的直接控制”,也没有公开批判“殖民统治咄咄逼人的势态”(12)胡志明:《〈毕司瓦斯先生的房子〉:一个自我反讽的后殖民寓言》,《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但他借毕司沃斯先生充满矛盾的个人价值追寻之旅缓解了后殖民社会中阶级他者和文化他者任人宰割的被动状态,并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对殖民地施加多元操控的西方世界,间接实现对殖民主义霸权话语的质疑和挑战。
二、 虚实交错的身份抗争
1975年,奈保尔以特立尼达黑人运动领袖马利克策划的谋杀案为原型创作的小说《游击队员》是一部饱受争议的作品。巴努乌(Dagmar Barnouw)认为作家过于专注对暴力、混乱和杀戮的描写,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最黑暗、最可怕的世界”(13)D.Barnouw,Naipaul’s Strangers,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3,p.39.。哈斯(Robert Hass)认为这是一部“最恶劣、最具排斥意味”的作品,不仅体现作家的“厌女情绪”和“殖民主体意识”,还反映出对“第三世界革命者和西方白人自由主义者”的强烈厌恶(14)S.Winokur,“The unsparing vision of V.S.Naipaul”,in F.Jussawalla(ed.), Conversation with V.S.Naipaul,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7,pp.114-129.。但奈保尔认为《游击队员》“只是一本描写暗杀的书”,杀戮的愉悦“悬在两次相当可怕性行为之间”,逐渐演变为一种“道德暴力”(15)[英]法·德洪迪:《奈保尔访谈录》,邹海仑译,《世界文学》2002年第1期。。
与毕司沃斯先生相比,马利克毫无主见,只知道听命行事。他没上过学,英国的熟人“认为他是个作家,所以他努力写作”;有些人“觉得他不只是个皮条客和诈骗犯,还能成为黑人领袖,于是他就去读有关领导才能的书籍”(16)V.S.Naipaul,“Michael X and the black power killings in Trinidad:Peace and power”,The Writer and the World:Essays,eBook v3.0,2004,www.vintagebooks.com,par.19.44.。而在小说中,吉米遭遇的身份危机比马利克更加严峻。马利克的父亲是葡萄牙白人,母亲是巴巴多斯黑人,混血身份使他既能博得白人的同情、接受资助创立公社,又能代表黑人发声。吉米虽然也是混血儿,但其父亲是华人,黄种人的样貌和中国姓氏让他变成黑白之间的异类。在伦敦时,尽管他社交广泛,但在白人眼中他只是“急于融入当地华人圈子”的“中国黑鬼”吉米·梁(17)V.S.Naipaul,Guerrillas,eBook v3.1,1990,www.vintagebooks.com,par.17.143.本文对《游击队员》的研究,皆基于此版本展开。;然而,黑人也看不起他,律师梅雷迪斯极尽鄙夷地认为吉米也许“不满足于在灌木丛中默默性侵贫民窟少年”,可能成为“百万富翁或是下一任总理”,但他终究只是“根本无法实现黑人政治抱负”的华人混血。
在婚姻方面,奈保尔虽对吉米妻子的种族和阶层语焉不详,却颇费笔墨塑造了英国白人妇女马乔里。在给马乔里的绝笔信中,吉米写道,“是你发掘了我的男性气质……以前我只是一个孩子,在你把我变成男人后我却无法忍受再把自己当成杂货店后屋里的那个孩子”。“杂货店后屋的孩子”隐喻吉米初抵英国时的混血身份,“被发掘的男性气概”则点明马乔里对吉米的控制和征服。马乔里的存在无疑恶化了吉米的身份困境,使其始终处于被支配、被利用的不平等关系中。当他顺从地扮演白人玩物、遵从一切指令时,他能获得白人支持,摇身一变成为英国黑人权力运动的大人物;当他心生不满、试图做回自己时,便失去了利用价值,遭到抛弃。赫曼威(Robert Hemenway)指出,奈保尔刻意回避史实中马利克的黑人妻子,因为黑人妻子既不符合“吉米的人物刻画”,也无法满足作家“以性契约反映政治挫折”的需求(18)R.Hemenway,“Sex and politics in Naipaul”,Studies in the Novel,Vol.14,No.2,1982,pp.189-202.。而马乔里不仅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也是作家剥夺吉米言说权力、彰显作者主体权威的媒介。但吉米既不想接受作家的人物定位,也不愿长期作为白人的附庸和奴隶,将文学创作当作他对抗霸权话语、消解身份错位的重要工具。
吉米笔下的叙事者是名为克拉丽莎的白人女性。作为英国统治阶级的一员,她以种族优越感十足的文字表达了对吉米的无边仰慕。“他的皮肤一点也不黑,呈现出让人愉悦的金色,像是一尊铜铸的神像,我很惊讶,心都跳到了嗓子眼……他的礼节堪称完美,他教会那些蠢笨的黑鬼表达尊敬、遵守纪律的方式,让我感到震惊”。非黑非白的浅金色皮肤蕴含吉米对父系与母系种族身份的共同拒斥,铜铸的神灵则象征创造力和强大的个体能动性,彰显了他对个人理想和自由身份的向往。尽管吉米的创作语言混乱不堪,叙事人物也呈现出明显的不可靠性,但他依然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将克拉丽莎描述为一个甘愿堕落、自轻自贱的女性,并借克拉丽莎之口以“黑人救世主”自居,“英国人只把他当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华人混血儿……但我看见他的高贵血统,只有我们这个阶层的人才能看出,他是一个来帮助贫苦黑人的王子”。换言之,吉米将克拉丽莎他者化,并假借其崇拜情绪为自身塑造了与权力主体相似的理想形象。
除文学创作外,吉米还以其他形式的语言表达了建构独立身份的决心。在他看来,文字是具有魔法的武器,虽然会让他“比孩提时更加迷失”,但也“带来无限可能”。公社门口指示牌的落款是“詹姆斯·艾哈迈德(哈吉)”。哈吉(Haji)本意为赴麦加朝圣过的穆斯林,吉米将之理解为“阁下”,以此彰显身份的独特与荣耀。他在宿舍墙上的自画像上写道,“我不是任何人的奴隶或种马,我是一个勇士和火炬传递者”。奴隶和种马不仅是吉米在英国出卖肉体和尊严时扮演的角色,也是白人统治阶级为黑人塑造的天生低贱的刻板形象。因此,吉米的宣言既体现了抛弃不堪过往的决心,也表达了他对白人灌输给黑人的自卑观念的强烈抗议。
吉米对简实施的性暴力和谋杀一直是引发学界对奈保尔厌女情绪口诛笔伐的导火索。巴拉特(Harold Barratt)认为吉米在谋杀前对简的性侵是对“自由主义中产阶级白人女性最彻底的降格”(19)H.Barratt,“In defence of Naipaul’s Guerrillas:A reply”,Caribbean Quarterly,Vol.29,No.2,1983,pp.63-71.。休斯(Peter Hughes)认为种族和性的双重厌女暴力使简的“身体、衣着和姿态从诱惑的欲望沦为污秽的污染之源”(20)P.Hughes,V.S.Naipaul,New York:Routledge,2014,p.82.。戛贾拉瓦拉(Toral Jatin Gajarawala)谴责奈保尔对白人女性极端“无情、残忍、厌恶和诅咒”的心态,认为他精心设计了一场“针对简的文学性谋杀”,迫使她在遭遇“和原型人物盖尔·本森同样的谋杀之外还受到强奸”(21)T.J.Gajarawala,“Fictional murder and other descriptive deaths:V.S.Naipaul’s Guerillas and the problem of postcolonial description”,Journal of Narrative Theory,Vol.42,No.3,2012,pp.289-308.。维斯则将简视为整个西印度社会的化身,她的悲惨遭遇与死亡皆预示前殖民地社会终将面临“后殖民的绝境”(22)Weiss, On the Margins:The Art of Exile in V.S.Naipaul,p.182.。诚然,吉米对简实施的性侵和杀戮无疑是暴力行径,但简的白人女性身份并不意味着吉米仇视的对象是女性群体。相反,简被谋杀的原因既非其女性身份,也非“承受了被殖民者仇恨的替罪羊”,而是被赋予了强大的男性气质(23)H.Wirth-Nesher,“The curse of marginality:Colonialism in Naipaul’s Guerrillas”,Modern Fiction Studies,Vol.30,No.3,1984,pp.531-545.。简自视甚高,聚会时总会歇斯底里地打断别人,“所谓的伦敦礼仪使她很喜欢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他人”。两性关系中,她像男性般强势,通过粗暴亲吻和发号施令。在画眉山庄里,吉米刚把手放在她肩上,她便张开大嘴索吻,试图用“暴力来展现她所知道的一切”。随后,她旁若无人地脱掉衣服,并主导了性行为的发生,吉米只能“笨拙地躺在她身上,被她夸张的接吻吞噬”。因此,虽然简的形象在某些时候和马乔里重合,但与其性别相比,其阶级和种族身份才是吉米真正仇视的对象。对吉米而言,他谋杀的并非作为女性的简,而是白人男性与白人资产阶级统治的双重化身。
可以说,《游击队员》是奈保尔矛盾创作内涵的集中体现。一方面,他借男性角色之口对白人女性极尽挖苦与蔑视,说明作家对女性自我认同的忽视与扭曲;但另一方面,错置的性别角色也体现了作家对男权社会和男性中心主义的质疑和批判。吉米的角色塑造也深受影响。他对女性群体施加的多重暴力——留学时的性侵案底、对强奸场景的反复回溯、自创小说中的性幻想,以及最终对简的侵犯与谋杀——彻底将其妖魔化,与西方为东方创造的愚昧、野蛮的刻板形象不谋而合。但在面对殖民压迫和身份困境时,他没有和原型人物马利克一样沉溺于用“借来的话语塑造自我”(24)V.S.Naipaul,“Michael X and the black power killings in Trinidad:Peace and power”,par.19.44.,而是以性暴力和谋杀向西方话语对殖民地的过度干涉发出挑战,并借由幻想式的文学创作短暂成为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挣脱了奈保尔对虚拟人物施加的多重文本限制。
三、 刻板女性的多重面孔
相较于研究奈保尔作品中男性人物时的百家争鸣,在探讨作家笔下女性角色时,学者们总会不约而同地指责人物的刻板化与相似性。表面而言,作家对女性的刻画和塑造的确枯燥单一,以一种“毫无必要的方式”呈现了对女性“极为刻薄、严厉的说教和审判”,试图借此“唤醒男性远古记忆中对女性的恐惧和憎恶”(25)H.Pyne-Timothy,“Women and sexuality in the later Novels of V.S.Naipaul.” World Literature Written in English,Vol.25,No.2,1985,pp.298-306.。实际上,奈保尔对女性群体的书写也具有多样性,尽管这些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长期承受男权话语的异化和压迫,但作家在建构性别他者时为部分女性保留了多重面孔和丰富情绪,重新赋予她们言说自我和挑战男权叙事的权力。
在奈保尔笔下,有色人种女性大多是屈从于男权社会压迫、不敢言说自我的沉默他者,她们不具备独立性和能动性,以“谦卑的姿态为核心家庭中的男性成员们服务”,这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女性的个体存在价值(26)D.C.Dance,“Matriarchs,Doves,and Nymphos:Prevalent Images of Black,Indian,and White Women in Caribbean Literature”,Studies i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Vol.26,No.2,1993,pp.21-31.。迦涅什的妻子丽拉和毕司沃斯先生的妻子莎玛是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莎玛则顺从而机械地扮演社会分配给印裔女性的模式化角色。婚前,她是家族用以吸引高种姓落魄男子入赘的工具,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母亲和叔叔许配给了上门画广告的毕司沃斯先生;婚后,她不仅默默忍受丈夫的指责和抱怨,还在他为实现个体价值和人生理想而远离家庭时,努力成为一个尽职尽责的母亲。她的人生可以说是图尔西家族辉煌历史和丈夫跌宕起伏经历中毫不起眼的注脚,而她自己的“欲望、恐惧、痛苦或生存动力”却从未受到“毕司沃斯先生和奈保尔的关注”(27)R.Espinet,“The Invisible Woman in West Indian Fiction”,World Literature Written in English,Vol.29,No.2,1989,pp.116- 126.。
与丽拉和莎玛相比,威严强势的图尔西夫人是奈保尔笔下的异类,其治下阶级森严的哈努曼大宅既是毕司沃斯先生实现个体价值、追寻独立身份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也往往被视为掩饰印度传统文化沉疴宿疾的保护伞。南丹(Kavita Nandan)在评论中将图尔西家族比作殖民主义,认为其不仅是英国殖民者的“追随者和模仿者”,更是殖民意识的实践者,通过“复制令人乏味的旧制度和殖民政体”在家族内部“对毕司沃斯先生进行殖民压迫”(28)K.Nandan,“V.S.Naipaul:A Diasporic Vision”,Journal of Caribbean Literatures,Vol.5,No.2,2008,pp.75-88.。作为母系家族女族长,图尔西夫人的强势作派实属无奈。图尔西先生因车祸去世后,传统教条剥夺了她改嫁的权力,加之子女偏多且均未成人,她只能接受种姓制度置于己身的枷锁,全力照看庞大的家族产业。但是,她并未盲目遵循种姓婚姻的嫁娶制度,反而要求婆罗门男性上门入赘。通过“娶丈夫”,图尔西夫人对男权社会和旧制度沉疴的发起挑战,“他们受外人尊敬仅仅因为和图尔西家族的关联,人们遗忘了他们的名字,他们成为图尔西家族的一部分”。同时,她鼓励家族女性参与家族生意,这种方式虽不能彻底改变女性被压迫、被禁锢的处境,但稳定的收入依然提升了女性的家庭地位,动摇了她们作为丈夫附庸的寄生者身份。
作为家族的主心骨,图尔西夫人是具有“生产性”的能动者,她通过具体计划“肯定她的主体地位”,并主动尝试“认识与她所追求的目标、所拥有金钱和权利相关的责任”(29)[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771—772页。。在家族状况稳定时,她珍视传统文化精髓,恪守印度教的各种信仰仪式,使子女免受外部世界侵扰;在家族遇到危机时,她果断决策,弃置居住多年的大宅,举家搬迁至矮山重起炉灶。尽管是家族权威,图尔西夫人却十分重视礼数,很少干预已婚子女的家庭生活,也几乎从不对入赘的女婿们恶言相向,就算看到儿子在宗教信仰上被毕司沃斯先生出言侮辱,也没有反唇相讥,只是策略性地假装晕倒,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同时,图尔西夫人与加勒比传统文学中专断、铁腕治家、欲望强烈的女家长截然不同,她性情温和、平静,尽管晚年因健康问题不时责骂女儿们,但却“小心翼翼地从不针对女婿们”,也从不把矛盾转移到在房子里学习的孙辈们身上。可见,不同于多数殖民地妇女逆来顺受的心态,图尔西夫人主动寻求改变,并扬弃传统文化,在饱受西方文化侵蚀的殖民地社会中努力保持自己的尊严和家族的完整。
在加勒比的英语文学中,白人女性遭遇了最为刻板的塑造,几乎每个人都被打上饥渴、放荡的标签,奈保尔也不能免俗。他总是刻意将白人女性置于殖民地男性和西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激烈交锋中,使之沦为“有色人种渴望、诱惑、并最终侵犯”的牺牲品(30)D.C.Dance,“Matriarchs,Doves,and Nymphos:Prevalent Images of Black,Indian,and White Women in Caribbean Literature”.。但《米格尔街》中的海瑞拉夫人(Mrs.Hereira)是个例外。起初,她并不被大街上的居民接纳,正如叙事者“我”所说,“在新住客搬进来之前我们就已经讨厌他们了”(31)V.S.Naipaul,Miguel Street,New York:Vintage Books,2002,p.131.本文对《米格尔街》的研究,皆基于此版本展开。。从外表上看,她并不像简那样以诱惑男性为目的刻意打扮,“她穿着非常考究,看起来格外美丽、优雅,以至于当她和街上的其他女人一起挤在玛丽的商店门口争抢面粉和大米时,你会觉得非常滑稽”。实际上,她和作家笔下其他白人女性一样,是婚姻中的背叛者。她的丈夫是名心地善良的医生,像父亲般地关心、保护她,但她却因无法忍受丈夫身上“干净的味道”选择和男病人托尼私奔。托尼是有色人种,样貌丑陋、性格粗暴、终日酗酒,还经常不分青红皂白殴打海瑞拉夫人。她一边和邻居们哭诉托尼的暴力虐待,一边却又在邻居们的一致谴责中为他辩护,将他的疯狂行径归咎于战争对其身体的摧残,甚至认为是自己“做错了事情而冒犯到他”。这里,海瑞拉夫人对待丈夫与托尼时的态度反差强烈,使她和低贱放荡的白人女性刻板形象牢牢地捆绑在一起,高贵、典雅的外表似乎只是掩盖其虚伪、不忠的伪装。她“离开几乎完美的丈夫转而追随热衷暴力的情人”不仅意味着“从富裕、安稳的白人世界中堕落”,还是一种“背离正轨的自毁之举”(32)B.King,V.S.Naipaul,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p.31.。
尽管如此,奈保尔在塑造海瑞拉时留下伏笔,暗示了她独立自主意识的存在。短篇故事的标题《爱,爱,爱,孤独》(Love,Love,Love,Alone)取自叙事者之母劝导海瑞拉离开情人的句子——“爱,爱,爱,孤独正是致使爱德华国王离开王位的原因。”原文中的“alone”一语双关,既有孤独之意,意指海瑞拉夫人无依无靠、遭遇三重拒斥的边缘身份——在婚姻中背叛丈夫被白人中产阶级社群排挤,来到米格尔街后因肤色被当地居民孤立,在家里被情人暴力殴打并逐出家门;也有独立之意,预示她终将做出选择,勇敢逃离情人的束缚。此外,海瑞拉夫人的称谓也别有深意。小说中的大多数女性角色没有姓氏,要么随夫姓,要么被称为“某某的妻子”,或直接被冠以名字。在《乔治和他的粉色房子》(GeorgeandthePinkHouse)中,叙事者写道:“乔治把屋里屋外的一切家务全部扔给妻子做……她从来不是一个体面人,只是乔治的妻子而已,几乎总住在牛棚里。”在男权观念中,男性有权将“配偶的个人身份纳入自己或家庭的身份范畴中”,而女性婚后改随夫姓被认为是“女性建立家族身份的职责所在”,因为这意味着“和丈夫建立从属性质的连接”或是“成为丈夫的一部分”(33)L.Hamilton,C.Geist &B.Powell,“Marital name changes as a window into gender attitudes”,Gender and Society,Vol.25,No.2,2011,pp.145-175.。在某种程度上,随夫姓使已婚妇女丧失了个体身份和价值,只能受制于在家庭和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反观海瑞拉夫人,她既不随夫姓“克里斯蒂安尼”,也不像劳拉一样只有名字,“海瑞拉”要么是其婚前姓氏,要么是化名,但无论哪种情况,她都保留了属于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尽管她最终回到丈夫身边,回归白人中产阶级的稳定富裕生活,但这恰恰是其主体意识和能动性的体现,是其有意追寻的最符合自身利益、实现个人价值的生活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作家在整部作品中给已婚妇女施加的无力和软弱,使她们看到消解男权压迫和殖民霸权的希望。
四、 结 语
在奈保尔笔下的后殖民社会中,精英阶层牢牢占据顶层资源,被殖民者被迫保持被统治、被压迫的属下身份。同时,女性群体在殖民地社会中呈现出浓重的悲剧色彩,西方中心话语成为男性霸权的帮凶,进一步剥夺了女性本就弱化的能动性。然而在二元对立的社会语境中,毕司沃斯先生终其一生寻求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不仅展现出被禁锢者的能动性和个体价值,也暗示了奈保尔对隐匿在社会问题之后的殖民主义的批判。混血儿吉米以幻想式的文学创作和对异性的侮辱与谋杀作为对抗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的方式,这种充满私欲的暴力虽然极端,却间接实现了对他者身份的双重消解。在独立后的特立尼达,图尔西夫人既没有既屈从于男权社会对女性家庭角色分工的刻板限制,她以“娶丈夫”的婚姻形式挑战了殖民地男尊女卑社会偏见,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女性始终作为男性附属品的悲剧命运。在刻画海瑞拉夫人时,奈保尔改变了塑造此类角色时常有的厌恶态度,在角色称谓和故事标题中埋下伏笔,隐喻了这一特殊人物的独立自主意识。诚然,在奈保尔笔下的众多女性角色中,上述两者略显人轻言微、分量不足,但这恰恰说明作家在遵循男性话语、强调性别差异时依然潜藏了对性别弱势群体的关怀,表现出其夹杂在厌女意识中的矛盾情感和复杂的创作动机。可以说,虽然奈保尔没有直接给出解决后殖民时代第三世界社会难题的答案,却提供了一种审视问题的新视角,使每个读者能从作品中感受作家试图动摇并解构主体、他者二元对立的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