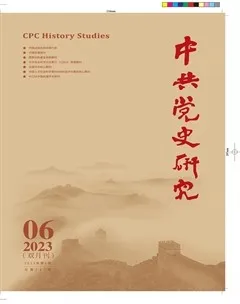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五年关中地区中共革命的兴起
2024-01-25冯峰
冯 峰
一般研究都认为,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力量是其领导中国革命获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对于“组织”内涵的理解以及组织能力的评价,还有不同意见。一种看法认为,中共是建立在不同的地方特殊性之上的基层组织的“集合体”,基层党组织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较强的自主性,地方革命者在革命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关于海外中共研究的“地方化”转向,参见Saich,T.(1994).“Introduction: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Anti-Japanese War Base Areas”.The China Quarterly,140,pp.1000-1006;周锡瑞:《关于中国革命的十个议题》,董玥主编:《走出区域研究:西方中国近代史论集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81—213页;陈耀煌:《从中央到地方:三十年来西方中共农村革命史研究述评》,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8期(2010年6月)。。另一种看法认为,在中共早期组织架构中,知识分子“社团”气味颇浓、“多元化”特征明显,经过大革命洗礼后,建立在列宁主义组织原则之上的现代革命政党才真正形成(2)参见Hans J.van de Ven (1991).From Friend to Comrade: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0-192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这提醒我们,讨论中共早期组织发展史时,要重视“地方性”和“多元化”的面向。
本文讨论陕西关中地区中共革命的兴起,即组织发展由多元化走向一元化的过程。由于关中早期革命运动主要表现为青年团领导的青年活动,本文重点考察围绕青年团的各种力量如何运作,以及地域文化所起的作用。(3)相关研究参见《陕西省志·共青团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39页;《陕西省志·中国共产党志》(上),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47—295页;《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42页;陈耀煌:《陕西地区的共产革命(1924—1933)——一个组织史的考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3期(2016年9月);〔美〕周锡瑞著,石岩译:《意外的圣地:陕甘革命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71—120页。陕西党、团组织起源于关中地区渭河南北两岸以及陕北的绥德地区,形成了渭北(三原)、西安、渭南、绥德四个革命策源地。除了陕北绥德地区以外(4)陕北地域文化与关中文化有着显著区别,这使陕北党组织的发展呈现出相当不同的特色。对此,需要另文论述。,其他三个策源地集中于渭河两岸的“政治—经济—文化圈”。这里是关中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以渭河为界形成事实上的南北军事割据,使得中心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功能出现分化。这种地域社会结构造就了渭河两岸革命运动兴起过程的“多元中心”特点,塑造了早期陕西革命组织的“多元化”发展模式。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渭河两岸革命力量逐渐走向合流,从而为建立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革命政党创造了条件。渭河南北地域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早期关中革命的基本图景。
一、渭河南北地域社会的基本格局
民初,关中地区以渭河为界形成了经济、文化功能分化的基本格局。渭河以南的中心城市西安的一部分经济、文化功能,被渭北中心城市三原、泾阳甚至渭河以南的渭南所分割。在传统经济贸易中,河道是地区贸易往来的重要途径。陇海铁路通到西安之前,省内主要贸易路线正好绕过了省府西安。从东部开来的商船停靠的最后一站是渭南的赤水镇,货物在这里卸载后,再通过陆路运到西安,因此,赤水成为渭河上的繁荣转运口岸(5)《华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20页。。陕西最早的青年团组织诞生于此,绝非偶然。而渭北中心城市三原通过四通八达的交通线,辐射邻近数十县,将渭北联结为一个整体。1923年,西安至三原、三原至同官(今铜川)的公路相继通车,进一步促进了渭北经济的现代化。陇海铁路通到西安之前,三原也是渭北重要的贸易集散中心,这里将甘肃岷县一带的药材转运东南各省,又将东南的布匹货物输送到西北。来自内蒙古、宁夏、新疆的商帮带来了皮货、马匹,在这里交换京广杂货,从而使得渭北成为联结京、津、沪、汉、甘、晋等地的贸易枢纽。(6)《三原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73、437页;《三原文史资料》第7辑,1990年印行,第140页。由于泾惠渠的开通,20世纪20年代后期,渭北泾阳、三原一带广种棉花,并与国际市场联系起来。虽然西安通往潼关的公路是省城与东部地区经济联系的重要枢纽,但从民初到20年代,它被大大小小不同的军阀所控制,境内关卡林立,道路缺乏修缮,以致商旅艰难,严重影响着省府对外贸易的发展。
民初西安地位的下降,明显地体现在人口规模和城市管理上。清末西安市区人口只有不到11.2万人,受军阀混战,尤其是1926年的“西安围城”影响,20年代的人口规模仍维持着较低水平,可能还有所下降。而1928年泾阳人口接近15万人,1924年渭南则有20.6万余人。与渭北中心城市以及渭河以南其他城市相比,西安都不占优势。由于人口规模的限制,西安长期缺乏统一的市政管理机构。民初延续清制,市区以城市中心为界,东部归长安县,西部归咸宁县管理。直到1927年西安才首次成立市政委员会,但由于人口不足20万,不够设市标准,很快废止。1932年,西京筹备委员会成立,但城市现代化建设很快又被搁置,直到1942年,才正式成立西安市政处。(7)《西安市志》第1卷,西安出版社,1996年,第445、241—242页。市政管理体系建立的曲折过程充分显示了西安城市现代化的迟滞。
工业化进程在相对闭塞的古都亦进展缓慢。清末民初,由于政治腐败、战乱频繁,西安的民族工业一直未能兴起。一战爆发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在西安,除几家为军阀混战服务的军械修造、铁器铸造厂外,民间经营的只是些手工纺织和生活用品作坊等,近代工业尚处于萌芽状态。(8)《西安文史资料》第19辑,西安出版社,1993年,第2页。迟至20世纪30年代,西安才真正进入现代化轨道。尤其是国民党政府推行“开发西北”战略、陇海铁路通到西安之后,西安的工业发展迎来崭新局面。但是,在本文叙述的1922年至1925年,西安工业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这从中共陕西地方组织准备大力发展工人党员时遇到的问题中可见一斑。在中共西安地委的计划中,最大的发展对象竟是官办军事企业陕西机器制造局(9)参见《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1992年印行,第18页。。该局肇始于清末左宗棠镇压回民起义而设立的西安机器局,1923年督军刘镇华购置机床,扩充了生产(10)《西安文史资料》第19辑,第11—12页。。而其他工人党员发展对象则集中于电力、邮务、印刷三个行业,可见当时西安工业布局之简陋。
在省会经济衰退、现代工业艰难起步阶段,20世纪20年代,渭北的经济发展迎来契机,即大型水利工程泾惠渠的开通。留学德国学习铁路和水利的工程师李仪祉,继承省水利局局长郭希仁遗愿,于1923年至1924年制定了两套“引泾灌渭”的水利方案。但是由于省内军事动荡和缺乏经费,直到杨虎城主政、华洋义赈会注入资金后,才于1932年6月完成了泾惠渠一期工程。(11)参见《法国汉学》第9辑,中华书局,2004年,第268—328页。该工程经过不断修整,为渭北经济发展注入了动力。其主要受益者是渭北中心城市泾阳、三原。据1936年统计,该渠可灌溉面积59.6万亩,其中泾阳境内25万亩;1941年渠系完善后,总面积增加到67.2万亩,泾阳境内26.4万亩,约占整个灌溉面积的40%。三原境内亦分布一、二、三、四支渠,长32.5公里,灌溉面积15.6万亩。自泾惠渠开通,三原引进的“斯字棉”创造了亩产150斤的世界纪录,小麦平均亩产也达438斤。(12)《泾阳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0页;《三原县志》,第293页。
除了经济上的繁荣,军事割据也加强了渭北相对于省城的独立地位。1918年至1922年,陕西靖国军占领了以三原为中心的渭北地区,成为事实上的割据政权。陕西靖国军兴起于护法运动之中,以反对陕西督军陈树藩为旗号,成员大多是籍贯在渭北的军官。其成立时的六路司令分别是:郭坚(陕西蒲城人),驻扎凤翔、千阳、陇县;樊钟秀(河南宝丰人),驻扎周至、户县;曹世英(陕西白水人),驻扎高陵、雨金、交口、栎阳;胡景翼(陕西富平人),驻扎三原、富平、泾阳;高峻(陕西白水人),驻扎韩城、合阳、蒲城、白水;卢占魁(察哈尔人),驻扎大程、雨金,后移驻耀县(13)李秀谭、朱凯:《于右任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2—93页。。除了樊钟秀、卢占魁,其余四人均为渭北人士,而受孙中山指派从上海回渭北就任总司令的于右任也是三原本地人。因此,靖国军代表了渭北本土军事精英对外来省级军阀的“反动”。即使1919年4月与陈树藩停战议和后,靖国军仍控制着三原、泾阳、高陵、富平、白水、蒲城、澄城、同官等渭河以北主要地区,维系着事实上对省城的“独立”(14)郭琦等主编:《陕西通史》第8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8页。。1922年,靖国军结束了在渭北的活动,但由此形成的“渭北割据”形势却并未结束。1925年陕西督军刘镇华下台,陕南军阀吴新田进驻西安取而代之,但省内要道潼关到西安的东半部由靖国军出身的胡景翼(驻扎开封)从河南遥控,而在渭北,拥有两万人马的田玉洁乘机将势力从三原发展到了渭河边上的渭南地区(15)《法国汉学》第9辑,第296—297页。。
总的来看,20世纪20年代,由于城市现代化的停滞,省城西安的部分经济功能被渭北的三原、泾阳甚至渭河以南的渭南所分割,尤其是靖国军割据造成的渭河南北军事对峙,使西安的政治中心地位遭受挑战,于是造成了关中地区高度“分化”的地域社会格局。正是这种高度分化的格局决定了以渭河为界多点起源、分途并进的早期陕西青年团组织发展模式。
二、渭河两岸革命思想的传播模式
仅有地域社会基础,并不必然造成革命运动的兴起,革命思想的传播是另一个必要条件。以返乡知识分子的活动为中心,借助学校、报刊、社团而形成的关系网络,是渭河两岸革命思潮传播的主要模式。传播媒介方面,有如下三种:
其一,现代出版业的初步发展。五四运动是一场现代城市阶层的政治运动。现代出版传媒事业的发展,将运动的消息传遍全国。西安的现代出版业虽然不如北京、上海发达,但在五四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报纸和期刊,与全国中心保持着紧密的信息沟通,传播着新思潮。这些出版物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各界人士兴办的报纸。如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第十天,《长安日报》首次刊登了相关消息;1920年7月,田芝芳、张仞鸣创办《鼓昕日报》,最早在陕西介绍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界人士何镜清、黄宪之的《新社会日报》也以“提倡新文化”为宗旨;流风所及,就连军人杨虎城也兴办《青天白日报》,为国共北伐鼓与呼。二是进步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以学校为基地兴办的刊物。如1919年9月,屈武、刘道洁等人创办《全陕学生联合会会刊》,社址在省立第一中学;魏野畴在一中任教时,先后兴办《青年文学》《青年生活》,鼓吹革命思想;武起(又名武思茂)、雷晋笙、崔孟博(又名崔物齐)、康少韩等创办《西北晨钟》《西北青年》,张秉仁(笔名每雨)、张秉辉、张金印等创办《陕西青年》,几本杂志先后成为青年团的机关刊物。(16)参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在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70—275、320—325页。
其二,中等学校学生的激进化。民初,西安高等教育虽然相对落后,中等教育却初具规模,并且成为激进思想传播的温床。五四时期国内省内的政治事件,往往引发多校参与的学生运动。如五四运动爆发后,西安各主要中学成立陕西学生联合会,兴办会刊,学联的办公地点在一中;1920年,西安教育界掀起“索薪罢教”风潮;1921年12月,西安学生要求督军刘镇华致电中央,拒绝在“九国公约”上签字;1923年,为收回旅顺、大连,掀起抵制日货运动;1925年五卅惨案引起的反帝浪潮以及非基督教运动中,都有西安中学生的身影(17)《陕西省志·教育志》上册,三秦出版社,2009年,“概述”第20页。。成德中学、渭北中学堪称渭河两岸中学激进化的代表。成德中学是陕西督军陈树藩出资兴办的私立学校,但显然并没有与陈树藩当局保持一致。屈武、武止戈、耿炳光等激进学生皆出自该校。在五四运动以及教育界“索取欠薪”风潮中,成德中学都走在学生运动的前列。(18)参见《西安文史资料》第2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2—66页。于右任主持的渭北中学聘请了若干北大、北师大,以及武汉、上海、天津等地的大学毕业生及留日学生。在渭北中学,学生们可以接触到众多五四时期的出版物,包括《科学与人生观》《天演论》《独秀文存》《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不平等条约》《新青年》《向导》《政治生活》《晨报》《民国日报》等,极大地促进了革命思想的传播。(19)参见《陕西文史资料》第12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0—101页。
其三,政治社团跨区域的影响。陕西的政治社团是带有鲜明地域性的组织,由此形成强烈的同乡观念,有利于在地域认同基础上形成现代革命团体。1922年成立的共进会就是依托于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的革命组织。成立初期,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以反对陈树藩治陕以及陕西教育当局“尊孔复古”的主张为宗旨。其核心成员李子洲、刘天章、杨钟健、魏野畴、屈武、杨明轩、梁鼎等,主要是来自北大、北师大等北京高校的陕籍学生。不过,随着共进会的成立与发展,其成员已不局限于陕籍,而是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南通、开封均有成员。共进会逐步从地方性社团上升为全国性组织。共进会兴办的《共进》杂志突破了仅关注陕西政局的地方眼界,将新文化运动等全国性事件纳入视野。(20)参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共进社和〈共进〉杂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8、461—467页。以共进会为纽带结成的关系网,对于早期陕西革命组织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共进社会员返乡后,在西安、三原、渭南、华县、榆林、绥德、延安、南郑等地建立共进会分社,出版刊物,发展会员。早期陕西的革命者为了发展党、团组织,往往以共进会为掩护开展活动,如李子洲、王懋廷在绥德师范时,就在共进会活动场所召开党、团会议。(21)《陕西文史资料》第9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3页;中共榆林地委组织部组织史办公室编:《中共陕北建党时间问题讨论集》,1999年印行,第72—73页。所谓“大共(共产党)小共(共进会),都是一共”,外界常将共进会与共产党混为一谈,并非没有道理。
上述三种传播媒介往往是孤立的,想要将它们联系起来形成关系网络,还需要返乡知识分子群体的积极活动。这个群体中的成员大都从北京、上海等地的知名大学毕业,又与家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是家乡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中介,强烈的地域认同使他们感情上与家乡休戚与共,在外求学的所见所闻又使他们急切希望改变家乡封闭落后的面貌,于是尝试利用一切现代手段——报刊、学校、社团——将革命思想传播到故乡,把故乡带入现代民族国家的“乐园”。
魏野畴、李子洲的革命经历颇能反映返乡知识分子的特点。魏野畴,陕西兴平人,三秦公学(后来的省立第三中学)毕业,1917年入北京高师(后来的北师大)史地部;李子洲,陕西绥德人,三秦公学毕业,1919年考入北大哲学系。1920年,二人与北大陕籍学生杨钟健、刘天章(三秦公学同学)等建立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后组织共进社,兴办《共进》杂志,其中李子洲被誉为“共进社大脑”。1921年夏从北师大毕业后,魏野畴回陕任教,在华县咸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历史教员,抨击历史教科书“实在可烧”,采用自编教材,改革教学方法。1922年重返北京,潜心修改书稿,1923年加入中共。李子洲亦于1923年由李大钊、刘天章介绍入党,当年夏天毕业后,受北大同学、共进社会员郝梦九(时任渭北中学校长)之邀,赴三原渭北中学执教,大开渭北新风气。同年夏,魏野畴应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之邀,复回陕任教,讲授《共产党宣言》《社会进化史》《社会科学概论》《资本论》,介绍《新青年》《向导》《共进》等。魏野畴离开后,杜斌丞又邀请李子洲到榆林中学任教,该校一时成为陕北革命思潮的大本营。未几,李子洲被任命为绥德四师校长,大胆改革师范教育,与王懋廷、田伯英、杨明轩等人创立陕北最早的党、团组织,使绥德四师成为“陕西的上海大学”。1924年至1926年,魏野畴赴西安,在省立一中、成德中学任历史教员,先后创办《青年文学》《青年生活》《西安评论》等刊物,集合西安主要中学学生,成立西安青年团第二支部。(22)参见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编:《魏野畴(传略·回忆·遗文)》,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页;陕西省革命烈士事迹编纂委员会编:《李子洲(传记·回忆·遗文)》,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38页。魏野畴、李子洲的经历符合返乡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他们都出于三秦公学,都在北京读书,都参加了共进社,都是中共党员,都通过师友相互引荐、返乡执教,都积极促成革命思潮在渭河两岸(三原、华县、西安)及陕北(榆林、绥德)的多点传播。显然,以地缘、师友、共同的信仰(马列主义)为基础而结成的关系网络,为返乡知识分子传播革命思想提供了便利条件。关中地区的青年团组织既因这些关系网络而蓬勃发展,又受制于此而使得一种组织化、纪律化的革命政党迟迟无法形成。
以返乡知识分子的活动为中心,借助学校、报刊、社团而形成的关系网络,革命思想在渭河两岸得以广泛传播。而渭河两岸的“政治—经济—文化圈”进一步为革命思想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从而促成了早期革命组织——青年团的组建。
三、渭河两岸青年团的多元起源
渭河两岸马列主义思想的逐步传播,为组建中共早期革命组织创造了条件。陕西的青年团正是兴起于渭南(赤水)、西安、三原等渭河两岸的中心城市。
陕西最早的青年团组织出现于渭南的赤水镇,创立者是王尚德。王尚德是渭南人,由西安法政学堂考入武昌中华大学。武汉青年团的骨干成员恽代英、林育南等都与王尚德过从甚密。1920年2月,恽代英、林育南等创办利群书社。1921年7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共存社,宗旨是“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的目的”。(23)李艳主编:《共青团史人物传》第1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第80页。王尚德积极参加利群书社和共存社的活动,不仅担任共存社营业委员,负责利群毛巾厂的工作,而且与林育南在武昌第一纱厂开办工人夜校,组织了声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和汉口租界人力车夫罢工的活动(24)《渭南文史资料》第5辑,1993年印行,第9—10页。。
1922年7月,王尚德加入青年团,同年8月从中华大学毕业,返回家乡渭南赤水镇,以兴办教育为名,发展团组织。他与张浩如、田涵荣、薛英伯等人筹措资金,一起兴办了赤水职业学校。(25)《渭南文史资料》第5辑,第11页。学校共开设三个班,招收15岁至19岁的青年,虽然也教学生一些纺织职业技能,但是主要以宣传革命思想为目的。如王尚德的“国文”课,讲《共产党宣言》、李大钊著《今》、恽代英著《秀才造反论》、恽代英译《阶级斗争》等。该校还通过办墙报、读书会、讲演会等形式,使革命思想深入人心。学生们可以接触到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中国青年》,以及《新青年》《共进》。学生刘映胜、武维化、张宗逊等人还在《向导》《中国青年》《西安评论》上发表过文章。(26)参见《西安文史资料》第2辑,1982年印行,第3—5页;《渭南文史资料》第5辑,第12—13页。
不过,最初赤水青年团组织的发展并不顺利。截至1924年5月,近两年的时间里,王尚德利用赤水职校只发展了三个团员,即他本人、张浩如和刘建侯(由临潼三育学校转来)。虽然团中央按时将机关刊物寄送赤水,但是王尚德两年没有向团中央递交过一份报告。对于团的工作陷入停顿,王尚德的解释是陕西革命基础薄弱,团员人数少,没有条件组织基层团支部。这可能是实情,但不可否认的是,团组织发展的停顿还与学生流动性大有着直接关系。学生毕业后即升学或工作,也就脱离了地方团组织。一个显例就是王尚德直接参与组织的华县咸林中学青年励志团,学校20%的学生加入了该组织,但在升学之后大多离开华县,而在北京等地加入当地青年团。(27)参见《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991年印行,第1—4页。
咸林中学青年团组织发展的条件比赤水要好。相比赤水职校,咸林中学与全国思想中心的联系更为紧密。其创立者杨松轩师从“关学殿军”刘古愚,清末即开始兴办“新学”。1919年4月,杨松轩在原临潼、雨金小学堂基础上创办私立咸林中学,交游省内政要,为学校争取到优质办学资源。(28)《陕西省志·人物志》中册,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15—516页。他通过自己在北大上学的儿子杨钟健(共进会核心成员),聘请北京各大学的学生到咸林中学。魏野畴、王复生、王懋廷等先后执教鞭。其中王复生为北大学生,加入了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最早的党员之一。1922年春至1923年夏,在咸林中学任教期间,王复生向青年学生推荐《先驱》《新青年》等刊物,发动学生集会,纪念二七惨案。王复生与王尚德乘机建立青年励志社,吸收潘自力、吉国桢、关中哲、杨慰祖等进步学生入社,从而为这些青年学生加入团组织创造了条件。(29)参见《陕西文史资料》第24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8—99页;《陕西省志·人物志》中册,第104页。
渭北是陕西中共革命发展的另一个中心。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学生早已组织了青年同志共进社,而后在李子健指导下,进一步发展为渭北统一的青年组织。李子健,又名李秉乾,三原人,1922年从渭北中学毕业,进入上海大学。当时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兴办教育的楷模,靖国军结束后,由三原赴上海的于右任出任校长,团中央负责人邓中夏任总务长,瞿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等先后执教,故该校尤其社会学系几乎成为党、团人才培养的基地。(30)参见李秀谭、朱凯:《于右任传》,第117—122页。李秉乾于1924年加入青年团,1925年1月带着整顿渭北青年组织的使命返回三原。他把三师的青年组织逐步扩展到渭北中学、第三职业学校、女子中学,改组成立渭北青年社,完全仿照社会主义青年团起草章程,并兴办《渭北青年》。在此基础上成立的三原青年团特别支部中,亢维恪、赵宗润、王之鼎(又名王之定)、姚志哲、杨纯德、薛应选来自三师,田怀德来自渭北中学。(31)参见《陕西文史资料》第12辑,第101—102页;《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373—378页。
与渭北一样,赤水青年团之所以能走出初期困境,也得力于返乡知识分子。来自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武止戈于1924年5月到赤水、西安指导青年团工作。他是渭南人,毕业于南开中学,在天津加入青年团,在北京参加共进社。1923年8月,在李大钊指导下,武止戈成为北京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1924年初受指派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随即前往苏联留学。(32)《陕西省志·人物志》中册,第94页。在出国之前,武止戈回到家乡渭南,与王尚德取得联系,促成了赤水团组织的重建。王尚德不仅恢复了与团中央的联系,开始积极报告赤水组织发展情况,而且到1925年1月,赤水支部发展到18人,新进团员皆为12岁至18岁的青年,并且积极开展了平民教育服务团的工作,支部还不定期召开会议。(33)参见《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5—11页。
赤水青年团的工作刚刚步入正轨,王尚德就着手统一渭河两岸的青年组织。当时三原有青年共进社,咸林中学有青年励志社,西安有青年文学社。鉴于青年组织发展的有利形势,王尚德建议中央批准以赤水为独立支部,统一领导渭河两岸的青年运动,并且无论以后陕西青年运动如何发展,赤水为唯一向中央负责之组织。为此,他积极联络西安团组织的张秉仁以及三原、华县方面青年组织的负责人,于1925年2月1日在赤水召开了四地代表联席会议。会上决定,以现有的青年共进社、青年励志社、平民教育服务团为基础,组织华县、三原团支部,与西安三个支部均受赤水支部领导,来自西安的张秉仁任联合支部书记,王尚德任主席。(34)参见《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7—8、12—15页。
但是,以赤水为中心统一渭河两岸青年组织的设想并没有实现,因为这些组织发展之初即呈现分散的多元化趋势。这首先与渭河南北的地域社会格局有一定关系,西安、渭南、三原“多元中心”的城市布局,决定了早期革命运动难以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来自武汉、北京、上海、天津等国内不同革命中心的返乡知识分子都参与到组织青年团的活动中,大大降低了渭河两岸青年组织统一的可能性。王尚德、武止戈、李子健、邹均(原名师守道)代表着不同时期、不同来源的上级指示,他们在陕西指导青年团活动,都被认为是合法的。
西安团组织的发展凸显出“分散多元”的特色。不同时期、来自不同地区的返乡知识分子都试图在省城建立团组织,从而产生了两个名称相同、风格迥异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西安支部。先组织起来的是第一支部。在陕两个月内,武止戈不仅恢复了赤水支部的工作,而且在西安发展了张秉仁、宋建旭、杨宏德三个团员,此后雷晋笙又介绍其他人加入,从而组成第一支部,推举杨宏德为干事。雷晋笙,长安人,早在1920年夏就加入青年团,1924年夏从上海震旦大学毕业,返陕前与主持团中央工作的邓中夏有往来,回西安后在陕西省教育厅任职。(35)《陕西省志·人物志》中册,第67页。杨宏德,任职于通俗讲演所,当时第一支部与团中央的书信都通过杨宅送达。张秉仁是成德中学学生、武止戈选定的支部书记,并且成为跨西安第一、第二两个支部的团员。他还与赤水王尚德取得联系,参加了赤水组织的联席会议,是渭河两岸不同青年团组织之间的积极联络人。(36)据称张秉仁是从咸林中学转往成德中学读书的。他的多重身份有利于在渭河两岸不同青年组织之间进行协调工作。参见《渭南文史资料》第5辑,第13页。
第一支部成员大都来自城市中等职业阶层。除张秉仁外,吕又乾、王钢军、杨宏德系通俗讲演所职员,宋建旭为省议会书记员,雷晋笙在教育厅做事,何以鸣为地方审判厅书记员,李通良、李凤娇为西北大学学生,另有刘化其(中学生)等三人无业。由于主要来自城市职业阶层,大多年龄偏大,有的已非青年,他们加入青年团,遭到了“名实不符”的强烈批评。一些人“私德”颇成问题,有人吸食鸦片,也有人喜好看戏、嫖妓,故代表上级整顿支部工作的邹均对他们的评价是“非青年,非学生,没思想甚至不够常识,大都有‘氓’气”。不过,第一支部也有其优势,因为拥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经验,他们可以利用关系网有效推进团组织安排的各项工作。比如在国民会议运动、非基督教运动以及平民教育活动中,第一支部的努力都颇有成效。(37)参见《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79—81、83页。
第二支部成员则主要来自学生群体。其中魏野畴为省立一中教员,周文化、任致远为一中学生,正谊、张含辉来自三中,武志祖、窦钧来自圣公会中学,师守命、宋乃谦来自甲种农业学校,吴宝书来自南开中学,何挺杰与跨两个支部的张秉仁来自成德中学。第二支部是在魏野畴指导下西安各主要中学革命青年的集合。魏野畴利用在一中任教之便创立青年文学社,兴办《青年文学》杂志,把西安主要中学的进步学生团结起来。第二支部成立后,《青年文学》改名为《青年生活》,成为支部机关刊物。该支部还通过西安中华书局订购《中国青年》《向导》,与团中央发生直接联系。第二支部选举张秉仁、师守命、正谊、任致远、何挺杰五人为组织干事,张秉仁担任《青年生活》编辑,师守命担任文书、会计,正谊负责付印、校对,任致远、何挺杰负责通告,分工之明确、组织之严密均在第一支部之上。由于几乎全为学生,第二支部思想纯洁、冲劲十足,批评第一支部成员思想落后、私德败坏。(38)参见《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77—81页。因此,作为武止戈选定的第一支部书记,成德中学出身的张秉仁却在观念上更认同第二支部的中学同道,更愿意参加第二支部的活动。
随着互联网的逐步成熟,共享经济、智慧酒店、深化度假方式等以创新服务深受用户追捧,我国在线旅游市场规模呈现出不断扩大的势态。2012年-2016年中国在线旅游市场交易规模增速保持在30%以上,其中2016年全国在线旅游市场交易规模达到7394.2亿元,同比增长56%,增速达到最高值。2017年第三季度中国在线旅游市场交易规模达到2025亿元,同比增长23.7%。初步统计2017年中国在线旅游市场规模将达到9701亿元,到2018年全国在线旅游市场交易规模将近12000亿元。
西安两个团支部的活动主要受津、沪返乡知识分子指导。武起为南开中学学生,1925年初回西安整顿青年团活动。针对两个支部的现状,他提议重组支部,但较认可第一支部的活动(39)《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65—66、68—69页。。邹均则更倾向第二支部。邹均,富平人,1920年春由省立三中考入南开中学,发起南开陕西同乡会,参加共进社,当年夏在北京加入青年团,1924年春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1925年初回西安,受命整顿西安团组织(40)《陕西省志·人物志》中册,第62页。。他同时参加了两个支部的活动,但在向团中央的报告中,对第一支部颇多微词,对第二支部则赞赏有加。邹均的偏向甚至鼓舞了第二支部的不满情绪,魏野畴就曾严厉批评说,第一支部不论年龄还是行为习惯,都不符合青年团的先进要求,强烈反对与其联合(41)参见《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75—81、83—84页。。直到崔孟博到来,两个支部的对立才暂时平息。崔孟博也是南开中学学生、共进社会员,1923年加入青年团,次年任团天津执委委员,1925年初返陕,调和西安两支部矛盾。在其努力下,西安两支部暂时结束了互相对立的态势。(42)参见《陕西省志·人物志》中册,第165页;《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61—62、81—84页。
四、“驱吴”运动与渭河两岸青年运动的合流
1925年5月,陕西学界掀起“驱吴”运动,渭河两岸青年运动多元发展的态势得到根本改变。多元分散的青年运动走向合流,为统一团组织的领导,以及团组织向青年群体输入观念与纪律奠定了基础。
“驱吴”运动是陕西教育界驱除督军吴新田的运动。吴新田是安徽合肥人,1921年进驻陕南,被任命为陕南边防军总司令,北依刘镇华(陕西督军)、西联孔繁锦(甘肃军阀)、南结刘存厚(四川军阀),形成了盘踞陕南的军事政权。刘镇华因卷入胡憨战争失败而被靖国军驱逐下台。1925年5月,吴新田接替刘镇华,入西安主持大局。吴新田在关中的统治基础太过薄弱,且与刘镇华一样无法摆脱“外人治陕”的恶名。因此,《共进》杂志在吴新田掌陕的消息甫一传出后,就高声疾呼:“这样一个大盗……不啻推陕西八百万生灵于火坑里。”(43)《穷凶极恶的吴新田能长陕么?》,《共进》第76期(1925年2月16日)。从吴新田上任的那一天起,“驱吴”就成了陕西各界的共识。
吴新田下台的导火索是一场由学生踢球引起的冲突。他上任仅仅四天时,1925年5月4日,省立一中学生在操场踢球,不慎将球踢到了紧邻一中的西仓吴部第28团驻地。学生前去捡球,与士兵发生冲突,驻军竟然集结兵力,冲入一中校园殴打学生,造成数十人受伤,其中四人重伤。(44)郭琦等主编:《陕西通史》第8卷,第115页。此即轰动地方的“五四惨案”。惨案发生当晚,一中教员魏野畴即组织学生集会,号召西安各学校联合罢课,表示抗议。5月5日,西安30多个学校举行罢课,成立西安学生联合会,向吴新田提出惩凶、治疗受伤学生、保证学生生命安全、赔偿损失、保证不再发生类似蛮横不法行为、将西仓驻军调离西安等条件。(45)《陕西文史资料》第11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1—202页。
吴新田对于学生罢课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他派人到一中找校长侯良弼居中调解,与西安学联开展对话,答应由教育厅出面解决学生的医疗费,同时将第28团调往灞桥,以示诚意,但同时亦以强硬态度迫使学生复课。吴新田的办法,一方面是封锁消息,使得西安学联与外界失去联系;另一方面则是向教育界施加压力,要求教师团体逼迫学生复课。起初,西安各校组成了西安教职员临时委员会,支持学生运动。但是,随着吴新田通过议会向其施压,教员遂改变立场,开始劝说学生复课。(46)参见《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152—157页。西安的局势一度极为紧张,军人见到穿学生制服者就加以盘问,致使学生扮成商人模样才敢上街(47)《陕西文史资料》第11辑,第203页。。吴新田的压迫使学生抗议活动陷入僵局。
西安学联的成立,本来是团组织发展的绝佳机会。该会主要负责人大多同时是西安团组织成员,以团组织之中心意志领导联合会之外围活动,应是顺理成章。但是,团组织在“驱吴”运动中的表现不如人意。三原团组织派往西安联络的李子健、赵宗润就发现,西安团组织成员不仅没有广发传单,以唤醒市民对学生运动的支持,而且没有很好地利用“五九”国耻纪念日,发动学生之外各社会阶级普遍参与(48)《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381—382页。。李子健和赵宗润的观察有一定道理,领导西安学联的大多是第二支部成员。与第一支部在群众运动中的表现相比,第二支部确实逊色不少。在当年1月为响应孙中山北上而掀起的国民会议运动中,陕西的表现相当出色。陕西国民会议促进会囊括了陕西实业会、农会、律师公会、报界公会、义赈委员会、国民拒毒会、普及文化社等诸多社会团体,活跃人物包括俞嗣如、魏野畴、段凌辰、李凤娇、何挺杰、王授金、胥元勋、羿文龙、刘述吾、吕佑乾、邹遵、韩少康、魏纯如等,而来自第一支部的社会职业群体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49)郭琦等主编:《陕西通史》第8卷,第105页。。显然,学生运动若只局限于学生群体内部,不能赢得更广大社会阶层的参与,就很难达到迫使当局妥协的斗争目的。
为了摆脱困境,西安学联作出了向三原转移的决定。各方的压迫使得继续在西安坚持斗争已不合时宜,因此向学生运动条件更为成熟、与省城军阀形成割据之势的渭北转移,就不失为良策。这时,渭北的学生运动风头正劲。李子健返回三原后,大大促进了渭北青年运动的全面发展。他由天津返陕时临近新年,学生早已放假,错失了动员学生的时机。但为了组织国民会议促进会,李子健与三原教育会会长、老同盟会会员程搏九合作,利用其在农会、商会的人脉,吸引30多个团体参加,将渭北社团网罗殆尽,成功促成了渭北国民会议促进会第一次筹备会的召开。待到第二次筹备会时,渭北各校学生已经开学,遂进一步将学生群体纳入进来。(50)《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373—375页。渭北的青年运动与国民会议运动的结合一开始就比较紧密。
李子健以组织国民会议促进会为契机,对渭北的青年团体进行了改造。三师的激进学生亢维恪等人组织的青年同志共进社,不仅引恽代英为“同志”,而且以青年团刊物《中国青年》《向导》为启蒙学生的“不二法门”。在此基础上,李子健组织渭北青年社,以反帝国主义运动、非基督教运动、平民教育运动引领渭北青年运动的新方向。(51)《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375—376页。以渭北青年社为外围,李子健进一步组织了三原青年团。与西安团组织接连错过纪念“五四”“五九”不同,三原团组织以渭北青年社集合渭北各主要中学学生,先后策划三原市民纪念“五四”大会、三原市民纪念“五九”大会,吸引农商界三四千人上街游行示威,把渭北的群众运动搞得如火如荼(52)《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379—380页。。
因此,当西安学联的骨干力量转移到渭北时,三原团组织领导下的青年运动已经相当成熟。这使渭河南北青年运动的合流成为可能。此前成立的渭北学生联合会,张安人任主席,赵宗润任宣传部部长,二人均是三原青年团成员,后者还担任书记职务(53)《陕西文史资料》第12辑,第103页。。因此,青年团已全面领导了渭北的学生组织。此次西安学联北渡,与渭北学联进一步组成陕西学生联合会。鉴于陕西学联诸人多非青年团同志,因此李子健让更多的三原团组织成员加入,以改造其成分。张安人、亢维恪、赵宗润、王之鼎、张云汉等青年团成员皆担任学联重要职位。与此同时,李子健、魏野畴在外指导,使青年团成为组织领导陕西学联活动的核心力量。(54)《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383页。
陕西学联成立之后的第一个重要决策是动员渭北学生罢课。团组织先召开会议,决定罢课策略,然后召开渭北青年社执行委员会会议,由渭北青年社出面鼓动三原各学校执行罢课决议,再召开学联会议,到各县开展组织、宣传工作,号召渭北各县学生罢课。经过层层动员,自6月1日起,同州、合阳、澄城等渭北各县以及陕北榆林、绥德等地学生纷纷冲破各地教育界封锁,宣布罢课,声援西安学生的“驱吴”诉求。(55)《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383—384页。
但是,渭北学生宣布罢课后,各校学生都提前放假回家,以至三原青年团、渭北青年社、陕西学联一共只剩十余人还在三原活动。青年团的活动因此受到不小的影响。如由三原支部、陕西学联提议召开的第一届陕西学联代表大会,虽经派往各县学校团员大力宣传,仍旧效果不佳,会期被一再推迟,到会者仅30余人。好在来自西安的张秉仁、师守命、张含辉、高文敏,来自三原的王之鼎、张安人,来自赤水的何思平,来自华县的岳炳光,皆为青年团同志,还有魏野畴从旁指导,使一切决议顺利通过,并对各地来的学生代表进行了团组织的教育。(56)《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384、390—391页。按:据称,会议通过了“学生参加学校行政运动”“修改学校课程运动”“民族革命与一般政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平民教育运动”“农村运动”等十余项决议。参见郭琦等主编:《陕西通史》第8卷,第117页。
陕西学联在成立之初就打算举办“夏令讲学会”,并向团中央写信,恳请恽代英、任弼时等亲自到渭北授课,指导学生运动。恽代英等人回信鼓励,但因为忙于应付五卅惨案而无暇西顾。(57)《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388页。不过,“夏令讲学会”还是于6月20日至7月15日在渭北中学顺利举办,听讲者包括中学生、小学教员以及学联代表约六七十人,授课者则囊括了渭河两岸著名的革命知识分子(见表1)。
其中,李子健、魏野畴、王尚德三人是三原、西安、赤水青年团的组织者,地位自不待言。耿炳光,澄城人,成德中学毕业后,入北京大学读预科,先后加入青年团、共产党,亦为渭北走出去的著名返乡知识分子(58)耿炳光是中共陕甘区委领导下第一任陕西省委书记,其生平参见《陕西省志·人物志》中册,第241—242页。。唯代表渭北中学尽“地主之谊”的赵保华出自共进社,与青年团关系稍浅。
总之,三原团组织、陕西学联的一系列活动初步扭转了渭河两岸青年运动相互分离、多元并进的局面,促成了渭河南北青年运动的合流。不过,学联的缺陷也十分明显,那就是没有很好地利用五卅运动而扩大影响。由于学联骨干移往三原,省城西安声援五卅运动的革命领导权被拱手让出。6月至7月西安工商学各界联合为援助五卅惨案掀起市民抗议活动时,渭北的青年团和陕西学联只是在机关刊物上发表了几个宣言,表示对运动的支持,而未能亲身参与其中。(59)《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186—187、190页。在省城动员中起到积极作用的是在西安恰逢其时的第一支部成员。继国民会议运动之后,来自职业阶层的第一支部成员又一次在重要革命运动中走到了队伍的前列。
五、渭河两岸青年运动的组织化与纪律化
1925年7月,在胡憨战争中胜出的国民军由洛阳一带进驻潼关,与此同时杨虎城、甄寿山从耀县南下,形成对吴新田的合围之势。7月15日,自知形势不妙的吴新田连夜西逃,仓皇退回汉中,结束了他两个多月的陕西督军生涯。7月16日,国民军第2军、第3军李虎臣、孙岳部进驻西安。8月,孙岳被任命为陕西省军务督办,李虎臣为帮办,杨虎城就任第3军第3师师长。陕西进入了国民军主政时期。(60)郭琦等主编:《陕西通史》第8卷,第117、122页。
在国民军入主西安后三天,7月19日,陕西学联宣布结束在渭北的活动,正式重返省城。但是,在学联渡河北上期间,西安的革命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重要的是兴起声援五卅运动的市民运动。各社会团体先后组织了西安市民追悼被英日屠杀同胞大会、陕西各界对英日屠杀同胞雪耻会、陕西学生对英日屠杀同胞雪耻会,尤其后两个组织的联合,沟通了学生界与社会各界,推动了省城革命形势的发展。(61)《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177、182—183页。
这时,在西安领导学生运动的是第一支部。由上海返乡的武起坐镇,与吕佑乾等第一支部成员进行了广泛的动员工作。武起为组织声援五卅运动的市民大会和遇难同胞追悼会,印发了讲义和传单,并出版《沸血》半月刊(62)参见《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87—89页。。第一支部还以《西北晨钟》《西北青年》为喉舌,鼓动抗议活动。《西北晨钟》最初只是发表些“复古”文字,但在惨案发生后,即于6月10日先后发表《对英日屠杀同胞宣言》《为“五卅”惨案通电》《为“五卅”惨案专电》,引领了省城舆论。改版为《西北青年》后,复发表两个宣言,提出“处驻沪英领事以死刑”“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收回领事裁判权”等激进主张,进一步声援五卅运动。(63)《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158—165、166、184—185页。陕西学生对英日屠杀同胞雪耻会亦为第一支部成员所控制。第一支部成功避免了学生群体孤立于其他社会阶层的“幼稚病”,通过与社会各界广泛联络,顺利垄断了学生界的话语权,并推动抗议活动狂飙猛进(64)参见《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101页。。
因此,陕西学联返回西安后,发现青年运动的领导权早已易手。在渭北经过再造而领导学联的青年团骨干试图重新夺回领导权,于是7月26日在西安召开青年团西安支部干事会会议,与会者包括西安本地的高文敏、魏野畴、张秉仁、师守命、张含辉,由北京返乡的耿炳光,由天津返乡的崔孟博,由上海返乡的武起、李子健,来自三原的王之鼎,以及陕北的杜嗣尧(65)杜嗣尧,佳县人,绥德四师学生。1927年夏,杜嗣尧建立中共佳县县委,是陕北地方党组织发展的重要人物。参见《佳县文史》第1辑,1995年印行,第36页。、刘志丹。(66)《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90页。这就不仅整合了渭河两岸青年运动的骨干力量,而且将京、津、沪返乡知识分子皆吸纳进来,将陕北团组织的重要人物亦加以网罗。团支部干事会还试图全面领导各界雪耻会、学生雪耻会、陕西学联等与青年团有关的组织,进一步组成工商学联合会,扩大反帝运动阵营。(67)《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91、93页。
会议的另一个目的是以第二支部融合第一支部。会议选举高文敏、崔孟博、张秉仁负责团的工作。高文敏、张秉仁都来自第二支部,崔孟博不仅调解过两个支部的矛盾,而且在学联北上期间与第一支部关系密切。在干事会看来,第一支部及其外围组织“组织与纪律都不很好”,于是高文敏、田克恭等人受命加入其中,予以督责与领导。(68)《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93—94页。
干事会的施压使两个支部的对立愈演愈烈。矛盾的爆发点是因组织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而产生的激烈竞争。1925年5月5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发出第30号通知,号召各地党、团组织帮助国民党建立省、县党部。先参与筹备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工作的是第一支部成员武起、吕佑乾、雷晋笙等人。(69)《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87—89、108页。但在学联返回西安后,第二支部逐渐把持国民党党部筹备事宜,在成立筹备会时,雷晋笙竟未能入选。双方矛盾爆发、互相攻击,以至国民党党员俱乐部成立后,选出刘含初为主席,赵保华为书记,两人均来自共进社,而非青年团(70)《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108页;郭琦等主编:《陕西通史》第8卷,第121页。按:一说刘含初为主席,杨明轩为书记,后者与共进会关系也相当密切。参见《陕西省志·中国共产党志》(上),第57页。。
西安两支部矛盾难以调和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初期的组织形态。最初,团组织是由地缘、学缘、职业而结成的“同人社团”,内部成员相对平等,并非上下级的领导与服从关系,对外则造成不同团体之间的“认同”冲突,很难形成现代革命政党的组织与纪律。若无外力介入,问题很难得到根本解决。
外力推动的结果是形成了革命政党的组织模式。来自上海和北京的中共代表通力合作,促成了西安团组织的正规化。吴化之(又名吴化梓),湖北汉川人,参加恽代英等人在武汉创立的利群书社,并加入青年团,后成为中共党员。1925年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归国后,他受共青团中央、中共豫陕区委和共青团豫陕区委指派,赴陕西整顿党、团组织。吴化之于9月先到咸林中学、赤水职校,规范了两地团组织活动,然后于10月到西安,与河北丰润人、中共党员安体诚(字存真)开展整顿西安两支部的工作。安体诚则是受中共北京区委指派,以陕西军务督办孙岳秘书身份为掩护,秘密参与西安党、团组织活动。(71)《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第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3—104、120页。吴化之、安体诚二人的外省人身份,避免了此前陕籍党、团员整顿团务工作时因身份认同而陷入派系纠葛的尴尬处境,有利于将组织与纪律输入青年团。
吴化之重组了西安团支部干事会,自任书记,宋树藩负责组织工作,张秉仁负责宣传工作。与7月成立的干事会相比,仅保留了张秉仁,吴化之、宋树藩则分别取代高文敏与崔孟博。宋树藩,西安人,毕业于南开中学,与崔孟博一同返陕,从事团组织工作,后来虽未参与其中,但参加了国民会议运动,后受杨虎城邀请,任杨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编辑《青天白日报》,同时参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筹备工作(72)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陕西近现代名人录》第3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63—164页。。吴化之引宋树藩为援手,把此前团组织的活动家崔孟博彻底边缘化。于是崔孟博另起炉灶,整合30余人,自任书记,雷晋笙任宣传部部长,李凤娇任组织部部长,张秉仁任学生部部长,武起任农民运动部部长,在西北大学附设国民学校,以原第一支部骨干为主力,先吴化之一步拟定了青年团西安地委的组织机构,大有与吴化之争夺西安团组织领导权之意(73)参见《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114—115页。。不过,崔孟博的组织建议似未获批准。
虽然遭到挑战,吴化之的改组工作还是颇有成效。为了严肃组织与纪律,吴化之对西安两支部成员进行了严格审查:已有合格团员11人,经干事会审查合格者14人,有提出异议者2人,对没有介绍人或虽经过上报团中央而未及批准者,呈报中央审查;初步审查不合格者中,不乏热诚勇敢、积极参加各项工作的同志,故将其编入团小组,进行训练。在对两支部成员彻底审查后,吴化之推进团组织发展的步伐,措施包括:在干事会会议后发展新团员8人,总人数超过30人,遂成立地委;团地委成立后不足一月,又发展16人,支部数由4个增加到5个;一个月内,支部开会18次,到会人数比例超过97%,另召开书记会议1次,地委会议4次,非基会议2次,学委及经委会议各1次,团地委大会2次,到会人数分别为20人、22人。吴化之进一步规范了团组织的进退机制:1926年1月底,团组织发展到59人,其中超过23岁者7人,被发展为中共党员;外地转来3人,转往外地9人;因为“三次无故不到会”“对主义与团体毫不认识”“根本不知革命是回什么事”“因为家庭环境的关系……思想行为与我们不能接近”等原因,开除4人。(74)《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95—96、110、113、119—120、134—135页。青年团西安地委不仅领导了西安各团支部,而且在青年运动发达的地区建立了5个特支(见表2)。

表2 青年团西安地委建立特支情况
以西安为中心辐射到渭河两岸各地,通过在西安加入团组织的学生到各县工作,向渭河两岸以及陕北地区进行团组织的“二次传播”,这就是吴化之的组织发展策略。延安四中和渭南固市渭阳中学都通过这种模式,与西安团组织建立了联系。由此,西安在渭河两岸团组织中的核心地位得以确立,扭转了初期组织发展中的多元化格局。
不止于此,吴化之还确立了党、团组织对其外围组织的领导关系。这尤其体现在对于青年生活社的定位上。青年生活社由青年文学社演变而来,是魏野畴等第二支部成员建立的外围组织,有社员90余人,散布于西安10个学校,拥有8个支部,吴化之急需借助该社扩大在青年群体中的影响,将其改造为党、团组织领导下的可靠力量。然而最初,青年生活社与团组织、陕西学联的关系呈“同心圆”结构,青年团处于核心位置,其外一圈是青年生活社,最外圈则是陕西学联,青年团向后两者输出命令(见图1)。此种组织结构仍未脱“同人社团”模式,不同圈层之间的渗透往往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同学、同乡观念,处于内一层的组织并非外一层组织的领导机构,缺乏明确的上下级关系。而经吴化之改造之后的组织模式是:党组织对团组织处于绝对领导地位,青年团之下则有青年生活社和国民学校两个下属机构,形成党对团、团对外围组织的上下级领导关系,建立起了革命政党的组织与纪律(见图2)。(75)《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97—99页。

图1 关中地区中共革命初期青年团与外围组织关系图

图2 改造后的关中地区党、团与外围组织关系图
严密的上下级组织关系为进一步成立党组织奠定了坚实基础。吴化之与安体诚的另一个任务就是帮助建立中共在西安的地方组织,在当时只有五个党员的情况下,唯有借助团组织及其领导下的青年生活社、国民学校的积极活动,才能扩大革命影响。1925年10月,中共西安特支成立,隶属中共豫陕区委,安体诚任书记;当年底安体诚北上后,由吴化之接任。与此同时,中共豫陕区委委员、郑州地委书记黄万平来陕,受命组建中共西安地委。而吴化之于12月先后赴三原、赤水,将三原青年团张仲实、王之鼎、赵宗润等人,赤水青年团王尚德、张浩如、张宗适等人发展为党员,先后成立中共三原特支、赤水特支。1926年初,中共西安地委正式成立,下辖西安、三原、赤水特支,黄万平任书记。(76)《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1卷,第44页。陕西的中共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六、结 论
渭河两岸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分化以及军事力量的对峙,决定了关中地区中共革命“多元中心”的起源。早期青年团组织正是在三原、渭南、华县、西安等地“多点并进”发展起来的。这些地方青年团的组建是返乡知识分子利用报刊、学校、社团等关系网络推动革命思潮传播的结果,由此也使得早期革命团体建立在共同的家乡、职业、价值观等基础之上,塑造了革命者多元的身份认同。如魏野畴既是中共党员、共进会会员、陕西学联的组织者、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筹备委员会成员,又组建了西安青年团第二支部。多元身份极易产生严重的认同冲突,不利于组织动员。如同是中共党员的雷晋笙,因为行为模式、价值观等与魏野畴等人不同,不仅另组西安青年团第一支部,控制雪耻会、西北青年社等外围组织,而且与第二支部领导下的西安学联在一系列革命活动中矛盾不断。身份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明显背离了革命政党组织与纪律化的要求。因此,如何克服早期革命组织发展中的多元化倾向,是建立一个革命政党要面临的首要问题。可以说,关中中共革命的兴起,就是一个由多元转向一元、由传统知识分子社团模式走向组织化与纪律化的现代革命政党的过程。
早期关中地区的党、团组织模式并非特例。这种认同冲突、多元化倾向在其他省份早期中共组织发展中也不罕见。英国学者方德万早已指出,只有以知识分子社团模式来看待中共广东地方组织的活动,才能对陈独秀在广东时的许多行为作出合理解释(77)参见Hans J.van de Ven (1991).From Friend to Comrade: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0-192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p.99-146。。台湾学者陈耀煌在关于中共河北地方组织的研究中,也揭示了李大钊如何利用地域、师友、职业认同,来发展北方区委领导下的党组织(78)陈耀煌:《统合与分化:河北地区的共产革命(1921—1949)》,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94期(2012年8月)。。即使陕北的中共地方组织发展史与关中有着巨大差别,也不可否认,其多元化倾向仍清晰可辨,突出表现为党、团之间的互相渗透关系,党组织最初并没有绝对的领导权。上述情况提醒我们,今天学界所熟悉的一些看似理所当然的结论,如中共党内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党的组织与纪律化要求,党对团组织的领导等等,都是后来才形成的。其成立初期的情况因时因地而异,必须作具体化的区域研究。早期党、团组织充分利用了地缘、师友、职业认同,因而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认同冲突,并非我们所想象的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革命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