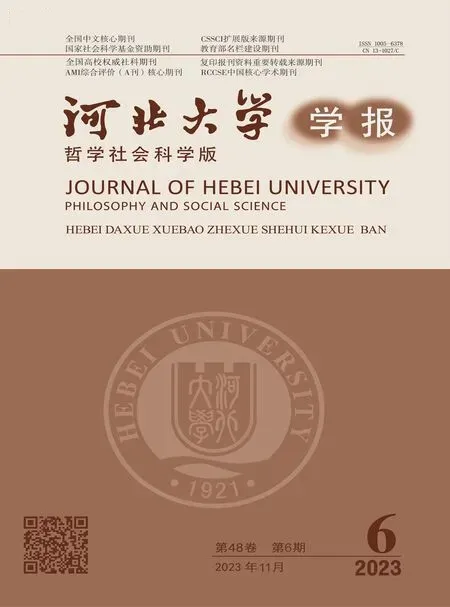李健吾的“自然”批评观探析
2024-01-25钱少武潘超青
钱少武 ,潘超青
(1.韩山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广东 潮州 521041;2.厦门大学 国际中文教育学院/海外教育学院,福建 厦门 361104)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最负盛名的重要批评家之一,李健吾的批评文本中多次出现“自然”一词,出现的频率和次数甚至远高于李健吾的其他用词。虽然李健吾从未以明晰的语言界定或阐释其笔下的“自然”术语,但如果把这些散落在他批评文章各处的“自然”放在一起进行综合性考查、辨析,探寻其在不同批评语境中所显现出来的意义、价值和功能,我们就会发现李健吾笔下的“自然”术语意蕴丰厚,具有多层次的意义蕴涵和多向度的价值指向,贯穿于作者对文学评价、创作和欣赏等的多重分析和论述之中,是李健吾其他批评观念得以阐释性展开的重心或旨归所在,因而构成了李健吾批评话语中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重要批评观念。
李健吾的“自然”文学批评观主要源自中国传统文学艺术批评中“自然”批评的思想和观念。传统的“自然”批评观由道家的“自然”思想衍生而来,居于传统批评的核心地位。李健吾非常推崇道家的“自然”思想,认为“宇宙的进行隐隐寓有一种自然的法度,看不见,然而感得到”[1],也熟知传统“自然”批评,只是作为一位中西兼容的现代批评家,李健吾显然从更为宏阔的批评视野来看待传统“自然”批评思想。他在批评实践中自觉承继、化用和拓新传统批评中“自然”的主要意蕴、精神和原则的同时,也选择性地吸纳、深化了西方批评理论中极其重要的“自然”范畴的一些内涵[2],从而形成了李健吾独具特色的“自然”批评观。
李健吾的批评虽“以印象主义为基本特征”[3],但其批评文本中内蕴的许多传统批评色素也同样不容忽视,因为相较于西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特别是印象主义批评的影响,中国传统批评对李健吾的影响则更深刻、持久。近些年来学界对此给予了不少关注。论者均立足于李健吾中西交融的批评特质,或谈论传统文论资源中“感悟式的批评理论”[4]、“‘性灵’说与‘妙悟’说”、“‘以意逆志’与‘知言养气’的批评方法”、“‘言不尽意’说”与“‘得意妄言’说”[5]、“‘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批评传统”[6]、“‘托物取象’的论证方法”[7],以及传统文论的“思维方式、言说方式、批评方法、审美取向”[8]等对李健吾批评产生的多层面积极影响,或在肯定“感悟式的批评方式和话语”增强了李健吾批评审美意识的同时,也指出“过于推崇直觉和印象,导致了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科学和理性精神不足的缺陷”[9]。笔者不揣浅陋,以这些研究为基础,从对李健吾文学批评中运用的“自然”术语的分析入手,探讨李健吾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集中体现于其批评文集《咀华集》和《咀华二集》,贯穿于其50多年批评生涯的自然批评观。李健吾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语境中对传统自然批评观念的创新性应用,不仅使古老的批评观念真正跻身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中,而且成就了中国现代文学自然批评的一个独特的成功范例,对当下建构以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内核的中国文学话语体系更是有着积极的启示、借鉴和参考价值。
一、一切要自然
“自然”是李健吾对作家、作品的一个重要评价标准,包含了他对评价对象的喜爱和肯定,甚至可说是他对评价对象所能给予的最高评价。他以此评人论文,阐释他的审美理想和价值取向。他称赞“自然正是丁西林先生的一个特色”[10]386,赞赏沈从文的《边城》“一切准乎自然”[11]60,指出艺术创作“一切要自然”[12]217。在李健吾的批评视界中,“自然”既是主体品格、创作特色或艺术成就的评判标准,也是艺术表现内容和技巧的评价尺度。透过李健吾不同批评语境中呈现的“自然”标准的价值蕴涵和意义指向,可以看出这一标准并不是李健吾自己凭空设定的,而是他立于现代批评语境对传统“自然”批评标准进行有机吸纳和化用的结果。
李健吾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他不仅重视传统对于创作的意义,认为“杰作”的产生离不开传统的滋养,“因为真正的传统往往不只是一种羁绊,更是一层平稳的台阶”[13],而且还看重传统的批评标准。对于“前人所定的标准”,虽然“政治组织”“社会关系”等标准所适用的“表面的条件”随历史的变迁发生了变异,但“其根本原则还是相同的”,因而“这些标准的原则始终能够应用”[14]。李健吾所说的“原则”,是指传统批评标准所内蕴的艺术追求、价值、精神等。王国维认为“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王国维所谓的“自然”,就是作为古代文学批评最高标准的“自然”。王国维“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的文学才称得上是“中国最自然之文学”[15],可说是对传统“自然”标准所做出的“最精要的概括”[16]。虽然“自然”这一批评术语内涵的具体指向在古代文学批评的历时时空中不尽相同[17],但强调文学作品如化工造物般浑然天成,不见任何人工斧凿痕迹的核心价值取向始终如一,重视源自庄子“贵真”艺术思想,推崇主观与客观之“真”,“自然会妙”[18]表达内心世界以及“如芙蓉出水”[19]般自然之美的创作追求也贯穿始终。李健吾厚爱古典美学,他立于个体审美眼光和现代批评理论对传统“自然”批评思想、观念进行反观、透视,将其中一些原则应用于其批评之中,因而他批评话语中“自然”的意义指向,在许多方面都呈现出与传统“自然”批评蕴涵相承续的特性。
在李健吾的审美评判中,他特别重视艺术创作的表现之“真”,要求创作主体所营构的艺术世界真实、逼真地反映社会人生的实际状貌,自然而然地呈现一个充满美感的真实艺术世界。李健吾批评语境中的“真实”“真淳”“逼真”等词不仅常常和“自然”相关联,还暗示了“自然”在求“真”的价值取向中所包含的多层面的意义指向。其中至少有以下几点:其一,现实世界的真实呈现或再现。“我得请读者多看一眼《电》的第六章,这一章写的那样真实,而又那样自然。”[20]44他赞赏朱端钧先生导演的《夜上海》,《夜上海》演员表演的“造诣”之深让人惊叹,“连一个小孩子,都扮的那样逼真,那样富有人性”,以致观众沉醉其中。剧中人的遭遇让他们感同身受:“‘都是《夜上海》中人’,此言不假。有谁不在这黑暗的孤岛生活吗? 泪潸潸然下了。”[12]217其二,故事情节的发展合乎生活或个体性格逻辑的真实。李健吾赞扬萧军不以理想来取代故事事件合乎逻辑的自然演进:“他不硬拿希望和贴膏药一样贴在小说的结尾。希望不是舶来品,而是小说进行之中一种自然的演述。”[21]103指出巴金笔下堀口的“转变是自然的”,因为“我们知道了堀口的性格,环境,教育,以及一切发展成为他精神存在的条件”,“他的性格先就决定了他的未来”[22]53-54。反对为了艺术效果而背离性格演变逻辑的“自然”:“这样一来,鲁大海的性格一致吗? 我晓得这里有很好的戏剧效果,杀而不杀。不过效果却要出于性格的自然与必然的推测。”[23]83其三,符合生命内在本能需求的真实。李健吾重视“生命”,肯定指涉“本能的”及“本能的需要”的“自然”:“即令雪莱(Shelly)再世,也不能否认恋爱属于本能的需要。如果革命是高贵的,恋爱至少也是自然的。我们应当听其自然。”[20]44
“真实”或“逼真”是李健吾对艺术表现对象或世界的最高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李健吾要求作者以纪实的眼光,毫无保留地呈现原生态的生活或自然场景。他看重主体创作对待他所要绘就的世界的“真诚”:艺术的根植是人生,决定它的是真诚[24]。而“真诚”要靠材料的真实和创作者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的灌注来实现,李健吾认为不管是写实的还是写意的,“自然”艺术世界的营构离不开“作者的真诚,材料的真实”这两点,它们“凝成一片”才是创作最高的自然境界[25]。因此,李健吾真正看重的,是经过作者审美理想和艺术心灵净化的原生态的地方风俗、景物或生活,是打破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藩篱的“逼真”的艺术世界,所以他极力推崇《边城》,认为《边城》熔铸了主体“肝胆相见的真情实意”[11]59,是沈从文“用他艺术的心灵来体味”的“更其真淳的生活”[11]61。
李健吾不仅把传统自然批评重视主、客观之真,“度物象而取其真”[26]的创作思想创造性地化用于现代小说、戏剧等的评价之中,强调艺术表现内容的真实自然,同时也承继了传统“自然”批评“同自然之妙有”[27]的创作追求,因而他非常重视主体艺术表现手法和表现技巧的和谐自然。他认为风俗戏是一个导演的试金石,对于它的表现,“没有过分夸张的讨巧的地方。一切要自然”[12]217。真实、自然的艺术叙事并不意味着不讲究叙事的手法和技巧,或者排斥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所需要的匠心和雕饰。李健吾看重艺术家为了“把最高的效果或者目的传达出来”的“苦心孤诣”[28]。他赞扬何其芳作文的用心:“他用技巧或者看法烘焙一种奇异的情调,和故事进行同样自然,而这种情调,不浅不俗,恰巧完成悲哀的感觉。”[29]139所以,李健吾看重的,恰恰是“苦心孤诣”所产生的看似无技巧的自然技巧,是“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的结果[30]。他欣赏丁西林《一只马蜂》的“误会就用得巧妙还又自然”,赞誉丁西林的戏剧“自然、隽永、意外”,“他的戏剧语言不仅意味隽永,耐人寻思,而且往往声东击西,最后给人一种意外感觉”,“而每一出的戏的幕也闭得恰如其时”[10]386。
传统自然批评重视人文一体,推崇“自然”是“文”的最高标准,同时也看重创作“文”的“人”的自然品格,如姜夔论陶渊明:“天资既高,趣诣又远。故其诗散而庄,澹而腴。断不容作邯郸步也。”[31]李健吾的批评,同样重视人与文的相契相生,追求作家与其作品的相互贯通。他论人及文,推重创作主体心灵和生命境界及其艺术表现本色、质朴、率真的呈现。李健吾的批评中一些地方虽然没有明确使用“自然”一词,但他评价中所使用的“本色、质朴、率真”等术语,直接指向包含了这些术语内涵的传统“自然”批评的价值取向,是李健吾审美意识和艺术价值批判尺度中“自然”标准的具体化。李健吾爱臧克家先生为人率真、不勉强,有时候“赤裸裸的如一个婴儿,或如明溪,天真可爱”[32];直言翻译家伍光健“渐渐失去他早年那点儿质朴。这很可惜”[33];赞誉“萧军先生不苟且。行文犹如做人,他要的只是本色”[21]93。李健吾承继传统“自然”批评特质的同时,又立足于现代批评理论,将传统“自然”批评精神语境化的同时又加以深化、拓展,直指主体纯净心灵关乎艺术本身,如陆蠡的创作成就“得力于他的璞石一般的心灵”,而主体“生命真纯”则是艺术节奏不变的源泉,节奏“从什么地方来? 我想大概是从生命里来的罢。生命真纯,节奏美好”[34]。
因此可以说,李健吾评判文学作品的“自然”标准,完全立足于文学的艺术价值层面,推崇“艺术作品”就像天然的鲜活生命体,不管是“光与影”的“配置”,还是人物的安排,看起来“一切是谐和”,一切都自然而然,根本“叫人看不出是艺术”,尽管它饱含了作者的审美理想和人生体验,浇铸了作者的独运匠心和辛苦劳作,却又不留下任何人为斧凿或雕饰的痕迹。李健吾认为这样的作品才堪称“杰作”,才是“千古不磨的珠玉”[11]60。
二、创作:纯粹“不自觉”的主体行为
李健吾认为创作应该是一种纯粹的“不自觉”的主体行为,即创作者心灵自发的而非受现实功利因素操控的无意识的艺术行为,“也正因为不自觉”,才会创作出“富有非人为的自然的美丽”的优秀作品。所以他特别推崇“不晓得自己是艺术家,不晓得在弄什么艺术的制作”的作家,他认为在众多旧小说里面,只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这“很少几部”“具有较高的文学的价值”,因为作者的创作动机、目的或意图是纯正、朴素、不自觉的[35]171。
李健吾的“不自觉”创作主张承继了传统自然批评论中“无意于文”的创作思想[36],甚至可看作是“无意于文”而为文思想的另一种表述。李健吾以此评析传统和现代作品,阐释他的创作理念。他认为许多“旧小说难以来到一种完美的发展”,就因为作者“不想感动人,却想教训人”,一心想着传达儒道之道,忘记了艺术创作行为本身,使作品“离艺术较远,离儒道更近”,成了变相的宣传品,所以失败[35]170-171。李健吾不反对艺术的传道、载道功能——单纯的愉悦功能会侵吞艺术作品必然具有的严肃性。他反感的是一些作家“忘记艺术本身便是绝妙的宣传”,不是把心思、功夫花在艺术本身上,把所要传达的理念不露痕迹地融会于艺术文本之中,而是仅仅把艺术当作一种说教的工具、手段,甚至“更想在艺术以外,用实际的利害说服读者”。所以,他虽理解“像巴金先生那样的小说家”由于时代因素或许被迫“从文字上图谋精神上的解放”,但对“他们宁可牺牲艺术的完美,来满足各自人性的动向”的做法深感不以为然[22]52。
不过,李健吾并不认为创作意识的“不自觉”就能够决定作品的品质和成就,主体“不自觉”的创作行为并不能保证作品必然取得成功。要使作品达到“自然天成”的艺术境界,创作者还必须要有深厚的艺术素养和对自我艺术能力的清醒认知:
一个好艺术家多少都是自觉的,至少他得深深体会他做什么,他能够做出什么。在把握一切条件之前,所谓工必利于器,他先得熟识自己的工具和技巧。这是制作的基本。而诗人或者文人,犹如一个建筑师,必须习知文学语言的性质以及组合的可能,然后输入他全人的存在,成为一种造型的美丽。[29]135
在李健吾看来,主体创作的“不自觉”与“自觉”是两个层面的话题:一个指创作动机、目的,强调创作应听从主体自我内心的召唤,而非满足外在功利的需求;一个指创作实践本身,突出的是创作所需要的知识储备、艺术积累和主体自我“全人的”无痕迹输入。对创作“自觉”的倡导恰恰可以看出李健吾认为创作是一门需要用心用力的技艺,绝非简单的“天才”一蹴而就的行为。
此外,艺术家还应当处理好“自我”和“表现”的关系,建构起真正的自然而然的艺术世界。李健吾重视主体“自我”,认为“自我”是一切艺术表现的重心,因为“一个真诚的艺术家永远在表现自我”[37]196。“自我”和“表现”之间合理的关系不是克服,或者合作,而是两者之间的相好无间,为此,主体创作要努力追求的是,其“自我”和对“自我”的艺术“表现”这两者之间如何达到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自然境界,从而成就独属于主体自我的艺术风格,尽管这需要主体多年的认识和摸索才能做得到。芦焚前期创作就没有处理好这一点,他努力征服自我以满足他的艺术“表现”,使“表现”背离了真正“自我”的个性、气质、艺术素养和生命体验,破坏了“自我”与“表现”的和谐融通。他“用力给自己增加字汇。他不忌讳方言土语的引用,他要这一切征象他所需要的声音,颜色和形状”,从而造成了文字表达“缺乏自然天成,缺乏圆到”,给人一种“坎坷之感”。李健吾坦诚地劝诫芦焚要逐渐走出对“诗意”表达的追求,回到他“真正的自我”,认为芦焚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已开始改变,他的小说《莱亚先生的泪》就是例证,鼓励芦焚最终会成为一位大小说家[38]147-148。
李健吾也看重创作者“热情”与作品“自然”的关系,认为韩愈是个“情感人”,是一位“被真理(他所宣扬的道)耽误了的热情者”。正是这股用自我内在生命灌注的“一腔真诚的热情”,使韩愈“一扫虚伪的矫饰的词句(六朝以来的把戏)”,“复活”了东汉以前古文中“起伏于人心之间的自然的语言”,真正“回到那被热情激荡的生命的节奏”,而这正是“韩愈文章的成功”所在[39]。李健吾肯定主体“热情”对文章表达“自然”的作用,比如韩愈,又如“生活在热情里面,热情做成他叙述的流畅”的巴金。李健吾说巴金“不用风格,热情就是他的风格”。在巴金热情的催动下,读者畅快淋漓的阅读会忽略掉文中的“毛病”:“你正要注目,却已经卷进下文”,“热情”使巴金的“文笔”拥有了“自然而然的气势”。茅盾就缺乏巴金的“行文的自然;他给字句装了过多的物事,东一件,西一件,疙里疙瘩的刺眼”,虽然文笔比巴金“结实,然而疙里疙瘩”。李健吾同时又对主体的“热情”保持着清醒的理性认知。他立于现代叙事理论的高度,指出这种热情对作家叙事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巴金“不长于描写”,因为“热情不容他描写”,“描写的工作比较冷静,而热情不容巴金先生冷静”,尽管巴金自然流畅的叙事抵补了他“描写的缺陷”[20]40。萧军本来是“描写的能手”,可拥有的“国家和种族的怨恨”破坏了他心情的平静,他“火一般炽着”的情感“时时刻刻出来破坏自己的描写”,使他“把每一句话都烧成火花一样飞跃着,呐喊着”。萧军虽然“努力追求艺术的效果”,可他的“热情”却在他不知不觉之中,“添给句子一种难以胜任的力量”,使他的作品失去了“亲切”的感受[21]98。可以说,李健吾以作品的“自然”追求为核心,多向度地阐述了主体“热情”对于创作的不同效用,公允中肯而又鞭辟入里。
三、儿童视角:“可爱”与“有趣”
李健吾推重表现童年的作品,因为童年是作者“灵魂的最安适的休息所,文学上的灵感的宝库”,因而作者在作品中“所表现得好的往往是童年”。读者在作者“天真的表现中”,总“能觉到自己甜蜜回忆和回应”。李健吾盛赞这类触及作者、读者心灵的作品是学界的“团茶”,它消融了作者、读者界限,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结果,“我们在表现自己,满足自己”,而这在李健吾看来,正是小说创作应该承负的使命所在[40]3。
在李健吾的批评话语中,“童年”“儿童”“天真”等词语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存在领域。可以说,对“童年”“儿童”“天真”的书写和表现最符合李健吾的创作理想和审美追求,其实质上也是李健吾所坚守的传统“自然”批评精神和原则在现代小说创作和欣赏层面的映射和深化。众所周知,明清文人的自然观中便开始拥有了“童子”“童心”等同“自然”的内涵。李贽认为“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主张以“绝假纯真”的“童心”著文:“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41]明清文人带给李健吾先入为主的“自然”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对外国文学的接受眼光和价值取向,因而他非常赞同乔治桑“童年全属神圣”的看法,认为它是《篱下集》这本书最好的“注脚”,“犹如乔治桑,我们得尊敬这神圣的童年”[42]70-71。
李健吾特别看重采用以童眼观察、童心感触成人世界的儿童叙事视角的作品,他对这一叙事视角的阐述明显寄托了他的社会、人生和艺术理想。李健吾认为,运用儿童视角的叙事策略不仅丝毫不会有损于作品,反而会加强作品的深度,增强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因为作者写的是小说,而不是童话,表现的是复杂的人生,而不是善恶分明的单纯童话世界。李健吾推崇《篱下集》作者萧乾“用一双儿童的眼睛来看人事”,并通过故事中儿童“用率真的单纯给自己解说”成人社会的一切,真切地表现出“成人世界”的虚假和荒谬,向童心未泯的人发出了“动人的呼吁”。从儿童视角书写故事,李健吾主张要尊重儿童的心理和思维特点,遵循由儿童到成年成长的自然规律,不能把成年人的眼光和标准强加于儿童身上,否则儿童的形象不过是“早熟的果实,不丰满,欠味道”,根本立不住脚[42]70-71。
李健吾还从读者接受层面阐述了儿童视角所具有的独特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和儿童拥有的天真善良美好品行密切相关。李健吾认为,儿童视角呈现的是作者“用天真体会繁难的世事”[42]70叙事策略营构的艺术世界。当乡村和城市,儿童和成人产生冲撞,结果却是来自乡村“光明壮实坦白的赤子”的“天真”被成人社会轻易“斫毁”[42]73。这种书写会让读者感到“分外悲哀”,激起他们强烈的同情善良无辜弱者的心理效应,因为“在弱者之中,儿童最属无辜,最不为人解”[42]70,因“无辜而更引人同情的”只会是“可告无愧于天的赤怀”[42]72。李健吾肯定同情让儿童视角产生的强烈的艺术效果,同时又认为对儿童遭遇过浓的同情会破坏读者的阅读感受和审美趣味,为此他很是欣赏沈从文在这方面的艺术处理手法“揶揄”。沈从文采用这种手法,是因为他“有了过多的同情给他所要创造的人物是难以冷眼观世的”。沈从文“晓得怎样揶揄,犹如在《边城》里他揶揄那赤子之心的老船夫,或者在《八骏图》,他揶揄他的主人公达士先生”,他不是把“揶揄”作为“一种智慧的游戏”,而是转换叙事情感基调,推动人物命运自然“转变”的得力工具[11]59。
李健吾赞赏书写儿童的作者所怀有的积极的理想主义情愫,指出萧乾笔下所展现的“儿童的天真”绝不仅仅是软弱的存在,它还具有强大的力量。改变荔子“粗野”观念的,“不是知识,而是感情,不是父亲,而是一群天真烂漫的儿童”。李健吾审美价值取向中的儿童,还包括“类似儿童的成人”,他们单纯、坚韧,“单纯,所以成为一种缺陷;坚韧,所以饱经尘世的嘲弄”。他们是社会意义上的“弱者”,但在作者的生命理想层面上却绝不是,因为他们有着“强壮”的身体、性格和灵魂。李健吾盛赞萧乾“粘着何等沉重的污泥”,却能够以一颗童心,“站在弱者群里”,“用心叙述人世的参差”,尽管“字里行间不免透出郁积的不平”[42]70-73。
从李健吾的批评用语中,不难看出他拥有一颗真正的童心,而由这颗童心孕育出的童趣,构成了他喜爱的众多趣味的底色。他总是以这种心态和趣味欣赏、评析文学。他的批评中多次出现“可爱”。他说朱光潜的文章《谈美》“通畅而且可爱”[43];李广田“肝胆相照,朴实无华,浑厚可爱”[44];“可爱! 这是沈从文先生小说的另一个特征。他所有的人物全可爱”[11]59。何谓可爱? 李健吾解释说:“可爱的人要天真。而且更要紧的是,要有弱点。”《雷雨》中的鲁大海并不可爱,他虽然天真,“天真到了赤裸的地步;他却没有弱点”[23]83。“可爱”其实也是李健吾批评的真实写照,他的批评多属随笔体,亲切,随和,又爱憎分明,充满了作者的真情实感,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和生活、艺术的自然情趣。
在李健吾审美评判中,作品除了“可爱”,还要“有趣”:“在这几篇中以《L君的话》为最好,结构,故事,叙述都极有趣。”李健吾说:“我非常欢喜它。”[45]而丁西林独幕喜剧《亲爱的丈夫》“追求”故事的“奇谲,戏写得非常有趣”[10]386。李健吾坦言自己是“书呆子,从来不懂生活,也不好和人往来”,这种好静、喜欢独处的个性让他一坐在书桌前,就会感到“怡然自得,别有一番乐趣”[46]。李健吾也因此非常看重作者及作品显露出的趣味。他肯定纯粹出自自然本心的童趣——这一点同推崇产生于至纯至真童心的自然趣味的明代公安派文人极为相似,也欣赏源自生活本身和作者心底的本色的艺术趣味。可以说他在承续传统自然之趣的同时又拓展了这种趣味。李健吾认为“浓郁的趣味”对创作非常重要,更是“小说所一刻不能离底”。趣味的产生不仅需要选材严谨,还需要作者拥有传统诗学素养以及创作个性的介入。蹇先艾小说《狂喜之后》缺乏趣味,连娱乐读者的力量都觉得嫩弱,根源就在于选材不细[40]1-2。丁西林因为“骨子里富有祖国的诗的传统,语言和意境清楚而又含蓄”,加之“对素材的掌握、对生活的熟悉”,虽然“写戏不多,题材范围不宽阔,可是经他一写,就像经玉匠雕琢过一样,通体透明,而又趣味盎然”[47]378。不过,他写右派副部长的四幕话剧《一个和风细雨的插曲》,写“五反”的独幕剧《干杯》,由于“脱离剧作者的特色、幽默感”,毫无趣味,却“不能算作成功之作”[10]385。
李健吾所欣赏的“趣味”范围广泛,意蕴深厚,包括乐趣、妙趣、风趣、情趣等。李健吾对“趣味”及其关联词语的论述虽带有个体审美体验的主观色彩,但却具有普遍性,这与他自然的美学追求,精深的艺术素养和雅致的艺术品位有关。他批评语境中与趣味相关的用词精准而具体,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认为丁西林的独幕喜剧会“逗人发出会心的微笑”,因为他“观察生活细心,能从平淡中领会出它的妙趣”[47]378。指出《室内游记》的作者“是一位极有风趣的小说家”,赞赏他的行文素朴、自然,毫无“雕琢的短处”[48]。即使是同一种趣味,李健吾在不同的语境中也凸显了其同中之异。同为“情趣”,于伶的作品让我们不时感到一种为一般中产阶级所钟爱的亲切的情趣[49],而披阅废名问世多年的《竹林的故事》,依旧能感受到它满载的雅致的情趣[29]133。
四、“谐和”或“冲突”的“自然”
李健吾批评语境中的“自然”意蕴主要来自中国传统文学艺术批评中的“自然”,但在一些时候也完全来自域外的“自然”观。“这个生就艺术气质的小苗子,好奇,好颜色,好自然里面所有的自然现象”[50],这里的“自然”显然指涉自然界、大自然、自然万物等意蕴,而传统批评中“自然”不包含此类意义。李健吾所论及的这一“自然”,对应的不仅仅是外在于人类社会的本色的或原生态的宇宙万物,更是经过主体心灵浸染的宇宙万物。李健吾认为书写自然的核心是“谐和”,他价值评判中的“谐和”显然有两个层级:一个是文本世界纯技术层面的“谐和”,即“自然”作为背景性的存在,与人物世界和谐一致,对人物、故事、情节等起到点缀、烘托或推进作用。他赞誉叶紫“知道运用风景配合心理的变化”[51],批评芦焚生活过的乡下“一切只是一种不谐和的拼凑:自然的美好,人事的丑陋。尤其可怕的是自然的冷静,人事的鼎沸”[38]148。另一个层级的“谐和”是李健吾在艺术层面对现代“自然”意蕴的深化,因而他倍加推崇。这种“谐和”强调“自然”的灵性化,即大自然有着和人类社会息息相通的灵性,其“运作性质或方式”“带有人类技艺的特征”[52],对人提供的不仅仅是天然的食物,还有心灵的养分和精神的馈赠:“一个没有家或者没有爱的孩子,寂寞原本是他的灵魂,日月会是他的伴侣,自然会是它的营养。”[21]94
在追求“谐和”之外,李健吾也看重“冲突”,看重被直接赋予了“人”的个性、情感和体验的人格化的“自然”与人物甚至书写者产生的冲撞和对抗。李健吾说读完萧军书写义勇军苦斗的血史的《八月的乡村》,“第一个印在我们心头的人物,不是那些形形色色的男女,而是具有坚强的性格的自然”。萧军笔下“自然”性格的所谓的坚强竟然是通过它的冷酷、无情表现出来,这不能不让李健吾感慨万端! 他叹赏熔铸了萧军灵魂地对“自然”的有力表现,抓住这一表现的艺术境界,把它转化成自己的心灵之声:“这茂盛的八月,理应给人类带来丰盈的喜悦的,如今却成为徒手的人民争夺自由的屏翼。”在冷血、暴虐的入侵者面前,“自然”“无所为力”,不仅没有义愤填膺,与受害者同仇敌忾,“反而随人作嫁”,甘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这怎能不让人伤心! “我们用了多少年恩爱开垦出来的土地,一瞬间就服服帖帖做了异性的奴隶。这冷酷的自然,张来也是它,李来也是它,打扮的那样迷离入目,原来娼妓一样迎新送旧! 任你生气,呼号,绝望,它依然故我;不问饮恨吞声,毁家纾难,它依然花枝招展。它讥笑人类的忧患,也是人类衷心的奸细。作者的敏感饶不过它。”李健吾完全站在作者一边,充满激情地声讨自然的冷酷,因为李健吾从萧军对自然的另类书写中准确地透视出对失去了故土“风物”,“由极爱到极恨”的萧军所怀有的“无省之民的心情”,“谁能不爱,便是朝三暮四也罢,从小长在我们的心头,它属于我们的心头! 我们热烈的无望加倍显出自然的冷酷。”[21]97-98同时指出萧军的另类书写“自然”的根源却在于他的浪漫情怀。在浪漫主义者眼中,“自然”充满了宽厚、理解和同情,浪漫主义者“用他的自我来诠释,他接近自然,因为傲然无伴,只有无言的自然默默容纳他的热情”[42]75-76。李健吾认为跑向自然寻找同情,临了发现自己越发孤独的这种对于自然的“浪漫的心情”,几乎是每个青年人成长过程中都会经历的,因此书写“自然的冷酷”[21]98也就成了处于这一阶段作家的当然产品。如果说“设想艺术与自然相谐和的方式”[52]91堪称浪漫主义文学教义的精髓,李健吾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释了自然与人的冲突,同样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应有之义。
结语
虽然今天对李健吾所用“自然”意蕴出处的词源学考据和辨析几乎难以做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传统批评理论中的自然观为李健吾提供了强大的知识背景和审美眼光,主导甚至决定了他接受西方自然观的方向和重点,而西方的一些自然观念,又拓宽和加深了李健吾对“自然”的理解。毋庸讳言的是,李健吾的随笔体批评,与讲求逻辑性和思辨性,以理性分析见长的当代批评还是有着一些明显的不同,倒是和重整体印象、重直觉感悟的传统批评更为接近。事实上,对理性透视和逻辑严谨的有意忽视,重视批评家的主观印象恰恰是印象主义文学批评的核心所在。李健吾印象主义批评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与中国传统批评的近似,无疑为厚爱传统的李健吾自觉承继传统自然批评思想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李健吾特别看重批评者“自我”,认为这是批评者个性、气质、才华、修养、对艺术的感悟和见解的自我表现,要求他们“必须抓住灵魂的若干境界,把这些境界变成自己的”[53]。李健吾立足于他的审美理想和艺术感受,在综合古典文论和西方近现代自然观基础上进行创新,从创作、欣赏、批评等不同层面系统而深刻地展示了他的“自然”的文学批评观。这一观念不仅赋予了传统自然批评在现代批评语境中得以继续存在的理由和依据,还丰富、拓展了传统自然批评观,使之具有了真正的现代内涵,如对“不自觉”“热情”“可爱”“有趣”“冲突”等与“自然”关系的阐述。虽然胡适、周作人、沈从文、废名、梁宗岱、朱自清、梁实秋、唐湜甚至茅盾、成仿吾等在批评中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传统自然批评观,但却没有一个像李健吾这样有意识地把传统这一批评观的丰富内涵拓展、深化,并巧妙地应用于批评涉及的众多领域之中。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西文论互鉴[54]批评语境中最有个性、最有风格的批评家[55],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以其对于“自然”这一术语的运用,不仅使传统的自然批评观念复活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和实践之中,而且诠释了这一观念在李健吾的印象主义批评中,不但不是可有可无的“他者”,反而更是主体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