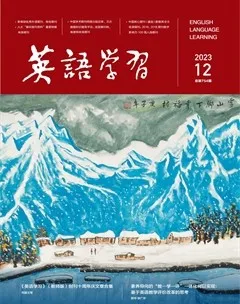后人类主义世界中的“科技病”
——评石黑一雄小说《克拉拉与太阳》*
2024-01-24马坤豪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马坤豪 南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张俊萍 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引言
石黑一雄是当代日裔英国作家,曾获得1989 年布克奖、2017 年诺贝尔文学奖、大英帝国勋章、法国艺术及文学骑士勋章、首届大益文学双年奖等多个奖项,代表作有《长日将尽》《上海孤儿》《莫失莫忘》等。《克拉拉与太阳》(KlaraandtheSun)是他的最新作品。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小说主人公AF 克拉拉(陪伴机器人)邂逅了身染“科技病”的主人乔西,并设法拯救她。正当乔西的母亲克里西选择放弃救治乔西而用机器人替代她时,克拉拉仔细观察,不断思考,发现可以借助太阳使乔西获救。于是,她摧毁了库廷斯机器,解放了太阳的力量,最终拯救了乔西。石黑一雄的《克拉拉与太阳》体现了后人类主义的思想。早在20 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人们就围绕着电子人的话题热火朝天地讨论起来,并形成了一种理解——身体是一种商品,可以通过现代技术塑化,对生物进行改造将会是未来的一种趋势,这种态度通常是由“对人类状况本身的厌倦”引发的(Baillie &Casey,2005)。而这种思想就像一种病一样,企图颠覆“肉体的人”的意义。针对这种声音,正如哈桑(1975)所提到的,人类形态——包括人类的愿望及其各种外部表现——可能正在发生剧变,因此必须被重新审视。当人类主义进行自我转化,并寻求与机器建立合理的联系时,后人类主义的进程也就开始了。就理性的话题,海德格尔对曾经理性比感性高级的论调提出质疑,他认为理性(rationale)是动物也拥有的一种比较低级的精神物质(Heidegger,1977);对于“具身化”的话题,后人类的建构观念并不要求他的主体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电子人(cyborg),无论身体是否受到干预,认知科学和人工生命等领域出现新的模式,都必然包含着一个被称为后人类主义生物学上依旧如故的“万物之灵”(海勒,2017);关于人类的地位,他们主张把人当作世界中的普通一员,人类不是自然界的例外,限制人类对于世界的过分探索,去人类中心才是真正保护人类的手段(Kumm et al.,2019)。
乔西病情的溯因:理性至上的荼毒
乔西的疾病是贯穿《克拉拉与太阳》始末的重要线索,她的病是人为的“基因提升”而造成的,而它的产生正是由于人们陷入了理性主义的泥沼之中,渐渐地忽视了人的感性价值。随着理性运动不断带来科学技术上的突破,有人开始认为人是一种高于动物的、有高度概括能力和推理能力的理性生物。后人类主义者们却发出不同的声音:人具有动物的一面,但是理性本来就存在于动物身上,所以其实理性也只能反映人的动物性,而非人性(Heidegger,1979)。文中乔西的母亲克里西和乔西也为理性至上所困扰。
首先,对于克里西而言,她作为乔西的监护人,在乔西是否进行基因提升的选择上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她却未能处理好理性与感性统一的问题。在做决定的时候,克里西为理性所裹挟,坚定地选择了基因改造,而非从乔西的身体出发进行考量,展现母亲应有的关爱。在乔西病危的时候,克里西对里克(乔西的男朋友)说,“我刚才在想啊,此时此刻你会不会感觉自己是赢家,感觉自己或许笑到了最后”(353),“她下了大注……结果输了”(354)。即便到了乔西病入膏肓的时候,母亲居然依旧把“基因提升”和“赌博”进行类比,忽视了人的生命和未来比赌桌上的筹码重得多得多。事关女儿的性命,母爱这种崇高的感情竟不知去向,令人黯然神伤。克里西经历过萨尔(乔西的姐姐)殒命之后,为什么没有为了乔西的健康而停止基因提升?如果说大女儿的去世是无可避免的悲剧,有不可抗力的因素,那么在小女儿乔西面对基因提升的选择之时,丧女之痛为什么没有警示克里西?由此可见,她没有处理好感性与理性的统一。
其次,面对全社会疯狂吹捧的基因提升,乔西也无力做好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乔西说了自己做决定的话,她也依旧会选择基因提升这条道路。饱受病痛摧残之际,她的理性战胜了名为自爱的感情。乔西借里克之口说“关于这个接受基因提升的问题……她说她会和你做出一样的选择”(356)。让人吃惊的是,原本是基因提升受害者的乔西即便已经饱受病痛煎熬也依旧愿意接受基因提升,可见乔西对于自己的生命的珍爱已经完全被命名为“基因提升”的理性浪潮所打败。人与机器最明显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人是有感情的。而如果基因提升只是打着提升人类的幌子,专注所谓的身体和脑力提升而忽略了人类最基础的情感关怀,那么提升后的人真的会获得幸福吗?乔西和萨尔就是血淋淋的真相。
再次,人们忽视了理性并不具有绝对性。小说中人们坚信基因提升代表着进入一流大学和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并奉其为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不免让人怀疑,这份理性是绝对正确的吗?基因提升者的死亡这一凿凿铁证无疑给了不少人一记耳光。基因提升者的身体健康必然是要放在考虑范围之内的,然后结合各方面的要素(如成绩提升、思想道德培育等),才能对基因提升是良方还是毒药作出一个客观公正的判断。可见理性本身不具有绝对性,任何所谓理性的观点都需要不断的勘验。而小说中最令人感到恐惧的是萨尔的死亡,它并没有给基因提升问题带来多么大的反响,即便是痛失爱女的克里西,也依旧对基因提升情有独钟,最终造成了乔西得病的悲剧。
总而言之,这种理性至上其实反映了以下两个问题:其一,忽略了感性的价值,未处理好感性和理性的统一;其二,忽视了理性不具有绝对性这一事实。文中克里西和乔西本人都没有处理好以上两个问题,他们对于乔西的基因提升都负有责任。若“理性至上”思想的顽疾无法根除,乔西的悲剧会在任何人的身上发生。
乔西病情的应对:科技建构中“具身化”的思考
乔西之病源于基因提升技术,因而治病也必然离不开科技。在科技高度发达的后人类主义世界里,人的身体结构可以为机器所改造,人的主体性也随之产生动摇。对于人的身体能否被技术改造,小说中的人们认为可以利用它来重塑人类的状况,克服人类的生理限制,使那些想成为“后人类”的人成为可能。至于工具是自然的还是非自然的则完全无关紧要。小说中,人们就是否采用机器替代乔西的肉身展开了激烈讨论,最终乔西身边出现了三种声音。
首先出场的是人文主义的守卫者,他们人数众多,主张守卫“具身化”,反对将精神置于肉体之上,承认并赞扬“肉体的有限性是人类存在的一种状态”,认为人的生命深植于极为复杂的物质世界,绝对不能用机器取代肉体的存在。其代表是梅拉尼娅管家、里克以及里克的母亲海伦。这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以肉体的乔西为中心,对最新的技术持排斥的态度。他们最初都对克拉拉怀有明显的敌意,谨慎地提防克里西会用机器人取代乔西。
当梅拉尼娅刚出场的时候,她会冲着身边的克拉拉吼叫:“AF,别再跟着我了,走开!”(61)最初,读者可能对于她这种没来由的火气感到困惑,渐渐便会发现她的所有行为都是想保护那个正在逝去的千金小姐,并提防着克拉拉取代乔西,她是乔西的守护者。当克里西想带乔西去见卡帕尔迪的时候,梅拉尼娅害怕克里西会用机器人来取代乔西,所以着急地对克拉拉说道:“AF,你看紧了……不然乔西小姐会出大事。”(221)由于陪同乔西去见卡帕尔迪的请求遭拒绝,她担忧地喊道:“我想和乔西小姐一起去,太太说没门。她要带AF。真搞不懂……你尽全力,AF。我俩一伙的。”(221)她守卫着的是有血有肉的乔西,是“具身化”的乔西,而非拥有乔西容貌的某种物件。
里克是乔西的童年玩伴和恋爱对象,他十分害怕克拉拉会取代乔西,因为那将不再是那个与他相伴至今的女朋友了,所以他说:“可惜(克拉拉的)许多事情都会妨碍(乔西与里克的)友谊。”(77)他清楚地认识到友谊或者他与乔西的爱情是具体的,是肉身的爱情,他所爱的绝非一个冰冷的空壳。
海伦并没有直接说要守护乔西的“具身化”,但是当谈及萨尔的机器人替代品时,她形容机器人是“看上去像萨尔”;而当里克说海伦把机器人认作萨尔的时候,她则会正色反驳:“萨尔去世了,那是一场巨大的悲剧,我们不会拿愚蠢的玩笑玷污她留给我们的记忆。”(186)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相信,对于用机器人取代乔西一事,海伦肯定也会采取反对态度。值得一提的是,海伦和儿子里克都被人视为“英国人”,一方面是由于口音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是“精神上的共同体”(周丽秋,2021),即都具备保守的性格特点,象征着他们是传统的人权捍卫者。
乔西身边传统的人文主义守卫者强烈地反对用机器人取代活人的反“具身化”思潮,但,也只能止步于此。对于机器人和科学技术的抗拒,使得他们在乔西身边扮演的更像是一个守护者而并非解救者的角色。
对待技术的第二种态度来自技术狂热者的坚实拥趸。克里西和卡帕尔迪先生是反对“具身化”的代表人物。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发现科技能代替人完成很多事情。因此有人认为只要能维持人类的行为和活动,机器人也可以代替人类存在。“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种行为是对于人性(human nature)的践踏,‘人不再为人’(cease to be human )”(法兰多,2019:14)。克里西产生用机器人替代乔西的念头至少有三次表现。第一次,乔西要购买克拉拉作为自己的AF 时,克里西要求克拉拉回忆乔西的长相和动作,最后的测试则是要求克拉拉模仿乔西的走路方式(20)。初读时,人们可能会误以为是主人在测试自己家机器的性能,而随着小说的推进,一个用机器人替代乔西的伏笔就此埋下。第二次,乔西病势加重,但是克里西没有选择陪伴在乔西的身边,而是让克拉拉陪她一起去看瀑布。在这场旅行中,克里西甚至要求与克拉拉进行亲子间的互动,要求克拉拉模仿乔西陪伴着自己(131—133)。第三次,则是克里西带着克拉拉去见卡帕尔迪,去实行把克拉拉“变成”乔西的计划。她的用意通过卡帕尔迪之口和盘托出:“我们不仅仅是要求你(克拉拉)模仿乔西的外在行为。我们还请你延续她,为了克里西,为了所有爱乔西的人。”“这真的就会是乔西。是乔西的延续。”(261)
卡帕尔迪先生是坚定的反“具身化”的人。作为一个科学狂人,他企图通过克拉拉对于乔西的模仿和认知,把这些记忆凝聚在一个芯片之中,再植入一个和乔西相似的机器人的体内,使得乔西获得“重生”。卡帕尔迪并不是乔西的亲人,所以他更多地会从科学技术层面而非亲情层面思考问题。卡帕尔迪帮助克里西更多是出于实验的需求,他已经彻底分不清现在有血有肉的乔西和那个躯体冰冷的机器人有什么区别了。通过克里西和海伦,我们得知萨尔的机器人取代计划失败了。萨尔的机器人疯狂地想逃跑,而克里西只能抱着那个冰冷的被她认为是女儿的机械生物。可见反“具身化”从技术层面上本身就是不可行的,更何况不管是克里西还是卡帕尔迪都忽视了乔西本人的意志,这是对伦理道德的蔑视。
卡帕尔迪和克里西都是反“具身化”的主要人员,他们相信只要意识和行为长存,肉体就可以被机械所取代。因此,他们才会说未完成的机器人是乔西的延续。他们针对乔西病症的方法只有一条,就是用机器人的躯壳取代乔西的肉体,让她以机器人的形式生活着。但是,如果深入剖析的话就会发现,这与其说是治疗,倒不如说是放弃,是逃避乔西病情恶化的事实,是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放弃了重病中的乔西。他们的行为不仅仅践踏了人权和伦理,而且具有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
最后一类人,便是乔西真正的救星——克拉拉与保罗(乔西的父亲)。他们都是后人类主义的信奉者。后人类主义指的是将人文主义的价值与其各种非人文的“他者”(机器)相结合。在西方的思想路线中,后人文主义标志着人文主义和反人文主义(反“具身化”)对立的结束,追溯了一个不同的话语框架,更肯定地寻求新的选择。即,后人类主义是对于人文主义的继承,如果人类可以无所顾忌地用机器的躯壳代替肉体,那是触犯了人文主义的底线,是在打着以人为本的幌子亵渎人类的尊严与身份。
克拉拉知道后人类主义是对人文主义的继承而非背叛。克拉拉多次尝试救助乔西,而这里的乔西是肉体的乔西。“我不介意损失了宝贵的液体。我情愿献出更多,献出全部,只要那意味着您会给乔西提供特殊的帮助”(345—346)。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克拉拉为了救助主人愿意奉献上自己的生命。救助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了乔西的彻底康复,而非用机器人替代乔西这种反人类的方式。
此外,克拉拉也意识到高科技世界中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不平衡问题。小说巧妙地设计了克拉拉惊人的观察能力。刚开始,她就敏锐地发现了阳光是机器人能量的来源这个设定(4)。紧接着她就观察到一个流浪汉和一条狗在晚上奄奄一息,却又在阳光沐浴下重获新生,由此开始揣测是否太阳对人类也具有疗愈作用。而在乔西病情不见好转的时候,她去了太阳落下的谷仓,在那里祈求太阳来救治乔西,并通过分析得出阳光的明亮度可能与库廷斯机器的污染有关的结论(300)。于是,为了拯救乔西,克拉拉设法与太阳达成契约,以摧毁库廷斯机器为代价来拯救乔西。在乔西危在旦夕之际,太阳照射到乔西的床前,乔西获救了。科技发展到极致的误区就是人类以为凭借科技可以为所欲为,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但是却从未反思过,在生产力条件低下的从前曾经多少次受到大自然的庇护。而阳光正是最具代表性的自然之物。克拉拉去向太阳求助也反映了去人类中心化的含义,即人类首先处于一个存在的环境中,只有回归于存在,倾听存在,人的本质才会本质性的发生(肖建华,2019)。
克拉拉意识到污染的机器才是万恶之源。库廷斯“先是发出一声尖利的呜鸣”,紧接着“三根短烟囱从它的顶篷里伸了出来,浓烟开始从那里面滚滚而出”。按照这种情况,人们应该采取一些措施。然而,“第二天,还有第三天,库廷斯机器依旧没完没了,白昼几乎变成了黑夜。”(37)这段文字象征着人们已经迷失在机器提供的便捷之中,却忘记了它会给自然环境和人类自身带来多少潜在危险。这也反映出乔西和萨尔因为基因提升得病,而克里西等人从未把问题反思到人类自身之上。
保罗的设定非常有趣。首先,他曾经是王牌科学家,对机器的运行甚至是破坏都有着极为准确的把控。在破坏库廷斯机器的时候,保罗提供了技术支持,准确地提出用机油来破坏这一方法。
其次,保罗更是个坚定的人文主义者。当保罗还在从事科研工作的时候,他并没有足够的时间顾全自己的家庭,以致最后离婚。而失业在使他失去光鲜工作的同时,又使得他的人性逐渐回归,他开始关注自己的女儿。所以他会说:“被替代使我得以用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世界,我真心相信这帮助我分清了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241)。他也怀疑可能女儿可以被取代,但是他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也许就是从他失业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坚定地站在维护“具身化”的乔西这边。当克里西试图把乔西留在实验室以获取更多数据的时候,保罗说:“乔西,我们现在就走。相信我,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257)这反映了保罗对于克拉拉变成乔西的实验毫无兴趣,坚定地守卫着“具身化”的乔西,因而保罗会成为帮助克拉拉破坏库廷斯机器的重要帮手。
最后,保罗可以与克拉拉共情,他会思考并执行克拉拉的建议。当克拉拉口头上说“对机器搞破坏”可以拯救乔西的生命,而又没有办法给出解释的时候,保罗沉稳地回答道:“那我们至少就试一回吧。”(278)通过这一细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开明的保罗,他没有摆出一个专业工程师和人类的傲慢,而是试着与克拉拉合作,最后利用P-E-G 9 溶液的成分摧毁了库廷斯机器,并且也间接拯救了乔西。
总而言之,只有克拉拉和保罗真正地把握住了后人类主义的精髓。人们既需要认识和运用机器,同时也需要守住人类身份的底线,守住“具身化”。显然克拉拉与保罗是对的。首先他们坚定了救治病重的乔西这个目标,而不是放弃她。其次,克拉拉借助阳光的力量,与保罗合力摧毁了万恶之源库廷斯机器,拯救了乔西。
通过以上三类人的三种选择,我们发现救助乔西,其实就是人们面对技术建构困局所作出的三种选择。有的人是顽固派,他们选择守卫传统的人文主义,排斥新技术。尽管他们能够守住为人的底线,但在面对科技疯狂的威胁时却茫然无措。第二类人是反“具身化”的狂热分子。这类人相信“人不是独一无二的东西”,因此肉身可以被任意替代,其结果自然是伦理遭践踏,人类的一切价值也被解构,机器人替代人类。而第三种就是后人类主义思想的探索者,他们学习、了解机器,并且本着以人为本的初心,更好地应对各种各样的挑战,适合在科技发达的后人类主义世界生存。
乔西治愈后的余波:后人类主义世界的隐忧
在小说结尾,乔西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看似皆大欢喜,其实危机重重。在乔西重获健康之时,三重隐忧也被悄悄地埋在了这个后人类主义世界。
第一,“科技病”一旦出现,便极难治愈。乔西的治疗离不开机器人克拉拉——一个热爱自己的主人而且具有出众观察能力的机器人,以及保罗——一个精通机器的父亲。只有二者通力合作才能成功治愈乔西。因此,乔西只是幸运的特例而已,更多的基因提升病者只能像萨尔一样等待死亡。
第二,乔西的治愈并未改变AF 机器人和基因提升加剧社会贫富差距的事实。小说中,当一个小男孩(羡慕想要机器人)可怜兮兮地看着克拉拉时,经理说道:“如果有时候一个孩子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你,带着怨恨或悲伤……一个那样的孩子,没有AF,一定会非常孤独的。”(13)AF 机器人作为陪伴孩子成长的最新产品,无法面向所有的孩子,只有少数家境优越的人才能获得。小说中有的贵妇还在饶有兴致地纠结选择B2 还是B3,而穷人的孩子却连拥有一台AF 的资格都没有。这在无形之中给予富人优越感的同时,也给穷人施加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然而,技术不仅给穷人带来精神上的痛苦,也堵塞了他们通过奋斗致富的道路。里克作为乔西的恋人正是这个时代的受害者。他既没有接受基因提升,也没拥有自己的AF,他的求学之路注定坎坷崎岖。首先,进入阿特拉斯·布鲁金斯大学,参加TWE(升学培训班)是必经之路,而成为TWE 的学员必须至少满足两个条件之一:要么接受过基因提升,要么付一大笔钱。但是,这简直是一个“第22 条军规”,基因提升历来就是被富人垄断的特权。因此,基因提升直接封锁了穷人通往顶级学府的道路。而里克如果想要进一步学习,就只能和其他未提升的学生争取百分之二的名额,不然就得成为一辈子的“下等人”。
里克的母亲海伦为他购买了(来自上一个时代的)“最好的教科书”,但这些书全都默认孩子的身边蹲守着一个导师之类的角色。这又间接导致“当他(里克)遇到一些他不理解的东西,而身边又没人跟他解释的时候,他就会灰心”(190)。因此,海伦才会请求克拉拉指点里克的学习。
里克的结局也非常现实,他没有选择进入阿特拉斯·布鲁金斯大学,而是尝试寻找一条新的道路。无疑,里克是不幸的,在一个机器主导的社会,他很难通过大学爬到社会顶端,实现阶级跃迁;而他又是幸运的,他在物理、工程类的领域很有潜力。可是,更多的基因未提升者资质平平,没有天赋。没有基因提升,也没有AF 机器人,他们比里克更加绝望。
第三,乔西的治愈并未引起人们对机器人的足够反思。随着机器人走入千家万户,“人与机器的反交流—交流”必然是人工智能时代中很长时间内的交流模式(陈昕,2020)。在乔西得救之后,克拉拉被克里西捧成了英雄,而沉浸在女儿康复喜悦中的克里西竟然说克拉拉理应(像人一样)得享善终,慢慢凋零,她终究是把克拉拉当成人了。而卡帕尔迪也并未因此放弃他的机器人替身计划。他在乔西康复后,表示想寻求克拉拉作为志愿者继续他的实验。可见,乔西是活了,但反“具身化”思潮并没有消亡,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关于如何对待机器人,恰恰是生病的乔西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在乔西与里克拌嘴时,克拉拉提议让自己代替里克玩“泡泡游戏”(填字游戏),但是乔西却回道:“我说,这行不通的。我不介意你旁听。可你说什么也替代不了里克的。门也没有。”(165)言下之意,这是只属于里克和乔西的游戏,即便克拉拉比里克更加能体察乔西的心意也不行。
在乔西晚上做到自己死亡的噩梦时,乔西也想要母亲的拥抱,而非克拉拉的拥抱。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乔西清楚“泡泡游戏”代表着情侣间的调情,想得到母亲的拥抱更是她对母爱的渴望,而这些绝非机器人能够替代。乔西在病重时让里克转述了她的话:“无论发生了什么,她都爱你(克里西),永远爱你,她非常感谢你能做她的母亲,她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换一个母亲,一次都没有。”(225)乔西理解后人类主义世界的意识(精神)包括感觉,情感,记忆和其他精神状态,而这一切都需要借助具体的身体传达出来(Pepperell,2003)。乔西认为肉体是边界,对待机器人可以友善,但是友情、爱情是人类的特权,绝不容机器人染指。
总之,乔西的“科技病”顺利治愈,让我们看到了三重隐忧。其一,“科技病”的治疗将难如登山;其二,科技的发展将会加剧贫富阶层之间的撕裂;其三,对待机器人的态度将会成为一个需要长期探究的命题。
结语
无论是理性主义的疯狂,或是反具身化的巨浪,又或是后人类主义世界的隐忧,都是过度的人类中心主义在背后操纵着一切。即,人类可以主宰世间万物的一切。然而,我们不是在克服现代性的局限适应力,而只是扩大了现代主义控制的幻想,因为它忽视了社会和生态的运转自有它独特的规律(Wakefield et al.2022)。“科技病”恰恰就是过度人类中心主义造就的恶果。
首先,理性至上反映了人类企图主宰情欲,是人类对自古以来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的一种执念。其次,“反具身化” 反映了人类主宰身体,坚信可以依照自己的意志改变自己的身体,反抗大自然的约束。最后,人类尝试左右后人类主义世界的方方面面:在主宰世界并利用机器创造科技产品的同时,也创造了更棘手的病毒;利用机器主宰人的上升通道,加剧贫富差距;创造机器人并自发地用它来取代人类自身,而不考虑这一举动将会对人类种族造成怎样的恶果。因此,去除过度的人类中心化是当今世界不可回避的问题。
小说给我们的启示是,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应该防微杜渐,时刻警惕过度的人类中心主义,只有这样,在步入后人类主义时代时才能做到心中有一道防线。“个体要立足当下,选择性‘遗忘’(过去的成就),从而进入建构新的身份”(刘杰,2020)。笔者认为,人们要防止过度的理性主义,认识到反具身化绝非是拯救人类苦痛的良药,后人类主义世界也有其自身的运转规律,而绝非人类自己可以随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