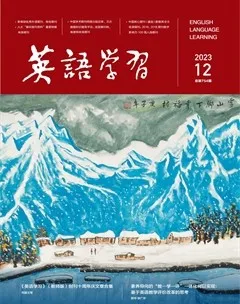四十载相伴同行:我的《英语学习》之路
2024-01-24武和平西北师范大学
武和平 西北师范大学
《英语学习》(教师版)不觉已经十岁了!此刻,我更愿意把时间线拉长一些,从我如何与《英语学习》结缘谈起,为这本既有历史积淀又散发朝气和活力的刊物送上真诚的祝福与祝贺!
我的英语学习生涯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高中毕业后,我被当地的师范学校录取,入学后做的第一道“选择题”是在“英语班”或“普通班”中作出抉择。也许是自己在潜意识里不甘“普通”,我懵懵懂懂地选择了“英语班”,虽然当时自己的英语几乎是零基础。没想到正是年少时期的这一选择,不经意间决定了我今后的职业生涯和人生道路。
我在“英语班”的第二年就订阅了刚刚复刊的《英语学习》。当时我的英语水平还很低,大多数文章都看不太懂,但有些栏目令我至今难忘。记忆最深刻的是北外刘承沛教授主持的刊物问答栏目。这一栏目虽然在每一期杂志的最后两页,却是我每次拿到杂志后最先阅读的。看得久了,慢慢就看出了一些“门道”——刘教授在解答来自全国各地英语爱好者五花八门的问题时,经常会告诉读者这个问题可以参考牛津学习者词典哪一页的哪一个例句。他的回答给了我一个“启发”——词典就是英语学习的“魔法书”,词典中的例句更像是解开英语学习之谜的“魔咒”,会查词典就能解决英语学习中的大多数问题。工作后,我就用自己的第一笔工资买了属于自己的牛津学习者词典。
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个乡镇中学当英语老师。这是一个基本上与英语绝缘的地方,当地几乎找不到任何与英语相关的资源。而《英语学习》这本杂志成为我眺望“英语学习”世界的唯一窗口,慢慢地《英语学习》就更像一位默默陪伴在我身边的师长,我会将一本薄薄的刊物反复翻看,将每一期都珍藏起来,到年末还会把当年的全部期刊装订起来,闲暇时间经常翻阅,大概直到我在90 年代又一次去外地负笈求学才停下来。如果说我目前在英语学习的道路上还有一点成就,那《英语学习》这位启蒙老师功不可没——她教会了我什么是“好”的英语,以及怎样才能“学好”英语。
2014 年,《英语学习》(教师版)诞生了!看上去似乎刊物的受众由英语学习者变为教育者,但我认为刊物的宗旨并没有变,因为国民外语能力的提升最终要靠外语教师整体能力的提升。新版期刊在网络时代应运而生,顺势而为,充分发挥网络媒体和纸质媒体各自的优势,通过微信群、公众号和视频号来传播文章观点,以“网”为媒,建立编者、作者和读者的联络通道。虽然是一本面向基础英语教育的“新刊”,但很快风靡全国,备受英语教师的青睐。
大概是在2015 年,编辑部约我牵头组织一些教师,就课标中有关“核心素养”的“文化意识”在《英语学习》微信群展开讨论。我当时邀请了自己英语教学生涯中结识的一些“故交”,如浙江师范大学的付安权老师和甘肃省民勤一中的王国己老师,也邀请了在《英语学习》微信群里“认识”但至今尚未谋面的“新朋”——人教社的陈力老师、时任浙江省教育评估院副院长的龚姚东老师、广州大学附中的陈晓云老师,还有一些“不期而至”的老师共同参与讨论。几位老师都对语言教学中文化教学有独到而深刻的理解,“聊天室”气氛热烈,吸引了很多英语教师前来“围观”。我们的讨论随后在当年《英语学习》发表,也引起了我对这一话题的持续思考。
在我接触的中小学英语教师中,很多教师对自己所从事的英语教育工作内涵的理解越来越狭隘,把“英语教育”等同于“英语教学”,又很容易把“英语教学”等同于“英语测试”,在教学过程中过分看中与“考点”直接相关的内容,对于英语课程的人文教化的功能越来越漠视,正如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所批评的那样:“只看见了工具,‘人们’没有了。”
我一直坚信,文化的核心是人。从文化的本义上来讲,文化就是一个“以文化人”的动态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外语课程中的文化教学,“文化”就不再是课标中的教学理念,也不只是教材中的文化知识点,更不是测试卷中的考点,而是以“人”为圆心和原点,通过“化人”来实现“育人”和“树人”的课程目标,将语言教学中的文化知识“内化”为个人的文化品德、文化自觉和内在气质,“外化”为对多元文化差异的尊重和理解以及对跨文化交流能力的获得。从这一意义上理解,文化教学的过程是一个提升国际理解精神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过程,是一个人的内在人格和外在行为的塑造过程,是一个在“自文化”和“他文化”交流与碰撞中提升跨文化意识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过程。
我个人虽然在20 世纪90 年代初就离开了中学教师岗位,忝列高校教师行列,但由于自己早年英语学习和在中学教学的经历,仍然心系基础英语教育教学,也非常关注其中的“文化缺位”现象。在与中小学英语教师有限的交往交流中,我发现了一个让人非常忧心的现实,那就是英语教育不断被“空心化”,不断被抽走“教育”的内涵——把语言教育简化为语言教学,再把语言教学简化为语言测试:凡是考试不涉及的内容,老师们大多选择“少教”或者“不教”;而与“树人”“育人”直接相关的文化教学,在很多英语教师眼中,恰恰属于可以“少教”或者“不教”的内容。如果说语言和文化如一对孪生子女,共同构成了语言教育中的“鸟之双翼”和“车之双轮”,那么脱离了文化内涵的语言教学就像“单翼鸟”和“独轮车”,学生最终学到的英语也是缺乏丰富文化营养的“畸形”英语。也正是基于这种担忧,每次编辑部就这一话题约稿,我都欣然应约,在《英语学习》上陆续发表的几篇相关文章也都是对这一话题的持续深入思考和探索。如果这种探索有助于外语教师能用“文化之眼”来发现语言教学中文化盲区,我将非常欣喜。
回望自己与《英语学习》四十年的缘分,深感《英语学习》不仅是我的知识伙伴,更是我思想的激荡者。感谢她陪伴了我整个教育生涯的每一步,也期待未来能够在英语教育这条道路上,与《英语学习》继续相伴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