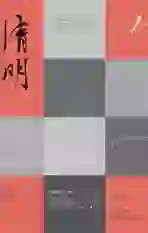在虚构中重建整体性的现实精神
2024-01-20吴长青
吴长青
2023年《清明》中短篇小说呈现了“严肃与通俗并行,写实与虚构同构” 的整体性特征。既有对时代命题的呼应,也有对传统人文精神的继承。秉持了《清明》多年来所坚守的“原创性、文学性和现实性 ”一贯主张。
一、重点作品围绕时代主题做出了积极的价值回应,体现了刊物的社会责任与时代引领作用。赵德发的中篇小说《美人鱼》(第1期)以当下最热点的“考公”作为主题,虚构了一个科级公务员家庭子女咸优优在“考公”失利后,偷偷应聘为一家海洋馆的美人鱼表演者。她面临的现实困境不仅伤害了一心期待她“上岸”的父母,尤其是担任科级干部的父亲,最后还失去了与她一起“考公”,但成功“上岸”的男友盛楼。
浪漫与现实的交织使得作品具有令人回味的美学价值。无论是为年轻时学俄语的二爷爷刻意安排一次与真实俄罗斯人做面对面交流的浪漫情节,还是对于从县级公务员岗位直接下派到基层工作的盛楼而言,他与咸优优的分开都是合理的现实。这也使得作品充满了一种理解式的温情。
同時,作品没有回避当下的敏感问题,尤其是外籍表演者因疫情原因未能按期续签合约,这也为咸优优担当大任提供了逻辑上的合理性。当然,小说提供的只是生活的一个侧面,因而只能在保持主导性积极向上的同时将其局限性缩小到最低限度。
杨少衡的中篇小说《此处有疑问》(第6期),同样选取了一个县级领导班子“我”——常务副县长董保山作为叙述视角,将县委书记梁越在车祸发生前的一周时间作为整个故事的剖面,将前任,甚至更前任领导与招商引资企业之间因利益扯皮遗留下且相当棘手的“土地”问题作为故事背景,既反映了当下一些地区政企之间的现实矛盾,也写出了企业家与地方官员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按理说,这种题材不仅敏感,而且在写作上具有一定的难度。小说《此处有疑问》将敏感题材处理得非常有艺术性,既体现了作家的政治敏锐度,又展现了其高超的艺术处理能力。首先,很好地处理了上下级官员之间敏感且复杂的人际关系,既没有使得作品陷入官场类型小说的窠臼,同时还创新了一种写法,很好地平衡了上下级以及同级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决策民主与庸俗官场生态的对立矛盾。其次,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建立了一种相对信任的互动对话关系,尤其是本土企业即熟人社会中复杂人际关系。小说将两种体系进行互文性的对照,作为当地的“我”,自然熟稔这两套运作模式,不是谁压倒谁的关系,也不是各走各道的自说自话,而是最终要走到一起,权衡各自的利益,这也使得作品具有了一定的超越意识。最后,作者以巧妙的艺术手段将所有疑似的“坏人”都成功地挽留在有可能堕落的边缘。比如梁越书记在车祸现场有疑似官场不洁的物证,甚至“我”与“班头”——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叶辰的非正常关系,本土企业家老谋深算的马镇不择手段,游走在黑白两道,等等。因此,作品将严肃性与通俗性以及文学性与可读性进行了高强度的融合。
同样,陈再见的中篇小说《烧衣》(第5期),让人读出了时代变迁中传统的穿透力——所谓“当代性”。作为故事的发生地,没有人知道鸭屎礁具体在什么地方,但是这不影响它本身所具有的震撼力。一句话,这是中国大地上任何一个不知名的地方都有可能发生的故事,也就是说它不是特例,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是的,这样的理解也许会将人带入到一片黑暗或者贬损他者的艺术世界中。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作者用了连续性的四次“反转”,因此产生了意外的效果。第一,这个叫“阿剩”的女子,尽管没有具体的姓氏,某种意义上呼应了她生活的那个地方,这个甚至连在地图上也找不到的犄角旮旯里。她能够与家暴她的丈夫周作甫离婚,显示了她具有一定的“现代”意识。当然原本阿剩这段婚姻就不具有合法性,十五岁时阿剩被母亲介绍给周作甫。二十岁时阿剩又成功逃脱了婚姻家庭,儿子斌仔被周作甫留在身边,等到她二十五岁再去看儿子时,她的情感再一次反转。第二,阿剩曾在当地渔场老板刘老大的食堂做过副手,当她再次出现在刘老大的渔场上时,她是有驾驶货车技能的女驾驶员,这也是她回到旧地生存的技能,更是令前夫周作甫意料之外的地方。因此,她具备了与周作甫谈条件讨要儿子抚养权的资本。第三,阿剩在用十万元钱作为交换条件换取儿子抚养权无效的情况下,开始用法律手段为自己维权,跳出了传统世俗的模式,这是阿剩逃离家庭长了见识,具有“现代”意识的又一次体现。第四,周作甫在得知自己不久将离开人世并直接向阿剩摊牌后,阿剩的态度再一次出现反转,周作甫在码头十多年省吃俭用,生病舍不得看病,最后将十万元留给了阿剩母子,将整个故事推向了情感的高潮。
也就是说,作者将传统与现代性贯穿作品的始终,没有脱离传统的现代性。还有,阿剩与郝明的离婚完全就是一种当代人的处理方式,这与两人穿梭在不同城市之间的跑车身份是吻合的;同时,这种现代性又不是静止不前的,它又具有一定的未来性。以斌仔为一代的新人,他们接受父母离婚的现实,也没有对回归的母亲表现出拒绝与回避,当母亲答应给他买电话手表时也表现出兴奋与满足,他们对这些当代新隐喻表现出乐观的接纳。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一种穿透在传统与现代的“当代性”恰恰是优秀作品所不可或缺的潜质。
二、对美好人性的发掘与讴歌,彰显了文学的抚慰心灵,净化灵魂的精神价值。陈蔚文以写女性情感见长,在其短篇小说《过云雨》(第3期)中,她不露声色地将情感节制住,甚至有些反情感的意味,颇有返璞归真之感。晓田作为一个从事导游职业的现代女性,见多识广,阅人无数,作品甚至还设定了一个特立独行的裴姐作为晓田的对照,但是晓田既没有裴姐夸张的人生方式,也没有表姐对生活的功利性选择。她的世界里除了与她一样的小镇青年——男友小柳之外,还有就是元彬托付给她收养的小猫——胖坨,这大概就是她情感生活的全部。
在《过云雨》的节制笔法中,会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道家,乃至也会将乌莜山中那只传说中的“白虎”与“道人”进行联系,那这个“道人”是谁呢?不用说,这个“道人”就是那个父亲,本在南方打工,后因工伤不得不举家迁回原籍的元彬。小说中的元彬就是晓田心中那个若隐若现的“白虎”。作家在有意无意地采取“意识流”的现代小说技法,将女性心中的另一种可能的遗存用若即若离的无意识表现出来。
晓田之所以能够抵挡住表姐的游说,留在家乡从事导游职业。又与裴姐的生活方式保持着一定距离,正是与这样洁净的生活态度有着不可分割的情感纽带关系。
最后,连元彬托付给她照顾的“胖坨”也成了她心目中从不曾出现过的“白虎”。
张惠雯的短篇小说《故人》(第3期),将一件网络舆情事件作为故事的前置,引入了“我”与少年的伙伴东诚的故事,可以说这是一个故事中嵌套着另一个现实故事的环形故事。
厚道、内敛的东诚在母亲心脏病突发离开人世后,他又承担起了照顾父亲的责任,在父亲去世后不久,两个姐姐指派证人说东诚不是父母亲生的,因此,父母财产——唯一的一套房产也就仅有二个继承人。面对着证人的指证,东诚接受了这个事实,于是做出了在外租房居住的决定。
张惠雯以亲情遭受金钱反噬的现实,对当下普遍存在的金钱拜物教提出了强烈批评。毋庸置疑,这种写法对东诚这样的美好人性寄予了肯定。同时,这种写实手法既呼应了加塞特对十九世纪欧洲文学整体得出的总结论——他们“把严酷的美学因素缩减到最低限度,让作品在虚构中涵盖人生的种种真相”,也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总体写实性的积极传承。
冯积岐的短篇小说《花样》(第4期),以极具画面感的快节奏将何玉琴、刘栓柱这一对苦命夫妻的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刘栓柱因为三轮农用车翻车压断了脊柱,造成下半身截瘫,从此卧床不起。何玉琴在“花样”旅馆从事保洁工作,目睹了若干不洁的性事,这也撩拨到她最为隐秘的心事。在这种无声的刺激中,何玉琴进而升华为一种捍卫道德的意识,对她个人而言,这是一种解脱,但遭到了旅馆老板朱慧莲以及乱性之人的反感。在迷惑与不解中,她又遭遇到丈夫刘栓柱不忍病痛折磨以及连累妻子所带来的痛苦而自杀。
作者从何玉琴的视角转到了刘栓柱的身上,这种转换已经不再是一种外在身体的视角,而是生命主体的转换。不可谓不是作者的一种高明之举。潜在的人性之美也就明明白白地完美呈现出来了。
曹多勇的中篇小说《结尘缘》(第4期),以国企陶瓷厂职工宗平和苏亚的全部生活作为时代缩影,记录并刻画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人的鸡零狗碎。虽然以虚构的手法,却达到了非虚构的艺术效果。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效果,在于作者刻意放弃了宏大叙事。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能有这样的不声不响,也算是一种奇迹。
反过来说,也只有在这样一种不显山不露水的环境中,或者说就是在一种平静的生活中,才能饱有这样安静的生活。属于个人的,带着个性的生活。貌似平淡,实则是全部生活的轴心所在。
而这种生活模式和记录手段在当时是落后的,保守的,也是不受人待见,甚至是被批判的。然而,如果不是这种安静,就没有宗平能够调动到文联,专门从事写作。在这层意义上,小说貌似在写个人的鸡零狗碎,实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观照社会与人构成的另一层联接的关系。我们不仅都在其中,而且相互作用着。
三、以细微的笔触揭示当代人情感生活的荒诞不经,引发人们对人性困境的关注。文学的存在本来就是人类精神生活二律背反的反映,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相容相生。因此,关注当代人的情感生活也是文学得以生成、生长的必然。小说作为反映时代,体现精神生活的容器,无处不在地起到一种积极的表现功能,以及作为一种反馈机制而存在。
姜贻斌的中篇小说《盯梢记》(第1期),写了一个物极必反的情感故事。李丽平与张晓平本是一对夫妻,丈夫张晓平极端、畸形的情感方式让妻子李丽平感到极度不适,张晓平不但不修正自己,反而变本加厉起来,竟然发展到盯梢和跟踪李丽平,这使得李丽平变得更加反感与厌恶,進而发展到出轨大学教授刘石桥。
李丽平与张晓平离婚后,本想与刘石桥结婚,可是等待她的却是刘石桥的不辞而别,整个故事并不复杂,甚至有些俗套。但是,其中所揭示的人生真相却是极其严肃而不含糊的。在为李丽平情感出轨和身体出轨提供合理性的同时,也引发了另一种可能的危机——任何一种逃避都有可能为下一场危机的出现制造新的空间。这也迫使我们正面迎接情感危机,决不为下一场危机提供借口和理由。
陈鹏的中篇小说《房子那么大的卡巴金》(第2期),以通俗故事的模式,拟真性讲述了一个执迷不悟的现代乌托邦徐老五迷恋马甸美女齐文雅的故事。卡巴金是一种良种马,这个徐老五自从患上深夜狂想症之后,就把研发卡巴金与追求齐文雅联系在一起。故事不乏具有一种现代主义意味,既有魔幻现实,也有一种浪漫主义风格杂糅其中。但就整体而言,全篇故事发生在一个封闭的时代,同样也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里。
反过来说,小说所要揭示的正是对这种封闭的疆域进行无情的批判,这样的疆域中诞生这样的狂想症患者是正常不过的,因此,小说的讽刺色彩也就直接对应着现实生活。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别现代”的现代模式。因为,在一种科学的名义之下,万能的科学恰恰误导了徐老五这样的执念者,他们以为科学是无所不能的,有因必有果的功利主义观念驱使着他们自己也无所不能。事实上,当将这种无所不能发挥到极致时,恰恰把人又推到另一个深坑当中去。
这样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因此,在这层意义上说,小说的批判性已经不言而喻。
陈武的中篇小说《恋恋的草原》(第2期),以民营出版业在作者与出版社三者之间的夹缝中的生存状态作为背景,以第一人称“我”暗恋设计师庞小朵作为主线,出其不意地将生态圈中的超强物种——国有出版社的资本大鳄,以及有着强势话语权的专家代表白老师的本相一层一层的抽丝剥茧式解剖。
由于资源的不均等以及由此造成的行业门阀制依然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痛点,甚至也是造成行业生态发展之所以枯竭的根源所在。小说颇具象征意义。
张学东的中篇小说《阿斯巴甜》(第4期),则是一篇反思小说。“我”与从事小学教育的妻子佟欣离婚后,情感一直游离不定。在佟欣因学生不按规则参赛遭到举报上门求助时,居然动了男性身体冲动的邪念;与同事黄莺又有着一种非是却是的暧昧;与开销售店的老方,既是对门邻居又是勾引自己妹妹顾乐的色鬼。在这三种复杂的关系中,最终选择了外调,以换取内心的平衡,并在这其中反思自己的种种“不彻底”。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设定,在生活、情感与亲情的网络中,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这也是人生的又一种真相。
纵观2023年《清明》中短篇小说,既有结构性的对照,也有题材多样性的特征,在艺术创新上同样体现出丰富多彩和风格各异的融合。当然,最具亮点的还属于对时代主题的快速反应,也对急遽演变的社会生活和个体情感细微观照的强烈干预,既体现了文学的时代晴雨表功能,同时也努力起到温暖人心和润物无声的治愈功能。一句话,批判的背后终究有阳光普照。
责任编辑 曾 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