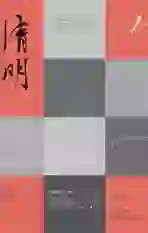次洛的可可西里
2024-01-20龙仁青
龙仁青
1
次洛家有一头毛色金黄的牦牛,被次洛叫作“黄牛”。那时候,次洛并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种牛就叫黄牛。直到上了学,他的老师扎门西在课堂上讲了牛的品种,次洛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除了牦牛,还有水牛、黄牛!次洛听扎门西老师讲完,觉得这个世界真是神奇极了,但一些疑惑也随之出现在他心里,他便怯怯地举起了手。
“次洛同学,你有什么问题吗?”扎门西老师即刻问道。
次洛怯怯地站起来,问:“老师好!我家有一头牦牛,是黄色的,我一直把它叫黄牛,我可以这样叫吗?”
扎门西老师听了次洛提出的问题,先是愣了一下,接着便笑了。同学们看到扎门西老师笑了,他们也笑了起来。扎门西老师笑的时候,只是把嘴角向两边扯开,露出白白的牙齿,并没有发出声来,但同学们却笑出了声,并且声音很大。那声音分明是在告诉次洛:次洛,你出洋相了。
“次洛同学提出的这个问题很好,现在我就给同学们讲一下牦牛的颜色!”扎门西老师边说,边抬手示意次洛坐下。刚才同学们的笑声让次洛很不好意思,脸也一下子红了。他急忙坐下来,低着头,不敢抬起来。
同学们看看扎门西老师,又看看次洛。听到扎门西老师说次洛提出的问题很好,同学们便安静下来,不再笑了。
次洛也慢慢抬起了头。
“同学们,咱们这儿把牦牛叫什么?”扎门西老师首先问同学们。
“诺纳!”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回答道。
“对!咱们这儿把牦牛叫‘诺纳’。同学们都知道,‘诺’就是牦牛的意思,那么,‘纳’是什么意思呢?”
“黑色!”同学们又争先恐后地回答道。次洛也回答了,但他的声音很小,淹没在同学们的声音之中。
“对!这说明咱们这儿的牦牛基本都是什么颜色的呢?”扎门西老师又问道。
“黑色的!”同学们再次争先恐后地回答道。这一次,次洛略微提高了自己的声音,但依然淹没在同学们高昂的声音之中。
扎门西老师所说的“咱们这儿”,指的是地处可可西里边缘地带的曲多县。这里紧挨着广袤荒凉的无人区,是牧草稀疏的高寒草原,平均海拔在四千五百米以上,广大,辽阔,无边的寂静统领着这里的一切。
“对了,咱们这儿的牦牛基本是黑色的!当然,也有黑白相间的花牦牛和像燃烧完的牛粪一样的青灰色牦牛,但很少。”扎门西老师认真地讲了起来。次洛心里想,马上就要讲到黄颜色的牦牛了,便紧盯着扎门西老师,满眼都是期待的目光。
“不过,并不是说,咱们这儿的牦牛是黑色的,世界上所有的牦牛都是黑色的!“
“还有黄色的!”扎门西老师的话音刚落,次洛忽然突兀地说了这么一句,声音虽然不大,却把扎门西老师的话给打断了。
扎门西老师便朝着次洛看去。
同学们都在认真听讲,教室里很安静,次洛忽然冒出来的这句话先是让同学们愣了一下,接着便笑了起来。
次洛的脸又一下子红了,他急忙低下头。
“次洛说得很对!”扎门西老师看看满脸绯红的次洛,又看看同学们说,“不过,在说到黄牦牛之前,我要先说说白牦牛!”
“拉雅!”扎门西老师刚说完这句话,就听到有位同学高喊了一声。声音是从次洛的后方传来的。同學们先是朝着次洛看去,以为像刚才一样是次洛发出的声音,但显然,这一次不是次洛。次洛和同学们都循着声音转头看去。次洛的后面有五六个同学,他们也转头往后看,但他们的后面并没有什么人,是教室的后墙。
扎门西老师随着同学们的目光向次洛后面的那几个同学看了过去,他也不确定刚才的声音是谁发出来的,便说:“刚才这位同学说得很对。那么,同学们,你们知道‘拉雅’是什么意思吗?”
同学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怎么回答。
扎门西老师的目光从所有同学脸上扫过,好多同学碰触到他的目光便低下了头。扎门西老师的目光再一次从同学们脸上扫过,所有同学都低下了头。
扎门西老师摇摇头,又点点头,说道:“看来同学们都不知道‘拉雅’是什么意思,那么,我来告诉同学们。”
“‘拉雅’是神牛的意思!”扎门西老师说完,停顿下来,等着同学们的反应。
同学们似乎并没有听懂老师的意思,依然低着头,没有做出反应。
教室里一时很安静,能听到同学们起此彼伏的轻微的呼吸声。在同学们轻微的呼吸声之上,盘旋着扎门西老师粗重的呼吸声。那呼吸声忽然拉长,轻轻地叹息了一声。随着这声叹息,同学们的呼吸声忽然变得零乱起来,但依然是轻微的。
这时,扎门西老师转过身去,拿起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拉雅”两个字。
“同学们请看黑板!”扎门西老师说。
一直低着头的同学们都齐刷刷地抬起了头。
“请同学们念黑板上的这两个字!”扎门西老师又说。
“拉雅!”同学们开始争先恐后地念着,接着便变得异口同声,整齐,就像是在敲击着节奏鲜明的鼓点。
扎门西老师做了一个暂停的手势,同学们的声音便齐刷刷地停了下来。
扎门西老师接着讲了起来。
“同学们!”他说,“刚才我说了,‘拉雅’是神牛的意思。咱们这儿把白牦牛叫作‘拉雅’。这是因为咱们这儿白牦牛太少见了,很珍贵,就像人群里忽然出现了一位神仙一样,所以就把白牦牛叫作‘拉雅’。”
同学们都认真地听着。
扎门西老师又说:“但并不是说,咱们这儿的白牦牛少,别的地方白牦牛也很少。”扎门西老师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就在离咱们这儿很远的祁连山深处,有一个古老的部落叫华锐,那里是白牦牛的故乡。如果你到了那里,会发现那里的牦牛基本上都是白色的。在那里,如果忽然出现一头黑牦牛,人们反而觉得很稀奇。”扎门西老师说完这句话,自己先笑了,同学们见扎门西老师笑了,也跟着笑了起来。在众多的笑声里,次洛的笑声很悠长,一下子凸显了出来。
“次洛同学,你是不是觉得很好笑呢?”扎门西老师问次洛。
次洛从座位上站起来。这一次,他不再是怯怯的样子,而是变得自信了许多。他止住笑,说:“老师,我想起了一群神仙里忽然出现一个人!”说完这句话,次洛又咯咯地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听了次洛这句话,扎门西老师大笑起来。
同学们看到扎门西老师笑了,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一边笑,一边看着次洛。这一次,同学们发出的不再是看次洛出洋相的笑,而是带着一点儿欣赏和羡慕的发自内心的笑。
次洛看到扎门西老师和同学们为自己的一句话笑了这么长时间,心里也很高兴。他一直站着,等到扎门西老师和同学们都笑够了,逐渐停下来,他又说:“老师,就像是一群扎门西老师里只有一个学生!”
扎门西老师听了这句话,先是愣了片刻,接着又哈哈大笑起来,同学们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在欢乐的笑声里,下课铃忽然响了起来,扎门西老师便止住笑,并向同学们做了一个暂停的手势,同学们的笑声也渐次停了下来。扎门西老师宣布说:“下课!”
“起立!”当班长的同学喊了一声,同学们便站起来,齐声说:“谢谢老师!”说完,向扎门西老师鞠了一躬。
扎门西老师向同学们鞠躬还礼,正要走出教室,次洛忽然说:“扎门西老师,您还没有讲黄牦牛呢!”
扎门西老师再次一愣,接着又哈哈大笑起来,站着的同学们也跟着哈哈笑。“耽误同学们一两分钟时间,我再按照次洛同学的要求,给大家说说黄牦牛!”扎门西老师示意同学们坐下,等安静下来之后,说,“我刚刚说了,黄牛是牛的一个品种,跟牦牛完全不一样,所以,严格地讲,黄色的牦牛是不应该叫黄牛的!”
“那黄色的牦牛应该叫啥呢?”扎门西老师刚说完,次洛便问道。
“黄色的牦牛,应该是金丝牦牛!”扎门西老师说。
“哇,金丝牦牛!”同学们听到这个名字,都不由得叫了起来。
“金丝牦牛是一种非常珍稀的牦牛品种,比咱们这儿的白牦牛还珍稀。”扎门西老师接着说。
“哇!”同学们又叫了起来。
“在咱们可可西里,有野生的金丝牦牛,但数量很少,全部加起来也不超过三百头,这也是全世界野生金丝牦牛的数量!”扎门西老师说,“次洛家有一头金丝牦牛,那可真的很珍稀,也许是金丝野牦牛的后代!”
“我阿爸也这么说!”次洛听了,立刻欣喜地说。话还没有说完,同学们再次“哇,哇”地大声喊叫起来,并都看着次洛,这让次洛有些不好意思,但他的心里美滋滋的。
“下课!”扎门西老师再一次大声宣布,深深鞠了一躬,便走出了教室。
教室里响起一阵杂乱的声音:桌椅被移动时与地面刮擦的声音、人与人碰撞在一起喊痛的声音、东西掉落在地上的声音……同学们喊叫着,向次洛扑了过去,很快就把次洛压倒在地上,不大一会儿,次洛的身上就摞了好几层人。
2
地处可可西里边缘地带的曲多县虽然地域辽阔,但它的县城却很小,整个县城只有一条主街。主街正中有高大门楼的是县委县政府,街道两侧鳞次栉比地排列着几家商店、饭馆什么的,都挂着汉藏两种文字的门头和牌匾。几幢楼房夹杂其间,从门牌和外观可以看出是医院、邮局、公安局什么的。马路上没有红绿灯,但依然车来车往,偶尔也会有牧民骑着马儿旁若无人地穿梭在汽车之间。整个县城看不到一棵樹,因为这里的海拔已经超过了“树线”,不适合树木生长。
在县城周边方圆一百多公里内,散乱地分布着一些乡镇和村社。说是乡镇和村社,其实就是一片片人烟稀少的荒芜草原,牧民们的帐篷更加散乱地分布在这里——在某一片草地,或某一个沟壑里,忽然冒出一顶孤零零的帐篷,帐篷顶上炊烟袅袅,氤氲出些许生机。帐篷周围,一些牦牛和藏羊在散乱地啃食着纤维粗硬的牧草。比如,次洛家就住在一个叫“哲茂隆哇”——棕熊沟的地方。据大人们说,早年这里有棕熊常常出没,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名字。偶尔牧民们会在自己的帐篷周围种一些燕麦或青稞。这些小片种植的庄稼,自从播下种子,牧民们就不再侍弄了,完全靠着天年。天年好的时候,牧民们也会收获一点点粮食,但更多的时候,燕麦草或青稞刚刚长出青绿的茎叶就被一场寒霜给打倒,再也不生长了。牧民们并不会因此感到气馁,虽说牧民们没有收获粮食,但牛羊过冬的牧草已经有了——把那些遭了霜打而不再生长的茎叶收集起来,刚好用来给牛羊过冬食用。一旦发生雪灾,这些枯草一样的茎叶就更加派上了用场。
次洛所在的学校,坐落在曲多县县城的城郊,是一所寄宿制小学。学校的学生们,他们的家就掩映在这些大地山川的褶皱里。这些学生们离家很远,交通不便,平时周末放假都来不及回一趟家。学校便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假期制度——周六周日照常上课,把周末的假期积攒下来,到了每月月末,一次性放假六天。这样,所有的学生都可以从容地回一趟家,再从容地返回学校。
学生们把这样的假期叫“月假”。
次洛一直盼着“月假”的到来。
就在前几天,县委县政府的干部到次洛家所在的“哲茂隆哇”去“下帐”,次洛的阿爸就让他们捎话给次洛:家里的“黄牛”生下了一头小牛犊,小牛犊通体黑色,只有两只耳朵之间的额头上有一块三角形的白毛。这样的牦牛,牧民们把它叫作“嘎娃”。次洛得到这个消息,心里生出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一方面,这个消息让他乐开了花。他想立刻回到家里,看看“黄牛”,看看它的小宝宝“嘎娃”。另一方面,他难以想象“黄牛”已经成了阿妈。在他的心里,“黄牛”还是一头小牛犊呢。他们曾经一起度过一段童年时光。如今,他依然还是个儿童,而“黄牛”已经成了阿妈,已经有了自己的宝宝!
他至今记得“黄牛”出生的那一年。
那是个乍暖还寒的初春。
而这个初春的故事,要从初春之前的那个寒冬说起。
那一年的冬天很冷,十月初就下了一场大雪。茫茫大雪覆盖了整片草原,牧民家的牦牛和藏羊都吃不上草了,只能把牛羊都关在圈里,每天给一些饲草饲料,等待着冰雪融化。好多牧民家缺少草料,牛羊死掉不少。还好次洛家储备了去年种在帐篷周围的燕麦草,他家的牛羊艰难地挨过了那个冬天。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次洛家的一头母牦牛忽然失踪了。那是一头被家里人叫作“断角”的黑色母牦牛。
这头母牦牛之所以叫“断角”,是因为它右边的犄角断掉了,只剩下左边的一只。关于这头母牦牛“断角”,阿爸给次洛讲过许多故事,次洛至今还记得。
那时,次洛还不到一岁,他的阿妈也还在。
曾经在城里生活的阿妈喜欢在家里种花,她把草原上的野花移植到花盆里,摆放在帐篷周围。夏天,次洛家的帐篷便被绿绒蒿、龙胆花等姹紫嫣红的野花围拢着,让帐篷里的烟火氤氲在一片蓬勃的生机里。阿妈还在花盆里种上了蒜苗,每每家里吃手抓羊肉,阿妈就会拔下一些蒜苗,洗净切碎撒在手抓羊肉上,羊肉的味道一下鲜美不少。
那时,“断角”还是个两岁的“雅玛”(两岁母牦牛的称谓)。有一次,家里煮了手抓羊肉,正要上桌吃饭的时候,不知道“断角”什么时候来到帐篷附近。它把蒜苗当成了一簇葳蕤鲜美的青草,舌头一卷就把蒜苗吃了个精光。
“我的蒜苗!”阿妈喊叫着冲出帐篷,去追打“断角”,“断角”已经跑得很远,追不上它了。
还有一次,“断角”和家里的一头“纳玛”(用来驮运东西的牦牛)打架,“纳玛”扬起双角冲向了它,它却显得临危不惧,稳稳地立在那里一动不动。等“纳玛”靠近,扬起头上的犄角要攻击它时,“断角”把头一甩,一只犄角不偏不倚,精准地插进了“纳玛”的鼻孔。“断角”又乘势猛地甩了一下头,“纳玛”的鼻孔瞬间就给撕裂了。“纳玛”疼痛难忍,哞叫了几声,即刻转身灰溜溜地跑了。
“断角”却依然站在原地,两只鼻孔里不断喷出一股股热气,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断角”断了一只角的那一次,它把阿爸崭新的摩托车差一点儿弄成了一堆废铁。
阿爸是一位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做了许多救助藏羚羊的事儿,可可西里藏羚羊救护中心就给他配备了一台摩托车——也就是那一天,阿妈悄然走了,她去了天堂,从此再也没有回来。阿妈走后的某一天,阿爸第一次到自家周边的山里去巡山,黄昏时分赶回家里。阿爸骑着摩托车,向家里驰来,离家越近,摩托车的声音越大。可能是摩托车的声音吵到了“断角”,它“哞哞”叫了几声,便毫不犹豫地朝阿爸冲了过去。阿爸看到“断角”径直向自己冲过来,急忙弃车而逃,把还在嗡嗡作响的摩托车扔在了地上。“断角”跑到摩托车跟前,没再继续去追阿爸,扬起一双犄角,接着后撤几步,加足马力,朝地上的摩托车顶了过去。等到阿爸费了不少周折终于把“断角”赶走,摩托车浑身坑坑洼洼,惨不忍睹,已经不能骑了。“断角”的一只犄角也断了,正在流血,它的半张脸也被血染红了。
从此它便有了“断角”这个名字。也有人说,“断角”是为了教训阿爸,教训他没有把家里的女主人守护好——阿爸到藏羚羊救护中心领取摩托车的那一天,阿妈乘着次洛睡着,便走出帐篷去散心。就在这时候,她忽然看到一只孤独的小藏羚羊趴卧在地上,好像和母藏羚羊走散了,显得孤独无助。阿妈心里满满的都是母亲对一个需要帮助的孩子的慈爱,便向小藏羚羊走去。小藏羚羊看到有人向它走来,惊慌地站起来,慌不择路地朝前方跑去,那里是一片沼泽地。那片沼泽地,被当地的牧民们叫作“登母”,意思是魔鬼的眼睛。在牧民的描述中,那片沼泽地就是一头浑身长满眼睛的女怪——那一泓泓的湖泊就是女怪的眼睛——平时,这个女怪总是躺在污泥之中睡大觉,一旦有人或者牲畜靠近,她的眼睛立刻会幻化成陷阱。一旦掉到陷阱里,便再也不能自拔。阿妈看小藏羚羊离“登母”越来越近,一下子惊慌失措,一边不断喊着“快回来”,一边继续向小藏羚羊跑去,但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踏入了女怪设下的陷阱……据说,阿妈在最后时刻,大声喊了一声“次洛”。
牧民们说,“断角”之所以要去顶撞那台摩托车,是因为它觉得,它和它的同伴们失去女主人,就是这个突突乱叫的铁家伙造成的,所以它把所有的气都撒在了摩托车上。
这头名叫“断角”的黑色母牦牛,忽然就不见了踪影。
“是那些可恶的盗猎分子干的坏事儿!”刚开始,阿爸怀疑是试图偷偷潜入可可西里猎杀藏羚羊的盗猎分子发现盗猎藏羚羊已经不可能——所有进入可可西里的路口都有森林公安把守,许多民间环保人士加入了保护藏羚羊的行列,加上像阿爸这样的当地牧民也成为环保志愿者,如今的可可西里可以说是固若金汤。新闻里说,可可西里已经有十年没有枪声响起。盗猎分子发现无机可乘,又不甘心空手而归,就动起了偷盗可可西里周边牧民牲畜的念头——这样的案例已经发生过几起。
盗猎分子做得再隐蔽,总会留下罪恶的痕迹——这样的痕迹逃不过阿爸这样的环保志愿者的眼睛。那几天,阿爸骑着摩托车在周边山里巡山,并没有发现盗猎分子来过这里的痕迹,这才忽然意识到“断角”的失踪可能与盗猎分子无关,而是与这几天出现在这里的牦牛群有关。
这是一群由一头雄性金丝野牦牛为首领的牦牛群。那一天,阿爸看到它们时,那头金丝野牦牛正张扬着粗大的犄角,时不时地扬起尾巴,左突右冲地跑动着。它一路上围圈了许多母牦牛,赶走了对自己造成威胁的其他公牦牛,让母牦牛们的一切行动都在自己的视野范围之内。它自立为王,妻妾成群。
阿爸看到这群野牦牛时,它们正从次洛家后山的草地上走过。它们边吃草边走动,看似涣散,其实组织严密,目标明确,不大一会儿就看不见了。看来它们乘着太阳落山之前已经翻越了后山,向着可可西里腹地靠近了。
“看来,‘断角’是跟着野牦牛‘私奔’了!”阿爸自言自语说。
阿爸从此没再去找过“断角”。
刚刚学会走路的次洛對此一无所知,有关“断角”的故事,都是阿爸后来讲给他听的。
转眼,次洛三岁了。
就在次洛过完三岁生日后的一天,同样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断角”回来了!
阿爸和次洛是第二天才看到“断角”的。
太阳升起来了,刮了一夜的大风随之停息下来。呼啸了一夜的寒冷此时已经没有了肆意呼啸的张狂,它惧怕阳光,不敢目睹太阳的眼睛,在明媚的晨光里正仓皇逃窜。温暖一点点地回来了,随着太阳的攀升,天气越发地晴朗起来。
早起的阿爸吃完早饭走出帐篷,忽然看到,原本之前拴着“断角”的拴牛绳一侧,“断角”静静地趴卧在那里——那个地方整整空了一年。阿爸一出帐篷,“断角”也看到了主人。它侧头朝阿爸看了一眼,趴卧在那里,嘴微微地张开着,舌头吐到了外边,急促的呼吸声中,一股股白气在乍暖还寒的空气里稍纵即逝。“断角”瘦骨嶙峋,看上去十分羸弱,好像得了什么病。令人惊奇的是,在它的一侧,还趴卧着一头小牛犊。这头小牛犊浑身金黄,阳光照耀在小牛犊身上,形成了金光闪闪的轮廓,漂亮极了。
阿爸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他看到“断角”脖子上的“恰如”居然还在,也进一步证明了眼前的牦牛就是“断角”。
“恰如”是每一头家牦牛身上必不可少的东西,是牧民把牦牛赶回家后,用来把它拴在一个固定位置上的装置:一条牛毛绳环系在牦牛脖子上,绳子的下端系着一只用木头或牛角做的划儿,就像是主人佩戴在自己心爱的牲畜身上的一串项链。与之相配套的,是家里拴牦牛的绳子,也就是那个固定位置的顶端有个环扣,把牦牛脖子上的“恰如”划在拴牛绳顶端的环扣里,牦牛就拴好了。在可可西里边缘地带,“恰如”是区分家牦牛和野牦牛的一个最直观的标志性物品。
“断角”被野牦牛围圈,当了这么长时间的“野牦牛”,但它脖子上的“恰如”其实一直在强调着它家牦牛的身份。
阿爸顺手抓起“断角”脖子底下的“恰如”,把它拴在了属于它的拴牛绳上。“断角”目光迷离,似乎连抬起头来的力气都没有了。阿爸看着“断角”,又看着它身边金黄的小牛犊,恍然明白了它回家的原因。
“断角”做了阿媽,却发现身体不行了——或许是在一次争风吃醋的打斗中败下阵来,受了伤,或许是意外得了什么病。而就在这个时候,它的小牛犊出生了。它没有做好任何准备,一个小小的生命忽然就来到了它的面前,怎么办呢?为了让小牛犊活下来,“断角”想到了回家。就这样,它带着小牛犊,设法脱离了那个家牦牛和野牦牛混杂的牦牛群,向着家的方向赶来。“断角”知道,在荒芜的野外,虽然天广地阔,自由自在,不会受到“恰如”和拴牛绳的束缚。然而,一旦遇到不测或病痛,往往束手无策。如今它身体羸弱,随时有可能失去生命,到那时候,它的小牛犊也难以保命。所以,只有回到家里才可以让小牛犊活下来,即便它死了,小牛犊也会被主人养活。就这样,母亲的天性,让“断角”在过了一年“野牦牛”的生活之后,带着自己的孩子又回到了家里。
阿爸把“断角”拴好,便朝着帐篷呼唤次洛:“次洛,快出来!”
次洛很快就走出了帐篷,一眼看到了“断角”和它身边金黄色的小牛犊。
“哇,黄牛!”次洛大叫一声,径直走到了小牛犊跟前。他看到“断角”看着他,也看着自己的小牛犊,目光里满是平和的柔情。
从此,这头小牛犊就叫“黄牛”了。
3
放“月假”的头一天晚上,因为第二天大家要赶车,次洛和同学们早早就躺下休息了。躺在宿舍窄小的铁床上,次洛却睡不着,一心想着他家的“黄牛”和小牛犊“嘎娃”。“黄牛”都当阿妈了,这是次洛感到最为好奇最为惊讶的事情。想起“断角”带着“黄牛”回到家里的那个清晨,恍若昨日,但掐指算起来,“黄牛”已经三岁了,次洛自己也已经七岁多了。比他小四岁的“黄牛”,却已经当阿妈了,说明它已经是“大牛”了。次洛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儿。原本,他是想着问问扎门西老师的,但回家的兴奋冲昏了他的头脑,让他忘了问。这会儿他心里后悔起来,甚至有点恨自己了。为了安慰自己,他便想,等回到家里,问问阿爸,阿爸也许会知道。这样想着,心里就舒畅了一些。想“黄牛”的时候,当然也会想起它的阿妈“断角”,想起“断角”忽然从帐篷门口消失,只留下孤独的“黄牛”无助地哞叫着的那个早晨。
其实,那个早晨以后,“断角”就死了,就像次洛的阿妈一样。“黄牛”和次洛都成了没有阿妈的孩子。
那个早晨,当次洛在微冷的晨曦中睁开眼睛的时候,帐篷里静悄悄的。帐篷的火灶里,几块牛粪正在燃烧,没有明火,微微的火光潜藏在牛粪之中,似是等待着一个时机——只要再添几块牛粪,它就会再次燃烧起来,给帐篷带来温暖,照亮帐篷里暗夜留下的黑暗。
“阿爸!”次洛明明知道阿爸已经走出帐篷,不在家里,但他还是习惯性地叫了一声,并等待着阿爸的回应,就像往常一样。次洛当然不会等来阿爸的回应,他便自己爬起来,穿上鞋子,披上“擦日”羊皮袍,也没有洗漱,便走出了帐篷。
是一个晴好的天气,刚刚从东山顶上升起来的太阳就像是一个已经长大到了三岁的孩子,不再留恋东山背后那个暖暖的被窝,总是想着到外面去玩儿——这是次洛想象出来的,在他的想象里,太阳就像他一样——急不可待地攀升到了半空,躲在一朵白云的背后,偷偷地看着次洛。
次洛没有去看太阳,他一眼看到了“黄牛”,却没有看到它的阿妈“断角”。次洛立刻走到“黄牛”跟前,发现“断角”脖子上的“恰如”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系在了“黄牛”的脖子上。“黄牛”被拴在平时拴“断角”的拴牛绳上,阿妈不在身边,“黄牛”显得有些孤独,急躁。它显然还没有习惯被拴牛绳拴着的生活,不断地奔突着,嘴里发出短促的哞叫声,试图从拴牛绳上挣脱开来,去找它的阿妈“断角”。
“你的阿妈呢?”次洛对“黄牛”说。他蹒跚地走过去,抓住了“黄牛”脖子上的“恰如”,试图把“黄牛”从拴牛绳上解开,但次洛的手还很小,也没有力气,更没有解开“恰如”的技巧,加上“黄牛”不配合,“恰如”便没有解开。折腾了一阵,次洛累了,便放弃了解开“黄牛”的打算,准备返回帐篷,等阿爸回来,让阿爸帮着解开“恰如”。这时,身后忽然传来阿爸的声音。
“次洛,你干吗呢?”
次洛急忙回头,看到阿爸正从太阳里向他走来。
“阿爸!”次洛向阿爸迎了过去。
阿爸停下脚步,蹲下身来。次洛看到阿爸身后的太阳猛地一下抬高了许多,一下子拉开了与阿爸头顶之间的距离。等次洛走到跟前,阿爸便张开双臂,把次洛揽进了自己的怀里。
“阿爸,‘黄牛’的阿妈呢?”
阿爸欲言又止,不知道怎么跟次洛说。
“阿爸,‘黄牛’要去找它的阿妈,你把它解开吧!”
阿爸把次洛紧紧搂在怀里,轻轻吻了一下次洛的额头,说:“次洛,‘黄牛’的阿妈走了,它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次洛松开搂着阿爸的小手,一下推开阿爸的脸,审视地看着阿爸的眼睛说:“它去了天堂吗?”
阿爸点点头。
阿爸的这个回答,次洛不止一次地听过——
“阿爸,我怎么没有阿妈呀,我的阿妈在哪里呢?”那时候,次洛总是这样问阿爸。
问得多了,阿爸便跟他说:“阿妈去天堂了。”
“天堂在哪里啊?”
“天堂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是在天上吗?”
“是的……”
“在天上哪里呢?”
“等你长大了,我们一起去找。”
“那,阿妈会等着我们吗?”
“……会的。”
从此,次洛便记住了他的阿妈在天堂。
“‘黄牛’的阿妈会在天堂等着‘黄牛’吗?”
刚才,次洛的话让阿爸陷入了回忆,次洛的这句问话一下又把他拉回了现实,也一下触到了他内心的痛处。阿爸刚刚松开的双手再一次把次洛搂紧了,默默地点点头,次洛“哇”的一声,大声哭了起来。
“黄牛”没有了阿妈,与同样没有阿妈的次洛同病相怜。喂养还没学会吃草的“黄牛”就成了次洛每天要做的事儿。阿爸给了次洛一只用牛角做成的奶瓶——牛角一頭粗大一头尖细,中间是空的,阿爸在尖细的一头打了一个小孔,平时用酥油把小孔糊住,再从大的一头装满牛奶。用的时候,把小的一头塞到小牛犊嘴里,糊在上面的酥油就被小牛的舌头舔去了,里面的牛奶就不断流出来,流到小牛犊的嘴里。每天早晨,阿爸挤完牛奶,便先在牛角奶瓶里装满牛奶,交给次洛,次洛便拿着奶瓶去找“黄牛”。次洛第一次拿着牛角奶瓶给“黄牛”喂牛奶时,“黄牛”不习惯,甩着头,拒绝把牛角尖含在嘴里。次洛并没有放弃,不断把牛角奶瓶往“黄牛”的嘴里塞。忽然间,它似乎发现了什么,只见它张大鼻孔,不断地闻着牛角奶瓶,慢慢安静下来。次洛便乘机把牛角尖塞到“黄牛”嘴里,“黄牛”微微迟钝了一下,便吸吮开了,并且它很快就习惯了。次洛发现,每次给“黄牛”喂牛奶,它总是要用鼻子闻闻牛角奶瓶。每次,看着“黄牛”贪婪地吸吮牛奶的样子,次洛忍不住也想吃,就把牛角奶瓶从“黄牛”嘴里拔出来,放到自己嘴里,大口吸吮几口。“黄牛”便着急地把它的嘴蹭过来,与次洛抢夺牛角奶瓶。一牛角奶瓶的牛奶,就这样被次洛和“黄牛”一块儿吃完了。
从那以后,“黄牛”成了次洛的跟屁虫,次洛也喜欢跟“黄牛”一起玩耍。次洛家帐篷前的那片草地,成了他和“黄牛”的游乐场。次洛和“黄牛”经常玩儿的一个游戏就是“东嘎”。“东嘎”是抵牾的意思,也就是两头牦牛之间,或者是藏羊与山羊之间面对面角抵角相互顶撞——“东嘎”似乎发生在同类之间,如今“黄牛”的“东嘎”伙伴却换成了它的小主人次洛。
“玩‘东嘎‘了!”次洛看着刚刚吃完牛奶,正在草地上撒欢儿的“黄牛”,便朝它这样喊一声,然后趴在地上,朝“黄牛”晃一晃脑袋。“黄牛”即刻跑过来,用它的头抵住次洛的脑袋,开始互相推搡。“黄牛”把次洛推翻在地,次洛爬起来又把“黄牛”顶一个趔趄。次洛快乐的笑声和“黄牛”哞哞的叫声响彻在帐篷周围。
阿爸没去放牧或巡山的时候,便坐在一旁看着次洛和“黄牛”,大声喊:“加油,加油!”看他们彼此翻滚在地上,阿爸便开心地大笑起来。
次洛躺在宿舍床上,想着这些,不断涌出的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他不断用手去擦,他的脸上也沾满了泪水,但在他的嘴角却挂着一丝无声的笑。
次洛心里开始企盼夜晚马上结束,明天早点到来,刚刚还让他睁不开眼睛的瞌睡这会儿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4
学校放“月假”,次洛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赶回了家。
早晨出发的时候,次洛没顾上吃早饭,就直接坐上了长途客车。长途客车到了青藏公路的某一个路口,次洛下了车,又搭乘上一辆大货车。在大货车上次洛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快要下车时,大货车司机因为次洛喜欢听他唱歌,就要给次洛送点东西。司机从一个帆布包里拿出一包方便面和一张CD,却把CD给了次洛,把方便面又装回了包里。次洛拿着CD,真想用CD把那包方便面换过来。一路上,次洛都在安慰自己的肚子:等到了家,一定要好好吃一顿。他甚至想,如果阿妈没有去天堂,知道他放了“月假”回来,一定会给他做好多好吃的:那种叫“馨”的藏式点心,放了好多新鲜酥油的糌粑,当然还会有手抓肉、血肠、肚包肉……
次洛到家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从昨天晚上在宿舍里吃了一碗方便面,一直到现在他一整天什么也没吃。正在等着“好好吃一顿”时,阿爸为他煮了一包方便面。次洛看着在火灶一侧忙碌的阿爸,想象中的阿妈消失不见了,随之消失的,当然还有那些好吃的。
或许是饿过头了,或许是想象中的阿妈给他做了太多好吃的,他对阿爸的方便面并没有多少兴趣。吃方便面时,他没有像还在路上时想象得那样狼吞虎咽。他很正常地吃完了方便面,便对阿爸说:“阿爸,我要去看‘黄牛’和‘嘎娃’!”
“这么晚了,明天再去看吧。今天你走了一天的路,也累了,早点休息。“阿爸说。
听阿爸说完这句话,次洛便没再坚持,他想,等明天早上早早起来去看它们。
早上从学校出发时,次洛特地穿上了阿爸专门为他做的“擦日”羊皮袍。这会儿,他把“擦日”羊皮袍脱下来,躺在火灶一旁的一条牛毛毡上,把那张CD随手扔在一旁,便躺下了。阿爸在火灶里的牛粪火上加了一些羊粪,帐篷里的火光即刻暗淡下来——牧民帐篷火灶里的牛粪火,除了取暖和做饭,到了晚上还有照明的作用。牛粪火用羊粪掩埋起来,就会延缓牛粪燃烧的时间,保留火种,同时也预示着到了晚上睡觉的时间。
次洛和阿爸便在越来越暗淡的火光中睡下了。其实,那一晚,他们两人各怀心事,谁都没有睡着。次洛想着“黄牛”和“嘎娃”,自然而然想起了自己的阿妈。就像之前的好多个夜晚一样,他想象着阿妈的样子,想象着阿妈在帐篷里忙碌的情景。阿爸也想着“黄牛”和“嘎娃”,自然也想到了自己的妻子。妻子的离去是他心里最大的伤痛,如果妻子还在,他和次洛该有多幸福啊!他更焦虑的一件事儿是,明天,怎样让次洛看到“黄牛”与“嘎娃”,特别是“嘎娃”。
在帐篷的天窗“喀次”里,满天的星星正眨着眼睛。次洛和阿爸静静地躺在越来越深的黑夜里,除了轻輕的呼吸声,再也没有其他的声音传来。偶尔,从很远的远处,传来一声狼嚎声,低沉,悠长,充满了说不清楚的哀伤。
清晨,从天窗“喀次“射进来的阳光叫醒了次洛。次洛睁开眼睛,发现帐篷里安安静静的,阿爸不在帐篷里,火灶里,几块牛粪掩藏着微弱的火焰,正在默默燃烧着。
“阿爸!”次洛习惯性地叫了一声,就像往常一样,帐篷里清晨的寂静回应了他。次洛从羊毛毡上爬起来,穿上鞋子,披上昨日脱下的“擦日”羊皮袍,也没有洗漱,便走出了帐篷。
太阳已经高悬在东山顶上,这会儿正在一朵白云的背后探头探脑地看着人间。晨风吹过,一股凉意袭来。看着眼前的情景,次洛恍然想起了他三岁时,“黄牛”的阿妈“断角”离开“黄牛”的那个早晨。
次洛急忙朝拴牛绳看去,那里曾经是“断角”的位置,如今那里也是“黄牛”的位置,但那里空空如也。
次洛正在纳闷儿,就看到阿爸从太阳里走来。强烈的逆光勾勒出了阿爸的轮廓,让他成了一道剪影——这个早晨,真的把他三岁时的那个早晨复制粘贴过来了。次洛惊讶地愣怔在那里。这时,阿爸已经走到了他跟前。
“次洛,你看这个。”阿爸说着,从怀里拿出一样东西递给次洛,“你还认识这个吗?”
“牛角奶瓶!”次洛从阿爸手里接过牛角奶瓶,说,“这是我和‘黄牛’的牛角奶瓶,我当然认识了!”
“那你知道这是用‘断角’的牛角做的吗?”
“啊?”阿爸的话让次洛很意外,他急忙拿起牛角奶瓶仔细端详,轻轻地抚摸着。这只牛角奶瓶,伴随他度过了一段美好的童年时光,让他和“黄牛”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玩伴儿。上面的每一道纹路他都非常熟悉,但他从来没想过,这只牛角奶瓶是用“断角”的牛角做的。次洛忽然想起,那时候,每次给“黄牛”喂牛奶,它总是要长时间地闻牛角奶瓶。次洛忽然明白了,那是它在闻阿妈的味道。
阿爸从次洛手里拿过牛角奶瓶,也像刚才的次洛一样仔细地端详,轻轻地抚摸。次洛看着阿爸,眼泪却不争气地夺眶而出。
阿爸伸手擦去次洛的泪水,转过身去,指着帐篷后面的后山方向说:“你看,那座岩山,让阳光涂成了金色。”次洛顺着阿爸的手指看去。他看到在他家后山的最远处,在雪线与林线的中间地带,一座小小的岩山就像是一座金字塔耸立在那里。
“有一头母雪豹,在那里安了家。”阿爸说。
5
这个早晨,阿爸原本要带次洛去看当了阿妈的“黄牛”和还没有见过面的“嘎娃”,然而,阿爸却牵着他的手,反身把他带到帐篷里。阿爸烧了奶茶,做了糌粑。两个人简单地吃完早饭,阿爸便说:“我给你说说那头母雪豹的故事吧。”阿爸低头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还记得‘黄牛’的阿妈‘断角’去天堂的那个早晨吧?”
次洛点点头,眼泪又开始在眼眶里打转了。
“就在头天晚上,我看到‘断角’拖着自己虚弱的身体站了起来。它当时是拴在拴牛绳上的,它用脖子紧紧拽着拴牛绳,拽得很紧,都绷直了。我知道它是不想被拴着,就过去把它脖子上的‘恰如’解开了。”
次洛克制着眼睛里的眼泪,克制着嘴里可能会发出的哽咽声,听阿爸给他讲母雪豹的故事。他不知道,这头母雪豹的故事,与“黄牛”的阿妈“断角”有关系。
那天晚上,阿爸把“断角”的“恰如”从拴牛绳上解开,顺手解下了“断角”脖子上的“恰如”,拴在了“黄牛”的脖子上,接着把“黄牛”拴在了“断角”的拴牛绳上。被解开了拴牛绳的“断角”目光平和地看着阿爸,看着阿爸麻利又悄无声息地忙碌着。或许是体力不支,或许是想给自己的孩子“黄牛”暖暖身子,它顺势趴卧在了“黄牛”的身边,伸出舌头舔着“黄牛”的头,舔着它浑身金黄色的毛,发出哞哞的声音,就这样轻声呼唤着自己的孩子,不再动弹了。
夜里,阿爸躺在床上担心着“断角”,一直不能入睡,到了第二天天光渐渐发亮的时候,阿爸恍惚听到了“黄牛”的哞叫声,便急忙起床,走出了帐篷。
天还没有大亮,一缕轻薄的云雾低低地旋绕着,让帐篷周围的一切都笼罩在一片铅灰色的朦胧之中。阿爸不由得伸手挥动着,一边驱赶眼前的云雾,一边向“断角”的拴牛绳走去。当他走近拴牛绳时,发现“断角”不见了,只有拴在拴牛绳上的“黄牛”焦躁地奔突着,嘴里“哞哞”地叫个不停。
阿爸从它不断奔突的方向判断,“断角”是朝后山去了,便循着这个方向朝后山走去。
阿爸在后山的岩山脚下找到“断角”时,它已经死了。一头母雪豹带着两头小雪豹正趴卧在地上啃食“断角”的身体。阿爸认识这头母雪豹,它与阿爸比邻而居,住在岩山上的一个洞穴里。岩山上怪石嶙峋,山势险峻,青灰的岩石之间一些纤维粗硬的植物散乱地生长在石缝里,远远看去,与雪豹身上的毛色十分相似。雪豹便是利用这样的环境,把自己并不庞大的身躯掩映在这荒芜之中,天然地掌握了一种隐身术。在这样的环境里,即便有人从岩山下走过,也很难发现它的踪影。
阿爸多次与这头母雪豹狭路相逢,想必母雪豹也认识阿爸,知道他是自己的邻居,所以见了阿爸,从来不会攻击,总是夺路而逃,这次也一样——母雪豹看到阿爸,低沉地咆哮着,警告阿爸不要靠近。见阿爸并没有离开的意思,它便从“断角”身体的大腿部位撕下一块血淋淋的碎肉,带着两头小雪豹,向岩山方向跑去——雪豹进入哺育阶段,此前一直厮守在母雪豹身边的公雪豹就会扬长而去,留下母雪豹独自哺育后代。阿爸等它们跑远了,便向着“断角”走去。
“断角”的身体已经被撕裂,血肉模糊,身上的肉大部分被啃食,露出了森森的白骨。阿爸不忍看,便侧过脸去,仓皇中一只手扶住了“断角”那只单独的犄角——雪豹的利牙凭借着强大的咬力,甚至啃咬了“断角”的头部,让那只犄角也松动了。阿爸轻轻摆动了几下,那只犄角便从“断角”头上脱落开了。
阿爸便带着“断角”的这只犄角反身回家。走在路上,阿爸心里想,“断角”来到母雪豹的洞穴附近,让母雪豹吃了它,也算是一次最大的施舍啊!母雪豹虽然凶狠,但进入哺育期后为了让小雪豹吃到东西,拖着刚刚生育不久,还很虚弱的身体四处捕猎,但它又不敢离小雪豹太远,担心自己如果走得太远,不能及时回来,小雪豹会遭到不测,所以总是在洞穴的附近捕猎,这样,它一天能够捕捉到猎物的几率就变得很小。不得已,它也去捕捉鼠兔、旱獭等草原上的小型哺乳动物,但这些哺乳动物太小,填不饱小雪豹的肚子。有时候,母雪豹也会偷袭牧民的牛羊。捕捉到了猎物,它宁愿自己不吃东西,也会把不多的食物留给孩子。阿爸之前多次见过这头母雪豹。它总是瘦骨嶙峋,追杀在岩山上的岩羊时,十之八九会失手。即便如此,母雪豹依然执着地捕捉猎物,总是要花费很多体力和时间。为了养育小雪豹,母雪豹从来不会怜惜自己的身体和生命。
“我把‘断角’的犄角带回来后,就把它做成了一只奶瓶交给你,让你去给‘黄牛’喂牛奶。这样,‘黄牛’每次吃奶时,也就等于它的阿妈‘断角’也在。”阿爸说着,把牛角奶瓶放在次洛手里,“把它收拾好,不要丢了。”
次洛看着牛角奶瓶,再次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问道:“阿爸,‘断角’为啥要离开‘黄牛’,独自走开呢?”
“因为‘断角’知道自己到了该走的时候。”阿爸说,“它把‘黄牛’交给了自己的主人,安心了。它不想死在主人家门前,所以它走了。这是牦牛的习性。”
“‘黄牛’真可怜!”次洛说着,忍不住哽咽起来。
“走,我带你去看‘黄牛’,还有‘嘎娃’!”阿爸说着站了起来,次洛也急忙站起来。
阿爸牵着次洛的手走出帐篷,又发动摩托车,骑了上去,抬头盯着站在旁边的次洛说:“来,过来!”
次洛便走到阿爸跟前,在阿爸的帮助下,骑上了摩托车的后座。
阿爸和次洛骑着摩托车向后山驰去。
在岩山的一侧,是一片平缓的草地,每到初春的季节,青草还没有发芽,金黄色的全缘叶绿绒蒿就在这里率先开花了。此时,绿绒蒿在这片草地上插上了金黄色的旗帜,昭示着高原的春天已经到来。这里是次洛家的冬季牧场。
阿爸带着次洛,很快就到了这里。次洛家的牦牛和藏羊就在这里吃草,它们散乱在草地上,散乱中又有着某种秩序。那一群藏羊在那片接近沼泽地的草地上啃食着牧草,牦牛群则分布在它们周围,对散亂的羊群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包围圈。
阿爸把摩托车停在离牦牛群不远的地方,两人下了车,阿爸对次洛说:“你叫‘黄牛’。”
次洛听了阿爸的话,即刻朝着牦牛群大声喊了起来:“黄牛——黄牛——”
正在牦牛群里吃草的“黄牛”听到次洛的声音,它先是有些不敢相信地确认了一下,接着就朝次洛飞快地跑了过来。一头小牛犊紧跟在它身后,一边跑,一边哞哞地叫着,很快就和“黄牛”拉开了距离。“黄牛”停下来,转头等着小牛犊,等小牛犊靠近了,接着又向次洛跑来。
不大一会儿,“黄牛”就带着小牛犊跑到了次洛和阿爸跟前。次洛又叫了一声“黄牛”,说了一声:“玩东嘎了!”便顺势趴在地上。“黄牛”看看次洛,“砰”的一下,次洛的脑袋和”黄牛“的头顶撞在了一起。如今“黄牛”已经长大,高大,强壮,但它掌握着分寸,看上去气势汹汹,但顶撞在一起的力度却很小。它知道这是游戏。
阿爸站在一旁看着次洛和“黄牛”做着“东嘎”游戏,喊起了“加油”,那头小牛犊呆呆地站在那里,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次洛这才注意到“黄牛”身后的小牛犊,便十分意外地打量起这只小牛犊。
这是一头青灰色的小牛犊,身上的毛色像烧过的牛粪一样。但在它的身上,还披着一张小牛犊的皮子,皮子有些干涩,显得凹凸不平。这是一张黑色的小牛皮,但次洛看到皮子的头部有一个白色的三角形。这张小牛皮是紧紧捆绑在小牛犊身上的。次洛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
“阿爸,这,这不是‘嘎娃’吧?”
“这是‘嘎娃’……”阿爸说。
次洛看看那头小牛犊,又看看阿爸,眼睛里充满了惊异。
阿爸看着次洛,张了张嘴,又张了张嘴,这才说:“这次你回来,我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嘎娃’呢?”次洛看阿爸有些吞吞吐吐,便焦急起来,大声问阿爸。
“其实,‘嘎娃’也把自己施舍给了母雪豹……”阿爸说。
“啊,这是怎么回事儿啊?”次洛的声音里带着哭腔,眼睛里的泪水已经流了出来。
阿爸走到次洛面前,伸手抓住次洛的手,说:“怪阿爸没有看护好‘黄牛’和‘嘎娃’。”阿爸说着,走到摩托车跟前,坐在摩托车的一旁。他让次洛也坐下来,说起了前不久刚刚发生的事情。
就在阿爸捎话给次洛,说“黄牛”生下“嘎娃”的第三天,或者第四天,马虎的“黄牛”把“嘎娃”带到了岩山底下,也就是母雪豹的洞穴附近。这头母雪豹今年又产下了两头小雪豹。“黄牛”是主人一点点喂养大的,小时候没有在野外待过,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它从小就缺乏危机意识,而且还有点不合群,总是离开牦牛群,自个儿单独到一处吃草。那天上午,阿爸要去巡山,巡山之前专门来到他家的冬季牧场看了一圈。他看到“黄牛”带着“嘎娃”在那里吃草——本来母牦牛和小牛犊要分群放牧,以保证母牦牛的牛奶不被小牛犊全部吃完,让主人也能喝上牛奶,但“黄牛”的奶水少,阿爸也就不给“黄牛”挤奶了,把它和它的孩子“嘎娃”一起放在同一片草地上。
晚上,阿爸准备把牛羊群赶回家的时候,却发现“黄牛”和“嘎娃”不见了。阿爸把牛羊赶回家,便骑着摩托车反身去寻找。阿爸很快就找到了它们,它们在岩山脚下。
太阳已经落山,原本险峻的岩山此刻有了一种阴森的感觉。阿爸远远就听到“黄牛”不断发出短促的哞叫,声音里满是急躁和惊恐,心里便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等阿爸走到跟前,便发现“嘎娃”倒在地上,屁股鲜血淋漓,身体抖动不止,已经奄奄一息了。显然,“嘎娃”受到了母雪豹的袭击。
“黄牛”站在“嘎娃”旁,不断地低头舔着“嘎娃”的伤口,一边舔,一边叫唤,试图帮“嘎娃”站起来。
阿爸快步走过去,抱起“嘎娃”放在摩托车后座上,骑着摩托车往家里赶。家里有一些止血的草药,他想抓紧时间给“嘎娃”治疗,也顾不上自己身上的“擦日”羊皮袍和摩托车的后座被鲜血染红。“黄牛”不断哞哞地叫着,紧紧跟在阿爸的身后。
可是,“嘎娃”没到家就不行了……
那几天里,“黄牛”不吃不喝,一直守在“嘎娃”小小的身体旁边,不断地用嘴拱着,试图让“嘎娃”站起来。“黄牛”的眼睛里泪水不断,阿爸不忍看下去,也陪着“黄牛”流眼泪。
第三天,次洛家的邻居——说是邻居,其实是居住在岩山的另一头,距离次洛家至少有十公里——雍西大叔听说了“嘎娃”被母雪豹咬死的消息,便抱着一头青灰色的小牛犊来到次洛家,说这头小牛犊的阿妈死了,让它顶替“嘎娃”给“黄牛”做孩子。雍西大叔告诉阿爸,把“嘎娃”的牛皮扒下来,用牛粪灰擦去牛皮上的血迹,披在青灰色小牛犊身上,让小牛犊去吃“黄牛”的奶,“黄牛”见到“嘎娃”熟悉的毛色,闻着牛皮散发出来的味道,慢慢地就会把青灰色小牛犊当成“嘎娃”。
阿爸照着雍西大叔的话去做,慢慢地“黄牛”果然认了这个“起死回生”的孩子,并且对它亲热有加。
太阳开始西沉,阳光在与寒风的拉锯战中一直占着上风,但实力强劲的阳光好像用力过猛,透支了许多的力气,这会儿它的势头慢慢微弱下来,寒风立刻乘势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反攻阳光,寒风的势头便又慢慢压过了阳光。次洛和阿爸依然坐在摩托车旁,阳光一点点地暗淡下去,寒风从他们的身边呼啸而过,声音越来越大。
听阿爸讲完这些,次洛一直没有出声,好像是陷入了沉思。慢慢地,太阳沉入了西山,夜色一点点地浓重起来,阿爸站起身来,伸出手,对次洛说:“咱们回家吧。”
次洛伸手抓住阿爸的手,阿爸稍稍用了一下力,次洛站了起来。
“阿爸,我想阿妈了……”次洛说。
阿爸把次洛揽入怀中,没有说话。
6
在家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次洛的“月假”结束了,明天次洛就要赶回学校去了。
次洛心里想,這次回到学校,请教扎门西老师的问题太多了。他要让扎门西老师仔细地给他讲一讲,关于母雪豹,关于牦牛,还有关于阿妈,关于孩子,还有关于爱,关于悲伤……
晚上牛羊牧归的时候,阿爸带上了次洛,他们一起又去了冬季牧场。
到了冬季牧场,次洛和“黄牛”再次玩起“东嘎”游戏,他还摸了一下青灰色小牛犊的头,叫了它一声“嘎娃”。
这也算是次洛正式接受了这头青灰色小牛犊,承认它就是“嘎娃”了。
阿爸和次洛正准备把牛羊赶回家里,忽然阿爸看到那头母雪豹带着两只小雪豹就在他们的牛羊群附近——那只母雪豹嘴里叼着一只已经被咬死的岩羊,站在一块岩石上看着牛羊群,看着次洛和阿爸,两只小雪豹则有些惊慌地紧贴在母雪豹身上。
“次洛,你看!”阿爸伸出右手,指着前方,大声地叫次洛,尽管他就站在次洛的身旁。
阿爸的声音让次洛吃了一惊,他急忙神情严肃地朝阿爸指的方向看去。
这时候,“黄牛”发现了母雪豹,它忽然短促地叫了两声,扬起尾巴,径直冲着母雪豹奔跑而去。母雪豹看着“黄牛”向自己跑来,依然站在那里。等到“黄牛”马上就要接近时,母雪豹扔下叼在嘴里的岩羊,转头朝岩山的方向跑去,两头小雪豹紧紧地跟在母雪豹的身后。
“黄牛“紧追不舍,距离母雪豹越来越近,这时候,青灰色小牛犊“嘎娃”忽然朝着“黄牛”叫了几声。“黄牛”听到叫声,停下来,转身看看小牛犊,又扭头看看已经跑远了的母雪豹和小雪豹,也用短促的哞叫回应着小牛犊。这时,小牛犊又叫了一声,“黄牛”便不再去追母雪豹,回头向着小牛犊跑来。
披着“嘎娃”牛皮的小牛犊扬起自己还没有长大的小尾巴,也向着“黄牛”跑去。“黄牛”和小牛犊会合,小牛犊立刻把头塞到“黄牛”肚皮底下开始吃奶,“黄牛”则定定站立着,任凭小牛犊在它的肚皮下不断地顶撞着,吸吮着。
这会儿,阿爸走到刚才被母雪豹扔下的岩羊跟前,看了一眼,说道:“这是母雪豹带着它的孩子来赔罪呢!”
次洛走过去,也看看那只被母雪豹咬死的岩羊,又不解地看着阿爸。
“母雪豹给‘黄牛’带了一头岩羊。”阿爸解释说。
次洛听了,更加不解,说:“‘黄牛’又不吃肉啊。”
“母雪豹以为它觉得好吃的东西,别人吃起来也很美味的。”阿爸说,“这只可怜的岩羊啊,就这么被咬死了。”
次洛愣愣地看着阿爸,目光从阿爸的脸上慢慢移开,延伸到了眼前广袤的草原。次洛心里想,是我的阿妈把她的母爱给了这片草原,所以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动物们才有了这样的母爱!这样想着,他忽然说:“我阿妈做的好吃的,谁吃起来肯定都觉得美味。”
阿爸张了张嘴,又张了张嘴,没有说话。
责任编辑 曾 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