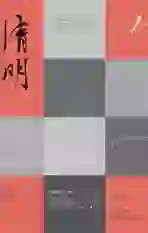钢琴梦
2024-01-20罗志远
罗志远
房东家的女儿在练琴。
一开始是音阶练习。她也许敲击了一下“do”,于是楼上短促地传来“do”的一声,透过木质天花板在屋内缓缓回荡。紧接着“re-mi”,连在一起“do-re-mi”,没有风,三个音符像丝绒一样,在透明的光线下徐徐飘落。“fa-sol-la-si”,“si”后面有细微的颤音,像是上下颚闭合,从牙齿缝挤出的一声。它们共同形成一组音阶。
母亲竖起耳朵,很仔细地听着,不愿错过任何一个流淌过的音符,午后的光线薄薄地照在砧板上,手上菜刀的动作也慢了半拍。无数个午后,她都是站在砧板前,腰间系着白色围兜。每杀完一头猪,她就要面对自来水龙头,两手来回搓。一块块割好的生猪肉挂在铁钩上,若风稍大些,便会晃来晃去。
街上人群来来往往,自搬来这里后,我从没听母亲吆喝过。若有生意,她就切下一块猪肉,套入塑料袋,放在秤上称量,拣肥拣瘦,几斤几两,少了,则多割一点,多了,便抖去少部分。若无生意,她更多的时候是坐在台阶旁的小板凳上发呆。我站在母亲身后,鋼琴声缓缓流淌,自然而稍显突兀的音阶变换着,不定时结束。
我只见过一次钢琴。忘记是什么时候了。天很干燥,货车停在路对面,房东慢悠悠地下楼签好收货单据,四个身材魁梧的汉子摘下帽子,一人抱住大纸箱一角,侧抬着,很吃力地搬上楼去。他们宁可后背蹭一路的墙灰,也不敢磕着钢琴。
我听母亲的话,没有上楼去。我两手托着下巴想象着纸箱里的钢琴是什么样,大的,小的,重的,轻的。后来,便没再想了。母亲喊我吃饭。
房东的女儿练钢琴大约有些日子了。从起初的磕磕绊绊,错乱杂弹,到后来慢慢能完整地弹出一首曲子。房东从没跟我们聊过钢琴的事,一月一度的交租日,每次母亲欲言又止地想要说些什么,最终全咽下去。
母亲至少一天要杀一头猪。她烧一大锅水,揪住四肢用绳子捆住的猪,按倒,然后刺杀放血。猪被剖开脖子,哼哼直叫。我太小了,以前还有父亲能搭把手,自他死后,多重的猪也需母亲一人搞定。
父亲死于一场车祸。自下岗后,全家从厂区搬出来,父亲用买断工龄的钱买了一辆二手皮卡跑运输。父亲不善言语,早出晚归,没有多余的爱好。车祸那天,下大雪,父亲开车去送货,没有照常回家。深夜时分,我们接到派出所的电话。父亲的那辆皮卡和一辆客运旅游车相撞,车子直直钻入路边丛林。父亲在医院躺了一天一夜,没再醒来。
全家的生计落在母亲一人身上,楼上的钢琴声也是在这时慢慢响起的。房租不菲,偌大的几十平方米,前屋卖猪肉,后屋睡人。钢琴声时断时续,我彻夜难眠,即使半夜起来上厕所,若有若无的声音依旧自天花板飘下。回来时,我偷瞧睡在床板上的母亲。她蜷缩身子侧躺着,其中一只耳朵对着天花板,很认真地在听。
十岁生日那天,母亲非要拉着我去买钢琴。
中央广场有很多钢琴店,随便走入一家,正中心处,一座巨大的黑色立式钢琴映入眼帘。销售员带母亲四处转了转,意大利卡罗德、德国卡纳尔、日本雅马哈……母亲问还有价位比较低的没有,销售员捂嘴笑,说这已经是最便宜的几种了。
母亲僵在原地,一时间不知所措。我站在她身后,一言不发。
四处有人走来走去,不断有人瞥向母亲。我看到一个戴太阳镜的年轻女人拉着一个小女孩的手,在一架崭新的钢琴上试弹了几下,随后便去前台登记付了款。人越来越多,母亲的手不断蹭着衣角,好像习惯性地在擦围兜。她回过头看我,神色复杂,嘴唇翕动。我不懂,摇了摇头。
最终,母亲掏空腰包,买回一架摆在商场角落的蒙灰的电子钢琴。
电子钢琴不包送货,母亲便一人扛回来。同样叫钢琴,同样是八十八个琴键,却有天壤之别。琴身简易,琴键干瘪,远没有真正的钢琴大而厚重。我略感失望。妈妈却很满意,拍了拍我的后肩,一阵忙活,把它郑重地摆在我的房间。她把家中所有窗户大开,光线透射进来,有了这样一架琴,家里好像一下明亮了许多。
首先是指法练习。照着音阶指法的说明书,从左“do”到右“do”一共八个音,我小心地把右手的大拇指放在中间“do”的位置上,于是琴键“do”很突兀地响起一声。
我花了不短的时间,慢慢学会用五个手指上下交替敲击琴键。房间凌乱、狭小、寂静,唯独钢琴声如涓涓细流传出。从搁在角落的扫帚和鸡毛掸子,到后厨的锅碗瓢盆,水槽中未清理干净的动物内脏,一把把贴墙挂着的森森刀具,墙壁上被熏黑的油垢,一切都沐浴在音乐的海洋中。
母亲在外头剁猪肉,像过去听房东家女儿练钢琴一样,全神贯注地听着,听得摇头晃脑。若有人走过,她还会故意大喊一声,闺女,弹一首贝多芬。而我连最简单的曲子也没学会,指法更是生涩,只能乱弹一气。这时她就会骂骂咧咧地说,刘思媛,你弹的什么玩意儿!
弹琴五六个小时,坐得屁股疼,我起身喝水,上厕所,琴声在中途戛然而止,反复几次,就到了吃饭时间。于是母亲抱怨我不专心,三心二意。我小心嘟囔几句,她就用筷子把碗敲得直响,呵斥说,你长大了,都学会顶嘴了。然后命令我坚持弹完最后一组音阶,不然不许上桌吃饭。
母亲是一个很能吃的人。猪肉炖粉条、猪下水炒辣椒、爆炒猪油渣……母亲坐在桌对面,丝毫没察觉任何不妥,混着一小勺猪油汤,每次都很愉快地舔干净饭碗。她的体重与日俱增,当她弯下身洗猪内脏时,滚圆的屁股透过花裙,若隐若现地对着我,我会不自觉地停下手中的动作。这时,母亲的耳朵就机敏地动一下,呵斥声传来:
“快弹——”
我哆嗦一下,于是琴键也顺理成章地跟着“do”一声。
有一段时间,楼上房东家的女儿很少弹琴了。一天,一个戴眼镜的男人跟在房东后面上楼,听说是指导老师,专程从外地赶回来调音的。我没有老师,自学自练,因此只能站在后面,静静地看着他们上楼。大约过了一个钟头,男人下来了。他在店门口停留了一会儿,也许是听到身边有顾客在议论。母亲犹豫了一下,自语道,又是指导又是调音的,有啥了不起?看我闺女自个儿练,这样不挺好吗!
后来母亲去上厕所了,我鼓起勇气走近几步,问那男人能不能帮忙看看我的钢琴。男人跟我进了屋,仔细看了两眼,摇摇头说这架钢琴不需要调音。
男人离开了,徒留我在原地,疑问从脑中冒出:为什么我的钢琴不需要调音?
我悄悄上了楼,房东不在,只有她的女儿专心坐在钢琴前试音。窗外阳光正好,钢琴盖大开着,第一次,我看到钢琴内部的肌理。映入眼帘的首先是密密麻麻的木材块,数量接近上百,它们形状精巧,干燥而光滑,纵横排列。晶莹的钢丝组成每一根琴弦,笔直拉伸,而后被定弦纽紧紧扣住。击弦机与琴键相连,每当敲击黑白琴键,琴槌击打琴弦,如同一颗颗心脏跳动,一个个轻盈的音符由此跳出。
我不觉呆了,在那短短一瞬,好像发现了这个世界的真理。等回过神,面前的门砰的一声已经关上了。我并不感到生气,而是压着内心的兴奋,下楼时连跌几跤,也并不十分疼。
回去后,我走进自己房间。母亲在铺被子,她摘下被套,翻出棉絮,抬手拍打,扬起无数粉尘。我在钢琴前深吸一口气,兩手抠住琴身缝隙,想要拆开来看。母亲大惊,拦住我说,好好的,干吗拆了?你不好好珍惜,弄坏了怎么办?一点常识也没有!
我只好放弃拆琴的想法。母亲接着铺床。自我练习弹琴后,母亲开始热衷于给整个屋子做保洁。每天,她都要拎一大桶水,拖地、擦墙。瓷砖上的油腻子,她用小刀小心地刮掉,再喷点水抹一抹,墙面顿时锃亮如新。母亲巡视每一个角落,不放过任何一处污渍。尽管我告诉她,第二天屋子总会凌乱不堪,她仍我行我素,乐此不疲。
“do——”
我怔怔看着正在劳碌的母亲,手指猛地敲击一下,声音回荡。母亲反手擦一擦额头的汗珠,身体顿住,紧接着抬起头,眼睛里涌起一种奇异的色彩。
“闺女,干吗停下了?继续弹啊。”
母亲揽下所有的活,于是一整个下午,我都在房间弹钢琴。时间在一次次枯燥的练习中过去,可是,我并没有学会弹贝多芬,只是通过了《车尔尼599》的入门、《巴赫初级钢琴曲集》以及理查德·克莱德曼的几首曲子。在外头切猪肉的母亲颇为不满,老是会大嚷,闺女,来一首贝多芬。是的,她只知道贝多芬。
“再拖欠房租,只能请你们走人了。”
一天,我看到房东和母亲说完这句话后把烟屁股丢到地上,用脚反复踩,母亲则垂下头,一声不吭。后来,房东带着两斤猪肉上楼了。她没有给钱。
年底,母亲连着一周不眠不休加班加点,总算偿还完欠下的房租。第二年春天,她早早把猪肉挂出去,也学着人家吆喝起来。
“快来买哟,新鲜的猪肉,猪耳朵、猪肚子都有!”
我抚弄黑白琴键,敲击下第一个音,恰和楼上的钢琴声一同响起。两首不同的曲子出现,音符如泾渭分明的两条河流一同放闸。母亲立马闭紧嘴巴,呆呆听着。我的琴声渐小,楼上的琴声渐大,由波纹变为掀起的海浪,一层一层涌来。我看看母亲,加大指下力度,顾自从头弹到尾,哪怕有错也绝不停下,拼命想要压过楼上的声音。不久,楼上的琴声终于小了,顷刻显得我的钢琴声乱而嘈杂。
母亲说我弹得不如楼上动听,这无疑激起我的好胜心。
后来,我有意错开时间,或者中途停止动作。我想象楼上的女孩正坐在钢琴前,两手贴着琴键,坐姿标准,一身公主裙,安静沉稳地弹奏乐曲。一首新曲子,反复练习很多天,从记谱到背谱,学会指法,节奏变换,或快或慢,不免仍稍显生涩。弹到三分之二,略一迟疑,一两个音错开,但不知怎的,她总能迅速纠正回来,余下部分一气呵成。
我默默计算,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她每天总共弹两个小时钢琴,从不多花时间,但偶尔会少弹。我撕下贴在墙上的日程表,把自己的弹琴时间调到比她多一倍。
于是第二年的一整个春天,母亲都没有任何休息,我也很少休息,屁股黏在琴凳上,一直弹到指关节发疼。母亲早早开张,切肉时,她一只手压着砧板,另一只手握住菜刀,时不时抬起头往楼上看,又反复回头看我房间,拼命咳嗽两声。我便有所领会,和她所想的一样,楼上楼下琴声同时响起,同时结束,甚至,每次我弹的声音都更大,时间更长。
放学后先练琴,再吃饭,最后赶作业。每次我拖着疲惫的身子爬上床时,往往已是深夜。
这个周末,我们弹的是同一首曲子。我默念着曲谱,当她敲下第一个音,我会迅速跟上;当她敲下第一段,我也亦步亦趋。不知为何,明明已经花了这么长时间,那么努力地练习,我琴下的音符还是显得笨拙、呆滞而僵硬,和楼上相比,很容易发现其中的破绽。
她的琴声忽大忽小,渐强渐弱,每次音符消散前会产生一段新的旋律。每有错音,也能很快纠正。而我抬高手指,很用力地弹,或者压低,很轻地弹,指下黑白键发出的声音没有任何区别。情急之下,弹得更是磕磕绊绊,杂乱无章。
我喊母亲,她系着围兜从店外匆匆赶来。
“妈,声音不一样。”
“哪有什么不一样,是你自己不够努力,所以不如人家。”
母亲喋喋不休地教训我,多弹,快弹,熟了才能生巧。
生意好的时候,母亲一人忙不过来,我自告奋勇要帮忙,她没答应。一天,好不容易生意结束,日落黄昏,母亲收了摊,然后花完最后一丝力气做好饭。她叫我先吃,自己躺到床上休息。她醒来时,饭菜已凉。母亲走出来,我再次和她说起帮忙的事。母亲提起一口气,教训我说:“小小年纪,少东想西想,你把琴弹好了,妈干活就有劲了。”
我只能弹琴,别无他法。楼上的琴声有段时间销声匿迹,没再响起,不知为何,我心底反而松了一口气,恢复日常的自我练习。深夜躺在床上,脑海里回响起白天钢琴的旋律,我摊开十指,对着虚空不自觉地敲击。没有声音,空旷的房间,唯独隔间传来母亲哼哼的梦话。
夏日不知不觉过去,我还是没学会贝多芬。
秋雨季,连下几天雨,地板渗水,墙面裂开几条缝。母亲穿上胶鞋和雨衣,戴上蓝色雨帽,咚咚咚咚一刀一刀剁猪肉。雨棚滴滴答答落下雨水。
天放晴后,母亲出门了,中午拎回一大袋东西。原来是墙纸。她把这些浅绿色的墻纸张开、抚平,反复欣赏,然后郑重地贴在墙面的缝隙上。缝隙遮住后,她退后几步歪头看,熏黄的白墙,若隐若现的细缝,她皱一皱眉,花光了一圈双面胶,遂把整个屋子里里外外贴满墙纸。
母亲贴墙纸,我弹琴。母亲贴完墙纸,我还在弹琴。我很努力地敲下每一个琴键,哪怕学不会贝多芬,也试着去弹莫扎特、舒曼和门德尔松,弹他们著名的《梦幻曲》和《春之歌》,哪怕仅仅只是一个章节。尽管母亲以为我弹的每一曲都来自贝多芬。
每晚七点,照例是母亲叫我吃晚饭的时间。我盖上琴布,不情愿地从房间内走出来。
“怎么又吃猪肉啊?”
“你这孩子,吃猪肉有什么不好?我小时候想吃肉还吃不到呢。”
母亲放下筷子喋喋不休,指关节一遍又一遍敲击着桌面。由于长期缺乏维生素摄入,她面部浮肿,像块泡发的面团。母亲站起身,把一大盘肉泥拨到我饭碗里。我看向母亲的手,这双手不知杀过多少猪,多少次浸泡在冷水中,显得粗大而红肿。我不由自主地低下头,捏紧拳头,又缓缓松开,什么也没说,离开了饭桌。只留下母亲在背后嘟囔:“爱吃不吃,什么毛病。”
母亲一日三餐吃猪肉,隔夜肉都用来做盘中餐。看到母亲津津有味咀嚼猪肉的模样,我很想告诉她,书上说,要多吃瓜果蔬菜,要营养均衡。可我一张嘴,就会被迅速反驳回来。
年底,母亲病倒了。摊位撤掉,家里没有收入,仅存的老底迅速被掏空了。那几天,隔间传来阵阵沙哑的咳嗽声,母亲横躺在床上,说,总有一口痰卡在嗓子眼里,吐不出来,咽不下去。
房东来过几次,嘘寒问暖。我领着她进屋,她鼓励我说,钢琴弹得不错,只是不要晚上练就好了。我点点头,借此机会,小心翼翼地询问她女儿为何弹得那么好。她张开五指,举出一个数,说,请老师啊,有专业的老师教,能少走很多弯路。我沉默片刻,紧接着问她女儿最近为何不弹琴了。
“和她爸一起出国了。”她漫不经心地说。
没有楼上的那个声音,我练琴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好像丧失了动力。不论怎么练,始终无法突破局限。每当我煮好菜汤,端到母亲面前,她都会别过脸去。我懂她的意思,练琴,快点练琴。
身体恢复后,母亲重新出摊,照例扯着嗓子吆喝,声音雄浑得像一个男人。
“卖猪肉了!新鲜的生猪肉!”
除了一些老顾客,很少有人来光顾了。
又是一年春天,某日,母亲正在给一位顾客切猪耳朵,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阳光斜斜地照在砧板上,母亲招呼一声,要买什么?男人什么也没说,直直往里走。母亲忙拦下他,一面拦一面说,哎呀,你到底是什么人,往我家里闯?男人停下脚步,打量母亲,龇牙说,大婶,这不是你家吧?告诉你一声,你没续约,房主已经把门面转让给我了,我今天就是来看看。男人从兜里掏出一份合同,在母亲面前晃了晃,母亲一下僵住了,脸色变得苍白。她接过合同,来回看了三遍,我站在她身后,她也没有察觉。
男人在屋子里四处打量,走来走去。他巡视了一下后厨,径直朝我房间走去。母亲上前挡在门口,尴尬地说,我闺女的房间,就不用看了吧。男人说,大婶,定金早交了,下月我就要入住,哪能不看呢?保证家具完好,心里才踏实啊。我默不作声地拉了拉母亲的衣角,她挪开了。
男人一眼便看到那台钢琴,但没有说什么,只是敲了敲墙壁和床板,然后出去了。我和母亲站在门口的台阶上,目送男人远去。也许是我的错觉,耳边隐约钻进一句嘀咕,都这样了,还弹什么琴!我看了看身边的母亲,她脸色木然,好似什么都没听到。我们许久都没进屋。一滴冰凉的水滴落下,我摊开手掌,仰起头。
下雨了。
离搬家的时间渐近,母亲去找过房东两次,没有得到回应。哎呀,怎么偏偏那时候生病!母亲不住地抱怨自己。我紧闭上嘴,思绪连篇,踩一踩脚下的地板,下面是更深层的土地。我们能在所谓的家待多久呢?房东之前那么殷勤探望,大概是出于内疚吧。
搬家那天,我已经十二岁,学琴满两年。物件太多,母亲不得已舍弃许多东西,唯独那架钢琴没有丢,也不能丢。母亲站在我的房间,第一次试图伸出手去抚摸钢琴。刚一触及,指尖猛地弹开。卡车要发动了,我背着书包,站在她身后,说,妈,咱们走吧。
母亲回过头,眼睛里再次露出那种奇异的光芒。她艰难地开口说,闺女,弹一首吧。我腹诽,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弹琴。母亲好像明白我的想法,轻声说,弹一首吧,就最后一首。
母亲小心地把那架所谓的钢琴放在桌案上,搬来凳子,拍了拍上面的灰,请我入座。我从未见过她如此谦卑安静,一直以来,在我印象中,她都是一个性格粗放,手握杀猪刀,嘴里放肆咀嚼猪肉的女人。
虽已疏于练习,我还是再次敲击下那个琴键,那个过去两年反复、反复敲响过的琴键。
“do——”
音符十分呆板,它看着自己,如开锅的蒸汽般袅袅作散,像是开始,也像是落幕。
我已弹不出曲子了,只能弹音阶。一组音阶弹完,渺茫的琴音再难寻觅。我下定决心,转头对母亲说,妈,别带走了,丢了吧。母亲瞪大眼睛,以为听错了,直到我重复数遍,方才回过神来。她说,你这小孩子怎么说话的?不能丢,绝对不能丢的。
她的语气坚决,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
她一把抱住琴身,而我死死抓住琴尾不松手,争抢中,那架电子钢琴摔在地上,四分五裂。
刹那,琴的内部展露无疑——
没有我想象中精密的结构、复杂的机械运转、巧妙如机关的设计,甚至琴弦、琴槌、绒布,什么也没有。只有两个形似扩音器的喇叭和几根电线,由于久未清理,内部边缘已经发潮起霉,好像一个腐烂的水果核。
一根缠绕在琴上的红色丝带轻飘飘地落在地上。我隐约回想起来,这根丝带早年一直是母亲随身携带的。那时母亲还很年轻,父亲也在,一家人其乐融融。母亲是居家主妇,不用上班,但仍会早起,对着镜子梳妆打扮。而父亲上班前夕,吃完早饭后,会陪我看会儿早间新闻。若收音机里传出钢琴曲的声音,母亲便拍一拍父亲的肩膀,让他把电视声关小,然后放下手中的梳子,闭上眼睛,用纤细的十指在梳妆台上模拟敲击,留下一个个椭圆形的指印。
时间停住了,好像一台大型机器内部相互咬合的齿轮被什么东西卡住,所有的声音戛然而止。母亲慢慢蹲下来,抱紧膝盖,我呆呆看着她。正当我不知所措之际,只见母亲慢慢伸出十根指头。因为是背对母亲,从我的视线望去,看不清她的面孔,但见到那指关节粗大、指甲熏黑、印有几道刀痕的手。原来在父亲逝去的这几年里,这双手早已疲惫不堪。
母亲半是犹豫,半是羞怯,悬空试探性地敲击下第一个指头。也许是我的错觉,好似从房间的哪个角落里,突兀地传出“do”的一声。然后,母亲再模拟敲击下第二个指头,“re”紧跟其后。接连着,她的十指一一敲击,来回反复,无人打搅,她顾自沉浸在一场个人演奏中。
我没有出声,呆呆地站在她身后,恍惚间,连贯的钢琴声在我耳边再次回响起来,进而沐浴整个房间。
责任编辑 刘鹏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