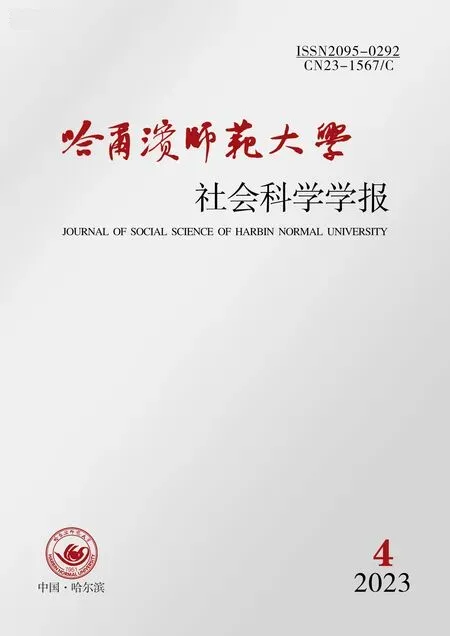消解、重构与合作:论后人类主体生成的三个路径
2024-01-18雷碧乐
雷碧乐
(广东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州 510006)
引论
根据贝德明顿的考据,“后人类”(post-Human)这个名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是俄国神智学派创始人布拉瓦次基(H.P.Blavatsky)在论述人类演化理论时提出的,而后,就很少被提及。[1](P78)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自然科学领域的新发现,“后人类”的观点和思想逐渐呈现,引发学者们的不断思考,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思想家哈桑(Ihab-Hassan)指出,人类的形态—包括人类的欲望以及所有的外部表征—可能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因此必须要重新构想“后人类”。[2](P830)此时的后人类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名词,而且成为一个学术概念,引起各领域的热烈讨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人类”这一含糊的新词更显示出强大的增殖能力和包容性,形成了一场跨越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批评实践,并把各种不同的思想运动囊括其中,如哲学的、文化的或批判的后人类主义,超人类主义、女性研究中的新物质主义以及具有完全不同视野的反人本主义,元人类主义等等。时至今日,后人类已经成为一种哲学思潮和批评性话语,仍然处于方兴未艾、风头正劲之势。但是,经由将近半个世纪的讨论,后人类这一话题依然处于众声喧哗之中。沃尔夫在《什么是后人类主义?》一书中干脆把后人类的概念进行了扩展,把它称为“后人类主义”:一种是作为思维方式的后人类主义,主要在实用主义、系统论、后结构主义等平行领域加以探讨;另一种是直接针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物种中心主义问题,主要探索我们的思考和阅读实践如何朝着批判的方向转变。[3]沃尔夫从哲学和技术层面指出了后人类的主要内涵,但在追寻后人类主体生成的路径方面,英国理论家罗伯特·佩普勒尔(Robert Pepperell)在《后人类状况》(1995)中提出的三种理解后人类的方式也许更加清晰一些。佩普勒尔指出:第一,我们可以在时间的线性层面上,把后人类看成是对人文主义所宣称的理性的、先验的、超越的、自主的“人”的挑战和批判,是对以人为中心的时代的终结;第二,我们可以把后人类看成是人类在技术塑造下的一种存在形态,曾经的血肉之躯在科技工具的肢解下成了在冰冷物质中传输的信息流,曾经的万物灵长的理性主体成了一个自动化控制的“缸中之脑”;第三种理解就是把后人类表征为一种思想观念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我们对自身、动物和环境在内的他者之间关系的一种反思。[4](P176)如果对佩普勒尔的理论做进一步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后人类主体生成的三个路径:第一,从理论上,可以追溯到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推崇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以笛卡尔(Rene Descartes)、康德等为代表的人类理性至上信仰的对话,反思和批判,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反叛,直至福柯、巴特等后结构主义理论家话语权力和性别批判以及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解辖域化理论;第二,在实践上,可以归结到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和控制论发展基础上对自然人类主体的扩容和重构,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图灵实验” (Turing Test)和 “莫拉维克实验”(Moravec Test)等对后人类图景的勾画;第三,从本体论建构上,可以归功于后人类理论家在解构主义、反人文主义和生态后现代主义对他者重写基础上提出的重新审视人类的本质并与非人类他者构成对照性批判,最终进入合作关系网络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本文尝试在佩普勒尔理论的基础上,从消散的主体、技术打造的主体以及作为他者的后人类三个方面系统地梳理后人类主体生成的三个路径,期望能为解析后人类这个复杂的概念提供一个较为简单和清晰的脉络。
一、消散的主体:“人”之死与后人类主体的雏形
对理性的信仰是古希腊以来西方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古希腊人在“哲学”中寻求智慧,在思辨中探求自然的本源与人的本质,将自由与理性与人的本质联系起来,开辟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先河。中世纪,宗教信仰占了统治地位,神造的人类只能匍匐在上帝面前,失去了主体的地位。16世纪在欧洲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又复苏了古希腊的人文主义精神,在重新发掘人性本质的同时,又赋予人类新的内涵,即把人类当成上帝的杰作和万物的灵长。17世纪,笛卡尔用“我思”作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恢复了自古希腊以来人的自由和理性本质,承袭了文艺复兴以来产生的个体主义理性精神,奏响了近代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转向的序曲,对18世纪的启蒙运动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在理性与信仰的白热化斗争中,启蒙学者们批判一切,任何被认为是不证自明、权威的说理和教条、任何制度、习俗、规范都要重新接受理性的审查,只有在理性面前证明自己为合理的事物才有存在的价值,人的理性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判断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通过理性批判,提出“知性为自然立法”,“理性为自身立法”的原则,将人的主体性提到了与宗教信仰同等的地位,理性成了“现代及启蒙的女神”。之后,黑格尔的绝对理性成为科学理性或逻辑思维绝对化的基础,并且将人性的本质完全归为理性,把人变成了孤立的、抽象的理性动物。
主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在推重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这个静态、孤立的实体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人性的傲慢和分离”,[5](P9)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哈贝马斯看到了现代化进程中启蒙理性的负面影响,把现代性压抑造成的生态环境危机、能源危机、价值信仰危机、人的“异化”等归结为以主体为中心的传统哲学。19世纪下半叶兴起的非理性主义思潮首先发起了对理性的反思和批判,20世纪60年代的解构主义理论在反抗现代性危机的过程中,也为后人类主体的登场打下了理论基础。
非理性主义思潮从德国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开始,从情绪、直觉、本能欲望、意志和潜意识等因素出发,从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上与理性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立,推翻了理性在人类认识和实践中的决定性作用。叔本华提出唯有意志是自在之物,科学理性无法认识真理和意志世界,只能靠人的知觉才能达到主客体的融合。尼采把叔本华悲观的生存意志改造成为以希腊酒神狄奥尼修斯为代表的强烈的生存意志,指出人类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就是要成为能够克服一切的“超人”,掀起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思潮。柏格森和狄尔泰从叔本华的思想中得到启示,从生命的冲动之中寻求宇宙万物的来源和主宰。海德格尔受到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启发,抛弃了“主体”“自我”等概念,用“此在”(Dasein)的概念来指代主体和客体混沌不分、不断发展变化的状态。弗洛伊德认为深埋在无意识中的人的本能欲望决定着人的行为,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意识是心理的实质,否认了理性的主导作用。
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反叛使人类自我中心的版图遭到巨大的冲击,但最猛烈和最直接的攻击还是来自于后结构主义理论家。他们对语言和语义系统展开科学分析,不管是人类主体囚禁于意义已然决定的语言系统之中的看法,还是意义会被无穷无尽地延宕的主张,都试图撼动甚至废黜文学作品中作者作为拥有创造意图的主体地位,消解了西方传统思想中统一、完整、自足的实体。20世纪60年代,德里达、拉康与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等形成了一个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德里达“元书写”(arch-writing)的概念以符号的“可重复性”和“不考虑讲话人之意图性”的特点打破了逻格斯的语音中心说,从而瓦解传统两元对立中的等级秩序。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正好与法国心理学家雅克·拉康的心理/主体理论相呼应。拉康认为传统奉为圭臬的理性主体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理性主体一开始就在无意识中处于语言文化建立的压迫体系中,是人类通过对“他者”的误认获得的虚假自我意识和自我存在感。巴特通过揭示“文本性”的实质宣告作者的死亡和主体的消解。福柯通过知识考古学和话语的谱系学分析指出,西方一直推崇的“人”的概念不是永恒的、无限的存在,而是话语建构的产物,并进一步揭示了话语作为生产人类社会的知识系统与权力的同谋关系。权力通过空间、话语或者非话语的领域规训个体的存在,也就是说,在权力和话语的操控下,个体被变成了主体(subjects),而后又屈服在(subject to)主导学科的规训之下,在建构人类主体的同时又消解了人类的主体性。
“人之死”和理性主体的消解,为“后人类”登上历史舞台准备了话语条件,德勒兹、瓜塔里的“精神分裂”和“游牧”的后现代主体孕育了后人类主体的雏形。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思想是对笛卡尔式主体观念的拒绝和对不断涌现鲜活感觉的生命个体的强调。在研读休谟、尼采、柏格森、康德、斯宾诺莎哲学的过程中,德勒兹和瓜塔里为主体寻找到了欲望-机器这样的一个“生成”点,并用“块茎”总结了它存在的特点。生成不是传统上对二元对立的彻底消解,而是一个不间断的生成异质的过程从而对抗同一的主流价值和实体概念。生成的场所是无器官的身体,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具有灵魂的身体,而是如尼采所言是多种异质的力的集合。身体就是偶然性的产物;它就是一群个体化的冲动相互作用的场所,这种作用就是为了产生构成人类生命的那种间隔,这些冲动的唯一的愿望就是使它们自身去个体化。[6](P10)由此,康德的先验主体的统一性和凝固性被异质性、多样性、流动性和生成性所取代。主体不再是自说自话的孤立和超验的个体,而是生活在各种力量交织而成的关系网络中,在欲望的驱动下,主体如块茎生上的点一样,不规则的跳跃式生成,没有固定的目标、没有终结,只有在“逃跑”过程对独断思想的回应、躲避和反抗。
非理性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打破了传统观念中人、意识、主体三位一体的存在成为绝对的“在场”的理念,解开了“自由人文主体”的辖域,为后人类主体多样的生命样态打下了理论基础,科学的发展和高新技术对人体的介入又从实践上推动了后人类主体的自然生成。
二、技术打造的主体:身心的分离和自创生主体
佩普勒尔(Robert Pepperell)在《后人类状况》(1995)一书中将“后人类”定义为人类“在延展的技术世界的一种存在形态”。[7](P32-33)后人类主体的生成除了质疑西方启蒙传统和人类理性及主体建构外,还从技术和科学进步前提下对人类物种本身展开反省,彰显了人类日益技术化和技术日益人格化的当代发展趋势。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进步,“人从来都不是‘自然的’,至少从创造文字开始,人类就在一直凭借知识、物质和科学技术增强自身的能力。”[8](P98)但是传统观念认为技术与人是截然两分的关系,技术是无生命的、被动服务于人类的意志和需求的工具。在传统思维方式中,控制的概念以及‘主 仆’关系的隐喻,是用来描述人与自然、人与技术工具之间关系的最有影响力的方式。”[9](P16)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造就的机器人、电子人以及生命科学技术创造的器官移植、试管婴儿、克隆技术、变性手术、身体整形术、基因编辑等奇迹,表明技术已经全面地介入人类的身体,从基因构成到生命本质等方面重新构造人类形态及其存在,“技术已经不是手段,技术成了一种揭示存在的方式。”[10](P12)电子人(Cyborg)也被称为赛博格,最早出现在诺伯特·维纳1948发表的《控制论—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一书中。“赛博格”的意义是,人工科技制造的无机物构成的机器作为有机身体的一部分(包括人与其它动物在内)从而使生物体的能力得到增强或强化。随后,生物学研究从控制论中得到启示,从功能主义上理解的、以有机体为中心的科学,转化为从控制论系统上所理解的、研究自动化技术装置的科学。人类原先纯粹的自然肉体或生物肉体被镶嵌进了许多高科技物质,如人造血液、人造肢体、人造器官、人造皮肤等,传统人文主义定义下的拥有自由意志、高贵尊严、征服和改造世界能力的理性主体,变成了技术打造下的新的主体。正如哈拉维所写,20 世纪后期是我们的时代,也是一个神话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全都是吐火女怪(chimera),在理论上和实际上成为机器和有机体的混合物;总之,我们是赛博格。[11](P79)控制论和生物学的结合,推进了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合作。1950年,计算机之父图灵依据人机对话的结果指出,计算机可以具有人类智能;20世纪80年代,汉斯·莫拉维克在维纳信息论的基础上提出,人类的身份(人格)在本质上是一种信息形式,而不是一种实体化的规定与表现,人的意识可以被下载到计算机并且存储起来,“世界就是一部真实的而非隐喻的图灵机,就是永恒计算的一部分”。[12](P119)人类主体可以通过意识操控和抛弃身体,身体不再是意识的宿主,俨然变成了一种可以脱离主体的“假体”,后人类成了“一种各种异质、异源成分的集合,一个物质—信息的独立实体”[13](P5)。
如果说图灵实验和莫拉维克的实验还是在讨论静态状况下意识和身体能否分离的问题,马拉图纳的技术自创生理论则从动态变化的角度赋予了机器完全的自主性和主体性。“根据马拉图纳的观点,生命组织保存自身的自创生组织的能力,是它们作为生命系统的充分必要条件。所有的生命系统都是自创生的。”[13](P182 )以此类推,所有的物理系统,如高级的智能机器如果可以像人类一样接收、储存、检索、转换和发送信息,在应对外界环境时,还能够自我组织、自我复制和演化,那么他们就是自创生的,那么也可以说是有生命的。自创生理论赋予机器完全的自主性和本体性,这不仅使生命定义超越了传统人文学的视野,也开创了一种新的理解生命观念和人类主体性的视野。
后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密切关系很容易让人把它和超人类主义混淆在一起。如我国有学者认为,所谓后人类主义,是一种以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太空技术和因特网等高科技为手段,对人类进行物质构成改造、功能提升,使自然的进化让位于以遗传科学为基础的人工进化,达到“提高智能,增强能力、优化动机结构、减少疾病与老化的影响”,甚至达到延年益寿、长生久视之目的的理论思潮”……简单地说,后人类主义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制造出能够在体能、智能、寿命等方面超越人类极限的“后人类”,如电子人、机器人与生化人。[14](P39)这个定义实际上与“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并不匹配,而是更贴近“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的内涵。超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主义都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与技术发展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超人类主义的英文是tranhumanism,trans作为前缀,表示“横贯”,“通过”,“到……的另一边”,同时还兼有转移,变化之意,所以,超人类主义指的是人类发展的过渡阶段,在这个过程中要经历“人类增强”(human enhancement)的变化,在此意义上,超人类主义也被翻译为H+,它的目的是研究智力生命进化的连续和加速,在增强生命的原则和价值的引导下通过科学和技术超越当前人的状态和限度。[15](P3-5)
但是,超人类主义利用技术改造和增强之后的人类主体与后人类主体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超人类主义是一种带有强烈技术乐观主义色彩的思想,这种取向其实继承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的无限完善性等观念,认为人类可以通过技术在心灵和身体上成为至高无上的存在者,从而成为外在自然与人类自然(生命)的主宰。超人类主义者提出,如果能为大脑提供无限的记忆、无限的计算能力和即时的无线通信能力,就能生产出一个智力无与伦比的人类,这样人机混合技术的发展将出现质的飞跃,人类本质的纯粹精神终将可以逃离有限的生物躯壳。后人类把技术生命本体论纳入主体生成的视野中,对技术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后人类虽然也提出人类身体和意识分离的可能性,但是,在1960年,控制论的第二波浪潮就提出了“反身性(reflectivity)”的概念进行自我批判;后人类理论家海尔斯反对自治主体和离身性的幻想,她坚持人的概念和边界依然依赖具身性的各种要素,认为人的身体与意识、人与技术(工具)、自我与他人实际上并不能截然分开,技术只是揭示人类生存的一种方式。因此,后人类关注的重点是技术创生新型主体的可能性以及人类的主体内涵与外延如何得到扩展,从而实现“后”学消除中心、消除总体、消除本质的目的,正如哈桑所言,后人类主体是现代社会的普罗米修斯,他具有恶魔和救赎者的双重身份,担负着解放人类和颠覆旧世界所有秩序的神圣使命。
三、作为他者的后人类:动态的交互合作的关系网络
在西方,人的概念的确立是从与对人相对的事物的比较中确立的,古希腊的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斯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文艺复兴中的思想家把人从神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提出了“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肯定人的力量,价值与尊严,启蒙运动把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概念上升到政治层面,确立了人作为例外的理性主体的权利。之后,又经过笛卡尔、康德和黑格尔的论证,以理性为主体的人最终在与非人的层级结构中登上了不容置疑的存在链的顶端,成了一个特殊的主体性的“自我”,自我之外的事物就成了与之对立的“他者”。自然是人类要征服的“他者”,动物是人类要驯服和可以随意屠杀的“他者”。但外部世界的差异对象除了环境和动物,也包括人类内部的等级差异、族群与文化的差别对立。性恋化的他者(女人)、种族化的他者(有色人种和土著)和自然化的他者(动物和环境)被排斥在“人类”的范畴之外,成为普世人文主义要么同化、要么驱逐的对象。20世纪60年代的解构主义和反人文主义、生态后现代主义浪潮从人与“非人”的价值体系和伦理关系出发,为后人类重新审视人类的本质并与非人类他者构成对照性批判,进入互动融合的和谐共生关系奠定了历史和理论之路。
福柯在《词与物》(1970)中将人文主义的傲慢消匿在“人之死”的宣言中,维特鲁威人作为完美比例的经典,成了一个偶然的话语建构物,这个话语又在德里达延异的无限重复中散播,暴露出人文主义普世价值观的虚伪性和霸权性。女性主义者弗吉尼亚·伍尔芙很早就注意到文学作品中女性只说男人话语的失语状态,西蒙娜·德·波伏娃犀利地指出了“人造女性”的本质,露西·伊利格瑞揭露了古典人性是欧洲的、白皮肤的、英俊强壮的男性本质。克里斯蒂娃呼吁打破男性主导地位的统治,向多样性的“内在的他者”开放。德勒兹用无器官的身体彻底消解了男/女、内/外之间的差异,用生成来解释主体的偶然性、流动性和差异性,把各种异质元素统一在一个自由流通的世界中。
德里达则从动物他者对主体的观看入手,解构了传统中认为动物缺乏言说(理性、赤裸意识、道德伦理)的能力的谬论。德里达通过解析与猫在浴室中相遇的事件的本质,指出作为“他者”的猫并不是一个被动的他者客体,猫对赤裸的主人的主动观看,使其感到局促不安并产生了羞耻感,此时的猫从他者客体变为观看的主体,而被观看的“我”则成了客体,猫引发了“我”的伦理回应,使“我”放弃自己的欲求去帮助它,“我”放弃了对猫的控制权,心甘情愿满足了他者-猫的欲望。生态女权主义理论家查伦·斯普瑞特耐克(Charlene Spretnak,1946-)指出宇宙间唯一的主体不是人,也包括自我扩展了的边界-自然。宇宙是我们生存的场所和依据,我们努力创造出了地球上的衍生物,所有的存在都在他人的思维之中,通过宇宙之链连接在一起。“人处于由宇宙/大陆/民族/生物区/社区/邻居/家庭/个人构成链条之中”。[16](P550-553)从表面上看,人作为社会原子,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但实质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内在统一的。我们不但与土壤、岩石、行星、动物和植物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且我们与土壤、岩石、行星、动物和植物一样,都是宇宙展现过程的一部分。
后人类主义批评与“反人文主义”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但在对待“人”的地位方面,它与反人文主义话语分道扬镳。反人文主义者习惯上通过与人类的遗产进行根本的、有时自称是科学的决裂,从而有力地粉碎人文主义的霸权。…… 然而,后人类主义通常不是把人文主义贴上不合法标签,而是将它的内在不稳定性作为出发点。[17](P374-375)关注他者之间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强调与他者(包括机器)之间的相互依存,因此,后人类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批判方式。沃尔夫对此有非常详细的解释,当“意义”被从意识、理性等封闭的形而上学之中解蔽出来以后,人类在沟通、互动、意义、社会性的意指(social significance)、情感投注方面的模式才能够得到更加具体的描摹。它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曾被理所当然地认定的人类经验,包括智人种正常的感知模式和情感状态;把这些经验置于其他所有生命体的整个感觉机制、置于这些生命体的“建立一个世界”的自创生方式中再语境化……当我们在谈论人的特殊性——在世的存在方式、认知观察描述的方式,我们也必须强调,人在根本上是一种虚拟(prosthetic)的创造物,他与技术、物质性以及那些完全非人的形式共同进化。[3](xxv)因此,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如何与他人、动物以及机器建立关系纽带,从而增强所有生物的力量是后人类主义的核心。赫布莱希特和卡勒斯指出,后人类主义要关注各种形式的拟人论、人类中心主义和物种主义,同时允许动物的人类化和人类的动物化,因此如何思及动物(thinking with animals)至关重要,因为忽略动物的在场实际上就是忽略人类未来生命的重要性,非人类动物在人类文化中是能动的:“人类不能脱离认知而到非人类动物对他们自身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结构来说的重要性来思考自身,包括他们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结构。”[18](P4)后人类主义者哈拉维在德里达动物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人与动物的伴侣关系和人类与机器共融的赛博格形态。哈拉维从女权主义者的立场出发,从肿瘤鼠的杂交形态来思考人类和动物的交往。肿瘤鼠是一个为了拯救女性乳腺癌而被制造出来的动物,哈拉维亲切地称其为“我的兄弟姐妹……雄性或雌性,她/他是我的姐妹”。[11](P79 )肿瘤鼠打破了纯净的血统、自然生育和死亡的法则,解构了性别论上的男女之间的差异,也颠覆了一直以来被视为绝对他者的动物和机器的被动和从属地位,以隐喻和想象的方式将我们对后人类主体的理解建立在流变性和多元性的图景之内。布拉伊多蒂在反人文主义和解构主义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后人类主体的游牧性,并将其定位于同多样化的他者关系流的肯定性纽带中,建立了一个更大意义上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交互关系网,将先前隔离开了的物种范畴和领域,以普遍生命力为中心的平等主义原则重新连到一起。这个有活力、有组织、充满了普遍生命力结构的后人类主体并不局限于我们人类,而是一个被扩散的关系型自我和生成他者-生成动物、生成地球和生成机器的过程。拉图尔用超越人与非人的行动者(actant)来取代专指人类的行动者(actor),在本体论层面消除主体与客体、人与物、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创造出一个本体性混合的行动者网络。“人类与非人类的力量在网络中相互交织、共同进化。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非人类力量和人类力量是对等的,两种能量互不相逊,平分秋色,在科学的考察中不能忽略任何一方。”[19](P11)人类其实从最开始就与技术共同进化,技术一直内嵌于人类的生活中,因此就像拉图尔所说的“我们从未现代过”一样,我们也从未人类过—我们天生就是赛博格。
地球是人类和所有物质生存的背景和栖息地,后人类主义要朝向一个以地球为中心的视角演变。迪佩什·查卡拉巴提(2009)指出以地缘为中心的思维模式有助于我们改变古老的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区分,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时候,不再把人类作为一个生物主体而是一个地质力量来考虑。[20](P121)后人文主义是对物质参与性和能动性的强调,巴拉德认为,物质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是处于“生成”过程之中,她认为事物之间的“内在互动(intra-action)” 比起相互作用(interaction)更能准确地表达“物质化”的过程,人类和非人类物质都是通过这种内在互动在操演的,这种操演颠覆了人文主义传统的“主体-客体”关系的认识论,进入了“后人类主义的空间”。[21](P478-475)在这个空间中,作为他者的后人类,不仅是一种活力物质和技术自创生的主体,而且是一种包括了人类,动物和地球整体在内的自然-文化的连续体,具有德勒兹和瓜塔所说的动态的生殖性力量,可以在所有虚拟力量的无限扩展和跨物种的流变中进入一个全球性的空间。
结论
后人类主体的生成是对文艺复兴和启蒙传统推崇的封闭理性主体的敞开,是在技术发展基础上对自然人类主体的扩容,是重新审视人类的本质并与非人类他者构成对照性批判,与机器、动物、自然环境最终进入合作关系网络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分析后人类主体的生成路径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其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后人类直面20世纪下半叶以来新科技革命对人类生存境遇和生命样态改变的现实,把建构理论从人类社会范畴扩展到了对动物、自然和人工机器的研究上,特别打破了现代性哲学文化中二元结构为对立双方划定的区域,努力打通分界,甚至驻足于分界处,使其成为新型主体话语的生长之地,无疑比此前的各种主体话语更有活力,必将影响和推动新的文艺理论话语范式的发展与创新。其二,分析后人类主体的生成也有助于我们构建新的批判理论框架,在人类,生态,环境,技术的全球生命共同体的蓝图中为走出后人类困境做出新的理论设计。但是,目前从这三个路径出发来分析后人类主体的生成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一,因为人的概念和边界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正如后人类理论家指出的并非我们人人都能够肯定地说,我们一直都是人。所以,后人类主体的生成还是一个在途中的探寻过程,其所引发的理论位移还远未完成。其二,后人类主体是一个正在绽开的视域,后人类主义研究的批评家或艺术家在勾画和推动这个动态的创造性进程中难免出现激烈的论争和不可弥合的裂隙,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后人类的繁复性与不确定性。但是,无论后人类这一主题如何扑朔迷离,讨论的中心话题都绕不开对生命本质、身体政治以及技术伦理的考量和分析,否则,超越了两元对立而又包罗万象的后人类主体难免会陷入被技术异化和资本操控的境地,真正的后人类幸福只能是乌托邦式的设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