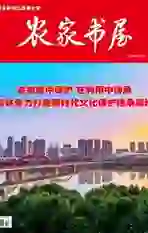《大医之路》
2024-0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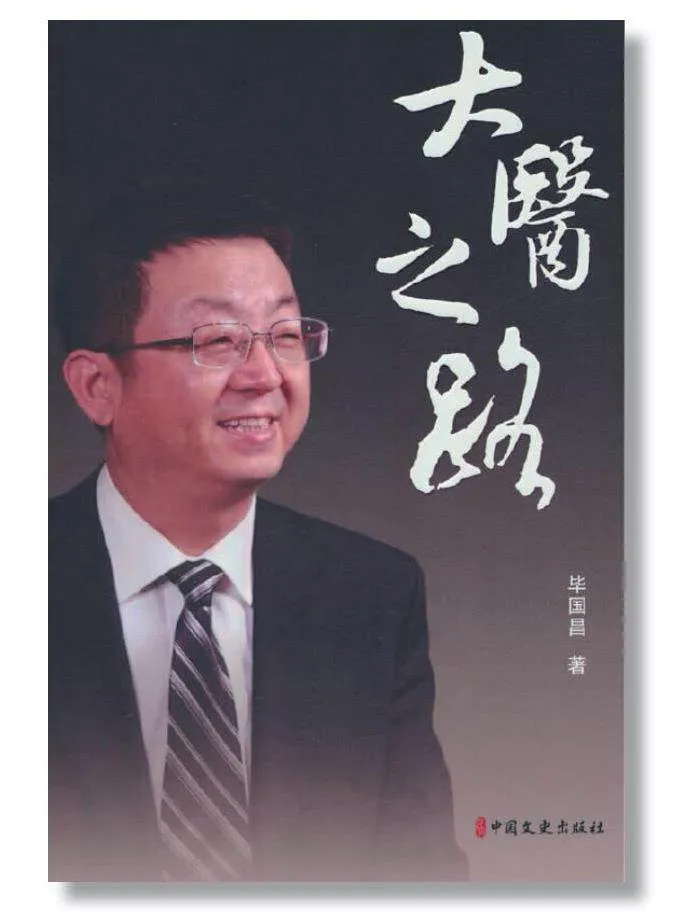
6摆脱手术求健康
大约是在两年之后,小冯又做了一次上述几家医院的“巡回”检查,值得强调的是,重回当年那家坚持给自己做支架的医院,检查证明小冯的冠状动脉基本正常,而左冠状动脉前降支中段钙化斑块、重度堵塞基本消失,末段钙化斑块所剩不多。小冯主动说起自己的这个改变,就是找中国中医科学院曹教授给治的。那位当年坚持要给他做支架的医生听完,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连连说:“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这个绝对不可能!”
“都说东北人实在,还真不如人家北京阜外医院,那位赵主任还真讲真话。”小冯撂下这话,起身走了。
几家医院,不同地点,不同等级,得出同一个结论,那就是小冯的冠心病基本痊愈,这是他最想要的结果。
小冯揣着踏实的治疗结果,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他同以前一样在供热岗位上工作,上班前到老婆开的那个早市菜点儿干上一阵活儿,赚点钱还这几年看病所拖欠的债务。他经常想,假如自己没有找曹教授而是做了支架,不管是在哈尔滨还是在北京,那往后不仅要做定期检查,而且每天都要服药,自己1800元钱一个月,吃了药还能剩下多少?关键是帮助老婆上菜卖菜的活儿根本就干不了啦,自己的工资还不够吃药的,自己和家庭将因这场病陷入严重困难的泥潭之中。曹教授不仅救了自己这条命,而且还救了自己整个家啊!现在自己跟从前一样,对生活充满信心,身体又没大碍,多干点少干点都没问题,欠下点外债不是问题,毕竟自己才40岁出头,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小冯跟老李、老张、文学、小汪他们一样,跟健康人一样,每天重复着过去的生活,在琐碎与平淡中体验着普通人家的幸福、安康与快乐。
太阳照样晨起暮落,每天都是这样灿烂辉煌。曹教授的医术和医德不断得到传播,像穆棱河的河水,一波接一波掀起的涟漪,是那方寸药方产生的力量,它在患者和家属的心中形成的高度认同、推崇和追捧,是再好不过的赞扬。而那些原本并不相识,或是根本不可能相遇的人,一点点地聚合在曹教授的周围。这个现象,无论是在中医还是西医,都是不多见的。应该讲,一个地方,一个区域,有一两名好医生,是人民群众的福音,至少大家在有病有灾的时候,知道去哪儿找谁诊治。
由于老李的作用,M市有近百名患者投奔到曹教授诊室求医问药。那天,M市的王波在门诊部对笔者讲:“我们都是曹教授的患者,M市的患者能有100多人,可以说形成了一个‘M市帮’。为啥都跑来看病?因为真的能救命呀!”
而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曹教授有着悲悯之心与精湛的医术,他为此又要付出多少休息时间和多少心血?
7慈心仁术成就他人幸福
由于老李的性格使然,他将曹教授的慈心仁术快速地传了出去,于是M市一个接一个的患者在曹教授那里得到了成功救治,形成了一个M市群。这个群体的形成极具现代社会特点,多数是朋友或亲属关系,通过微信或电话宣传中医药的确切疗效,大幅减轻了东跑西颠求医问药的疲惫与困惑。短短几年就有百余人在曹教授那里获得了新生。这是对疾病的抢救、对健康的修复,是爱的传递、生命的延续。
M市数以百计的冠心病患者会集到曹教授的门诊,传出了若干感人肺腑的故事,这无疑也是在传承中医药优秀文化,彰显中华民族的国粹在当代依然具有闪闪发光的力量。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最近连续发声力挺中医,他有一句话是很符合逻辑的,他说:“中医很科学,很环保。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个靠的是中医,西医引进才两百多年。”“不是中医,难道是西医?”
张艺谋是位睿智的艺术大家,对中医药的认识也是这样深刻。笔者想起了扁鹊、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叶天士等中国历史上若干中医药大家,是他们不断丰富着中医理论和实践,支撑了我们这个民族世代繁衍、生生不息。曹教授继承和发扬了先祖圣贤的中医药文化,在具体的临床实践中稳步推进中医药的发展,至少在当下我国冠心病如此高发、患者如此众多的情况下,他的处方是具有时代意义的,有着开路先锋式的标杆作用。像M市这样的群体还有许多,比如在我国东北部,地处大兴安岭南麓向松嫩平原延伸的过渡地带,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三省区交界处的一个县级区域——扎赉特旗,也有着同样的患者群,那里发生的故事其实比M市更早,群体更大。
下面的事情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扎赉特旗一位钱姓木匠退休前患上了冠心病,也是在55岁至60岁之间。
钱木匠心绞痛,胸口憋闷,喘气困难,睡眠受到严重影响,诸如此类的症状,与其他冠心病患者的反应并无两样,而且呈现病情不断加重的趋势。
钱木匠放下手上的活儿,去哈尔滨,找在哈尔滨铁路局公安处工作的二弟。二弟是公安处的处长,家族有这么一个习惯,遇到大事都去找老二出主意、想办法。
二弟带大哥去了哈医大附属第一医院。一番检查,确诊是冠状动脉重度狭窄,唯一的办法是及时做支架手术。
什么是支架?这种手术国内开展不久,钱木匠听了好半天才听明白,满心地高兴,心想还是人家大城市大地方办法多,自己总算有救了。可一打听费用,顿时眼睛瞪圆了:15万一个,两个就得30万元。木匠不吭声了,转身走了。回到扎旗,跟老婆商量,把两间房子卖了,再凑凑,也够30万元,可都给了医院,往后的日子咋过?还得留点过河钱不?给儿女留点不?
思来想去,木匠终于想明白了,自己已经是土埋半截的人了,就是死了也不算太亏,做支架手术怎样,不做支架手术又怎样?于是,他又给二弟打电话,让他再想想别的办法,反正这个手术是不做了,不是因为别的,实在是做不起呀。
钱木匠与二弟商量好后,再次来到哈尔滨。二弟领着大哥去了曹教授的办公室。
当时曹教授还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是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医学博士,因治疗心肌炎等心血管疾病而颇有名气,在校园内与社会上被传得神乎其神,找他诊病得半夜排队挂号。
曹教授听完木匠的陈述,经望闻问切四诊,辨证分析后,当即处方开药。站起送客时,他很自信地笑道:“如果吃药后觉得有效,来个电话,我再给你调调药方。”
钱木匠揣好药方,在哈尔滨转了一圈儿,便打道回府。当天早上去的,当天又回到扎旗。从程序到内容,都显得过于简单。更主要的是,人家连挂号费也没要,属于朋友之情谊。
木匠并没有在意这个中药方子,揣在上衣口袋里,没有马上抓药服用。两张纸扑克牌大小,只有那书写的字显得一板一眼、工工整整,而且横竖有韵,用笔遒劲,结体隽永。木匠文化水平不太高,所以格外看重人的文化素养,他认为有无文化,首先看字写得如何,这或许有些道理。那天,在曹教授办公室,他见到的曹教授就是一个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人,首先从接人待客上,举止做派彬彬有礼,声音不高,让人感觉到了他的真诚和谦和。而这张处方上的字迹也印证了人家的这种儒雅。木匠将它放进贴身的衬衣上兜,是因为喜欢。此时木匠只是看到了外在美,还没有发现其内在的神奇。
因为头天晚上没有睡好觉,干过一阵活儿,觉得心绞痛、胸口闷、喘气困难的毛病都一起找上门来了。这时木匠方想起那个已被收起的药方,立马抓药、煎药、服药。或许是精神作用,第一服汤药下肚,木匠就感觉症状有所减轻,这无疑使他重视起来。这个草药能有那么神?曹教授笑盈盈的面容又浮现至眼前,那天他还说了一句话:“如果吃了觉得有效,来个电话,我再给你调调药方。”
“人家那叫心里有底呀!”木匠猛地拍了下自己的大腿,“如果心里没数,人家能这么说吗?”
接下来,钱木匠是一服接着一服喝起汤药。服药3剂后,木匠的气短、气不够用的感觉明显减轻。大约服十几剂药后,木匠真真切切地感觉到身子骨轻松多了,那隐约的胸痛与胸部憋闷感都明显减轻了。
木匠来劲儿了,药还没用完,他又抓了20服。他兴奋地跟二弟在电话里称赞起曹教授:“别看人家曹大夫那么年轻,药却是真灵。”这时,老二告诉大哥,在哈尔滨找曹大夫看病得半夜两三点排队才能排上呢。钱木匠告诉二弟:“我发现曹教授的药还真有特点,药味并不多,才十几味,都是药店买得到的普通中药,不仅不缺,还相当便宜。”
后边的事情悄然无声地继续发展下去,曹教授的药在木匠体内形成一种力量,似绰尔河畔的春风,悄然静寂地溶解着木匠几条血管几十年淤积而成的斑块,那几条狭窄的血管在中药作用下,缓缓地释放了一种能量,一个涌动向前的推力加快了血液的流淌。
木匠没有想那么多,他同往日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恢复了正常生活起居和工作,只是早中晚增加了服用中药的流程。他的血液循环在改变,这个改变是在钱木匠主观上并不敏感或并不自觉的状态下进行的,却悄然推进血液流速流量的改变,修复并提升着血管的通畅能力。
钱木匠是一个方子吃到底。他觉得这药好,真好,这么有效,没必要再换药方。断断续续地喝了六七年汤药,只是偶尔因别的事,才去哈尔滨找曹教授调调药方,那时曹教授已经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校长,而钱木匠已迈进耄耋之年的门槛,身体还是棒棒的。
若干年后,钱木匠的弟弟提起此事,说:“啥人啥命,我大哥就是有福,不做那个支架,也没花那么多钱,没遭那份洋罪。那么缠手的大病,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好啦。这得亏是找对了大夫,85岁了,没有什么疾病,真心感谢曹教授啊!”
8无声胜有声
木匠的病好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有人留意,有人留心,更多的人是无心无意,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冒了。扎赉特旗原本是个不大的地界,谁跟谁差不多都认识,留心留意的,多半是自己或是家人有心脑血管疾病。这个病如果找西医治疗,做一个支架当时的花费都得10多万元,90年代初,一个家庭能有多少积蓄呀。花钱遭罪不说,还有很大的风险和许多没完没了的后账。中医不光能治好,而且能让身体越来越好,治疗费用一般人都能够承受,重要的是不用终生服药啊。
那天晌午,日头高照,钱木匠同工地上的一位兄弟扛起一根大圆木走了100多米,撂下后,也没歇息,操起木锯,接着就干起了活儿。那位兄弟愣愣地瞅着他,半晌说不出话来。
正在锅炉房处理照明电的电工小于眨了眨眼睛,脑子里转起来:看来老钱的病是真治好了,和健康人一模一样的,他真找到一位杏林高手啊!
“大哥,等哪天你把药方带来,我也抄一下。”小于放下手上的活儿,跟老钱要药方。
“咋的,你也想吃?”老钱笑嘻嘻反问道。
“我大哥吃,他的冠心病也挺重。”小于唠起大哥的心脏病,说,“仅冠心苏合丸就吃了有一土篮子啦。”
老钱问小于:“那么他都有什么症状呀?”
“凡是冠心病的症状他全有。”小于典型的东北黑吉一带的口音,“胸闷呀,心绞痛,放射性那种疼痛,阴天还上不来气儿,说话气儿不够用呀,胆小呀,自己没事找气生呀,吃一点饭就胀肚呀,睡不着觉呀,难受的事多了去了。”
“好了,别说了,我现在就回家给你取。”老钱为人实在,跨上自行车就去取药方。
“钱大哥,不用急,不着急呀。”小于在后边怎么喊都不管用。
只是十几分钟的工夫,老钱回来了,递给小于一张巴掌大小的处方笺,虽有些喘息,但呼吸还是非常均匀的:“冠心病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说没就没呀。这药方,管用,真好使,赶快用。”
小于谢过钱大哥,放下手上的活儿,走进一家药店。那药店不显眼,在农电站的后身,被一片片高低错落的住宅楼包围着,一般人不注意还找不到。
这是一个小药店,只有一位坐堂医,是一个姓张的中年人。本来张医生并没有在意这个药方,他抄了一遍方子,然后又在一个计算器上核算了一下价格,便面带微笑地问道:“40服才这点钱,治啥病的,这么便宜的药?”
“治冠心病的。这个方是我们单位老钱的,他吃了很有效。”
“就那个老头儿,有70多岁了吧?”张大夫问,“他有效,并不等于你有效呀。冠心病?”张大夫困惑的眼神在小于的脸部上下移动,半天才似乎转过向来。“好吧,稍等。”张大夫转身向药柜走去,那并没有穿白色大褂的背影,使小于心中对这药店产生了一丝隐约不安的情绪。哪来的,因为什么,小于也说不清楚,那只是一种感觉。
“你开的药多,对我不是坏事,可是你得想好,药品不是别的,是不能退的。”张大夫左手拿着秤,右胳膊伸向药柜时,还不忘叮嘱小于。
“谢谢!放心吧,出事了也赖不上你呀!”小于明显不快,让对方懂得不必多说。
小于转身出去了,张大夫开始认真琢磨起这个方子:黄芪、党参、瓜蒌、薤白、法半夏、白术、茯苓、川芎、木香、柏子仁、枣仁、生龙骨、甘草、生姜……
“这些药既不缺也不贵,一服药15.6元。”小于一边嘀咕着,一边将一包包草药标注好名称,再装进两条尼龙丝袋子。
小于径直去了邮局,将这40服草药邮给大哥。大哥住在北京女儿的家里。
这边,张大夫却是看着这药方发愣:就这些药,能治好冠心病吗?张大夫虽说是赤脚医生出身,但是他坚持实践出真知的道理,生活中一些好方、妙招都可能经过自己的手,善于识别,加以应用,将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东西,自己不就有声望有名气了?所以他格外注意一些药方的出处、疗效。他曾经尝过这种思路的甜头。
真实的生活远比想象的更曲折,更富有戏剧性。
小于的大哥收到了那两大包的草药,并没有马上用。首先是大嫂持怀疑态度,逻辑很简单:“这么吃能行吗?又没找大夫看,就吃药。”
“老三说行嘛。”大哥回复老婆。
“老三是大夫啊?他说行就行呀?”大嫂一句话就给大哥噎了回去。
大哥在心里也犯嘀咕:“是呀,怎么知道这药有效呢?老三是个电工,说说电器的事还八九不离十。”
小于不知道大哥这边的情况,还掐算着日子呢,根据钱大哥的用药经验,他开始推算大哥用药后的效果。
10天后,小于打通了大哥的电话:“怎么样,服药后感觉怎么样,有效吗?”
大哥在那边回复:“还没吃呢。上次从医院开的药没吃完,等吃完的吧,两个药也好有个比较。”显然,大哥和大嫂事先已做好了回应的准备。
又过了10天,小于又把电话打了过去。大哥在电话里讲:“再等等,我最近心脏的感觉好像好了一些。”
又过了20多天,当小于听到大哥讲,那40服药还一点都没动呢,顿时就怒火中烧,知道问题出在大嫂身上,于是直接说:“大哥,你把电话给大嫂。”
“什么事啊?”大嫂在电话那边有点紧张,语调里明显流露出一些不安。
“大嫂,那是我亲哥,我能害他吗?”
小于有话直说,弄得大嫂在电话那边不敢多说,赶紧回道:“还有两天,上次医院的那药就吃完了,就两天啦。”也不管电话那头还要说什么,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本来,在一个家族里,三弟关心大哥的疾病,主动推荐了中药,还花钱费力抓了药,又不厌其烦地寄到京城,这体现了兄弟的亲情。谁料,这事受到大嫂的阻止,她不理解三弟的这份热心好意,觉得这事不怎么靠谱,天下的事怎么会这么简单?
一般情况下,大嫂这样的一种推断不无道理,如果都比照别人吃中药的效果去抓药服药,那得有多少医生失业?
可是就这个逻辑,在曹教授这里就被突破了,后来发生的事情,说明一切都有可能,事先妄加揣测是没有依据的。小于的大哥在小于紧追不舍的督促下,开始服用曹教授的中药。使他意外和惊喜的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首先是喘气不那么困难了,心绞痛减轻了,胸闷乏力的症状明显地得到控制。而睡觉的改善,也带动了整个人的精气神,就连吃饭也不一样了,那种食不甘味的状况也发生很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让大哥喜出望外,大哥兴奋地打通了三弟的电话:“老弟呀,再给我开点中药啊,那个药好使,真好使。”大哥在电话里情不自禁地夸起小于给他抓的这药,“你那个药方从哪儿淘的?真灵,真就是灵丹妙药!”大哥告诉小于,吃到第五服药时,他就感觉气顺溜了,身子骨舒服了,晚间睡眠也随之改善了。“睡觉睡得香,好幸福呀,多少年了,多少个夜晚,睡觉那叫一个难,真难,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气不够喘,怎么能睡得好?这回真找到了管用的药,我能不激动不高兴吗?”
小于是个倔强之人,电话那边的反应是冷冰冰的。知道三弟还在生气,还在挑理,于是大哥就把责任推给了自己的老婆:“都是你大嫂误事,开始不让我吃中药,如果早吃不是早好了吗?”大哥那边一通认错,才让小于顺过气来:“再给你抓60服吧,凑100服,怎么样?”
撂下电话,小于笑了:“我能害自己的大哥吗?你是我亲哥啊!”于是直奔药店按老钱的药方又给大哥抓了60服药。
之后3年多的时间,大哥不间断地让小于买药,然后寄往北京,他们感觉这地界中药便宜得多,而且质量还好。
就这样,在3年多的时间里,大哥的症状几乎消失了。在自我感觉上,大哥觉得自己已经被治好,可他自始至终都没有见过曹大夫,他同样认为,既然服药有效,那就接着用呗,省得再麻烦人家,听说曹教授忙得不得了,号也不好挂。大哥再没有因为心脏的事去过医院,这也是实情。
这种简便、省心、省钱的治疗也算民间一种创举,在大哥的老家扎赉特旗得到一些百姓的认同。基层群众有基层群众的文化,在他们看来,同样的病,用同样的药,效果应该大体一致。有趣的是,老钱几年一贯制的用药歪打正着验证了曹教授治疗冠心病的优势。曹教授通过温阳益心法治疗冠心病的临床研究结果显示,有效率达90%以上。
约30年后,小于跑到北京找到曹教授诊病,曹教授才知道竟然有这么一档子事。对此,曹教授不置可否。我们无法揣测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但我们可以由此推断,30多年前他就有了可以成功挽救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患者,使他们免于手术刀之苦,恢复健康的医术。
9诊疗方式的选择
许多事情存在着内在逻辑,只是多数时候是后来才会弄明白。小于给大哥按方抓药寄药,忙着忙着,发现自己也患上了冠心病,大哥说的症状自己慢慢都有了。“这病咋跟传染病似的,我也得上了。”小于在电话里告诉大哥,“现在我也在苦苦地煎熬着,晚上睡不着觉,自己坐在床上,身上披着棉被,常常是一个小半夜就坐在床上,没有一点睡意,那个难受的滋味甭提了。去医院一查,果不其然是冠状动脉狭窄。”
药方在自己的手里,医院又给了这么明确的结果,那么直接抓药吧,至于支架,只有拒绝了。
小于上山下乡时曾经当过兽医,学徒时跟着师父摆弄中药。几十年前,师父给牛马羊等牲畜治病,也经常弄来一些中药,先煮一遍,让小于先喝,喝完还要把味道及流淌到脏腑的感觉说给师父听,师父就是用这个办法提高了小于对不同中草药不同味道的辨识能力,进而再体味药性,以便日后运用。从那时起,他就练出了辨识中草药的能力,现在他为自己的病又启动了这个久违的技能。若干年后,他与笔者唠起曹教授开的中药。他说,喝曹教授的中药,一入口,他就能感觉到一种特别的味道。他把曹教授处方上的药都研究了个遍,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解读,主方是从什么脏器切入的,配伍的药大概是起什么作用的,君药是什么,臣药又是哪几味,根据药方的排序猜测。瓜蒌、薤白、黄芪、党参、木香、枣仁、半夏、白术、茯苓、川芎,每一味药,他都在百度上查询一下,药性、药理、功用等各项指标都有解读。他告诉笔者,原方上的每一味药,他都先单独煮过,都喝过,目的是细细品味,体味药性,然后把味道和流淌到脏腑的感觉都记录下来,再反复查找药典,搜索百度,调动自己已有的一些中医药知识,再一味药一味药地对比自己的认知,挖空心思地理清药方的配伍,消化理解这个方子的奥妙所在。这个工作让他非常自觉地意识到,这个药方确实有效,而且他能分辨出哪味药或哪几味药在发挥关键作用,是君药,哪几味是起辅助作用的,即所谓的臣药。这不仅令他增加了知识,也让他提高了服药的自觉性,无疑起到精神上的助推作用。
应该说,皇天不负有心人,小于如此认真地研究使用曹教授的中药方,效果也真的不错。在服到第五六服时,他身体就有了感觉,心前疼痛等一些不适感程度减轻,使他有了如同卸下重负的轻松。
服药大约有三四年的时间,查心电图就已经恢复正常了,在这一过程中,他从始至终都没有见过曹教授。不能不说,曹教授的这个原方带有一定的广谱性。民间的复制这样有效,或许曹教授也始料不及。
那药方犹如一个救命的火种,在内蒙古大草原上点燃一盏盏生命之火,让更多人在生命的征程上看见希望之光,重新扬帆起航。
小于的治疗效果相当于黑龙江省M市的老李,也可以说老李和小于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干了同一件事,即主动或被动地传播着曹教授的医德仁术。其实,小于参与传播比老李更早。写到这里,笔者不禁会联想,这是笔者偶然间发现的两个群体,称为扎赉特旗群与M市群,那么在其他地方有没有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几年后,小于又添了新病高血压,这时他想到去北京找曹教授,问问曹教授治疗高血压有没有好办法,这是老钱那个中药方给他的启迪,更是他对素未谋面的曹教授的崇拜。得了新病,自然而然在第一时间想到找曹教授。
小于下决心进京,当时他想,不管挂号有多难,他都要找到曹教授。应该是2017年4月26日,笔者在中国中医科学院门诊部碰上小于和他弟弟以及他们的家属,他们是一家结伴前来找曹教授诊病的。
在诊室外边,我同小于哥儿俩唠起了找曹教授诊病的过程。
小于笑了,是那样真诚:“以前,我虽然没找过曹教授看病,可没少吃他开的汤药啊。刚刚我又找到他,我的高血压控制得不错了。”
我和小于兄弟聊着聊着,又聊回老钱用过的那个药方。他从手机上调出来给我看,就是老钱当年在哈尔滨找曹教授时拿到的第一个药方(现在记录在手机上,如今的传播手段更快捷,只需几秒钟)。小于告诉我:“这个药方就是钱木匠用的第一个方,经我就给出200多人,可以说大多数人都收到良好疗效,个别人没效。”他进一步解释,岁数太大的没有效,女患者的效果差些,但也不能一概而论。他们那儿有一位老太太,开始心脏不舒服,症状跟他差不太多,她把方子要走了,一吃就是几年,人家也不调方,后来她讲心脏病吃好了,说得谢谢他,也谢谢并不认识的曹大夫。如今老太太80多岁了,耄耋之年,却拥有一个棒棒的身体,现在还为一家十几口人做饭烧菜,好不精神,周围邻居都非常羡慕。这20多年来,小于兄弟几人,在扎赉特旗反反复复做着这样一件好事。让于家兄弟欣慰的是,经常会收到一些亲朋好友的感谢:“哎呀,你给的那个药方真好使呀,我的心脏病应该没啥问题了。”“老于家他大哥,你发给我的那个药方真灵,现在我心脏不舒服的毛病都没了,不然是不是就得做支架呀?那得遭多大的罪呀!哪天请你吃饭啊。”
每当碰上这种感谢,小于兄弟都会笑着解释:“这可不是我的药方,是人家曹教授的药方。人家是咱们国家的中医大专家,要感谢人家曹教授啊!”
小于大多是在张大夫那里抓的药,这不能不引起张大夫的高度重视。张大夫认识到这个药方肯定是有效的,否则不可能有这么多人重复使用这个方子,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逻辑。后来,张大夫真的靠这个原方赢得不少信誉和夸赞。有人在“外圈跑道”上救治了不少冠心病患者,也是一件好事。那么,张大夫之外是不是还有“外圈跑道”呢?
起始是在老钱这儿,主线是小于这儿。于家兄弟几个用曹教授的药方在亲属、朋友圈内燃亮了中医药救治冠心病的火焰,而出乎意料的疗效又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于是更多的人开始传颂这个药方的确切疗效,给许多家庭带去了安康、欢乐和幸福。这正是曹教授的初心。
这些都是那个小城里的故事。曹教授这个药方的疗效如此确切,它的方便、廉价,深受民众普遍认可和欢迎。
有趣的是,小于兄弟一家人开始跑北京,直接找到曹教授面对面诊病时,一些脑瓜灵光的亲戚朋友也跟着进京诊治。2017年4月26日,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一次来到中医门诊部的就有20多人。小于兄弟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一批批患者带到北京曹教授的面前。这对一名医生而言,无疑意味着群众对他的一种高度认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