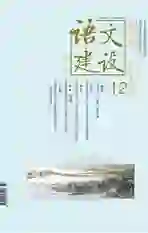“吕叔湘之问”的新时代解决方案
2024-01-17陆志平
【关键词】吕叔湘之问;新时代;语文教学;语文课程改革;解决方案
在中国语文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吕叔湘先生以他特有的跨文化视野、深厚的学养、科学的精神,参与了中国语文现代教育体系的建设,在知识体系、课程教学等诸多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1978 年3 月16 日吕叔湘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的文章,提出:“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是个老问题,也是当前不容忽视的一个严重问题。中小学语文教学效果很差,中学毕业生语文水平低,大家都知道,但是对于少、慢、差、费的严重程度,恐怕还认识不足。”“十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在百废待举之时,这惊天一问,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中小学语文教学的高度关注,对于推动语文课程教学的反思、研究与重建,发挥了巨大作用。至今,仍然熠熠生辉,激励着中小学语文教育工作者不断改进语文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全民族的语文素养。
“吕叔湘之问”已经过去40多年了,中小学语文教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21世纪初开始的语文课程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语文新课程实际上是“吕叔湘之问”的新时代解决方案。但是,面广量大的中小学语文课堂,总有难以尽如人意的地方,全民族语文水平也有待整体提高。因此,语文界内外还常常有人重提“吕叔湘之问”,并以此讨论语文问题。可仔细推敲,每个人心中的“吕叔湘之问”并不完全一样,对语文教育的期待也不完全相同。
今年,我们纪念吕叔湘先生120 周年诞辰,学习吕叔湘先生的思想,探究“吕叔湘之问”的内涵和本意,研究先生所说“少、慢、差、费”的根源,探讨解决语文教学突出问题的方向和思路,这对深入认识和理解语文新课程,深化语文课程教学改革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吕叔湘之问”的内涵
吕叔湘先生发表在1978年3月16日《人民日报》的文章中所说的当时语文教学中的两个迫切问题,一个是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一个是高等院校的公共外语问题。文章比较短,对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具体问题未能展开论述。而一个多月后,吕叔湘先生在江苏师范学院有一场题为《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1]的演讲,则把他的思想表达得比较充分。在这次演讲中,吕叔湘先生主要指出了课堂教学与作文教学两个方面的问题。
课堂教学的问题是讲解与分析为主。吕先生说,语文教学有讲的传统。以前学的是古文,老师念一句,翻译一句,老师做的是“翻译员”。后来,不学古文了,学的是白话文,学生看得懂,“不需要老师翻译,老师就失业了”,“改行了”,“就不当翻译员,当分析员了”。就“大讲微言大义”,“分析时代背景啊,中心思想啊,文学手法啊,等等”,“有些作品不分析还能感动人,一分析倒不行了。这就叫七宝楼台,拆下来不成片段”。学生听老师讲,就像“听评书”一样,并不是真正的学习。
与此相联系的是,学生阅读量小。吕叔湘先生说:“我们的课本不但小学,就是中学都是薄薄的一本,恐怕世界各国的语文课本论分量,厚薄,没有比我们分量再少,本子更薄的了。我看见过好几种外国课本,起码一厘米那么厚,有的是两厘米厚。而我们呢,几个毫米,不够讲,老师很苦啊!”因此,只能“放胖”,只能“绕来绕去”[2]。
吕先生认为,“教育就是诱发学习者的积极性的、主动的努力,这几乎是所有教育家的一致意见”[3]。“应该以学为主,教师是帮助学生学习。”[4]语文教学“要引导学生自己学习”[5]。学习作品“主要是读,听人读,自己读”,而不是听讲。不能因为纸张紧张而“限制好的教学方法的实行”。同时,要重视课外阅读,吕先生从多个角度强调“课外阅读是很重要的”。
作文教学问题表现在命题作文与作文评改上。吕先生认为,命题作文,“这是种很重要的方法”,但是,命题脱离学生生活,“他无话可说,写不出来”,“只好抄书抄报”。所以“题目要出得学生生活里有”。同时,“我们作文不一定限于命题作文”。比如“改写”“缩写”“听写”等等[6]。总之“就是多写,大作文、小作文、笔记、周记、日记等等都可以”[7]。此外,要重视作文评讲,选择有代表性的作文评讲,而不是篇篇“精批细改”。
我们重温吕叔湘先生的教诲,感到先生就在眼前,讲得非常清楚透辟,直接聆听引用即可,无须多作阐释。先生所说“少、慢、差、费”主要是指,学生阅读量小,听得多,读得少,写得也少。可以自由抒写、写自己熟悉的东西的机会少。老师绕来绕去的分析多,精批细改花的时间精力多,又“徒劳无功”。这就“慢”了,效率不高,效果也就“差”了。既浪费了学生的时间,也浪费了老师的时间,误了学生的青春年华,这就“费”了。这里的关键是“少”,“少”带来连锁反应。2700多课时,大量时间“先生讲,学生听”[8]。“学生的学是被动的,教师的教也是被动的。”“学生是无可奈何地写,教师是无可奈何地改。”[9]教师和学生“愁眉苦脸地在那儿教,愁眉苦脸地在那儿学,效果决不会好”[10]。
二、“少、慢、差、费”的根源
关于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根源,吕叔湘先生认为与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有关,他在《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一文中指出,“一种教学的目的是要学生获得现成的知识,越多越好。与此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就是教师多讲,学生死记,考试就是考你记得多少,能否一字不误。结果是学生脑子里装满了很多现成的知识,但是不会运用这些知识去解决遇到的问题,更不会闯出路子来取得新的知识”[11]。
自古以来,语文学习就讲究“多读多写”,为什么变成读得少,写得少,讲得多,听得多,使得“填鸭式”教学大行其道呢?
自20世纪初,我国开始办学校,语文独立设科,以班级为单位授课,按课时教学,废止读经,推行白话文,语文教学就面对一系列新的挑战。比如,从私塾、书院的精英教育,到面向大众的学校教育,语文教育性质怎么定位?语文独立设科,不再是文史哲不分,语文学科的边界怎么划定?班级授课,一个教师面对几十个学生,用什么方法教学生?按课时教学,教什么内容,怎么组织?白话文一看就懂,怎么教?诸多问题交织在一起,比较复杂,难以简单处置。特别是工业化的大批量、流水线、标准化生产方式和科学主义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着学校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使得知识中心、学科中心、课堂中心、教师中心渐渐形成。在语文学科,按四五十分钟一课时切分学科知识,由教师讲授灌输知识,单篇短章就成为最佳选择,整本书阅读逐渐退出语文课堂,教师讲解分析成为课堂教学的主要方式,学生听讲,死记硬背,做练习,应付考试,也就逐渐成为常态。
中国的知识界很早就发现了这些问题,并且积极探索解决方案。
1923年,梁启超先生指出,“不能篇篇文章讲,须一组一组地讲。讲文时不以钟点为单位,而以星期为单位。两星期教一组,或三星期教一组,要通盘打算”,“不注重逐字逐句之了解”,“用讨论式的讲授”。[12]
1931年,陶行知先生说:“中国的教科书,不但用不好的文字做中心,并且用零碎的文字做中心,每课教几个字,传授一点零碎的知识。学生读了一课,便以为完了,再也没有进一步追求之引导。我们读《水浒》《红楼梦》《鲁滨逊漂流记》一类小说的时候,读了第一节便想读第二节,甚至于从早晨读到夜晚,从夜晚读到天亮,要把它一口气读完了才觉得痛快。中国的教科书是以零碎文字做中心,没有这种力量。”[13]因而,他们提倡读整本书,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朱自清的《经典常谈》都是具体指导读整本书的。胡适在1920年3月24日演讲中“主张用‘看书’来代替‘讲读’”[14]。他于1923 年起草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国语纲要》里要求精读和略读“都用已经整理过的名著”[15]。叶圣陶先生说:“要养成读书习惯而不教他们读整本的书,那习惯怎么养得成”,“读惯了单篇短章,老是局促在小规模的范围之内,魄力就不大了”,“国文教材似乎该用整本的书,而不该用单篇短章,像以往和现在的办法。退一步说,也该把整本的书作主体,把单篇短章作辅佐”。[16]
另一方面,他们积极探索以单元组织单篇选文。自20世纪30年代起,语文教材以单元组织选文日益发展,单元组合形式渐趋多样化。不仅有以文体、作家、时代、题材为内容的单元组合,更有读写结合与集语文知识、范文和作业于一体的综合单元。在综合单元中,前者以孙俍工编的《国文教科书》(神州国光1932年出版)最为典型,后者以夏丏尊、叶绍钧编的《国文百八课》(开明1935年出版)最具特色。[17]单元组合的理念也有突破学科中心、文体中心的探索,叶圣陶《开明国语课本》(1932年)开宗明义:“本书内容以儿童生活为中心。取材从儿童周围开始,随着儿童生活的进展,逐渐拓张到广大的社会。与社会、自然、艺术等科企图作充分的联络,但本身仍然是文学的”,“本书每数课成一单元,数单元又互相照顾,适合儿童学习心理”。[18]以儿童为中心,适合儿童心理,跨学科,都是了不起的进步。
遗憾的是,学校、学科、课时等带来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方法影响太大,读整本书,以整本书为教材,并没能付诸实施,单元组织内容的优势在教学环节也未能得到很好的发挥,依然是单篇短章的分析教学主导课堂。1949年以后,语文教材虽大致沿用《国文百八课》的单元编写思路,可是学生学习语文的方式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叶圣陶先生在1941 年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论国文精读指导不只是逐句讲解》[19]。同时期的《论中学国文课程的改订》一文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要改进教学方法,必须废除现在通行的逐句讲解的办法。”[20]一直到1978年,叶圣陶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一个座谈会上,仍然在说这个问题:“从逐句讲解发展到讲主题思想,讲时代背景,讲段落大意,讲词法句法篇法,等等,大概有三十来年了。可是也可以说有一点没有变,就是离不了教师的讲。而且要求讲‘深’,讲‘透’,那才好。教师果真是只管‘讲’的吗?学生果真是只管‘听’的吗?一‘讲’一‘听’之间,语文教学就能收到效果吗?我怀疑好久了,得不到明确的答案。”[21]看来,这个问题一直没得到解决,这个问题也实在难以解决,因为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相当复杂,涉及学校教育体制等诸多问题,需要有居高临下的系统改革。
三、新时代的解决方案
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是一个划时代的重大决策,决定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的高度,从“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结构、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诸多方面,深化教育改革。这实际上是对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现代学校教育的全面反思与整体改革。国务院旋即启动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从课程理念、目标、内容、教学方法、评价、管理六个方面入手进行改革,这为语文课程教学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多年难以解决的难题,提供了百年未有的最佳历史机遇。
语文课程改革20多年来,教育部颁布了8个课程文件①。这8个课程文件,凝聚了全国语文教育工作者的智慧,根据国家课程改革的方向和总体思路,21世纪一代新人的培养要求,深刻反思总结了几千年来特别是近100年来语文课程教学的经验和教训,汲取了哲学、心理学、教育理论、学习科学、语言文字、文学文化、信息技术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融合创新,建设并且逐步完善了语文新课程。
语文新课程定位为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突出了语文课程的育人价值,超越了知识本位的局限,突出以人为本,以文化人。聚焦学生核心素养,构建素养型培养目标体系,改变了知识点、能力点线性排列的目标系统,促进人的语言、思维、审美、文化等方面素养的整体提升。设置语文学习任务群,构建了新的结构化内容体系。语文学习任务群改变了学科中心的课程结构,统筹学科逻辑、学习逻辑和生活逻辑,加强了课程组织的整合性,兼顾了课程组织的连续性、顺序性和整合性。[22]课程底层结构突破了以课时作为单一方式的局限,选择典型的学习情境、学习内容、学习方式组成系列学习任务,实现了泰勒所说的“课时”“课题”“单元”三种方式的有机整合[23]。提出学业质量要求,构建了发展性评价体系,坚持教、学、评一致,注重评价学生的学习表现和运用语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不是评价学生死记硬背得来的知识。
突出情境性、实践性和综合性,引领教学的变革,“力求改变教师大量讲解分析的教学模式”[24]。聚焦核心素养,基于学习任务群的教学,改变教师中心的教学,突出学生主动积极的学习,坚持以学习为主线,以生活为基础,以主题为引领,以任务为载体,综合运用识字与写字、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等多种方法,在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学习,在探究和创造中学习。特别是注重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加强单元整体教学设计,加强整本书阅读,加强跨学科学习和当代文化参与;注重多读多写,强调少做题多读书,强调自主阅读,自由写作,加强口语交流与沟通,加强跨媒介阅读与表达,加强信息时代新的语文实践能力的培养。
语文新课程在素质教育的大潮中,面向未来,乘势而为,继承、改革、建设、发展,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科学与人文多重文化冲突中,实现了融合与创新,为提高国民素质提供了科学的语文教育方案。这也是“吕叔湘之问”的新时代解决方案。在吕叔湘先生120 周年诞辰之际,我们献上这份方案,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