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表达
2024-01-17李继峰
□ 李继峰

孙大勇/图
1989 年高考,先报志愿,后考试。那年招生计划减少,第一志愿高了,第二志愿满了,调剂去了聊师,还好是中文系。没有录取到心仪的一、二志愿,起初心里有些失落。高三同班一女生,复课插班,平时成绩平平,听从班主任建议,提前批冲省内一普通院校外兼文。成绩下来,竟然进入全省文科百名以内,最后还是去了提前批志愿。想想这个同学,沮丧少了很多。
刚入学,也曾立志考研。一打听,学长中成功者微乎其微,1990 年研究生招生变为学校先推荐再考试,便心灰意冷,投身写作。从农村来的,本来就没见过世面,倒也没有太多失落。即便现在,真正考上清北的,也是凤毛麟角。写了篇记录军训文章,竞选写作课代表,题目《一枝一叶总关情》如今看来油腻老套,却被刘明老师看中,在班里亲自诵读,投票“屈居”第一,信心自此大增。
院报是学校影响力最大的平台,帮助很多同学第一次实现铅字梦。刚开始,到编辑部送稿,做贼一样,丢下就跑。慢慢发现王刚、宋宝和、马中祥、姚启明、王凤刚诸师位高权重人却好,便慢慢造次起来,心底敬重而亲近。王刚老师特幽默,有时确切说是搞笑。他的乒乓球自己说全校第二,没人敢称第一,屡屡挂靴,屡屡言而无信。幽默搞笑与高超球技咋能如此完美结合到一个人身上?至今纳闷不已。第一篇见诸校报的文字《歌唱祖国》是姚启明老师编发的,记忆尤为深刻,心底尤为感激。该文如今看来,感情依然真挚,水平实在汗颜,再次感谢老师包容。多年后,在济南四处打听,联系上同城姚老师,席间提及这事,举杯表达感激,他却说记不得了。虽然写得很苦,由于底子薄,回头看,当年文章题目、内容都很硬,直白歌颂居多,时代特色浓郁。纸媒体时代,学生宿舍区门口广告栏公布的各种征文、歌咏、体育比赛结果,便足以让很多同学一夜出名,校报更不用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知名写手。
当年,大学生被誉为天之骄子。考入大学,街坊四邻都觉得荣耀。现在看来,我们那代人,文字基础、知识结构、思想深度都存在天然缺陷,与现在的学生判若云泥。即便是系里的老师,组成和来源也非常复杂。有“文革”前名牌大学生,有工农兵大学生,也有刚留校的学长,博士学位的师资一个没有,硕士也就三五人。写作开始都是模仿。现在知道,学习写作之初,苦读名著见效并不明显,消化不了,三流的作品才好效仿。2021 年4 月,在省直机关工作23 年后,被组织安排到滨州学院工作。到校第二天,就找校报的同志借阅近几年的校报合订本。我觉得,校报是观察学校的绝佳窗口。
1990 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5 周年,中文系举办大型文艺演出,钟美兰老师任总指挥,88 级师兄巩洪波为学生会宣传部部长,安排我撰写脚本。花了整个暑假时间,几易其稿,演出效果大好。当年不会宣传自己,至今没几个知道脚本是我写的。虽算不上发表,自己特意留了打印本,悉心粘贴在笔记本上,留存至今。有这个经历,后来写一些长篇的文字,就不再怵头。
汉语言文学专业不是培养作家的,但文字写作能力是基本功,不然何以传道授业。在校期间,尝试过诗歌、小说、散文,甚至文学评论。因为缺乏敏锐的感知,诗歌写起来缺乏诗意;因为缺乏想象力,小说更像自传;因为缺乏理论工具,文艺评论就是写感慨。逐渐地,散文成了主要的写作形式。刘明老师当年说,散文像压缩饼干。这话曾像火炬一样照亮了我。如今,我觉得,写散文就是解剖自我、拷问灵魂。工作中,点灯熬油,写过无数言语铿锵、布局严谨、内容丰富的应用文,任务完成后也曾有一丝丝得意。时间久了,总觉得缺乏成就感,不如写散文信马由缰,形散而神不散,我笔见我心。
年轻时虚荣,发个豆腐块,也想听到同学、老乡或真或假地夸赞。如今偶尔有个冲动,想写篇文章,发给校报,让老师和留校的同学看看我现在的水平,有无长进,后又觉幼稚。2019 年,山东财经大学做校报编辑的同学段春娟看到我微信朋友圈里的一篇原创《异乡的月亮》,问我能不能在她的报纸上发一下,便一口答应。后来,收到样报,还收到20 元稿费。这个数额比当年《聊城师院报》多多了。
“塾远愁过市,家贫梦买书。”我买书是出了名的,大规模地买书、藏书,是在大学期间。聊城师范学院门口有个旧书摊,存在了多年。摊主是博平人,一对夫妻和三十多岁的儿子。虽是旧书,全部正版,是各地书库压仓底儿的书,牛皮纸捆扎的原装,价格极低。中华书局版一套12 册的《史记》,仅售15块钱。淘书好比早市,去晚了会一无所获。睁眼一看窗外有些亮光了,便一跃而起,半梦半醒地冲向旧书摊。多数情况下,我是以“写”养“买”,写文章发表挣了稿费,就去抱一堆旧书回来。大学期间,发表文章一二百篇,多数稿费变成了旧书。有一次连续几天没有买到中意的书,很是郁闷,便多了个心眼儿:直接去摊主家。周五下午三点,借了辆自行车,直奔二十公里以外的博平镇。聊城是黄河滩区,泥土像面粉一样细碎。一起风,对面不见人,只是当时还没有沙尘暴的说法。同学们中间有句话非常盛行:聊城一年一阵风,从春刮到冬。那天的风,刮得昏天黑地,且是顶风,赶到博平时,一抹脸上,半水半泥。摊主很热情,说我是第一个到家里买书的人,价格也便宜不少。在那趟买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第一卷的扉页上,我专门记下了这件事。泉城安家后好不容易有个书房,一面墙全部打成书橱,那一捆捆跟着我颠沛流离多年的书终于有了安身之处。一日午夜,灯下看书,“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这句诗一下震到了我。吾等庸常之辈,天资愚钝,追逐文字半生,能够表情达意已是奢望,做人虽也恭谦和善,谨慎敬业,何曾有此境界。让好友蒋乐志写成横幅,悬挂案头,懈怠慵懒时也算是个警醒。
回头来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几乎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个“文学梦”。多数人的文学梦萌芽于中学时代:有了一定阅读量,词汇积累相对丰富,生理发育逐步成熟,感情变得丰富细腻。在中学、大学,谁写得一手好文章,就会被称为才子,受人羡慕。改变命运的原始动力让我们对知识、对文学孜孜以求。文学也需要童子功,与体育、绘画、音乐等爱好相比,看起来写作的门槛很低,只需要一张纸一支笔,其堂奥却极深,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大学四年为1989 年至1993 年,那几年正好在大学里的人,是时代幸运儿:衣食供求基本满足,西方译著大量出版,学术研究走上正轨,社会风气日渐开明。说实在的,大学期间恣意涂抹那些文字也没有多好,破绽随处可见,可过了那么多年,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它们,它们已成为生命中最重要的印记。如今,网络传输的便捷、微信的普及,使得各类文本唾手可得,作家,早已失去了七彩的光环,成为普通职业,与荣耀全无关系。
文字是工具,现在看来,练习写作,就是一个学习表达的过程,是寻找适合的表达方式。能够比较熟练地舞文弄墨,算是学会了表达。前几年,到母校公干,带队领导说到学生食堂吃顿饭,体验一下生活。走到第三个窗口,打菜的师傅竟一下认出了离校二十多年的我,一大勺红烧肉瞬间倒进餐盘,接着还要再盛。二十多年没见,这勺肉,是母校对我最深情的表达。
篆刻作品欣赏
王 平/篆刻

为政清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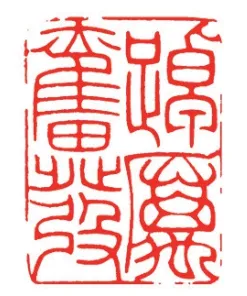
踔厉奋发

笃行不怠
